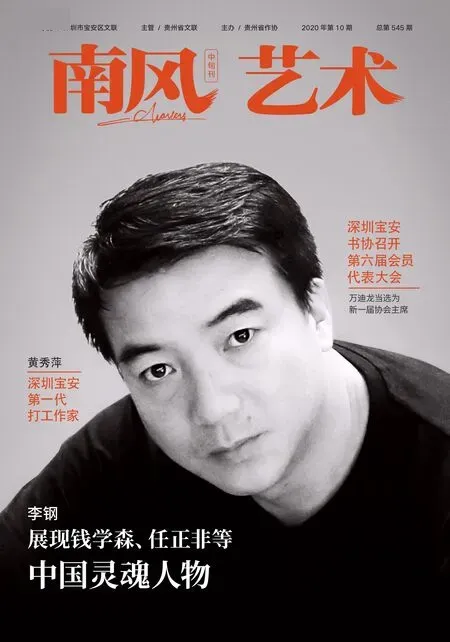“美術革命”與山水畫“中西融合”路徑的形成
文/王先岳
現代美術史上,“美術革命”無疑是一個標志性事件,盡管其在興起之時并沒有形成浩大聲勢,但事實上它成為中國畫從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演進的轉折點,其影響之深遠,幾乎波及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美術的發展。追根溯源,“美術革命”首先是從山水畫領域發端的,并主要形成了中西融合、汲古開今、寫生創新三種演進路徑與革新方式。
● “美術革命”與“中西融合”思潮的興起
作為一種繪畫創新方式,“中西融合”很早就出現在清代宮廷畫家郎世寧等人的繪畫創作中,但時人以“筆法全無,雖工亦匠”(鄒一桂)的評價將其打進“不入畫品”之列;而作為一種繪畫思潮,其思想淵源至遲可以追溯到近代社會改革家、思想家康有為。1917 年,康氏在《萬木草堂藏畫目》中提出“合中西而為畫學新紀元”的主張。繼之,1918 年1 月15 日出版的《新青年》(第6 卷第1 號)以通訊形式同時刊發呂澂、陳獨秀的同名文章——《美術革命》。針對以“四王”畫派為代表的文人山水畫入纘畫學正統所導致的陳陳相因的摹古風氣,陳獨秀主張:“畫家也必須用寫實主義,才能夠發揮自己的天才,畫自己的畫,不落古人的窠臼。”并提出了打倒“王派畫”的口號,認為“像這樣社會上盲目崇拜的偶像,若不打倒,實是輸入寫實主義,改良中國畫的最大障礙。”其所謂“輸入寫實主義”,其實正是“中西融合”思想的早期版本。

徐悲鴻 漓江春雨
“美術革命”的主張,引發了中國近現代美術史上關于中國畫革新問題的激烈論爭,并主要形成了革新派和國粹派兩大陣營,其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是否要汲取西洋畫的方法以及怎樣汲取的問題上。其中,徐悲鴻的觀點尤為引人矚目。1918 年5 月,徐悲鴻在《北京大學月刊》發表《中國畫改良之方法》,開宗明義地提出了改革中國畫的主張:“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絕者,繼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畫之可采入者,融之。”“畫之目的,曰‘惟妙惟肖’,妙屬于美,肖屬于藝。故作物必須憑實寫,乃能惟肖。待心手相應之時,或無須憑實寫,而下筆未嘗違背真實景象。”徐氏關于中國畫改良的守、繼、改、增、融五字法訣,與“惟妙惟肖”的繪畫目的論、“作物必須憑實寫”的方法論,將“美術革命”思潮從理想層面直接推進到技術途徑和操作方法的層面,基本形成了“中西融合”與“寫實主義”的繪畫思想,深刻地影響了此后漫長的中國畫革新之路。1947 年,他因北平藝專國畫組教授秦仲文、李智超、陳緣督罷教事件引發的風波而發表《新中國畫建立之步驟》,提出“素描為一切造型藝術之基礎”,但又認為:“建立新中國畫,既非改良,亦非中西合璧,僅直接師法造化而已。”此后,他雖然反復聲明“研究藝術,以素描為基礎”的主張,但他似乎已將早年的改良主義和“中西融合”論發展為“師法造化”論,而其實在教學和創作實踐上,他始終未改初衷。徐悲鴻以其在美術界的地位和影響,建構起“中西融合”與“寫實主義”的堅固堡壘,造就了現代中國畫發展的一代新人新風,直接影響了中國畫的改造革新。關于他的這一理念與做法,美術界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其余響不絕如縷,至今猶存。
● “中西融合”路徑與山水畫的革新實踐
在“美術革命”思潮的影響與推動下,其時的中國畫發展呈現出紛繁復雜的局面,而作為中國畫之大宗的山水畫,其演進線索盡管千頭萬緒,但主要形成了中西融合、汲古開今、寫生創新三種革新路徑,并在整體上呈現出兩方面特征:在文化觀念上,一些致力于“為人生”的寫生山水畫逐漸摒棄了文人山水畫逍遙適性、高蹈遠引的精神特質,尤其是嶺南畫派與西北寫生畫家的開拓實踐,以其關注現實的繪畫題材強化了山水畫的入世精神;在語言風格上,無論是主張融會中西,還是汲古開新,抑或是寫生創新,寫實造境逐漸成為山水畫演進的一種新趨向,這是“美術革命”思潮興起以降美術寫實主義整體性轉向的一個時代縮影。
就創作實踐論,其實早在“美術革命”以前,海派畫家吳慶云就嘗試與探索過“中西融合”的創作方式。吳氏尤擅潑墨煙雨之法,他參用西法和日本畫法,融于米家山水的水墨點染,渲染景物的陰陽相背,表現光影的晦明變幻,水暈墨章,煙嵐流蕩,一派天機。新文化運動后,“中西融合”逐漸成為繪畫主流,堅持這一繪畫路徑的畫家被稱為“革新派”。但其內部又存在寫實與表現兩種不同的取向選擇,其繪畫作品的風格特征也表現出較大的差異性。
以徐悲鴻為代表的一批中國畫家堅持以西畫的寫實方法“改良”中國畫,而徐悲鴻的創作主要在人物畫方面,他將素描作為一切造型藝術的基礎,為人物畫的現代轉化開辟了新的途徑和方法。他的少量水墨山水畫如《山林遠眺》《雞足山》《漓江春雨》《西天目山老殿》等,多運用焦點透視經營畫面結構,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傳統視覺觀念,其物象造型以寫實為理念,卻又匠心獨具地運之以書法性筆墨,透顯出現代寫實與傳統寫意相交融的趣味。徐悲鴻的藝術理念影響了一大批弟子,其中在山水畫創作上取得較大成就的是陶冷月。其創造的月景山水畫在當時別具一格,畫家大膽地吸收了西洋畫的明暗、光影和焦點透視手法,將傳統山水的丘壑營造與西洋風景的空間處理、光影畫法等融合為寫實造境的新型繪畫語言,營構出具有強烈真實感、現場感而又清幽遼夐的山水意境。
嶺南畫家提出“折衷中西,融會古今”口號,是將“中西融合”與寫實造境付諸山水畫革新實踐的典型代表。而究其實,嶺南派的“折衷中西”是中日美術的折衷,且其“折衷”實踐也早于“美術革命”思潮。而“日本美術在‘明治維新’之后經西方藝術的熏陶和日本傳統的結合已呈盎然新意”,可見嶺南畫家的“折衷中西”實是中、日、歐美術的交融與會通。嶺南畫家對日本美術的技法汲取,除了渲染一法,還吸納了在中國幾近匿跡、在日本卻風靡一時的水墨蒼勁的南宋院體山水畫風。而在中國本土,二高一陳還繼承了自居廉、居巢以來基于寫生而產生的生動性和寫實性。其中,高劍父的山水畫最具代表性。在繪畫技法上,他注重畫面的寫實感,著力渲染畫面背景,強調明暗、光感、透視、空間和氣候的表現,擅于營造迷蒙氤氳的畫面境界。值得一提的是,高氏晚年提倡新宋元畫和新文人畫,肯定了宋元畫形神兼備而典雅的傳統功夫,也肯定了文人畫強調個人風格和超俗筆墨的詩情畫意,明確提出要繼承和吸收文人畫寫意和宋元畫寫實的各自優點和特點,汲取并發揚前人寫實與寫意的表達能力,用來更好地抒發時代的情懷。這反映出高氏晚年對于傳統文人畫的回歸傾向,他未將“折衷中西”的主張貫徹到底,以及在語言形式上最終不自覺地走向一種非寫實主義,這與辛亥革命的悲劇性歷史命運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遠寺夕照圖 吳慶云 1903年 104cm×57.1cm 紙本水墨設色

傅抱石 觀瀑布
林風眠的藝術創作,則代表了借鑒西方現代美術而以表現為特色的“中西融合”路徑。林風眠從繪畫媒材、樣式、構圖、語言等各個方面對“中西融合”進行了前無古人的探索和嘗試。其彩墨山水作品,多取方形構圖,畫面較為強調水平線。在繪畫語言上,他將中國畫寫意和西洋現代繪畫富有表現意味的畫風進行了嫁接、融合與再創造。他的繪畫線條淡化了文人寫意畫的書寫性和金石意味的追求,而遠紹漢唐壁畫的線條傳統,獨具一種潤滑爽利的趣味;他大膽突出色彩運用,將中國畫水墨與西洋色彩進行了水乳交融的糅合,用墨彩捕捉大自然的神奇與靜謐,謳歌燦爛的自然生命。他的畫面意境孤高夐遠,格調沉郁,充滿了憂傷、蒼涼的詩意,而又隱含空靈、飄逸的內在神韻。這正是林風眠的成功之處,他在意境營造上將中西融合的學理層次推向了深邃的美學境界,這在當時幾乎是無人能及的。
類似林風眠追求個性表現的“中西融合”型畫家還有傅抱石、劉海粟等。傅抱石早年師法石濤野逸畫風,并廣泛涉獵歷代名家范寬、高克恭、王蒙、倪瓚、梅清、程邃等,后留學日本,既注意吸收西畫面向自然的寫實性,又受到橫山大觀、竹內棲鳳等人的影響,對日本畫水色暈染、朦朧濕潤的空氣感與氣氛烘托有所領悟和取法。抗戰期間,傅抱石寓居重慶金剛坡自創“抱石皴”,成為“師造化”家喻戶曉的藝壇佳話。他有感于巴山蜀水煙籠霧鎖、郁蔥秀潤的優美景致,以獨特的散鋒筆法突破傳統筆墨程式的束縛,用橫刷直掃、迅猛剛烈的運筆表現出大自然的動勢之美,創造出風雨飄搖、蒼茫雄奇的山水境界,表達了畫家不可遏止的磅礴激情。

林風眠 漁獲圖

劉海粟 天下奇觀
劉海粟的早期山水師法三石(沈石田、石濤、石溪),尤為服膺石濤,因為石濤的筆墨風格與他的豪放個性頗為契合。此外,他還將印象派后期大師塞尚、高更、梵高的情緒性筆觸與形式表現融入山水畫創作,以強烈的創造性面貌獨樹一幟。
● “中西融合”路徑與山水畫寫生方式的拓展
“中西融合”的繪畫路徑,不僅是落實于畫面的藝術創作方法,更是體現在寫生過程的一種藝術實踐行為。相應于“革新派”與“國粹派”的觀念分野,西式寫生和“師造化”無疑是兩種不同的寫生方式。傳統山水畫的“師造化”,是一個具有哲學意味的術語,有較濃的形而上色彩,其在認識論、方法論意義上都與西洋美術中的“寫生”有所區別。就當時情形言,雖然兩者都主要著眼于藝術語言的革新,并在一定意義和程度上并行不悖,但在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大背景下,兩者都不可能完全保持其純粹性,它們之間的技術融合,成為一種無可避免的趨勢。在材料工具的使用、觀察方法、視覺觀念、技巧運用等各個方面,兩者相互影響交融,從而對山水畫的技法語言、繪畫風格等產生決定性影響。這樣一來,自然生發出一種別樣的寫生方式——“中西融合”式寫生。
“中西融合”式寫生,一方面強調“對景”,注重選取具有強烈現場感的自然風景入畫,講求明暗光影的即時變幻,以焦點透視的方式組織畫面,注重景深和層次;一方面又一定程度地將“外師造化”與“中得心源”統一起來,從而將寫實造型與寫意筆墨調和成一體。正如高劍父所說:“要忠實寫生,取材于大自然,卻不是一時服從自然,是由心靈化合提煉而出,取舍美化,可謂自我的寫生……”,他的作品從真實的視覺經驗出發,注重呈現寫實性的視覺效果,但又經由心源的提煉與再造,并出之以神韻亹亹的寫意筆墨,達到了“中西融合”的新境界。
作為山水畫革新路徑的拓展,“中西融合”式寫生改變了中國畫家的思維方式、觀察方式和表現方式,使山水畫創作更加貼近現實生活,打破了明清依賴畫譜程式取象造境的藝術僵局,走出了陳陳相因的摹古泥淖,增強了山水畫家對于自然造化的感悟力和對于語言圖式的創造性,強化了山水畫的表現力,拓展了山水畫的表現空間,發展了相對停滯的山水畫技法語言,帶來了全新的視覺圖式革命,從而為山水畫的現代變革提供了全新的參照與方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