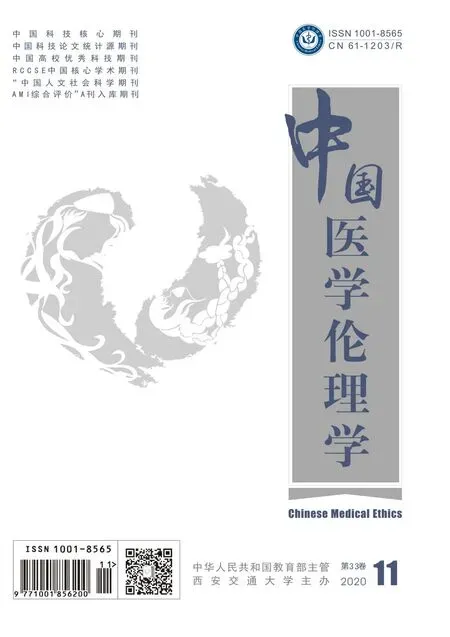醫學生醫患溝通能力實踐性課程培養體系構建*
孫連榮,王 沛
(1 上海師范大學天華學院,上海 201815,slr@163.com;2 華東師范大學教育學部,上海 200062)
醫學生是未來醫生的人才儲備,培養醫學生具備醫患溝通所必需的素質和技能是保證其后期臨床行醫實踐中踐行有效醫患溝通的必要基礎。遵循“以患者為本”的原則,世界醫學教育聯合會早在1999年組織制定的“全球醫學教育最低基本要求”(GMER)中就將溝通技能作為7項從醫基本技能之一。中國醫師協會也將“溝通能力”列為“人文醫學執業技能培訓”的核心學習內容[1]。由哈佛大學醫學院和斯坦福大學研究者聯合中國學者組成的“中國大陸醫患信任”研究團隊發表《重建醫患信任白皮書》中也進一步強調:要從根本上緩解中國當前危機頻發的醫患沖突,應將醫學生人文教育體系中醫患溝通技能的訓練列為重中之重[2]。可見,提高醫生執業過程中的溝通能力,對于避免醫患沖突發生,構建和諧醫患關系具有重要的意義。
1 我國醫學生醫患溝通能力培養實踐的現狀
整體而言,西方國家比較重視醫患溝通能力培養的研究與實踐。在英國和日本,醫學院校專設的“醫患溝通學”等人文社會科學類課程的學時數占到了醫學專業課總學時的1/8,美國和德國甚至高達1/4;其課程內容不僅涉及有效醫患溝通的界定以及如何建立良好醫患關系的方式,同時還包括如何在醫療過程中恰當運用法律知識等相關教學內容。在課程開發的同時,還陸續構建了醫生溝通能力考評體系,并取得了豐富的成效。其中,“四習慣”培養模型、醫患溝通技能評價量表(SEGUE)、利物浦醫生溝通能力評價量表(LCSAS)、標準化患者(SP)考核以及Roter溝通分析系統(RIAS)等都是檢測效力深受國際認可的醫患溝通能力考核體系[3-4]。
相對而言,國內有關醫患溝通能力的研究及醫學教育實踐起步較晚。檢索國內“醫患溝通能力”主題相關的論文發表情況發現,對醫患溝通問題的相關研究始于2001年前后、2008年開始大幅度增加并持續增溫:從前期7年間(2001—2007)論文發表總量50多篇到2008—2011年的200余篇,再到2011—2019年的500余篇。在研究主題和內容方面,國內大多是基于國外研究評述進行國內推進現狀調查,也有研究試圖提出可借鑒的醫患溝通能力培養策略。比如,有研究者針對國內50所醫學院的調查表明,僅有40%的醫學院校開設了溝通類的課程,個別醫學院校(如山東大學口腔醫學院、湘雅醫學院、南京醫科大學等)在課程設置中安排了醫患溝通能力相關的基礎課程,且絕大部分安排為選修課的形式;而其余60%未開設醫患溝通類課程的醫學院校, 一般只是在醫學基礎理論課程中以零散的方式涉及少量與溝通相關的概念性知識[5];另有研究調查了醫學生對于他們所接受醫患溝通能力培養的反饋后發現,當前國內醫患溝通的教學仍以理論指導居多,教學形式以講授為主,實踐性的訓練比重極低[6]。在理論研究方面,侯勝田等[7]提出6S醫患溝通模式,主張醫患溝通的實踐不僅需要向患者普及相關疾病知識和建立良好醫患關系,更強調將獲得患者的信任和提升醫療機構形象作為醫患溝通的核心目標。
縱觀國內針對醫學生醫患溝通能力的培養,目前總體呈現出理論研究逐步增多而教育實踐推進相對滯后的現狀。盡管已有部分相關的實踐探索,但仍處于起步階段,存在諸多亟待后續推進的方面。主要表現為:
第一, 對醫學生醫患溝通能力培養重要性的認識不足。文獻綜述國內醫學院校課程體系后發現,醫學生培養的人文社會科學課程學時在總學時中所占的比例不足8%,而醫患溝通的內容僅占人文教育內容中的極小部分[8]。在長期應試教育模式的慣性影響下,國內醫學高校目前的總體傾向仍是重專業知識教育、輕人文素質及實踐能力的培養;對于醫患溝通能力培養的重要性認識更多仍停留在醫學教育體系制定者的頂層設計中,而在醫學教育實踐中未能得到充分體現[9-10]。
第二,醫患溝通能力培養的課程設置缺乏邏輯體系。目前,國內大部分醫學院校的本科教育中沒有涉及關于“溝通能力培養”的統一規劃,也沒有對應的教學大綱和計劃;醫學生的溝通教育分散、零碎地分布在其他專業課程中,缺乏系統性。雖有部分醫學院校已開設醫學生醫患溝通能力的相關課程,但缺乏明確的培養目標,尤其是對與醫學生后期從業實踐需求對應的醫患溝通能力培養目標沒有明確的描述[11]。
第三,醫患溝通能力培養的形式偏理論、輕實踐。當前國內的醫患溝通課程仍以理論知識內容居多、講授式教學形式為主;醫學生醫患溝通技巧絕大部分是通過實習過程中帶教老師的言傳身教而獲得,而大多時候臨床帶教老師更加側重對學生臨床專業技能的指導,相對忽視醫學生的溝通交流技能;實習過程中也少見對醫患糾紛案例討論和以問題為導向等學習形式[12-13]。此類培養方式不足以保證醫學生具備處理臨床實際中復雜醫患關系的能力。
第四,醫患溝通能力的培養缺乏評價體系。國內現有嘗試推行醫學生醫患溝通能力培養的實踐以各醫學高等院校的教學模式各自為陣,缺乏科學的課程評價機制[14]。
為此,當前亟須以提升醫患溝通實踐能力訓練為抓手,構建系統的醫學生醫患溝通能力培養體系以及可操作的課程實施方案,并據此設計科學的課程實施效果評價體系。這對于實質性強化醫學生對醫患溝通能力重要性的認識以及系統化提升醫學生醫患溝通能力的培養效果具有重要意義。
2 醫學生醫患溝通能力培養課程體系的初步構建
2.1 課程體系構建的總體思路
針對以上當前國內醫學生醫患溝通能力培養體系所存在的局限,我們嘗試構建醫學生醫患溝通能力培養的實踐性課程體系。該課程體系旨在重點體現如下四個特點:
第一,明晰培養目標。該課程體系的培養目標主要聚焦于兩個方面:①注重對醫學生醫患溝通能力重要性在課程教學層面的落實和體現;②對應醫生從業實踐中對醫患溝通能力的需求,構建醫患溝通能力素質構成模型,并錨定醫患溝通能力的核心內源性素質。
第二,構建系統化的課程體系。結合醫患溝通能力素質構成模型,分階段、分模塊開展醫學生溝通能力的培養。具體內容包括:在醫學生低年級進行醫學基礎知識的學習階段,實施醫學生人文素質模塊教學內容,著重培養醫學生對患者的人文關懷能力;在醫學專業技能學習階段,實施醫患溝通基本技能模塊的課程,以實踐性教學法為主,著重加強對醫學生構建良性醫患關系技能的訓練;在醫學見習和實習階段,實施醫患溝通應激性技能模塊的課程,通過案例呈現及臨床實踐,增加醫學生接觸醫患溝通不良案例的機會,著重加強對醫學生處理醫患溝通沖突能力的訓練。
第三,增加實踐性教學的比重。在大比重增加實踐性學時的基礎上,推進實踐性培養模式,加大問題導向教學法(PBL)、標準化病人教學法(SP)、臨床實踐教學法(CAP)等的滲入。相對于講授方式而言,PBL、SP、CAP等教學方式利于在教學過程中再現真實的醫患溝通困難情境,比如設置溝通障礙、模擬患者焦慮、憤怒以及不合作等負性的情緒和行為,有助于更具操作性和針對性地訓練醫學生的醫患溝通技能。
第四,實施量化的課程評價。基于CIPP課程評價模式,分別選取課程體系實施前、中和后的時間點,采用標準化測量工具,對參與課程體系后醫學生醫患溝通能力各模塊技能變化的情況進行測試;同時,基于教育研究中常用的準實驗設計思路,比較課程體系實施前后數據的變化,以對課程體系的實施效果進行科學、客觀的評價。
2.2 課程體系框架和內容
對應以上總體思路,基于人際心理學以及醫患溝通領域的相關理論研究基礎,構建醫學生醫患溝通能力素質構成的理論模型(詳見圖1中“素質/能力培養目標”部分)。

圖1 醫學生醫患溝通實踐能力課程體系構建
該模型主要呈現的有效醫學生醫患溝通能力培養所需關注的三個部分——作為醫患溝通能力核心素質的共情能力訓練、基本溝通技能訓練以及應激性溝通技能訓練。該模型的主要觀點為:
①共情能力是提升醫學生醫患溝通能力的內源性核心因素。就其本質而言,醫患溝通作為社會互動過程中人際溝通的一種典型特例,有其實質的社會心理機制和基礎。人際溝通心理學的研究表明,人際互動中的共情能力,即個體在區分自我和他人的基礎上對他人情緒的體驗和理解能力是獲得有效溝通的基礎能力[15];共情能力不僅可以提高親社會行為的發生概率,還可以有效抑制攻擊行為[16]。信息溝通者的共情能力是溝通能力的核心素質[17],個體對他人情緒的體驗和理解能力,是保證溝通者各類溝通技巧和策略效用的發揮、促成有效溝通的前提和基礎[18];而就醫患溝通的性質來看,醫生是醫患互動過程中的主導者,也是影響溝通效果的主要溝通主體。因此,醫生的共情能力是保證醫患溝通有效的核心內源性因素。
②醫學生醫患溝通能力的訓練包括基本技能和應激技能兩個層級。研究表明,人際溝通主要涉及普適性的溝通技巧和人際沖突管理兩個部分[19]。結合醫生從業的日常實踐來看,醫學生醫患溝通能力的訓練內容也需對應基本溝通技能訓練和應激性溝通技能訓練兩個部分展開。其中,基本溝通技能是指非沖突情景下構建和諧醫患關系所需的溝通技能,包括如何有效了解患者信息、如何增進醫患信任、如何參與患者治療方案的制定、如何促進患者對治療方案的依存性、如何告知患者不好的消息以及如何疏解患者的消極情緒等諸多方面所需的溝通技巧;應激性溝通技能主要是指建設性解決醫患糾紛或沖突事件所需的溝通策略,包括與患者談判的技巧、突發性事故處理、暴力沖突降級等所需的溝通技能[20-22]。
③醫學生醫患溝通能力的培養,需要考慮將素質技能與現有課程體系有機結合,按層級進行遞進式推進。醫患溝通能力是醫生從業過程中其個人能力結構中人文素質和專業技能所兼需的部分。因此,醫學生醫患溝通能力的培養需要與現有醫學院校常規的課程設置體系進行有機結合,以保證醫患溝通能力培養的操作可行性和培養效果。目前,國內醫學院校本科層次人次的培養大多以“通識素質教育+專業教育+臨床實習”的體系按年級推進[23]。醫患溝通能力的培養可對應這一體系,按年級逐層、遞進式開展共情能力訓練、基本技能訓練和應激技能訓練等分模塊的課程設置。
3 醫學生醫患溝通能力培養的課程實施方案
基于以上課程體系構建的思路,借鑒國外醫學生醫患溝通培養的POM(Practice of Medicine)框架[24],結合國內醫學實踐中對醫生“軟技能”需求以及各類醫學院校學生各學年的能力培養目標,構建“三合一+分階段”醫患溝通實踐能力培養的課程體系(見圖1中“教學技術/形式”及“課程設置計劃”部分)。該課程體系旨在以“共情”能力的訓練為核心切入點,在向醫學生普及人際溝通心理學相關知識的基礎上,將對其醫患溝通共情能力、醫患溝通基本技能及醫患溝通應激性技能的訓練合三為一,從下到上以“金字塔”結構系統進行逐級遞進式溝通技能指標分解,并編寫對應教學方案落實到課程實踐中。在其中,“金字塔”的最低一層基于人際溝通心理學相關概念結合醫患溝通技能培訓目標形成“醫患溝通基礎知識”模塊,內容涉及面向醫學生介紹人際溝通心理學相關知識,并結合醫患關系實質明晰醫患“共情”的必要性。這一部分的設置目的主要有兩個:一是強化醫學生重視醫患共情的意識;二是為后續實踐技能訓練提供必要的理論框架背景。隨后,在此基礎上逐級設置實踐技能訓練體系:首先是“共情能力訓練”,內容涉及普適、通用的共情能力,即日常人際溝通過程中的共情關注、共情表達、情感換位以及避免共情疲勞技能訓練;其次為“醫患溝通一般技能訓練”,內容主要涉及將共情通用技能融入醫患互動非沖突、非緊急情境下的參與性溝通、影響性溝通以及患者情緒疏導等技能的訓練;最后為“醫患溝通應激性技能訓練”,內容涉及將共情通用技能運用于醫患沖突、糾紛、疾病特殊信息告知等突發應激情境處理技能的訓練。總體上,上述“三合一”醫患溝通技能訓練體系中所貫穿的思路是從日常人際溝通中普遍的共情能力逐級聚焦到醫患互動特殊情境中的共情技能,模型中的前一層級和下一層級互為基礎準備和推進、延伸。
對照以上“三合一”技能指標設計,課程方案對應體現為“分階段”實施,即作為醫學類專業學生培養方案中的學科基礎課程類別,在學生培養年制的第一至第三學年當中,結合采用巴林特小組、PBL(案例教學法)、SP(標準化病人訓練)及CAP(臨床實踐訓練技術)等教學技術和方法,按序分別設置相應課時當量的課程來體現對醫學生的醫患溝通基礎知識普及,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共情能力、醫患溝通基本技能以及醫患溝通應激性技能的實踐訓練。具體方案為:
在培養年制的第一學年中,開設共32學時的醫患共情能力培養的課程。共情能力訓練模塊的教學形式主要依托巴林特小組訓練技術,該技術針對人際溝通過程中共情能力的訓練效力已被國際上眾多實證研究及實踐所證實[25]。這個階段主要對應上述“三合一”體系中普適、通用共情能力部分;
在培養年制的第二學年中,開設共32學時的醫患溝通基本技能訓練模塊課程。對應上述“三合一”體系中將共情技能融入醫患互動非沖突、非緊急情境下參與性溝通、影響性溝通以及患者情緒疏導等部分,該模塊的教學形式主要綜合采用問題導向教學法(PBL)[26]和標準化病人教學法(SP)[27],著重進行醫學生與患者建立良性人際關系、增進與患者的相互信任、促進患者對治療計劃的配合以及幫助患者調節不良情緒等方面的理論素養及技能技巧訓練。
在培養年制的第三學年,結合學生開始參與各科室臨床實踐的實際情況,開設共64學時的醫患溝通應激性技能訓練模塊課程。對應上述“三合一”體系中將共情通用技能運用于醫患沖突、糾紛、疾病特殊信息告知、突發應激情境處理等部分,該模塊的教學形式以臨床實踐教學法(CAP)[28]為主,輔助于標準化病人教學法,著重培養醫學生應對醫療突發事件時的醫患互動及溝通技能,包括告知患者壞消息的技巧、應對患者溫怒或投訴的技巧、沖突出現時的談判技巧、相應法律法規解讀、醫生及患者沖突降級及應激情緒釋解等的相關素養及技能技巧訓練。
實踐性課程擬實施計劃詳見表1。

表1 醫學生醫患溝通能力訓練課程體系實施計劃
4 醫學生醫患溝通能力培養的課程評價
相對于國外醫學生醫患溝通能力培養的推進實踐而言,國內缺乏科學的課程評價機制,且鮮見于針對相應實踐方案效力的檢測報告,導致實踐效果無法確定、實踐方案缺乏改進依據。對此,結合課程方案的推行,我們也同步構建對該實踐性課程效果的科學評價體系。具體地,依托于美國學者斯塔弗爾比姆提出的CIPP四步評價模式[29],以對培訓實踐方案的“促進發展”為宗旨,對本研究中課程體系從理論構建到實施過程,再到訓練效果進行逐步檢驗。課程評價的實施過程如下:
首先,進行“背景評價”。背景評價即要明確課程構架邏輯的合理性以及課程相對于學習對象需求的必要性。我們按專家評價法的標準和流程對此部分進行評價設計:通過邀請從事醫學、心理學及社會學相關研究及教學實踐領域的專家組成評審組,進行多輪次的評審—修正循環,對本課程體系理論構架的合理性及其與現實需要的擬合程度進行評價論證。
其次,進行“輸入評價”。輸入評價的主要內容是對課程計劃方案進行評定。對此,通過組建包含心理學專業主講教師、醫學專業帶教老師、課程教學督導專家在內的教學團隊進行課程計劃的集體備課,并行采用分組設計、微格試教、擇優遴選的流程確保教學方案的有效性;與此同時,開展教學研討析出醫學生醫患溝通技能培訓類課程的核心要素及影響變量。
再次,進行“過程評價”,即對課程實施的科學性進行評價。“過程評價”是課程體系評價的關鍵。針對于此,通過運用高信效度的測量工具客觀而量化地檢測課程實施前后醫學生的共情能力、醫患溝通能力的認知和態度等醫患溝通技能指標發生良性變化的情況,對醫學生醫患溝通能力的提升進行動態監測。擬定流程為,以“醫學生醫患溝通能力訓練”(包括共情能力訓練、基本溝通技能訓練及應激性溝通技能訓練在內)為整體單元,在第一學年所有的訓練項目切入之前和第三學年所有的訓練項目完成之后就醫學生共情能力、醫患溝通能力以及醫患溝通認知及態度等進行總體前測和后測,并對兩者做一對比以整體驗證本研究構建的醫學生醫患溝通技能課程群體系的訓練效應;同時,以各學年中特定一項針對性能力目標訓練為小單元,在訓練環節切入前后就醫學生相應能力進行前后測并對比驗證各類教學技術/形式對特定溝通技能達成的訓練效應。基于“共情能力是醫學生醫患溝通能力的核心素質”的理論基點驗證,我們還在每一學年的小單元訓練技術完成后進行醫學生共情能力的后測,以檢測各類訓練技術是否具有共情能力提升的效應。
最后,進行“效果評價”,即收集與培訓結果有關的各類課程指標,并與課程開設目標及對教學對象需求滿足的程度及教學對象相關能力改變的程度相結合進行課程價值評價。針對于此,我們綜合考慮將評價維度和評價主體相結合,在“過程評價”與“結果評價”中均多時間點綜合提取醫學生在醫患溝通技能培訓課程中、醫患互動臨床實踐中以及模擬醫患沖突情境比賽等各類實踐形式中醫患溝通技能表現,作為本課程培訓實效的檢驗指標。
為了確保課程評價的客觀和科學,以上過程中遴選運用國際通用、權威的教學方法及測量工具(見表2)。同時,在培訓對象層面,擬基于上海及長三角地區中醫類院校醫學生、軍事類院校醫學生以及康復類院校醫學生作為對象開展并行實踐,旨在以課程方案效力驗證的結果為依據,提煉對后期參與不同臨床實踐的醫學生醫患溝通能力中的一般(G)因素和特殊(S)因素;同時,為此類課程體系在其他高校醫學及健康類專業學生溝通能力培養中的推廣提供實踐參考。

表2 課程實施及評價工具

續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