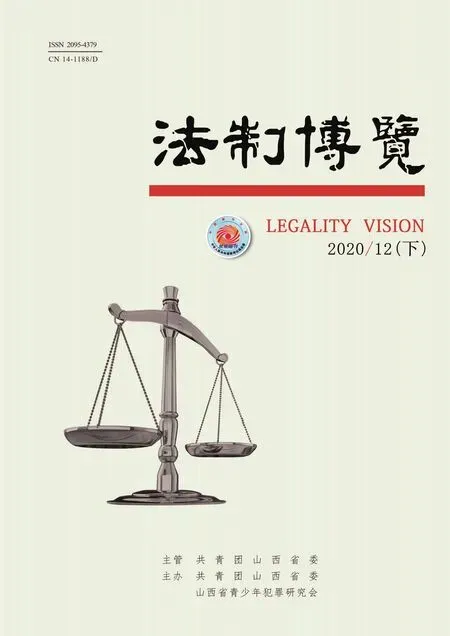無公司決議對外擔保成立要件
王昊艷
上海市普陀區人民法院,上海 200333
2019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發布《九民會議紀要》后,高院對于《公司法》第十六條規定的理解明確認為債權人對于公司對外擔保負有審查股東會或董事會決議的必要,除了規范公司擔保內部決策程序之外,還兼有規制公司擔保能力的性質[1]。之前,有觀點認為此條僅是公司內部效力問題,無須外部審查,司法實踐中大量案件按照前述觀點判決造成損害中小股東和公司的利益問題突出。現在,此條賦權性與強制性相結合的條款效力被充分肯定[2]。同時,《九民會議紀要》考慮到我國公司經營多有不規范,為此又規定了四種無須機關決議的例外情況。故而又有新的問題擺在面前,在具體到各個案件中是否可以適用、如何適用例外情況?本文想通過一個生效判例就公司對外擔保能否成立進行分析。
一、案件事實及法院認定
A公司、B公司、C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為張某。A公司的股東為B公司占股20%和C公司占股80%。C公司的股東為B公司占股75%,其余為兩名自然人占股共計25%。B公司的股東為張某占股90%,另有10%由另一名自然人占股。2017年之前,A公司向云公司采購鋁錠并支付貨款。后轉由B公司向云公司采購鋁錠,A公司不再向其采購,A公司、B公司與云公司為此簽訂了一份《擔保合同》,約定由A公司為B公司向云公司采購的鋁錠所發生的全部貨款提供擔保,各公司加蓋公章,張某亦簽字。之后,B公司拖欠云公司貨款1000萬元,并向云公司出具一份《情況說明》,說明B公司采購的鋁錠全部運往A公司,并且用于A公司的生產。B公司因經營不善無力支付貨款,故云公司起訴B公司要求支付貨款1000萬元,并要求A公司承擔擔保責任。法院受理后,B公司到庭表示認可云公司的訴訟請求。在該案審理過程中,A公司被裁定受理破產,A公司的管理人到庭則辯稱由于云公司未能提供A公司為《擔保合同》而出具的股東(大)會的書面決議,因此A公司不應承擔擔保責任。云公司為此提供4份生效判決,該4份判決均是B公司為A公司提供擔保,并且法院判決B公司應承擔擔保責任;云公司又提供一份類似《擔保合同》,A公司為B公司向其他公司采購貨物的貨款進行了同樣的擔保,故云公司認為A公司與B公司有商業互保的行為,該種情形下無須股東會決議。C公司亦表示當時知曉A公司為B公司擔保之事,且公司經營過程中沒有召開股東會的習慣。
法院認定:首先,從A公司的經營習慣中看出其對外擔保不經公司決議就做出對外擔保;其次,A公司與B公司存在互相擔保的情形;最后,買賣合同關系雖然發生在B公司與云公司之間,但貨物均是運往A公司并且用于A公司的生產經營。綜上,確認A公司需對B公司的擔保承擔連帶擔保責任。
二、案例分析
上述案例中,A公司雖然沒有出具公司對外擔保的決議,但仍需承擔相應的擔保責任,是因為其符合《九民會議紀要》中無須機關決議例外情況中的“公司與主債務人之間存在相互擔保等商業合作關系”。一般來說,兩公司之間有相互擔保的情形,說明在雙方的經營往來中有密切合作關系,該種互相擔保的行為既是為了經營需要,又使得兩家公司中的各中小股東利益得到一定保證,故該行為不存在損害公司利益的情形。在我國現行法律體系下,若這種情形的擔保被認定無效,顯然失之偏頗,就會造成案例中A公司在明知的情形下逃脫法律責任,給云公司造成損失,也造成B公司承擔之前擔保責任的不公平,有違誠實信用原則。上述案例中,若云公司未能發現生效判決或者其他類似擔保合同,其在舉證商業互保關系時就存在一定困難。若是上市公司尚且可以通過各年度報告查看是否有商業互保行為,但是非上市公司年報不公開,可能也未經審計,在擔保的公司否認擔保有效的情況下,原告存在客觀的舉證困難。既然《九民會議紀要》已經明確表態審查公司決議的原則,筆者提醒各債權人注意應當要求擔保方出示相應的公司決議后再行簽訂擔保協議,以規避可能出現的法律風險。
在該案審理過程中,也有觀點認為張某通過B公司、C公司實際控制A公司,并且間接持有A公司三分之二以上股份,張某在《擔保合同》的簽字符合無須機關決議中“擔保合同系由單獨或者共同持有公司三分之二以上有表決權的股東簽字同意”的例外情形。另有觀點認定,雖然張某間接持有三分之二股權但其表決權應當被排除,且對該間接計算股權的方式不予認可。筆者認為,在各國法律中公司對外擔保有限制或禁止兩種做法。中國法律對于公司對外擔保并未明確禁止,可以從《公司法》第十六條看出對于對外擔保的認可,但該條也從公司治理結構的角度對公司擔保進行了規范,將立法重心放在擔保決策權的程序控制上[3]。公司除了為他人擔保為主營業務的擔保公司外(該類公司不在公司法調整范疇內),其對外擔保的目的與公司的真實意思表示應當具有一致性。綜觀整個《公司法》,只有公司的重大決策如增減資、變更公司形式等需要股東所持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表決通過,其余的一般事項為二分之一表決通過即可。同時,《公司法》第16條規定“公司為公司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提供擔保的,必須經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決議。前款規定的股東或者受前款規定的實際控制人支配的股東,不得參加前款規定事項的表決。該項表決由出席會議的其他股東所持表決權的過半數通過”。綜上,筆者認為,公司為股東或實際控制人提供對外擔保時,應向債權人提供在排除有重大利益關系股東外,其他股東有過半數表決權同意的決議。在非前述情形下公司提供的對外擔保,應向債權人提供超過三分之二股東表決通過的決議。本案中,若是一般情況下,應排除B公司后由C公司蓋章即可,但由于C公司有三分之二以上股權的股東仍舊為B公司,筆者認為還應排除B公司在C公司的表決權后,由兩位自然人過半數有表決權的簽字。但值得思考的是,從該例外情形的表達來看沒有考慮決議應當有的程序問題,這在我國法律實務中決議瑕疵的處理上有重權利輕程序的問題[4]。筆者想提醒相關擔保權益人有權且有義務要求公司擔保人出示符合法律規定的相應決議,該審查行為的履行應構成擔保權益取得民事上善意行為人的必要條件。
至于《九民會議紀要》中無須機關決議的例外情形的第四種即“公司為其直接或者間接控制的公司開展經營活動向債權人提供擔保”,在該案例中,C公司若是為A公司做擔保,亦可以用此條進行論述,但本案中情況恰好相反,所以無法適用該條。
三、延伸討論及思考
值得探討的是,在公司沒有決議的情況下,若公司的擔保是為其自身利益如公司非負責人或非法定代表人為公司經營借款并提供公司作為擔保的(之所以排除負責人或法定代表人是因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23條的規定法定代表人或負責人借款用于公司經營的,公司可以被認定為共同責任),此種情況應從公司的真實意思出發判斷擔保的有效性,筆者認為該擔保應被認定有效,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十六條的立法原意,亦不會過分加重債權人的舉證責任。
《九民會議紀要》公布之后,已經對公司對外擔保有了更為明確的審理思路,因此也會對債權人、公司在對外擔保時要求更加謹慎。公司法出臺的目的本就是規范公司的組織和行為,且保護公司、股東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筆者能感受到時下司法界推進我國公司法的立法規范及公司自身的經營規范問題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