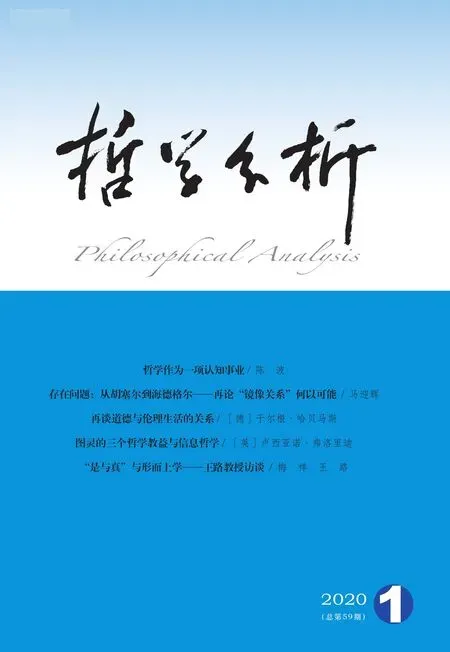人類本質(zhì)與自主
——哈貝馬斯對自由優(yōu)生學的批判①
[德]丹尼爾·C.亨利希/文
計海慶/譯
一、導 言
隨著生物工程和醫(yī)藥技術的發(fā)展,相關的倫理邊界問題也在不斷地增加。這方面的一個例子就是胚胎植入前基因診斷技術(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以下簡稱為PGD),該技術可以對試管內(nèi)受精的人類胚胎進行基因檢測。在德國,1990年頒布的《胚胎保護法案》 (以下簡稱為ESchG)對人類胚胎相關的法律問題作了規(guī)制。但鑒于1990年時還沒有PGD的臨床應用,因此ESchG中并沒有針對PGD的條款。①艾倫·漢迪薩德介紹了1990年PGD的首次成功臨床應用。參見Alan Handyside, “Pregnancies from Biopsied Human Preimplantation Embryos Sexed by Y-Specific DNA Amplification”, Nature, Vol. 344, 1990,pp. 689—796。由此,法庭便不得不自行決定在何種程度上PGD可適用ESchG的一般性規(guī)則。2010年6月,德國聯(lián)邦高等法院的決定認為,PGD在原則上并不與ESchG的規(guī)定相抵觸,但該技術只能被用來發(fā)現(xiàn)嚴重的基因缺陷;基于如性別、膚色等具體的特征對胚胎進行篩選,則不被允 許。
相比之下,在美國就缺乏這方面的監(jiān)管限制。因而,非醫(yī)療目的的篩選標準并沒有被禁止,例如性別。在同樣背景下,英國生殖生物學家艾倫·漢迪薩德(Alan Handyside)提出:父母應該自己來決定孩子的特征,尤其是那些具體的特征,例如智商;但是用直接的基因干預的方式來改變智商過于復雜且難以有效控制(假設將來同樣如此)。②Alan Handyside, “Let Parents Decide”, Nature, Vol. 464, 2010, pp. 978—979.
對于這樣一種自由主義觀念③布坎南等人把這類觀念稱為“個人服務模式”,參見Allen Buchanan, From Chance to Choice, Genetics and Jus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2ff。的批評意見認為,這類技術跨越了人類本質(zhì)的邊界,因為它以一種令人反感的方式對后者進行了篡改。這種批評隱含了一個問題,即“人類本質(zhì)”這個概念是否確實具有為生物技術設定倫理邊界的能力。此外,這個概念也尤其質(zhì)疑了那些認為在自然和道德之間存在明確區(qū)分的倫理學探討。這方面,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的觀點具有鮮明的代表性并引起了大量關注,可參見他在2001年發(fā)表的《人類本質(zhì)的未來》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一文(該文的德語版還有一個副標題:“我們正在邁向自由優(yōu)生學 嗎”)。
二、基因工程與異化決定
在上述文章中,哈貝馬斯提出的問題是:后形而上學思想能為基因干預的倫理學做些什么?他預言道:“一開始,普通民眾、政治家和議會將傾向于認為,如果這樣一種PGD技術被限定用來診斷為數(shù)不多的幾種明確的且嚴重的遺傳性疾病,那么這在道德上和法律上是可以被允許的。”④Jürgen Habermas,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 Oxford: Blackwell, 2003, p.18.這與2010年6月德國聯(lián)邦高等法院作出的決定是一致的。哈貝馬斯還提出,跨出這步后,接下來那些為了預防基因疾病的基因干預技術也將合法化,這便踏進了一塊處于消極優(yōu)生學和積極優(yōu)生學之間的灰色地帶。哈貝馬斯指出,我們所面臨的是一種兩難的挑戰(zhàn),在優(yōu)生領域中,迫切需要一道明確的邊 界:
在那些邊界變化不定的情境中,我們應該做的就是去劃出并捍衛(wèi)一條清晰的分界線。①Jürgen Habermas,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 p.19.
由此,哈貝馬斯的《人類本質(zhì)的未來》便可理解成一次嘗試,即試圖為基因干預技術劃出一道倫理邊界,這也是后形而上學能為生命倫理學去做的。本文認為,哈貝馬斯達到了這一目標,卻偏離了其一貫堅持的義務論倫理學的路 徑。
首先,有必要指出的關鍵是,哈貝馬斯把基因工程(PGD)的倫理問題與人類胚胎的道德地位問題區(qū)分開進行討論。理由有二:一方面,對于道德,哈貝馬斯堅持的是主體間性的和面向語言的立場,這意味著人的尊嚴不能被理解為是任何特殊實體的內(nèi)在屬性;另一方面,就像其一貫表明的那樣,哈貝馬斯相信,對生命倫理問題的回答必須在世界觀上是中立的,即擺脫了任何形而上的假設。但對胚胎道德地位的探討無法滿足這一中立性的要求,于是他選擇了一條不同的路 徑。
哈貝馬斯的核心觀點認為,通過基因評估的方式對胚胎進行選擇,或者對胚胎進行基因修改意味著對人的一種新的控制形式,它破壞了人的自主,損害了其作為道德能動者來行動的能力。哈貝馬斯稱之為“反異化決定(alien determination)的論點”②Ibid., p.86;此外,哈貝馬斯也曾用過“異化的共同作者身份(alien co-authorship)”來表達同樣的意思。。
對哈貝馬斯來說,在整體上修改基因?qū)е赂淖儭叭祟悺蔽锓N的倫理自我理解的風險。因此,他主張“將人類本質(zhì)道德化”,這可視為對現(xiàn)在的人類倫理自我理解的承諾。但就像哈貝馬斯所提出的,“從整體上對道德作出的評價,其本身并不是一個道德判斷”③Jürgen Habermas,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 p.73.,因而,對上述承諾給出任何道德上的論證是不可能的。據(jù)此,哈貝馬斯提出了一個古老的非義務論問題“為什么(人)應是道德的?”但是,就像我將要論證的,他沒有回答這個問 題。
三、基因工程與人類本質(zhì)的物化
除了一篇1958年的百科全書詞條外,在哈貝馬斯的著作中很難發(fā)現(xiàn)明確地對“人類本質(zhì)”或人類學進行論述的文字。④關于哈貝馬斯早期著作中關于人類學地位的論述引自霍耐特,參見Axel Honneth, “Habermas’Anthropology of Knowledge: The Theory of Knowledge-Constitutive Interests”, in The Critique of Power,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1, pp. 203—239。即便在他的《現(xiàn)代性的哲學敘事》中,哈貝馬斯只是在不顯眼的地方提到了阿諾德·蓋倫(Arnold Gehlen)和赫爾穆特·普萊斯納(Helmut Plessner),但沒有用到人類學這個詞。盡管從一封寫于1972年的信中,似乎可以看出普萊斯納的著作對他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但他仍堅持認為人和(其他)動物之間最重要的區(qū)別在于語言。因而,哈貝馬斯把普萊斯納的“去中心的位置性(excentric positionality)”這個概念理解成語言結(jié)構(gòu)的表達,而不是相反。哈貝馬斯對人類學的這種懷疑,針對的是其中所包含的任何一種本體論的態(tài)度和具體的人類學的結(jié)論。這導致的問題是,30年之后哈貝馬斯自己是否能應對自己提出的這個批評。 《人類本質(zhì)的未來》一文中的“人類本質(zhì)”是否也是一個本體論概念 呢?
在那篇文章中,哈貝馬斯并未對人類本質(zhì)給出任何明確的定義,這令人奇怪。文中的“人類”給人的初步印象就是:人是(自然)出生的,例如沒有經(jīng)過基因修改。這里的“自然”或“自然的”意味著帶有偶然性的“生長”。哈貝馬斯將“生長”與帶有意圖的“制作”進行了區(qū)分。考慮到當今生物技術引發(fā)的挑戰(zhàn),這一自然的、偶然的人類出生,對于每個人類個體而言具有的是一種生存論的和規(guī)范性的意義——因此對其進行操控將導致嚴重的倫理后 果。
盡管這是一種十分普通的偶然性,但就我們對其所能的理解而言,它已被證明是人有能力成為自己、以及人際關系中根本性的相互平等的必備條件。①Jürgen Habermas,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 p.13.
由此,對人類個體的“自然”屬性進行基因修改,改變的是這個人的自我理解以及他或她與社會環(huán)境的關系。之所以如此,源于一個事實,即該個體的“自然”屬性成了一個外在主體的意愿的表達。哈貝馬斯稱之為“一種特別的家長專制(paternalism)”②Ibid., p.64.,以此來強調(diào)基因工程從根本上不同于其他形式的越俎代庖,因為它改變的是人的自然稟賦。如果考慮到哈貝馬斯一貫所持的乃是非形而上學立場,這個觀點便成了問題的關鍵所在。布坎南(Allen Buchanan)在其著作《從偶然到選擇》中指出,如果不訴諸形而上學的資源而把基因修改定義為單一決定因素,這是不可能的。③Allen Buchanan, From Chance to Choice, Genetics and Jus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另 可 參 見Bernard G. Prusak, “Rethinking ‘Liberal Eugenics’”, Hastings Center Report, 6:31—42, 2005,p. 32ff。
(哈貝馬斯的)觀點似乎是想說,基因干預導致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個體的產(chǎn)生,而環(huán)境干預只能對這個人稍作改變。這類形而上學的隱喻是誤導性的。基因型和表現(xiàn)型之間的關系,不能還原為任何傳統(tǒng)的形而上的關系,例如質(zhì)料與形式、物質(zhì)與屬性、本質(zhì)與偶然性。①Allen Buchanan, From Chance to Choice, Genetics and Justice, p.160.但是,哈貝馬斯明確拒絕他的論述具有本體論或形而上學的維度,他認為基因作用和其他形式的作用之間的區(qū)別植根于“不同行動方式的邏輯”,后者在生活世界中是確定有效的。這與我們區(qū)分無機和有機的直覺能力一樣,依賴于“和世界打交道的具體方式”②Jürgen Habermas,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 p.44.,并與后者緊緊交織在一起。通過援引亞里士多德,哈貝馬斯在行動者的技術態(tài)度——即“從事生產(chǎn)的人的態(tài)度”(同前引),與實踐態(tài)度——即“在互動交流中理解他人的態(tài)度”③Ibid.之間作了區(qū) 分。
值得指出的是,在接下來的論證中,哈貝馬斯對所有形式的實踐態(tài)度作了比較。“述行的態(tài)度(performative attitude)指的是主體希望(通過語言交流)理解他人……,農(nóng)民的實踐是馴化牲畜和耕作土地,醫(yī)生的實踐是診斷并治愈疾病,育種者的實踐是選擇改善種群的遺傳特征”④Ibid., p.45.,這些實踐的共同特征都是對自然有所尊重。通過這個論證,哈貝馬斯強調(diào)了一種特殊形式的人類實踐⑤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同時把它(即述行的態(tài)度)與一種特殊的對待自然的態(tài)度作了對比。如果不這么處理的話,就不能把上述對自然的修改和干預的行為(例如治療)與技術的態(tài)度區(qū)分開 來。
類似栽種、治療和培育等的典型的實踐活動,都顯示了對自然中自我調(diào)節(jié)的內(nèi)在力量的尊重。如果他們不想失敗,那么就要尊重這些力量。⑥Jürgen Habermas,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 p.45.
作為一種特殊形式的技術態(tài)度,基因工程并不遵守任何自然的力量,它混同了生長和制 造。
通過隨機選擇而運作的物種進化,現(xiàn)在卻納入了人類不得不負責的基因工程干預的范疇;于是,哪些是被制造出來的、哪些又是自然而然產(chǎn)生的之間的差別被抹平了,但這些差別在生活世界中仍保有其劃分邊界的力量。⑦Ibid., p.46.
依據(jù)這一論點,基因干預混淆了兩種不同的人類行動——基于技術態(tài)度的和基于實踐態(tài)度的,后者正是構(gòu)成人類物種成員的自我理解的關 鍵。
這一基于行動理論的論證,也可以在另一處得到印證,即哈貝馬斯反對把社會化和基因工程二者進行等價。在其文章的第四章中,他拒絕了那種認為社會對個人的影響和基因干預施加的影響二者可以等量齊觀的觀點。在他看來,社會化是一種(可能帶有偏見的)交往,但“處于其中的成人仍有機會作出回應,并逆向操作性地擺脫這種關系”①Jürgen Habermas,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 p.62.。相比之下,對未來的個體進行基因操作意味的是一種“工匠或修補匠式的”使之物化的態(tài)度。②Ibid.
哈貝馬斯的論證,讓人回想起了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的《啟蒙的辯證法》,該書提出對于外部自然的對象化會帶來殃及人類本質(zhì)(人類的內(nèi)在心靈)的后果。③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W.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Philosophical Fragments,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就哈貝馬斯自身而言,相關的概念背景可以追溯到其早期著作中關于行動理論的論述,尤其是《交往行動理論》一書④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1, Cambridge: Polity, 2006, p. 84ff.。簡言之,哈貝馬斯對真正形式的人類實踐(交往活動)和次等形式的活動——如工具化的活動(技術的態(tài)度)——作了對比。并設定交往活動是人類互動的首要形式,具有特別的規(guī)范性。相比之下,工具化的活動是派生的形式,與物質(zhì)世界以及人們在其中通過選擇合適的工具來實現(xiàn)物化的目的有關。因而,后者勢必削弱前者的規(guī)范性。
哈貝馬斯認為工匠或修補匠的態(tài)度屬于工具化行動,這點具有特別的意義。據(jù)此哈貝馬斯提出,基因工程代表的就是對人的物化,且具有嚴重的倫理后 果。
那些對人類胚胎實施治療的人,他們對胚胎這一準主體的理解方式與對物質(zhì)世界的理解方式是一樣的。⑤Jürgen Habermas,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 p.50.
為了避免破壞任何一種基因干預的可能性(尤其是那些出于治療目的的),哈貝馬斯構(gòu)想出了一場虛擬的商談,一方是外科醫(yī)生,一方是未來已發(fā)育成人的患 者。
這種構(gòu)想出來的知情同意,把自我為中心的行動轉(zhuǎn)化成了交往行動。……基因修改的實施者,以述行的態(tài)度參與到了與身處未來的患者的互動中,并希望后者同意治療的目標,似乎這個目標是可協(xié)商確定的。⑥Ibid., p.52.
因此,基于行動理論對“人類本質(zhì)”這個概念的理解,不僅依賴于一個事實,即原則上并沒有外來的干預發(fā)生;而且還取決于基因修改的實施者(醫(yī)生)與胚胎之間是否進行了一場虛擬的商談,并由此拒絕了物化態(tài)度的產(chǎn)生。于是,哈貝馬斯的行動理論版本的“人類本質(zhì)”概念可以定義如下:“人類本質(zhì)”是指個體的這樣一些特征,即這些特征完全是由其自己的決定而產(chǎn)生的,同時也包括在預料同意的條件下被賦予 的。
就算我們同意哈貝馬斯的說法,仍有一個關鍵的問題有待解決:對未來個體本質(zhì)上(物化)的干預措施,對那個個體的人的倫理自我理解是否會產(chǎn)生任何實際的影響?換言之,即便基因工程確實意味著某種形式的物化,可為什么我們的道德判斷要依賴于這樣一種干預行 為?
四、人類本質(zhì)是人類倫理自我理解的條件 嗎?
如果在行動理論的視角下,“人類本質(zhì)”可被理解成作為人的倫理自我理解的條件,那么對這個“本質(zhì)”的基因干預作出規(guī)范性評價只有在兩種(不同)的預設下才可能:或者,把“人類本質(zhì)”自身就定義為一個名義上的規(guī)范性前提——但這將引起自然主義的謬誤;或者,關注基因干預的(倫理)后 果。
在《人類本質(zhì)的未來》中,哈貝馬斯選的是后一種方案。他的核心觀點認為,基因工程是來自另一個人的異化決定,這破壞了成為道德能動者的關鍵條件,即自主的意識(consciousness of autonomy)。就基因修改而言,受試者缺乏了“某種精神性的條件來滿足道德上的期許,即自己對自己的生活負責”①Jürgen Habermas,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 p.82.。上述觀點具有一個非先驗的假設,人類本質(zhì)可以作為倫理自我認識的前提。這似乎與哈貝馬斯一貫的商談倫理的基本假設是矛盾 的。
在商談倫理中,哈貝馬斯提出了道德原則的普遍有效性問題,其論證訴諸所謂的先驗—實用主義,即聚焦于“商談(discourse)”這個概念及其規(guī)范意義。其想表達的是每一種(語言)交往必然暗含了帶有具體規(guī)范性內(nèi)容的原則,想進行一場嚴肅的商談的每位參與者,對此必須是接受的。只有在述行的矛盾(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中,這些原則才可以被忽略。②對哈貝馬斯來說,這些預設具有獨一的認識論地位,相比之下,阿佩爾認為其中也包含了生存性的內(nèi)容,這使得每個參與者都不得不遵守。
哈貝馬斯明確指出,“商談”并不是伽達默爾的“對話(conversation)”,因為商談預設了一個理性的、解決問題的交往模式,借此可以在不同的行為方式和文化之間尋找非暴力的解決方案。這一商談使得參與者在保有具體的規(guī)范性預設的同時,可以理性地越過文化的邊界,這就是商談在哈貝馬斯的道德哲學中具有核心位置的原 因。
通過商談倫理的策略,從一般的論證基礎上來獲得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內(nèi)容,這是很有希望達成的。因為商談代表了一種超越了具體生活形式的、復雜而巧妙的交往形式,在其中作出符合道德規(guī)范的行動的預設被抽象出來加以設定并普遍化 了。
這里對“商談”這個復雜的概念已不需要再深入下去,只需強調(diào):語言互動的規(guī)范性預設,對于通過商談倫理來重建道德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只有在交往的互動中,才可能切實地重構(gòu)道德主張,并確保道德的有效性。因此就最低限度而言,談論道德要具備兩個條件:有效的主張(validity claims)以及由之而來并代表這些主張的互 動。
在這樣的預設下,基因編碼的修改所具有的嚴重倫理后果轉(zhuǎn)換成了這樣一個問題,即在我們的“本質(zhì)”與(作為必然預設的)交往之間是否有任何關聯(lián)。①Daniel C Henrich, Zwischen Bewusstseinsphilosophie und Naturalismus, Zu den metaphysischen Implikationen der Diskursethik von Jürgen Habermas, Bielefeld: Transcript, 2007.當然,哈貝馬斯似乎是要明確地指出這一 點:
前人格的人類生命概念以及我們對它的態(tài)度,植根于從穩(wěn)定的物種倫理(ethics of the species)語境中生發(fā)出來的人權(quán)主體具有的理性道德性中。如果道德本身不想產(chǎn)生滑坡的話,這個語境必須保持住。……如果后者發(fā)生變化,那么道德語言游戲的語法形式,即作為遵循規(guī)范性理性的存在的言說者和行動者,難道就不會從整體上發(fā)生改變嗎?②Jürgen Habermas,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 p.67.
即便承認了哈貝馬斯的假設:基因干預將改變語言游戲的語法形式,但他竟然沒有就這個問題作詳盡的考察,這點還是讓人感到吃 驚。
本文作者的一個設想認為,“自主意識”這個表達(以及反對異化決定的論證本身)是不夠清晰的。一方面,哈貝馬斯對“基因操作改變了語言游戲的規(guī)則本身”有所質(zhì)疑,因而指出反對異化決定的論證要捍衛(wèi)的對象是一種準先驗形式(quasitranscendental)的自主,后者是(道德)語言游戲的構(gòu)成部分。③Jürgen Habermas, “The Language Game of Responsible Agency and the Problem of Free Will: How can Epistemic Dualism Be Reconciled with Ontological Monism?”, Philosophical Explorations, Vol. 1, 2007,pp. 13—50.另一方面,“自主意識”似乎指的也是道德能動者的某種心理狀態(tài)(下文的例證中將涉 及)。
因此,反對異化決定論論證的解讀,可以有強和弱兩個版本。弱版本把“自主意識”這個概念主要理解為道德能動性的心理條件。這方面,哈貝馬斯的論說中并未包含在原則上反對基因工程的論證。只有某些基因被修改的個體可能對其道德責任產(chǎn)生懷疑。這樣的話,對基因工程的倫理評價,將依賴于每個個體的心理狀態(tài)。要想對此進行證明,就應對那些基因被修改的個體的道德和倫理人格的自我形象進行經(jīng)驗研究。當然,關于自主所作的普遍的和準先驗的預設,并不受這個解釋的影 響。
根據(jù)強版本的解讀,哈貝馬斯的論證提出了基因工程從整體上危及了自主,同時人類的道德也在整體上受到了挑 戰(zhàn)。
哈貝馬斯的論證,為這兩種解讀都留出了可能。但哈貝馬斯自己強調(diào)他的工作既不是一種嚴格的心理學,也不是倫理自然主義,因此在一些關鍵的問題上仍有待回答。但在處理這些問題之前,論證涉及的另一個難點也需要指 出。
五、異化決定、新生性和基因中心論謬誤
雖然表面看起來,哈貝馬斯反對異化決定的論證依賴于一個預設,即主體的生活規(guī)劃和意圖被基因修改“決定了”(基因決定論)。但是,他堅決地否認其論說并不包含任何意味的基因決定論。問題并不是基因決定了怎樣的人的特征,而是這種干預影響到了人與其自身的關 系。
問題并不是在現(xiàn)實中基因編碼在確定特征、性格、技能,或是決定未來人的行為方面可以走得多遠,而是說,事后對這些情況的知曉將干擾人與其自身的關系、與其身體或精神存在的關系。①Jürgen Habermas,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 p.53.
為了說明這個觀點,他引用了阿倫特的“新生性(natality)”概念,并指出“出生作為一個自然事件,在概念上符合了構(gòu)建一個人力所不能控制的開端的要求”②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9.。據(jù)此,只有出生才具備開始某種全新的事物的潛力。因而,行動才可以理解為“新生性這一人之為人的條件的實現(xiàn)”③Ibid., p.178.。
新生性的事實從根本上說是一個奇跡,它把世界,即人類事物的領域,從其平凡的、“自然”的廢墟中拯救了出來;行動的本體論的根基正是扎根于此。④Ibid., p.247.
通過援引這一立場,哈貝馬斯把出生理解為“自然和文化之間的分界”⑤Jürgen Habermas,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 p.59.,也就是說把出生表征為一個條件,它象征了人可以把自己作為自己行動的發(fā)起者。就此而言,哈貝馬斯的論述事實上并不代表了基因決定論,相應地,這里的主要問題是對基因修改這一事實的知曉。①這里暫不討論哈貝馬斯引用阿倫特的“新生性”這個概念是否正確。
這種改變將在內(nèi)心中發(fā)生……當被修改者長大成人后,知道了自己基因曾被修改以改變某種身體特性,而這又是出于另外一個人的設計。那么在這個人客觀化的自我感知中,對自己的身體是自然生長得來的認識,將被替換成自己是被制造出來的。②Jürgen Habermas,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 p.53.
同時,這個論證暗示出:似乎只有反對異化決定論證(同時也是自主概念)的弱解讀版本才是正確的。理由是,如果改變僅是在內(nèi)心發(fā)生,那么基因修改并不必然會導致作為一個負責任能動者的自我認識的喪失,因為得知這一情況后導致的結(jié)果是因人而異的。
即便是這樣,對于基因被修改者來說同樣有必要知道的是:基因工程不可能(也永遠不可能)從根本上決定他或她的行動和抱負。針對這種情況,杜普雷(John Dupré)把那種認為人們的具體的意圖和生活規(guī)劃可以被(基因)預先決定的觀點,稱作“基因中心論的謬誤”,特別是那種認為:基因是決定某些具體體征的最終原因的觀點,在科學上也是不正確 的。
認為“基因決定了”這種或那種特征,如眼睛顏色、智力、身高、性取向等,類似這樣的觀點現(xiàn)在仍常常耳聞。盡管可以說,某種蛋白質(zhì)的復制必然在外觀上呈現(xiàn)出某些特點,但是其中的作用機理卻遠還沒有得到充分的揭示。記住這點十分重要。③John Dupré, Darwin’s Legacy, What Evolution Means Toda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84.
漢迪薩德對異化決定論這一提法的適用范圍也作了說 明:
PGD技術的效果是有限度的,理解這點很重要。很多人關注所謂的“設計嬰兒”問題,但是想要在性別、頭發(fā)或眼睛顏色等普通的體征之外確定某個特征,以此來對胚胎進行選擇,這還將受到其他許多因素的制約。首先,與某種體征相關的基因必須存在于父母一方或雙方體內(nèi)。其次,一次典型的體外受精過程后,只能產(chǎn)生為數(shù)不多的、可供活體測試或?qū)嶒灥呐咛ァ_@些胚胎中,出現(xiàn)具有與預定特征相符的基因組合的胚胎的幾率很低,以至于并不值得去作出這樣的嘗試,如果考慮到即便在具有生育能力的夫婦中,也僅僅只有一部分的胚胎可以成功植入,則更是如此。最后,盡管研究表明像智力這樣的復雜性特征具有很強的基因相關性,但有太多其他的因素使得辨認出這樣一個帶有特殊性征的胚胎幾乎是不可能的。①Alan Handyside, “Let Parents Decide”, Nature, Vol. 464 2010, pp.978—979.
這段話對于哈貝馬斯論說的意義在于,基因決定性征的種種限度表明,還是可以重建起個體自主的范圍(基因修改仍是在自主的范圍之外),以及自己決定自己生活的可能性的,這也將影響到關于自主的意識本 身。
六、“為什么(人)應是道德的”人類學的短板
哈貝馬斯探討生命倫理的那篇論文,以一個關鍵性的選擇開始,即討論基因干預的倫理挑戰(zhàn),而不涉及胚胎的道德地位。進一步,他把問題聚焦在了這種干預對人類倫理自我理解所產(chǎn)生的影響上。其主要的理論假設認為,對他人的基因修改體現(xiàn)為一種特殊的決定形式,這破壞的是人類道德的構(gòu)成性條件。被基因修改的個體不得不接受一個“本質(zhì)”,即自己是他人意志的表達工具,這取消了成為道德上負責任的能動者的精神性前 提。
這個論證將我們的道德能力置于一個自然化的語境中,把道德能力作為道德行動的可能條件。“物種倫理”這個概念表達的正是這個思想,因為它把自然作為出發(fā)點,從整體上人類道德可以理解成一種“物種倫理”,因而它是存在發(fā)生轉(zhuǎn)變之可能的。同時,這個概念也蘊含了一個斷裂,與哈貝馬斯一貫所堅持的商談倫理中的核心——義務論倫理學的不一致,后者強調(diào)的是道德哲學的先驗性。盡管,在康德那里并沒有忽略“人類本質(zhì)”概念所具有的意義,但他還是否定了把道德哲學和倫理的有效性建立在人類學論斷之上的可能。②Jeffrey Edwards, “Self-Love, Anthropology and Universal Benevolence in Kant’s Metaphysics of Morals”, 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 Vol. 53, 2000, pp. 887—914.
就哈貝馬斯而言,在其早期著作中,贊同上述康德的觀點。他在“倫理的”和“道德的”二者之間作了明確的區(qū)分。他把“倫理的”從“風俗 (ethos)”的意義上來理解,大致相當于“習慣”和“約定俗成”。③“道德的”這個概念,通常是在指人類行動的具體的規(guī)范性命令層面而言的;而“倫理的”是理論層面的用法,指對具體道德規(guī)范性的分析。因而,倫理通常指的是“道德的理論”。根據(jù)這種習慣意義上的理解,倫理學和道德哲學可以是相互替換的同義詞。在哈貝馬斯看來,倫理的商談是“基于生活歷史的語境中的”,并不要求是普遍的,要處理的是類似生活風格和身份認同等依托于文化背景的具體問題。相比之下,“道德的、實踐的商談要求與所有現(xiàn)成的、具體的倫理生活保持距離,把自己從賦予個人身份并與其緊密交織著的生活背景中脫離出來,因為后者都是未經(jīng)質(zhì)疑的和反思的真理”①Jürgen Habermas, Just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Remarks on Discourse Eth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2001, p.13.。基于這樣的觀點,倫理的標準和道德的標準是不同的,因為它們各自合法主張的適用范圍不同。倫理規(guī)范提供的是行為應符合的文化習慣,這是與具體的語境相關聯(lián)的;而道德原則的主張獨立于任何文化語境,是普遍性的。哈貝馬斯稱之為“正義高于善(primacy of the just over the good)”。依循著康德,哈貝馬斯認為善生活的問題(倫理學)要和正義問題(道德)相互區(qū)分。決不能把道德置于倫理的語境中討論。相反,倫理和道德問題的區(qū)分,必然導致了他從普遍主義的視角來構(gòu)建其商談倫理。②參見Jürgen Habermas, “Morality, and Ethical Life: Does Hegel’s Critique of Kant Apply to Discourse Ethics?”,in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Cambridge: Polity, 1995, p.157。否則,道德的有效主張將僅僅淪為基于某種特殊文化背景的表達,因而成為相對 的。
必須強調(diào)的是,為了應對生物技術的挑戰(zhàn),哈貝馬斯放棄了這一清晰的劃分,因而危及商談倫理的基礎。與此同時,哈貝馬斯沒有對倫理背景和人類道德之間的關聯(lián)作深入分析,相應地,也沒有提出任何關于為什么應該堅持倫理自我理解并把人類本質(zhì)道德化的論證。由此本文認為,哈貝馬斯的進路突然變成了相當程度上的獨斷主義——為什么我們要堅持現(xiàn)實中的倫理自我理解,并防止其被基因工程改變?筆者對此的假設認為,這類問題的解決只能在某種“善生活”的概念范疇內(nèi),或是訴諸某種規(guī)范的倫理學才可 能。
由上可知,哈貝馬斯的進路導致的問題便很明顯了。他沒有從嚴格的義務論觀點著手來論證,這造成了一個問題,即從根本上說我們?yōu)槭裁磻撌堑赖碌摹τ谙駚喞锸慷嗟率降挠^點或者人類學的倫理學這類非義務論的探討來說,這是一個典型的問題。因此,對人類本質(zhì)的人類學的,而不僅僅是行動理論的理解,這就顯得有其必要了。然而,就其早期著作而言,哈貝馬斯并沒有談到這個問題,因此有必要從他本人的其他文本中去搜尋是否存在任何可以支持其論斷的線 索。
有兩個概念值得關注,一個來自喬治·米德(George H. Mead),即由語言作為中介的并通過社會化而達成的個體性,另一個來自阿諾德·蓋倫,即人作為一種有缺陷的存在(Mangelwesen)。③關于哈貝馬斯早期著作中人類學和實用主義關系的進一步分析可參見Axel Honneth, “Habermas’ Anthropology of Knowledge: The Theory of Knowledge-Constitutive Interests”, in The Critique of Power, Cambridge, MA: MIT Press,1991, pp. 203—239。在哈貝馬斯的著作中包含了這兩種人類學的解說,但他僅提到了米德——盡管如此,他還是沒有明確地指向人類學。事實上,他以實用主義的立場借用了米德的自然主義和非還原論的方法,重構(gòu)了人類的演化發(fā)展。在這樣的語境中提到米德的思想,十分重要。其理由有二:一方面,這暗示出哈貝馬斯明顯思考過米德的思想,這具有某種人類學的意義;另一方面,哈貝馬斯突出了語言相對于其他人類學方法的意義。①Jürgen Habermas, “Individuation through Socialization: On George Herbert Mead’s Theory of Subjectivity”, in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6, pp. 149—204.由此,米德可以理解為這樣一位哲學家,他為哈貝馬斯道德論述的語言理論提供了人類學的基礎。同時,他對哈貝馬斯近年來著作中提出的“弱的自然主義”概念也有所助 益。
米德之外,哈貝馬斯的著作中還可以發(fā)現(xiàn)一個更強意義上的人類學解說,盡管他本人對此從未進一步論說。這一路徑把人類個體的道德和語言技能,理解為在文化上對其自身特殊的脆弱性作出的補償。就此而言,它把道德的功能作為彌補人類為了抵消其特殊的脆弱性而采取的補償性行動,而這種脆弱性又是人類(生存功能的)先天不完整性導致的結(jié) 果。
我把人類的道德行為理解為某種建設性的應對,針對的是由機體構(gòu)成方面的不完整性導致的人類的依賴性,及由之而存在的人類自身固有的弱點。②Jürgen Habermas,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 p.33.
這個論述是蓋倫觀點(把人類作為有缺陷的存在)的回響。蓋倫把人類的各種鮮明的特質(zhì)理解成相對于各種內(nèi)在和外在弱點而作出的補償性行為。與蓋倫不同,哈貝馬斯并不認為人類需要通過訓練來保持其文化方面的特征;相反,他在《交往行動理論》中表明,對人類而言,作為“理性空間”的語言才是社會和文化繁衍的本質(zhì)媒介,因為語言具有一個語法的和規(guī)范性的內(nèi)核。因而,對哈貝馬斯來說,從后形而上學的立場上看,語言為重構(gòu)道德現(xiàn)象的義務論內(nèi)容提供了必要的概念基礎。這種重構(gòu)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所謂的“有效的主張”,哈貝馬斯用這個概念來論證:即便是道德商談中達成的理性的、共識性的結(jié)果也不得不使自己成為可能(規(guī)范的認知主義)。換言之,只有當“純自然(pure nature)”已經(jīng)戰(zhàn)勝了對于“理性空間(space of reason)”的偏好,道德才會顯現(xiàn)。但問題是,哈貝馬斯并沒有對自然和理性間的聯(lián)系作出明確的論說——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人類學的意義上。但就算在哈貝馬斯的著作中可以發(fā)現(xiàn)這類跡象,他還是沒有運用它們來論證自己的道德哲學。對此的理由或許是他并不想完全放棄正義高于善的理論假 設。
但是,當哈貝馬斯提出生物技術的挑戰(zhàn)可能敗壞我們的道德時,他便偏離了義務論倫理學的路徑,并由此產(chǎn)生了“為什么(人)應是道德的”這個問 題。
七、結(jié) 論
從哈貝馬斯的論文中可以提煉出三個假設:(1)“人類本質(zhì)”為人類道德提供了一個具體物種的背景,哈貝馬斯稱之為“物種倫理”;(2)對這一本質(zhì)的基因修改體現(xiàn)出一種特殊形式的物化,如果“要避免道德本身發(fā)生滑坡的話”①Jürgen Habermas,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 p.67.,對此應加以杜絕;(3)“把人類本質(zhì)道德化”的要求,可以由假設(2)得到辯 護。
在其商談倫理學中,哈貝馬斯賦予了人類自主以準先驗的地位;與阿佩爾(Karl-Otto Apel)不同,他認為沒有必要作出“對于道德的元承諾”。②Jürgen Habermas, Just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Remarks on Discourse Eth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2001, p.76ff.因為,人類一直以來都是生活在社會的、也是規(guī)范的環(huán)境中,他未曾考慮過需要從整體上對道德作出評價。然而,當面臨生物技術的挑戰(zhàn)后,情況發(fā)生了改變;哈貝馬斯認為面臨物種倫理的問題時,義務論的解說已無力給出答案 了。
即便是認同了某些生命倫理問題無法用義務論的解說來回答,那么還有另外的兩個問題沒有解決——自主概念的模糊性,以及為什么從根本上說應堅持我們現(xiàn)在的倫理自我理 解。
對此,哈貝馬斯弱版本的觀點或許是無可爭議的。有些人在得知自己被修改基因后,會產(chǎn)生身份質(zhì)疑,但另一些人則可能沒有這方面的問題。當然,也是由于這點,弱版本的論點無法從普遍的意義上為反對基因工程的觀點提供論證,它把問題留給了心理學研究和相關的治療方案。盡管這或許并不是一個無法接受的結(jié)果,但哈貝馬斯論證的其他部分并不與此相容,尤其當他提出基因工程從整體上對準先驗意義上的人類道德產(chǎn)生威脅時。進一步看,哈貝馬斯把人類本質(zhì)道德化的主張仍是不清晰的,其主要原因是他沒有解釋為什么要堅持道德自我理解,以及為什么不能改變它。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僅僅求助于“自主的意識”是不夠的;如果從嚴格意義上來要求的話,哈貝馬斯需要提供一個善生活的理念或是一種規(guī)范的人類學來作為支撐,才能回答這個本質(zhì)上不屬于義務論的問題——“為什么(人)應是道德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