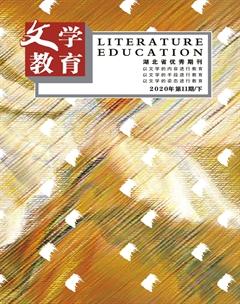《書目答問》與文學批評
余媛
內容摘要:張之洞的《書目答問》,是清末學界流傳甚廣的一部目錄學著作,該書旨在指導當時的后生學者: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為善。該書目按照四庫的經、史、子、集四個部類,再加上“叢書”一部,一共五個部類來編排書目。在書目的取舍、編排順序、序言和提要等內容中,無一不流露出張之洞的文學批評觀念,同時也是清朝末年文學思想的一個縮影。
關鍵詞:張之洞 書目答問 目錄學 文學批評
一.目錄學之于文學批評
“目”,本義是眼睛,眼睛為雙數,故后世便以目來表示復數。其引申義用于逐一稱述的事物,諸如節目、條目、項目、名目。“錄”字,在許慎《說文解字》中,解釋為釋為“凡錄之屬皆從錄”。由于錄需要刀刻,后來便加上一個“金”字偏旁。錄,從而由刻木之義,引申為記錄、抄寫和次第冊籍等義。
目錄學,“目”指的是書目分類的層次和結構,“錄”指的是敘錄,這些敘錄包括:概述書本思想內容、著者事跡及寫作、學術源流、品評版本等內容,后世簡而言之為解題、提要等。
目錄之學功用有三:
其一,有助于掌握歷代文獻的基本狀況,了解歷代文獻學發展之大概。通過這些輯錄而成的書目,可大致了解各時代文獻的基本情況,略知一代文學的盛衰。如饒宗頤《潮州志·藝文志》,《漢志·諸子略》對“九流十家”的著作凡189家共4342篇的著錄,從中想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諸子散文發達之盛況,《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對詩歌辭賦作品的著錄共106家1318篇,據此可知西漢時期詩歌辭賦的蓬勃發展。
其二,利用目錄及目錄只是進行專題研究。
可參見余嘉錫《目錄學發微》一書所列舉的古人利用目錄學考辨古籍的六項方法,此六種方法,對古籍的考辨、整理而言也是極其合適的。
其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指示讀書門徑。考古發現,甲骨文書就有按類別存儲的情況;孔子整理文獻,將《詩經》分為風、雅、頌;孔子修《春秋》,刪《詩》、《書》,訂《禮》、《樂》,纂《易》;漢代劉歆撰《七略》,形成我國第一個完整分類體系,首創類目。
余嘉錫在《目錄學發微》一書中,也曾言及目錄學的分類及功用:
目錄之書有三類:一曰部類之后有小序,書名之下有解題者;二曰有小序而無解題者;三曰小序解題并無,祗著書名者。……綜以上諸家之說觀之,則其要義可得而言。屬于第一類者,左論其指歸,辨其訛謬。屬于第二類者,在窮源至委,竟其流別,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屬于第三類者,在類例分明,使百家九流,各有條理,并究其本末,以見學術之源流沿襲。[1]
張之洞之《書目答問》,其撰書目的非常明確。卷首之《書目答問略例》有言:“諸生好學者來問應讀何書,書以何本為善。偏舉既嫌絓漏,志趣學術亦各不同,因錄此以告初學。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2]
可見,作者撰寫《書目答問》,其目的即是為了指導后學,告訴學生們,該讀何書,而書應該選擇哪一個版本,如何做到事半功倍地讀書學習。
余嘉錫先生曾言:“目錄之學,實兼學術之史。”[3]古典目錄學,不僅是一種讀書治學的門徑之學,而且是一門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為特色的傳統學術,是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因而張之洞的《書目答問》一書,作者的主觀本意,是為了方便后生讀書治學,實現了目錄學的治學門徑功能;而另一方面,這本書也客觀體現了,清朝末年洋務派代表人物、一代名臣張之洞對中國學術源流的理解與闡釋。
二.《書目答問》與其文學批評觀念
文學批評反應了客觀真實的文學史關于目錄學與文學批評之間的關系,吳承學《〈郡齋讀書志〉與文學批評》這一;篇文章時曾經有過這樣一段話:
“學人治書部的途徑之一是學習古典目錄,古典目錄的學習也是一種中國古代文化學術研究和學習的重要資源,古典目錄的學習也就是歷史的學習,這種學習從西漢時代劉向父子專門著的書,到后來西晉劉昫著述的《舊志》,目錄學這一學科開始確立自己的地位,古典目錄學顯然已經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與此同時這一學科又與其他學科存在密切聯系,目錄學和文學批評之間也是這種關系,“一方面,目錄學著作會摘錄文學批評典籍,同時設立對應的科目以表現目錄學對文學批評發展的認識,另一方面,各種書籍中的序言和摘要都屬于目錄學批評的對象,目錄學的文字批評功能開始顯現,也正是這個原因,古典目錄學成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一種形式。”[4]
這段話充分說明了目錄學之于文學批評的中重要意義。《書目答問》是清朝末年新舊文化交接碰撞之時的產物,在中國目錄學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義。《答問》的編排、類目的設置、序文和提要,無不反映著張之洞的文學批評觀念。
《書目答問》體現的第一個文學批評觀念,是尊經崇儒。
張之洞尊儒而斥諸子,而且他所尊宗的是純正的孔儒之學,就連“八儒”之一的荀子,他都加以批評。他在《勸學篇·內篇·宗經》中說到:“《荀子》雖名為儒家,而非十二子,倡性惡,法后王,殺〈詩〉、〈書〉,一傳之后,即為道經籍之禍。”[5]
在《書目答問》中,選書目錄最大的一門,是經學,包括了漢學和漢宋兼采兩派的作家作品,數目達到了二百零二人。這二百零二人中,漢學家占據多數,達到了四分之三左右。由此也可看見,張之洞的“漢宋兼采”,其實仍然是以漢學為基本。朱維錚認為《書目答問》“述及清代初中葉的學術文化,更其是乾嘉漢學,則贊禮之情躍然紙上……且不說這般見解在根本上沒有超越漢代就有的‘通經致用模式,即如說理習文從政都離不開經史考證,哪一項不是顧炎武、黃宗羲到戴震、阮元等人舊說的回聲”。[6]在《書目答問》對儒家經學書籍的收錄上的數量之多,可以看出張之洞的尊經崇儒思想;而在對儒家思想的解讀上,采用了以漢學為主、宋學為輔、漢宋結合的學術思想。
《書目答問》表現出來的第二個文學批評觀念,是濃厚的經世致用思想。
從林則徐的“開眼看世界”開始,接著魏源提倡“變古愈盡,便民愈甚”的變法主張,以及論學應以“經世致用”為宗旨,再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清朝的內憂外患之際,經世致用在當時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思潮。中法戰爭之時,為抵御外族侵略張之洞起用馮子材,組織邊防、購置武器、調撥物資,中法戰爭不斷取得勝利,這就是經世致用思想的體現。
從《書目答問》所收書目種類上看,有關于當時西方先進技術的新書品種的加入,對知識“實用”性的推崇,使得這本目錄學著作有別于當時及之前的傳統目錄著作。
應該說,張之洞的經世致用思想,來源于其父親張瑛及業師胡林翼。張瑛平素教子說:“汝輩當力學問、樹功名,慎勿為田舍翁所為,予之所深惡也。”然而致力于“為學”只是一端,另一端則是以務實為主、不尚空談的經世致用思想。
《答問》一書所錄書目,都是以實用、真確為標準。《書目答問·略例》言及書目之五不錄:
凡無用者、空疏者、偏僻者、駁雜者不錄,古書為今書所包括者不錄,注釋淺陋者、妄人刪改者、編刻偽謬者不錄,古人書已無傳本、今人書尚未刊刻者不錄,舊槧書鈔,偶一有之,無以購求者不錄。[7]
在諸多“不錄”的書中,“無用”之書,是第一個剔除的。《書目答問》一書中,所呈現出來的“經世致用”思想,可以說是這本目錄書籍的主線,這也是在這樣的一個大的時代背景下,有社會責任感的士大夫對年輕學子提出的期盼和要求。
《書目答問》體現的第三個文學批評觀念,是對乾嘉學派考據學的重視。如前文所述,張之洞主張“漢宋兼采”、“為學忌分門戶”,然而在漢學和宋學之間,從收錄漢學書目是宋學書目的三倍,可以看出他在漢學和宋學之間,是有所側重的。
朱維錚在《近代學術導論》一書中,也強調了這一點:
“張之洞雖然嘴上說著‘為學忌分門戶,但是實際上張之洞十分欣賞漢學文化,比如說《書目答問》通篇都不提及邵氏,這就讓人感覺非常奇怪,因為《禮經通論》曾經這么說到,體例不受刊書不能作為自己不著述的原因,文末附《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數百人都在這個列舉里面,但是舉邵懿辰還是沒有提及,這更加讓人覺得奇怪,倘非顯示張之洞本人的某種價值取向,便很難解釋。”[8]
從《書目答問》這本目錄學著作看:張之洞將“經部”分為“正經正注”、“列朝經注經說經本考證”、“小學”三個部分,而在每個子目的安排上,《論語》、《孟子》、《爾雅》也都單獨列出,而且收錄的這類儒家經典的闡釋著作,多數都是清代乾嘉考據學者的作品,充分突出了考據學在張之洞所倡導的學習體系的重要性。
綜上所述,張之洞的《書目答問》,體現了清朝末年學術界的尊經崇儒思想,同時也在內憂外患的現實環境中,不斷進取、吸收外來的知識文化。隨著清帝國的衰落、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到來,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學與傳統儒學相互交匯,迎來了新生的曙光。
參考文獻
[1]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古書通例》,北京:中華書局,2007,第8頁.
[2]張之洞:《書目答問補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3頁.
[3]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北京: 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9頁.
[4]吳承學,黃靜:《郡齋讀書志與文學批評》;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第1期,第1頁.
[5]張之洞:《勸學篇·輶軒語》;北京:中國盲文出版社,2014,第27頁.
[6]朱維錚:《近代學術導論》;上海:中西書局,2013.第47頁.
[7]張之洞:《書目答問補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3頁.
[8]朱維錚:《近代學術導論》;上海:中西書局,2013.第44頁.
(作者單位:廣州涉外經濟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