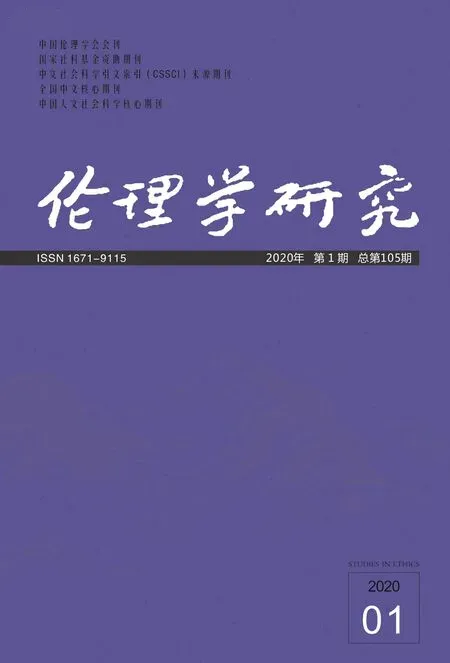荀子“禮”教的倫理秩序向度及其邏輯
李 萍,吳之聲
“禮”與“教化”是先秦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先秦儒家以禮來教化人,范導人倫關系,從而構建社會的和諧倫理秩序。孔子以仁釋禮,孟子攝禮入心,重視禮對于人的德性教化功用,通過人的道德修為與德性涵養,由內向外、由己及人地達致人倫關系與社會秩序的諧和。但進入戰國末期,禮制衰落與仁義價值危機使社會關系和倫理秩序走向崩潰邊緣。面對“禮義不行,教化不成”(《荀子·堯問》)的社會現實,荀子在批判繼承孔孟的禮與教化理念的基礎上,重新闡釋了“禮”,并以禮為核心系統重構了儒家的倫理與教化理想。荀子“禮”教為戰國末期的分亂轉向秦漢時代的大一統提供了倫理秩序支撐,對儒家思想向國家意識形態的轉型具有重要而突出的作用。因此,重新審視與把握荀子“禮”教的倫理秩序向度及其內在的邏輯理路,為當代社會轉型期的道德教育與秩序建設提供借鑒,具有重要意義與現實價值。
一、“人之生也不能無群”:荀子“禮”教的邏輯起緣
“人”是先秦儒家教化的對象,對“人”及“人之所以為人”的不同思考與理解形成了先秦儒家教化的不同范式。孟子以人心之善推證人性之善,認為人皆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辭讓之心、是非之心,“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孟子以四心言人的仁義禮智之性,并將之提升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的高度,故言人無四心非人也。孟子還認為人之異于禽獸就在于人能以仁禮存心,“由仁義行”(《孟子·離婁下》),愛人敬人,將心性之善發用到人倫日常中,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從而形成良善的人道秩序。孟子在孔子“仁”的基礎上進一步將“禮”內化于心,人存其心、養其性便能獲得人之為人的本質和道德主體性。在這里,主體的道德形塑相對于主體與他者的倫理關系結構具有優先性。與孟子不同,荀子從具體的歷史文化與社群結構及人在其中的社會文化角色[1](P18、26)來理解和回答“人”及“人之所以為人”的問題,并以此闡釋禮教的起緣與必要性。
荀子關于“人之所以為人”問題的思考與回答,在《非相》篇有明了闡述:“人之所以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故人之所以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無毛也,以其有辨也……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禮”。人道何以異于禽獸,荀子進一步回答:“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荀子·王制》)由此可以看出,荀子對“人”的理解確實與孟子有著不同的視角和理路,荀子是從“群”與“人道”來揭釋和把握人的本質的,人之所以為人乃在于能群,群道(人道)秩序之所以形成乃在于人的“辨”與“分”,“辨”與“分”之所以可能乃在于“禮”和“義”。在荀子看來,人是一種社會性存在物,人在“群”的禮義中獲得文化身份和道德義務,人之“群”也由禮義而形成具有秩序的社會整體,故牟宗三先生說荀子“從未孤離其所牽連之群與夫其所依以立之禮(理)”[2](P210)來空談人。“禮”是人成其為人、獲得社會文化角色與自我主體性的道德資源,也是群成其為群、群中個體與他者的人倫秩序之形成的客觀理據。
荀子認為孟子以人的四心言人之本質,并由仁之親、義之敬的推己及人過程來型構社會秩序,沒有關涉人所存在于其中的禮義世界及其具有的群之整體性,僅有仁義之心而無禮不足以成就人的德性與人倫之秩序。故荀子言:“仁有里,義有門。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荀子·大略》)楊倞解釋:“雖有仁義,無禮以節之,亦不成”,“里與門,皆謂禮也”[3](P476)。因此,人不能脫離禮而徒存仁義之心,仁義之心的發用及其推恩亦不能脫離禮所涵有的客觀規定性。依乎此,荀子以禮言人之高義乃在于為人的仁義之心和人道秩序的落實尋覓客觀的文化歷史境域。荀子言人之“義”“辨”與人之“群”“分”都離不開“禮”,“禮”是聯結個體之人與整體之群的客觀基礎和成群之道,此即“人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故“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荀子·王制》)。人要成其為人、群要成其為群就離不開禮的涵化與形塑,荀子由此從人之所以為人和人道秩序落成的維度證成儒家禮教的必要性。
荀子不僅看到了人具有“群”的社會屬性,還看到了人性中好惡喜怒之情與欲的自然屬性,并分析了情與欲對群之秩序的影響。荀子認為“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荀子·性惡》),“寒而欲暖,勞而欲息”(《荀子·榮辱》),是人生而有之、自然而然的情性,具有“材樸”的性質,也即是《中庸》所說的“喜怒哀樂之未發”的“中”的狀態。但在現實生活中,“中”之性的發用往往受惑于外物與利欲而離其“材樸”之資質,趨向與人爭斗、亂理犯分之“惡”。荀子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他在論釋禮的起源時指出,人生而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滿足便會向外強求,這種欲求若沒有度量與價值的規約,人與人之間就會陷入爭斗的漩渦,人倫秩序就會走向混亂與崩潰。荀子進一步點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荀子·性惡》)人之情與欲所具有的惡之趨向對人的群性和群之秩序構成了根本性的威脅,如何矯治人的情欲以維護群的穩定性和人倫秩序的諧和成為荀子需要直面的問題。荀子的回答是以“禮”來理化人之性、涵養人之禮義精神,也即“化性”與“起偽”。
面對人之趨惡的情欲,荀子認為以“禮”來化性與起偽不僅必要而且緊迫,“不教無以理民性”(《荀子·大略》)。在荀子看來,人如若順從自然情欲的任性發展而不受禮之約限,就會唯物利是圖、偏險悖亂而不正,故荀子強調“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荀子·性惡》),以使人之情性合乎人道而歸于治。荀子在《禮論》篇中亦有云:“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可見,“禮”既節制人的情欲,又滋養人之情欲,使人的欲求在外物世界中得到合理滿足。人之趨惡的情性也正是在“禮”之節與養的相互作用中不斷被遷化而向善,進而使人倫關系由爭亂窮困之態歸于皆有所稱、各得其宜之態。同時,荀子還重視通過“心慮而能為之動”(《荀子·正名》)的思慮與習偽之過程來使禮義規范內化而成為人的德性,以此成性偽之合而達乎天下之治境。由此處可知,荀子言人亦重“心”,但荀子之“心”不同于孟子的道德本心,而是以義辨為基礎指向人倫秩序的“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荀子·性惡》),故荀子云:“治亂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荀子·正名》)。在荀子那里,“心之知”和“心之偽”為禮之教的內化,為人徙惡向善、由自然情性走向社會群性提供了通途。
統而言之,荀子重視與高揚儒家的“禮”教乃緣起于他對“人”的重新認識和思考,在荀子看來,人要擺脫自然情性狀態下的逐利紛爭而走向有“義”有“分”、人倫秩序諧和的“群居”狀態,就要接受“禮”的教化。這里的“禮”為個體和群體提供了契合于孔子之仁的生活方式與秩序[4](P235),也為《中庸》所言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之“和”提供了可能。
二、“群居和一”:荀子“禮”教的倫理歸旨
構建諧和良善的人倫與社會秩序是儒家推崇仁禮及其教化的目的所在,體現了儒家對人類理想社會與生存狀態的追求。孔子從“入則孝,出則弟”(《論語·學而》)出發,以忠恕之道與中庸之則來推己及人,從而構建“個人—家庭—社會”仁愛和諧的秩序圖景。孟子在孔子的基礎上,由仁禮之心向外“推恩”,追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天下諧和之境。可以說,“貴和”是儒家社會秩序圖景的特征,也是儒家使仁禮之價值在社會群體生活中得到落實的保證。“和”為“禮”所內涵,是“禮”諧和人際、安倫經國的內生性功能,故《論語·學而》云:“禮之用,和為貴。”荀子從“人生不能無群”出發,在“貴和”的基礎上進一步描繪出儒家以禮義教化人所要達致的“群居和一”之社會理想。
荀子認為人生而有不能離群之社會性,但群的凝聚不是不待而然的,因為在社會性之外,人還有趨利嫉惡好聲色的自然情性,順任情性的自然發展就會使群分崩離析,自然性與社會性的矛盾需要“禮”之涵化和調節,才能使個體與他者在有序平衡的互動中成就“分”明“倫”定之群。荀子云:“故先王案為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愨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荀子·榮辱》)荀子的“群”不是個體簡單粗俗集合而成之群體,而是個體經由禮的教化與涵養,不斷揚棄自身自然情欲后向之歸復的倫理共同體,“群”是個體在禮的化分下獲得現實而具體的倫理角色與道德自覺的共同場域。“和”與“一”是荀子之群的旨向與價值特征。在荀子看來,群之和諧與穩定不在于人與人之間的齊一無異,因為“分均則不偏,埶齊則不壹”,“埶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荀子·王制》),故要以禮定分,以分安倫,使人在群之分位層級結構中獲得情欲的滿足,從而促成人際之和,并在和中達致群之一統。在禮的范導與涵化下,群的“和”亦即群的“一”之狀態,是人的爭奪分裂之狀經由禮之教化而進達諧和統一之態,“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荀子·王制》),由此人之為人與成群才能優異于群外之物。
綜而言之,“群居和一”的人倫與社會秩序理想是荀子“禮”教的歸旨。
第一,荀子以禮之“普遍化”使內稟自然情性的個體向群之倫理實體復歸。面對具有趨惡之自然情欲的個體,荀子認為要化其性不能僅“順詩書而已”(《荀子·勸學》),而須“待乎禮之條貫以通之”[2](P196),也即使內具自然情欲的個體在禮的教化中獲得其明確的社會文化身份與倫理道德義務,從而使自然情欲的個別性經由禮的教化與提點之普遍化而獲得其在社會倫理實體中的客觀規定性。此時之人,已不再是自然的、孤立的、趨惡的個體,而是內化社會規范、踐履道德義務、維護倫理實體的群中之人。由此處言,則荀子之“禮”為儒家仁義精神與價值的發用和落實提供了客觀的框架與情境。在荀子之“群”中,為人君者“以禮分施”,為人臣者“以禮侍君”,為人父者“寬惠而有禮”,為人子者“敬愛而致文”,為人兄者“慈愛而見友”,為人弟者“敬詘而不茍”[3](P228)。個體之人由禮而獲得其在群中之分位權利及其責任義務,個體在認同權利和義務的過程中化性而起偽、修禮而成德,進而自覺維護與歸復于群之倫理實體,成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荀子·王制》)的和諧秩序。
第二,荀子以禮之涵融實現社會層級分明與人倫諧和的統一。荀子身處戰國末期,人之情欲膨脹與社會秩序破壞的現實使荀子意識到須要以禮來重新確立社會分位層級和重整人倫秩序。荀子在《富國》篇云:“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君王到庶人皆要由禮之分而定其位,在各自的分位上各守其職、各盡其能。農人“分田而耕”,商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與大夫“分職而聽”[3](P210),以禮定分、以分定職才能使“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荀子·王制》),可見禮對社會職分秩序結構的化造之功。值得重視的是,荀子以禮化定的社會分位層級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人們對禮的踐履與成德情形而動態流動。在荀子看來,人可為堯禹,可為農賈,在于人之習禮積偽;“無恤親疏,無偏貴賤”(《荀子·王霸》),雖出身貴族,如若不修禮成德,則歸之于庶人。荀子經由禮構建了一個尚賢使能、無德不貴的公道社會,“于不平之中暗寓平等”[5](P112),從而實現社會分位與人倫關系的有序和諧。
第三,荀子以禮之范導使人的情欲滿足與約制趨向“和一”。荀子認為人生而有情欲,需要向外尋求滿足,但外物資源是有限的,若不能使人的情欲追求得到“度量分界”,人與人之間就會陷入爭奪敵斗的無序無群狀態。故荀子以禮來安排和落定人們在社會中的分位,依據分位賦予人們不同的權利與義務,從而使人們的欲求得到滿足但又不逾越其必要限度。如此,人與人之間就不會因為欲求受到資源限制而落入爭亂窮困之境,資源亦不會因人的無限欲求而被消耗殆盡,“欲”與“物”得以相持而長。由乎此,荀子在《王制》篇中所言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便可得見其深層蘊意。事實上,戰國末期的生產方式與經濟結構較孔孟時期更為復雜與多元,人的欲求亦隨之而日益多樣,荀子察悉于此,明乎人倫與社會秩序之諧和不能僅依仁心的發用,更要依靠具有客觀性的禮來范導人之情欲,發揮情欲之積極功用。荀子以禮來定分和化導人的欲求,使人在禮的涵養中各載其事、各得其宜,“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荀子·富國》),從而使整體之社會進達“群居和一”之境。
三、禮道合一與秩序合理性:荀子“禮”教的價值皈依
儒家教化的意旨在于構建諧和的人倫與社會關系,這種關系在其本質上是合客觀性與主觀性于一體的實存倫理秩序關系,其“首要問題是秩序的合理性和正當性”[6]。孔子以仁釋禮與成禮,孟子則攝禮入心,盡“四心”而知人性與天命,從而使孔孟的以禮化人獲得仁義的價值基礎,以仁義為基礎經教化而形成的人倫與社會秩序便具有其合理性。此外,孔孟的仁義還因其聯通了天命與人性,人通過道德修養可達天人合一之境界,從而使儒家的教化獲得超越性的價值,這在《中庸》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中可見其邏輯意涵。與孔孟不同,戰國末期社會轉型的時代背景使荀子重新思索人與天的關系,荀子認為天對人的德性涵成不具有主宰性的價值意義,人類社會倫理秩序重構的合理性與正當性亦不源于天道,而是源于人道的覺醒和有為。“禮”是人道覺醒與有為而累積形成的行為規范和倫理制度,為人的仁義之心的發用和人倫秩序的落成提供了客觀的社會框架,而不致使仁義之心因天之神秘而脫離人道實際。同時,荀子視“禮”為人道之極,從“道”的高度揭釋“禮”的本質,從而使禮之教化與人倫秩序落成不僅具有外在的規范,亦獲得內在的價值皈依和合理性。
荀子認為萬物的存在與運行皆有其道,“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荀子·天論》),天道并不主宰人道,人之德性與社會有序運行的價值本原并不來自于天,故荀子提出“明于天人之分”(《荀子·天論》)的主張。在荀子的思想體系中,人道更為可貴與重要,荀子在《儒效》篇說到:“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而“在人者莫明于禮義”(《荀子·天論》)。在荀子看來,“禮”為人類社會存在與發展的“道”,是成人之道、成事之理、安國之命,人不接受禮的教化涵養,不遵循禮的規范原則,便不能化性而起偽,就會成為“無方之民”(《荀子·禮論》),如此人和社會便會失“道”而陷入爭斗紛亂的無序狀態,故荀子曰:“禮者,人道之極也”(《荀子·禮論》)。作為人道之極的禮并非生成于天,而是圣王用心思慮、后天習偽,也即人道有為的結果。禮生于人道之偽,是人道之偽的結晶,但其一旦形成便具有“道”的獨立性與本體性,從而為個人的成德和人類社會的有序運行提供本原價值與合理性依據。荀子還把事天地、尊先祖與隆君師作為禮之三本[3](P340),禮是聯結人與天地、先祖、君師的價值紐帶,人循禮化性、修禮成德便能達致與天地參之境界,人類社會接受君師的禮教而謹守踐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荀子·天論》),便能進達秩序諧和的治平之境。可見,作為人道之極的禮為人倫與社會秩序提供了其所以然之理據,而諧和的人倫與社會秩序又體現了禮之價值。
作為人道之極的禮與人的內在情感和心理結構相契合,禮因緣于人的內在情理變化,又協調人之自然情感的向外發用,滿足著人對情感的價值訴求,從而為禮之化人及社會秩序落實提供價值合理性。“情”是荀子倫理與教化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具有情欲與情感的兩個基本義涵。荀子以禮教化人既是要矯治人之性情中的趨惡之欲望,又是要范導人的自然情感表達、形塑人的內在情理結構。荀子在《禮論》篇以儒家重視的喪禮與祭禮為例,揭釋人之情感與禮的內在聯系。《禮論》有載:“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又載:“祭者,志意思慕之情也”。喪祭之禮根據人的情感需求而設立,蘊含著人對逝者的哀傷之情與對先祖的念思之情,同時,喪祭之禮的規范又約限著人的悲哀與思慕之情的表達程度,使人的情感得到合理表露,使情與文(禮)諧和俱盡,故荀子云:“因以飾群別、親疏、貴賤之節而不可益損也”(《荀子·禮論》)。因此,以喪祭之禮對人進行道德教化,可以涵養人的情性操行、調節社會的人倫秩序,這與《論語·學而》所云之“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相呼應。喪祭之禮與哀思之情的關系可以進一步延展為具有普遍性的禮與情的關系,即禮出于人的內在自然情感需求,又約制與化導人的自然情感,“是人的沖動的文明表達”[7](P6),從而使人在禮的教化下“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荀子·修身》)。禮既因出于人之情理而獲得其合理性,又因其使人的情理表達有序、無過不及而蘊涵著中庸之道與價值。
作為人道之極的禮還是人類社會規范與制度背后的“理”,為規范與制度的存在、運行提供客觀依據和價值正當性。在荀子的禮論思想中,“禮”既是具體而詳的規范準則和制度系統,又是具有普遍性、客觀性的理和道。禮之為理與道,表現出了禮所內具的渾厚、廣大、隆高與誠明之本質,故荀子曰:“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荀子·禮論》)也正因為禮具有這樣的本質特性,荀子把禮喻為“直之至”的“繩墨”“平之至”的“衡”“方圓之至”的“規矩”,故人學習禮和效法禮方能克服虛偽詐利之情欲而成為“有方之士”,群體社會以禮為規范制度之法式方能成為有序諧和之整體。明乎此,荀子何以謂禮為人道之極便可得其要旨。禮內蘊著理和道,為其成為人之行為規范原則與社會制度框架提供合理性根據與基礎,人接受禮之理與道的滋養而化性成德,人之群體接受禮之理與道的分疏涵養而化成秩序公正合理之治平社會,故荀子亦曰:“禮者,治辨之極也”(《荀子·議兵》)。
四、“禮樂之統”與秩序極成:荀子“禮”教的落實途路
荀子之“禮”教起緣于“人生不能無群”的人之社會性與“人之性惡”(《荀子·性惡》)的自然情欲之間的矛盾和張力。基于此,荀子根據人的自然情性結構,通過禮的定分和養欲,對人進行禮義教化和德性涵塑,使人從自然性的存在走向社會性的存在,使人的情感與欲望得到合理恰當的表達和實現,使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在禮的協調涵化下走向有序諧和,從而使禮義教化的意旨和價值訴求在現實實踐中得到落實。荀子根據人生來有欲求的人性現實和“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荀子·榮辱》)的人倫實際,以禮義為價值基礎,賦予人們不同的社會定位和倫理角色,以“分”來約限和范導人們的情欲追求,使人的自然生命在禮的涵養中與禮義精神交融互通,從而提升人之德性和避免人在自然狀態中的犯分亂理,故荀子曰:“群而無分則爭……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群矣”(《荀子·富國》)。
荀子的“禮以分養和”主要從人倫關系和社會職事之分際進言,在禮的涵養協調下使人的情欲實現和社會的秩序建構趨向合理與公道。從人倫關系言,荀子認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是人與人之間的重要倫理關系,這些倫理關系建基于人性之實與自然情感,又內涵著禮對人之角色與義務的規定,如“遇君則修臣下之義,遇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則修子弟之義”(《荀子·非十二子》),故荀子強調人與人之間的貴賤有差、親疏有別、長幼有序對人倫和社會秩序的極成具有重要功用,并曰:“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瑳而不舍也”(《荀子·天論》)。從社會職事言,荀子認為“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荀子·富國》),個人的道德修為和技藝能力有限且與他人相異,社會要實現整體之有序諧和發展就要依禮分職分工而事,故有君王、諸侯、士大夫、庶人之分,又有農人、賈人、百工之別,此即荀子所謂“謫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荀子·儒效》)。從事不同職位之人修己安正,守禮盡責,發揮自身的內在潛能,使個人的情欲與價值追求得到合理且充分實現,社會由此達致職分而民有德、次定而序有齊的“群居和一”景象,荀子云:“夫是之謂政教之極”(《荀子·君道》)。
荀子以禮定分與安倫,使禮對人的范導和人倫秩序的形成在客觀實踐中落實,但如何使規范之禮內化于人心而植根于人的精神生命中,荀子則進一步提出了以樂致和、禮樂相統的化人進途,使人在樂的陶冶熏化中心悅誠服地順和于禮。人如果只是機械地接受禮而沒有樂的陶養,則會失去性情之感性與生命之柔性;社會秩序如果只是單維地接受禮的安排而沒有樂的疏導,則“人與人之間,會導致精神上的離隔”[4](P235),社會徒有秩序之規范而無人心之諧和。因此,儒家重視樂在人的情理結構與道德人格之培養中的功用,使人之性情豐圓和人倫秩序和融在樂的化育中得以成就。孔子曰:“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又有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論語·憲問》)孔子和《論語》常將禮、樂連用,禮與樂相統而成,樂是人的仁禮之心得以生成發用、社會禮制規范得以入化人心的保證。孟子以仁義釋樂,豐富了樂的道德意蘊。荀子承繼了孔子和儒家以樂治心、養情與成德的傳統,并在“禮”的系統中重新闡釋了“樂”,發揮“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荀子·樂論》)之特點,禮樂相兼并施,使儒家之教化真正落入人心。
與禮之源起一樣,荀子亦從人的自然性情來闡釋樂的起源,認為樂為“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荀子·樂論》),樂起于人的內在性情需要,同時又陶治人之性情而使之和順合善。在荀子看來,人生而有好惡喜怒哀樂之自然情感,這些自然情感的表達顯露若不合于禮義之道則會流于邪惡,從而使人情不化、人與人之間陷入偏險爭亂之境地。圣人先王為了避免人與人之間的紛爭悖亂,故制禮樂來修正人之行為,陶冶涵養人之性情,使樂之“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荀子·樂論》),天下便能因人之情感與行為表現合乎禮樂而歸于順和,荀子故云:“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荀子·樂論》)。荀子之所以以樂陶養人之性情而使之合于禮,是因為樂能以其鼓鐘、音律、節奏來恢弘人之志意、肅莊人之容貌、齊正人之行為;樂之清明廣大及其旋律還內蘊著順合天地與時變的禮道,以樂化人即是以道制欲,使人的趨惡之自然性情在樂之潛移默化的陶冶涵養中揚棄其惡而內植與他人諧和有愛之德。明乎荀子此意,孔子之“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和《禮記·樂記》之“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便可深明其旨。
荀子以禮定分、以分區別人之社會角色而形成人倫秩序,同時又以樂致和、以樂和順人之心性與情感,使禮和秩序之規范內化為人心之自覺自律而終得落實。在荀子的教化理論中,“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荀子·樂論》),禮之經在于顯發人之真誠敬意而教人踐履秩序之規范,樂之情在于直達人心而化外在規范為人之清明心志和德性,禮樂相統使得教與化、規范與德性、秩序與和諧相互融通而落實于人心。故荀子云:“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荀子·樂論》),樂蘊涵著中庸之道,君臣聽之則和敬,父子兄弟聽之則和親,長少貴賤聽之則和順,樂“審一以定和”(《荀子·樂論》),導引人在禮之分異中尋思和體認禮之一道,并在此中感化人心、變化風俗,使天下和睦治平。可見,“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禮記·樂記》,禮為天地之序,樂為天地之和,有禮而無樂或有樂而無禮皆不能安倫與化物,只有禮樂相統方能極成人倫有序之架構與社會諧和之秩序。綜而言之,荀子以禮統樂、以樂通禮,在禮樂之教化中轉變人之自然質性,陶冶人之心性情感,使人情理融洽、志意清明,“人自盡其心而涵厚其德”[8](P109),并由人之成德而使整體之社會進達“天下皆寧,美善相樂”(《荀子·樂論》)的“群居和一”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