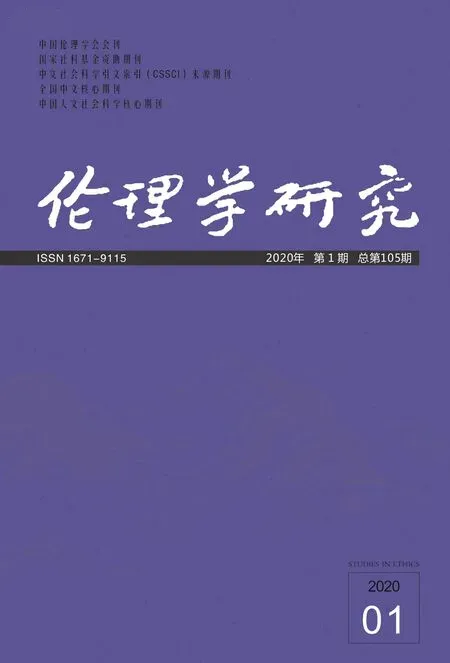論勒維納斯的倫理意向性
陳攀文
在現(xiàn)象學(xué)運(yùn)動中,意向性問題始終是一個中心課題。胡塞爾在認(rèn)知者與認(rèn)知對象的關(guān)系上對意向性進(jìn)行了探討;海德格爾盡管極力避談意向性,但其哲學(xué)中仍然暗含著生存意向性理論。勒維納斯不僅不認(rèn)同胡塞爾意向性的智性主義傾向,也反對海德格爾將意向性內(nèi)在化的生存論基調(diào)。勒維納斯跳出了經(jīng)典現(xiàn)象學(xué)中的“表象世界”“先驗自我”等范疇,從“自我”出發(fā)走向陌異性的“他者”。勒維納斯意向性理論的落腳點(diǎn)在于“思想對被思考者的開放”,在勒維納斯的意向性概念中,意向行為和意向相關(guān)項之間不再是對象化的構(gòu)造關(guān)系,而是隱喻的表達(dá)與“越出”的關(guān)系。這種獨(dú)特的關(guān)系也意味著意向性在勒維納斯這里實現(xiàn)了一種轉(zhuǎn)向。意向性的終點(diǎn)不再是如胡塞爾或海德格爾所主張的主體自身,而是與主體絕對陌異性的他者。勒維納斯展顯的是既不同于胡塞爾的意識意向性,也不同于海德格爾的生存意向性的一種別樣的意向性。勒維納斯將這種別樣的意向性叫做“倫理意向性”。
一、超越認(rèn)知意向性
勒維納斯對意向性的理解是從關(guān)注胡塞爾的意識意向性理論開始的。作為現(xiàn)象學(xué)倫理學(xué)家,勒維納斯同樣肯定意向性學(xué)說的重要性。胡塞爾通過批判中世紀(jì)的內(nèi)在對象說,尤其是在揚(yáng)棄布倫塔諾的意向性學(xué)說的基礎(chǔ)上建構(gòu)了意向性理論。在胡塞爾的意向性理論中,意向性的本質(zhì)特征是“指向性”,先驗自我是意向性之“主體”,而意向之意義則出自純粹意識之授義活動。胡塞爾認(rèn)為,意向性存在于意向體驗與意向?qū)ο笾g的指向關(guān)系。當(dāng)意向體驗指向某物時,意識就處在意向狀態(tài)之中,也就與該物建構(gòu)起了意向關(guān)系,該物也就成為了意向體驗的對象,即意向相關(guān)項。而先驗自我是純粹心理認(rèn)知意義上的意向性之“主體”,是意向活動的執(zhí)行者,各意識活動都是從先驗自我處發(fā)射出去,同時又由先驗自我聚合起來。先驗自我通過意向活動構(gòu)造出了意向相關(guān)項。純粹心理認(rèn)知意義上的意向之意義出自純粹意識之授義活動。意義指的就是意識的意向,是意識對于對象的念及,是對意向的觀念性把握。意義通過意識的念及活動,搭建起了意向體驗與對象之間的聯(lián)系。盡管意義通常是由個體的活動所展顯,但它又獨(dú)立于個體活動而始終保持自身的觀念性。因此,意義不具有“人”或“時間”的性質(zhì),也不具有存在的狀態(tài)。意義是一種觀念的、一般性的存在。意義完全是觀念的,屬于“純本質(zhì)”的領(lǐng)域。在胡塞爾看來,“意向性”的基本要義就在于意識對意向?qū)ο蟮淖陨斫o予的目的指向性。意向?qū)ο笫怯梢庾R通過意義賦義所建構(gòu)的,因而胡塞爾的意向性是一種意識意向性。
胡塞爾把先驗自我與認(rèn)識對象之間的關(guān)系界定為一種意識中的內(nèi)在建構(gòu)關(guān)系。于是,對于胡塞爾的意識意向性而言,表象在意識中居于絕對優(yōu)先地位。但是,勒維納斯不認(rèn)同胡塞爾給予表象這種統(tǒng)治地位。在勒維納斯看來,對表象的偏好與盲目拔高不僅致使了一種非歷史的存在觀念,而且顯露出“占有”或“統(tǒng)治”欲望的現(xiàn)象學(xué)之內(nèi)在動機(jī)。于是,勒維納斯又把胡塞爾的意識意向性看成認(rèn)知立場的意向性。
在對“被感知狀態(tài)”的定位中,海德格爾引進(jìn)了胡塞爾的意向性理論。但是,依海德格爾之見,圍繞著意向性問題存在著諸多偏見。海德格爾批評了意向性之顛倒妄想的客觀化以及意向性之顛倒妄想主觀化的錯誤傾向。通過對關(guān)于意向性理論兩個誤解的澄清,海德格爾窺見到了此在的生存對于意向性的重要性。海德格爾不僅洞察到了此在的生存對于意向性的重要性,也以此為突破口展開了對胡塞爾的意向性理論進(jìn)行了三個方面的批判性改造,實現(xiàn)了從意識意向性向生存意向性的轉(zhuǎn)向。首先,意向性之“主體”是生存價值意義上在世的此在而非僅有認(rèn)知意義的先驗自我。在海德格爾看來,意向性既不是現(xiàn)成者意義上的客觀性范疇,也不是傳統(tǒng)內(nèi)在主體意義上的主觀性范疇。真正的意向性根本不屬于現(xiàn)成者的范疇,而是本原的從屬于此在之生存。其次,意向之意義出自此在之實踐和價值性質(zhì)的籌劃而非純粹意識之授義活動。在此在籌劃于世之際,此在早已“出離自身”,早已“生存—出來”。正是這一“生存—出來”,使現(xiàn)成存在者得以被揭示。此在生存著,即籌劃著、超越著。只有此在能超出自身。此在存在于自身之中,是借助自身越出自身。這一越出自身并非單純的意向性之指向行為,同時也意味著從世界中領(lǐng)會自身。此在的生存本身就意味著“超出”。因此,超越性是此在得以指向某物或指向自身的先決條件。超越性使此在自身得以綻露。在此在綻露出的“此”中,存在者才能被遭遇到和被領(lǐng)會,并在此基礎(chǔ)上成為專題的“意向相關(guān)項”。可見,此在自身就是“自我指向的”,是與其他人共存的,是棲息于在手之物與現(xiàn)成物之中的。最后,意向性之指向性根源于使生存價值得以綻出的時間性而非意識的本質(zhì)結(jié)構(gòu)之事實。胡塞爾把時間性看作過去、現(xiàn)在與將來三維統(tǒng)一體,認(rèn)為每一現(xiàn)在之意識均被過去之“滯留”與未來之“前攝”所纏繞。胡塞爾把時間性看作過去、現(xiàn)在與將來三維統(tǒng)一體,認(rèn)為每一現(xiàn)在之意識均被過去之“滯留”與未來之“前攝”所纏繞。但海德格爾不像胡塞爾那樣把時間性歸于意識現(xiàn)象,而是歸于此在之生存。他在時間性的三維中更強(qiáng)調(diào)將來在時間性視域中的優(yōu)先地位。此在是“先行于自身的”,是從它所預(yù)期的最本己的存在能力來領(lǐng)會其自身。此在以預(yù)期其存在能力的方式走向了自己。過去、現(xiàn)在、將來是時間性的三重綻出狀態(tài),它們在其自身之中以同源的方式相互歸屬。具有綻出的規(guī)定的時間性是此在存在建制的條件。
在海德格爾看來,表象是一個關(guān)乎存在的問題。意識不是在世界之外,而是世界的一部分,主體與客體是在一個否認(rèn)彼此的主宰與獨(dú)立地位并確保持久互換的過程中,彼此構(gòu)造并為彼此所構(gòu)造。因此,海德格爾哲學(xué)暗含著一種生存意向性。在勒維納斯看來,海德格爾的生存意向性仍然含有胡塞爾式智性主義傾向。“當(dāng)海德格爾用‘存在’為那樣一種‘意向’奠定基礎(chǔ)時,那‘存在理解’的結(jié)構(gòu)就仍然有效,這種‘存在理解’的結(jié)構(gòu)是指對于‘此在可能性’的揭示,這種揭示是通過對他自己所實踐的和操勞的對象之同化與占有而完成的。”[1](P148)因此在勒維納斯看來,海德格爾生存意向性的存在論立場本質(zhì)上仍然屬于胡塞爾意識意向性的智性主義認(rèn)知立場。換句話說,海德格爾的意向性仍然是認(rèn)知意向性。盡管勒維納斯不認(rèn)同意向性理論的認(rèn)識論與生存論立場,但并未徹底拋棄意向性,而是在批判中超越胡塞爾與海德格爾的認(rèn)知意向性。在胡塞爾意識意向性理論的影響下,勒維納斯起初把意向性描述為意識通過與某種不同于它的東西相遇而實現(xiàn)自我超越的保證。而后,勒維納斯在揚(yáng)棄海德格爾的生存意向性理論的基礎(chǔ)上,又對胡塞爾的意識意向性理論作出了批判。
勒維納斯認(rèn)為,意向性并非如其所是地呈現(xiàn)世界,也不是完全復(fù)制意識早已擁有的東西。他對意向性的定義作出了關(guān)鍵性的修改:意識不再只是對某事物的意識,而是一種“逃離”,一種自我與絕對陌異性的他者相遇。在勒維納斯看來,認(rèn)知意向性中的認(rèn)知關(guān)系是一種占有、同化的內(nèi)在關(guān)系。真正的意向性不是認(rèn)識論意義上的整體化、同一化的建構(gòu),它相反地面向具體的東西。勒維納斯要超越認(rèn)知意向性,不再把與意向相關(guān)項的關(guān)系視作內(nèi)在同一化建構(gòu)關(guān)系,而是以開放性、超越性取代內(nèi)在性,賦予了意向性別樣的意蘊(yùn)。勒維納斯宣稱,意向性預(yù)設(shè)了“無限”觀念,尤其是不一致。認(rèn)知意向性中的意向行為是一種消除意向相關(guān)項之差異性、外在性、他性的同一化行為。在這里,無限不能被規(guī)整,無限與同一相對立。盡管無限是認(rèn)識之基礎(chǔ),但無限本身不能被認(rèn)識所把握。由于無限不受認(rèn)識活動所支配,因此認(rèn)知意向性不僅不是根本性的,也顯露了其局限性,即意識與意向相關(guān)項在其中保持一致的意向性并未在意識之基礎(chǔ)層面界定意識。在勒維納斯看來,無限意味著認(rèn)識的占有與同化權(quán)能的喪失,無限與認(rèn)識論意義上的主、客體沒有任何相關(guān)性,而是指向他者。因此,勒維納斯在這里強(qiáng)調(diào)的意向性是一種別于胡塞爾與海德格爾的意向性。在胡塞爾、海德格爾那里,意向性體現(xiàn)的是自我的自發(fā)性、主動性,其追求的是同一化。而在勒維納斯的意向性中,自我是對差異性、絕對他者之他性的追求,體現(xiàn)出的是一種自我在與他者之關(guān)系中的被動性。“在形而上學(xué)的思想內(nèi),有限擁有無限觀念;在這里,發(fā)生了根本的分離,同時也發(fā)生了與他者的關(guān)聯(lián)——我們?yōu)檫@種形而上學(xué)的思想保留了意向性、對……意識這個術(shù)語。這種意向性是對于言辭的關(guān)注或者對面容的歡迎,是好客而不是主體化。……它恰恰因此而能夠歡迎它與之分離的那個存在。主體是一個主人。”[2](P291)自我與他人之間是一種“面對面”的“友好”關(guān)系。但他人始終是一個保留著陌異性、絕對他性的他者。他人不會被我同化,不會消融在我之中。雖然自我始終有一種形而上學(xué)的欲望,但這種欲望不是以占有為目的的需求,而是一種永不滿足的“為他人”的倫理訴求。勒維納斯所展顯的意向性是一種倫理意向性。
二、倫理意向性的初步彰顯
勒維納斯的倫理意向性是自我這個存在者在不停的“逃離”中彰顯出來的。在《論逃離》中勒維納斯意識到要逃離“存在之重”。在《從存在到存在者》中,勒維納斯指明了逃離的切口,即逃離ilya。存在者在逃離ilya之后,其存在成為了位格的存在,即“具身性自我”。在《時間與他者》中,勒維納斯挑明了具身性自我遭遇到了陌異性的他者,逃離了位格的孤獨(dú)。在《整體與無限》中,勒維納斯指明了具身性自我是如何遭遇到陌異性或者說絕對“他性”之他者。
在《論逃離》中,勒維納斯借助“羞恥”“惡心”等戲劇化詞匯并通過延伸到海德格爾的“存在論”描繪了自我與存在的關(guān)系。在勒維納斯看來,自我在與存在的關(guān)系中羈縛于自身,因此自我與存在之間最初始的關(guān)系并不是本真性的。從本質(zhì)上看,存在是一種限制性的束縛,它必然帶來壓抑和囚禁。“存在的基礎(chǔ)是由超出的需求所構(gòu)成的,因此,對于這一需求來講,存在是一個我們要極力沖破的禁錮。”[3](P55)于是,勒維納斯宣稱要超出(excendence)、逃離這束縛性的存在。但是,在《論逃離》中勒維納斯只是意識到要逃離“存在之重”,還未指明逃離之切口。
在《從存在到存在者》中,勒維納斯指明了逃離的切口,即逃離ilya。Ilya是一個先于世界、先于主客分化的概念,是一個無人稱的、非位格的存在。勒維納斯用“黑夜”與“失眠”對ilya進(jìn)行了刻畫。黑夜是ilya的真正體驗,形象地詮釋了ilya的匿名性和非位格性。“我們被牢牢釘在這黑夜中,我們和任何事物都脫離了干系。但這種‘無物’并不等于一種純粹的虛無。這其中無‘此’亦無‘彼’;這其中沒有‘某物’。但這種普在的不在場,反過來卻也意味著一種在場,一種絕對無法回避的在場。”[4](P57)失眠則由永無止境的意識構(gòu)成。人們不能從這種警醒中撤出,無處逃遁。失眠的體驗正好揭示了ilya的存在境況。“存在不可瓦解,存在的工作永無止境;這就是失眠。”[4](P72)失眠中的意識并非真正的意識,而是一種無意向性的意識。它既不可對象化,也抽離了主體。在勒維納斯看來,黑夜的漫無邊際,失眠的永無止境給人帶來的是不安全、不確定和恐懼。
勒維納斯在這里強(qiáng)調(diào)的“恐懼”不同于海德格爾的“畏”。海德格爾的“畏”是積極的,它能夠把此在帶回到自身面前,是此在面對自身的一個前提,是此在有所關(guān)懷的明證。而勒維納斯的“恐懼”是非位格的,比死亡更原始、更深厚,是完全消極的,是要逃離的。于是,逃離就意味著點(diǎn)亮那漫無邊際黑夜,終止那永無止境的失眠。這種點(diǎn)亮、終止的力量就在于思維主體之意識。但勒維納斯并非像胡塞爾那樣將意識設(shè)想為先驗形式的純粹意識,而是把意識看作占有空間位置的“某物”。“思想有一個出發(fā)點(diǎn)。這不僅僅關(guān)乎一種定位的意識,更是一種不會再消失在意識、消失在認(rèn)知中的意識的定位。”[4](P77)勒維納斯在將意識位置化的同時,也為意識劃定了一個起點(diǎn)——“此處”。“而作為我們出發(fā)點(diǎn)的此處是置放的此處,它先于一切理解、一切視閾及一切時間。它就是這樣的事實:意識即源起,它以其自身為出發(fā)點(diǎn)。它是存在者”[4](P80),勒維納斯將存在者浮現(xiàn)出存在,通過與存在的距離而建立自身存在的這一事實稱之“位格化”。于是,存在者在逃離ilya之后,其存在也就成為了位格的存在,即“自我”。
勒維納斯還將“此處”與海德格爾“此在”中的“此”作出了嚴(yán)格的區(qū)分。海德格爾認(rèn)為,從來就沒有封閉孤立的、無世界的“此在”,“此在”一開始就遭遇了世界。“此在”中的“此”表明的恰恰就是此在隨時隨地與周遭世界的關(guān)系。勒維納斯的“此處”“場所”首先強(qiáng)調(diào)的并非與世界的關(guān)聯(lián)性,而是“此處”的孤立性。自我正是借助“此處”從而凝結(jié)在自身之中。然而,置放的過程又是由身體實現(xiàn)的。勒維納斯在這里就引入了“身體”概念。身體是意識在存在中的場所。“身體不能被放置,它即是置放。”[4](P80)這樣,勒維納斯對“身體”之意義作出了別于以往哲學(xué)的理解。身體不再是單純的存在者,同時也是“介入存在、置放自身的方式”[4](P81)。這種存在形式一旦形成,也就宣告了ilya的破裂,從而凝結(jié)為存在者。于是,自我也就成為了一種“具身性自我”。Ilya的破裂是自我意識到自身與存在本身的分裂。
從無人稱的ilya中位格化的具身性自我,只是停留在對ilya的忘卻層面。從表面上看,主體的位格化似乎實現(xiàn)了從ilya中的成功逃離,但逃離后的境況是留下了一個閉鎖在“魯濱遜孤島”內(nèi)的具身性自我。這逃離后的具身性自我仍然沒有擺脫巴門尼德式的同一的命運(yùn)。于是,在《時間與他者》中,勒維納斯借助“愛欲”和“繁衍”去打破具身性自我的這種同一性,進(jìn)一步逃離位格的孤獨(dú)。也正是在逃離位格的孤獨(dú)中,具身性自我遭遇到了他者。在勒維納斯看來,愛欲的本質(zhì)不是結(jié)合,而是一種分離。愛欲表現(xiàn)的是一種超越性。它既不步入無名的存在,也不是攜帶自身,而是在超越自我的同時,保持著一種陌異性。在愛欲中,他者是向具身性自我開放的。愛使所愛之人跳出自身去擁抱被愛的陌異性。于是,封閉孤立的位格在愛欲中就面向了他者。但愛始終表現(xiàn)為與他者的一種“不對稱性”。一方面,在愛中具有一種能夠超出自身而達(dá)于他者的傳送性力量;另一方面,他者之陌異性縱然在愛欲最為親密的關(guān)系中也不會消失。勒維納斯用在愛欲中的男性與女性的關(guān)系來表示自我與他者的關(guān)系。他認(rèn)為,這種關(guān)系促使他者之陌異性保持其純粹性,從而抵抗了巴門尼德式同一性傳統(tǒng)的吞噬。勒維納斯又進(jìn)一步從愛欲中引申出“繁衍”來詮釋具身性自我與他者的關(guān)系。繁衍形象地展顯了與位格相異的他者。繁衍意味著愛欲超越了時間與死亡,而且在與他者的關(guān)系方面上升到了一個新層面,即具身性自我能夠在他者的陌異性中保持自身,而不是喪失在他者之中。
在《時間與他者》中,勒維納斯只是挑明了具身性自我遭遇到了陌異性的他者,而并未說明是如何遭遇到陌異性或者說絕對“他性”的他者。在《整體與無限》中,勒維納斯作出了解釋。對于勒維納斯來說,實在世界中的某物的他性不是真正的他性,而是一種在本質(zhì)上只能夠被掌控的“在彼處”的他性。而掌控就意味著對他性的懸置,因此這種他性最終仍然要還原到自我。但在另一方面,勒維納斯在身體性實存與異于意識的實在中窺見了世界先于且外在于意識的明證性依據(jù)。在這一點(diǎn)上,勒維納斯與胡塞爾的觀點(diǎn)出現(xiàn)了對立。對于胡塞爾來說,世界是在意識的意向性中被建構(gòu)的,世界相對于純粹意識而言是一種外在的存在。在勒維納斯看來,世界對于“身體”而言,其外在性不能被懸置。勒維納斯指出,具身性自我是通過“欲望”和“語言”達(dá)至他者的。欲望與需要的匱乏不同,欲望并不滿足需要。由于需要是自我逃離ilya的首要標(biāo)志,也是同者之最初始的運(yùn)動,而享受又是需要的延續(xù),是一種利己主義口號,在享受的滿足中宣告了對ilya的逃離。自我在享受中盡管并不反對他者,但自我是絕對為己的。需要是自我在“經(jīng)濟(jì)性”中滿足自身、回到自身。需要的實質(zhì)就是將他者同化。欲望則完全不同,欲望的東西不是需要所能滿足的。欲望是一種向外的超越性,是外在性、陌異性、他性,其特點(diǎn)是不斷地追求。欲望指向無限,以此來超越自我。于是,欲望在“總體”傳統(tǒng)中鑿開了一條縫隙,也正是在“總體”的裂縫中,絕對陌異性的他者才得以產(chǎn)生。勒維納斯進(jìn)一步指出,語言維持了具身性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關(guān)系。語言不是思想之表述,而是與他者交往溝通的條件。語言在用于交往溝通的同時,把他者當(dāng)作他者加以接觸。語言意味著具身性自我與他者話語,意味著請求、召喚他者,把具身性自我展顯給他者。語言不是認(rèn)識他者的工具,而是與陌異性他者相遇之場所。在應(yīng)答我的召喚、請求中,他者顯露出來。
在逃離ilya的過程中產(chǎn)生了位格化的具身性自我,而在逃離位格的孤獨(dú)的過程中又遭遇了他者。也正是在位格化的具身性自我與他者的合力中,倫理意向性得以彰顯。
三、倫理意向性的確立
勒維納斯確認(rèn)了自我遭遇到了他者以及解釋了自我是如何遭遇到他者。但是,這自我遭遇到的“他者”究竟是何意?勒維納斯在《整體與無限》中作出了回答。也正是在回答這個問題的同時,勒維納斯最終確立起了“倫理意向性”。
勒維納斯指出,“面容”就是他者的顯現(xiàn)。于是,當(dāng)自我“面對面”遭遇他者之時,“面容”就是他者。換句話說,在這里他者與面容是同一的。在勒維納斯看來,他者與自我在“經(jīng)濟(jì)”世界中處于“自我中心”狀態(tài),自我與他者的關(guān)系是圍繞著自我而展開的。“可以肯定,他者袒露在我所有的權(quán)力之下,屈從于我所有的詭計,我所有的罪行。”[5](P55)勒維納斯在這里指出了自我與“他者”在“經(jīng)濟(jì)”世界中的一種自我霸權(quán)關(guān)系。在這種霸權(quán)關(guān)系境遇下,“他者”可以選擇兩種方式進(jìn)行抵抗。一是“他者”集聚所有力量與自由所擁有的資源來反抗我;另一是“他向我呈現(xiàn)出他的面容……來反對我”[5](P55)。在勒維納斯看來,第一種方式在本質(zhì)上是自我霸權(quán)的變樣,于是必須采用第二種方式,即面向他者之面容。面容“打開的正是無限的維度,由此終止了同一與我的不可抗拒的帝國主義”[5](P55)。盡管與他者相遇是一種“面對面”的關(guān)系,但不能把面對面的關(guān)系視作海德格爾意義上的“共在”。“在海德格爾那里,交互主體性是共在,是一個先于自我和他者的我們,一個中性的交互主體性。而面對面,則既預(yù)示了社會,又允許維持一個分離的自我。”[5](P43)。面容的出現(xiàn)打開的是一個外在性向度,打亂了具身性自我的秩序,突破了“經(jīng)濟(jì)”世界中自我霸權(quán)關(guān)系。于是,意向性在勒維納斯這里發(fā)生了一種完全的顛倒:“外在的無限性成為奠基性的,逼近‘臉’(面孔)的外在性的‘超越意向’就是‘從外面賦義’,即將意向性倒置了,方向性地改變了意向性本身的結(jié)構(gòu)。”[6]
因此,他者與具身性自我是處于一種“無抵抗之抵抗”的倫理關(guān)系之中。勒維納斯在闡述面容的可見性與不可見性中解釋了這種倫理關(guān)系。面容的可見性就是指面容作為一般認(rèn)識對象之可塑的外形。但面容自身正在不斷地破壞和超過其可見性形象而指向某種不可見的東西。這種不可見性的面容與人的身份、五官無關(guān)。面容包含的不可見的東西就是“意義”。“面容就是意義”[7](P186)。而意義又是借助表達(dá)而展現(xiàn)的。于是,勒維納斯在這里就把面容與語言聯(lián)接了起來。在勒維納斯看來,面容是他者身上最具表達(dá)功能的部分。因此他將面容稱之為表達(dá),甚至與話語相等同。他說,“面容說話,面容的顯示已經(jīng)是話語”[2](P185)。然而,話語意味著必須應(yīng)答。在他者的面容表達(dá)中,他者注視自我,自我則應(yīng)答他者。在應(yīng)答中,勒維納斯引出了“責(zé)任”問題。“你對面容的反應(yīng)就是一種應(yīng)答,不僅僅是應(yīng)答,而且是一種責(zé)任,這兩個詞密切相關(guān)”[8](P169)。于是,自我與他者的關(guān)系就成為了自我為陌異性他者肩負(fù)責(zé)任的關(guān)系。這種責(zé)任,也就是擔(dān)負(fù)應(yīng)答的能力。因此,勒維納斯宣稱,“話語,確切地說,應(yīng)答或責(zé)任是面容的本真關(guān)系。”[7](P88)這種本真關(guān)系實質(zhì)就是一種倫理關(guān)系。這樣,借助于“面容”與“話語”,勒維納斯也就把自我引導(dǎo)進(jìn)了倫理領(lǐng)域。“面容打開了原始的話語,它的第一句話就是任何‘內(nèi)在性’都不允許回避的義務(wù)。”[2](P185)在這里,面容不僅只是經(jīng)驗性的注視,更是超越性的由“話語”與“應(yīng)答”進(jìn)一步引申出的責(zé)任問題,引申出面容的倫理問題。面容具備表達(dá)無限和超越的能力以及逃離存在的能力的依據(jù)就在于面容的倫理特性。對此,德里達(dá)作出了較為中肯的解釋。“因為它打開和超越了總體。這也就是為什么它標(biāo)識了一切權(quán)力、一切暴力的邊界,標(biāo)識了倫理的起源。”
在勒維納斯看來,不僅對他者面容的應(yīng)答是一種倫理關(guān)系,而且面容自身就頒布了道德律令。面容作為完全陌異性的他者,“我只能想去殺死一個絕對獨(dú)立的存在者,它無限地越出我的權(quán)能,并因此并不與我的權(quán)能相對立,而是使權(quán)能的能夠本身癱瘓”[2](P183)。于是,面容就打破了自我霸占世界的迷夢。在自我之“占有性”與他者之“他性”的張力中,“他人是我能想要?dú)⑺赖奈ㄒ坏拇嬖谡摺盵2](P183)。但是,“這種比謀殺更強(qiáng)大的無限,已經(jīng)在它的面容中抵抗我們,它是它的面容,是原初的表達(dá),是第一句話:‘汝勿殺’”[2](P183)。面容的第一句話就是“汝勿殺”這一義務(wù),“這是一個命令,是顯現(xiàn)在面容中的命令,就像主人對我說的”[7](P189)。勒維納斯把“汝勿殺”作為其倫理責(zé)任的首要律令。這個律令并非來自神圣的權(quán)威,也不奠基于功利之中,更不是源自康德式的道德命令。它不是被建構(gòu)的,而是其他一切道德規(guī)范的源泉,是最根本性的道德律令。它源自他者的面容,他者之絕對異己的“他性”。“汝勿殺”不是在威脅中作出的回應(yīng),而是自我對自身暴力傾向的發(fā)現(xiàn)。這種自為的感覺正是在面向他者之面容時被觸發(fā)的。當(dāng)具身性自我由“殺他人”的暴力本性轉(zhuǎn)向“汝勿殺”,轉(zhuǎn)向“歡迎他人”之時,也就意味著自我占有、同化他者之權(quán)能的喪失。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在勒維納斯哲學(xué)中,道德其實是一種外于存在的意義。它扭轉(zhuǎn)了自我之存在本性。于是,勒維納斯在這里完成了一個根本性的超越。與他者相遇如果說還只是一種可描述性的經(jīng)驗性事件,那么面容的第一句話——汝勿殺——則是一純?nèi)坏牡赖率聭B(tài)。這是一個臨界點(diǎn),既能夠從經(jīng)驗現(xiàn)象層面考察,也能夠從倫理層面體驗。勒維納斯的哲學(xué)就是要找尋這個臨界點(diǎn),也就是他所謂的“存在中的洞”。在這個“洞”中,勒維納斯揭示了具身性自我與他者之間本真的倫理關(guān)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