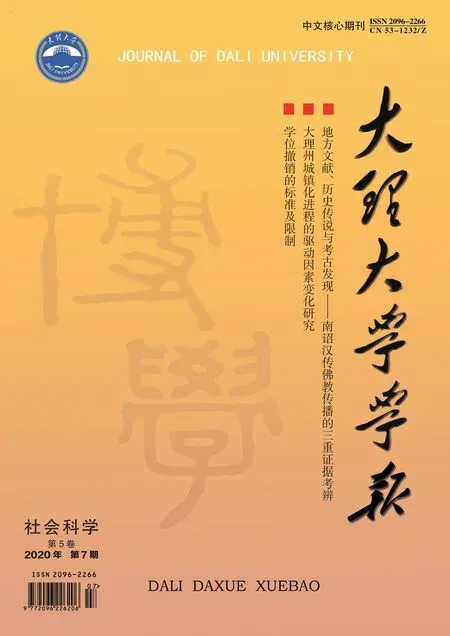壩子社會:洱海與白族的宇宙觀
楊德愛
(大理大學民族文化研究院,云南大理 671003)
壩子是指內部相對低平、周邊相對較高,內部地面坡度在80°~120°的山間中心型盆地,小型河谷沖積平原,河谷階地,河漫灘和沖積洪扇,起伏較緩和的高原面、剝蝕面及高原面上的低丘,較大的山谷等地貌類型〔1〕。通俗地講,散布于山脈河谷間的平地,云南人俗稱為“壩子”。蒼山、洱海之間的平地,俗稱為“大理壩子”。但實際上,當地人觀念中的“壩子”,不僅是與“山區”相對的地理區域,而且還是一個在特有地理空間內生存、生產及生活中長期累積起來的社會文化系統。這個系統之網,稱為“壩子社會”。
一、澇災與白族神話的表述
大規模的澇災屬于偶發性事件,并非年年如此。但是急于向下拓展村落、開墾土地的人們卻無力預測,也很難應對這種災害,因此歷代沿洱海邊而居的白族先民都飽受澇害。據相關文獻記載,僅在清代,因西洱河堵塞導致洱海水溢的重大災害便有幾十起。壩區環境的整體性,必然導致洱海澇災一損俱損,這種自然災害覆蓋面積廣,且很難根治。因而,基于高原壩子這種特殊的地理地質構造,居于其內的先民便憑借想象力將其生活空間的開拓過程逐漸神秘化,并結合各種文化元素建構出諸多開辟壩區的神話。在壩子社會中,這類以排水為核心的開辟神話為在區域范圍內生活的人們作了得以存在的合理解釋,也為人們處理水澇災害預留了以宗教方式來消解的空間。可以說,這類神話是白族群體空間心理的最直觀呈現。在大理壩區,相關的開辟或排水神話主要有兩則,即《白古通紀》載:
《觀音伏羅剎》講,大理盆地原為澤國,為羅剎一部統治,稱為羅剎國。羅剎喜啖人眼、人肉,觀音愍其受害,乃化為梵僧,牽一犬自西天來。羅剎貴臣張敬引見于其王,梵僧遂與羅剎立契券借地,并用“袈裟、白犬”之術贏得羅剎國土。后乃幻上陽溪石室,為金樓玉殿,以螺為人睛,飲食供張百具。羅剎喜,遂移居之。一入而石室遂閉,僧化為蜂由隙出。自此羅剎之患乃息……于是老人鑿河尾,泄水之半,人得平土以居……時觀音大士開疆,水退,林翳,人不敢入。有二鶴,自河尾日行其中。人始尾鶴而入,刊漸漸開,果得平土以居。〔2〕53-55
《段赤城斬蟒》講,洱河有妖蛇名薄劫,塞河尾峽口,興大水淹城。王出示:“能滅者,賞盡官庫,子孫世免差役。”有段赤城愿滅蛇,縛刀入水,蛇吞之,蛇亦死。水患息。王建寺,鎮之以蛇骨灰塔,名曰靈塔。〔2〕65
以上兩則神話,前者借觀音之力降服羅剎,并打開了洱海水道,泄水之半,人們才得平土以居,解釋了大理壩子之由來。后者則通過講述段赤城殺死塞河尾峽口之妖蛇,說明河道雖開,但是水澇之災依然存在。
《小黃龍大戰大黑龍》的一些版本中,也有“小黃龍打敗了盤踞在西洱河的大黑龍,使得洱海水得以從天生橋排出”,或“大黑龍被小黃龍打敗以后,急于逃命,便沖開了天生橋下的石崖,由此洱海水便排了出去”之類的結尾。“天生橋”為扼洱水西流之咽喉,成為大理壩子地理結構的最關鍵點,因而如今上面還建有江風寺,寺內還塑有龍王段赤城之像。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重修圣元西山碑記》載:“按郡志:貞觀癸丑,圓通大士開化大理,降伏魑魅,鑿天橋,泄洱水,以妥民居。”〔3〕此外,李元陽纂《嘉靖大理府志》古跡一項中講:“天橋在城南三十五里。觀音大士鑿洞山骨,使洱河水下趨處也。初未鑿時,蒼洱之間水據十之七,鑿后水存十之三矣。古人謂之石河”〔4〕。《僰古通紀淺述》則說南詔勸利晟七年(公元822年)“有巨鯨自浪(穹)流入洱河,塞于河尾大橋口,河水壅滯不流,泛濫于國鄉城市”〔5〕。此處將巨蟒換為巨鯨,更能突出堵塞河尾之物體形的龐大,造成澇災之嚴重。而以上這些神話都反映了古人對壩子空間形成的認知,并將澇災歸咎于怪獸。
古代社會,應對壩區澇災的唯一辦法便是疏浚西洱河(即洱海)。使用人工之力,將淤積于河口及河底的雜物、泥沙打撈挖出,使得河口通暢、河床變深,加大其排水量。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沒過幾年,河道依然會有泥沙沉積,因而疏浚西洱河成為歷任地方官員的重要任務之一。疏浚西洱河可謂勞民傷財,卻又恐于湖水上漲淹沒田畝屋舍,因而每有澇害人們便認為是天生橋口又遭巨蟒所堵,此時就要訴諸于神話中能斬蟒疏河的龍王段赤城,尋求成本更低的宗教解決途徑。在修筑天生橋節制閘之前,每有漲水,各地百姓便會紛紛至供奉段赤城的廟宇中,磕頭燒香,祈求段龍王能盡快使海水退去。
在田野調查期間,我們經常聽老一輩的人提及洱海的澇災,暴雨過后,海水突漲,不僅危及房屋和田地,有時也會害及人畜性命。新溪邑村的何YQ老人(時年87歲)告訴我們,以前洱海過幾年就會漲水一次,而且還多是秋季要收割水稻和玉米的時候,其次子出生那年(1966年)的秋季,連續下了十多天的大雨,結果一覺醒來海里面的水都漫到了家里,村中心的橋也被洪水淹沒了。房子好多都是土坯墻,倒塌了一大片。田地被淹,隊里幾個人就借了一條小木船去搶收莊稼。可到了田野,已經分不清哪里是河哪里是地,大家一躍跳下船,結果正好跳進了河道里,河水齊頸。他們被河水沖出幾百米后,才被河口的幾棵柳樹擋了下來,很幸運地撿回了命①訪談對象:何YQ(男)。訪談地點:新邑村訪談對象家中。訪談時間:2017年8月12日。。河矣城村,則在1962年秋,洱海水上漲,村民到水淹田中搶收玉米時,超載沉船,結果造成了12人溺亡的嚴重后果〔6〕。
囿于排水問題,作為高原湖泊的洱海給居住于其岸的人們帶來了許多痛楚,然而這些痛楚也以宗教神話的方式形塑了白族人的宇宙觀,使其在一個相對獨立的壩子社會中按照自己的認知方式思考和生活。段赤城信仰便是這種壩子社會宇宙觀視角下的產物,龍王段赤城至少在精神世界保證了白族人生存空間的續存,他與巨蟒的對抗也隱喻了人們與澇災的對抗。
二、分水線與被分治的洱海
對洱海的空間認知中,除了著眼于壩子整體的“水陸平衡”外,在壩子內部,人們也因區域差異,于宗教層面上對其進行空間劃分,這也是白族宇宙觀的一種體現。洱海沿岸,在海東、雙廊、磻溪等地都有“南北海神”和“分水線”的說法。簡言之就是洱海中心有一條分水線將海面一分為二,南北水域都有各自的海神掌管。
北海的水神是雙廊紅山本主廟內供奉的王盛、王樂和王樂寬祖孫三人,他們共為雙廊的復式本主。王盛被敕封為“赤男靈昭威光景帝”,白族話稱其為“紅山老谷”或“奔老谷”,即“北邊的本主”。王氏原籍海東魯川,即挖色壩,因為是漁民出身,故很識水性,王盛被南詔分官,掌管洱海水軍。天寶戰爭中,王家三將大敗李宓水軍于洱海,致李宓落水溺亡,白族人有感于其忠勇,便建廟于紅山世代祭祀。
紅山本主同時是雙廊、康海、大建塝和島依塝四村本主,每年農歷正月初四至初七為本主圣誕,屆時四村白族居民要用花船接本主雕像回村,并由眾人抬著依次繞境巡游。農歷四月十五日則為紅山本主會,該會是洱海北岸最重要的廟會,參會的主要是來自喜洲、周城、挖色以及洱源鄧川等地的善男信女,許多沿湖的漁船民也會劃船前來朝拜祈禱。廟會期間紅山廟前的洱海湖面往往白帆點綴,百舸爭流,十分熱鬧。
據嵌于正殿內的《景帝寶殿重建碑記》介紹,該祠始建于大理國初期,當然無史可考。但是洱海北岸老一輩的白族漁民卻認為王家三位將軍因其忠勇而被封神,他們管理著洱海中的一切事物,甚至如段赤城一樣會化為一條額頭上寫有“王”字的綠蛇繞海巡游,因而漁民見到水中游蛇便要給紅山本主磕頭燒香,以示敬重,由此,方能得到其佑護,自己才能船穩而魚豐。紅山本主廟內幾位本主塑像都戴三龍頭冕,這是龍王的標志,幾尊為便于村民游神搬動而雕刻的較小神像,其中為龍王妻母的則頭戴魚冕,也與海有關。紅山本主佑下的子民多討海為生,因而將南詔水將封為海神也無可厚非,但是幾位當地蓮池會的老齋奶卻告訴我們,紅山本主本為天上神仙,觀音老爹①傳說中,觀音化為梵僧開化大理,因而這個男性形象的觀音就被稱為“觀音老爹”,與“觀音老爹”相對的“觀音老母”則在大理城南觀音塘。打通西洱河,將大理壩子的水排掉大半,卻發現無人管理洱海,他擔心沿岸百姓遭受水患,才叫來紅山本主坐鎮洱海。《紅山本主經》載:
“南無佛艾海神那慈南另抬王光景帝……慈南另招本姓王六詔支持一將官后來神圣歸天位敕封景帝鎮紅山……修成正果觀音朝六鵝山②六鵝山,是紅山后面的一座大山。下金身塑手持寶劍斬妖魔一堂三代父子宣。”〔7〕
在紅山廟大殿內王盛塑像的右側便是觀音老爹,他慈眉善目,手拄拐杖,身穿袈裟,形象與上陽溪羅剎閣中的觀音老爹如出一轍。而觀音老爹背后的墻畫所畫的正是大理壩子被水淹沒的情景。
與紅山本主廟南北對峙的水神是“南海將軍”,白族人稱其為“南老谷”,即為“南邊的神”,其廟宇“南海將軍廟”坐落在下關石坪村中心,在修建環湖公路以前,該廟宇同應海廟一樣都為鄰水而建。據嵌于南海將軍廟內撰于2006年的《南海將軍廟碑記》載,該廟始建于明代,村賢并擬定今名。廟內祭祀的是囊聰獨秀冠眾應化景帝——字將軍父子。
將軍父子,山東荔城縣人氏,唐李宓將軍之部將。唐玄宗天寶十三載(公元754年),隨師征南詔。詔王閣羅鳳采“誘敵深入,堅壁清野”之策,誘父子所部駐下關天生橋附近。南詔鄉兵之“白衣沒命軍”以“羊陣”夜襲所部,老將軍急得面紅耳赤,張口無語,小將軍率卒奮勇殺“敵”,兩月后,唐師因缺糧、染疫,被南詔軍民聚殲,將軍父子戰殞于關外豆糠坡一帶。因父子生前英勇善戰,忠義可嘉,殞后敕封囊聰獨秀冠眾應化景帝,其地位為高眾神之意。③下關石坪村《南海將軍廟碑記》,楊躍雄田野調查收集(2017年8月)。
南海將軍雖非石坪村本主,卻為周邊各村百姓所祭祀,并被南村、下和等八個村寨共同奉為本主,民間也稱“八處廟”〔8〕。在漁業興盛的年代,南海將軍廣受洱海南岸漁民信奉,漁民常用生豆腐、生魚祭祀,其會期是農歷八月二十三日。
在宗教祭拜層面將湖泊劃區而治的方式,或許是為了避免不同村寨的漁民因漁場之爭而引發沖突,也有可能是為了標注和記憶各種魚類的繁殖習慣,和與之相關的物候知識,但是洱海被一分為二的說法其實由來已久。明李元陽《西洱河志》載:“東岸有分水崖,儼如斧劃,漁人謂自崖下分水為兩界。南為河,北為海。咸淡不類,河魚不入海,海魚不入河,魚游至此則返。”〔9〕176早在明代便有大理當地的漁民以海東山崖作“分水”地標,將洱海劃為兩份,甚至說南邊是海,北邊是河,其中水質還分咸淡,魚兒們也是涇渭分明,不越雷池。如今這面分水崖依然矗立于海東玉案山,崖上還建有一座雞巖寺。該寺是挖色鎮重要的水神廟,位于海印村附近,傳說始建于元代,以前還有一座雞巖塔,如今塔已被毀。其中塑有主神雞巖景帝,他黃袍露齒,危坐正中,一副龍王面貌。一位手握鯉魚的配神立于大殿左側,應為魚神。此外還有一位馴養魚鷹的神祗,這些都和捕魚有關。就在2000年前,海東一帶還是一副交通閉塞、田少地貧的面貌,漁獲是當地居民最重要的生計方式,因而漁民熱衷于供奉龍王、魚神,以求豐衣足食。
海東分水崖對岸正西便是銀橋鎮磻溪村,該村就是所謂分水線的西接點。據村民介紹,村內原有一塊天然大巖石,號稱可平分大理洱海,此石為人們所崇拜,但是在1958年被毀,后在其基礎上建了磻溪村的大黑天神本主廟〔10〕。我們田野所見,如今在本主廟廣場入口處,后人重新立了一塊高約1米,被打磨得光滑的“分水奇石”。石背刻有題記:“此石名曰分水石,其延伸得到海東。相傳觀音大士負來此石欲架磻溪至海東之大橋。分水石是百二山河的分界,也是洱海西岸的中分點,洱海的中分線。古人曾贊遇到:‘磻石鎮中流平分山河百二,溪泉歸大海變成氣象萬千’。”
“百二山河”一詞經常出現于大理境內的一些題記上,至于“百二山河”為何意,村中心廣場,珠連閣對面的壁畫上有介紹云:“‘百二山河’是指洱海北端的龍首關(上關)與龍尾關(下關)相距約一百華里,故以‘百二山河’。又取意于戰國時期‘百二秦國’或‘百二雄關’之典故,比喻大理襟山帶海,關鎖南北的險要戰略地勢。”
“百二山河”源于《史記·漢高祖本紀》中“百二秦關”一說,原比喻山河險固之地,據說明代嘉靖年間四川狀元楊升庵被貶謫至保山,途經大理時見此地兩關雄踞、山河壯闊,便寫下“百二山河”一詞。從此“百二山河”成為人們對大理壩子樹山鏡海地貌的普遍形容,從而也助長了以劃分山水來抽象空間的地理認知方式。清《滇南志略》卷二大理府一條中有記載:
洪圭山,在點蒼山之半,分點蒼為兩截。自龍首至此,再起分支,聳脈至龍尾。其東支下垂獨長,直抵海中,亦分海為兩半,曰鵝鼻嘴,亦曰分水涯。南為湖,北為海,海咸湖淡,湖魚不人海,海魚亦不人湖,各不相混。〔11〕
此處提及的洱海分水線,及南湖北海的說法可能為作者由當地人處得知,與李元陽文雷同。但是其中分水線的具體位置卻有所出入,在文中洪圭山(即今弘圭山)被認為是點蒼山之分割線,它將龍首至龍尾分為兩半,而弘圭山東延至洱海中的山體部分則被視為洱海的分水涯,其南為湖,其北為海,實際上該分水涯便是今天喜洲金圭寺村附近的海舌。隨著洱海水位的不斷下降,乃至穩定,海舌原本被湖水淹沒的部分也得以成為陸地和灘涂。金圭寺一帶因近洱河神祠,又有龍湖內嵌其中,風景優美,歷來都是喜洲城及大理附近百姓喜來游玩之名勝。后來原本作為船港的龍湖在轟轟烈烈的“大躍進”年代被填埋為農田和魚塘,服務于生產。如今龍湖雖然已經人力清挖,退塘還海,但卻早已被村落包圍,與海隔絕。就連在1939年由喜洲四大家族之一的董家修建的海心亭也變成了人們口中的“田心亭”,游客不讓入,失去了休閑功能。
再往前追溯洱海分水線說法的由來,可見于《白古通記》中的記載:“點蒼山腳插入洱河,其最深長者,惟城東一支與喜洲一支。南支之神,其形金魚戴金線;北支之神,其形玉螺。二物見則為祥。”〔12〕此處洱海也因南北兩水神之差異被分為了兩部分。而所謂“點蒼山腳插入洱河最深長者”,也就是海西平原延伸至洱海中的兩處最東者,我們今天從衛星地圖上看,這兩處大概也就在喜洲河矣城村“洱河神祠”大理城東龍鳳村“洱水神祠”所處的位置。當然李元陽的認知也是受到《白古通記》影響的,他在《西洱海志》一文中便引用了《白古通記》中羅荃法師建寺鎮壓羅剎余孽的故事〔9〕176。《南詔圖傳》是《白古通記》成書的主要資料來源之一,因而分水線的說法最早的文字記載應出自《南詔圖傳》,該圖傳文字卷載:“二者,河神有金螺、金魚也。金魚白頭,額上有輪。蒙毒蛇繞之,居之左右,分為二耳也。”可見,在南詔末期便有“分為二耳”的提法。此外,李文中說:“八月望夜,河海正中,有珊瑚樹出水面,漁人往往見之。世傳海龍獻寶。”這與文字卷“扶桑①扶桑是中國古代傳說中的神木,由兩棵相互扶持的大桑樹組成。它生長在東方的大海上,是太陽升起的地方,也是連通神界、人間、冥界的大門。《山海經·海外東經》有載:“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影照其中,以種瑞木,遵行五常,乃壓耳聲也”亦有所相似。而《南詔圖傳》中關于洱海的記載有轉自已佚的《西洱河記》,該書在南詔時期已有之,所以“分二洱”的提法應更早,似乎早在南詔時人們便有洱分二湖的認知,并且不同的水域已配備不同的水神,即南為金魚,北為金螺。
三、“海東”“海西”與社會差異
洱海流域實際上分布有多個壩子,即高原盆地,自北向南有洱源壩子、鄧川壩子、大理壩子和鳳儀壩子,壩子里面因為有肥沃的土地和充足的灌溉用水,自古以來便聚居了流域內大部分的人口。隨著地質變遷和人為的對自然的改造,各壩子中的湖泊逐漸縮小,今天僅剩洱源的茈碧湖、鄧川的西湖以及洱海,而鳳儀壩子中原有的湖泊則已完全干涸。洱海壩子孕育了南詔大理文明,也是滇西地區人口密度最高的盆地之一。除了有南北分水線之說外,在現實生活中,洱海東西兩岸(當地人稱為“海東”“海西”)的白族人為湖水所割,交通不便,也形成了一定的社會及經濟文化差異。在海東、海西之間交流十分不便的時候,人員和物資的往來幾乎只有輪渡一條路徑,且乘船渡海風險極大,若遇肆虐的風浪則兇多吉少,甚至會葬身魚腹,因而一個區域的人們要和陸上的鄰居關系更為密切。在2000年以前,甚至更早的時候,洱海周邊的各區域在行政上也分屬于不同的縣管理,如海東鎮曾隸屬于賓川縣管理,上關及雙廊地區曾是洱源縣的轄區,20世紀以后,當地政府為了更好地方便管理和保護洱海才將其沿岸涉及的所有鄉鎮納入到大理市的管轄范圍內。
但是在旅游經濟未惠及海東地區之前,該區域僅挖色壩有些許良田,其余則多是山地紅土梯田,這些梯田只適合種耐旱的玉米和果樹。彼時環湖公路尚未貫通,東西兩岸的貿易交流多以船為交通工具。每逢大理、喜洲的集市日,東岸的人們便背些核桃、梨、板栗等山貨,早早到碼頭坐船至西岸趕街,出售以后再買些稻米和生活用品。海西的農民則喜歡乘船去趕海東集和挖色集,海東除了有便宜的火把梨,還有毛色呈紅或黑的“海東豬”,這些豬結實抗病,深受海西農民的喜愛。蒼山出產細膩精致的大理石,海東的玉案山則多出優質的花崗巖,以前海西人家要建新房,首先得雇大船至海東采購用來打基礎的花崗巖。這些花崗巖還是燒制生石灰的好原料,因此海西的生石灰也需至海東采購。據張奮興所著《大理海東風物志》所載,在玉案山南端的向陽灣原有兩處古渡口,一個是塔村渡,古名叫“塔頭渡”,另一個便是向陽渡,古名叫“佛頭渡”。這兩處渡口相距不到1 500米,主要航線是橫渡洱海西至大理城、馬久邑、龍龕,南至下關、鳳儀(今滿江),北至喜洲、沙坪、上關、挖色。此外,航線還可到洱源長育、雙廊、海潮河、江尾,形成以海東為中心的海上交通網絡。這兩個渡口客流量多則可達每日上千人,平日也有百十人。
除本地所產水果、土特產品以外,海東商人還發揮自身的地緣優勢,以人背、肩挑、馬馱等方式從賓川、永勝等地運來花生、紅糖、甘蔗、粉絲、棉花、棉布等貨物,再通過兩個渡口銷往下關、海西,遠則可達保山地區,返程則從海西、下關運回工業品、日用百貨至海東銷售〔13〕。塔村渡與向陽渡據民國《海東志》載,早在明代成化年間便已有村落分布于周邊,但因此處“惟山多田少,厥土赤壤,性干、質燥,春宜于豆麥,秋宜于白谷,它項之谷類雜糧一無所宜耳”,由此古人才“于此正不知幾經躊躇,棲于高山平坦之處,開墾梨園,以補歲需之不足。所幸者有渡口二,向陽一,塔村一,惟日揚帆鼓棹,直奔妙香國售果,歸來盡得免于凍餒”②(民國)李文農纂修:《海東志上》,民國二十一年抄本,楊躍雄田野調查中收集(2018年7月)。。不難看出這兩處渡口給洱海東西兩岸的交往和貿易提供了多少便利。
在婚配方面,因為在以前海西的經濟條件要好于海東,所以很少有海西的姑娘愿意嫁到對岸。按照老人們的說法便是海東缺地少水,日子苦,有時候吃米飯里面還要摻上玉米面。有些海東的女孩經人介紹嫁到海西,因為她們淳樸能干,很招人喜愛。在海東人眼中,對岸的海西人日子好過、見過世面,不過也精打細算,有些還精于算計。
洱海東西兩岸白族人的口音也有所差異。上關、雙廊兩鎮原為洱源縣轄區,其居民的口音也與洱源人的口音類似,而挖色、海東兩鎮以前則為賓川縣所管,所以其居民口音與賓川人的類似。因而海西地區的人們往往聽不懂洱源劍川一帶的白語,但雙廊的白族人卻可以在劍川話和大理話之間游刃有余。
盡管,時至今日,“海東”“海西”的差異不太明顯了,但是因地理、歷史、宗教層面上的理解等所形成的宇宙觀,依然或多或少地體現壩子社會的某些特征。
總之,大理壩子地理地質構造特殊,居于其中的白族先民們便憑借想象力將其生活空間的開拓過程逐漸神秘化,并結合各種文化元素建構出諸多開辟壩區的神話。以排水為核心的開辟神話如《觀音伏羅剎》和《段赤城斬蟒》等為在區域范圍內生活的人們做了合理解釋,也為人們處理水澇災害預留了以宗教方式來消解的空間。對洱海的空間認知中,除了著眼于壩子整體的“水陸平衡”外,在壩子內部,人們也因區域差異,于宗教層面上對其進行空間劃分,這也是白族宇宙觀的一種體現。此外,千百年來,除了有南北分水線之說外,在現實生活中,洱海東、西兩岸的白族人因湖水所割,交通不便,形成了一定的語言、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差異,也從側面反映了壩子社會的諸多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