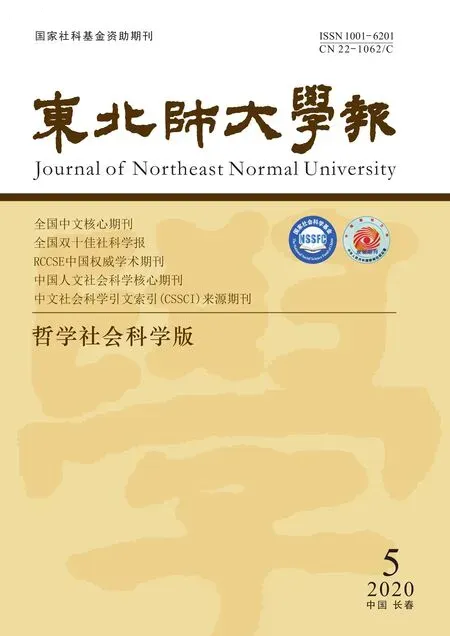試論人的基于本能的認知
史 寧 中
(東北師范大學 數學與統計學院,吉林 長春 130024)
如果一個學科希望具有科學的屬性,那么,這個學科的首要任務就是清晰這個學科所要研究的對象和對象之間的關系,因此,需要建立一些概念表述研究的對象和研究對象之間的關系。這些概念往往是基于現實的,是人抽象的結果,并且能夠得到人們普遍的共識。比如,數學從數量和數量關系中抽象出數的概念,以及數之間的大小關系;從圖形和圖形關系中抽象出點線面的概念,以及點在線上、線在面上這樣的關系。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數學是研究數量關系和空間形式的一門科學。
本文將要討論的問題是,人為什么能夠基于現實抽象出數以及數之間關系、點線面以及點線面之間關系的概念。顯然,這個問題可以拓展為人為什么能夠認知數學,或者更一般地說,人為什么能夠獲得知識。這是一個古老的哲學問題,也是一個現代的認識論問題,至今得不到滿意的答案,正如羅素所說的那樣[1]141:
經驗主義和唯心主義同樣面臨著一個問題,迄今哲學一直沒有找到滿意的解答:那就是,說明我們對自身以外的事物和對我們自己的心靈活動如何有認識的問題。
胡塞爾也表述了類似的論斷[2]:
如所周知,認識論這門學科想要回答這些問題,但至今為止也沒有在科學上清晰地、一致地、決斷地回答這些問題,雖然那些偉大的研究者們在這些問題上已經進行了所有那些思維勞作。
本文將基于人對數學的認知嘗試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回顧爭論的要點所在,在回顧的過程中分析問題的本質,然后基于現代科學的研究成果,針對問題的本質給出結論。數學與哲學的關系眾所周知,因此,本文所得到的結論適用于哲學和認知論。
一、關于概念如何存在的爭論
概念的形成不可能獨立于經驗。但是,經驗是個體的,基于個體經驗形成的概念為什么會得到人們的普遍共識呢?數學得到的結論為什么會具有一般性呢?從哲學形成的那天開始,人們就不厭其煩地討論這個問題。古希臘學者柏拉圖認為人的經驗可以隨著時間、地點,甚至心情的變化而變化,但數學的概念應當是永恒的存在,于是他得到結論,數學概念不可能是經驗的結果[3]:
他們討論的并不是他們所畫的某個特殊的正方形或某個特殊的對角線等等,而是正方形本身,對角線本身。他們所畫的圖形乃是實物,有其水中的影子或影像。…… 是只有用思想才能“看到”的那些實在。…… 幾何學的對象乃是永恒事物,而不是某種有時產生和滅亡的事物。
可是,思想能夠看到的那些實在是如何存在的呢?思想又是如何“看到”那些實在的呢?柏拉圖用洞穴里的人進行比喻。洞穴里的人面向洞穴的墻,人和墻之間沒有其他東西;如果在人的背后升起一團火,就會把人身后事物的影子映射在墻壁上。于是柏拉圖說,人的經驗所面對的東西就是這樣的影子,影子不是真正存在的事物,真正存在的事物在人的背后,只有通過思想才可能看見[4]168-169。柏拉圖的這種述說顯然是荒唐的,但無論如何,柏拉圖強調概念的一般性是必要的,因為幾何學研究必須建立在一般概念上的幾何圖形,而不是那些具體的、因人而異的幾何圖形。不僅數學,其他學科也是如此,涉及的概念必須是一般的,因為普遍的性質和規律必須建立在一般概念之上。
柏拉圖的這種關于理念的述說,直至今日,仍然深刻地影響著人們對數學的認識,人們稱這樣的認識為柏拉圖主義[5]。許多數學家,包括許多哲學家(比如羅素)認為,數學的基本概念,以及建立在基本概念上的公式和定理是獨立于人而存在的,因為只有這樣的存在才可能是永恒的。比如,1+2=3這樣的結論就是與經驗無關的永恒的存在,這樣的結論是通過觀察得到的;再比如,行星運動的軌跡是個橢圓這個結論也是客觀的存在,開普勒的工作只是發現了這個存在。因此,數學家的工作就是觀測或者發現這樣的存在[6-7]。
亞里士多德不同意柏拉圖的觀點,在著作《形而上學》中對柏拉圖的理念進行了反駁[8]50-51[9]125:如果按照柏拉圖的觀點,那些不能被察覺到的東西,諸如未知的東西、錯誤的東西、消失的東西也都應當具有理念,于是,不能被察覺到的如此眾多的東西必然要淹沒那些能夠被察覺到的具體的存在,而后者才是認識的原始材料。于是提出質疑:事情是不是被柏拉圖搞得過分復雜了呢?亞里士多德進一步從邏輯上反駁了柏拉圖,然后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一般概念不是客觀的存在。任何一個稱謂,只要這個稱謂適用于一類事物,這個稱謂就是概念,這些概念本身不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客觀存在,它們是名而不是實。
可是,不存在的概念怎么可能被人感知呢?人們又怎么可能把知識建立在不存在的東西之上呢?亞里士多德提出了著名的共相理論[4]213。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共相,是指一些事物所共同擁有的那些東西,借助共相人們可以對事物進行區別,把具有共相的事物歸為一類,并且對這類事物建立專門的稱謂,這就是概念,建立概念的方法是抽象。亞里士多德以數學為例闡述[8]185,246-247:
例如,數學家用抽象的方法對事物進行研究,去掉感性的東西諸如輕重、軟硬、冷熱,剩下的只有數量和關系,而各種規定都是針對數量和關系的規定。
這樣,概念就不是現實的存在,而是人抽象出來的東西。現實世界中,數字2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那些與2對應的兩匹馬、兩個蘋果。也就是說,一般概念不是特殊事物的稱謂,一般概念存在于特殊事物之中。雖然距今兩千多年了,但我們仍然有必要說明亞里士多德思考的不足,因為這些不足恰恰是“名實之爭”得以持續的緣由。這就是,許多數學概念并不都是直接從現實世界的具體存在中抽象出來的,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數學家在創造數學的過程中并不顧忌現實的存在,比如,四元數以及與四元數有關的麥克斯韋方程、高維球面以及與高維球面有關的龐加萊猜想。這些概念以及建立在這些概念上的結論,至少在創造的那個時候,并沒有對應現實的具體存在。
無論如何,因為這兩位哲人關于概念如何存在的論述,特別是由于亞里士多德對柏拉圖的反駁,從古希臘時代開始引發了曠日持久的“名實之爭”,這個爭論吸引了后世諸多學者,延續至今依然眾說紛紜,正如艾耶爾所說[10]:
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在公元前4世紀提出的那些問題,至今仍然被爭論不休。而且所有這一大段時間內的工作依然沒有使我們更接近于找出一個哪怕只是大多數當代哲學家能接受的答案。
也正因為這樣的曠日持久的爭論,使得“如此截然區分現象與實在確實一直是西方哲學中一個相當不尋常的特征”。但事實上,在長久爭論的過程中,爭論的焦點發生了演變。
二、關于概念如何獲得的爭論
文藝復興以后,問題爭論的焦點發生了演變,從概念如何存在演變為概念如何獲得。這個轉換是從英國哲學家培根和法國哲學家笛卡兒開始的,這個轉換激發了人們的科學精神。
培根毫不留情地批評古希臘的思考原則,在《偉大的復興》的序中論述[9]340-345,古希臘人創造出來的那些方法可以用來討論知識,卻不能用來創造知識;可以用來討論真理,卻不能用來發現真理。培根苛刻地批評了亞里士多德所創造的基于演繹的邏輯學[11]:三段論不能用于發現新的科學,他用他的邏輯毀壞了自然科學。于是,為了科學發展的需要,培根要“給人類的心靈和理智介紹一種更完善的方法,從而使人們能夠達到自然界那些更遙遠、更隱蔽的地方”,培根所說的更加完善的方法就是他所提倡的現代歸納推理,這是一種基于經驗的推理方法。
可能是因為寫作形式和論證方法的原因,許多現代學者認為笛卡兒步亞里士多德之后塵[12],但在本質上,笛卡兒倡導的是柏拉圖。笛卡兒把“我思故我在”作為哲學思考的第一原則,認為只有具有思想的我才是真正的存在,這個存在不依賴包括身體在內的任何有形的東西,這個存在的載體是心靈,于是笛卡爾強調心靈的作用[13]:
我已經明了,在真正的意義上,即便是形體的認識也不是因為感官或想象力,而是因為理智;它之所以被認識不是因為被看見或者被摸到,而是因為被思想所理解或了解。這樣就很明顯,對于我來說,沒有一件東西比我的心靈更容易認識了。
這樣,從培根和笛卡爾開始,西方哲學開始關注概念是如何獲得的,如杜蘭特所說[14]:從此便開始了一場關于認識論的偉大游戲。
首先是洛克反駁笛卡兒。洛克繼承并且發展了培根的思想,為了進一步強調經驗的重要性,他創造了人的知識完全源于經驗的學說,因此被稱為經驗主義的奠基人。在著作《人類理智論》中,洛克提出了有名的白板論[15]68:
假定心靈像我們說的那樣是一個白板(1)洛克原著中的white paper源于拉丁文Tabula Rasa,如下面萊布尼茨所標明。這個詞出自于亞里士多德的著作《論靈魂》,意思為“未真正開始寫字的書板”,可以翻譯為白板(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張強教授的建議)。,上面沒有任何記號,沒有任何觀念。那么,心靈是怎樣得到那些觀念的呢?……我用一句話來答復這個問題:是從經驗得來。我們的全部知識建立在經驗之上,知識歸根到底都是源于經驗的。
可是,心靈作為一無所有的白板,怎么可能從經驗中獲得知識呢?為此,基于獲得的形式,洛克把人的知識分為兩類:一類是直覺知識,一類是理性知識。所謂直覺知識是指那些清晰可靠的知識,這種知識的獲得只需要借助直覺,比如幾何圖形的認識;理性知識是一類間接判斷的知識,獲得的過程中需要插入一些諸如推理、計算之類的觀念,比如三角形內角和與180度之間關系的判斷。雖然理性知識的獲得不是直接憑借直覺,但判斷知識獲得過程中所需要插入的觀念借助的依然是直覺,這樣,洛克就得到結論,人的知識是基于經驗憑借直覺獲得的[15]520-522。
洛克強調了經驗的重要,卻忽略了人的活力,于是,與牛頓同時發明了微積分、充滿活力的萊布尼茨也參與到這場爭論之中。萊布尼茨不同意洛克的觀點,在《人類理智新論》的序言中說[16]:
對于一些相當重要的問題我們之間是有差別的。問題就是:心靈本身是否像亞里士多德和《人類理智論》的作者所說的那樣,完完全全是空白的,好像一塊還沒有寫上任何字跡的白板(Tabula Rasa),心靈上留下的任何痕跡都是通過感覺和經驗得來的。
萊布尼茨認為,雖然人的感覺是重要的,但是,感覺的對象是具體的事物,具體的事物不足以提供全部認識,更不能保證真理的普遍與必然。比如,數學的任何命題都不是具體的舉例,這些命題的證明只能依賴天賦的內在原則。因此,人的認識不單純依賴感覺的經驗,而要探究事物發生的原因,探尋事物發展的規律,這就是天賦的內在原則。
于是,萊布尼茨理直氣壯地反問:難道我們的心靈就這樣空虛,除了外來的影像就一無所有?萊布尼茨發明“前定和諧”的理論,不僅強調笛卡兒所說的心靈的作用,并且認為心靈與身體融為一體,相信人的心靈不是空虛的,人的心靈具有某種天賦的東西。這樣,萊布尼茨就強調了人的主觀能動性,雖然萊布尼茨被歸類于唯心主義者,或許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唯物主義的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寫道[17]:你知道,我是佩服萊布尼茨的。
休謨堅信洛克的經驗主義,利用他所創立的因果關系學說,論證一切知識的獲得只能通過經驗。他的著作《人性論》的簡縮本《人類理解研究》產生了很大影響,開篇不久休謨就限制了精神的作用,認為人的創造只不過是把感官和經驗獲得的材料進行簡單加工[18]。雖然休謨對歸納推理的發展做出過貢獻,但休謨解釋不清其中的原理(2)至今為止也難解釋清楚,于是羅素認為:“歸納也許是整個知識理論中最難的問題。”參見:《哲學大綱》,羅素著,黃翔譯,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11頁。:一方面基于因果關系的認知不能通過演繹推理獲得,否則歸納推理將是演繹推理的特例;另一方面,完全憑借經驗無法論證歸納推理的合理性,否則將會陷入通過經驗論證經驗的循環往復。休謨最終陷入不可知論。正如羅素評論的那樣[1]196:他(休謨)把洛克和貝克萊的經驗主義哲學發展到了它的邏輯終局,由于把這種哲學做得自相一致,使它成了難以相信的東西。
據說,是休謨的簡縮本把康德從“獨斷的睡夢”中喚醒過來[1]197,247,寫出巨著《純粹理性批判》。正如這部巨著的序言所說的那樣,康德認為需要論證的問題是,脫離一切經驗,人的知性和理性還是否存在認知,能夠認知什么。康德論證了經驗之外純粹理性的可能,強調人的精神的作用,也就是純粹理性的作用。為了論證純粹理性脫離經驗的可能,康德區分了兩類不同的直觀:一類是基于經驗的,稱之為經驗直觀;一類是基于先驗的,稱之為純粹直觀。經驗主義學者也強調經驗直觀,不需更多解釋;對于純粹直觀,康德是這樣述說的(3)參見《純粹理性批判》,康德著,鄧曉芒譯,楊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6頁。“直觀”對應的英文是intuition,德語原來的單詞是anschauung,字面講的是“觀看”“觀察”的意思,參見《西方哲學史·下》,羅素著,馬元德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251頁。:
我把一切在其中找不到任何屬于感覺的東西的表象稱之為純粹的(在先驗的理解中)。因此,一般感性直觀的純粹形式將會先天地在內心中被找到,在這種純粹形式中,現象的一切雜多通過某種關系而得到直觀。感性的這種純粹形式本身也叫作純粹直觀。
對于個體的人,都可能會感覺不到許多東西;可是,對于所有的人,存在整體感覺不到的東西嗎?如果存在,這樣的東西是什么呢?康德認為這樣的東西是存在的,因為這樣的存在針對所有的人,因此這樣的存在不依賴人的經驗,這就是事物賴以存在的空間和時間。空間和時間概念的建立是由于純粹直觀而不是經驗直觀,空間和時間是人用來整理感覺的工具;知識的獲得并不單純依賴經驗直觀,其中有一部分是通過人的先天存在的純粹直觀獲得的。這樣,康德就論證了純粹理性的可能。
自康德以后,許多哲學家,甚至包括許多科學家和數學家,開始更加理性地研究認知問題,發表了大量的真知灼見,使得有關概念越來越繁多,論證方法越來越深奧。但是,這些研究或多或少都受到康德的影響,因為直到今日為止,康德的基本理論仍然是所有成熟哲學的原理[14]263。也正因為如此,所有的這些研究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那就是,這些研究都是基于思辨的,關注的是那些形而上的東西,或者更確切地說,關注的是那些建立在觀念之上的東西(4)如胡塞爾所說,我們必須做如下的理解:我們始終停留在純粹現象學的領域以內,并且不去思考與事物經驗的身體和自然的聯系,參見《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胡塞爾著,倪梁康譯,商務印書館,2002年,第34-35頁。。
事實上,單純從思辨的角度思考,是很難把“如何有認識”這個問題論述清楚的。這樣的研究存在的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從“人本身”入手展開思考,沒有關注“人如何有認識”這樣的最為基本的、也是最為本質的問題。
三、人的本能對于認知的作用
與西方哲學區分現象與實在的特征不同,中國古代哲學的特征是把人融入思維的系統之中。我們從《大學》入手分析這個特征。因為科舉的原因,《大學》的述說在中國深入人心,對中國哲學,以及中國人思維方法的影響非常大,以至于胡適認為[19]:從11世紀到辛亥革命,中國哲學的全部歷史都集中在這個作者不詳的小書的解釋上了。《大學》的這段話在中國家喻戶曉: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修身,修身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這就是耳熟能詳的八條目。朱熹認為人的認知過程就是“物格而后知至”,簡稱為“格物致知”,在《四書集注》中給出詳盡解釋,我們用現代語言把朱熹的解釋表述如下[20]:
人的心靈是具有認知能力的,天下的事物也都是有一定道理的,只是這些道理沒有被徹底認識時,人的認知是有限的。于是《大學》一開始就教人接觸天下的事物,從已有的知識出發進行深入地、不間斷地探究。長期用功之后,如有一天豁然貫通,就可以把事物由表及里、由粗到細地認識清楚,同時自己的心靈也會豁然開朗,再無蔽塞。這就叫格物,這就叫知之至。
關于認知過程,朱熹的這段論述不亞于三百多年以后的培根和笛卡爾。有所不同的是,朱熹論述的事物主要是與人有關的事情(5)原文為:“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參見《四書集注》第6頁。:“物”相當于事,“格物”就是窮盡事物的道理。因此,朱熹所說的道理主要是指做人的道理以及人做事的道理。雖然王陽明不贊成朱熹的觀點,明確地說“天下之物本無格者,其格物之功只有身心上做”,并且用“頓悟”替代朱熹的“漸悟”。但是,王陽明對“物”的理解與朱熹是一樣的(6)原文為:“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參見《王陽明全集·下》,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72頁。:物就是事,有了意念就可能會成事,而有意念的事就是物。
因此,就認識論而言,中國古代先哲總是會把思考的人放到思考的事物中,使得主客觀沒有明顯界限。這樣就形成了與西方哲學的明顯差異[21]:關注的是類與類的區別,而不是特殊與一般的區別;對事物的認識強調是感悟,而不是理解。也正因為如此,中國古代哲學不可能形成諸如三段論那樣的從一般出發的演繹推理的論證形式,也不會像西方哲學那樣思考如何區分現象與實在這樣的問題。
但是,完全不把人放入思維的過程中,或者只是用精神或心靈作為人的替代也是不可以的,特別是對如何有認識的研究。因為認識的問題歸根結底是人的認識,對數學的認知是人對數學的認知。可惜的是,至今為止關于認知何以可能的研究都沒有從人的角度進行研究,更確切地說,都沒有從人的本能的角度出發探討康德所說的“純粹直觀”或者羅素所說的“心靈活動”到底是什么。或許,這樣的探討只有在科學發展到一定程度的今天才可能開始,我們嘗試討論這個問題。
20世紀的末葉,生物學出現了一個被稱為表觀遺傳學的新興學科,雖然所有的研究還只是處于基因表達的階段,但可以宏觀認為,這個學科的研究基于這樣一個基本事實:雖然每一個生物體都攜帶了從祖先那里傳遞下來的遺傳基因,但是,如果得不到后天的適時并且適當的刺激,有些遺傳基因將得不到充分表達。這個基本事實可以延伸到人,如果在孩提時代不創造環境讓孩子練習說話,那么長大以后再學習就困難了。這樣,表觀遺傳學就明確告訴我們,人的經驗是重要,但是,人的經驗不是從“白板”開始的;后天有目的的經驗過程,能夠激活人自身攜帶的、先驗的(或者說祖先經驗過的)遺傳基因,使得這些遺傳基因得到充分表達。
進入21世紀以來,腦科學和認知神經科學得到迅猛發展,全力研究人腦關于感知、記憶、聯想、判斷、決策等與行為科學有關的生物物理學機理和生物化學機理,得到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成果與人腦的構造有關,也與遺傳基因有關。腦科學、認知神經科學,以及表觀遺傳學的研究成果,必然會促使心理學,甚至包括教育學這樣的學科走向科學,成為這些學科的立論基礎。但是,對于任何一門學科,立論基礎都不可能是其他學科直接給予的,需要這些學科根據學科自身的特征進行加工,并且,這樣的加工過程必將與哲學或者認識論有關。
對于哲學或者認識論,上述表觀遺傳學、腦科學和認知神經科學的發展,至少提供了兩個方面的啟迪:一方面告訴我們,雖然知識的來源不可能獨立于經驗,但人的認識不是憑空的,人之所以可以認知,是因為人具有先天的以大腦和神經為核心的構造物,這些構造物攜帶著從祖先那里繼承下來的遺傳基因;另一方面告訴我們,完全憑借對物的研究不可能得到精神的全貌,需要哲學或認識論對科學研究的成果進行必要的歸納與提升。或許可以認為,科學的研究越是走向深入,哲學的研究就應當越是走向本質,這是因為,科學研究越是走向深入則意味著研究越來越細化,恰恰相反,哲學研究越是走向本質則意味著研究越來越概括;哲學的研究要借鑒科學研究的成果,科學的研究要尋求哲學研究的指引。哲學從思辨的角度探究世界的本質,科學從驗證的角度探究世界的本源,哲學與科學不是對立的,哲學與科學相輔相成,共同成長。
這樣,表觀遺傳學、腦科學和認知神經科學的研究就告訴我們,“人如何有認知”這樣的最為基本的哲學問題是可以,并且是必須研究的。這就意味著,思維的起點是存在的,這個起點存在于人的本能,這個本能是地球生物四十多億年進化的結果,這個結果是依賴遺傳基因傳承下來的,是憑借大腦和神經的活動激活的,這個激活依賴的是人后天的經驗。
四、人的認知數學的本能
雖然與哲學一樣,數學研究的對象也是抽象了的東西,但二者之間卻有著本質的區別,正如康德所說的那樣[22]:哲學知識只是在普遍中考察特殊,而數學知識則是在特殊中,甚至在個別中考察普遍。
我們可以這樣把握數學概念產生的思維過程:形成是從特殊開始的,思維是從直觀開始的。事物的存在是客觀的原始材料,這些原始材料必須經過人的思維的加工,才有可能成為數學研究的對象。這個思維加工就是數學抽象,這個思維加工的過程是從人的直觀開始的。
那么,人的數學直觀的思維基礎是什么呢?或者更確切地說,人能夠進行數學抽象的思維前提是什么呢?事實上,數學抽象的思維前提是人所具有的兩個先天本能,這就是:對數量多少的感知和對距離遠近的感知。從這兩個先天本能出發,通過人所特有的兩個基本思維能力[23]:抽象能力和想象能力,使得人的數學抽象成為可能,進而使得人的數學認知成為可能。我們分別討論這兩個先天本能以及這兩個先天本能對人的數學認知的作用。
對數量多少的感知。從遠古時代開始,因為日常生活和生產實踐的需要,人們創造出表達事物量多少的語言,在中國,這個創造可以追溯到殷商甲骨文。雖然這樣的語言表述中含有數字,但所有的表述都有具體背景,表現于數字的后綴名詞。稱這種有實際背景的、關于量多少的、具有后綴名詞的表達為數量。數是對數量的抽象,是一種符號表達。在形式上,數的符號表達舍去了數量的后綴名詞;在實質上,數的符號表達舍去了事物的現實背景。這樣,用符號表達的數就具有了一般性,比如2這個符號既能表達兩匹馬的數量,也能表達兩個蘋果的數量。
對于數學而言,用符號表達研究對象不是本質的,重要的是建立這些研究對象之間的關系,因為只有通過研究對象之間的關系,才可能分析清楚研究對象的性質,才可能發現研究對象的規律。因為數是對數量的抽象,數的關系必然涉及數量的關系,因此,我們需要探討數量關系的本質。
可以籠統地認為,動物能夠分辨清楚的東西往往就是本質的東西。動物能夠分辨數量的多少,來了一只狼,一條狗或許敢于抗衡,如果來了一群狼,這條狗就會逃跑,狗能分辨數量的多少。因此,數量關系的本質是多與少。顯然,對數量多少的感知也是人的本能,孩子對于數量多少的感知是本能,而不是教育的結果。基于這樣的本能,再加上人所特有的抽象能力和想象能力,人就對數量和數量關系一并抽象,得到自然數和自然數的大小關系。基于這樣的大小關系,就可以得到自然數的加法:加一個自然數比原來的數大。這樣,代數學的發展就有了根基:通過加法的逆運算得到減法,并且把數域由自然數擴充到整數;通過加法的簡便運算得到乘法,通過乘法的逆運算得到除法,并且把數域由整數擴充到有理數;通過極限運算定義實數,并且把數域由有理數擴充到實數。如此這般,一個嚴謹的代數系統就逐漸建立起來了。在這樣的過程中,人得到了關于代數學的認知。
對于距離遠近的感知。數學另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是幾何學。幾何學研究空間圖形,包括物體的形狀,也包括物體運動的軌跡,圖形是人們通過數學認識世界的原始材料。圖形比數量更為生動直觀,因此人們對圖形的抽象早于對數量的抽象。比如,西班牙阿爾塔米拉洞穴的巖畫、印度拉科杰瓦爾巖畫、中國賀蘭山巖畫,記錄了一萬年前人類生活和狩獵的場景。
人對圖形抽象的前提是對距離遠近的感知,這也是一種本能,動物也具有這樣的本能,獵豹的捕食一定會奔跑在最短路徑上。對于具有抽象能力和想象能力的人而言,從對距離遠近感知的本能出發,可以派生出對物體大小的判斷,派生出對線段長短的判斷。
幾何學的本質在于度量,度量的本質在于線段的長短,因為基于線段的長短可以規定度量單位。這樣,基于人的對距離遠近感知的本能,以及抽象能力和想象能力這兩個特殊的能力,就可以從線段長度出發,得到面積、體積、角度的度量;得到全等、相似、垂直、平行這樣的關系。如此這般,一個嚴謹的幾何系統就逐漸建立起來了。在這樣的過程中,人得到了關于幾何學的認知。
更為重要的是,無論是對數量多少的感知,還是對距離遠近的感知,都是對大小關系的感知,因此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這就意味著,基于兩種本能發展起來的關于數學的認知可以貫通,可以融合。也正因為如此,代數學與幾何學得到的結論不悖,使得現代數學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此外,大小關系具有傳遞性,而傳遞性又是數學推理的邏輯基礎[24]。
綜上所述,數學認知的先驗起點不僅存在,并且對所有的人是共同的。正是因為人們從共同的思維起點出發,遵循相同的思維邏輯,去認識相同的自然客體,因此,才可能得到大體一致的數學認知。也正是因為這樣的大體一致,才使得數學得以產生和發展,使得數學的傳承成為可能。
人之所以會進化出這樣的本能和能力,或許,如恩格斯所說的那樣[25]:
我們的主觀的思維和客觀的世界服從于同樣的規律,因而兩者在自己的結果中不能相互矛盾,而必須彼此一致,這個事實絕對地統治著我們的整個理論思維,它是我們的理論思維的不自覺的和無條件的前提。
數量的多少和距離的遠近,是自然界事物“量化”的根本,因此是人通過數學認識、理解和表達世界的根本。我們生活在地球上,我們是“這個”世界的產物,因此,正確的思維就是指那些能夠合同于“這個”世界的思維,能夠合同于“這個”世界已經存在了的規律的思維。或者可以反過來說,自然界只能依照自然界自身的規律進行自然選擇,這就是達爾文所創立的進化論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