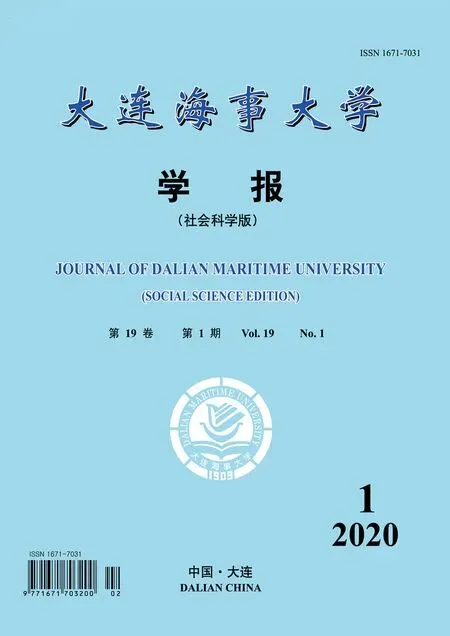論家族共產制下私產與個人主體
谷佳慧
(北京大學 法學院,北京 100871)
現代學者在討論中國傳統社會關系時,已經默契地將“家”認定為基本元素。“家”向外延伸,是包括戶婚田土等各種社會交往行為的主體;向內部深入,是家庭成員共同服務的對象,幾乎所有的勞動收入都要貢獻于家族,日常支出也從家產中提取。這種家庭生活模式被滋賀秀三先生稱為同居共財的家族共產制,他認為這是解讀中國傳統家族關系的基礎,亦是家族法的原理所在。在家族共產制度下,每個人都是家族的一員,作為家族財產的共有者,似乎并不存在脫離家族的個人財產,也沒有獨立的財產使用權。俞江教授在《論分家習慣與家的整體性——對滋賀秀三〈中國家族法原理〉的批評》一文中提出,“在中國古代社會,不可想象將某項財產歸入某個生物性的個人的名下”,“雖然存在著少量的個人支配或專有的現象,但當財產進入到流通領域時,嚴格地說,這些財產行為只有以家的名義才能成立或展開,而一切以個人名義的財產處分行為都是可爭議的”。[1]59俞江教授雖然承認極少數私人財產的現象,但從根本上否定了傳統社會中“私產”的存在。滋賀秀三先生在《中國家族法原理》一書中則用“家族成員的特有財產”來代指家產之外的私產。在家族共產制下,傳統社會的財產權與今日民法討論的“所有權”有很大不同,但在龐大家族體系下艱難生存的“私產”卻在一定程度上與物權法下的“所有權”契合。從所有權與個體地位關聯角度出發,若有“私產”的存在,則大大提高了傳統社會中個人主體的存在意義。基于此,本文將通過闡述古代產權制度,辨析傳統社會中是否存在具有“所有權”形態的“私產”,進而思考在討論古代民事法律制度時,是否必須一切以“家”而非“個人”為起點。
一、家族共產制中“產權”與民法“所有權”
滋賀秀三先生將“家族共產制”作為其名著《中國家族法原理》一書論述的基礎,認為“家族共產”是一切家族活動之所以呈現出如此面貌的基礎。所謂家族共產制,就是家族靠一個錢袋來生活,各個人的勤勞所得全部湊集到這個錢袋里,每個人的生計也全部由這個共同的錢袋供給,從而財產作為共同的家產得到保持。這樣的生活模式,貫穿在清末近代化開始前的整個傳統中國社會。實際上,連家的概念規定也可以說是那樣的。[2]12在這種生活樣式下,家產可以成為財產,但每個家庭成員甚至包括家父都不能成為所有權人。因為按照民法共有說,每個家庭成員都是共同共有人;如果不考慮家庭內部共有說,僅以“家”作為權利主體,每個家庭成員都不是家產的所有人,都不可作為主體來看待,只有類似于法人的“家”財稅所有權人。而這種狀態下的家產即是共財,具有如下特點:第一,每個人勞動所得都歸入總的單一會計,成為“家計”;第二,同居共財的家庭成員的必要生活支出,由“家計”提供;第三,經過生產、生活支出后的“家計”剩余財產,成為整個家族的共同資產進行儲蓄。[3]按照仁井田升先生和滋賀秀三先生的觀點,除了家父,其他家庭成員都沒有處分家產的權利,只有被動接受被分割的家產以及享有使用家產進行增殖的權利。按照俞江教授的觀點,甚至連家父都沒有處分家產的權利,家產不屬于任何人,只屬于“家”支配。學界基本將家族以及財產看作是理解古代傳統社會的基礎,“家”、“國”關聯是我國傳統社會“差序格局”宏觀構建的關鍵。[4]許多文獻記錄也支持這一觀點。如《禮記·曲禮上》中記載,“父母在不有私財”;《禮記·坊記》有云,“父母在不敢私其財”;司馬光《涑水家儀》指出,“凡為人子者,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收入,盡歸之父母,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因此,家族共產情況下,產權實際是被割裂為處分權與部分使用權,而現有研究所討論的,更多是處分權層面的“產權”。
然而,判斷財產權利是否存在,不能僅僅靠處分權判斷,所有權也占有重要地位。廣義上家產的所有權毋庸置疑屬于全體家族,但因其所有者是復雜的家族共同體,這種所有權的性質也與今天我們理解的所有權有極大不同。首先,雖然家產的產權對外是“家”獨有,但對內是家族成員共有。[4]而物權法下的所有權,指的是包含占有、使用、處分、收益的內容和表現,同時還有排除他人干涉的法律之力,即有對標的物的管理權能,以及從標的物收益的權能。[5]家族下的“共有”不同于今日的、有條件的“按份共有”或“共同共有”,對于家庭成員來說,“分中有合也有繼”強調家產的不可分割性,以求保持其完整性。這與一直以來的嫡長子繼承制一脈相承,奠定了傳統社會的倫理基礎。其次,家產的產權并非“一物一權”,而是“一物眾權”,所有家族成員都是所有權人,卻同時對家產享有不同權益。例如家長對家產享有直接管理權,老人基于贍養而擁有間接管理權能,后代子孫基于血脈沿襲和產生的期待管理權能等。[6]這些權利是同一層級上的權能,構成了家產產權的一物多權。而現代所有權雖然存在所有權下的用益物權、擔保物權等例外,但指向的對象卻是同一的,而非對共同體內單一個體的割裂性劃分。這兩點區別造成了家族共產下“產權”與現代“所有權”的本質不同,也引發了今日學者研究傳統財產權的一個重要視角:傳統社會只能以“家”為出發點進行民事法律關系分析,不存在個人民事權利,也就不存在個人財產權利或者說討論個人財產權是無意義的。這種視角的邏輯起點正是基于對家族共有下“產權”的理解,而非對當代“所有權”的理解,這勢必造成了在“產權”理論下,不存在個人私產的判斷。
從“家”的角度來看,家族共產的財產權的理解是完備的:財產由“家”獨立并始終享有,分家后,再由新的“家”主體承繼。然而,即便觀察傳統社會的歷史發展都是以“家”為出發點來看其社會活動的進行,人始終是社會最基本的元素,任何活動都無法忽視人的主觀能動性,每個“家”行為都是人行為的組成。因此,直接拋棄“個人”而選擇“家”作為傳統社會的討論基礎,有合理之處,卻略有偏頗。在家族單位之下,每個人的個人行為,都可能對家族財產甚至國家財產產生深遠影響;具體財產使用和繼承運作到每個人身上,也都有截然不同的反應和效果。學者們雖然肯定家在研究傳統社會財產權方面的重大意義,但也有所列舉,承認個人財產并非全然不存在,可以找尋到私產在傳統社會的歷史痕跡。這種痕跡往往是生存于大“家”概念的陰影下,其在財產法律發展當中的意義被忽略了。而以純粹現代所有權觀點來看,家族共產下私產的權能并不完善,但若以傳統“產權”觀點來分析,辯證地加上“個人”作為主體視角,就會發現在家族共產之下,有一些不能為家產所容納的財產,實際上是個人私產在傳統社會的存在模式。
二、家族成員“特有財產”與“私產”
通過上文對家產產權與典型所有權的比較,否定了傳統家產成為個人權利客體的可能性。然而在傳統社會經濟關系中,除去家族共產,社會財產中依然有特殊的財產存在。這些未被歸納為家產的財產,實際上是本文所討論的“私產”的直接來源。對于這類財產,滋賀秀三先生在《中國家族法原理》中有極好的歸納,并命名為“家族成員的特有財產”。但滋賀秀三先生寫作時似乎并未意圖將這類財產與個人權利做聯系性的分析,因此也未定之以“私產”或“個人財產”的名稱。不過若從前文所論述的古代“產權”理論來判定,會發現其書中描述的“特有財產”與“私有財產”有極其相似之處。
(一)個人特殊身份所得財產
個人特殊身份指的是朝廷官員、軍人的職業身份,或者是成為義子、贅婿后的親屬身份。首先,對于外出為官取得的官俸,可以認定為自己取得的報酬而不計入家產。如《中國家族法原理》中提到的金元和唐代規定:金元時代立法有,應分家財,若因官及隨軍,或妻家所得財物,不在均分之限;唐戶令分條,其父祖永業田及賜田亦不均分。[2]981這種官俸、軍俸或永業田,只能為自己的子孫繼承,不被納入到整個家族的家產中,不參與分家時的分配。其次,成為義子、贅婿后,從養父家或妻子家獲得的財產,不再參與原親緣家庭的財產分配中。而這種從養父家庭或妻子家庭獲得的財產,成為一種贈予,一種特有財產。[2]542如《民事習慣調查報告錄》中有記載:河南襄城等縣習慣,凡義子,無論自幼抱養,或長大后收養者,均不準繼嗣,但許與繼子俵分繼產,其分給成數,各縣不同[7]1049;湖北省漢陽等縣習慣,婦招夫養老或撫子者,其前夫之財產均得歸后夫承受,其前、后夫均有財產者,即由后夫之子平均分析[7]805。《大清律例·戶婚》規定,若義男女婿為所后之親喜悅者,聽其相為依倚,不許繼子并本生父母用計逼逐,仍酌分給財產;其招婿養老者,仍立同宗應繼者一人承奉繼祭祀,家產均分。因為家族財產與祭祀香火相連,享有繼承權意味著享有祭祀先祖的權利,[8]顯然義子、贅婿并不在其中。因此這種財產與原有的家族共產割裂,形成了新的財產權,對于義子、贅婿而言,擁有絕對的所有權。
(二)個人其他勞動所得和無償所得財產
這里討論的其他勞動所得,是指不依靠家族財產資源增殖的財產,比如,不依靠家族提供原始資本而獨自外出經商所得。而無償所得僅指“白白從別人那兒得到東西”,例如過年時親戚、親友給的禮金。這兩種所得之所以被滋賀秀三先生列為“特有財產”,在于并沒有使用家族的資本。在家族共產制下,個人的時間和勞動力自然屬于家族,但在傳統社會的學而優則仕的價值觀下,外出為官貢獻的勞動力價值顯然大于在家務農的價值。而作為農業社會的古代中國,家族的最大產業就是田地,經商不使用家族田地,自然也不能算做家族的收益。
(三)夫妻共有財產
妻之隨嫁之產有別于夫家之財產,但根據夫妻一體原則,這部分財產可視為獨立于家族財產的獨立夫妻共有財產。脂粉地、妝奩田都是典型的妻子隨嫁財產,夫妻二人可以不經夫家家長同意,出典甚至交易這些土地。這些田地的處置可以由丈夫來執行,但必須經過妻子或妻子家長的同意,這一點,不同地區風俗不同,《中國家族法原理》也有不同描述。但總體來說,還是在一方所有人同意下可以自由支配的財產。而一旦雙方離婚,如果是妻子的錯誤,這些隨嫁財產將成為丈夫的個人財產,如果是丈夫的錯誤,則將回到妻子個人的名下。
(四)婦女的個人財產
在夫妻一體原則下,女性本來沒有自己獨立的財產權與繼承權,而且婦女往往無法實現外出為官或經商,沒有額外收入。《禮記·內則》有云:“子婦無私貨,無私蓄,無私器,無私假,無私與。”但出嫁之時所攜帶的純個人用品、本人勞動的工錢等可以成為個人財產,成為女性私產的來源。第一,婦女出嫁時帶來的首飾和日常生活用品,即一般意義上的“嫁妝”,為女性所獨有。這些財產往往來自于娘家的贈予,將伴隨婦女未來生活相當長時間。唐宋以來,嫁妝一般稱為“妻家所得之財”、“隨嫁妝奩”、“隨嫁田”等,[9]根據法律規定,嫁妝不在分家財產之內,最終由女兒或兒媳繼承。例如,元代法律規定,“官及隨軍或妻所得財物”為私有財產,當與兄弟分家之時,不算做家族共有的財產范圍之內。第二,婦女勞動所得的工錢。在農業閑暇以及家務閑暇之余做工所得報酬,可以成為個人獨立的財產。當然,這些閑暇的勞動不可以與正規家務或農務相沖突,否則正規勞動所得還應屬于家庭。第三是婦女錢財的收益。例如,私房錢外借的利息等。[2]544-550
列舉個人財產的存在,不僅在于可以證明家產外依舊有私產的生存空間,更重要的是,私產是行使個人權利的基礎,只有存在私產,才有建立其之上的有效的個人財產行為,從而產生個人財產性權利。雖然這些財產的數量與龐大的家產相比微不足道,但日常民事行為活動并非全然是大宗的土地買賣、每月的家用支出,也有很多容易為人們忽視的瑣碎而小額的物品使用和財物易換,而其中正充斥著許多的私產。例如,在物質并不發達的傳統社會,一般人家的許多家設日用都是長時間使用的,而這些又有很大一部分來自于妻子的隨嫁。這當然可以算作夫妻甚至妻子個人財產,脫離于家產之外。但其之上的使用權對日常生活來說,又是極為重要的。因此,私產或特有財產的存在并不是極少數或偶然現象,只是太容易被掩蓋在龐大的家產之下。
三、被“中斷”私產
事實上,很多認為古代社會沒有私產的學者,做出判斷的重點并非是否認上節中“特有財產”的存在,而是認為這些財產并沒有形成完整的私產模式,當私產所有者一旦獨立成戶,成為新的家長,其所擁有的私產又成為新的家產。這種私產的中斷,使得私產喪失了成為獨立財產的可能性,又回歸到家族財產之中。
(一)私產如何被“中斷”
最典型的私產中斷,是私人財產所有者一旦組成了新的家庭、成為家長,他的財產就成為新家的家產、公財。例如,根據特殊勞動所得私產者,雖然在外為官或經商獲得了脫離家族的財產,但他一旦要成家立業,這時,私產就成為其家產的一部分,成為日后要分割給子孫的家底,失去了隨意使用的私有價值。對于依據特殊身份取得財產的人,如被寡婦招贅的男子,如果夫妻雙方意見不合,可以離去,且“往往有向寡婦要求分割財產的情事”。這種情況下獲得的財產,當然屬于個人財產,但如果該男子再次成婚,這份私產又會變成家產。[1]同樣,因為特殊身份獲得的“長子田”、“長孫田”,或者前文提到的養子從親生父母處獲得的財產,一旦真正取得,又會成為其所在家或“房”的家產。總之,這種私產到家產的回歸被認為私產失去了其特有的意義,財產的流動成為一個循環,截斷了個人所有權,財產權的主體最終還是要變成“家”。
其次,夫妻共有財產也不被認為是私產。雖然法律已有明確規定,妻子隨嫁的財產可以不納入大家族的財產中,分家后妻子帶來的財產也可以不算做家產,但因規定“婦人財產,并同夫為主”[10],丈夫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同妻子一起管理嫁妝的權利,丈夫的參與使妻子失去了對妝奩田或脂粉地的單獨處分、收益權利,處置共產須雙方共同同意。另有情況是,明清法律規定,當丈夫去世、寡妻改嫁時,嫁妝并不能由寡妻帶走。《大清律例·戶律·戶役》規定,“其婦人改嫁者,夫家財產及原有妝奩,并聽前夫之家為主”。這種狀態下,雖然妻子擁有名義上的所有權,但丈夫同妻子一起享有部分使用權,這種財產情況共有被學者認為是極為勉強的私有財產,或者說,他們其實不愿承認這種不完整的財產權的存在。
(二)私產的“中斷”與個人行使財產權的聯系
私產的中斷是家庭關系變化不可改變的結果,但這種中斷是否可以完全否定個人財產權的存在?筆者認為,從私產存在的過程來看,沒有否定;從部分私產轉變為“家產”后的存續來看,也沒有否定。
首先,對于因為私產所有人建立新的家庭或者分家而產生的私產“家產化”,個人的私產確實在新家產生后消失了。但物權的存續本身就有時間和過程,哪怕是現代制度下的物權,一旦標的物毀滅、消失,物權都會自動消失;對于現代制度下的土地使用權,更是有30年、70年不等的期限。現代物權,或因物毀損而消失,或因法定事由而消失,那么對于傳統社會中的個人財產權,其終結原因不過是從私產到家產轉化的完成。對于現代曾經存續的物權,我們并未否定其價值,同樣對于古代的私產也不能認定其不存在。只要所有人曾經在一段時期內擁有個人產權,就應正視傳統社會存在私產的事實。例如,外出經商者可能將經營收入投放到進一步的買賣中,官吏為了回報鄉黨可能用官俸在家鄉設立義學,這些行為都是使用私產的體現,也都是個人財產權利存在的佐證。
其次,對于夫妻共有的財產,應當算作正當的私產。正如滋賀秀三在《中國家族法原理》一書中所描述的,嫁妝來到夫家后,成為獨立于夫家家產的夫妻特有財產。雖然在嫁妝(無論是日用品還是土地)的處分的內部關系上,丈夫需要得到妻子或者妻子家長的同意,但不可否定這種財產權的行使,已經脫離了夫家家族的掌控。當下夫妻雙方結婚后,大部分的財產也成為夫妻共有財產,但在人類社會中,夫妻本為一體,這種親密關系下的共有財產已被人們視為私有財產的一種。這種共有財產與家族共有財產不同,前者的紐帶是普世的,更便于理解的;而后者的紐帶是中國特有家族文化的產物,僅存在于同居共財的傳統社會中。家族財產的處理,往往要面臨分家、利益紛爭等問題,確實難以認定為自由無拘束的私有財產;但夫妻共同財產的處理,基本朝向一個利益方向,除去離婚,也較少出現因矛盾紛爭而行使權利不自由(尤其在古代社會,婦女地位低下,離婚和與丈夫的紛爭并非多數)。因此,對于這種夫妻共同財產,今日社會尚且認為是私有財產,更何況夫妻一體、妻隨夫權的古代社會?
從以上兩點可以看出,這種所謂的私產變化或私產中斷,并未對私產的存在產生本質化影響。雖然由私產變為家產,但之后依然會有源源不斷的新的私產出現,而夫妻共同所有的私產,則是一種名正言順的共同共有的私有財產,甚至由于妻子對財產的權益高于丈夫,丈夫僅有部分管理、使用、收益權。這種財產權高于當今民法體系下的夫妻共有財產模式。私產的中斷并未導致個人財產權的喪失,許多判例中也都展現了行使財產權利的情況。如《名公書判清明集》卷六戶婚門中“訴奩田”一案就詮釋了這一情形:
巴陵趙宰石居易念其侄女父母雙亡,沒有財產嫁妝,故打算將在孟城的田地出售,換作錢財給侄女做妝奩,并將售賣之事托付給侄子石輝。石輝本應遵從叔父石居易的囑托,竭力幫助妹妹,卻不料在將田地賣給劉七后,擅自把所得四百多貫錢用于償還自己所欠債務。后侄女的丈夫廖萬英來取要嫁妝財物,石輝謊稱自己被劉七所騙,沒有取得賣田錢款。于是廖萬英將石輝和劉七訴至官府,認為其貪昧了妻子的妝奩。
司法官對此案進行調查后,否定了石輝的做法,認為其“以士自稱,乃變詐反復,仿盜賊小人之所為”,也批評了丈夫廖萬英在意妻子妝奩錢財而無視親戚輯睦之義的行為。最終判決石輝“決竹箄二十”,并將“引監日呈納上項價錢”交付劉七,贖回田產交付廖萬英,契仍寄庫。
此案裁判中明確了以下兩個規則:第一,女子的奩具乃私人財產,妻子娘家男子無權擅自變賣。石輝作為哥哥,對失去雙親的妹妹本應承擔撫養義務,卻貪心于叔父贈予妹妹的嫁妝,并轉賣給其他人,侵害了妹妹的財產權。即使石輝作為女子的家人,也無權代替其處分嫁妝。第二,丈夫作為妝奩的共同所有人,有權要求收回妝奩;但同時裁判也聲明,丈夫不應覬覦妻子的嫁妝,這非大丈夫“光明磊落”的做法,應在道德上加以批判。由此可見,傳統判例基本支持女性單獨擁有嫁妝,不受娘家和夫家控制,雖然丈夫有一定程度的共同所有權,但這種高于現代夫妻財產共同共有的財產權,完全可以視為私有權的存在。
四、從“私產”到“私主體”
學者否定“私產”的出發點是對于“家主體”的肯定,落腳點也在于透過“家”來討論傳統社會生活模式。誠然,“家”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具有不可撼動的地位,諸多法律事件中關系、情實的理解都需要從“家”入手。然而,在肯定“家”分析的同時,是否要全然否定“私”的存在?或者,在不斷談論“家族”的同時,是否要關注“個人”主體的歷史痕跡?前文已經討論了家族共產下私產的存在,那么有私產是個人主體地位的基礎,換言之,有私產就有個體,個人也是研究傳統社會法律關系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
首先,私產的存在,可以證明個人主體在傳統社會中有可研究的價值。前文列舉的“特有財產”并非滋賀秀三先生絞盡腦汁在茫茫案例中找到的特殊情況,而是廣泛存在于社會生活之中。對于龐大家族下的每門每戶或者每個人,難免都有自己或多或少的私有儲蓄。俞江教授認為,這種為了自己“小家”爭取到的利益,并不是“自私”的體現,而是為了“小家”的公。[1]這種看法或許有些牽強。實際上,對于國家而言,家族已是私,那么對于家族而言,“小家”更是私。“公”與“私”的概念本就是相對的,“家族”是“大公”、“小家”是“小公”這種循環論的說法,只會陷入“公”、“私”定義之爭,而無視背后主體行為對整個社會發展的價值。而正視私產與私人的存在,才會將我們的視野拉到個人民事行為的觀察中。雖然個人主體的行為仍舊在傳統制度的約束下進行,也被家族觀念所影響,但卻比家族行為更具有自由性和近代權利的意味。正如前文“訴奩田”案中,雖然丈夫討要妝奩的行為被家族倫理情義所批判,但其權利的行使與保障的出發點,卻在于保障個體權利,司法官最終的判決也肯定了維護奩產的意義高于親戚情義,此處個人財產權大于家族倫理。
其次,近代中國經歷了從家產到私產的變化,其中個人主體的作用不容忽視。我們一直重視外在的變法對家庭關系乃至社會關系的影響,卻不太關注家族中個人主體力量發展的作用。例如,有研究認為民國時期大理院判例主動融合了近代法律規定與傳統家族習俗,使親屬繼承關系也逐漸從身份走向契約。[3]但往往法律習慣發生變化的原因并不是外力強制作用,個人主體的不斷發展,是否也自發性地突破了傳統家族繼承關系?而這種變化與突破又是從何時開始的?探討這些問題,就不能無視傳統社會中私產和私權的存在。關注“私產”、“個人主體”在整個古代社會的軌跡,而不是截斷性地從近代開始言說這些概念,也許能從另外的視角觀察到我們近代的轉型。
五、結 語
私產在傳統法律研究中一直不是重點話題,這與“家”、“國”觀念過大有關。學者往往將家與國并列為傳統社會的兩極模式,因為家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細胞,是最小的一極,國家與天下、民族等概念集合,是最大的一極。[11]然而,“私”并未如過去被忽略的地位一般,在法律發展中影響低微。造成這一錯覺主要因兩個誤區:一是對傳統社會中“產權”概念不明晰,錯誤地將現代“所有權”定義套入傳統社會,來理解古代民法財產權含義;二是對權利存在形態認識錯誤,以為“私產”劃歸“家產”就失去了所有存在意義,然而財產權的存在形態本來就是變換流動的,由私有到共有再到私有是正常的變化,不應因此否定曾經存在且連綿不絕的私人財產權。正視私產,亦會讓我們重新理解個人在傳統法律生活中的地位和影響。私主體一直在家、國的夾縫中生存,然而在推動法律發展方面,卻也有不容小覷的意義。尤其在法律近代化歷程中,私主體是連接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一根重要線索。關注傳統社會中“私主體”的法律演化,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國民事法律變革進程,也利于為當下的民法發展添加本土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