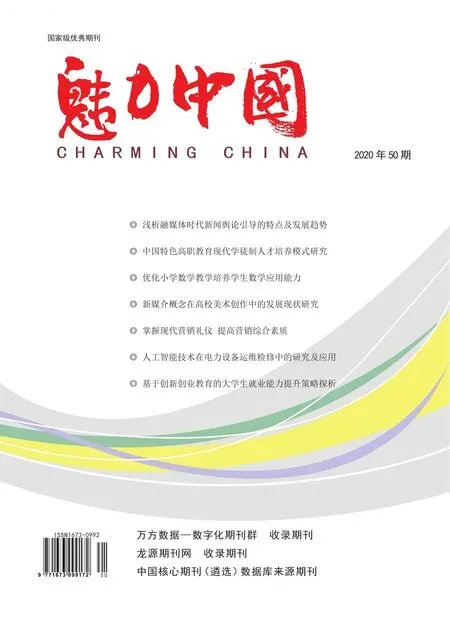符號互動理論視角下翻轉課堂教學模式存在的問題與對策
黃敏
(溫州大學教育學院,浙江 溫州 325062)
引言
當前,信息化時代要求學生掌握豐富的科學知識和高效的學習方法,以教師講授為主的課堂過于注重知識的傳授,對學生的問題和思考關注度不夠。而此時,將學生分為小組以討論探究為課堂主要內容的翻轉課堂已經得到了廣泛的研究。先前的研究表明其學習成果與傳統教學法比較時:翻轉課堂可以提高學生的表現,最壞的情況是不會損害學生的學習。在已出版的翻轉課堂研究中,只有少數研究(例如,Gundlach等人,2015年)報告說,傳統教學法的學生表現要好于翻轉課堂的學生。但是,其在本土化過程中我們仍應追問:相較于傳統課堂,翻轉課堂學生課下的觀影過程是否可以實現師生即時性的互動?課上是否可以滿足符號意義的創建?教師是否可以實時掌握學生學習情況有針對性的調整上課節奏?本文將在符號互動論的視角下解釋這三個問題,并在當前時代背景下提出具有可行性的三條解決方案。
一、翻轉課堂教學法概念界定
Lage等人定義為:“傳統上發生在教室內的事件現在發生在教室外,反之亦然”。Bishop等人認為僅僅是教學方式和學習活動的順序調整不足以代表這種教學模式的實踐,他們認為翻轉課堂是技術支持的教育學,由兩個基本的部分組成:一是在課堂外,直接通過基于計算機的視頻講課的方式進行個別學習;二是在課堂上組織小組的互動學習活動。他特別強調嚴格要求了課外的視頻學習作為學習的組成部分。
二、翻轉課堂教學模式存在的問題——基于符號互動論視角
符號互動論中最重要的著作當推米德的《心靈、自我與社會》一書,該書提出了“本我”(I)“客我”(me)等概念,對生成性課程有一定的啟示。但其試圖將行為主義學說原則應用于心智過程中,遭到了布魯默的反對。布魯默認為只以個人心理的刺激—反應來分析忽視了社會互動的本質,故其在刺激與反應之間加上了詮釋,即刺激—詮釋—反應。在詮釋過程中個人需設身處地進入他人的角色,也可以說這是一種意義互動的過程。
本節基于布魯默的符號互動論的三個基本原則的視角對翻轉課堂進行全過程審視,提出并解釋其存在的問題,下一節在此基礎上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
(一)課前視頻互動不足
布魯默在符號互動論三原則的第二條指出“事物的意義在個人與他人的社會互動中浮現出來。”即事物的意義不由事物本身的存在而決定,而是在人與人的社會交往過程中逐步浮現,形成事物對彼此的意義。如在某些考察默契度的游戲中,相處時間久的人對某些事物更容易有特殊的意義,故用特殊的符號表達時更易猜中,也更容易拿到高分。
在翻轉課堂課前觀看視頻的環節中,學生各自在家觀看教師提前錄制好的視頻。雖然學生在頭腦中理解了視頻內的知識點的意義,但這個過程在形式上剝奪了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的即時性互動。也正因為形式上缺少師生、生生互動,故其在內容上也剝奪了學生在課堂提問與小組討論等互動中才能建構的意義。
根據布魯默的符號互動論中意義的浮現過程,在空教室錄制視頻的教師與各自在家觀看視頻的學生都沒有完成對所學知識的意義的建構。縱然這種教學模式解放了課堂時間,比傳統課堂有更多的時間讓學生與小組成員和老師進行互動,但其課前觀看視頻階段互動的缺失及其課堂情景、師生互動的失真仍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二)課中意義創建缺失
布魯默在符號互動論三原則的第一條指出“人類對事物行動的基礎建立在事物對他們的意義上。”即個人的意識在理解事物時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作用,當人們意識到這件事對他們而言是重要的時,他們才便會發揮主觀能動性,采取積極的行動完成這件事。如學生對不同學科的看法不同,故而對不同學科付出的行動也不同。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高中的3+3高考模式:物理由于難度大,連年成為最冷門的高考科目。
翻轉課堂課堂教學模式教室內上課的過程中,學生不是空著腦袋進教室的,而是帶著自己對新知識的理解和不解。某些觀看視頻過程中已經熟悉的概念會幫助學生更好地和其他同學圍繞新知識進行討論,先入為主的錯誤理解會在討論與講解的過程中逐漸通透,對視頻的不解和疑問也會在課堂上深入的討論中撥云見日。但是,上述的討論效果是是建立在學生認真觀看視頻并在沒有教師和同伴監督的情況下仍堅持反思與做筆記的前提上。
結合布魯默三原則的第一條來看,學生會在所有學科選擇自己認為最重要的學科重點觀看認真思考,不重要的學科則渾水摸魚聽之任之,有些自制力差傳統課堂上都會跑神的同學的觀看效果會更差。而低齡學生自我意識尚未發育完全,不能根據事物的重要性來安排自己的時間,且觀看視頻需借助電子設備,很容易被未經凈化的網絡誘惑。不同學科的區別化對待和自制力的兩極分化讓本來傳統課堂上“強扭”來聽課的“瓜”有了更多的選擇和自由,也讓翻轉課堂至關重要的第一步的“夭折”風險加劇,課中具有升華意義的討論和解疑也會因小組成員兩極分化的“前結構”和全體師生沒有達成共識的符號意義而缺失,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早期代表人物米德提出自我的發展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即自我意義建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由于教學是一種復雜的長時間的雙邊活動,所以當個人在課下觀看視頻進行學習并進行漸進地自我符號意義建構后,再次返回班級和集體內其他成員上課交流時,自學時所使用的符號意義便不再完全適用,沒有達成共識的意義符號來讓課堂活潑起來便間接降低來翻轉課堂的效果,這也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三)教師學情分析乏力
布魯默在符號互動論三原則的第三條也即最后一條指出“事物的意義經由人的詮釋過程而確定。”結合前兩條原則,個人先由自我意識傾向選出具有重要意義的事物,而后經由與他人的互動使其意義不斷浮現,再經由自我對話修訂事物對他的意義,最后才能下決定。
在翻轉課堂視頻錄制過程中,教師缺少實時的表情觀察與互動,很難了解到學生的學習情況,亦難通過手勢動作、眼神、語言提醒在講重點內容時開小差的學生。同時錄制視頻時場景的單調性以及無生的環境使教師很難考慮到學生在某節課中真正的痛點,即使是有數十年經驗的老教師也只能考慮到學生可能會存在的一般性問題,不具有針對性和代表性。教師學情分析上的乏力使學生預習情況成為黑洞:預習做的不夠好,之后課上的討論解疑便會被吸入黑洞中,變成對他人問題及回答的模仿,模糊了翻轉課堂與普通課堂的邊界,使其優勢淡化。
結合布魯默三原則的第三條來看,在翻轉課堂中教師錄制視頻和教室內上課的整個教學過程不可避免地會和自身的人生觀、價值觀、角色認同感、自我在以往或者現存生活世界中的經驗進行互動,在這種互動中,教師會主動地去詮釋自己的教學設計和動作,教學效果便自然而然地具有差別。由于教師對學情的掌握乏力,影響了教師對課堂的認知和闡釋,講和問、討論、答的割裂以及課堂上學生討論狀況的不可控性對教師的應變能力提出了較高的要求。
符號互動論者還強調在自我的發展中不僅要自我互動,詮釋產物,社會互動亦不可少。課程是在師生、生生、生本互動中不斷發展生成的,相同的一節課可因創生路徑的不同可產生不同的教學效果。教師由于不甚了解學生預習情況不僅影響自己詮釋課堂意義的過程,而且有讓教學變成單邊接受或輸出過程的傾向,這亦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三、翻轉課堂教學模式存在問題的對策研究
BTS新教學思維是葉丙成教授在臺灣各地中小學、大學教師推行的教學思維,指的是“for the students,by the students,of the students”。BTS新教學思維主要通過使用Google Form(谷歌調查單)設計《影片預習進度回報》、《課堂評分回報》來承擔班級的數據統計工作;使用投影機讓學生展示自己的答案從而省去課上作業展示的時間;按學生意愿將班級分成三人小組,每組至多有一位成績優秀的同學,方便幫扶進度慢的同學;翻轉課堂實施的前兩周在課堂觀看影片并留出半節課的時間討論和做題,兩周后再把視頻觀看放到課下,影片放在課下觀看時就不再布置課程作業;翻轉課堂成為常態后,課前先詢問觀看視頻的同學,對觀看和未觀看的同學給予差異化對待,幫助同學適應這種新的學習方式。
在BTS教學思維的指導下,結合疫情期間在線課程和直播軟件如雨后春筍般層出不窮背景,將可行性考慮在內提出下述三種解決辦法。
(一)預習單的即時填寫與提交
針對課前視頻觀看互動不足,可依托釘釘在線文檔進行改善。首先是預習單即預學案的填寫與分享,題量不宜過多,5道以內即可,要預留出學生的疑問區。另外,完整觀看視頻并提交預習單的同學在釘釘群內接龍。除此以外不再布置其他作業,與新知識點相關的討論和練習放到課堂上進行。由于在線文檔的編輯和接龍全體學生都可以看到,所以沒有觀看視頻的同學會在同組同學的監督和同伴壓力下認真觀看,較好地解決了課前互動不足的問題。
(二)實施有選擇的翻轉
針對課上意義創建缺失,可采取不必全部課型均翻轉的方法。一般而言,新授課上是師生、生生、師本、生本再互動過程中創建符號意義最為關鍵的時候,此課型可以采取師生面對面的授課方式。而此后的復習課與練習課中可采取翻轉課堂的教學模式。如下例中的雪萊老師她有選擇的翻轉的是可以激發學生好奇心和學習興趣的視頻,在此案例的啟示下課采取有選擇地翻轉新授課、復習課、練習課等不同課型來解決課中符號意義創建缺失的問題。
雪萊在加拿大薩斯喀徹溫省穆斯喬的草原南高 中教英語、科學和技術。她不認為翻轉課堂是現有教育的救星,因為“晚上看講課視頻、白天做作業”這種形式只是傳統課堂的重新安排。但她認為課堂時間的釋放,在正確的教師手中是一個巨大的機會,特別適合探究性學習。雪萊不是在她的所有 課堂教學中都使用翻轉,也不是每晚都分配給學生 視頻講座,她更喜歡有選擇地進行。“我在學生需要新的信息時才使用翻轉模式。”她說,通常情況下,她分給學生的可能不是講課視頻,而是旨在建立好奇心、啟發學生思考的簡短片段。這些視頻配合著一個班級的維基一起使用,幫助學生組織、交流和理解材料。
(三)Moodle平臺進度跟蹤
針對教師學情分析乏力,可依托Moodle(Modular Object-Oriented Dynamic Learning Environment)平臺觀看每一位同學的視頻觀看情況,互動情況,這些結果會以圖形報告的形式呈現。該平臺還可靈活配置當前課程的線上討論活動、教師自己設定評分標準提交日期等用以評判學生的作業等。但是此平臺多用在大學課程管理中,浙江師范大學、溫州商學院等高等院校均使用該平臺實施課程管理,但是其在中小學階段的應用較少,雖然理論上可以解決教師教師學情分析乏力的問題,但是實踐效果仍有待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