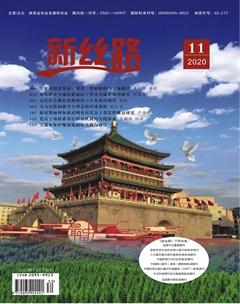李儀祉構(gòu)建陜西民間水利糾紛解決機(jī)制的繼承與創(chuàng)新

摘 要:被稱為近代“水圣”的李儀祉從民國十一年(1922年)起長期主持陜西省水利建設(shè)事業(yè)和管理事務(wù),在解決民間水利糾紛制度和機(jī)制建設(shè)方面根據(jù)民國時期陜西水利糾紛案的主要特征,繼承傳統(tǒng)解決方法,創(chuàng)新現(xiàn)代管理模式,采取民間依例調(diào)解和政府終審判案相結(jié)合的形式,賦予各方監(jiān)督權(quán)力,對于其它各省解決水利糾紛事件起到了“開制度之先”的示范和標(biāo)桿作用,值得我們今天深入研究,充分借鑒。
關(guān)鍵詞:李儀祉;陜西民間;水利糾紛;解決機(jī)制
中國社會長期以農(nóng)立國,而水利是農(nóng)業(yè)的命脈。由于水利資源的短缺,圍繞水權(quán)問題發(fā)生的糾紛在中國農(nóng)村經(jīng)常發(fā)生,且甚為激烈。地處西北內(nèi)陸的陜西干旱少雨,再加上民國時期陜西戰(zhàn)亂頻仍,災(zāi)荒不斷,吃飯靠天的農(nóng)村和農(nóng)民在水利方面的糾紛呈愈演愈烈之勢,甚至成群械斗,釀出了人命。被稱為近代“水圣”的李儀祉從民國十一年(1922年)起長期擔(dān)任陜西省水利局局長職務(wù),一度出任陜西建設(shè)廳廳長,不僅主持修建了“關(guān)中八惠”,澤被三秦,而且在解決民間水利糾紛制度和機(jī)制建設(shè)方面也在繼承的基礎(chǔ)上多有創(chuàng)新,對于我們今天化解社會矛盾、構(gòu)建法治社會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民國時期陜西水利糾紛案的主要特征
1935年,李儀祉在為陜西省水利局撰寫的年度工作報告《一年來陜西之水利》指出了陜西水利糾紛的亂象及其危害。指出由于歷史水權(quán)未經(jīng)現(xiàn)代法律明確而導(dǎo)致“霸王之諺”:“本省農(nóng)田水利,歷史悠久,水權(quán)相沿至今,未經(jīng)確定,值灌溉期間,爭先用水,強(qiáng)者得利,良民抱屈,各處有霸王之諺,尤以陜南為最盛,關(guān)中區(qū)次之。”[1]認(rèn)為由于政治腐敗和懶政怠政,導(dǎo)致糾紛頻發(fā)多發(fā),且拖延不決:“本省灌溉水利,古負(fù)盛名,近以水政窳敗,專管無人,任人民各自為政,平時不知修堰疏渠,旱時用水,則械斗相爭,聚訟不決……”[2]據(jù)李儀祉先生在報告中統(tǒng)計,在民國初年至二十三年(1934年)期間,陜西境內(nèi)共發(fā)生大大小小的水利糾紛案百余起,而且很多都是積年未決的案件。綜合分析民國時期陜西水利糾紛案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幾個方面:
1.時間分布特征
從時間分布特征看,民國時期的陜西水利糾紛案多發(fā)生在大旱之年。民國十一年到民國二十二年(1922-1932)黃河流域發(fā)生了歷時十年之久的罕見旱災(zāi),陜西災(zāi)情尤為嚴(yán)重,據(jù)當(dāng)時國民政府西北災(zāi)情考察團(tuán)南京賑濟(jì)委員會1930年報告稱:“陜西全省九十二縣,無處非災(zāi)區(qū)”,西安近郊“田黍枯萎,焦如火焚,高低尺余,收獲不足一成,棉花亦然。居民十室十空,板房售賣者十之四五,樹皮果實,早經(jīng)采罄,現(xiàn)食糠秕土粉,災(zāi)民遍野,日有餓斃。”[3];而夙有“江南水鄉(xiāng)”之譽(yù)的陜南地區(qū)“亢旱三年,顆粒無收,災(zāi)情之重,父老相傳,為空前所未見聞”。災(zāi)情的嚴(yán)重導(dǎo)致了人們對漸趨枯竭的水資源的爭奪日趨激烈,水利糾紛頻繁發(fā)生。據(jù)學(xué)者統(tǒng)計,僅在民國十一年至十三年(1922-1924)和民國十七年至十八年(1928-1929)兩段時間計五年期間,由陜西省水利廳和建設(shè)廳甚至國民政府行政院依法處置的水利糾紛案件多達(dá)29起,而其他由民間依例調(diào)解的的水利糾紛案更不計其數(shù)。
2.空間分布特征
從空間分布特征看,民國時期的陜西水利糾紛案多發(fā)生在關(guān)中和陜南,而在陜北鮮有糾紛。究其原因,按照李儀祉先生的分析,“歷史悠久”、“古負(fù)盛名”的陜西省灌溉水利主要集中在關(guān)中和陜南地區(qū),如秦代關(guān)中就有鄭國渠,漢代陜南就有山河堰,重視水利興修,灌溉農(nóng)業(yè)發(fā)達(dá)。而陜北古為游牧民族生活區(qū),近代又由于溝壑縱橫,水源稀少,灌溉農(nóng)業(yè)落后,因之水利糾紛案相對較少。關(guān)中、陜南水利糾紛案在近代日漸增多的原因,固然與人口顯著增多而水源有限、水利設(shè)施年久失修而用水量逐年增高、大旱之年圍繞水權(quán)爭奪械斗日甚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而戰(zhàn)亂連年、吏治腐敗、水政荒疏也是重要原因。民國時期陜西各路軍閥相互攻打殺伐,戰(zhàn)爭連年不斷,大小土匪嘯聚山林,騷擾禍害百姓,官員胥吏忙于搜刮民財,怠于日常政務(wù),“水政窳敗,專管無人”。李儀祉先生尖銳指出官民矛盾幾至不可調(diào)和,而橫征暴斂依然如故,“況乎澤已竭矣,魚又何附?骨以見矣,肉將安取?”[4]一些案件的久拖不決也導(dǎo)致關(guān)中、陜南的水利糾紛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民國四年(1915年)發(fā)生的長安縣水寨村與徐家村的水利糾紛案屢判屢訟,甚至出了人命,直至民國十三年(1924年)才得以最終解決。
3.糾紛主體特征
民國時期的水利糾紛案主體多以民間為主,主要是兩類糾紛。一類是不同水利灌溉單位之間發(fā)生的糾紛,一般表現(xiàn)為同一流域的上堰與下堰、左堰與右堰用水單位的糾紛。由于中國傳統(tǒng)血緣宗法觀念的影響和自然經(jīng)濟(jì)的結(jié)構(gòu),往往是一姓結(jié)族而居,形成自然村莊,同氣連枝,在水利方面也就形成一個灌溉單位,經(jīng)常在水權(quán)的分配、用水秩序的先后、水利設(shè)施的修浚與維護(hù)費用等方面發(fā)生糾紛和沖突,糾紛和沖突的雙方均以村莊為單位,男女老少齊上陣,往往演化為群體械斗,影響最大也最難解決。如民國十一年(1922年)至民國十八年(1929年)關(guān)中長安縣發(fā)生的七起水利糾紛案,均是村莊與村莊之間的糾紛。此類糾紛常常是上游村莊憑借天然地理優(yōu)勢侵害下游村莊用水權(quán)益,破壞傳統(tǒng)用水規(guī)則與秩序,這種行為特別在大旱之年屢有發(fā)生,導(dǎo)致下游村莊無法耕種澆水,引起群體憤怒。如民國五年(1916年)、民國十三年(1924年)渭南張義村兩次在河水上游開渠筑堰,與下游臨潼寇家村發(fā)生糾紛,互相訴訟,官府難以判決,成為積案。民國十八年(1929年)大旱之際,周至縣大莊寨村與南洪水堡村因水權(quán)問題發(fā)生大規(guī)模械斗并致死人命,轟動當(dāng)時。
另一類是同一灌溉單位不同田戶之間的糾紛。此類糾紛是最為常見的水利糾紛,糾紛的焦點問題是用水的先后次序和用水量的大小,相對而言規(guī)模較小,限于一家一戶之間,但有時候也發(fā)展成為村莊之間的沖突。如民國十七年(1928年)長安縣史家坡村與灣子村之間發(fā)生的水利糾紛,起初是個別村民因用水量不均發(fā)生爭執(zhí),后來發(fā)展成為兩村村民之間的大規(guī)模械斗。甚至還有一些惡霸地痞、流氓無賴故意破壞水源或截斷下游用水,蓄意引起沖突。如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三原縣東里堡周永秀、來成林、門生才等地痞無賴,故意將渠水截斷放入東里城壕,導(dǎo)致下游八復(fù)渠村民無法灌溉,引起訴訟。而這種情況在灌溉區(qū)屢見不鮮。“用水經(jīng)常被地痞、流氓、惡霸、豪紳把持操縱,私自霸水或賣水。”[5]普通民眾往往敢怒而不敢言,深受其害。大旱之年這種霸水或賣水行為與生存和性命攸關(guān),人神共憤,引發(fā)大規(guī)模群體反抗行為。
二、繼承:民間依例調(diào)解
歷史上的陜西水利的興建,主要是官修、官督民修、民眾集資自修三種形式,灌溉區(qū)或者受益區(qū)構(gòu)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但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水利糾紛往往因此產(chǎn)生。為了解決糾紛,官方厘定規(guī)章制度,民間建立鄉(xiāng)規(guī)民約,將公法與慣例法兩者結(jié)合以化解矛盾,處理糾紛。但在李儀祉所處的民國時代戰(zhàn)亂連年,“政府對各渠堰,事先并未詳訂規(guī)章,遇有爭紛,張皇失措,調(diào)卷查案。”[6]在這種情況下,民間調(diào)解就成為化解水利糾紛的主要形式。民間調(diào)解主要是依靠習(xí)慣法與鄉(xiāng)規(guī)民約,夾雜以情理,出面調(diào)解者往往是鄉(xiāng)村自治組織的族長、德高望重的鄉(xiāng)紳。但這種調(diào)解形式建立在民眾自覺遵守古規(guī)舊例,調(diào)解人堅持情理兼顧、公正公平的基礎(chǔ)上,缺乏剛性的制度約束和執(zhí)行的權(quán)威性,如果調(diào)解者依仗宗族勢力強(qiáng)大、官方人脈深厚、財勢雄踞一方而有所偏袒,則極易激化矛盾,加劇糾紛,甚至釀成村落族群之間大規(guī)模的械斗。
1.公舉“水老”
李儀祉在主持陜西水利建設(shè)的同時,高度重視化解民間水利糾紛。他首先繼承了傳統(tǒng)的民間依例調(diào)解制度并加以改良,使之更契合近代水政管理。鑒于“本省(陜西省)各項水利事業(yè),向乏管理團(tuán)體,大半操諸豪紳之手,利己害眾”[7]的情況,在涇惠渠修成之后,草擬了《涇惠渠灌溉章程》,仿照古例以斗口為單位,由民眾推舉以“平解斗內(nèi)用水紛爭”為主要職責(zé)的“水老”一人,下設(shè)斗夫一人,渠保若干人,負(fù)責(zé)日常水利管理工作。“水老”一詞當(dāng)屬李儀祉在繼承古代鄉(xiāng)里管理制度時的獨創(chuàng)名詞,秦時鄉(xiāng)置三老一人,漢代增設(shè)縣三老,“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xiāng)一人;擇鄉(xiāng)三老一人為縣三老。”[8]三老的主要職責(zé)是掌管教化,排解鄰里糾紛。李儀祉參照古代“鄉(xiāng)舉里選”和借鑒近代民主選舉的方式公舉水老,“由闔斗人民每十戶舉出一代表,由代表用記名投票方式公舉水老,舉定后報告管理局備案。”[9]而且在繼承的基礎(chǔ)上對水老推選的條件也提出了五點新的要求。“水老的資格須:(甲)年在四十歲以上者;(乙)有相當(dāng)田產(chǎn),以農(nóng)為業(yè)者;(丙)不吸鴉片私德完善者;(丁)未受刑事處分者;(戊)凡曾任官吏軍士者,不得被選舉。”[10]其中第五條要求主要是為了防止官員利用過去的關(guān)系網(wǎng)謀取私利和倚仗權(quán)勢欺壓良善。1933年頒布的《陜西省水利通則》明確規(guī)定了水利的民間自治原則與組織,“多人共享或舉辦之水利事業(yè)及其所屬建筑物,得組織水利協(xié)會或者合作社,經(jīng)營管理保護(hù)之。”[11]同年公布的《陜西省水利協(xié)會組織大綱》規(guī)定水利協(xié)會設(shè)會長1人,分會長若干人,均由會員代表大會記名投票選舉,而會長、分會長當(dāng)選資格必須是“非現(xiàn)任官吏或軍人”。與李儀祉在《涇惠渠管理章程擬議》 中提出的資格條件基本相同。按照《陜西省水利協(xié)會組織大綱》的規(guī)定,分會長“得以習(xí)慣稱堰長、渠董或水老”。[12]
2.依例調(diào)解
民間水利自治組織水利學(xué)會及其分會的主要職責(zé)是“評處各分會或會員間之糾紛”。[13]調(diào)解方式和依據(jù)主要是繼承傳統(tǒng)的依例調(diào)解。這一點李儀祉在1935年總結(jié)的《一年來之陜西水利》一文中闡述的非常清楚:“按照該各堰古規(guī)舊例,參以學(xué)理及現(xiàn)在情形,秉公處糾……”[14]如當(dāng)時發(fā)生或者積訟多年的漢中山河堰左右高橋與孫家垱案、富平縣大小白馬渠分水洞案、三原縣清峪河八復(fù)渠與東里堡案、周至與眉縣爭引澇水案等,均先由公眾推舉的水老、堰長出面,依據(jù)傳統(tǒng)的習(xí)慣法鄉(xiāng)規(guī)民約、碑石刻文進(jìn)行調(diào)解,調(diào)解不成者,再依據(jù)現(xiàn)代水法《陜西省水利通則》處置,然后“飭令各該縣政府執(zhí)行在案”。
近代陜西處于新舊水利制度交替之際,在新法未行或難以服眾的情況下,傳統(tǒng)的依例調(diào)解就成為調(diào)解水利糾紛的主導(dǎo)方式。即使在古規(guī)舊例遭到人為破壞的情況下,仍然尋求舊有的習(xí)慣法作為處理糾紛的主要依據(jù)。如民國十三年(1924年)發(fā)生的長安縣嚼嘶坡村與橋頭村水里糾紛案,起因在于清水河上游的嚼嘶坡村筑壩截水,導(dǎo)致下游的橋頭村稻麥無水可灌,旱干枯死,兩村村民各有理由,爭訟不已。最后由陜西省水利局派員清查原來的地契糧冊,要求兩造將原來登記為旱田后改造為水田的一律取消用水權(quán),以圖恢復(fù)舊有的用水規(guī)則。1933年頒布的《陜西省水利通則》根據(jù)國情與省情,賦予古規(guī)舊例以法律地位:“各地方之水利事業(yè),其相沿之習(xí)慣或者規(guī)約,與現(xiàn)行法令不抵觸者,得從其習(xí)慣或規(guī)約。”
水老、堰長既是用水規(guī)則的制定者,也是水利糾紛的調(diào)解者和執(zhí)行者。如位于今西鄉(xiāng)縣境內(nèi)的金洋堰,在清朝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由堰長楊發(fā)榮“暨三壩士庶以前輩議定明條”,規(guī)定無論本地外地買壩田一畝提堰納稅錢一串錢,買車田提堰納稅錢一畝600文。民國十四年(1925年),楊成裕買田二畝多,“意懷紊亂堰規(guī),因遷延年余,分文弗給。”被時任堰長查處后,召集三壩鄉(xiāng)紳,“會集處問。”[15]可見堰長的權(quán)力很大,既有規(guī)則的制定權(quán),也有糾紛的調(diào)解權(quán),還有違規(guī)的調(diào)查權(quán)與懲戒權(quán)。
三、創(chuàng)新:政府終審判案
中國傳統(tǒng)社會在水利糾紛處置方面雖然以民間調(diào)解為主要形式,但國家的法律權(quán)威也起著重要的主導(dǎo)作用。從西周時期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水利法規(guī),漢代稱為“水令”,唐代頒布了水利專門法典《水部式》,北宋時代出臺了《農(nóng)田水利約束》,明代項忠巡撫陜西時制定了《水規(guī)》,體現(xiàn)了國家在水利治理層面的努力。但到了近代,西方的水資源國有化的理念和管理政策傳入中國,對水資源的全面規(guī)劃、統(tǒng)籌管理、綜合利用和有效保護(hù)開始成為水法的主要內(nèi)容與系統(tǒng)設(shè)計。由于民國政府統(tǒng)治的時代戰(zhàn)亂連年,“水政窳敗”,直到1942年才頒布了中國近代第一部《水利法》,配套以行政院制定的《水利法實施細(xì)則》。在此新舊制度交替之際,留學(xué)德國柏林皇家工程大學(xué)土木工程科專攻水利等專業(yè)的李儀祉深受西方先進(jìn)水利管理思想的影響,曾遍游歐洲諸國"考察河流閘堰堤防",親眼目睹了西方國家水利事業(yè)的昌盛發(fā)達(dá),痛切感受到中國水利事業(yè)的頹廢落后。回國后踏遍祖國江河大川,出任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長兼總工程師職務(wù),長期主持陜西水利建設(shè)與管理事務(wù),終生以治水為志,為中國水利事業(yè)的近代化做出了卓越的貢獻(xiàn)。特別是在陜西主政水利期間,引進(jìn)西方管理理念,與中國傳統(tǒng)水利管理制度相結(jié)合,篳路藍(lán)縷開創(chuàng)性地出臺了一系列水利管理法規(guī)和制度,推進(jìn)了中國水利管理事業(yè)近代化的進(jìn)程。
1.出臺管理規(guī)章制度
在擔(dān)任陜西省水利局局長和建設(shè)廳廳長期間,李儀祉參照西方的水權(quán)制度,結(jié)合中國國情和陜西省情,提出了《涇惠渠管理管見》,制定了《涇惠渠管理章程》《陜西省水利行政大綱》等規(guī)章制度,將陜西省水利事業(yè)管理提升到一個新高度。
在涇惠渠一期工程竣工之后二期工程繼續(xù)進(jìn)行之時,李儀祉立即將“實為要事”的管理事務(wù)提上議事日程,于1932年在涇惠渠放水典禮上宣布了《涇惠渠管理管見》,以求“善謀其始”。[16]關(guān)于擬定管理制度的宗旨即“水利之理想”的五條意見中,第一條意見就是“欲求水量配劑之平均”,這里的“水量” 不僅包括引用涇河水量的調(diào)劑,也包括灌溉總渠各支渠、斗門的水量調(diào)劑,以化解可能因此而引起的水利糾紛。這就將過去上游與下游因用水不均而導(dǎo)致的糾紛與沖突在管理層面予以消弭,體現(xiàn)了西方水資源國有制的理念。但李儀祉認(rèn)為“管理之組織仍以農(nóng)民為主體”,政府“居于監(jiān)督指導(dǎo)之地位”,[17]體現(xiàn)了孫中山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現(xiàn)代國家設(shè)想。在此之后,李儀祉即撰寫了《涇惠渠管理章程擬議》計十六章65條。在第一章《總則》開宗明義,確定“涇惠渠之管理,由官民合組為之”。[18]在第七章《用水糾紛》中,明確規(guī)定了水老、管理局處置用水糾紛的范圍和權(quán)利,并規(guī)定“凡不按規(guī)章用水者,另訂有罰則”。[16]第八章《管理局》規(guī)定“管理局設(shè)局長一人,……局長須以深具水利工程經(jīng)驗之工程師(工科大學(xué)畢業(yè),服務(wù)水利工程至少五年以上)充之,不合資格者,不得被委”。[17]這就保證了局長必須由具備專業(yè)技術(shù)知識和水利實際工作經(jīng)驗的人員出任,以防止“外行領(lǐng)導(dǎo)內(nèi)行”和亂指揮、瞎指揮。并規(guī)定管理局“得雇用警生六人”,[18]賦予了管理局一定的司法執(zhí)行權(quán),確保管理局在處置水利糾紛事件的合法性與權(quán)威性。
1933年,在李儀祉等人的推動下,陜西省政府公布了《陜西省水利通則》,成為民國時期省級政府出臺的著名地方性水利法規(guī)。在1935年,李儀祉先后著寫了《陜西省水利行政大綱》《陜西水利工程十年計劃綱要》《一年來陜西之水利》等文章,專門就貫徹落實《陜西省水利通則》等法規(guī)制度、解決水利糾紛等問題進(jìn)行了探討。他認(rèn)為“利之所在,人必爭之,故水利的糾紛甚多,不能不有完美的法律管理”;[22]明確指出確定用水權(quán)為“根本解決水利糾紛方法”,主張“以主要河流為綱,次要河流為目,劃分全省水利區(qū),分別實施”用水權(quán)注冊登記,“以后憑證用水,庶免攘奪之風(fēng)。”[23]
2.政府終審水利糾紛
李儀祉是孫中山主張的人民掌握政權(quán)、政府行使治權(quán)的“權(quán)能分治”理論的忠實實踐者。在處置水利糾紛事件問題上,他始終堅持以民眾自治組織的調(diào)解為主要形式,只有在民眾自治組織調(diào)解無效的情況下,交由政府或由“政府代人民管理”的管理機(jī)構(gòu)在深入調(diào)查研究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處置,這一處置方式具有終審性和強(qiáng)制執(zhí)行性。按照李儀祉的這一理念,他主持修建的“關(guān)中八惠”分別設(shè)管理局或類似機(jī)構(gòu),處置水利糾紛,鑒于陜南用水糾紛較多,于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夏天“特設(shè)漢南水利管理局,專司其事”。[24]如果各管理機(jī)構(gòu)難以處置者,則交由水利局或建設(shè)廳等政府機(jī)構(gòu)進(jìn)行具有終身性質(zhì)的判決。按照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李儀祉主持的陜西省水利局統(tǒng)計的《陜西省各河流域歷年人民水利糾紛案件處理情形統(tǒng)計表》,民國五年至民國二十三年(1916年-1934年)陜西發(fā)生的19起重大水利糾紛案件,均由陜西省水利局或建設(shè)廳判決處理,交由所在縣政府執(zhí)行。[25]而據(jù)李儀祉統(tǒng)計,在同一時期陜西省關(guān)中和陜南地區(qū)發(fā)生的水利糾紛“共計百余案”。[26]可見大多數(shù)案件由民間依例調(diào)解,只有在民間依例調(diào)解無果或管理機(jī)構(gòu)處置無效的情形下,呈交政府水利局或建設(shè)廳判決后由所在縣政府執(zhí)行。這種不由法院判決而由政府機(jī)構(gòu)處置的方式是處理水利糾紛案件的一種創(chuàng)新,原因在于全國水法沒有出臺的背景下,法院判決無法可依,而政府專門機(jī)構(gòu)既熟悉舊規(guī)古例,又有專業(yè)技術(shù)人員具體負(fù)責(zé),按照“古規(guī)舊例,參以學(xué)理及現(xiàn)在情形,秉公處糾”,具有專業(yè)權(quán)威性質(zhì),故成為終審判決。
從民國五年至民國二十三年(1916年-1934年)由陜西省水利局或建設(shè)廳判決處理的陜西發(fā)生的19起重大水利糾紛案件來看,共同特點是糾紛積訟多年,大旱之時尤為激烈,民間水利自治組織多次調(diào)解無效。如長安縣水寨村與徐家村的水利糾紛案從民國四年(1915年)就起根發(fā)苗,甚至發(fā)生了大規(guī)模的械斗,出了人命,民間水利組織的調(diào)解和地方政府的判決多次均告無效,直至民國十三年(1924年)才由省水利局判決得以最終解決。而富平縣的大小白馬渠分水糾紛案從清朝嘉慶年間就已開始,整整持續(xù)一百余年,到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糾紛又起,最后由省水利局呈請省政府判定,交由富平縣政府強(qiáng)制執(zhí)行才得以平息。李儀祉主持的陜西省水利局和建設(shè)廳處置水利糾紛案件的一般程序是在民間調(diào)解和縣級政府判決均告無效的情況下,由省局或省廳派員查勘,按照古規(guī)舊例與現(xiàn)行法規(guī)相結(jié)合的方式進(jìn)行處置判決;如省局與省廳判決仍難以為兩造接受,則直接呈請省政府判決;如省政府判決依然難以執(zhí)行,則上報中央政府行政院作出判決。如民國十七年(1928年)大旱之時藍(lán)田縣發(fā)生的兀家崖村與薛家河因分水不均導(dǎo)致兩村村民械斗互毆,釀成命案,省水利局和建設(shè)廳多次調(diào)處無效,最后上呈國民政府行政院,行政院于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作出終審判決,令藍(lán)田縣政府強(qiáng)制執(zhí)行。
3.賦予各方監(jiān)督權(quán)力
在水政機(jī)制建設(shè)方面,李儀祉特別注重監(jiān)督機(jī)制建設(shè)。他認(rèn)為水利事業(yè)“固須有極完健之組織,上得國家之信倚,中得地方之協(xié)力,下得人民之樂從,始能望其成績”。[27]而在這一“極完健之組織”中監(jiān)督機(jī)制的設(shè)立與行使、防止權(quán)力的濫用是其中重要的一個環(huán)節(jié)。按照李儀祉的設(shè)想。水利事業(yè)監(jiān)督機(jī)制建設(shè)主要包括四個方面:民眾自治組織對管理機(jī)構(gòu)和政府部門的建議彈劾權(quán);管理機(jī)構(gòu)和政府部門對民眾自治組織的監(jiān)督指導(dǎo)權(quán);一般民眾對民眾自治組織、管理機(jī)構(gòu)和政府部門的監(jiān)督批評權(quán);設(shè)立視察區(qū)的視察權(quán)和特別機(jī)構(gòu)的顧問權(quán)。
民眾自治組織對管理機(jī)構(gòu)和政府部門的監(jiān)督彈劾權(quán)主要體現(xiàn)在水老或堰長的職責(zé)與權(quán)力方面。按照李儀祉制定的《涇惠渠管理章程擬議》,由民眾公舉的水老主要職責(zé)是“平息斗內(nèi)用水紛爭”,“監(jiān)督斗夫、渠保履行職務(wù)”,而且每年要舉行兩次會議,“有建議于管理局請改良關(guān)于管理事項之權(quán),有向省政府建設(shè)廳彈劾管理局失職之權(quán)。”[28]后來出臺的《陜西省水利通則》采納了這一做法,將水老、堰長的建議權(quán)和彈劾權(quán)以法律的形式予以合法化。由于水老、堰長是民眾水利自治組織的重要代表,所以這一規(guī)定實際上體現(xiàn)了民眾自治組織對管理機(jī)構(gòu)和政府部門的權(quán)力制約與監(jiān)督。
管理機(jī)構(gòu)和政府部門對民眾自治組織的監(jiān)督指導(dǎo)權(quán)主要體現(xiàn)在管理局、水利局、建設(shè)廳的職責(zé)與權(quán)力方面。在涇惠渠引水工程竣工之后,李儀祉明確指出:“管理之組織以農(nóng)民為主體,而政府設(shè)官,居于監(jiān)督指導(dǎo)之地位。”[28]他親自撰寫的《涇惠渠管理章程擬議》第八章《管理局》中規(guī)定管理局的“監(jiān)督管理行政事項”共有十條。在1935年所作的《一年來之陜西省水利》報告中,李儀祉明確要求省水利局“分派專員赴各縣指導(dǎo)組織”水利事業(yè)之管理。李儀祉將管理機(jī)構(gòu)和政府部門的這種監(jiān)督指導(dǎo)權(quán)有時候稱為管理“督率權(quán)”,可見既包涵有對民眾自治組織的監(jiān)督管理職責(zé),也包涵有以身作則、率先垂范的自身要求。管理局和政府部門也有對民眾水利自治組織處置糾紛案件的調(diào)查權(quán)和指導(dǎo)權(quán)。如1923年和1924年,長安縣發(fā)生的兩起水利糾紛案件,最終由水利局派員實際調(diào)查,提出指導(dǎo)性處置意見。1934年渭南縣赤水農(nóng)業(yè)中學(xué)與華縣發(fā)生的水利糾紛案,在陜西省水利局派員多年調(diào)查研究的基礎(chǔ)上,廣泛征求兩縣水利自治組織意見,調(diào)解爭端,最后提出指導(dǎo)性解決方案。[29]
一般民眾對民眾自治組織、管理機(jī)構(gòu)和政府部門的監(jiān)督批評權(quán)主要體現(xiàn)在管理機(jī)構(gòu)和政府部門工作的主動性上。按照李儀祉的要求,管理機(jī)構(gòu)的日常管理工作不僅在于“嚴(yán)厲執(zhí)行灌溉章程”、“調(diào)處各斗各村堡用水糾紛”等方面,也要不定期“召集各大支渠水老、斗夫、渠保及民眾分別開會”,征求各方意見,“曉諭用水章程”。[30]為了開啟民智,提高人民群眾的水利常識和維權(quán)意識,減少用水糾紛,李儀祉于1937年撰寫了《倡辦三渠民眾教育議》,由省政府核準(zhǔn)施行。他倡議在涇惠渠、渭惠渠、洛惠渠三大灌溉區(qū),由管理局職員利用業(yè)余時間開設(shè)民眾學(xué)校,“課程為識字、寫字、習(xí)算、公民、農(nóng)民、水利常識”,“開啟人民愛國合群之心理。”[31]這一建議體現(xiàn)了李儀祉的“民權(quán)”主義意識,具有提升民眾自身知識和修養(yǎng)的重要作用。
在《涇惠渠管理章程擬議》中,李儀祉專門設(shè)置了第九章《視察區(qū)》,將整個灌溉區(qū)分為四個視察區(qū),每一視察區(qū)“各置視察員一人,雇員一人”,其主要職責(zé)是“視察渠務(wù),并隨時代管理局就近調(diào)查水利糾紛事項”。[32]實施分區(qū)視察制度是李儀祉在近現(xiàn)代水利管理制度史上的嘗試和創(chuàng)新,有利于提高解決水利糾紛案件的的效率。鑒于華洋義賑總會、華北慈善聯(lián)合會等慈善組織及檀香山華僑捐款捐物,“于涇惠渠最有功德”,李儀祉在涇惠渠引水工程竣工之初就建議將其“永遠(yuǎn)延之為顧問團(tuán)體.并請求常派專家指導(dǎo),襄助本省農(nóng)工業(yè)之發(fā)展”,[33]此后在《涇惠渠管理章程擬議》中特設(shè)《顧問團(tuán)體》一章,“禮聘華洋義賑總會、華北慈善聯(lián)合會及檀香山華僑為永久顧問團(tuán)體”,規(guī)定每一顧問團(tuán)體“各派代表一人,對涇惠渠管理常加指導(dǎo)”。[34]這種顧問權(quán)、指導(dǎo)權(quán)實際上也是一種監(jiān)督權(quán),對于提升管理機(jī)構(gòu)的管理水平具有特殊的意義。
四、結(jié)語
李儀祉先生作為中國近現(xiàn)代史水利事業(yè)發(fā)展史上的泰斗,不僅推動了家鄉(xiāng)陜西省的水利建設(shè)走在了當(dāng)時全國各省的前列,而且于構(gòu)建陜西民間水利糾紛解決機(jī)制方面將傳統(tǒng)解決方法與現(xiàn)代管理模式相結(jié)合,在繼承的基礎(chǔ)上多有創(chuàng)新,對于其它各省解決水利糾紛事件起到了“開制度之先”的示范和標(biāo)桿作用,值得我們今天在大力發(fā)展陜西省水利水文事業(yè)、邁出追趕超越新步伐的征途上深入進(jìn)行研究,充分吸收借鑒。
注釋:
[1][2][7][14][20][24][26][30]李儀祉.一年來陜西之水利.李儀祉水利論著選集.水利電力出版社,1988,344、342、344、340
[3]梁敬鋅.江南民食與西北災(zāi)荒.時事月報,第1卷第2期,1929.12.88
[4]李儀祉.請恢復(fù)鄭白渠、設(shè)立水利紡織廠、渭北水泥廠、恢復(fù)溝洫與防止溝壑?jǐn)U展及渭河通航事宜(一九二七年).李儀祉水利論著選集.水利電力出版社,1988.286
[5]冶峪河小型水利調(diào)查報告.載白爾恒《溝洫佚聞雜錄》第一輯,中華書局,2003.159
[6]李儀祉.陜西之灌溉事業(yè).陜西水利季報,1936.22
[8]《漢書》卷一《高帝紀(jì)上》
[9][10][18][19][20][21][28][32][34]李儀祉.涇惠渠管理章程擬議.李儀祉水利論著選集.水利電力出版社,1988,318、320、321、322、324-325
[15]金洋堰重整舊規(guī)理處違背條件碑記.民國十六年立碑,見陳顯遠(yuǎn)《漢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424
[16][17][28][33]李儀祉.涇惠渠管理管見.李儀祉水利論著選集.水利電力出版社,1988,316、317
[22]李儀祉.陜西省水利行政大綱.李儀祉水利論著選集.水利電力出版社,1988.338
[25](民國)陜西省水利局.陜西省各河流域歷年人民水利糾紛案件處理情形統(tǒng)計表.陜西水利月刊,第3卷第2-5期,1935年
[27]李儀祉.黃河水利委員會工作計劃(一九三三年).李儀祉水利論著選集.水利電力出版社,1988.74
[29]渭南市臨渭區(qū)水利志編纂辦公室.渭南市臨渭區(qū)水利志.三秦出版社,1997.276
[31]李儀祉.倡辦三渠民眾教育議(一九三七年).李儀祉水利論著選集.水利電力出版社,1988.420-421
作者簡介:
盧九源(1989--),陜西省西安市人,供職于陜西省漢中市水文水資源勘測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