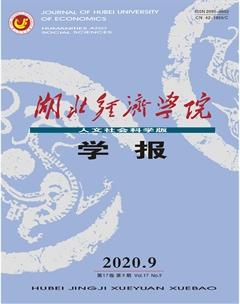安東妮亞:一位蘊(yùn)含“雙性同體”的新女性
蘇博雅
摘要:“雙性同體”是20世紀(jì)女性主義批評(píng)的一個(gè)重要概念,它突破了性別二元對(duì)立的傳統(tǒng)思維框架,達(dá)到女性主義的新境界。本文通過(guò)探討雙性同體在《我的安東妮亞》中的體現(xiàn),從而說(shuō)明雙性同體有利于打破性別二元對(duì)立的僵化局面,促進(jìn)兩性之間的和諧相處。
關(guān)鍵詞:雙性同體;性別二元對(duì)立;和諧
一、簡(jiǎn)介
薇拉·凱瑟(1873-1947)是20世紀(jì)一位重要而又獨(dú)具特色的女作家,她的題材清新雋永,文筆優(yōu)美細(xì)膩。當(dāng)代英國(guó)著名學(xué)者安東妮亞·蘇珊·拜厄特撰文認(rèn)為“凱瑟和托妮·莫里森是第一流的美國(guó)女小說(shuō)家,超過(guò)沃頓和斯陀夫人,凱瑟與詩(shī)人狄金森一樣堪稱一流,乃是因?yàn)樗蛟炝艘环N藝術(shù)風(fēng)格。”(拜特2001:151)她創(chuàng)作初期的“內(nèi)布拉斯加系列”包括《啊!拓荒者》(1913)、《云雀之歌》(1915)和《我的安東妮亞》(1918)三部小說(shuō),為她躋身優(yōu)秀女作家行列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
14歲時(shí),安東妮亞隨家人從波西米亞移民到內(nèi)布拉斯加州。為了在這樣一個(gè)完全陌生的地方生存下去,一家人艱難地勞作,然而父親因?yàn)樗监l(xiāng)親切和一系列挫折而選擇了自殺。安東妮亞的哥哥(Ambrosch)能力有限,一人之力支撐不起全家,妹妹(Julka)年幼,弟弟(Marek)有智力障礙,從此,安東妮亞由一個(gè)無(wú)憂無(wú)慮的小姑娘變?yōu)榧依锏囊桓е0矕|妮亞決定放棄學(xué)業(yè),幫助哥哥分擔(dān)責(zé)任。后經(jīng)吉姆的祖母介紹,她到哈利家(Harlings)去做廚娘,后來(lái)為了捍衛(wèi)自己跳舞的權(quán)利而辭職。安東妮亞在舞會(huì)上見(jiàn)到了一位列車員拉里·多諾萬(wàn)(Larry Donovan)并迅速墜入愛(ài)河,懷有其身孕的她最終被列車員拋棄。然而她并未就此而一蹶不振,而是更加堅(jiān)強(qiáng)地努力生活。最后同一位同是波西米亞的異族男子結(jié)婚,他們生養(yǎng)了11個(gè)(文中說(shuō)也可能10個(gè))孩子,種植了果園,開(kāi)墾了新地,過(guò)上了幸福而又愉快的生活。
國(guó)內(nèi)外的研究學(xué)者對(duì)《我的安東妮亞》的研究側(cè)重于女性主義、女性生態(tài)主義、新歷史主義、文化研究、新批判主義、成長(zhǎng)主題、文化回歸、敘事學(xué)等角度,而很少有人從“雙性同體”角度解讀《我的安東妮亞》。從“雙性同體”角度解讀《我的安東妮亞》的碩士論文只有三篇,一般期刊一篇。雖然已有學(xué)者從“雙性同體”的角度解讀《我的安東妮亞》,但作者認(rèn)為仍有從這個(gè)角度解讀的空間,因此,本論文嘗試從“雙性同體”的角度來(lái)解讀《我的安東妮亞》。
二、雙性同體
雙性同體(androgyny),也稱雌雄同體,就詞源來(lái)看,由希臘語(yǔ)andro(男性)和gyn(女性)組成。并非醫(yī)學(xué)上表示雌雄同體的詞“hermaphrodite”。1973年,美國(guó)女性主義作家卡洛琳·郝貝蘭(Carolyn Gold Heilbrun)出版了《朝向雙性同體的認(rèn)識(shí)》(Toward a Recognition of Androgyny)一書(shū),書(shū)中提到了一個(gè)重要概念:雙性同體。該書(shū)認(rèn)為無(wú)論是在哲學(xué)、文學(xué)還是宗教中,雙性同體應(yīng)該是一種最完美的理想。其實(shí)早在古希臘時(shí)期,柏拉圖在《會(huì)飲篇》中將人分為三類,即:女性、男性和雙性同體,而雙性同體是最完整最完美的人。雙性同體的理論在榮格的心理學(xué)說(shuō)中早已有定論,他提到阿尼瑪和阿尼姆斯。阿尼瑪是男性的女性特征,阿尼姆斯是女性的男性特征,每個(gè)人身上都有異性的某些特質(zhì)。一個(gè)人保持平衡與和諧就“必須允許男性人格中的女性因素和女性人格中的男性因素在個(gè)人的意識(shí)和行為中得到展現(xiàn)”。(馮川1987:53)弗吉尼亞·伍爾夫?qū)⑦@一思想引入女權(quán)批評(píng),在她的《一間自己的房間》一書(shū)中,她說(shuō):“在我們之中每個(gè)人都有兩種力量支配一切,一個(gè)男性的力量,一個(gè)女性的力量。在男性的頭腦中男性勝過(guò)女性,在女性的頭腦中女性勝過(guò)男性。最正常、最適宜的境況是這兩股力量在一起和諧地生活、進(jìn)行精神合作的時(shí)候。”(Woolf 1989:98)她引用英國(guó)詩(shī)人柯勒律治的話“偉大的心靈都是雙性同體的”,認(rèn)為“藝術(shù)家應(yīng)該是雙性同體的”。在伍爾夫看來(lái),莎士比亞、濟(jì)慈、斯特恩、蘭姆、柯勒律治等都是雌雄同體的。(Woolf1989:98)因此,伍爾夫指出:“任何人在寫(xiě)作時(shí)意識(shí)到自己的性別都是致命的,做一個(gè)純粹的男性和女性也是致命的,只有大腦中男性和女性共同創(chuàng)造才能完成藝術(shù)創(chuàng)造。”(Woolf1989:103)同時(shí)伍爾夫意識(shí)到想要達(dá)到雙性同體的難度以及雙性同體的不確定性,因此說(shuō)道:“要你們?nèi)フ页鰜?lái),去判斷哪些值得保留”。(Woolf 1989:4)到了上世紀(jì)80年代之后,美國(guó)女性主義評(píng)論家托瑞·莫依(Toril Moi)運(yùn)用法國(guó)批評(píng)家德里達(dá)和克里斯蒂娃的解構(gòu)理論,認(rèn)為她的雙性同體說(shuō)法其實(shí)是試圖脫離早期狹隘的男女兩性對(duì)立抗?fàn)幍挠^點(diǎn),反對(duì)二元對(duì)立的,“在強(qiáng)調(diào)兩性相異性的同時(shí),也強(qiáng)調(diào)兩性的相通性。”(程錫麟2011:100)
作為女作家的凱瑟,內(nèi)心矛盾重重,一方面羨慕莎士比亞、福樓拜等大師為代表的男性文學(xué)傳統(tǒng),另一方面她又感到社會(huì)對(duì)女性作家的不公,渴望追求并享有男女平等的權(quán)利。凱瑟的作品既不受男權(quán)文化的束縛,也不被絕對(duì)的女權(quán)意識(shí)所左右,她的作品《啊!拓荒者》、《云雀之歌》和《我的安東妮亞》中的女主人公都體現(xiàn)著“雙性同體”的特征。《我的安東妮亞》一書(shū)以男性身份“吉姆”之口來(lái)講述女主人公“安東妮亞”,這從另一個(gè)角度來(lái)看也體現(xiàn)了凱瑟的“雙性同體”愿望。本文認(rèn)為雙性同體有利于打破性別二元對(duì)立的僵化局面,促進(jìn)兩性之間的和諧相處。
三、“雙性同體”特征在《我的安東妮亞》中的體現(xiàn)
(一)安東妮亞的男性特征
安東妮亞的父親不忍思鄉(xiāng)之苦與開(kāi)墾新家園的種種挫折而飲彈自盡。安東妮亞傷心難過(guò)之余,深刻地意識(shí)到父親死后自己肩上的重?fù)?dān),像男人一樣干起了粗重的農(nóng)活,她自豪地對(duì)吉姆說(shuō):“我現(xiàn)在能像男子漢那樣干活了”(Cather 2005:85),盡管吉姆的祖母說(shuō)她像個(gè)大男人,不秀氣,但她說(shuō):“我就是喜歡像個(gè)男子漢”(cather 2005:94)。此時(shí)的安東妮亞已經(jīng)不是剛來(lái)內(nèi)布拉斯加州時(shí)的心境與行為了,安東妮亞此時(shí)的男性特質(zhì)占了上風(fēng),并未被眼前艱難的處境所嚇倒,而是盡全力擔(dān)負(fù)起家里的重?fù)?dān),這是對(duì)男權(quán)社會(huì)男性擔(dān)負(fù)養(yǎng)家職責(zé)的極端諷刺,表明她內(nèi)心認(rèn)同男性性別的價(jià)值取向。而祖母評(píng)價(jià)說(shuō)她像大男人,不秀氣也說(shuō)明了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上女性處于不平等的地位,即使身為女性的祖母也被這樣的男權(quán)社會(huì)所同化。后來(lái),吉姆的祖母介紹安東妮亞到哈利家當(dāng)廚娘,有一次安東妮亞到鎮(zhèn)上跳舞,被哈林先生發(fā)現(xiàn)后下達(dá)了最后通牒:“你要么放棄跳舞,要么就另找下家,”(Cather 2005:140)。傳統(tǒng)的父權(quán)制要求女性溫順恬靜,賢良淑德,相夫教子,認(rèn)為只有男性才可以追求自己的事業(yè)與興趣愛(ài)好。被“消音”的女性根本沒(méi)有發(fā)言權(quán)可言,男女地位極端不平等,而安東妮亞卻敢于堅(jiān)持自己的想法,從未出現(xiàn)過(guò)“失聲”的情況。面對(duì)自己的工作機(jī)會(huì)和跳舞的夢(mèng)想,安東妮亞選擇了后者,她并未表現(xiàn)出女性的唯唯諾諾,一味聽(tīng)從長(zhǎng)輩的行為,而是說(shuō)道:“那么,我走好了”(Cather 2005:141)這段話語(yǔ)不僅是女性對(duì)父權(quán)社會(huì)女性地位不公的反抗與控訴,也證明了具有反抗精神的新女性所體現(xiàn)出的男性特征,打破了傳統(tǒng)性別二元對(duì)立的固定模式。傳統(tǒng)婚姻觀認(rèn)為女性應(yīng)該聽(tīng)從媒妁之言,然而安東妮亞竟然與一位拈花惹草的列車員拉里·多諾萬(wàn)(Larry Donovan)自由戀愛(ài),并且在未婚先孕的情況下被對(duì)方拋棄,最后她只得回到家鄉(xiāng)。波伏娃在她的書(shū)《第二性》中曾說(shuō)過(guò):“故事中總有一位單純無(wú)知的女孩受到負(fù)心情人的欺騙,最后發(fā)生了一些事情。情節(jié)中必不可少地有家人和朋友的庇護(hù),最后是墮胎,雖然可怕,但卻是唯一可以想到的可行的辦法”(波伏娃1972:470-471)。然而安東妮亞卻非尋常女子,她選擇回家生下孩子。當(dāng)村里人得知她的事情后,閑言啐語(yǔ)不斷,但是安東妮亞沒(méi)有逃避抱怨,而是用她那瘦弱的肩膀辛勤地工作,勇敢地面對(duì)眼前的困難。“那年春天和夏天她都像個(gè)男幫工那樣干活”“大家因?yàn)樗诳炀粗厮冀吡ο駴](méi)出過(guò)什么事兒那樣對(duì)待她。”(Cather 2005:214)她就像《紅字》里的海斯特·白蘭一樣默默無(wú)聞毫無(wú)怨言地辛勤工作著,從而得到了大家的寬恕與諒解。“她談?wù)撐骞群吞鞖猓孟袼龔膩?lái)沒(méi)有其它興趣一樣”(Cather2005:214)她儼然一位男性形象屹立在田野,完全不像只會(huì)操持家務(wù)的傳統(tǒng)女性那樣。她在田野干活一直到臨產(chǎn)的當(dāng)天,“她的腳步越來(lái)越沉重”“就在那天她生下了那個(gè)孩子,她沒(méi)有喊一個(gè)人,沒(méi)有哼一聲。”(Cather 2005:215)此時(shí)的安東妮亞身上的男性特征多于女性是因?yàn)樗媾R的處境造成的,只有這樣才能支撐她繼續(xù)走下去。
正是她那積極向上永不言敗的樂(lè)觀精神吸引并鼓舞了她的丈夫安東·庫(kù)扎克(Anton Cuzak),她的丈夫是個(gè)身材矮小的波西米亞族男子,作者塑造這樣一個(gè)外形的男子是巧合嗎?安東(Anton)是安東妮亞(Antonia)名字的一部分,作者以此來(lái)說(shuō)明,男性并不總是強(qiáng)壯勇敢的代名詞,男性也有脆弱無(wú)助的時(shí)候,安東對(duì)農(nóng)事了解很少,而且經(jīng)常打退堂鼓,安東妮亞對(duì)吉姆說(shuō):“如果不是因?yàn)槲疑韽?qiáng)力壯的話,我們肯定捱不過(guò)去。”(Cather 2005:233)他們生了“恐怕有十個(gè)或十一個(gè)”孩子。(Cather 2005:224)面對(duì)柔弱膽怯的丈夫和生養(yǎng)密集的孩子,安東妮亞能做的就是擁有堅(jiān)強(qiáng)的意志,像男性一樣去田野勞作。傳統(tǒng)的女性總是被描述成柔弱被動(dòng)的形象,是男性保護(hù)和拯救的對(duì)象。這里的安東妮亞不但沒(méi)有被困難壓垮,反而拯救了她的丈夫安東。小說(shuō)中,安東這樣一個(gè)男性人物也具備了女性氣質(zhì),摒棄了男性霸權(quán)意識(shí),轉(zhuǎn)而擁有女性軟弱,細(xì)膩的一面。
(二)安東妮亞的女性特征
然而,一個(gè)身強(qiáng)體壯、意志堅(jiān)強(qiáng)的女性只擁有完全的男性意識(shí),而忽略了女性溫婉柔美的一面,那么世界上將只有男性(即使生理上是女性也是男性意識(shí)的女性),這是一種狹隘的女權(quán)主義思想,并不利于社會(huì)、人民的健康發(fā)展,這并不能構(gòu)成健全的人格。凱瑟想要塑造的是一個(gè)不僅擁有男性特質(zhì)還擁有女性特質(zhì)的完美女性,因此凱瑟對(duì)安東妮亞的女性特征也進(jìn)行了細(xì)膩的勾勒和渲染。安東妮亞的女性特質(zhì)體現(xiàn)在她與自然的聯(lián)系和適時(shí)地向男性示弱兩方面。
生態(tài)女性主義者認(rèn)為,自然與女性本身就有著隱喻意義。女性孕育子女的功能與自然生產(chǎn)萬(wàn)物的功能極為相似,因此常常有“大地母親”之說(shuō)。生態(tài)女性主義者強(qiáng)調(diào)女性特有的關(guān)心、愛(ài)護(hù)、體貼等特質(zhì)對(duì)自然的修復(fù)與改善功能,反對(duì)男性中心論中男性對(duì)自然,女性的野蠻征服與占有。被列車員拋棄回到家鄉(xiāng)后,安東妮亞沒(méi)有放棄對(duì)貧瘠土地的開(kāi)墾,而是將貧瘠的荒原變?yōu)榱艘恋閳@般的果園。20多年后,吉姆再次回到內(nèi)布拉斯加草原去看望安東妮亞時(shí),他看到“整座果園就好像一只注滿了陽(yáng)光的酒杯,我們能聞到樹(shù)上成熟的蘋果。……掛滿枝頭,紫里透紅,表面泛著一層薄薄的銀光”。(Cather 2005:231)這是因?yàn)榘矕|妮亞并不像父親哥哥那樣想要征服土地,而是懷著對(duì)土地深沉的愛(ài)細(xì)心呵護(hù)澆灌土地。安東妮亞懂得如何與自然為伴,與荒原融為一體和諧相處。她是草原女神,豐產(chǎn)女神,有著草原獨(dú)特的莊嚴(yán)肅穆之美。《紐約時(shí)報(bào)》贊揚(yáng)道:“凱瑟?jiǎng)?chuàng)作了一個(gè)新的神話,在這個(gè)神話里那種離開(kāi)土地到城市打拼的傳統(tǒng)美國(guó)英雄被一位對(duì)土地有深厚感情及崇敬土地上所有生命的豐產(chǎn)女神所替代。”(OBrein 1987:446)
安東妮亞在男性面前并不意味地強(qiáng)裝堅(jiān)強(qiáng),她也有女性柔弱體貼的一面。安東妮亞的父親自殺后,她傷心地一把抱住吉姆,吉姆深切地感到:“她緊靠著我的時(shí)候,我仿佛感覺(jué)到她的心在碎裂。”(Cather 2005:79)傷心不已的安東妮亞像個(gè)嬌羞的小女孩一樣借著吉姆的臂膀釋放自己壓抑的情緒,內(nèi)心的女性特質(zhì)在吉姆面前展露出來(lái)。弗洛姆說(shuō):“我們必須永遠(yuǎn)記著,在每個(gè)人身上都混合著兩類特征,只不過(guò)與‘他或‘她的性別相一致的性格特征更占多數(shù)而已。”(弗洛姆1988:259)父親死后,安東妮亞經(jīng)歷一系列的挫折與磨難,男性特征始終占上風(fēng),支撐她堅(jiān)強(qiáng)地生活下去,然而生下孩子后,她的女性特征展露無(wú)疑,母性的光芒熠熠閃光,她把嬰兒的照片放在鍍金的大鏡框里掛在照相館里展覽。她未婚生下的孩子就好像她“結(jié)婚生的,從未為她感到丟臉。……安東妮亞是個(gè)天生的好媽媽”(Cather 2005:216)安東妮亞在后來(lái)和吉姆的交談中說(shuō)道:“自從我有了孩子,我就不想殺死任何東西。”(Cather 2005:233)面對(duì)軟弱悲觀的丈夫,她總是鼓勵(lì)他,而且為丈夫一笑露出堅(jiān)實(shí)的牙齒而自豪。除此之外,她還經(jīng)常在外人面前夸獎(jiǎng)自己的丈夫,“我男人以前在佛羅里達(dá)州的橘子園里干活,會(huì)嫁接果樹(shù)。我們這一帶沒(méi)有哪一家的果園結(jié)得比我們好。”(cather 2005:231)在安東妮亞的心里,丈夫是家里的頂梁柱,是個(gè)能干的幫手,值得她驕傲并托付終身的好伴侶。西蒙·波伏娃認(rèn)為,婚姻把兩個(gè)獨(dú)立的個(gè)體結(jié)合在一起,夫妻二人不應(yīng)該被看成是脫離了外界社會(huì)的單獨(dú)個(gè)體,丈夫和妻子都應(yīng)該是社會(huì)的組成部分,兩個(gè)人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尋求自我的發(fā)展(波伏娃1972:470-471)安東喜歡喝酒,有時(shí)喝到半夜回家,可以說(shuō)他是個(gè)“不安分的主兒”,但是安東妮亞尊重他的個(gè)人喜好,從不干涉,原本“寂寞得差點(diǎn)兒瘋掉”(Cather 2005:249)的安東因?yàn)槠拮芋w貼、善良、熱情地把家收拾地妥妥帖帖而更加心系家庭。
(三)和諧的兩性關(guān)系——安東妮亞的“雙性同體”特征
孫紹先說(shuō):“女性既不應(yīng)該繼續(xù)作父系文化的附庸,也不可能推翻父系文化重建母系文化。出路只有一條:建立‘雙型文化”。(孫紹先1987:130)文章首次介紹女主角是以安東妮亞(Antonia)的名字呈獻(xiàn)給讀者,隨著吉姆與安東妮亞關(guān)系越來(lái)越熟絡(luò)而喚其小名托尼(Tony)。安東妮亞是一個(gè)女性化的名字,而托尼卻是一個(gè)男性化的名字,這兩個(gè)名字附在一個(gè)人身上體現(xiàn)了此人的雙性同體特征。
20多年后,當(dāng)吉姆去看望安東妮亞時(shí),她看到了安東妮亞經(jīng)歲月洗禮后所具有的獨(dú)特個(gè)人魅力。吉姆、安東和安東妮亞在田野散步時(shí),吉姆發(fā)現(xiàn)“這兩人相處得似乎很好,很愉快。顯然,她是沖擊力,他是矯正器。他們上坡的時(shí)候,他不斷地斜著眼睛望她,看她是不是聽(tīng)懂了他的意思,或者她聽(tīng)到了有什么反應(yīng)。”(cather 2005:243)兩個(gè)人之所以能夠相處的那么融洽,是因?yàn)楸舜硕寄苷莆蘸米约后w內(nèi)男性和女性特質(zhì)的分量,女性體內(nèi)的男性因素和男性體內(nèi)的女性因素會(huì)隨對(duì)方的增加而增強(qiáng),減弱而減弱。一方面安東妮亞跳出了傳統(tǒng)的男權(quán)社會(huì)的束縛,打破了傳統(tǒng)的男性主導(dǎo)的桎梏;另一方面,她作為一位好母親、好妻子把家里操持地妥妥帖帖、紅紅火火。男性特質(zhì)和女性特質(zhì)在安東妮亞身上靈活地轉(zhuǎn)化,促進(jìn)了家庭和諧穩(wěn)步前進(jìn)的步伐。“安東妮亞是女性傳統(tǒng)的繼承和延續(xù)者。她完全履行了一個(gè)女人所能擔(dān)負(fù)的所有責(zé)任,其最終形象的神圣性暗示了女性美學(xué)對(duì)生命的蘊(yùn)生和感召力。”(金莉2010:51-52)
當(dāng)吉姆和安東妮亞穿過(guò)田野走在回家的路上時(shí),文中寫(xiě)到:“太陽(yáng)落下來(lái),……月亮從東邊升起……有五分鐘,也許是十分鐘那么久,這兩個(gè)發(fā)光體遙遙相對(duì),停歇在世界相反的兩端。”(Cather 2005:218-219)因著太陽(yáng)月亮同時(shí)出現(xiàn)的這五分鐘或十分鐘,文中寫(xiě)到:“在這種奇異的光照下,每一棵小樹(shù)……都挺得高高的,把自己突顯出來(lái)……那種黃昏時(shí)分來(lái)自田野的莊嚴(yán)的魔力。”(Cather 2005:219)“在原始文化中,女性原則或厄洛斯以月亮為代表,男性原則或邏各斯則以太陽(yáng)為代表。”(易小松2003:51)另外,月亮因其外形的變化周期與女性的月經(jīng)周期極其相似,因此常常用來(lái)指代女性。代表女性的月亮與代表男性的太陽(yáng)此刻同時(shí)出現(xiàn),在太陽(yáng)與月亮“合體”的片刻連植物也煥發(fā)了勃勃生機(jī),可見(jiàn)“雙性同體”的美妙,這正是凱瑟所倡導(dǎo)的理想的人格狀態(tài)。
安東妮亞·蘇珊·拜厄特這樣評(píng)價(jià)薇拉·凱瑟,“她比任何作家都注意到自己筆下的人物是完整的、完成的。”(盛寧2001:152)安東妮亞在薇拉·凱瑟筆下完成了自己人生的完美蛻變,她的人生既完滿又完整。薇拉·凱瑟的墓志銘是引用《我的安東妮亞》的一句話:“這便是幸福,融于某個(gè)偉大完整的東西之中。”(金莉2010:52)可見(jiàn)凱瑟對(duì)這部作品的喜愛(ài),安東尼婭的婚姻觀、幸福感也是薇拉·凱瑟所推崇的吧。
四、結(jié)語(yǔ)
女性主義批評(píng)者認(rèn)為“雙陛同體”是一種完美的理想人格,這反映了女陛在尋求自由和個(gè)性解放歷程中對(duì)和諧兩性關(guān)系建立的憧憬和探索。男人和女人生來(lái)平等,傳統(tǒng)的父權(quán)制阻礙了男女和諧相處的狀態(tài),而雙性同體有利于打破性別二元對(duì)立的僵化局面。女性應(yīng)該學(xué)會(huì)在困境面前堅(jiān)強(qiáng)勇敢起來(lái),男性并不需要時(shí)時(shí)刻刻保持堅(jiān)強(qiáng)勇敢的形象,應(yīng)該適當(dāng)?shù)貙W(xué)會(huì)釋放內(nèi)心被壓抑的情緒。男女之間的男性力量和女性力量相互協(xié)調(diào)作用才有利于兩性關(guān)系的和諧發(fā)展。安東妮亞兼具男性和女性特質(zhì),她既是位漂亮、體貼、溫柔、熱情的好女孩、好母親和好妻子形象;又是位堅(jiān)強(qiáng)、勇敢、獨(dú)立、堅(jiān)韌、有責(zé)任感的新時(shí)代女性形象。薇拉·凱瑟以敏銳的雙眸、細(xì)膩的內(nèi)心觀察并感知著周圍的女性,希望她們成為懂得兩性和諧相處之道的完美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