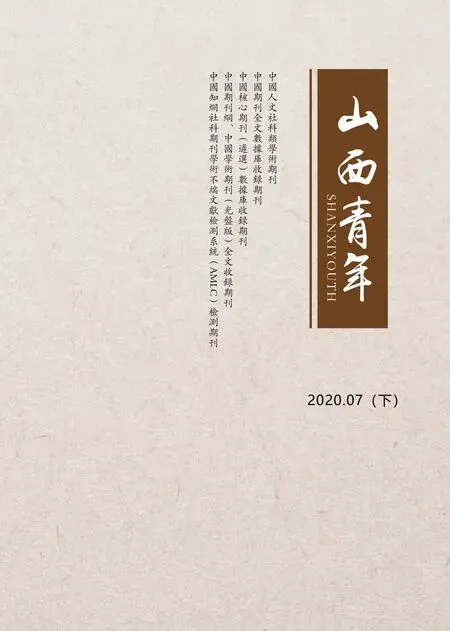論我國完全不負刑事責任年齡規定的困境
潘智源
河南大學法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隨著科學的發展與網絡信息技術的成熟,人們接受信息的速度越來越快,特別是處于身心發展時期的未成年人,其接受信息的能力以及學習的能力通常比一般人強,如果不加以正確的引導,在這特殊的成長時期難免不受外界不良信息的影響而誤入歧途。從整體上看,近十年來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從數量上確實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犯罪低齡化、暴力化的傾向卻越來越明顯。“未成年人犯罪低齡化趨勢持續發展,多次違法犯罪的比例在增加,結伙犯罪的組織化程度有了明顯提升”。[1]未成年人犯罪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但是一直都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隨著新聞媒體對惡劣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報道,處于各個案件中心的未成年犯罪人往往遭到社會公眾的口誅筆伐,可是因為他們犯罪時的年齡都未到14周歲,因而都不用承擔刑事責任,只是其被責令要嚴加管教或者送到政府的有關部門收容教育。犯罪手段殘忍的罪犯不能得到應有的刑罰的報應,逍遙法外的“小惡魔”一次又一次地刺激著社會公眾的敏感神經,《刑法》關于完全不負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更是成為眾矢之的。
一、爭鳴: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是飲鴆止渴還是與時俱進?
2016年全國兩會上,民進中央提交了《關于遏制校園暴力傷害事件的提案》建議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以使更多的未成年人納入承擔刑事責任的范圍。每每有新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被報道出來,社會各界關于修改未成年犯罪方面的法律的呼聲越來越高。
支持者認為,雖然我國對待未成年人犯罪一貫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但是若忽視犯罪的主觀惡性以及手段的殘忍程度,從而寬泛地討論未成年人犯罪是“錯”而不是“惡”,在懲罰措施上一味強調“教育”而忽視“懲罰”,這樣的做法有些流于偽善,而不能真正解決問題。廣東省律師協會未成年人法律專業委員會副主任鄭子殷律師主張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他依據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一項針對10個省市5864名中小學生的調查顯示的數據——32.5%的人“偶爾被欺負”,6.1%的人“經常被高年級同學欺負”認為,校園暴力數據與未成年人犯罪數據的巨大差距反映出大量未構成犯罪的暴力事件“依法無法處理”,未成年人初次犯案不被追究刑事責任,又沒有輔以有效的社會矯治措施予以懲治,不但會使得涉案的未成年人進一步深陷犯罪的泥潭,還會傷害了其他無辜的人。[2]湖北省律師協會未成年人保護法律專業委員會主任李春生亦認為,目前法律對低齡未成年人犯罪行為缺乏打擊力度,應該修改刑事責任年齡從14周歲降低至12周歲。[3]
盡管社會對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呼聲越來越高,但是對此也不乏反對的聲音。有學者認為,《刑法》有其穩定性,不宜輕易修改,并且當前我國完全不負刑事責任年齡存在的弊端并沒有達到全盤否定的程度,因此而修改法律的成本過高。[4]亦有學者認為,未成年人犯罪屬社會問題,是家庭因素、學校教育、社會管理等多種原因共同造成的,許多未成年罪犯的主觀惡性相對于成年人罪犯要小,具有較強的可矯治性,如果隨意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相當于把社會責任轉由未成年人自己一力承擔,具有推卸責任之嫌,并不能從根源上解決犯罪低齡化、暴力化等問題。[5]還有學者認為,對實施危害行為的未成年人動用刑罰,不僅容易造成交叉感染,而且使可塑性很強的未成年人被貼上犯罪標簽,不利于其融入社會,反而有可能誘發更嚴重的犯罪行為。[6]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問題必須弄清楚:極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是普遍現象還是個別現象?有沒有一種可能就是我們所知道的這些惡劣的案件,其實占未成年人犯罪總量的一個很少的比例呢?如果他占的比例很少,刑事責任年齡的修改到底有沒有必要,畢竟刑法的修改是很慎重的,隨著網絡媒體的發展,越來越多的極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被曝光,但這并不能說明全國范圍內都普遍存在這一現象。
二、降低完全不負刑事責任年齡確有必要
2004年在北京召開的第17屆國際刑法學大會形成的《國內法與國際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責任決議》規定適用特殊刑事責任的最低年齡不得低于14周歲。根據我國《刑法》第17條的規定,最低刑事責任年齡亦規定為14周歲,與國際上普遍的做法相一致。這種涇渭分明的刑事責任年齡劃分制度清晰地劃定了刑事責任能力的界限,在實踐中具有很大的可操作性,節省了紛繁復雜的認定程序。可是隨著越來越多惡劣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被新聞媒體曝光,我們隱隱看見如今我國刑法關于完全不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的規定所面臨的問題——當行為人的年齡低于完全不負刑事責任年齡時,無論其行為手段如何殘忍、主觀惡性如何惡劣,刑法亦對其無可奈何。
從本質上來說,我國關于刑事責任年齡的這種規定方式有悖于未成年人身心發展的客觀規律。首先,我國面積廣大,地域遼闊,存在著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沿海與內陸、城市與農村發展差距較大,不同地區的未成年人接收外界信息的質和量上存在巨大差距,僅僅從辨認能力的角度來分析,沿海或者城市的未成年人遠比內陸或農村的未成年人要好。
其次,一個人的刑事責任能力的形成是一個量變的過程,而量變的速度因人而異,有的人年僅12歲可能就有了遠超同齡人的辨認和控制能力,實踐中如何把握刑事責任能力從量變到質變的一個平衡點是一個暫時無法解決的難題。因此,我國現行關于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種政策考量,并非萬全之策。[7]
最后,我國目前仍在使用1979年《刑法》關于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但在這四十多年來,中國的社會環境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導致許多農村家庭空有家庭結構但卻喪失家庭功能,物質生活的改善使大部分孩子營養過剩、生理提前發育而性格自律嚴重缺失。[8]1979年《刑法》對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是根據當時的基本國情來制定的,但這套規定似乎已經不能適應現在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形勢,舊的規定在新的環境下顯得捉襟見肘,修改完全不負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確有必要。
三、完全不負刑事責任年齡的下調要立足國情
其實,人們呼吁降低完全不負刑事責任年齡最根本的目的是想打擊未成年人犯罪,而未成年人犯罪的懲治不能僅依靠《刑法》的修改,更要從犯罪學中深究其原因,修改法律只是緩兵之計,治標不治本。正如上海政法學院刑事司法學院院長、上海市法學會未成年人法研究會會長姚建龍所言,“如果13歲孩子殺人,我們就把刑事責任年齡降到13歲。又出現一個12歲的孩子犯罪,再降到12歲。我們還有10歲摔童案……如果按照這個思路,沒有一個底線,這是完全不具有可操作性的。”①
相對于我國而言,一些國家對于完全不負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比較低,如美國的路易斯州規定為10歲,內華達州為8歲,俄克拉荷馬州為7歲,新加坡規定為7歲。這些國家對于完全不負刑事責任年齡都規定的比較低,而且它們對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控制也比較好,所以有許多人認為我們應該向它們學習,把完全不負刑事責任年齡規定得低一點,以讓更多的未成年人納入到刑法所調整的主體中。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列舉的國家都具有比較完整的未成年人犯罪的責任追究體系與更加完善的教育體系,學校普及程度廣,未成年人的整體素質比較高,因此法律的要求也相對提高,這些都與我國的未成年人所處的環境不同。在向國外先進制度學習的同時,我們還應該立足于我國的客觀情況,我國未成年人的綜合素質雖比之前有所提高,但是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一定的差距,法律不應該對其作過高的要求,大幅降低完全不負刑事責任年齡會使我國的青少年承受一些他們不應該承受的壓力與責任,適得其反。法律的修改應該循序漸進,謹慎而行,不能一蹴而就。因此,筆者認為,我國完全不負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不宜大幅度更改,規定為12周歲比較合適。
第一,對于未成年人犯罪,關注的重點應該是社會的治理,從家庭環境、學校教育、社會關懷等方面入手,而不是拘泥于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對完全不負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并不能對未成年人犯罪的防控發揮十分有效的作用,因此,不應該作大幅度的調整。
第二,縱觀這目前的未成年人暴力犯罪,犯罪時的最低年齡大都是12歲左右,12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因為其生理上還沒完全發育,主觀惡性不大,其危害性受到一定的制約,一個低齡的未成年人是不會對社會、對人們造成非常大的危險,把完全不負刑事責任年齡下調至12歲已經可以解決大部分惡劣犯罪得不到懲治的問題。
第三,12歲的未成年人已經基本完成小學階段的教育,具有了對社會、對生活、對是非的基本認識,形成了相應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對是非判斷有自己的想法和觀點,也具備了一定的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能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四、結語
社會學家米爾斯說過,每一個人都生活在社會當中,都是由社會塑造的,被歷史的洪流挾裹推搡而行,單憑他活著的這樁事實,他就為這個社會的形貌、為這個社會的歷史進程出一份力,無論這份力量多么微不足道。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之中的絕大多數人,都必須為社會結構中的惡來負責。每個人一生下來只是一張白紙,家庭觀念、學校教育、童年的交往圈子、身處的文化環境等因素自己都無法選擇,但這恰恰都是未成年人人格形成的決定性因素。面對未成年人犯罪,我們要根據實際情況適當調整完全不負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使未成年人犯罪得到較好的控制,但正如李斯特所言:“最好的社會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9]犯罪的預防不僅僅依靠法律,還需依靠社會多方面的努力,法律對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控制只能是輔助性的,并不能包辦一切,盡管我國關于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略有不足,但是法律的缺陷不應成為社會逃避責任的借口。
注釋:
①上海舉行“少年司法改革與法律體系完整”研討會上上海政法學院刑事司法學院院長、上海市法學會未成年人法研究會會長姚建龍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