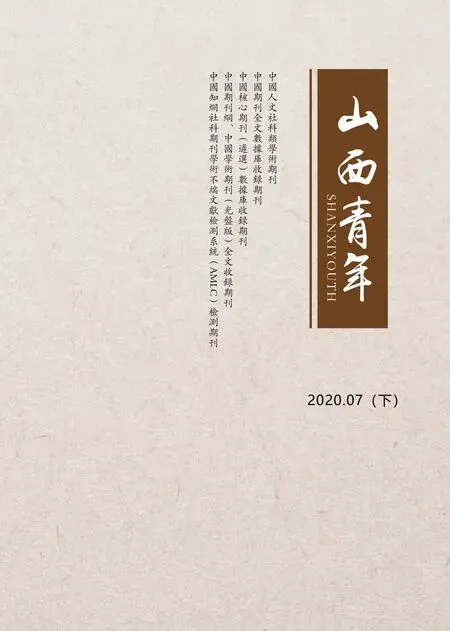試論康德崇高的形式
姜鵬越
云南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崇高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應(yīng)該有不同的表現(xiàn)形式。比如在李澤厚的《美的歷程》中對于青銅饕鬄文化的講述,那時候人們要用神秘恐怖獰厲可畏的形象作為一種對自己部落的保護。這種沉淀著歷史力量的形象是當時一種崇高的形式。隨著人類文明的不斷發(fā)展,崇高的形式也在不斷的發(fā)生變化,但是無論是在哪一個時代,崇高都是人的本質(zhì)力量對象化的顯現(xiàn)。
人類的審美活動對人類的大腦中的思維是有一定要求的。審美活動是超功利的,審美主體要擺脫現(xiàn)實生活的束縛是前提條件。在這一點上崇高也是和其他審美范疇是一樣的。當海嘯要淹沒的人的生命的時候人只會感受到威脅和恐懼,人自然是無法體會到崇高的美感的。恐懼和崇高之間也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但是是否崇高都是由一定程度的恐懼轉(zhuǎn)化而成的呢?這個問題會在后面進行探討。
審美活動的主體是人,固定審美對象在不同的審美主體的心理產(chǎn)生的結(jié)果不同,審美對象在審美主體心里產(chǎn)生的感受也是不可估計的。那么崇高的審美對象一定是“力”的無限大和“數(shù)”的無限大是不是過于絕對呢?這兩種一定會讓人產(chǎn)生崇高嗎?不是這兩種形式能不能也產(chǎn)生崇高呢?
一、崇高對象與美的對象的關(guān)系
首先,崇高和美都是人在審美活動中做出的判斷。既然是審美活動就都是超功利的。那么能不能同一個審美對象,既然人產(chǎn)生美感又讓人感到崇高呢。當然這里不能把“美感”這一概念的含義擴大化。要是說崇高也是一種美感那么就無法進行討論了。這里說的美自然是指讓人精神愉悅輕松的。如果依照康德所說“美只涉及對象的形式,崇高卻涉及對象的無形式,形式總是有限的,無形式則是無限的”。
也就是說康德認為同一個審美對象是不能夠讓不同的審美主體同時產(chǎn)生美感和崇高的。因為美的對象是要依賴形式的。而崇高的對象則是無形式的無限的。畢達哥拉斯認為美是和諧,美在比例。赫拉克利特認為對于神來說一切都是美的。再美的人在神面前也像一只猴子。智者學(xué)派則認為一切都靠人的主觀感覺,是通過視聽給人以愉悅的感覺。美的內(nèi)容需要美的形式來表達,形式美是內(nèi)容美的存在形式。那么當人們超越了形式美看到內(nèi)容美,或人們直接對內(nèi)容感到美,沒有形式美。那么這個時候,是不是美的對象就可以跳脫出形式的束縛了呢?
大多數(shù)美的對象需要依托美的形式,動人的音樂要有美的旋律,美麗的畫作需要畫面布局各種高深繪畫技法,美麗的姑娘要五官端正。但是在這個多元的時代,隨著人們接受的開放,會不會聽到某個人打噴嚏的聲音也像天籟,會不會小孩毫無章法的涂鴉中也有人類最初心底純真的美,會不會某個哪怕臉重度燒傷的姑娘,也有著驚人的美麗呢?雖說大多數(shù)的美需要依托形式。但是美的對象偶爾也會跳脫形式的牢籠,被人捕捉到,并產(chǎn)生美感。
崇高最早是古羅馬美學(xué)家朗吉弩斯提出來的。生命圣化道德,恐懼是崇高的主要來源。還有一些抽象的形式。博克認為崇高的形式是無限的、巨大的、晦暗的。赫爾德認為崇高的形式是一和多,一的特質(zhì)強烈就是崇高,康德則認為是數(shù)的無限大和力的巨大。也就是知解力無能為力的事物。但是這就出現(xiàn)了矛盾,縱向是科技的發(fā)展,導(dǎo)致過去人們知解力無能為力的事物,那些神秘的恐怖的。現(xiàn)在可能一切都在人類的眼中變得不神秘不恐怖。具體來說,比如龍卷風(fēng)在過去是不可預(yù)測的。在人們遠觀的時候可能覺得恐懼害怕,在確認自己不會被龍卷風(fēng)卷入其中的時候又會產(chǎn)生崇高。這種崇高從何而來呢?因為人可以置身其外的時候,會感嘆龍卷風(fēng)的壯觀恐怖,自己在這偉大的自然當中存活下去,心中有愛眼中有如此廣袤的世界。但是現(xiàn)在,龍卷風(fēng)是可以預(yù)測的,已經(jīng)對人類不再構(gòu)成威脅,甚至連損失都可以避免,但是它依然可以是崇高的一種形式。
橫向的矛盾是,可能存在一種即使人類的知解力無能為力的形式,比如經(jīng)典的例子海嘯。處于海嘯中的人會只有恐懼,因為危及到生命,這種情況下不會產(chǎn)生崇高。但是在岸上安全區(qū)域觀看的人則會產(chǎn)生崇高。那么就這個例子來說,厲害的判斷,在審美判斷之前。是不是并沒有逃出審美活動的超功利性。也不符合審美判斷的先驗性。
二、崇高與恐懼的關(guān)系
博克說:“任何堪稱引起恐怖的事物都能作為崇高的基礎(chǔ)”。雖然說的是任何引起恐怖的事物,但是博克和康德的論述重點卻是自然現(xiàn)象。這就脫離了藝術(shù)創(chuàng)作,事實證明藝術(shù)創(chuàng)作實踐中,崇高并沒有缺席。藝術(shù)作品中同樣可以感受到崇高感,這就是對康德崇高理論不完善的質(zhì)疑。并且恐怖也不應(yīng)當僅僅包括自然現(xiàn)象,應(yīng)該包括社會歷史文化等等很多方面。阿多諾主張:“我們能夠從藝術(shù)作品所展現(xiàn)事物的高大和力量中體驗到崇高”。
崇高與恐懼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既可以是現(xiàn)實生活當中的,也可以是藝術(shù)當中的。除此之外,康德還遺漏了因為信仰民族宇宙觀的不同,會出現(xiàn)令一個種族產(chǎn)生恐懼的事物,對另一個種族則沒有這種影響。比如漢族人比較畏懼老虎,所以武松打虎是一種英雄的做法。但是納西族人卻不怕老虎,納西族人把老虎當作自己的祖先。
克服恐懼產(chǎn)生的崇高應(yīng)該是,人在面對恐怖的對象的時候感受到了自身的強大,從而產(chǎn)生了崇高。在原始社會,當人逐漸有了主體意識,從新認識了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人便開始不是完全臣服于自然。而是借助自然的力量去克服對自然的恐懼。古老的巫術(shù)儀式和祭祀儀式中,人們就認為人類可以某種方式獲得自然的力量,或是跟自然達成某種協(xié)議。比如中國的“天人合一”、“天人感應(yīng)”。皇帝在古代被看成是一個自然的象征,一舉一動都代表著上蒼的旨意。人們把對自然的恐懼轉(zhuǎn)換成了對帝王的尊敬。
三、崇高的現(xiàn)實意義
朗基納斯在《論崇高》的第七章中說:“我親愛的朋友,我們應(yīng)當懂得:在生活中為一切高尚心靈所鄙棄的東西,決不會是真正偉大的。沒有一個真有見識的人會認為財富、名譽、光榮、勢力或為榮華富貴圍繞著的一切是幸福……”現(xiàn)實生活中,崇高是一種對于人的靈魂的完善。人能夠不再原地踏步,沖破被世俗限定的桎梏實現(xiàn)靈魂的升華,是需要自我否定的能力,和面對自己的勇氣的。崇高像是耶穌那張仁慈而悲傷的面孔,當人們把對自然的崇敬和畏懼轉(zhuǎn)移到耶穌身上的時候,崇高也悄悄的住在每一位基督徒的心理。
崇高似乎總是發(fā)生在人對客體的情感當中,無論是遠古的太陽神伏羲女媧還是通過奉獻生命靈魂得到升華的英雄們,人們總是在客體當中看到崇高的光芒。蔣孔陽在《美學(xué)新論》中提出了;“崇高是人的本質(zhì)力量的自我顯現(xiàn)”的觀點。隨著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不斷提高,人們的主體意識越來越強,那么是不是就是說人類從群體回歸個體,這就使作為個體的人和崇高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呢?
答案是否定的。每一個靈魂都需要得到升華,只有險隘的人生才是始終在原地踏步。赫爾德認為:對人類的愛,是一種人道的崇高。這就包含人的道德、人對生命的愛重、人的抱負等等。這就對人的自我靈魂的不斷完善提出了要求。
無論是那些為了推動歷史進步,用自己的生命作為祭奠的人,還是傳說中為天下蒼生嘗遍了百草的神農(nóng)氏,抑或拯救蒼生功德無限的菩薩,還是只是一個平凡普通的個體。崇高是貫穿整個世界整個歷史的。崇高離生活并不是遙遠的抽象的失去現(xiàn)實意義的。
崇高來自人們追求文明的力量,來自人類道德和理智的光輝。正如復(fù)旦大學(xué)林新華所說:“因此,在多元的文化時代,我們能夠運用這種跨文化美學(xué)的分析方法,深入到不同的文化情景當中,有時甚至還要克服自身的文化局限,才能獲得崇高感。這里實現(xiàn)了崇高的主體和客體之間的一種互動”。對生命和世界懷揣敬畏之心,崇高就在離我們不遠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