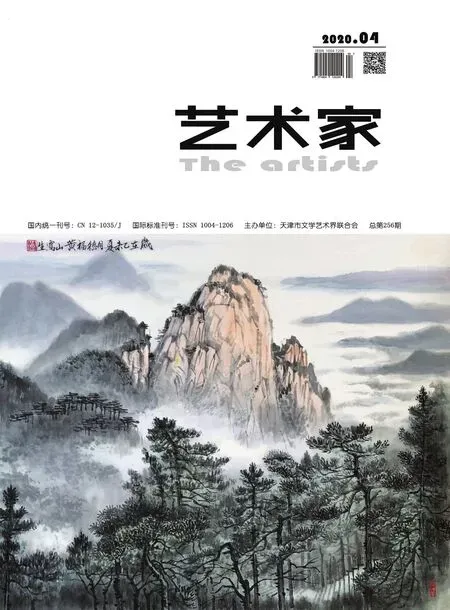論鄧椿《畫繼》中的鑒賞標準
□葉沁怡 華南師范大學美術學院
一、畫者,文之極也
“畫者,文之極也”是鄧椿提出的新觀點,意思是說畫是文化的最高境界。繪畫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被人們認為是俗工的技藝之事。《歷代名畫記》中有太宗召閻立本寫生的記錄,說道立本“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揮丹青,目瞻坐賓,不勝愧郝”,由此可見,當時畫家和繪畫的地位都很低,沒有被看作是和詩文一樣能抒情達意的藝術。
到了南宋初年,鄧椿一反舊習,把繪畫當作“文之極也”,不得不說這是一個石破天驚的轉變。因鄧椿父祖皆喜收藏名畫,所以他自小受家族藏畫氛圍的熏染,培養了獨特的眼光。《畫繼》中說道:“其為人也多文,雖有不曉畫者寡矣;其為人也無文,雖有曉畫者寡矣。”這一觀點把繪畫抒情寫意功能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后來,隨著文人畫地位的提高,文人士大夫開始逐漸參與繪畫作品的創作與品題,說明繪畫逐漸變成人們抒情的媒介,而不再是為帝王將相繪畫或者為宗教習俗傳教的工具。
鄧椿認為天地萬物,凡是詩書文能表現的,繪畫也能通過筆墨丹青來傳達,這樣就克服了繪畫只有教化作用的片面性。鄧椿還認為物也有神,要使畫作氣韻生動,就得畫出傳物之神。這是鄧椿的發現,也是對前人顧愷之、郭若虛等人觀點的發展和繼承。繪畫若只有“藝”而沒有“文”,那便是工匠之事,而不是真正的畫家。鄧椿以是否有“文”來區別畫與非畫,也就是說繪畫要有一定的內涵和韻味,這對當前的美術鑒賞活動很有啟迪意義。
筆者聯想到中國繪畫的發展軌跡,繪畫從開始的原始圖騰崇拜紋樣逐漸被帝王貴族、宗教神學等用于繪畫紀實傳教的工具,后來在各種文人思想的沖擊下,人們逐漸有了表達自己內心想法的需求,繪畫逐漸轉變成表達畫家內心所想所感的工具。由此可見,中國畫的內涵是不斷積累、不斷沉淀和不斷豐富的。筆者認為,現代藝術繪畫早已不是原來為宗教、為宣傳而服務的工具了,當代繪畫家們應該把自己作品中的“文”放在首位,即作品中所蘊含的哲理內涵。聯想到如今很多人在創作時只是依據照片作畫,作品雖是寫實卻少了一些韻味,顯得死板僵硬。繪畫比照片更有生動性的地方就是,繪畫是畫家藝術加工后的產物,國畫講究的“虛實相生”,這樣才能更好地體現畫中意境。所以繪畫并不是把眼前所見完全畫出來,而是需要有一定的取舍,才能體現其“文”。
二、獨推高雅的鑒賞觀
鄧椿推崇逸品,以高雅作為品鑒的標準。他“既不滿宋徽宗之尚法度,亦不滿石恪等之放佚”,他說:“鑒賞家分品有三:曰神、曰妙、曰能,三品之外,更增逸品。然乃以逸品為先,其余三品次之。”而宋徽宗推崇以逸神妙能為次。由此可見,鄧椿獨推高雅,注重欣賞繪畫的逸品。
宋徽宗皇家畫院推崇法度,審美注重法度和形似,畫院的考試也以此為評價標準。《南宋畫院錄》中提道:“畫以史稱豈能逞玩好以娛心目哉。”由此體現了畫院作畫的嚴格要求,敘述了畫院的倫理功用,而且極力追求形似,以摹畫為能事,排斥“以玩好之心娛目”。但是,這正是表現畫家個性閃光和抒發情感的地方,所以畫院里的畫師們都變得毫無個性,只能算“藝術工作者”或者是“流水生產的繪畫機器”。
鄧椿提倡繪畫應該跳出形似的狹小圈子,體現作者本身的“意趣”,尊重畫家自身情感的表達和抒發。所以他不滿宋徽宗的專尚法度,而把逸格放在繪畫鑒賞的首位。雖然他對崇尚法度有所不滿,但是他從不排斥“形似”,只要立意繪畫手法新穎,即便畫院的畫也是值得肯定的。鄧椿所指的“逸格”是既不拘泥形似與法度,又不流于狂放、詭異的一種審美標準,他提倡的高雅也是從“立意”上著眼的。在皇帝崇尚法度的年代,鄧椿獨推逸格、高雅的鑒賞標準,是站在時代前面的,是超前的意識觀念,也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鄧椿《畫繼》中體現了他獨具高雅的藝術審美眼光,他是在前人經驗的基礎上探究出自己的獨特觀點。每位畫家的風格、技巧各有特色,但人的格調卻有高低之分。格調是通過風格、技巧折射出來的審美意趣,而“逸品”的審美意趣源泉是“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的人生體悟。所以,我們在今后的藝術創作中要注意“逸品”“格調”,要想讓繪畫中真正有“文”,就要不斷提升自己的審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