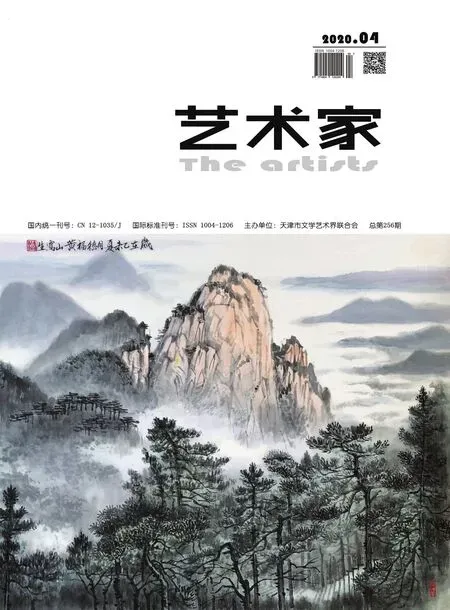新媒體時代藝術傳播形態研究
□張皓 浙江傳媒學院設計藝術學院
藝術離不開傳播,藝術家創作出來的藝術作品總是希望能夠得到更多展覽展示的機會,得到各種傳播媒介的推送,獲得一定程度的批評和認可,這是藝術世界中至關重要的一個環節,也是藝術作品得以真正完成的最終步驟。哲學家貝克萊有句名言:“存在即被感知。”要讓藝術得以存在,就必須得到人們更多的欣賞和解讀,否則就無法實現其存在的價值意義。藝術的創新和發展,包括藝術家的聲望和市場價值的提升都離不開藝術傳播的巨大推動力。尤其在進入新媒體時代的今天,發達的、迅捷的全球化傳播交流網絡已經構成我們社會的基本根基,藝術自然也要與時俱進,逐漸建立一種與之相適應的表現形態,形成新的傳播形態。這種傳播形態已經不僅僅是對藝術主題、內容的傳播,而是更側重對于藝術本身觀念的重大變革。
首先,非常重要的一個變革就是藝術越來越趨向于日常生活化,真正實現波依斯提出的“人人都是藝術家”的觀念,實現從現代主義時期就推動“藝術與生活的統一”的理想。如果仔細考察藝術史,我們可以發現藝術有著一個逐漸脫離特權階層向更為普羅大眾層面傳播擴散的漫長演化進程。在藝術產生之后的漫長時期內,無論中外,王公貴族和上層官僚階層作為藝術的重要贊助人和受眾主體,幾乎完全掌控著藝術創作的主題、內容和展示、表現形式,藝術家的社會地位也較低,只是眾多手工行業中的一種,也普遍缺乏文化知識。雖然在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開始獲得較多尊重和一定的自主權,在文化上也因為時常和當時有識之士交流,地位獲得較大提升,但在整體上依然依附于上層階級[1]。從19 世紀30 年代開始,西方許多重要的面向大眾開放的博物館相繼設立,如柏林的博物館群、巴黎的盧浮宮、佛羅倫薩的烏菲齊、西班牙的普拉多、英國的大英博物館、維也納的藝術史博物館等,這也讓藝術傳播的受眾得到了全面拓展。原本只供少數人欣賞和觀摩的皇家私人藝術收藏開始面向全民開放參觀,并且逐漸轉化為全民族的、國家的文化象征,藝術也由此邁向了走入日常生活的第一步。工業革命帶來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第一個推動力,進一步打破了特權階層的審美趣味對藝術的控制,讓藝術家全面獲得了藝術的自主權,也極大地加大了審美觀念的傳播。
大工業機器的生產和消費社會的形成,火車、汽車、電報、電話等快捷交通、傳播技術的相繼發明和運用,使現代化都市生活日新月異,流動不居,這也讓藝術家們不再滿足于建基在古代傳統典范之上的藝術規則和審美趣味,而是希望用新的藝術語言去表現節奏更快也更為雜亂多元的現代日常生活景觀。印象主義畫家開始用散亂的點狀筆觸捕捉轉瞬即逝的微妙光影以及新興中產階級豐富多彩的休閑娛樂生活,成為波德萊爾所稱的“現代生活畫家”。“現代性就是過渡、短暫、偶然,就是藝術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變。”只有通過對一切組成這個時代外界生活的事物進行細致的研究,提取人類生活偶然加進現代性的神秘之美,才能理解當今美的特殊本質,使“現代性”獲得新的永恒,形成審美泛化趨勢。對流光溢彩的日常生活的追逐,使藝術家以反叛者的姿態以機器美去替代古典雕塑的美,引發了現代主義的革新浪潮。作為最具反叛精神的達達主義的傳承者,杜尚不斷挑戰各種藝術觀念、藝術機構,他的作品“三種不同尺度的繩子”就是以改變“米”這一標準的長度度量標準來嘲諷所有的藝術規范。而他著名的命名為“泉”的小便池作品,便是以完全日常生活化的工業產品去挑戰和揭示某個展覽主辦方所提出的看似寬泛自由、沒有偏見的藝術評價標準背后所隱藏的標準,使思想和相互作用的新形式創造成為可能。
現代主義藝術以一種類似新聞報道般的求新求異的方式和手段進行傳播與擴展,而一項重大技術的發明則在進一步拓展了藝術傳播形態的同時,也開始瓦解藝術家對藝術的掌控權,讓更多的人能夠介入藝術的創作和審美趣味的爭奪中,形成更為多元的藝術發展格局,這就是照相機的發明和普及性。本雅明從照相機以及攝像機的發明和運用中感受到這些低廉的“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不僅讓高貴的藝術作品達到前所未有的傳播廣度和深度,并且還能夠被所有人自由截取、修改和挪用,完全深入社會的內部肌體之中,改變了人們感知藝術的方式,不再是靜觀默思,而是運動游走。藝術作品被賦予的獨一無二的“光暈”被消解,從膜拜價值轉變為展示價值。而處于如今建基于數字和網絡技術之上的新媒體時代,藝術作品的生產和復制技術更為方便易得和便捷修改,圖像的展示功能占據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每個人都能夠像杜尚一樣,可以隨意在著名的“蒙娜麗莎”臉上畫上胡子來表達自己特立獨行的姿態。因此,從如今的傳媒技術層面來說,藝術和生活的統一思想在新媒體時代已經基本得到了實現,生活就是藝術。魯爾瓦·納格姆在《日常生活的革命》一書中說道,如今的時代已經從之前為宗教、階級等崇高意識形態的革命轉變為更為淳樸的日常生活的革命,追求“生活高于一切”的訴求。人們認識到,要在每個人都具有的生活意志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社會,在“以全民享受為目標的自我享受”的基礎上描繪一幅社會藍圖,從而完成從非人性的歷史向人性的現實的轉變。
藝術和日常生活的融合,導致了藝術終結理論的產生。利奧塔在1979 年出版的《后現代狀態:關于知識的報告》一書中就闡述到,從“二戰”之后,尤其是60 年代前后以信息化為特征的后現代社會的到來,建基于理想基礎上的科學話語逐漸沒落并失去其合法性,導致宏大敘事的終結,進入了文化多元共生時代,一個更具日常生活性的時代。美國哲學家阿瑟·丹托和德國學者漢斯·貝爾廷都不約而同地撰寫了有關藝術終結的論著,雖然兩人的思想觀念并不完全一致,但他們都看到藝術和生活相對清晰的邊界已經被打破,藝術的地位和性質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藝術走向哲學化、觀念化,不再有進化論上的歷史發展意義,從宏大敘事轉向日常私密敘事。那么向死而后生的藝術將不再是依賴實際的物質媒介而存在的通常意義上的藝術,也將不再具有明確的創作者和觀看者的區分。藝術或非藝術只依賴構成藝術世界的社會情景也依賴傳播效應,這些決定性因素都是不斷流變的,沒有固定物質實體的觀念形態,藝術也因此進入一種非物質的形態中。
藝術傳播中非物質性的形成,一方面體現在新媒體數字化和網絡化技術形態中,更重要的是體現在藝術對觀念性的側重上。藝術作品本身已經不再重要,藝術是為了傳播和建構一個事件或情景,提供一個公共領域,一個能夠遠程交流互動的平臺,讓日常生活中孤獨、自閉,渴望真誠、自由與愛的人們能夠從中得到一種歸屬感和認同感,并且能夠激發人們的認同感和新觀念的擴散。這種情景類似于普魯斯特在《追憶似水年華》中品嘗“瑪德琳蛋糕”時的情節,那似曾相識的味道觸發了普魯斯特對一件往事的不盡追憶,連綿思緒總是于不經意中從看似極為平常的事物中激蕩開來,猶如落入平靜水面的樹葉激起層層漣漪,不斷播撒開去,激發出人們潛藏在內心深處的記憶以及與之伴隨的情感,撫平傷痕,打破偏見,突破局限,讓人更具包容性和開放性,推動新的創造力的爆發。這種日常的、偶發的卻能帶給人久久難以忘懷和難以平復的心動感受的奇異時刻正是藝術應該達到的傳播效果和目的,也是藝術創作所應該的前進方向。
1985 年,法國哲學家讓-弗朗索瓦·利奧塔(Jean-Francois Lyotard)推出了“非物質”展,集中探討當時剛剛展現其改變社會的巨大社會影響力的網絡和計算機技術在藝術層面的人與物質關系的變革,追問“信息化社會”中的人作為存在者的理念以及獨特的知識狀態。產生于計算機和電子技術的“非物質”不再是實物的物質,而是對“人”的意識和自由身份的一種解構。人的大腦皮層如同電子場或一個復雜的化學組織,“由媒體所傳達的信息組成,并與各種符碼發生臨界接觸,‘翻譯’就是在這個臨界處發生的”[2]。非物質的時空環境是一個充滿流動的信息和不可見界面,消弭不同領域之間界限的時空,沒有中心和邊緣、內部與外部之間的對立和明確的標識和邊界。這次展覽不同于現代意義上的憑借天賦和智慧以及想象力和意志力去創造新的事物的藝術創作觀念,其不突出作品和個人,而是強調事件和多重敘事,是一個參與式的平臺。人類主體在其中只是一個翻譯者,即以人類的神經組織致力于對未知信息的收集、獲得和重組。一切知識都感官化和情緒化了,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對知識給予視覺化(影像化)和聽覺化的處理,重新激活和強化了圖像與聲音傳輸信息的能力。
未完成態是新媒體時代藝術傳播的第三個重要形態,強調了藝術不斷生成、流變的特質。游牧式網絡形態催生了追求行動和語境,推動了參與性、互動性和合作性,關乎過程而非物質的藝術形態。薩拉·庫克提出了相應的新媒體術語:合作(collaborative)、分布式(distributed)和可變的(variable)。這三個特性使新媒體時代的藝術不會出現合法的、讓人崇拜的當代藝術體系,自由游走在歷史的控制和無趣的規章外,也使其更注重新技術帶來的激發各種創造思維的可能性。新媒體時代的藝術作為一種當代前衛的編碼方式,具有一種“元媒體”特性,呈現“再媒介化”(remediation)傾向,以新的媒體形態去更新前一種媒體形態,形成一種傳遞或傳播過程的美學,定義作品的語境就是網絡和系統本身。所有藝術都是一個媒介化過程,即通過媒介自身來媒介化某種思想觀念。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新媒體時代的藝術作品就是要能夠驅動觀眾之間的對話和交流,創造有傳播性的事件,交流本身就是作品。
從尼采宣布“上帝已死”到羅蘭·巴特宣布“作者已死”,再到阿瑟·丹托和漢斯·貝爾廷的“藝術的終結”,清晰地呈現了藝術從神到精英再擴大到大眾的傳播進程,藝術的權威性和體系化也在這個進程中得到完全顛覆和革新。新媒體技術只是加速了這一進程。非物質性和未完成態作為藝術進入日常生活狀態的具體表現,消解了對藝術完全操控的可能性,也使完整實體性的藝術作品概念也不復存在,有的只是圍繞藝術“文本”的多元化和微觀化的闡釋。德勒茲非常強調差異與生成(difference and becoming)的思想觀念,批判傳統建立在“存在與認同”(being and identity)基礎上的思維模式,堅持一種生成(becoming)而非存在(being)的生成論美學,這種美學顛覆了柏拉圖主義及摹仿論傳統,認為不再有某種源頭或存在作為生成的基點,消解柏拉圖式的原本/摹本、真實/虛假的二元對立觀念,以活力論的多元視角對傳統的人類主體論視域解轄域化,使德勒茲的后結構主義思想游牧成為可能。一切存在皆不過是生成生命(becoming-life)之流中的一個相對穩定的瞬間。而驅動這種川流不息的生成變革的力量來自人內心渴望擺脫權威束縛的欲望。欲望不斷運動,探尋各種逃逸路線或出路,總是拒絕被最終具象化。個體身份也因此呈現出形態復數,通過不同的行為和干涉關系形成多元的身份,生成就是存在的本質[3]。
法國學者安德烈·馬爾羅深受以攝影為代表的機械復制技術所帶來的藝術傳播的巨大影響的啟發,提出了創建“無墻的博物館”的想法,消弭藝術作品于觀眾在物理距離與心理距離的隔閡,但這一理想在新媒體時代的數字和網絡技術普及之后才真正獲得實現的可能。只是這種實現并非僅僅將藝術簡單用新媒體呈現,新媒體時代的藝術所要實現的目標是要創建一種平均分布的有生命的信息空間,一個能夠推動相互交流、合作的透明、靈活、富有創造性的空間,創造人們與藝術直接“交流和對話”的機會,拋棄偏見、突破束縛,主動地介入和參與藝術創造過程,以充滿生命力的態度去獨立思考、自由創作和傳播,建構德勒茲在“塊莖”理論中所描繪的一種新的思維模式,一種非中心化、非統一化、非層級化的傳播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