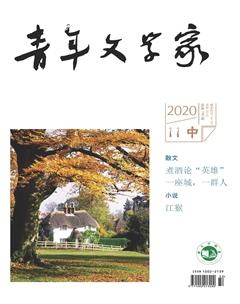試論葉芝《駛向拜占庭》中“拜占庭”符號的隱喻特征與象征意義
摘? 要:著名的前期象征主義詩人葉芝在其《駛向拜占庭》一詩中,建構了“拜占庭”這一多義性的象征形象。在本詩中,拜占庭不僅是審美對象的復合象征、東方世界的奇幻想象,更連接了古典世界,此岸世界與彼岸世界。詩人在塑造拜占庭的形象時,對這一象征形象進行了唯美的處理,而歷代文學批評家對于這一形象論說不一,都做出了自己獨到的闡釋。本文將試圖闡釋拜占庭這一符號的隱喻特征與多重象征意義,從而對詩歌中象征主義手法的運用有整體的把握,并進一步管窺葉芝的生命哲學。
關鍵詞:葉芝;象征;符號;拜占庭
作者簡介:王堯(1999.7-),男,漢族,北京市人,中國石油大學(華東)本科在讀,專業:漢語言文學。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32--02
一.引言
羅馬帝國在滅亡五百年之后,它的文化遺產卻并未湮滅,而是在東歐保留了下來。拜占庭帝國繼承了古希臘與古羅馬殘存的遺產,在未來的數個世紀,成為了東歐重要的文化中心,起到了興廢繼絕的作用,并獨自點亮了黑暗的中古時代漫長的夜空。正如恩斯特·康托洛維茨在《國王的兩個身體》一書中所引用的那首敘事詩所言:
你們的皇帝已經在許久之前拋棄了你,羅馬,
你的榮耀和名號已經消失不見,去向了希臘……
如花綻放的拜占庭現在被認做是全新的羅馬,
古老的羅馬,道德衰頹,壁畫脫落,是你的命運。[6]
如花綻放的拜占庭,因其深邃悠遠的歷史,夢幻燦爛的文明,自然也成為了愛爾蘭詩人葉芝所中意的審美對象。對于歐洲文明的童年——古希臘的緬懷,是自18世紀以來屢見不鮮的母題。如《希臘古甕頌》,《哀希臘》等。1927年6月,葉芝在都柏林圖書館閱讀了天主教會所編撰的上古歷史著作《歷史之花朵》后,出于對逝去文明的緬懷,于次年即1928年創作了不朽的名篇《駛向拜占庭》,并于1930年創作了續詩《拜占庭》。而在《駛向拜占庭》這首詩中,對于拜占庭這一核心象征形象,葉芝對其進行了高度濃縮的加工,以其境界和情思的朦朧,內涵的多義性,給閱讀受眾提供了多種解讀的可能。
誠如葉芝本人所言,“詩歌之所以引起我們的共情,只是因為它是象征主義的”。由此可見,象征主義,是葉芝衡量詩歌藝術水準高低的重要準繩。顯然,象征主義詩歌力圖規避外部描寫的傾向,而是“向內轉”。但是內心的情感與直觀卻需要外化才能獲得豐滿的具象。為了探尋“象征的森林”[3],將可感的物質與超驗的內心相統一,葉芝一派詩人才廣泛的運用暗示等手法,并且頗為強調詩歌的神秘性和音樂性。而象征符號的對象化,則是完成這一探尋過程的必要環節。正因如此,我們需要破解《駛向拜占庭》一詩中的核心象征符號,即“拜占庭”本身。而破解這一符號,需要通過對拜占庭這一象征形象本身加以闡釋,并對其象征層進行剖析。
二.拜占庭的表層境界——光怪陸離的東方
1.異域風物的書寫
葉芝在詩中,首先建構了奇幻絢爛的東方世界,并成為了拜占庭的第一重象征層。詩人運用怪誕華美的詞匯,別出心裁地創造出異想天開、從未有過的意象。強烈的主觀色彩常表現為意象復合的“通感”,往往能夠化腐朽為神奇,化平易為驚險、瑰麗,塑造了一系列鮮明瑰麗的異域風物,如圣火,鑲嵌磚,金銀器等,可謂奇崛險怪,風格獨特。
對于東方異域文明的書寫與想象,在浪漫主義勃興的年代已然蔚然成風。如英國大詩人拜倫的《東方敘事詩》系列、《恰爾德·哈羅德游記》、《唐·璜》,以及雪萊的《伊斯蘭起義》、《麥布女王》等等。汗牛充棟,不勝枚舉。而拜占庭,作為東歐與西亞文明的薈萃之地,自然也是異域文明敘事書寫的不可多得的完美對象。拜占庭文明吸收了希臘、波斯、土耳其、阿拉伯多種文化內核,博采眾長,文化多元。較之西歐人來說,是“他者”的哲學范疇,具有濃郁的東方風情與神秘氣息。在《駛向拜占庭》中,牧師們“立于神的圣火之中”,金鳥“在純金的樹枝上歌唱”[1]讀來令人滿口生香,使得審美主體不由得浸潤在濃郁的異質神秘文化氛圍之中。
2.審美主體的個人偏好
葉芝本人有著強烈的貴族情結,在他的認識中,只有貴族才有豐富的知識,與良好的教養,才能真正傳承優秀的文化和藝術。然而,葉芝眼中的貴族并不是按照血統或物質財富來區別于平民的,而是精神上的貴族。正是這種貴族主義的傾向使得葉芝把目光投向了東方——以中世紀拜占庭王國為代表的貴族文明。在古羅馬的奴隸制貴族制度崩潰,西歐進入軍閥混戰和封建割據的灰暗年代,拜占庭王國保存了古希臘文明的火種。
對于自己的祖國,葉芝具有著復雜的感情。在詩人看來,“道德敗壞”是祖國的重要屬性,而這種道德的喪失不僅由于英國人對愛爾蘭社會長期的文化入侵,更在于資本主義時代的到來,將愛爾蘭人庸俗化,使得愛爾蘭人失去了貴族精神。對于已是耄耋之年的詩人,古老的拜占庭與墮落的祖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拜占庭,象征著萬世不朽的永恒力量。
正因如此,創作主體強烈的主觀情感取向,也就自然而然的被注入在這首詩歌之中。正如葉芝在其《詩與傳統》一書中所言的那樣:“祖國,我看清了你,所以新的象征物正在等待我的追尋”,“對于我來說,等待我的那個象征物,那就是拜占庭王國。[2]”
3.穿越時空的激情
自1453年拜占庭文明毀滅,至葉芝創作本詩的20世紀20年代,已是五百年有余。亡故的國家,到處可見的城跡,殘留的石墻,不僅引起了詩人的懷古憂思。另一方面來說,愛爾蘭孤懸北海,拜占庭則位于黑海之濱,可謂山川相阻,路途遙遠,詩中的主人也只得“駛過汪洋和大海萬頃”[1],方才得以一窺這座異域之都的風貌。時間與空間的雙重距離,大大強化了詩歌風物的“他者”特征,也增強了詩歌整體的審美蘊藉。
詩人希冀抒發他的情感,然而在氤氳著這些情感的原型中提取素材,也就需要合成與其相切合的意象符號。正如卡西爾所言,“所有的文藝形式都是符號形式。[7]”詩人將歷史現實的拜占庭抽象為意象符號,然而還需要加以還原成象征意義豐富的象征物,才能最終完成意象的建構與實現過程。因此,“拜占庭”所代表的同歐洲異質的東方世界鏡像,只是這首象征意義濃郁的詩歌的表層意象。
三.拜占庭的深層境界——愿為金色的鳥兒
在表層意象之下流動著的,是葉芝所隱喻河暗示的深層次意象。
形象學理論家亨利·巴柔認為,“一切形象的生成,在于主客意識的分化,出現了‘本體與‘客體,‘自我與他者,‘本邦與‘異鄉等等關系的對立之中[7]”。通過對拜占庭這一東方異國的書寫,葉芝為自己塑造了一個理想的國度,在詩中建構的鏡像世界中,年輕人“都迷戀于種種肉感的音樂,忽視了不朽的理性和杰作。”但“一個老年人不過是卑微的物品,披在一根拐杖上的破衣裳” [1]。靈與肉的對立,生與死的對立,此岸世界與彼岸世界的對立,是西方文學史中永恒的主題。生命短暫如白駒過隙,青年時代沉溺于肉欲享樂,帶來的卻是老年后的精神與肉體的雙重空虛。面對死亡這一不可避免的永恒歸宿,詩人提出了一個獨到的解決方案。即是將靈與肉相分離,讓靈魂脫離肉體的羈絆,在高貴的古典藝術品中追尋彼岸世界的永恒價值與精神自由。
然而,令人痛惜的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人與人關系的異化,金錢拜物教的統治一切,以及世界大戰對于歐洲的摧殘,祖國愛爾蘭的骯臟,天主教派別與新教派別的內斗,葉芝悵然中明白,在丑惡的現實社會“沒有音樂院校誦吟古典的輝煌藝術品。[2]”于是,拜占庭,這一歷史象征,被詩人化用作彼岸世界的寄托,那是一座永恒之都,有著金枝,金鳥,圣火,馬賽克壁畫的古典大城,是人類歷代所有古典美的結晶。超脫于污濁的現實世界,是一個文化藝術所臻萃的伊甸園,只有崇高,典雅與圣潔。正如符號論美學家蘇珊·朗格所言:“藝術家表現的絕不是他自己的真實情感,而是他認識到的人類情感。一旦藝術家掌握了操縱符號的本領,他所掌握的知識就大大超出了他全部個人經驗的總和。[4]”這句話雖有所偏頗,但詩人葉芝在其創作中,正是以其對于人類普遍情感的真切把握,寄托于“拜占庭”這一唯美的符號,為我們展開了一幅人類至高美與至高純潔的藝術畫卷。
葉芝曾在《幻象》一詩中,對于歷史的本質作出了獨到的判斷,即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循環的過程,日光之下,并無新事。而《駛向拜占庭》詩中的主人公,愿意“把我放在那金枝上作為一只金鳥歌吟,歌唱那過去和未來或者是當今,唱給拜占庭的貴族和平民。[1]”流動的時間長河,在葉芝的筆下,圍繞著拜占庭永恒循環,拜占庭代表著古典的世代,此岸的世代與彼岸的未來。而靈魂,只有融入拜占庭,才能不受生死的拘束,不懼時間的流動,永葆青春的容顏。正如葉芝在《老人臨水自賞》中借老人之口寫道:“凡美麗的終必漂走,如流水一般。”[1]寫作《駛向拜占庭》時已是風燭殘年的詩人,對著歲月的長河若有所思,希冀于自己的靈魂在拜占庭的不朽藝術中得到永生。
四.結語
符號學理論家卡西爾在《神話思維的概念形式》一書中,對各種符號形式進行考察,并將它們放回到人類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去,而后,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人類的各種符號形式的形成,共同構成了人類精神成長的史詩。而在這些的形式中,語言能力和神話傳說又是最為悠久的,它們是人類的思維能力與文明文化的濫觴,更是人同動物相區別的關鍵性標志。[5]”葉芝本人也曾在《溫暖與安靜的月光》中向我們傾訴,“我盡量使我的思維下沉到意識之下,從而與宇宙萬物的精華融為一體,使其為我的創造力提供源泉,這種創造力來源于種族世世代代的文化烙印,而不在我個人;從這種暗流中,我們能夠回溯到我們的先輩乃至始祖的那些動人的神話傳說與民族史詩。[2]”
拜占庭,作為在羅馬帝國廢墟上建立的國度,其所承載的古希臘與古羅馬文化原型,深深的潛藏在所有歐洲人的集體無意識中。而葉芝以其純熟的象征主義手法,將這一文化原型賦予多重象征意義,解構了歷史上那個真實存在的那個奴隸制東方王國,而是重構了富含隱喻特征的藝術天堂,使之成為人類最高靈魂的寄托之地,從而借詩中老人之口,將作者對人類終極問題的思考與關懷予以表達。
在這首詩中,葉芝借靈魂的不朽以追求生命的永生,對年老肉體進行了決絕的摒棄,從而為富有濃郁人文主義色彩的生命哲學提供了堅實的內核。與同時代D.H.勞倫斯和T.S.艾略特等象征主義詩人對以死亡為中心的非個人化詩歌結構關注不同,葉芝為凡人“生命的完美”的實現,給出了自己肯定的回答。對于仍然無法解決生與死,靈與肉等矛盾的我們,同時又生活在后現代文明之中的我們,仍然具有著深刻的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1]袁可嘉(譯).葉芝詩選[M].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2.
[2]王家新(譯).葉芝文集[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3]查爾斯·查德維克.西方當代文藝批評譯叢:象征主義[M].北岳文藝出版社,1989.
[4]蘇珊·朗格.藝術問題[M].外文書局,1981.
[5]伊萬·斯特倫斯基.二十世紀的四種神話理論[M].中山大學出版社,1985.
[6]恩斯特·康托洛維茨.國王的兩個身體[M].崇文書局,1991.
[7]伍蠡甫.西方文論選[M].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