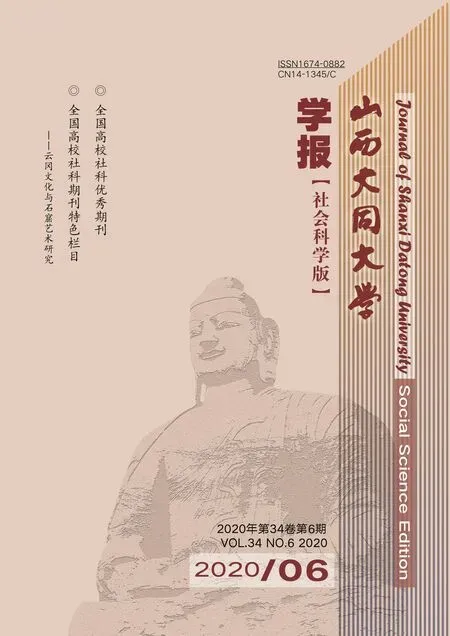斷裂與缺失:王祥夫小說“敘事空洞”策略探析
郝春濤,郭劍卿
(山西大同大學文學院,山西 大同 037009)
王祥夫曾因短篇小說《上邊》而獲得魯迅文學獎,他的小說以其充滿人性的鋪排、溫情脈脈的敘事而備受關注,作品清新雋永,意味深長,氣韻生動。王祥夫曾說:“優秀的小說家應有白日見鬼的功夫”,這種功夫不僅體現為通過精巧別致的結構、出人意料的結尾使人蕩氣回腸,還在于利用某些陳述要素的缺失,即所謂“敘事空洞”來逗引讀者持續閱讀的組構技巧,來建構小說獨有的內在張力。
所謂敘事空洞,是指敘述者對某一關鍵事件保持沉默,造成文本語義鏈的斷裂。因敘述者無心彌合這一空洞,使得這個在時間鏈上已經消逝的事件被無限期擱置,由此構成情節上的懸疑,其意義指涉被“其他事件”分化和彌散,敘事的有效領域則在于因這一空洞的袒露而凸顯出的“其他事件”的關聯組合,以及由此呈現出的別樣意義。
一、敘事空洞前置的陌生化效應
2018 年12 月,《新華文摘》轉載王祥夫的小說《棚戶區的畢爾》;2017 年12 月,《新華文摘》第23 期刊載王祥夫的散文《清蓮記》,而就在前一年,也即的2016 年,王祥夫的兩部作品被《新華文摘》轉載,分別是《窗戶人》(刊載于第3 期)和《氫氣球》(刊載于第17 期)。自《新華文摘》1982 年第6 期首次刊載其散文《荷心茶》之后,王祥夫的作品8 次榮登全國頂級哲社期刊(如2005 年第6 期刊載的小說《上邊》,2005 年第23 期刊載的小說《婚宴》,2008 年第12 期刊載的小說《看戲》,2014 年第15期刊載的小說《翩翩再舞》),其藝術價值不言而喻。這些作品以其獨特的構思、溫婉的語言、精妙的結構而動人心弦。
評論家對王祥夫的關注,大多集中于他對“底層”的書寫。檢索中國知網,有關王祥夫的研究論文共149 篇。這些論文大多集中于研究他的“底層寫作”,試圖通過“對社會底層卑微人生個體日常生存的關注”來體現底層敘事、底層經驗,也即從文本話語表達所蘊藉的意義生成的角度進行論述。而從敘事學角度研究其小說組構技巧的文章則十分少見。李云雷的論文《王祥夫的“中國故事”及其美學》認為,王祥夫“好像并不是在‘寫小說’,而只是在豐富復雜的中國經驗中剪下了一角,稍加點染,便成了一幅意趣盎然的畫、一首意味雋永的詩”,[1]論者借鑒“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傳統美學觀點觀照王祥夫的小說;王迅在《詩性在雕琢中流失》中認為,王祥夫等名家“皆以短篇體制磨煉筆法,尋求藝術形式的多元探索”,[2]但遺憾的是該文并沒有詳細論述“多元探索”的具體呈現;裴劍平的《王祥夫短篇小說文體研究》從“先鋒嘗試的現代性魅影”“由先鋒到寫實的審美轉型”“個性稟賦的自覺追求”三個方面,考察王祥夫短篇小說的文體與作家及社會文化語境的關系;[3]魏冬峰的《在“藝術”與“底層”之間——讀王祥夫的小說》認為,王祥夫小說呈現出“小”和“巧”的辯證法,在敘事張力上表現為“慢”的特點;[4]萬潞姣的《王祥夫底層敘事中的“中國故事”》關注的是其小說對“底層精神世界的深度挖掘”。[5]所謂王祥夫小說結構中的“敘事空洞”技巧,乃筆者首次提出。
《氫氣球》即是利用空洞敘事延伸語言張力的成功之作。《氫氣球》中,天健逛超市時購物袋里莫名其妙多出的一部手機,以及為尋找這部手機的主人而跟通訊錄中人物的一一對話,構成了小說敘事的基本框架。手機主人與多個男人的“曖昧”關系是通過無法查證和識別的陌生語音之間的關聯實現的,但手機來源成迷,形成了小說敘事的空洞。彌漫于小說文本的焦慮掩蓋了對手機來源的追尋,當然,敘述者顯然也沒有把彌補這一空洞當做敘事的源動力,而在于利用這種“神秘”去精心組構另一個陌生化的故事——陌生的手機、陌生的男人、陌生的關系以及這一連串陌生背后的內在關聯。敘述者以“仰敘”的角度去努力理解這個不明不白的、有別于明朗的意義和明確的關聯的世界,“我”的困惑等于閱讀者的困惑,敘述者的主體性也被這種困惑牽引和拉扯,變得無足輕重,主體性被懸隔,一種忽隱忽現的不正常男女關系反而得以浮現,由此實現了胡塞爾現象學所謂“面向事物本身”的目標,“因為只有懸隔主體性,事物才有得以顯靈的機會,才能夠以其超越的力量而顯現其本身的精神性。而能夠與事物形成靈性相通的藝術便不以人為尺度,而以萬物為尺度,這樣的藝術才有無限余地去呼應萬物,而不至于在貧乏的自我表白中窒息。”[6]和傳統敘事不同,以長度為支柱的句段存在的意義不在于集中表現某個明確的意旨,而在于通過以片段信息的透露形成的樹干式的人際關系,凸顯超市那兩個“漂亮女孩”之一(按照文中暗示應該如此,當然,敘述者也在竭力擴大這個空洞,比如也可能是到醫院探望哥哥的朋友的手機)的完全有悖于傳統道德觀念的人生態度和生存方式。文本中不斷出現的敘述漂移(如天健到醫院看望哥哥天康、找新的停車位以避免樹倒了砸壞等)只是在稀釋因陌生手機帶來的焦慮,并不阻礙事件組構的順延性,意義鏈可以跨過敘事空洞,在時斷時續的故事鏈之上,暢通無阻地生成不斷延續的縱深經驗。
二、敘事空洞“纏腰”的動力性鞭策
喜歡利用敘事空洞造成的語言張力,表現“事物本身”存在(或消失)的當下狀態,并暗示其外溢的意旨,是王祥夫許多小說吸引讀者閱讀興趣的駐足點。如果說敘事空洞設置于小說開始之處,可以一直勾起讀者閱讀的胃口;那么,將其設置于故事中段,則是“鞭打”敘事動力,讓其更為強勁的有效手段。
短篇小說《街頭》中,先用倒敘之法交代已經成為不祥之物的被警戒線圍起來的白色寶馬的車主——那個年輕美麗的姑娘和被帶走的“啞子”之間發生的嚴重事件。“啞子”在交流中存在的先天性阻礙,是構成寶馬車主蹭倒啞子正要修理的“破舊的老舊自行車”后被中年男人“胡子”欺凌、訛詐,并最終導致流血事件的癥結所在。小說中部,“人們不知道他(中年男人‘胡子’)和這個姑娘是什么關系,這個姑娘又為什么總是住在他那里”,構成敘事的空洞,但敘述者顯然無心探究這二者的關系,敘事的興趣點在于由這種不明不白的關系衍生出來的盛氣凌人的偏袒,以及“胡子”、姑娘、啞子和看不慣欺凌準備拿三千元息事寧人的“小胖老板”之間的沖突。啞子之“啞”使他無法以聲音宣示一種語域,“呀呀呀呀”模糊不清的表達,也無法形成完整的“語義鏈”,在場者與閱讀者只能通過各種非語言符號的并置,努力找到語義之間的關聯,但是,這種關聯具有明顯的不穩定性,由此產生的“間離”效果直接導致了連敘述者都無法把控的情節的出乎意料性。“呀呀呀呀”的模糊性造成了主人公、在場者以及讀者之間的心理懸隔,但“聲音就像巴赫金所說比問題具有更多的意味,在某種意義上將是超文體的。聲音是文體、語氣和價值觀的融合”。[7](P20)當啞子的“價值觀”無法用聲音在表達時,行動(刀刺欺凌者)便是他最直接的表述。
《豬王》細敘村子里70 多歲的“老光棍”劉紅橋與養了10 年多“比一般豬大得多,然后是,這頭豬簡直要長成一頭大象了,大得自己都站不起來,要人幫著它才能往起站”的豬王相依為命的故事。劉紅橋在塘沽打工摟鹽二十年卻幾乎“什么都沒掙下”,構成的懸疑形成敘事空洞,但敘述者無心填補這一空洞,其衍生出的劉紅橋“在村子里話一天比一天少,人也一天比一天孤獨,他很少去別人那里,別人也很少去他那里”構成的孤獨與寡言,使他與豬王互為一體,“斷點”的缺失反而成為情節順延的鞭策性動力。
小說《登東記》用雞蛋把廁所以及“城里人”與“鄉下人”勾連起來,“鄉下人”在不同的時間節點三次出現又轉瞬消失,構成了三個敘事空洞。一次是用雞蛋換玉米面的“山東大鼻子”,僅僅幾句對話之后便不再出現;一次是“一到冬天就過來拉大糞的鄉下人”,他們和他們的糞車一樣循環出現又迅速消失;一次是被父親領進我們家廁所的那個“臉憋得彤紅的鄉下人”,與前兩次相比,這個鄉下人在文本中“生存”的時間稍長一些,并在消失之前,留下了當時極為珍貴的10 顆雞蛋。作者無意彌補前兩個鄉下人消失形成的空洞,只是將其作為串聯敘事與時間的扭結點。結尾處的“那個鄉下人在哪兒呢?”,我站在那里想;“那個鄉下人現在在哪兒呢?”,直到現在,我還在想,則是在彌合最后一個鄉下人瞬間消失與現在想起之間的溝痕,也就是說,試圖把這一瞬間從時間序列里獨立出來,表達敘事空洞形成的“外溢”意義,也即鄉下人的淳樸善良,沒有這種“消失”,其一直黏著的“外溢”意義也會被沖淡,這樣一來,“瞬間”也就成了“實體”。戴衛·赫爾曼將這種消失的瞬間稱為“斷點”:“故事中發生斷點有兩種模式:敘事要素的暫時缺失(在閱讀過程中建構的故事中的缺失,這些斷點將在以后填補)或永久缺失(斷點將永遠保留)。”“兩種模式都顯示某些事件,以此引導包括讀者在內的敘述者的聽眾把某些事件包括在所有配置之內,而把另一些事件排除在配置之外”。[8](P24)由于敘述者的導引,讀者的興趣也不再糾纏于那些斷點,而會把注意力集中于斷點產生之后引發的溢出效應,這樣,敘述者也就成功實現了事件與主旨的配置。
三、敘事空洞后置的懸疑式揣測
將敘事空洞設置于結尾,可以呈現出惴惴不安的懸疑效果。
在《帽子橋》中,始終生活于帽子橋下的養蜂人,和他那個在菜店打工的女人,在一場突發的大雨后消失無蹤。雨后,游泳而至的老王“趴在水泥墩子上往那邊看了一下,橋下邊什么都沒有了,只有一層厚厚的淤泥”。《小河南》中,直至中午,小河南的五金雜貨店還沒有一點點動靜,當人們提心吊膽地打開幾道大門后,卻發現小河南劉金貴和他的幾個孩子莫名消失。而到了傍晚,跳舞的“鑼鼓點給這邊的河南街憑空增添了一些喜氣,人們就是在這莫名其妙的喜氣中擠來擠去,這一天就這樣過去”。《窗戶人》中,朱光大狼狽地發現對面窗戶一直有人窺探他,這種“無隱私”狀態使他忍無可忍,但當他終于敲開對面門時,才發現是一個下半截完全沒有了的殘疾人,這一瞬間讓他產生“不知對誰說對不起”的沖動。結尾處:
朱光大回臥室的時候卻發現對面窗戶人的窗子還亮著。朱光大馬上用望遠鏡朝那邊看了看,發現窗戶人在窗臺上趴著,像是趴在窗臺上睡著了,又過一會兒,朱光大又看了一下,窗戶人還在那里趴著。又過了一會兒,朱光大又看了一次,那個窗戶人還趴在窗臺上。
“肯定是睡著了。”朱光大對自己說。但朱光大自己卻睡不著了。
朱光大又下床去看了一下,那個窗戶人和剛才一樣,還趴在窗臺上。
另一部小說《饑餓》的結尾,那條因眾人饑餓而被覬覦已久的瘦狗“魚肚子”在被人打斷后腿之后陷于蘆葦叢中,“從蘆葦里鉆出來的時候,我又忍不住回頭叫了一聲,‘魚肚子——’,魚肚子又在蘆葦中嗚咽了一聲”。之后,魚肚子是否活著不再交代,形成空洞,村民的興趣已被房頂上的大蛇所吸引,“這么大的蛇,能燉一鍋肉!”“魚肚子”也便成為海德格爾所說的“存在的被遺忘”者。
藝術表達的模糊性所帶來的想象空間,使敘事的空洞彌漫出無限的引力。上述四部作品的共通點在于:現實的證據是確定的(眼見為實),但“歷史證據”的消失卻使得閱讀者無從查證這些人(動物)生存與否(想象為虛)。慣性閱讀與對閱讀的解構使讀者處于一種不平靜的猶疑中,敘事的空洞造成的斷裂需要讀者填補,這種填補只能通過似乎合理的“嫁接”而產生聯想,由此形成“但愿活著”的一廂情愿。
羅蘭·巴特把愉悅分為“文本的愉悅”(Plaisir du Texte)和“愉悅的文本”(Texte de Plaisir)。意義的愉悅有兩種:即愉悅(Plaisir)和極樂(Jouissance),它們分別和文本聯系在一起:“當我們面對作品,消費之,理解之時,我們獲得愉悅,但文本卻與極樂聯系在一起。”[9](P171)一般來說,Plaisir 代表一種狀態,而Jouissance 則代表一種行動。“在這種閱讀中,我們尋找透明的意義,有時也會出現斷裂,我們會設法填平斷裂。從總的情況看,我們要求透過符合文化習慣的、更為舒適的閱讀而獲得滿足。”[10](P185)“符合文化習慣的、更為舒適的閱讀”,意味著我們的愉悅更多來自于對上述敘事空洞的美好“臆測”,這種臆測又來源于傳統文化“大團圓”式結局的期待。王祥夫顯然不想“得罪”讀者,把美好的事物毀滅給人看,反而試圖給讀者帶來某種“愉悅”乃至“極樂”,但現實的鴻溝無法逾越,一些悲劇總在上演,于是,敘事空洞的設置正好提供了某種便利:一方面沒有違背藝術原則,一方面又把有關空洞的遐想推至讀者:是你們這樣想的!讀者在填平“空洞”的過程中也就獲得了藝術美感。
從文本組織的整體層次上考察,敘事空洞帶來的是一種“不確定性”以及由此造成的敘事邏輯無法閉環引發的不安。一般而言,敘事是對連續或片段事件的再現,這些事件按照“生活邏輯”有條不紊地進行著,敘述者通過對這些連續或片段事件的感知,構建遵循“藝術邏輯”的文本結構,不過,這種感知先天性地受到敘述視角和事件本身完整性的制約,敘述者有時通過對事件的配置與闡釋努力彌補這一缺陷(空洞),有時則故意將這一“不完整性”推給讀者,讓讀者嵌入自己的生活經驗加以完善,改變連續性敘事活動強加給讀者的確鑿意義。從上述作品分析可看出,敘事空洞指涉的事件本身已無足輕重,由此衍生出來的其他事件才是敘述者拋給讀者的重要信息,就事件的結局而言,體現為“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如帽子橋下一家、小河南一家、窗戶人、“魚肚子”的“生”或者“死”),似乎是兩個面,而事實只有一個面,讀者在這兩個面之間猶疑,迫不及待地在互為隱含、互為交融但又互不相容、互相矛盾的兩種闡釋中選擇其一。從讀者參與角度來說,這種敘事空洞產生的藝術效應,遠遠比敘述者一以貫之的大滿貫敘事完整得多,也多元得多。
必須指出的是,與傳統敘事技巧之“懸念”不同:敘事空洞之“洞”一直被擱置,是因為敘述者的平行視角與讀者所知相同,無法填平,是為“無解”;懸念則是有懸必有解,其敘述視角多為全知敘事,“扣子”松開之后給讀者造成的放松感,帶來的是“此在”之美;而敘事空洞引起的閱讀興趣,則更多體現為跨越空洞后突然呈現的“別有洞天”,以及由此產生的“風景這邊獨好”的“彼在”之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