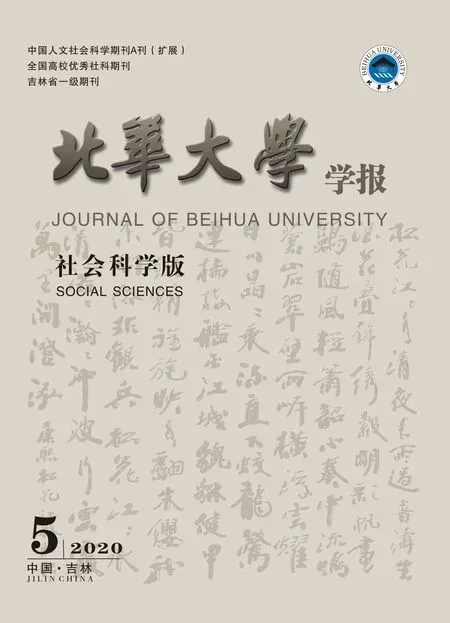創傷與記憶:日軍侵華暴行公共記憶的重構
宮健澤
引 言
自1972年中日建交以來,兩國在前30年間相互關系平穩發展并取得重大成就,盡管其間出現過各種問題,但總體上中日友好不斷深入人心,合作關系不斷擴大,民間友好不斷加深,雙方關系密切前行。
在2000年前后,中日由于歷史問題導致政治關系出現倒退,影響雙方政治互信的主要是歷史遺留問題和領土問題,諸如中日釣魚島問題,日本否定侵略的教科書事件,日本政要參拜為軍國主義招魂的靖國神社事件,以及否定南京大屠殺和“慰安婦”歷史等。現實中日關系中存在的其他分歧與問題,如安全保障存疑,隨著中國國家綜合實力的逐步提升,日本國內普遍產生一種恐懼心理,這一方面由其島國天然危機感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其企圖領導亞洲的傳統軍國主義觀念作祟。
經濟合作方面的東亞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簡稱FTA)難產。建立中日韓自貿區是個呼吁多年的倡議,由于種種原因至今尚未實現,雖然中韓沖破層層阻礙建立雙邊的FTA,但是距離當初中日韓自貿區的設想相去甚遠。要想實現東亞中日韓FTA任重而道遠,其中中日關系的和平友好至關重要。
中日釣魚島爭端后,在國民好感度民調方面的中日兩國國民彼此好感度下降,由于受中日關系政治環境和國際日美同盟意識形態的影響,日本民眾對中國好感度下降。因此,加強中日民間交流特別是青年人對彼此的了解非常必要。南京大屠殺與“慰安婦”等歷史問題也是橫亙在中日之間的現實問題,日本的態度決定中日關系改善的程度。
一、不能遺忘的創傷:歷史上的日軍侵華暴行
明治維新后的日本,隨著國力逐漸增強,開始走上對外擴張侵略的道路,由于地緣因素,日本周邊國家朝鮮、中國成為日本向外擴張的首要目標。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積貧積弱的清政府以完敗日本而結束戰爭,戰后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賠償日本白銀兩億兩,相當于當時每個中國人需要賠付一兩白銀。在隨后的中日關系中,日本通過1904年的日俄戰爭,打敗俄國,占有俄國在中國的租界,將日本勢力進一步滲透到中國的內陸。1926年,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向天皇提交奏折,指出:“日本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欲先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這就是有名的“田中奏折”,也成為日本開始向外侵略的指導性文件。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入侵沈陽,進而侵占整個東北。1937年發動盧溝橋事變,開始全面侵華戰爭,迅速侵占整個華北,進攻上海,占領南京。1937年12月13日,占領南京城后,實施了駭人聽聞的屠殺中國士兵和平民的暴行。根據戰后東京審判和南京審判結論,日本在南京實施為期6周的集中屠殺,加上后期陸續的零星屠殺,總共屠殺南京市內軍民30萬人以上,這是鐵的事實,不容抵賴和否認。東京審判法庭判定:“20萬人以上……不包括拋尸長江、挖坑掩埋和以其他方式處理的尸體在內”的數字,南京審判法庭認定“集體屠殺28案,19萬人,零星屠殺858案,15萬多人,死難人數達30多萬”[1]的數字,日本南京大屠殺人數已有歷史結論和法理定論。
南京大屠殺慘案只是近代以來日本侵華所制造的眾多屠殺慘案之一,其他還有許多屠殺慘案,按照時間先后順序有,旅順大屠殺、平頂山慘案、上海屠殺等。其中旅順大屠殺發生在中日甲午戰爭期間。自旅順大屠殺發生后,盡管當時的日本政府曾一度試圖掩蓋事實,但國內外有良知的媒體記者、學者沒有停止過對真相的探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當時美國《紐約世界報》的隨軍記者克里曼的長篇紀實報道,真實還原了當時旅順被攻陷后日軍的暴行;英國人詹姆斯·艾倫在其所著的《在龍旗下——甲午戰爭親歷記》一書中,以目擊者的身份,細節呈現了日軍在旅順虐殺中國人的情景;民國學者孫寶田于1935年在日本殖民下的旅順冒死查證,終得匯編《日寇旅順屠殺兩萬人》一文;王蕓生的《六十年來中國和日本》也對日軍在旅順的屠殺做了詳盡的記述。平頂山慘案也稱為撫順大屠殺,發生在日本侵華的九一八事變之后,是日本軍國主義者在侵華期間犯下的又一重大罪行。與旅順大屠殺類似,日本侵略者在事后采取了一貫的毀尸滅跡的齷齪行徑,企圖完全銷毀暴行罪證。平頂山慘案史料的支撐也主要是基于美國記者愛德華·威廉·懷特“搶救性”的實地調查與日本投降后戰犯的供詞及目擊者的證言等。
中日學術界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慘案實際狀況的考證、慘案規模以及對幸存者進行的口述調查。如佟達的《平頂山慘案》、周學良的《撫順平頂山慘案紀念館故事》以大量史料為依托,全面披露了平頂山慘案發生的全過程,成為研究該慘案的重要參考。日軍在上海制造的屠殺慘案,主要表現在屠殺平民和戰俘,屠殺平民主要集中在上海市區和郊縣,據統計,“自戰爭開始,至10月21日,在公共租界內為日方流彈擊中死傷人數即高達5 000余人,其中死者計2 057人,傷者2 955人。至1937年底,公共租界工部局統計的界內華人死亡人數已高達35 171人。在上海郊縣的屠殺就更加血腥和肆無忌憚,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法西斯的極端殘忍和殘暴性。僅寶山、金山、奉賢、南匯、松江、崇明等上海郊縣的部分暴行統計,侵華日軍就屠殺無辜百姓15 488人。”[2]
日本人認為,“中國人沒有完整的戶籍法,特別是兵員之中流浪者很多,如果將俘虜殺害,同釋放到其他地方一樣,在世界輿論上不會出現問題。”(1)此處引文參見日本陸軍步兵學校內部資料《對中國軍戰斗法之研究》(日本陸軍步兵學校,1933年第32頁)。為了實施恐怖威懾并消滅中國抵抗力量,日軍在上海戰場上,更是明目張膽地野蠻屠殺中國俘虜,據中方資料記載:“1937年9月16日,日本上海派遣軍一部從上海羅店撤退時,將被抓來的十幾名中國傷兵釘在墻壁上,用刺刀一個個開了膛,還割下傷員腿上的肉喂軍犬。”[3]
以上三次大屠殺與南京大屠殺相比,無論在規模上還是人數上都無法相提并論,但是這些屠殺反映出日本侵略本質是具有同等效力的,正如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張建軍所言:這些慘案,無論說3千人,3萬人,還是30萬人,它的性質都是一樣的,每一個慘案都是日本軍國主義反人類的罪行。而我們開展此項研究的目的正是為了要更好地追思過去,關照當下,面向未來。
對于日本侵華期間所制造的屠殺慘案、屠殺平民和戰俘的違反國際法的行為,這種戰爭犯罪行為超出正常人類所能想像的認知范疇。日軍的行為與戰后中國實施的遣返日本僑俘行為形成鮮明對比,在戰爭結束時,中國戰區日本僑俘人數不少于300萬人,國民黨政府采取“以德報怨”的政策,與共產黨合作,在美國的協助下,全力遣返日本僑俘,沒有發生一起報復和屠殺行為,這在國際戰爭史上也屬罕見。對于此舉,當時的日本政府也是感恩戴德。與此對比鮮明的是,處在蘇聯占領區域內的日本僑俘命運就沒那么幸運了,他們被蘇聯拘留,進行勞動改造,許多人被疾病和虐待致死,終其一生沒有返回日本。對此,日本一直耿耿于懷,曾經在201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南京大屠殺檔案》列入“世界記憶名錄”時,為了表明日軍也是受害者,多方搜集戰時日軍資料,并欲將這些資料申報為世界記憶遺產。于是日本欲將當時接收遣返日軍僑俘的“舞鶴遣返紀念博物館”資料整理申報世界記憶遺產名錄。在日本戰敗后,約有60萬—80萬軍人和平民被拘留在蘇聯勞改營,“舞鶴遣返紀念博物館”保存了1945—1956年有關拘留和遣返人員的詳細記錄。對日本此舉,俄羅斯外交部批評了日本的這一做法。
對于日軍屠殺中國的俘虜和平民,在東京審判的判決書中也有指出:“被捕的中國人,其中許多人都被拷問、屠殺,編進勞動隊中為日軍做工,或者是被編入偽軍中為傀儡政府服役。至于拒絕為這些偽軍服務的俘虜,其中有些人就被送往日本,去緩解日本軍需產業中勞動力的不足。在本州西北海岸的秋田收容所中,這樣被送去的一群中國人,在981名中有418名就由于饑餓、拷打或忽視而死亡了。”(2)參見曹大臣《東京審判日本辯護證據研究——以南京大屠殺案為中心》(《南京大屠殺史與國際和平研究院項目報告》第178頁)。
對于日軍所犯罪行,日本高層也有意地模糊掩蓋,以“事變”為借口,否認對華“戰爭”,“按照日本軍方的邏輯,日本沒有向中國宣戰,中日間的作戰是‘事變’,不是‘戰爭’;因為不是‘戰爭’,作戰抓捕的人員就不是‘戰俘’,因此便進行了任意的殺戮、奴役、虐待。”[4]在中國戰場上不設置俘虜收容所,不承認戰俘的存在,被俘虜的中國士兵大多在戰地就直接遭到了屠殺。
“忘記屠殺,就是第二次屠殺。”歷史雖已遠去,但其經驗教訓卻歷久彌新。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從旅順到撫順到上海再到南京,我們的先輩所遭遇過的,它不僅是中華民族的苦難,更是人類文明史的黑暗與悲劇。然而戰后以來,歷屆日本政府及其國內的右翼分子不僅不能積極承擔戰爭罪責,反而一味積極策劃“篡改”歷史,不斷給受害國人民的傷口上再添新傷。
二、缺失的共同記憶:戰后日本對侵華暴行的忘卻
近代中日關系,無論對中日兩國關系,還是對亞洲和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意義。日本關于近代歷史的認識問題一直是影響兩國關系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二戰后日本歷史認識問題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
(一)教科書中的記憶缺失
關于日本教科書的歷史認識與書寫問題,內田樹認為,“俄羅斯的教科書里也沒有反省三國干涉還遼,美國的教科書里也沒有關于朝鮮戰爭的內容。日本教科書里沒有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也是正常的。”[5]41在2001 年日本文部科學省審定“合格” 獲得通過的《新歷史教科書》中,對于日本國家軍隊對亞洲各國尤其是中國人民所犯下的無以計數的極端暴行極力加以淡化、否認或辯解。
對此,中國學者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駁斥,卞修躍分析了2001 年4 月3 日由日本文部科學省審定通過的《新歷史教科書》歪曲歷史事實、美化侵略戰爭、宣揚錯誤史觀、掩飾日本國家侵略罪惡等反映戰后日本國家錯誤歷史認識的表述和企圖,并從歷史基礎、思想基礎、國際環境基礎和經濟基礎等方面對日本國家錯誤的歷史認識的形成原因進行了研究。[6]184-207張宬對日本戰后小學、初中、高中三階段的歷史教科書審定和修改前后的內容進行對比,從文本上分析政府意見對教科書修訂帶來的直接影響。[7]步平分析了2005年日本文部科學省審定通過的《新歷史教科書》,認為該書的歷史觀決定了日本對歷史事實的歪曲與掩蓋。《新歷史教科書》所反映的歷史觀即肯定戰前日本的“國體論”,轉移或淡化侵略戰爭的歷史事實和侵略戰爭的歷史責任,這種歷史觀有可能把日本引向戰爭的道路。[8]
隨著外部政治環境的變化,從記憶深處浮現突出的主題也隨之變化。中國人民沒有停止過對日本的批判。內田樹認為:“一種做法是中國政府不刻意壓制國民內心對日本的憎恨之情使之公然表現出來,另一種做法是政府施加政治壓力使中國民眾不能表達對日本的憎恨之情。相比之下,中國人能夠坦率地吐露對日本的真實感情是一種較妥善的處理方式。”[5]45-46教育實際上是由國家主導的有目的、有組織、有計劃、系統地傳授知識和技術規范的社會活動。從教育的實踐中體現出其根本價值,包括普及先進的文化知識,宣傳國家主導意識形態,推動經濟增長,推動民族興旺,促進人的發展,推動世界和平和人類發展。因此,“任何國家,不論其意識形態之間存在著多么巨大的差異,國民教育都是政府的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和任務,這一點在日本同樣也不例外。教科書既是文化知識、思想觀念的物質性載體,同時也是國家向其國民,尤其是下一代未來的國民傳播知識、灌輸思想觀念、宣揚國家主導意識形態的根本媒介。”[6]200
安倍晉三出任首相之后,積極強化對教育領域的管控,主要表現在:“強化對教科書的管理,使之符合自己的歷史觀念。安倍政權認為,許多教科書還是建立在‘自虐史觀’之上,存在著偏向的記述。為了清除這樣的教科書,他著手大幅度修改教科書。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強化‘學習指導要領’的制定,提出了更加詳細而具體的要求,而‘學習指導要領’是編寫教科書的基本依據。如此一來,真正的學術研究和學校教育之間就豎起了一堵難以逾越的高墻。”[9]
日本的歷史認識問題有其深層的歷史、文化原因,也有外部與美國、中國等國的交往中的觀念有關,認清日本歷史認識問題的原因有利于形成對中日關系的正確認識及今后中日關系的走向的正確預測及應對。有學者指出:“不同于以往的美國縱容論、皇國史觀論,從日本人的以退為進的罪己心理、既往不咎的放棄心理和唯強是從的實用主義心理,分析了日本歷史認識和戰爭責任問題‘右傾化’的原因。”[10]“文化防衛論在完成其文化主張闡釋的同時,擔負起了為不同層面的歷史認識做辯護的責任。蟄伏的日本文化論,構成日本歷史認識史觀的根部土壌。”[11]姜克實則從日本的基本政治立場、影響國民的無構造史觀、戰后的反省程度以及片面的被害意識等方面,分析日本人歷史認識問題的癥結所在。[12]
歷史認識問題,并不是具體歷史事實的問題,而是對歷史深層認識問題,也就是某個歷史事實在當下的外交關系中處于何種位置的問題。重要的不是過去的事實,而是現在對那段歷史、對某個歷史事件的解釋。日本把侵略中國正當化,以致現在日本的年輕人要么不知道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要么認為日本侵略中國是要實現“東亞共榮”,幫中國實現“共存共榮”,甚至把“侵略”中國誤認為是“進入”“進出”。
(二)日本和平紀念館的記憶與忘卻
戰后出生的日本國民,現在成為日本社會的中堅,如何讓他們形成二戰中日本對周邊國家造成的傷害的記憶,是當今中日雙方史學家所面臨的共同任務,如何構建公眾共同的記憶,而不是忘卻歷史是我們面臨的共同話題,也是雙方學者義不容辭的使命。“當今的日本,站在加害國民的立場投身反戰和平運動的民間團體力量還比較薄弱,他們的聲音還難以影響社會的主流。為此,全體國民的參與就顯得十分重要。”[13]41內田樹認為:“中國的近代史是列強侵略的歷史,中國僅僅反抗日本的侵略是不公平的。最先敲開中國大門,對中國侵略的始作俑者是英國。19世紀末期,法國、德國、俄國、美國都隨英國之后紛紛進入中國,對中國進行瓜分掠奪。日本是最后參加了‘瓜分戰’,比起英國,日本的罪責要輕。”并狡辯到,“英國也沒有對侵略中國進行道歉。在把香港占領100年之后歸還中國時,英國首相、外相、女王也沒有對中國道歉。”[5]39-40
在與他者的關系中研究記憶主體,通常加害者容易忘記加害的事實,而被害者卻保持被害的記憶。關于戰爭責任問題,受害國要求日本保持侵略戰爭造成人權侵害的記憶,而日本作為加害者卻采取了忘卻的態度。但是,日本對由“唯一原子彈爆炸國”的被害記憶而喚起的加害的事實卻沒有忘記。
正視歷史,還原真相,是今后中日關系走向的重要影響因素。日本應承認真相,向國民展示、講訴歷史事實,并承擔相應歷史責任和進行賠償,這才是日本今后應該走的路,也是中日國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期待。
三、公共記憶的重構:中日關系的困境和希望
在歷史事實中應該忘卻什么,應該記憶什么,對每個人來說都是重要的心理過程,這個過程將形成一個集體,并對集體價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作為國民國家,往往忘記在戰爭中殺害的敵人,而對于被殺害的本國軍人卻進行表彰、讓人民永遠銘記在心中。集體記憶的形成促進歷史教育及國家性象征性紀念活動的進行。[14]163
“記憶共同體”的形成需要有共同的歷史記憶,擁有共同的過去。不同時代的人形成的共同記憶也會有所差異。如年輕一代認為,“中日戰爭是我們出生之前的事情,我不清楚那些事”,年輕人選擇了忘卻。而上了年紀的人卻說,“你們年輕人可能不懂,從前我們……”這些人只選擇了對自己有利的記憶。“記憶共同體”形成之初,就有意識地忘卻戰爭殺戮的場面、忘記陰暗部分,只記憶光榮事件、光明部分的歷史。戰爭責任之所以被認識到,一方面是由于被暴力侵害國家的被害者提出訴求,還有一方面是國內戰爭被害者或其他有良知的文化人對“記憶共同體”形成挑戰,也就是說“記憶共同體”受到外部壓力和內部挑戰的相互作用。
(一)日本戰爭責任意識模糊化
對過去戰爭的責任,是否所有的日本人都應負此責任?未參加戰爭,未曾傷害或殺害中國人的日本人是否也應負戰爭責任?答案是肯定的。戰時不反對戰爭,擔當了戰爭責任的日本人都不能免除戰爭責任。
“(20世紀)90年代戰爭責任論發生了質的變化,人們更加關注對于戰爭被害者如何進行補償,對此法律專家、律師在理論上及實際賠償方面做出了積極貢獻。另外,賠償組織與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等國際機構的關系,超越國界的NGO的聯合都具有重要意義。”[14]197
從恢復性正義的視角來看,了解真相是達成和解,通向和平的必經之路。但單純地了解真相并不夠,還需要確定加害行為的具體責任,即加害人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并依據法律對其加害行為作出賠償,這是恢復性正義的重要組成部分。[13]166
與戰爭本質論相比,人們更關心對因為戰爭而遭受嚴重災難的人們的補償問題,即開始從人權的角度對待具體的問題。并且,個人的補償要求不是通過被害者所屬的國家,而是直接向作為戰爭主體的日本政府要求補償。因此,隨著戰后要求補償的市民運動的發展,“戰后補償”一詞也被廣泛使用了起來。“戰后補償”不再是市民運動團體作為個人案件提出的法律問題,而是法院這一國家機構必須正式處理的問題,也就是對戰爭中的被害者個人如何進行補償的問題。基于人權的考量,日本未經歷戰爭的年輕一代也認為像“從軍慰安婦”這樣的暴力性奴役是嚴重的人權侵害,真是難以置信、法理不容。有許多年輕人參加了戰后補償運動。根據1993年《朝日新聞》的調查,有70%的20年代的年輕人認為日本政府應該進行戰后補償。[14]200
(二)日本戰爭責任意識模糊化的緣由
日本右翼勢力散布“戰爭不可避論”。一部分右翼勢力宣揚日本資源缺乏,軍事上進攻其他國家是為了生存而采取的不得已的行為。“侵略”是“優勝劣汰”的必然選擇。1995年島村文相在就任后的記者招待會上極力宣揚“戰爭不可避論”。聲稱戰時沒有其他的選擇,戰爭是一種天災,戰時的一切災難都是戰爭引起的不可避免的事情。日本聲稱,戰爭是悲劇。然而,戰爭難分善惡。不能說哪方是正義的,哪方是非正義的。它只是國與國之間差異摩擦的結果,當政治上解決不了時,作為最終手段只能發動戰爭。[15]甚至有日本人主張,只有戰爭,才能讓散亂的國民意識得到統一,才能讓腐化墮落的生活作風有壓力得到自律,才能推動技術革新,也只有戰爭的威脅,能刺激一個國家避免死于安樂。這是極其嚴重的宣揚“戰爭正當論”的言論,對日本的歷史認識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日本在論及歷史認識問題時的伎倆就是避重就輕,混淆歷史事實,推托戰爭責任,認為戰爭時期和現代的年代沒有關系,無需承擔前輩們的戰爭責任。
(三)日本刻意強化被害意識
日本人在回顧1937—1945年的戰爭時,其回憶多是被害者意識。約有300萬人參戰,尤其是二戰后期,日本本土66個城市遭受的美軍大規模的轟炸和廣島、長崎的原子彈爆炸,使日本人內心濃厚的被害意識到達頂點。幾十年來,生存下來的日本人在內心深處深深刻下了受苦和破壞的記憶。著名的廣島、長崎和平紀念資料館所展示的原子彈爆炸帶來的恐怖后果,令人印象深刻。1999年在東京開館的高層建筑昭和館,主要展示了戰時和戰后使用的日用工藝品和生活狀況。[16]
被害意識的加強使日本這種后發帝國主義國家忘記了曾經壓迫、侵略別國的歷史。廣島和長崎屬于相同的民族共同體,擁有共同的歷史記憶,這加強了這兩座城市的被害意識,這種被害意識也影響了參觀過紀念館、不了解這段歷史的每一個日本人。[17]
中日兩國國民對于過去的歷史事實沒有形成共同記憶,從“場”產生的記憶自然就會存在分歧。在1937—1945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國的歷史事實面前,中國對歷史事實選擇了記憶,“前事不忘后事之師”,而日本則選擇了刻意遺忘,遺忘掉對自己不利的事實。
(四)重構日本侵華暴行公共記憶的希望
日本侵華暴行問題是中日之間遺留的重大歷史問題,如何認識這段歷史,如何面向未來發展中日關系,始終是橫亙在中日之間的一個懸而未決的基礎性問題。時至今日,戰后70多年過去了,日本政府沒有正式承認侵華暴行,沒有進行賠償道歉,沒有把史實真相正確地傳達給本國民眾。中日間如何重構共同的歷史記憶,共同面向未來發展新型的國家關系,既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也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學術問題,雙方的學者有義務為了建立公共記憶而建言獻策。一味地指責和否認,只會加深彼此的不信任,只有建立在承認歷史史實的正確歷史觀基礎上,才能構筑“自立與共生”的東亞共同體,中日兩國才能和平走向未來。
如今的美日關系,看似沒有隔閡,對于美日之間的戰爭,日本和美國都采取了共同忘記,好像一夜之間都忘記了過去的一切。共同殺戮的經歷不可能一夜之間全部忘記,雖然難以忘記,卻使之忘記了。這是美日在國民間采取的騙術。對于日本和美國之間的歷史問題,日美之間不是基于“共同記憶”而是“共同忘卻”。不應該被忘記的過去的記憶,經常在某個時間某種情況下被想起。并且,往往是不應被想起的時候浮現出來。共同記憶與共同忘卻看似相似,實則相異。日美對于互相殺戮的歷史在雙方的協議下共同忘卻了。而中日對于殘殺的歷史卻沒能達成共同忘卻的協議,中日共同記憶的歷史雖然對雙方來說是種深深的傷害,但卻比日美共同忘卻的歷史更適應歷史發展的規律。歷史應該在共同記憶的影響下書寫,因此中國和日本應該形成更多的共同記憶,在歷史認識問題上,基于歷史事實形成更多的共同記憶,這是中日關系的未來發展方向。
結 語
戰后70年來,由于戰后處理不徹底等原因,日本長期在歷史問題的困頓中糾結。日本國內在歷史認識問題上始終沒有達成全社會的普遍共識。在解決戰后和解問題上,日本期待的是一種外交上最低成本的邊際效益,一種技術處理,并非追求自身精神層面的蛻變。[18]陳景彥從教科書問題、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問題、對待侵略戰爭的態度問題等方面分析了日本首相及政府的歷史觀及日本政府右傾史觀的原因,認為應該理智而冷靜地對待歷史認識問題。[19]
筆者認為:從作為加害者與受害者立場的記憶與忘卻視角的研究還不是很充分,有待于進一步研究。應該從人權的觀點來討論、研究日本的戰爭責任和戰后補償問題,這不僅有利于進一步澄清歷史問題,而且對中日關系及亞洲和世界的和平發展之路都具有啟發意義。
從中日甲午戰爭到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日軍在侵略中國的過程中,燒殺搶掠奸淫婦女無惡不作,犯下了累累罪行,這種罪行已經成為了日軍的伴生物和標志,充分暴露了日本軍國主義的殘暴性、掠奪性、破壞性和它發動侵華戰爭的非正義性,給我們民族和國家的發展造成了巨大破壞和無法估量的損失。
當我們回首這段歷史,譴責當年日本法西斯對中國人民生命財產的無情踐踏時,其出發點并非出于對本民族曾經苦難的無法釋懷,更不是要激發記憶中的民族仇恨,而是要讓人們對戰爭的本質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喚起人們的和平意識。只有深刻理解戰爭帶來的苦難與破壞,以史為鑒,面向未來,才能更加珍愛和平,避免戰爭及類似悲劇的再度發生。
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下,“重新回憶歷史的傷痛,不是一個種族對另一種族的反對,也不是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偏見,它的目的是希望將這段歷史的創傷固化為人類社會共同的記憶,從而避免重蹈歷史覆轍。”[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