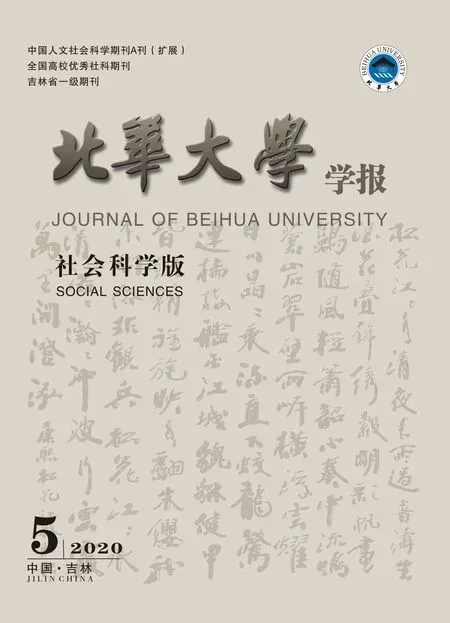小澤一郎與日本政治右傾化
孫巖帝
作為日本政壇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小澤一郎不但通過提出“保守兩黨制”和“普通國家論”政治理念一舉成為日本新保守主義的理論旗手,而且在實踐層面縱橫捭闔推進了以實現這兩大政治訴求為目標的日本政治右傾化進程,既給日本未來走向帶來了不確定性,亦為東亞和平埋下了隱患。因此,在中日關系向好發展但又不時出現齟齬的今天,厘清小澤一郎在日本政治右傾化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對把脈未來日本政治走向和中日關系走勢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戰后日本政治右傾化的演變軌跡
關于“日本政治右傾化”概念,學者們尚無統一定論。依筆者所見,如果說日本政治右傾化是一種思想傾向和政治趨勢,那么就應該系指日本政治從戰后民主主義、和平主義向戰前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回歸的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政治演進過程。右翼思想重新成為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右翼政客重掌國家軍政大權,右翼學者為侵略戰爭翻案,民間右翼分子重演恐怖暗殺一幕,政府官廳加快“強軍修憲”步伐以及挑戰戰后國際秩序等一系列行為,即系戰后日本政治右傾化的具體表現。從民族主義飆升、單邊主義大行其道這一日本國內外形勢看,日本政治右傾化已發展成為令人憂慮的難以逆轉的趨勢。其過程大體經歷了以下四個時期。
第一時期,在美國改變對日占領政策背景下的發軔時期(1945—1952)。太平洋戰爭使美國遭遇了建國以來最大的民族災難。為避免日本再度成為美國的威脅,加之亞洲國家強烈要求,戰后初期美國占領當局不但主導擬制并頒布了“和平憲法”(《日本國憲法》),為防范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提供了一塊“壓倉石”,而且對戰敗國日本進行了“非軍事化”和“民主化”改造、對東條英機等2 000多名大小戰犯進行了審判、對鳩山一郎等20多萬軍職人員進行了“整肅”,大大削弱和打擊了日本右翼勢力。然而隨著冷戰(1947—1991)的過早到來,美國在“扶蔣反共”失敗后轉而“扶日反華”,由此日本作為國際反共“橋頭堡”和“防波堤”的地位凸顯出來,因之美國占領當局遂將戰后初期實施的“懲罰”日本政策改為“扶植”日本方針,不但提前釋放了全部在押戰犯、恢復了所有軍職人員公職,而且開始重新武裝日本。自此,日本政治右傾化便在美國當局改變對日占領政策的背景下隨著右翼分子“重見天日”而開始啟動。
第二時期,在傳統保守主義引領下的緩慢推進時期(1952—1982)。《舊金山和約》簽訂后,隨著戰前軍國遺臣重返戰后政壇和軍界,日本政治右傾化緩慢向前推進。諸如,類似戰時東條內閣的商工大臣岸信介、戰時日本鐵道總務局長佐藤榮作、戰時日本特高課課長奧野誠亮等軍國遺臣當上戰后首相和大臣者,不乏其人;右翼政客個人或集體以“私人”身份參拜靖國神社,絡繹不絕;右翼學者拋出的戰爭翻案謬論,系統而又全面;朝野右翼分子啟動的“強軍修憲”步伐,逐漸加快。特別是其“強軍修憲”主張,為日本政治右傾化“指明”了方向。自鳩山一郎內閣否定吉田茂政府的對美一邊倒政策,[1]最早發出“強軍修憲”號召起,后來的岸信介內閣、池田內閣、佐藤內閣等歷屆政府,都接過了這一主張并付諸實施。但由于受到日本國內外正義人士的譴責和反對,其“強軍修憲”主張和行徑遭到抵制,政治右傾化勢頭也受到一定的遏制。
第三時期,在新保守主義推動下的快進提速時期(1982—2000)。日本政治右傾化之所以在此期間提速,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日本重新崛起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為其政治右傾化奠定了經濟基礎;二是“鷹派”政治強人中曾根康弘出任日本首相,為其政治右傾化提供了政權保障;三是中曾根康弘出版《新的保守理論》和小澤一郎出版《日本改造計劃》即新保守主義的出籠和系統化,為其政治右傾化提供了指導思想。諸如,中曾根康弘首相拋出“戰后政治總決算”口號和首開首相八一五“公職”參拜靖國神社之惡例,森喜朗首相仍然篤信日本是一個“神的國家”[2],小淵惠三政府敦促國會通過“周邊事態法”,內閣大臣不時跳出來就侵略歷史大放厥詞,右翼學者兜售種種戰爭翻案謬說,“大和民族優秀論”等思想糟粕沉渣泛起,等等,均系日本政治右傾化提速的具體體現。
第四時期,在小澤一郎主導下一度實現“保守兩黨制”的轉折時期(2000—2019)。此間由小澤一郎一手導演的兩大政治事件,在日本政治右傾化進程中具有“轉折”意義。一是1993年由小澤一郎斡旋建立的八黨聯合政權中止了自民黨長達38年的執政歷史,首次實現了“五五年體制”形成以來的政黨輪替,在日本政治右傾化進程中具有“轉折”意義。二是2009年小澤一郎率領新保守政黨民主黨在眾議院大選中大獲全勝而奪取政權(成立鳩山由紀夫內閣),使自己的“保守兩黨制”政治理想一度變成現實,這在日本政治右傾化進程中無疑具有“里程碑”意義。盡管這一初創的“保守兩黨制”政治格局后因民主黨逐漸式微而曇花一現宣告結束(即重新回到自民黨一黨獨大局面),然而日本政治右傾化總的趨勢不曾改變,演進速度也不曾放緩。實際上,在自民黨執政的小泉內閣、麻生內閣、安倍內閣時期以及民主黨執政的鳩山內閣、菅直人內閣、野田內閣階段,日本政治右傾化進入了“快車道”。小泉純一郎首相首開六年任內每年“公職”參拜靖國神社的惡例等,將日本政治右傾化向前推進了一步。安倍晉三首相解禁集體自衛權,“強軍修憲”步伐提速,認為“日本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擺脫戰后體制”[3],不在乎別人叫他“右翼軍國主義者”[4],在大庭廣眾之下三呼“天皇陛下萬歲”,以“公職”身份參拜靖國神社,在外交上構筑圍堵中國的“菱形”包圍圈,[5]在釣魚島問題上頑固堅持日本“固有”的錯誤立場,等等,均是日本政治右傾化加快的具體表現。
二、小澤一郎是日本政治右傾化的重要推手
在世紀之交前后的40余年間,小澤一郎之所以成為日本社會家喻戶曉的政治人物,一方面緣于其獨樹一幟的從政風格和鮮明另類的行事特征,另一方面與其在日本政壇導演的推進日本政治右傾化進程的一幕幕政治大劇密切相關。從小澤一郎矢志實現“保守兩黨制”和“普通國家論”政治訴求的從政軌跡不難看出,他確系日本政治右傾化的理論旗手、精神領袖和關鍵人物。小澤一郎如下六個時期的從政生涯,當足以反映他在日本政治右傾化進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發揮的關鍵作用。
其一,看其崛起于自民黨時期的政治作用(1969—1993)。1942年小澤出生于巖手縣一政治世家。母親系國會議員之女,擔負起相夫教子之責;父親小澤佐重喜出任過吉田茂內閣的運輸大臣等。這一政治世家背景和母親的言傳身教,對小澤一郎鮮明政治個性的形成影響巨大而又深遠。慶應大學畢業翌年即1968年,小澤在自民黨干事長田中角榮的點撥下回家鄉參選國會議員,一舉成為日本政壇最年輕的政治家(時年27歲),并很快成為備受矚目的政治新星。1975—1986年,小澤不僅在黨內歷任眾議院運營委員長等職,而且在政府中也擔任過內閣自治大臣等要職。從1985年起,深諳“金錢政治、雙重權力、人際力學”[6]真諦的小澤,先后背棄“政治恩師”田中角榮、竹下登而轉投自民黨政治家金丸信,不但成長為自民黨歷史上最年輕的干事長,而且成為掌握首相人選裁決權的權傾朝野的日本政壇關鍵人物,為形成和貫徹自己的新保守主義政治理念及推進日本政治右傾化奠定了基礎。
其二,看其在新生黨時期的政治作用(1993—1994)。1993年5月小澤一郎出版《日本改造計劃》一書,正式提出了影響巨大而又深遠的“保守兩黨制”和“普通國家論”兩大新保守主義政治理念,并成為日本政治右傾化的“思想指南”。為早日實現“保守兩黨制”和“普通國家論”政治夙愿,小澤一郎立即于同年6月率44名自民黨籍議員另建以羽田孜為黨首的新保守政黨新生黨,自己則以“代表干事”身份掌控實權。小澤一郎突然采取這一地震般政治行動的結果,導致自民黨在同年7月的眾議院選舉中僅獲223個席位而未過半數(240席)。政治嗅覺靈敏的小澤從中窺視出政權更迭的希望。因此,在其縱橫捭闔運作下誕生的由新生黨、公明黨等八黨成立的聯合政權(新黨黨首細川護熙出任首相),一舉中斷了自民黨長達38年的連續統治而實現了政權更迭,在日本政治右傾化進程中具有“轉折”意義。然而,由于新生黨與公明黨、社會黨、民社黨在政治理念上存在差異,加之執政聯盟各黨在政府中權力分配不均,該聯合政權僅執政10個月便在1994年7月曇花一現宣告垮臺。繼之,小澤又將羽田孜扶上首相寶座,而羽田內閣卻成為執政只有兩個月的最短命內閣。細川政府和羽田內閣的垮臺之所以如此迅速,系與小澤一郎反復無常的政治操守息息相關。但這并不影響小澤對日本政治右傾化的影響力。
其三,看其在大起大落的新進黨時期的政治作用(1994—1997)。為使政權失而復得,小澤一郎加緊整合在野黨。1994年底,他首先以新黨和新生黨為基礎建立新進黨,繼而又將民社黨等7個在野黨拉入其中。盡管新進黨黨首由前首相海部俊樹出任,但實權仍然掌握在干事長小澤一郎手中。從《黨綱草案》中諸如推動“修憲”討論,爭取早日“入常”,實施行政改革,奉行自由化經濟政策等項規定來看,[7]新進黨是一個以小澤一郎的“保守兩黨制”和“普通國家論”兩大新保守主義政治理念為政治訴求的新保守政黨。由于新進黨在國會中擁有214個席位,與老牌保守政黨自民黨旗鼓相當,表明日本政黨政治向小澤一郎設定的“保守兩黨制”目標又邁進了一大步。在小澤領導下,新進黨在1995年參議院選舉中大獲全勝的基礎上成立了以小澤一郎為“影子首相”的“影子內閣”;同年底親任副黨首,躊躇滿志地欲率領該黨奪回政權。然而,由于新進黨發生分裂,三黨聯合政權日漸鞏固,公明黨轉而投靠自民黨,小澤一郎被迫于1997年底解散新進黨,這無疑是其政治生涯中的一大挫折。
其四,看其在以退為進的自由黨時期的政治作用(1997—2003)。小澤一郎認為,鑒于理念分歧和組織松散是導致新進黨解散的兩大要因,因此著手建立一個理念統一和組織嚴密的新型保守政黨便勢在必行。在小澤一郎緊鑼密鼓的運作下,1998年初一個完全符合上述建黨要求、在理念和政策上唯小澤馬首是瞻的更加保守的新保守政黨自由黨宣告誕生。盡管自由黨是一個擁有54個國會議席的不宜忽視的在野黨,但卻面臨著執政的自民黨支持率高,在野的民主黨異軍突起,本黨的黨員脫黨嚴重等不容樂觀的政治形勢。為避免坐以待斃,小澤一郎決定暫時收起“保守兩黨制”旗幟而謀求與執政的自民黨合作。[8]1999年初,隨著以小淵惠三為首相的具有濃厚小澤色彩的“自(自民黨)自(自由黨)”聯合政權誕生,日本政壇出現了兩大新老保守政黨聯合執政的政治格局。然而,隨著小淵首相將公明黨拉入政權即向“自自公”三黨聯合政權過渡,小澤一郎和自由黨的影響力大為削弱,這是小澤所不能接受的。就在小澤以退出聯合政權相要挾之際,小淵惠三首相突然病逝于工作崗位上(2000年),不僅導致“自自公”聯合政權垮臺,而且使自由黨至此淪為僅有30個國會議席的在野小黨。這是小澤一郎政治生涯遭遇的又一大挫折。
其五,看其初步實現“保守兩黨制”執政格局的民主黨時期的政治作用(2003—2012)。這是小澤一郎政治生涯的巔峰階段,而其轉擇點便是2003年率自由黨加入迅速崛起的民主黨,意在“借船出海”奪取政權。躋身于民主黨后,小澤首先憑借理念鮮明、擅長選戰等優勢,不僅很快實現了民主黨政策理念上的“小澤化”,而且在民主黨內迅速集結成以小澤為核心的最大派系“一新會”,使該黨迅速壯大為日本政壇最大的在野保守政黨。小澤一郎在2006年3月被選為“黨代表”即成為民主黨掌舵人之后,首先領導該黨取得了2007年國會大選的階段性勝利。盡管期間一度因試圖與福田康夫首相合作而引來不滿和質疑,但小澤還是領導民主黨一舉贏得了2009年的眾議院選舉而奪取政權,初步實現了自己的“保守兩黨制”政治抱負和理想。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身為黨首距首相寶座觸手可及的小澤一郎,卻因政治獻金丑聞等負面因素的影響而與首相寶座擦肩而過,即大選勝利的果實以成立鳩山內閣的方式呈現在世人面前。自此,小澤一郎在日本政壇逐漸被邊緣化即進入日薄西山階段。
其六,看其在日漸式微的生活黨和(新)自由黨時期的政治作用(2012—2019)。盡管小澤一郎始終沒有登上權力的頂峰,但其斗志和影響力并未因年事已高而有所減弱。2012年7月,已屆古稀的小澤一郎集結49位國會議員成立國民生活第一黨并親自出任黨首。鑒于該黨作為眾議院第三大黨和參議院第四大黨難以挑戰執政的自民黨,小澤一郎遂于同年底合并日本未來黨,以迎接第46屆眾議院大選。然而事與愿違,吸納了未來黨的國民生活第一黨的議席數竟由選前的61席銳減為9席。小澤一郎仍不氣餒,為使獨立出來的“生活黨”有朝一日卷土重來,“不能這樣任由自民黨一家獨大”[9],他又試圖與民主黨、日本維新會、日本眾人之黨重組新黨,以最終實現“保守兩黨制”政治目標。然而此時的小澤一郎已當年不再,不但民主黨反應冷淡,而且被日本維新會揶揄為“政界的破壞者”而拒絕合作。2014年7月,小澤一郎再次祭起在野黨聯合大旗,不厭其煩地號召擬“實現政權更迭……有必要推進選舉合作”[10],“只有各在野黨達成共識、通力合作,在下次眾議院選舉中,必將取代現在的自民黨、公明黨聯合政權”[10],“不合作就無法奪取政權,如果各謀其政就會再遭慘敗”[11],等等。結果還是事與愿違,生活黨在同年底的眾議院大選中僅獲2個議席,失敗更慘。盡管后來又先后將生活黨更名為自由黨(2016年10月)、將自由黨合并進國民民主黨(2019年4月),但同樣難有起色。
綜上所述,作為一位熟諳政治權術運作和派閥斗爭精要的政治人物,小澤一郎在自己漫長的政治生涯中,不但通過出版《新的保守理論》一書提出“保守兩黨制”和“普通國家論”政治理念,成為日本新保守主義的理論旗手并為日本政治右傾化提供了“思想指南”,而且通過縱橫捭闔締造一個又一個新保守政黨,實現了日本政壇的政黨輪替和一度使“保守兩黨制”變成現實,成為日本政治右傾化的幕后強有力推手。對其政治理念及實踐的歷史作用和政治影響,我們應作出準確的評估。
日本政治右傾化在小澤一郎的推動下已進入前所未有的新階段,不僅內政和外交全面右傾化,甚至滲透到了國家政權(右翼政客掌控了軍政大權)和國民意識(盲從右翼勢力的比例不斷上升)層面。在單邊主義和民族主義迅速抬頭的國際大背景下,在右翼勢力重新抬頭、蠢蠢欲動和加快“強軍修憲”步伐的日本國內形勢下,日本政治右傾化已呈難以逆轉之勢。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
小澤一郎在日本政治右傾化進程中處于“承上啟下”地位和發揮了“承前啟后”作用。即無論其新保守主義政治理念還是政治右傾化實踐,均承中曾根康弘之“上”和之“前”、啟安倍晉三之“下”和之“后”。盡管小澤一郎幾度與首相高位擦肩而過,但其“保守兩黨制”和“普通國家論”政治理念早已成為日本新老保守勢力不變的政治追求。對小澤一郎政治理念及其實踐給日本未來走向和中日關系走勢帶來的不確定性,我們要密切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