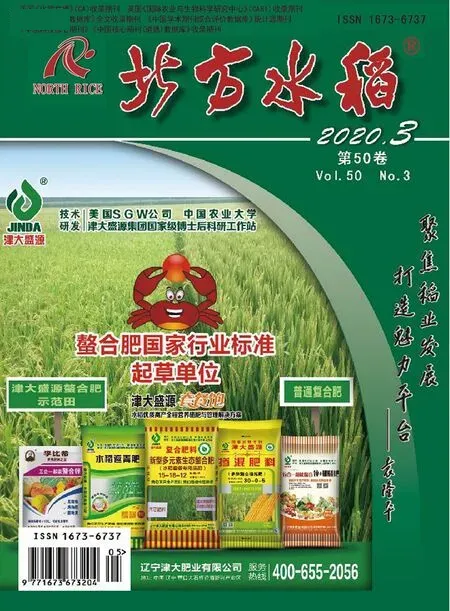光周期調控水稻開花期的分子機制研究進展
王詩宇,王志興*,隋亞云,黃 河,宋曉波,郭素華
(遼寧省鹽堿地利用研究所,遼寧 盤錦 124010)
對于植物來說,開花是其重要的生理變化,它使大多數植物從營養生長轉變為生殖生長。 從營養(莖和葉的產生)到生殖階段(花序和花朵的產生)的過渡決定了開花時間(或谷物的抽穗期),并且是植物生命周期中重要的發育轉變過程[1]。開花是由植物自身的遺傳特性和外界環境因素共同控制的[2-3]。 遺傳特性主要是指植物激素的生物合成和信號轉導過程, 以及控制生長發育過程的各種基因調控網絡等[4]。 環境因素主要包括光照、溫度以及養分條件等。許多植物為了繁衍,具有在適宜的生長季節里開花的能力, 并且主要受到隨著季節變化而改變的日照長度即光周期的精確調控[5]。這種依賴光周期而開花的能力使得植物能夠適應不同緯度、不同海拔的生存條件。根據植物對日照長短的反應,可將開花植物主要分為三大類,即長日照、短日照和日中性植物。長日照植物和短日照植物分別在長日照和短日照條件下能夠被促進開花轉變, 而日中性植物則表現出對日照長度的變化不敏感的特性。 由于光周期與其他外界環境條件相比較為穩定, 其影響植物開花的相關研究也更加深入。
光周期途徑是植物中最為保守的開花響應通路, 它通過整合生物鐘和日照長度等環境因子來決定植物開花的早晚。目前研究認為,光周期通路是調控水稻開花期的關鍵途徑[6]。擬南芥是典型的長日模式植物,增加光照時間,可以促進其開花。最近幾十年來, 通過分子遺傳學的手段對其開花時間的調控機制進行了廣泛的研究。 擬南芥中克隆的一些與光周期調控開花時間相關的基因在水稻中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但水稻是短日照植物,在水稻中肯定存在其特有的光周期調控通路。
1 光周期途徑
光周期是影響開花期的一個重要途徑, 它是指一日之內晝夜長度的相對變化情況。 光周期現象是指植物對日照長短的規律性變化的響應。 光周期現象是美國園藝學家Garner 和Allard 于1919 年在煙草中首次研究發現的。 任何植物對光周期的感受都有一個臨界的日照長度, 即臨界日長。 臨界日長是區別長日照或短日照的日照長度標準, 指晝夜周期中能誘導植物開花所需要的最低或最高的日照長度標準。 短日照植物要求的日照時數必須小于臨界日長, 而長日照植物要求的日照時數大于臨界日長, 否則就延遲開花或不能開花。植物感受光周期的部位是葉片,在葉片中產生的光周期誘導信號物質通過維管組織長距離運輸到頂端分生組織后引起植物開花, 并且根據后來的研究這種物質被稱為成花素。
2 擬南芥光周期調控開花期的分子機制
大 量 研 究 結 果 表 明,GIGANTEA(GI)、CONSTANS(CO)和FLOWERING LOCUS T(FT)是光周期調控擬南芥開花期通路上的關鍵基因,三者存在GI-CO-FT 的遺傳調控關系, 三者遺傳上的調控關系也是擬南芥開花期調控通路中最主要的途徑[7]。GI是調控植物生物節律和開花的關鍵因子[8],GI可以促進CO和FT的表達,進而促進擬南芥開花[9]。 CO 作為轉錄激活因子,在長日照條件下是促進開花的關鍵調節劑。 擬南芥CO位于FT的上游,在長日照條件下通過調控FT的表達, 進而促進擬南芥開花, 而在短日照條件下CO基因對擬南芥開花沒有影響[10-11]。FT 是擬南芥中發現的成花素, 在葉片中合成經由韌皮組織運輸到莖頂端生長點,從而促進開花[12]。 近年來,隨著功能基因組學的不斷發展, 越來越多的擬南芥開花期相關基因的作用機理被解析, 因此調控擬南芥開花期的光周期途徑也不斷被完善[13]。
3 水稻光周期調控開花期的分子機制
3.1 同 擬 南 芥 保 守 的 水 稻 中 的OsGI-Hd1-Hd3a 調控模型
2000 年,Yano 等人采用圖位克隆的方法在日本晴與Kasalath 的雜交分離群體中克隆到一個光周期敏感的主效QTL, 并命名為Heading date 1(Hd1)[14]。Hd1是水稻中最早克隆的抽穗期相關基因,位于第6 號染色體上,是擬南芥CO的同源基因。 Hd1 在水稻光周期開花中的獨特性源于其具有的雙重功能。 它在短日時充當開花促進因子,而在長日充當開花抑制因子[15-16]。Oryza sativa Gigantea(OsGI)是Hd1的上游主要調控基因[17]。短日照條件下,OsGI使Hd1的表達水平上調; 相反長日照條件下,OsGI使Hd1的表達水平下調。 水稻光周期敏感性基因Heading date-3a(Hd3a)是位于水稻第6 號染色體上的與抽穗期相關的數量性狀位點[18-19]。Hd3a為水稻FT-like基因家族的成員,與擬南芥的FT基因高度同源[20]。Hd3a的表達也具有節律性,mRNA 的積累在黎明時達到最大值[21-23]。 在短日條件下,Hd3a的轉錄水平增加。通過表達分析Hd3a的轉錄水平被Hd1上調,在野生型水稻中引入外源的Hd3a會引起水稻的早花表型。 這些結果都證明了Hd3a可以在短日照條件下促進水稻開花。
3.2 水稻特有的開花期調控基因
水稻中有幾個擬南芥中不存在的、 獨特的開花期調控基因, 包括Ehd1、Ehd2、Ehd3、Ghd7和OsMADS51等[24]。Early heading date 1(Ehd1)是一種B 型反應調節因子, 通過正向調控Hd3a和Rice flowering locus T1(RFT1) 的表達, 來調控Hd1非依賴型的調控途徑[25-27]。Grain number,plant height, and heading date7(Ghd7)編碼一種CCT(CO,CO-LIKE,TIMING OF CAB1)結構域,該結構域含有一種在長日照條件下通過下調Ehd1的表達水平而強烈抑制開花的蛋白質,相反在短日照條件下對開花時間并沒有影響[28-30]。Early heading date 2(Ehd2)是水稻中存在的玉米Id1同源基因, 可以上調Ehd1的表達。Early heading date 3(Ehd3)在長日照條件下通過下調Ghd7的表達而促進開花[31-32]。OsMADS51在短日照條件下,正向調控Ehd1的表達[33]。 水稻中存在這些調控因子,而擬南芥中卻沒有,這也充分表明這兩個物種的開花調控通路具有一定的差異性。
3.3 短調日控照模條型件下水稻開花期的分子機制
水稻是短日照植物, 短日條件可以促進其開花[34]。 在短日條件下,Hd1 蛋白充當成花素基因Hd3a表達的促進因子[35]。 因此, 進化上保守的OsGI-Hd1-Hd3a 途徑促進開花。 B 型反應調節因子Ehd1在短日條件下也誘導Hd3a表達。Ehd1表達在早晨被藍光激活,并且該時間由OsGI控制。
3.4 長日照條件下水稻開花期的分子機制
長日照下,Hd3a的表達量很低,甚至不表達,即RFT1是長日照條件下的主要開花促進因子[36]。Ghd7、O.sativa LEC2 and FUSCA3 Like 1(OsLFL1)、Oryza sativa LEAFY COTYLEDON1(OsLEC1)等基因會抑制Ehd1的表達, 而其下游基因的表達也都要受到抑制, 從而抑制開花; 相反OsMADS50可以正向調控Ehd1的表達水平促進開花。Oryza sativa EARLY FLOWERING 3(OsELF3)、Ehd3則通過抑制Ghd7的表達,促進Ehd1的表達,進而促進下游相關基因的表達促進開花[30]。
綜上所述,短日照條件下,調控水稻開花主要存在兩條途徑: 一條是進化上保守的光周期開花調控途徑——由Hd1參與的OsGI-Hd1-Hd3a 組成的保守促進途徑;另一條是由水稻特有的Ehd1基因參與的Ehd1-Hd3a 途徑。 而在長日照條件下, 水稻開花主要存在兩條抑制途徑和一條促進途徑, 分別是OsGI-Hd1-Hd3a 抑制途徑、Ghd7-Ehd1-RFT1 抑制途徑和Ehd1-RFT1 促進途徑。這些途徑分別依賴于Hd1和Ehd1對成花素基因Hd3a、RFT1表達的調控,從而影響水稻開花過程。
4 展望
水稻的開花期(即抽穗期)是決定水稻產量的重要農藝性狀。 水稻只有在適宜的生長發育階段和適宜的季節里抽穗、開花,才能確保產量。 過早抽穗、開花會縮短水稻的營養生長期,進而降低水稻的生物產量和經濟產量;而過晚抽穗、開花則容易發生障礙性或延遲性冷害, 影響水稻的灌漿和結實,從而造成產量降低。 因此,開展水稻開花期調控分子機理的研究, 對于探明水稻開花期的基因調控網絡, 利用人工手段改變和調節水稻開花期, 指導成熟期不同的水稻品種選育, 調節播種期, 保證雜種優勢利用過程中雜交種子的父母本花期相遇,提高水稻的適應性和產量,改善水稻的品質,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