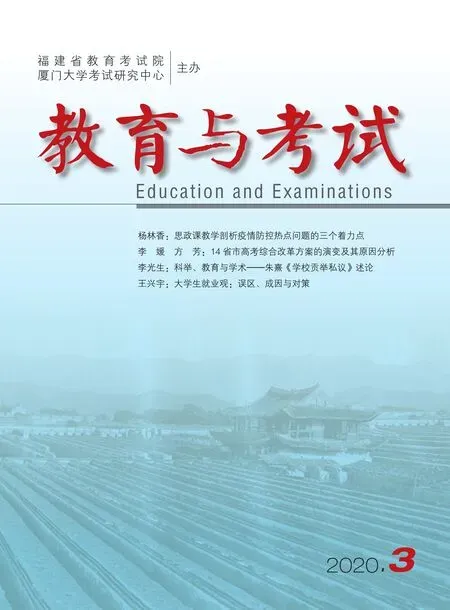書院、游學與清代甘肅武威科舉之盛*
陳尚敏
一、引言
清代武威文風之盛,前人多津津樂道。雖是一鱗半爪的觀感,但吉光片羽,彌足珍貴。“武威文風甲于秦隴。”[1]“自乾嘉以降,彬彬多文學士矣!”[2]其“人文之盛,向為河西之冠”[3]。嘉慶十三年(1808年)戊辰科鄉試,姚元之典試陜西,他說:“甘省文風,初為寧夏最盛,今則莫盛于涼州之武威。”[4]在道光朝任古浪知縣的陳世镕也說:“陜甘分省,闈場在陜,中額不分。甘肅文風以皋蘭、武威、伏羌、秦安為盛。”[5]

清代武威科舉人才的時間分布
在上表中,“/”前為武威各功名的中式人數,后為甘肅全省的總數。甘肅在康熙初年從陜西析出,獨立建省,其轄境包括今甘肅省全境、青海省東部地區和寧夏回族自治區大部分地區;另外,新疆建省前,天山北路實行府縣地區采取雙重歸屬體制,一方面在建置上就近劃入甘肅省,令陜甘總督轄制,另一方面在行政上命烏魯木齊都統管理[6]。光緒元年(1875年)之前,陜甘合闈,甘肅和新疆文教統由陜甘學政管理,鄉試在陜西省會西安舉行。光緒元年,陜甘分闈,新疆文教改由甘肅學政管理,鄉試在甘肅省會蘭州舉行,這一狀況即使在光緒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之后也未有變化。有關新疆士人的硃卷和齒錄在介紹自己的籍貫時,也注明是“甘肅省某州某縣”。如李俊之為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補行庚子(二十六年,1900)恩正并科舉人,其齒錄所載的籍貫為“甘肅迪化府迪化縣”;蔣舉清為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恩科舉人,其硃卷所載的籍貫為“甘肅新疆迪化府昌吉縣”。因此,就本文所論述的地理范圍而言,實際包括了今甘寧青新四個省區,總共包含83個縣級行政單位①。
在清代甘肅各縣的科舉人才統計中,皋蘭人數最多,其次是武威。傳統社會基本上是以政治為主導型的社會,正如皇權所在地既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經濟中心一樣,聚集著更多的公共資源。如皋蘭縣,作為省會蘭州府府治所在地,清代陜甘總督,藩、臬二司以及蘭州府、皋蘭縣的衙署均建于此。光緒元年,陜甘分闈后此地又增設提督學政衙署。當時建有書院四所,其中蘭山、求古為省級大書院,五泉和皋蘭分別為蘭州府和皋蘭縣屬書院。作為全省首善之區,這里擁有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優越條件。
清代科舉實行分區取錄政策,究其實質,是將競爭限制在一定區域范圍內。學額決定一個縣的科舉人才數量。鄉試中額不僅決定著一個省的舉人數量,而且還與其他類科舉人才的數量,如進士,五貢當中的優、拔、副貢具有相關性。因此,清代科舉人才的地理分布若以省為單位進行比較是沒有意義的;同時在進行一省范圍內縣域之間的科舉人才數量比較時,應將基于學額而產生的生員以及以論資歷而非考選的歲、恩貢剔除。上表中的“貢生”數量是指優、拔、副三貢的總和。
計量史學在20世紀50年代的西方,特別是在美國相當流行。20世紀80年代后,我國史學界開始引入這一方法,逐步應用到歷史學的諸多分支學科中,比如在探究歷史上的人文變遷時,往往以人才的時空分布為視角。計量史學方法的運用使得這一研究趨于精確。不過,數量統計是結果,探尋其背后的致因才是研究的重點。
二、天梯書院與武威科舉人才的養成
書院之名始于唐代,是中國古代獨特的文化教育組織形式,兼具藏書、刻書、祭祀、育才等多種職能。縱觀書院的發展,它與地方官學存在著一個此消彼長的關系。當地方官學衰微之時,往往是書院興盛的時期,此時的書院是作為地方官學的補充而存在的。清代書院即其顯例:“各省書院之設,輔學校所不及”“儒學浸衰,教官不舉其職,所賴以造士者,獨在書院”[7]。“士子不居于學宮,則講藝論道,胥為書院。”[8]武威文風的興起,是與本籍的書院教育密不可分的。
武威的前身為涼州衛,是涼莊道的道治所在地②。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涼莊道武廷適創建成章書院。乾隆十二年(1747年),由涼莊道張之浚倡議,涼州知府朱佐湯暨涼州府所屬五縣知縣增修書院③。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顧光旭出知涼州府,武威知縣請求修復書院。“涼州舊有天山書院,歲久致圮。”書院修復后,更名為天梯書院④。由上述零星的記載擬作如下推斷:其一,天梯書院的初名為成章書院,后曾更名為天山書院;其二,天梯書院原初應為涼莊道屬。書院初建,隴西進士宋朝楠撰寫創建碑記:“延師友、萃諸生,群聚肄業。闔屬之士,莫不望風褰裳。”[9]“闔屬之士”應指涼莊道所屬士子。雍正二年(1724年)時,裁撤涼州衛,新置涼州府,置府之附郭武威縣;裁鎮番衛置鎮番縣(治今甘肅民勤縣),裁永昌衛置永昌縣,裁莊浪所置平番縣(治今甘肅永登縣),裁古浪所置古浪縣,一并來屬⑤。乾隆十二年(1747年),涼州府所屬五縣知縣參與增修書院,可見當時的書院應為涼州府屬。無論涼莊道屬還是涼州府屬,其轄境變化不大。但當書院更名為天梯之后,書院就成為武威縣屬了。
另外,光緒元年(1875年),涼莊道成定康捐俸修建雍涼書院,在武威縣城內西北隅⑥。有關雍涼書院的資料,現在能見到的不多,因而無法置評。
書院是“私學發展到高級階段的產物,是種制度化的私學”[10]。書院的屬地特點也是由其私學性質決定的。具體言之,清代書院從興建緣起、經費籌措以及建筑維修等都有民間力量的參與。書院教育的屬地特點,即誰出資、出力誰享受的邏輯結果。在筆者收集到的自嘉慶以降鎮番、永昌、平番、古浪四縣士人的近百份硃卷和會試同年齒錄⑦的師承關系中,未見有肄業天梯書院的例子,這也可以作為天梯書院僅為武威縣屬的一個旁證。
“武威自明季李銳登甲榜,官汀州太守,至方伯再成進士。故吾鄉入國朝來,方伯為甲科開先云。”[11]有明一代,武威只有李銳一人成進士。引言中的“方伯”,即孫詔,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壬辰科進士,獲館選,曾歷官至湖北布政使。明清“布政使”向有表率一省府州縣官之義,故尊稱為“方伯”。清政權建立將近70年時,武威才有了第一位進士。
武威文風丕變,由衰轉盛,始自王化南、劉作垣二人先后主講本籍書院。王化南,字蔭棠,乾隆四年(1739年)己未科進士,獲館選,曾官至山東平度州知州,后引疾去。當道“延主書院講席,教法即淳且備”“矻矻孜孜,俾不得斯須嬉,士風為之一變”[12]。劉作垣,字星五,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辛巳科進士。自安徽舒城縣知縣罷歸后,主講書院。“一時從學之士,文章皆有程式可觀”“吾鄉所以文教日上,不乏績學之士者,山長誘掖之力實多”[13]。
天梯書院變為縣屬之后,可以說其教育長盛不衰,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山長選聘得人。從筆者收集到的相關硃卷和齒錄來看,任職天梯書院山長者有相當一部分來自本籍的進士,如郭楷(乾隆六十年乙卯科)、楊增思(嘉慶七年壬戌科)、張美如(嘉慶十三年戊辰科)、王于烈(嘉慶二十四年己卯科)、張兆衡(嘉慶二十五年庚辰科)、陳作樞(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科)、張詔(咸豐六年丙辰科)、袁輝山(咸豐六年丙辰科)、張景福(咸豐六年丙辰科)、周光炯(咸豐九年己未科)等,他們當中大都曾受教于天梯書院,進士中式后,又有于天梯書院講授的經歷。進士劉開第(同治元年壬戌科)、倫肇紀(光緒六年庚辰科)、李于鍇(光緒二十二年丙申科)也曾主講雍涼書院。在清代甘肅府、縣兩級的書院中,有如此多的進士作為山長,武威為僅見。
清代科舉考試,名為三場,但應試者能否中式,看重的實際上是首場八股文的寫作水平。八股文寫作的立意是“代圣立言”,這就要求考生具有豐富的經史知識以及對其的理解。在形式上,八股文更是有著諸多限制,寫作時須先破題、承題、起講;正文部分須用有聲律要求的四個有邏輯關聯的對偶段落來層層深入地闡發題旨,即所謂的“體用排偶”;文字要清真雅正;結構要起承轉合。八股文作為考試文體,其程式化的寫作就需要掌握相關的技法。因此,作為應試者,若無名師指撥,全憑自我摸索,成功的概率不會太高。進士作為科舉的終端,他們才稱得上是科舉真正的成功者。長期在科場的摸爬滾打,進士們擁有自己的成功經驗,他們主講書院,就有著其他功名獲得者所不具備的優勢。
在清代歷史上,人們熟知的吳敬梓、蒲松齡等富于文學才華,但在科場上卻是悲劇性人物。他們的文學氣質和文學才華,不僅不能為八股文寫作增色,而且還有可能適得其反,帶來更多負面的影響。武威張棟,“凡十五入秋闈無所遇,窮阨以死”;“其為文,時而恣縱、時而高簡、時而光怪陸離,不樂揣摩場屋風尚為熟軟格調”[14]。“不樂揣摩場屋風尚”其實就是他“每見摒于有司”的真正原因。試想,若有熟知科場經驗者的指導,再若張棟能夠虛心聽取,他的命運或許會發生轉機。
傳統士人與故土的聯系往往受制度和觀念的影響,如父母故去,必須辭官回籍守喪的“丁憂制”。清代雖然沒有致仕歸籍的規定,但是基于孝親觀念,他們依然要回歸故土。進士鄉居期間,于書院主講自然也是一個體面的選擇,但其前提是書院能夠提供豐厚的修金。因為依進士的聲望,他們有著寬廣的社會流動途徑,書院山長之于他們也絕非唯一的選擇。不過,主講于天梯書院的武威籍進士,大都也曾是該書院的受教者,他們后來又成為書院的主講,其中當有一種回饋意味。
三、游學與武威科舉人才的養成
所謂“游學”,其本義為“在外地求學”,“外地”是相對于本籍而言。從硃卷和同年齒錄的履歷來看,本籍是指個人出生的縣。因此,凡是離開了本籍的求學行為都應視為“游學”。就清代武威籍士人的舉業而言,除了在省會蘭州,陜西和京師是他們最主要的兩個游學目的地。另外,一些清代地方官尚保留著傳統循吏講學的流風余韻,衙署即學署,身兼官師兩重身份。傳統時代,士人往往轉益多師,師之所在,即學之所在,游學最能反映這一點。
(一)游學省會蘭州
雍正十一年(1733年),世宗諭令各省建立省級書院,并給每所書院賜銀千兩。蘭山書院就是在此次諭令下建立的甘肅省級書院。“書院之大者在省會,當道校諸郡縣士而拔其尤。延名師董教之,日餼月廩,費在出公帑,澤甚渥也。”[15]圍繞蘭山書院,清代甘肅遂形成了一個教育中心。“蘭山書院為隴右人文薈萃之所。”[16]“士之文秀者,則往往聚于省城。”[17]光緒九年(1883年),總督譚鐘麟、學政陸廷黻在省會蘭州創立求古書院。至此,甘肅就擁有兩所省級書院。“省城蘭山書院,督臣為政;求古書院,學臣為政。”[18]也就是說,蘭山書院由陜甘總督主持,求古書院由甘肅學政主持。學政為清代掌管一省學務的官員,晚清時,非翰林不得出為學政。學政雖為臨時差委性質,而且所帶官階也如原品級,一般不是很高,但其職事關一省風化,地位優崇,權力不小。學政與督撫等疆臣平行往來,因此,學政一般也被認為是省級官員。
清代省級書院的設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改變了傳統時代省一級無學校建置的歷史,地方教育生態也隨之發生變化,士人尋師訪友不再局限于狹小的縣域,而是擴大到省區。因蘭山書院由陜甘總督主持,不僅書院建筑規模宏敞、藏書豐富,而且還能給肄業士子提供豐厚的膏火,更為重要的是,蘭山書院山長的選擇是在全國范圍。“自初設至今所延院長,率皆名宿。最著者為(浙江)錢塘胡兟、(江蘇)常熟盛元珍、(山東)滋陽牛運震、(陜西)武功孫景烈。四十年來,肄業諸生成科名、貢成均者指不勝屈。”[19]因此可以說,蘭山書院的設立也為引入文教發達地區士人講學甘肅提供了平臺,這大大提升了甘肅科舉教育的水準。
乾隆間吳鎮主講蘭山書院,“其教人也,務崇實學,士多成立”,其中進士中式者有秦維岳、周泰元、李方苞、郭楷四人⑧。其中周泰元、郭楷皆武威人。劉開第為同治元年(1862年)壬戌科進士,其會試硃卷的“業師”中就有蘭山書院山長的題名:“蔚峪田老夫子,諱樹楨,鞏昌伏羌縣人,辛丑進士,翰林院編修,前蘭山書院山長。”這表明劉開第在其舉業階段有到蘭山書院的肄業的經歷。其他如趙元普,同治九年(1870年)庚午科帶補丁卯科舉人,其鄉試硃卷的“業師”中亦有蘭山書院山長的題名:“徐楊小梅夫子緒,舉人,蘭山書院山長。”張銑為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進士,其會試硃卷的師承關系部分載:“年伯張敦五夫子國常,皋蘭人,丁丑進士,刑部主事,特賞員外郎銜,主講蘭山書院;劉遠峰夫子光祖,秦州人,丙戌進士,刑部主事,主講求古書院。”
(二)游學陜西
甘肅作為獨立的行省,始于康熙初年,當時是從陜西析出,但陜甘兩省的關系卻又有著特別的地方。關隴并稱,遠遠早于甘肅行省建立之前,說明兩地有著獨立的地理單元意味;分省之后,這一稱呼依舊延續,又說明兩地多有一體之意。在文教方面,光緒元年(1875年)之前,陜甘合闈,共有一個學政。有清一代,在陜西境內有兩所書院可以招收甘肅士人讀書。“關中、宏道兩書院為陜甘兩省士子肄業之區。關中督撫主之,宏道學政主之。”[20]關中書院設于西安,始建于明萬歷三十七年(1609年),關學大師馮從吾、李颙曾主講于此,是明清西北最著名的書院。宏道書院位于三原縣,始建于弘治七年(1494年),原是陜西三原學派的講學之處。
龔玉堂,嘉慶三年(1798年)戊午科舉人,其鄉試硃卷師承關系部分就有關中書院山長的題名:“路老夫子,諱談,辛未科進士,翰林院編修,關中書院山長,寧夏府人。”陳作樞,道光十七年(1837年)丁酉科舉人,二十四(1844年)甲辰科進士。其鄉試硃卷師承關系部分有兩位關中書院山長的題名:“張玉溪夫子,諱美如,甘肅武威縣人,嘉慶戊辰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戶部廣西司員外郎;路閏生夫子,名德,陜西盩厔縣人,嘉慶己巳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戶部湖廣司兼河南司主事,軍機章京,方略館協修。”郝永泉,道光十九年(1839年)己亥科舉人,其鄉試硃卷有一宏道書院山長題名:“閏生路老夫子,印德,宏道書院山長”;一位關中書院山長題名:“桐舫程老夫子,印儀鳳,關中書院山長”。咸豐二年(1852年)壬子科進士王之英的會試同年齒錄也見有關中書院山長的題名,表明他們都曾有肄業關中書院的經歷。上述均是成功的例子。
據武威張澍講,他父親有位朋友名叫劉文洵,其父曾做過直隸丘縣知縣、易州知州,家饒資財。劉文洵立志博取功名,遠赴關中書院學習。但歷經十年,未能如愿,等他回來時,“田宅蕩然,二子乞食村野間,依墟墓以居”。劉文洵悲憤交加,一月多時間雙目失明,只得隨其子行乞于城。張澍父親見到這位落魄的朋友,時在嘉慶十年⑨。由此可見,武威士人游學關中絕非個案,而是帶有一定的普遍性。
(三)游學京師
清代甘肅士人在學術上取得成就最高的無疑是張澍。張之洞《書目答問》附錄《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中,張澍列名于經學家、史學家和金石學家。張澍入《清史稿·儒林傳》。梁啟超說:“甘肅與中原窎隔,文化自昔樸僿,然乾嘉間亦有一第二流之學者,曰武威張介侯澍。善考證、勤輯佚,尤嫻熟河西掌故。”[21]這里的問題是,既然“甘肅與中原窎隔,文化自昔樸僿”,為什么會在乾嘉間挺生出一位第二流的學者?
張澍七歲受業于本籍進士劉星五,“先生奇愛之,病其筆端縱橫”,才佳而文法不符時藝。但時官陜甘學政的章桐門看中的正是這一點,又憐其年幼,遂以童試第二的名次甄選入涼州府學⑩。時為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章桐門,即章煦,桐門為號,浙江錢塘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進士。張澍進學之年,又恰逢恩科鄉試舉行。張澍參加了此次鄉試并中式,也就是說,乾隆五十九年,張澍實現了由童生到生員再到舉人的跨越。鄉試中式后,張澍即隨章煦來到京師。“澍自甲寅登鄉薦以后,即在京師肄業。”[22]他先后從邵晉涵學習經史、管世銘學習時文?。張澍游學京師,學業精進,李于鍇對此有著甚為精彩的描述:
十四為諸生,學使章桐門攜上京。乾隆甲寅,舉鄉試第四人。嘉慶己未,成進士,選庶常。京師書籍海,人才淵藪,以先生游期間數年,盡師魁碩,盡友群雅,盡窺中秘。由是聲氣驟廣,記覽驟博,援筆伸紙,如天馬馳風,不可羈縶;劇談今古,如海河四溢,不可堤障。一時巨公,自朱文正、阮文達而降,皆交口薦譽之[23]。
朱珪、阮元分別為嘉慶四年(1799年)己未科的正、副主考官。該科中式者除張澍外,尚有姚文田、王引之、郝懿行等,“諸人皆一時樸學之選,人才之盛,空前絕后”[24]。邵、管、朱、阮諸氏皆為樸學大家,乾嘉時期正是此學如日中天之時,張澍京師游學對他日后的學術活動的影響自可想見;同時他得中高第也應與這段經歷相關。
唐代,應試舉子落第后往往寄居京師過夏,課讀為文,是為“京師夏課”。“夏課”后來成為一詞,專指外地落第士人在京師攻讀舉業,以待下科再考。這樣既可節省盤費,又可避免舟車勞頓。京師人才濟濟,既方便問學,又可交流應試心得。居留京師期間,在紳宦之家覓一館地以維持生計,也是當時滯留京師舉子不錯的選擇。張澍居留京師期間,兩度“館鉅公家”[25]。“武邑每科赴禮闈試者百余人,榜后留者十余輩”,潘挹奎便要為他們“謀館谷,俾資旅費”[26]。潘挹奎,武威人,嘉慶十三年(1808年)戊辰科進士,時官吏部考功司主事。“挹奎性伉爽,能救人急難。”[27]
(四)其他
余英時先生認為:“漢代的循吏便早已重視‘教化’,往往在朝廷所規定的‘吏職’之外,主動地承擔起儒家的‘師’的責任。所以他們所至‘講經’并建立學校。”這一傳統一直影響到清代的畢沅、阮元,乃至晚清的曾國藩、張之洞等?。在清代宦甘的州縣官中,其實也不乏其例。
牛運震,字階平,號木齋,山東滋陽人,雍正八年(1730年)庚戌科進士。乾隆三年(1737年)出知秦安縣。“運震擇士之俊者,親授之業。又買官署旁民宅,別設隴川書院。自署內穿牖相屬,旦夕親往訓諸生,以讀書綴文之法。秦安科第始盛。”[28]乾隆十年(1745年),牛運震調平番縣(治今甘肅永登縣)。因“秦校諸生戀不能舍,因攜來平署,續講舊業。平邑尚有一二人,少可指示,并皋蘭、武威二邑就學者頗多,皆收置署中,一體不拒。現在開圃筑室以為講肄之所,冀于簿領之暇,自圖休息,并可開誘后學,益廣其傳,亦未知果能有成不也”[29]。牛運震在平番時的受業弟子中,有秦安的吳墱、狄道(治今甘肅臨洮縣)的吳鎮、武威的吳懋德,三人皆負俊才,善詩文,有“三吳”之稱?。吳墱后中式乾隆十六年(1751年)辛未科進士;吳鎮、吳懋德也先后鄉試中式。其時,尚有武威的孫俌,“時山左牛運震宰平番,俌喪既除,往從之學。”[30]孫俌也中式乾隆十六年辛未科進士。
陳世镕,字雪爐,安徽懷寧人。道光十五年(1835年)乙未科進士,分發甘肅,曾署理隴西知縣、岷州知州,后銓古浪知縣。武威李銘漢曾受知于陳世镕,據李銘漢哲嗣李于楷講:“府君連不得志于有司,而己亥房師懷寧陳雪爐于闈中得府君卷獨賞異之。先生負海內重名,所著經說、詩、古文可數尺許。后調任古浪,手書招府君,先大母命君往從之學。”[31]“房師”為“同考試官”的別稱。鄉試的正、副考試官由清廷臨期任命,均需翰林出身。因鄉試在各省舉行,“同考試官”一般由該省具有進士、舉人功名的州縣官充任。引文中的“己亥”即為道光十九年(1839年),當時陜甘鄉試合闈,“同考試官”在陜甘兩省的地方官中拔取。鄉試取錄要經過“同考試官”的閱卷、薦卷再到正、副考試官取中這樣一個過程。“同考試官”將自己認為優秀的試卷推薦給正、副考試官,正、副考試官互閱商酌,最后取定。“同考試官”“薦卷”,當時稱作“出房”,是應試者能否中式的關鍵一步。正、副考試官與“同考試官”之間的觀點不盡一致,當屬正常現象,如房師陳雪爐對李銘漢的考卷“獨賞異之”,但最終還是未被取中,說明正、副考試官并不認同陳的推薦。后來,陳雪爐將李銘漢招致衙署教讀,在他看來,李銘漢顯然是可塑之才。另一位受知于陳世镕的甘肅士人,是伏羌(治今甘肅甘谷縣)的王權。“十六應童試,為古浪令懷寧陳雪爐先生所欣賞,旋入庠食餼,招至署中肄業”;“陳海內巨儒,精漢學。先生乃學陳所學,不屑屑于舉子文。力務暗修,一祛近世講學家虛矯之弊”[32]。安徽是清代漢學“皖派”的發祥地,王權在追憶于陳世镕門下讀書的情景時說:“文探班馬奧,經抉鄭王心。”[33]王權、李銘漢是晚清甘肅有影響的學人,兩人治學主張漢宋融會,其學術風格的形成與其師陳雪爐不無關系。
四、余論
張澍《五涼舊聞序》稱:
涼州為金天甌區,自漢武開辟,刺史宣化,名賢鵲起及五代割據。張氏四世忠晉,多士翳薈,郁若鄧林,往籍可按已!隋唐之際,尚多偉人。迨宋元,則荒倫已甚。我朝文教覃敷,玉關以西,黌序莘。涼州甲科鱗次不絕,人文蒸上[34]。
武威的人文在漢至唐時興盛,宋元以降趨于衰落,清代再度興起。這與“隴右”在歷史上的人文變遷基本上是一致的。隴右由盛轉衰,唐安史之亂是其拐點。安史之亂爆發后,守衛河隴地區的唐朝邊兵精銳征發入援,吐蕃乘機占領河隴地區。兩宋時期,政權中心東移;同時,伴隨著回鶻西遷、黨項北上,甘肅遂成為少數民族政權割據地區。所謂“隴坂以西,劃為異境”[35]。明王朝鼎革后,殘元勢力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一直威脅著明政權。明沿長城一線設置九邊以抵御蒙古騎兵南下,九邊當中有三邊在清代甘肅的轄境內。明代政區大面積內收,在西北,其實際統治僅及嘉峪關以東。為因應變局,當時的河西地區在行政建制上實行帶有軍事性質的衛所制。作為邊防重地,重武輕文,勢所必然。因此,清代武威科舉之盛絕非歷史的自然延續。
有清一代,清廷通過尊崇黃教、滿蒙聯姻等手段大大降低了甘肅來自北方和西南方向的戰略壓力。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伴隨著三藩平定和臺灣收復,清廷劍指新疆的準噶爾叛亂。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準噶爾部的叛亂被平定,新疆收復,西北邊防線大大向西推進。乾隆帝就說:“陜甘自展拓新疆以來,伊犁已駐將軍,烏魯木齊、巴里坤久成腹地。”[36]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新疆東路實行府縣地區設立儒學,與中原腹地一道同風。這就是張澍所謂的“玉關以西,黌序莘莘”。
清廷安定西陲、統一新疆歷經康雍乾三朝,耗時數十載。在此期間,河西地區始終發揮著軍事前沿陣地的作用,如提供兵源、轉挽糧餉等,承受與戰爭相關的侵擾是不可避免的;但基于河西地區戰略地位的提高以及清政權在中原統治地位的漸次穩固,自康熙朝始,清廷也重視了河西地區的經營,實施了一系列重要措施,諸如民族隔離、扶助生產、蠲免糧草和救濟災荒等。武威在康熙、雍正朝已有進士和舉人產出,這與一個相對穩定的政局密不可分。但必須看到,穩定的政局之于地方教育只是一個外部條件,其決定性因素,還在于教育本身的內生能力。
傳統中國,以農立國,有限的財力無法支撐起一個龐大的教育規模。這反映在教育制度設計上,就表現為重取士而輕養士的特點,所謂“就已有人才而甄拔之,未嘗就未成之人才而教成之”[37]。只求收獲,卻不務耕耘。因此,負有真正教育之責的主體是家庭和社會。正是基于傳統教育的民間性質,地方教育生態的培植和維系在很大程度上倚賴于地方社會所擁有的科舉人才數量,特別是作為高級功名者的數量。在清代的科舉人才結構中,唯有進士能保證出仕為宦;舉人和貢生雖說具有做官資格,但銓選遲滯;生員若無捐納和軍功,幾乎沒有入仕的可能。另外,清代士人做官,事實上大都相當短暫,其生平的大部分時間還是在自己的故土度過的。換言之,正是由于地方社會沉淀著相當數量的士人,傳統教育才得以延續。成書于道光年間的《武威耆舊傳》,其60余位傳主生活當在清初至嘉慶朝,在地方從教是他們帶有普遍性的經歷。如蘇暻,雍正八年(1730年)庚戌科進士,曾知山西文水縣。“以不習吏事罷歸,設教于家,說詩習禮,一時文學彬彬。”[38]孫俌,乾隆十六年(1751年)辛未科進士,曾知廣東翁源縣。“性坦率,不能事上官,未幾罷去”“歸而從學者日眾,先生隨其材之高下而導之文,各就乎范”[39]。另外,在武威士人鄉會試硃卷和部分會試同年齒錄的師承關系中,還能見到翰林張澍(嘉慶四年己未科)、尹世衡(嘉慶十六年辛未科)、牛鑒(嘉慶十九年甲戌科)等人的題名。就現有資料看,上述三人既未主講過本籍書院,也未曾設帳授徒,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都曾指導過家鄉子弟的讀書。
至少在乾隆以前,武威是不具有教育內生能力的。那么,士人,特別是高級功名士人的教育養成就需要依靠其他途徑和手段來實現,如前已述及的“游學”。除此之外,還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書院聘請外籍人士作山長,以提升當地教育質量;其二,地方官培植。清代官員銓選有嚴格的回避制,自督撫乃至州縣官,一律不許在本省擔任。回避制的實施,使得來自文教發達地區的官員任職落后地區成為可能。清代地方官參與地方教育也是其職責范圍內的事,如知縣和知府分別是童試首場縣試和二場府試的主持者,地方書院的官課也是由地方官來承擔等。基于治教相維的傳統,地方官往往視倡學興教為頭等大事。有些地方官甚至扮演起師的角色,親自指點士子讀書,如前述的牛運震之在秦安。這類例子在地方志書中并不鮮見。科舉發展至清,制度臻于完善,各級官員幾乎是清一色的科第出身,即如府縣這類基層官員,進士出身者也并不在少數。官員的學者化,使他們本身具有了為師的能力。地方志是地方教育史料匯集的重要載體。乾隆十四年(1749年)成書的《武威縣志》?為武威唯一的清修縣志,且又十分簡略。因此,上述兩個方面的情況只能作為問題提出,以供研討。
通過游學以及王化南、劉作垣先后主講書院,應該說在乾隆中后期,武威已經聚集了一定數量的具有高級功名的科舉人才。這就意味著當地教育內生能力的形成,人才的產出具有了可持續性?。
雖說科舉人才的養成成本無從精確估算,但可以想見的是,在傳統農業社會,收益的增多主要依靠勞動力的投入,對一個家庭而言,多一個應舉之人便少了一個耕作之人。而且從事舉業尚需必要的消費,如購置圖書、應試川資等。加之科舉考試的長期性,以及不受年齡限制,治舉業者大都有家室之累。顯然,科舉的成功需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在理論上誰都可以參加科舉的考試,即法制并不限制,社會并無成見,已有功名之家對未有功名之家并不歧視;對凡有適當志愿與力量的人,這一條路總是開著”;“凡是能利用科舉在社會階梯上上升的,必需有個經濟的條件”[40]。武威地處古絲綢之路的要沖,交通便利,商業發達;境內有石羊河及其支流,充沛的水源,適合農業發展。武威“土地平衍,阡陌交通,河流縈委,土沃民饒”[41]。左宗棠曾說:“涼州向稱富庶。”[42]清代文教發達地區往往也是富裕地區,這與當時教育的民間性特質是密切相關的。
注釋:
①這里的縣包括“散州”和“散廳”。散州、散廳與縣平級,是地方三級政區。
②涼莊道設于康熙二年(1663年),領鎮番、永昌、涼州、莊浪四衛,古浪一所;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析甘肅道領之甘州府來屬,尋改道名為甘涼道,轄甘、涼二府。參見牛平漢主編《清代政區沿革綜表》,中國地圖出版社1990年版,第461頁。
③參見乾隆《五涼全志校注》,張克復等點校,甘肅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頁、第57頁。
④參見顧光旭:《響泉集》卷8《天梯書院》,“清代詩文集匯編”本,第37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33頁。
⑤參見牛平漢主編《清代政區沿革綜表》,中國地圖出版社1990年版,第457頁。
⑥清季新政時期,清廷諭令各省書院,在省城者改設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改設中學堂,各州縣改設小學堂。參見《德宗景皇帝實錄》卷486“光緒二十七年八月乙未”條,《清實錄》第58冊,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20頁。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雍涼書院改設為涼州府中學堂。參見宣統《甘肅新通志》卷38《學校志·學堂》。由此也可以判斷,雍涼書院為府級書院。天梯書院的改設情況未見記載,原因很可能是在同治回民起義期間,天梯書院就已經被毀了。
⑦“同年齒錄”是指各級各類科舉中式者按年齡長幼編纂的名錄,其中也附有中式者履歷,大多只包括中式者的個人簡介和家族譜系,只有少部分會試同年齒錄有師承關系內容。同年齒錄和硃卷一樣,也沒有刊刻時間,一般認為是在考試后不久。
⑧參見李華春:《皇清誥授朝議大夫湖南沅州知府吳松厓先生傳略》,見吳鎮:《松花庵全集》卷1,“中國西北文獻叢書”本第163冊,蘭州古籍書店1990年版,第383頁。
⑨參見張澍:《養素堂文集》卷35《先府君行述》,“中國西北文獻叢書”本第167冊,蘭州古籍書店1990年版,第381頁。
⑩參見張澍:《養素堂文集》卷24《劉星五先生傳》,“中國西北文獻叢書”本第167冊,蘭州古籍書店1990年版,第266頁。
?參見馮國瑞:《張介后先生年譜》,“中國西北文獻叢書”本第99冊,蘭州古籍書店1990年版,第427頁。邵晉涵,浙江余姚人,乾隆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進士,曾充四庫館纂修官,史部之書,多由其最后校定,提要亦多出其手;管世銘,江蘇陽湖人,乾隆四十三年進士,累官至戶部郎中。
?參見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新版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參見潘挹奎:《武威耆舊傳》卷3《孫韋西先生傳》,“中國西北文獻叢書”本第99冊,蘭州古籍書店1990年版,第177頁。
?乾隆《武威縣志》,見《五涼考治六德集全志》。《五涼考治六德集全志》有張克復等的點校本,題名“五涼全志校注”,甘肅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清代科舉在鄉試一級有另編字號政策,旨在保證邊隅士子的中式。左宗棠就說:“邊額之設,國家原以天荒難破,明定名數,俾免向隅。”參見《答吳清卿學使》,見劉泱泱主編《左宗棠全集》(書信二),岳麓書社2009年版,第481頁。順治二年(1645年),編寧夏丁字號中2名,甘肅聿字號中2名。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將涼州、西寧五學編為聿左號,甘州、肅州五學編成聿右號,各中一名;乾隆七年(1742年)對入場卷數的統計,聿右僅是聿左的三分之一,此后一科同編聿字憑文取中,一科分編左、右各中1名;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涼州歸通省卷內,甘州、西寧編聿左,肅州、安西、烏魯木齊等處編聿右,各取中1名。光緒元年(1875年)陜甘分闈后,甘肅鄉試另編字號政策廢止。參見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錄》,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78-79頁。“乾隆三十六年涼州歸通省卷內”說明該地文風興起,另編字號政策反成限制。此時,除武威,涼州府所轄鎮番、永昌文風亦興起,地方官員、士紳要求取消另編字號政策,最終得到清廷同意。參見陳尚敏:“清代河西地區的科舉家族探析”,《石河子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5期,第111-117頁。本文將武威教育內生能力形成的時間界定在乾隆中后期,涼州取消另編字號政策也是一個重要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