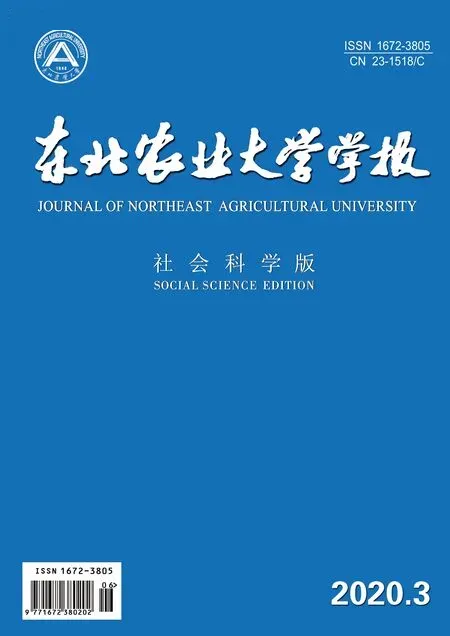乾隆初年直隸地區旱災治理與皇權維護
吳文杰
華中師范大學,湖北武漢 430070
對于技術落后的農業社會而言,雨水是一年收成的重要保障。直隸地處華北平原北部,屬于典型溫帶季風氣候,春夏兩季極易發生旱災。清朝都城北京能直接感受到直隸旱災的巨大影響。作為王朝政治核心,皇帝必須采取措施賑濟災民,緩解旱災對政治穩定的沖擊。實錄和地方志代表中央和地方兩種不同的歷史書寫。實錄記載相對完整,為還原旱災發生和賑災情況提供了史料。地方志記載散碎,卻是很好對比對象。本文嘗試通過梳理實錄和地方志中朝廷應對乾隆七至九年旱災采取的賑災措施,理解兩種歷史書寫中禨祥與政治、中央與地方、旱災與祈雨的關系。
一、乾隆七至九年旱情
乾隆七年、八年、九年,直隸、山東兩省均發生不同程度旱災。考慮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本文重點關注直隸旱災及應對措施。乾隆七至九年直隸旱災并非全年性旱災,而是季節性春旱和夏旱。春旱影響春種和夏收,夏旱影響夏收和秋收,甚至影響翌年收成。
乾隆七年,直隸地區春夏連旱,旱情嚴重。“(三月)入春以來,雖得微雪,而雨澤未沛”“(三月,乙亥)數月以來,雨澤稀少。朕宵旰靡寧,虔誠祈禱。雖得微雨,未為沾足。”[1]三月間直隸偶有降雨,但“京師一帶,尚未得有沾足雨澤,殊切廑望也”[1]。四月旱情開始擴大,“(四月,乙卯)尋奏查順天保定、永平、正定、河間、天津、順德、廣平等府屬,直隸易州、冀州、趙州、深州、定州等州屬,未得透雨”[1]。至五月,畿輔地方降水依然不足,旱情未得到有效緩解,“除宣化、大名二府及古北口外熱河一帶,雨澤沾足,二麥可望豐收。至順天、保定、永平、正定、河間、天津、順德、廣平等府,暨易州、冀州、趙州、深州、定州等州屬,雨水均未沾足普遍,麥收分數,勢必減少”[1]。直到五月十七日,“十七日夜,荷蒙上天降賜甘霖”[1]。延續三個多月的春夏連旱才得到緩解。
乾隆八年,直隸地區夏旱極其嚴重。“上冬今春,仰蒙上天屢賜瑞雪,二月間又曾得雨,方冀二麥有收,以裕民食。不意一月有余,時雨未降。”[1]以致“京師正在望雨,近畿之地,想亦同然”[1]。但旱情反而迅速發展,“今歲夏至以后,天氣炎熱,甚于往年”[1]。對在京朝貢的蘇祿國使臣,乾隆皇帝特下恩旨“著禮部派官員加意照看,多給冰水及解暑藥物,并遣醫人不時看視”[1]。足見當時京師天氣炎熱程度。至六月旱災仍在持續,不見緩解趨勢,“(六月,壬子)雖有雨澤,并未沾足。若再數日不雨,恐禾苗有損,且人民病暍者多”[1]。極端高溫天氣還在擴展,“今年天氣炎熱,甚于往年。聞山東、山西、河南、陜西所屬地方,民人竟有病暍”[1]。而天津、河間地方,旱災已成,秋收無望,“天津、河間二府所屬地方,雨澤愆期,秋成失望,百姓流移外出者甚多”[1]。此次夏旱直到“(六月)二十二三及二十五六等日,京師連得透雨”[1],才得緩解,但旱災依然造成天津、河間等地秋收無望,導致整個秋冬,乃至翌年春天農民無糧可吃,只能依靠朝廷救濟。
乾隆九年,春旱嚴重,直隸一些地方自從上年夏旱錯過秋種后,一直處于災情中,“(九年,正月)諭大學士等,直隸天津、河間等處,去年歉收,入冬又復少雪。現在加恩賑濟,一切地方民隱時廑朕懷”[1]。自乾隆八年入冬后,降雪較少,整個乾隆九年春,直隸地區旱災持續蔓延。至翌年二月仍無雨,春種受到影響,“京師及附近府屬,如天津、河間等處,自冬徂春,雨雪稀少。今清明已屆,農事方殷。朕心深為憂惕,宮中默禱,已非一日矣。此時雖未至雩祭之期,亦當敬謹祈求,以期膏澤早降”[1]。至三月,“直隸地方,至今尚未得雨。朕心深為憂慮。上年天津、河間等處,被災最重,是以加意籌辦”[1]。四月無雨,旱災繼續發展,在災區面積不斷擴大,蔓延至大城、寧津、故城、肅寧、衡水、深州、安平、饒陽、新城、雄縣、霸州、文安十二州縣。五月依舊不雨,已錯過芒種之期,“二麥黃萎。今逾芒種之期,甘霖猶未普降,切恐秋禾難以布種,民食堪虞”[1]。直至五月十六日,“今京師于五月十六日,已得透雨,近畿大概相同,看來秋成尚屬可望”[1],延續整個春天的干旱方結束。
乾隆七年、八年、九年的旱情,時間上并不完全接續,但對農業及后期賑災影響卻連續不斷。頻發旱災令乾隆皇帝分外憂慮,尤其乾隆九年正月已見春旱征兆,“惟是上秋被旱之后,冬月雨雪又少,麥苗待澤甚殷。東作方興之時,麥秋收成未卜,窮民尤堪軫念”[1]。控制災情、賑濟災民成為朝廷維持直隸地區穩定的重中之重。
二、救災措施分析
面對直隸地區三年旱災,清政府采取整飭朝政、赦獄、寬禁、賑濟、默許災民遷移、祈雨等多種方式救災,對控制旱情起到一定作用。
(一)整飭朝政、赦獄、弛禁,以感天和
傳統天人感應觀點認為朝廷行事不當則天地之氣失和,即導致災異頻發。因此糾正朝廷行事之失,“以感天和”,自然成為救災措施之一。面對乾隆七年旱災,乾隆皇帝首先考慮整飭朝政。在“飭九卿大臣體國盡職”諭中言,“入春以來,雖得微雪,而雨澤未沛,朕心甚為憂慮。……朕謂當此旱勢將成未成之際,我君臣正當早作夜思,力圖補救。若旱已成災,夫復何及。……然所謂公忠體國、克盡大臣之職者,則未可以易易數也。不過早入衙署,辦理稿案,歸至家中,閉戶不見一客,以此為安靜守分,其自為謀則得矣,如國事何?朕亦非因天時稍旱,而以此責諸臣也。凡朕所以責諸臣者,皆朕早夜之所自責”[1]。此諭中乾隆皇帝聲稱并非因天時稍旱而責備臣下,但詔書明顯曉諭群臣應恪盡職守為皇帝分憂,及時勘察旱情,且應早作準備。事實證明了乾隆皇帝的先見之明,乾隆七年春夏連旱在直隸京師造成重大影響。乾隆八年六月,旱災持續發展,為緩解旱情,皇帝詔諭:“近來天氣炎熱,臣工有奏請暫停引見者。朕思寒燠關乎庶征,今歲蒸暑倍常,即是上天垂象示儆。朕當省愆思咎,惕勵黽勉,勤于政治,以感召休和。若因此習于晏安,則大非祗承天戒之意。所有部院及八旗引見人員,照常引見,其應辦事件,亦按期速辦,毋得稽遲。”[1]此次雖未大規模整飭朝政,但透露出乾隆皇帝欲以此感天和、消弭旱災的強烈愿望。
赦獄和弛禁,是感天和最常用之法,甚至成為常例。如乾隆七年,“諭:數月以來,雨澤稀少。朕宵旰靡寧,虔誠祈禱,雖得微雨,未為沾足。從前因天時亢旱,曾降旨清理刑獄,今著刑部將在部各案內,有牽連待質者,及輕罪內情有可原者,或應省釋,或應末減,會同都察院大理寺,悉心詳查妥議具奏。至于直隸、山東、江南三省,目下雨旸不均,亦著照此例行。嗣后各省如遇災眚之年,著該督撫將清理刑獄之處,奏聞請旨”[1]。值得注意的是此措施須在成災以前使用,還要避免赦獄造成的不良影響,如乾隆判斷海州災情時指出:“今海州既已成災,而始清刑獄,是為時已遲。且明示以麥熟為期,則小民無知,以為此半年之間,可以觸法抵禁,肆行無忌,是誘民為非也”[1]。為抗旱,乾隆八年六月提出弛禁,“內開向例禁止燒鍋、賭博、斗雞鵪鶉之類,應大弛其禁,使民自便,則和氣感召,自可雨旸時若”[1]。其作用與赦獄相同。
“整飭朝政、赦獄、弛禁,以感天和”等辦法施用于災前,通過皇帝修政寬禁以感天和,消弭災害。背后邏輯源于董仲舒“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2]。災情作為禨祥成為推動整飭朝廷政治的動力,是董仲舒用以規范皇權的一種設計。但就乾隆七至九年災害發展而言,這種方式無法直接緩解旱災,但在客觀上可提高官員應對旱災的效率,使朝廷各種抗旱活動得以實施。
(二)賑濟災民
農作物生長需一定時間,即使旱災結束百姓也會在長時間內無糧可食。因此在旱災發生后的較長時間內官府必須賑濟災民。方法有二,一是直接發放糧食等物資。乾隆皇帝格外警惕直隸附近旱災,一旦出現旱災征兆即預先命令豐收省份籌集糧食,以便隨時調撥。如乾隆七年四月,“諭:山東上年有歉收之州縣,直隸今春二麥,亦未見豐稔,恐二省將來有須用米糧接濟之事。此時糧船經過山東,著即速行文與漕運總督,將尾幫漕糧截留十萬石,酌量于臨清、德州二處,分貯備用”[1]。乾隆九年年初出現旱災跡象,乾隆皇帝多次密令兩湖、河南等地預先購買糧食以備直隸旱災。“諭:軍機大臣等……今春直隸地方,雨澤愆期,麥秋失望,恐將來有須外省接濟之處。可密寄信與鄂彌達,令其豫備米麥,或二十萬石,或三十萬石。若直隸需用之時,信到即速運送”“今春直隸地方,雨澤愆期,麥秋失望,恐將來有須外省接濟之處。可密寄信與碩色、紀山,令其豫備米、麥、谷,或二十萬石,或三十萬石。若直隸需用之時,信到即速運送,庶不致稽遲。碩色、紀山接到此旨,即先期料理,不必聲張。”[1]預先籌備之糧雖未派上用場,但可見皇帝對京師及直隸地方旱災憂慮程度之深。
二是以工代賑。乾隆九年二月,春旱迅速發展。直隸總督高斌上奏提出以工代賑,“天津、河間等處地方,若城垣有應行修筑之處,興工代賑。今查大城、阜城二縣,本應修筑。但磚城工大費繁,惟照景州、滄州土城之例,修筑土工。小民得以力作糊口,為合以工代賑之意”[1]。建議得到乾隆皇帝認可。
直接發放糧食或以工代賑只是權宜之策,隨旱災時間不斷延長,糧食消耗不斷增加,成本不斷提高。如天津等地賑濟,從乾隆八年七月開始,雖然乾隆九年五月十六日得雨,旱災好轉,但直到該年七月賑濟才得以結束。
(三)默許災民遷移
歷代封建王朝均限制百姓遷移,清代尤甚。對于關外所謂龍興之地的管理,更是嚴格。但當旱災不斷蔓延,無法有效緩解之時,災民必然四散逃荒。直隸附近災民一般向富庶的北京或人口壓力相對較小的口外遷移,“自交六月河、津、冀、深等府州亢旱成災,各屬民人或出口外,或赴京師”[3]。
對遷移到京的災民,乾隆皇帝最初下令不得入京師,乾隆八年十一月下詔,“來京就食之民,日益眾多,蓋因愚民無知,見京師既設飯廠,又有資送盤費,是以本地雖有賑濟,伊等仍輕去其鄉而不顧,且有已去而復來者,不但拋荒本業,即京師飯廠聚人太多,春暖恐染時氣,亦屬未便”[1]。在直隸總督高斌執行禁止“令入京師”措施之后,乾隆皇帝回復高斌“朕反悔前諭之失斟酌矣。夫民不幸而遇災,幸有京師就食糊口之一路,又復邀之途而使空返焉,赤子其可以堪。卿其體貼前后所降諭旨,酌中行之”[1]。顯然,赴京災民得到救濟,故而大量災民涌向北京。乾隆八年十一月之后,此勢頭被遏制。
對于災民遷往口外,乾隆采取默許態度。乾隆八年九月,皇帝詔諭“本年天津、河間等處較旱。聞得兩府所屬失業流民,聞知口外雨水調勻,均各前往就食。出喜峰口、古北口、山海關者頗多。各關口官弁等若仍照向例攔阻,不準出口,伊等既在原籍失業離家,邊口又不準放出,恐貧苦小民愈致狼狽。著行文密諭邊口官弁等如有貧民出口者,門上不必攔阻,即時放出。但不可將遵奏諭旨、不禁伊等出口情節令眾知之,最宜慎密,倘有聲言令眾得知,恐貧民成群結伙,投往口外者,愈致眾多矣。著詳悉曉諭各邊口官弁等知之”[1]。災民出口外并未嚴格受限,因而遷移之舉一直未斷,直至乾隆九年六月,“欽差大臣尚書公訥親奏:直隸、山東荒旱。貧民不恤,轉徙他鄉,亦出于不得已,非盡輕去其鄉也。臣愚以為,似應密行該督撫,轉飭地方官,不必拘定資送之例,迫令回籍,但勿令聚處滋事。俟應行資送時,仍照定例資送,庶災黎謀生之道益寬”[1]。此時乾隆皇帝仍表示:“近因雨澤沾霈后,密行各處,有愿回籍耕種者,資送回籍。余亦不強。”[1]可見,朝廷對此依舊采取相對寬松的態度。“今日徒手空歸,竟至棲身無所,待哺莫訴……地方官急宜籌畫安頓,給以口糧,毋得拘泥。”[3]默許災民遷移,亦撫恤災民返鄉,對于減緩災情具有一定作用,但措施相對而言較為被動。
(四)鑿井、引河
旱災是因長期無雨或少雨而又缺乏灌溉,影響作物正常生長致其枯死,造成大量減產甚至絕收的災害。在無法獲得降水時,通過其他途徑為作物提供水源,是緩解旱災的有效手段。有學者指出中國鑿井取水歷史悠久,明清時期已積累大量相關技術。修建水利設施、引河水灌溉農田也在明清時期取得長足進步①唐嘉弘《井渠法和古井技術》,農業考古,1984(1);廖艷彬《二十世紀以來明清長江流域水利史研究綜述》,中國經濟與社會史評論,2012。。可見鑿井和引河是清人在抗旱時可用的有效手段,但兩項措施在直隸地區的推廣均遇困難。
乾隆朝實錄中很少提到鑿井這一措施。乾隆九年五月,直隸總督高斌參奏灤州知州李鐘俾“不能體察民情,及時出借口糧,遽赴延慶州交盤,致有刁民羅天才等乘機糾眾,搶割麥田,強借糧食等事。……李鐘俾玩視民瘼,理應報參”[1]。乾隆皇帝則提及李鐘俾勸民鑿井一事,“猶憶劉于義曾奏李鐘俾勸民開井有效云云”[1]。實際早在乾隆二年直隸地區即試行鑿井備旱。乾隆二年六月,原任營田觀察使陳時夏進《區田書》三冊,其中提到“鑿井澆灌,是備旱之法”,認為“且鑿井備旱,于北地尤宜”[1]。但“但法久不行,事經創始,必從容辦理,毋遽毋擾,使小民有趨事之樂,而官吏無督促之煩,然后可垂永久。臣等酌議,請于直隸地方先試舉行。”[1]可見此前鑿井灌溉之法在直隸地區并不普遍。此后鑿井之議數起,但乾隆皇帝以“切勿為屬員所朦蔽,以致有名無實,徒滋擾累”[1]為憂,并未大面積推廣鑿井之法。加之各地情況復雜,“鹽山土疏泉苦,得井難;慶云土堅水淡,得井易”[3]。因而鑿井取水無法確保干旱之地能獲得地下水源。
至于修建設施、開河引水,在京津地區也存在相當難度。以天津為例,乾隆八年天津道陶正中“請自天津護城河起由八里臺東至佟家樓開渠一道,接連賀家口舊有,引河藉城東南隅之海河閘,以通潮汐,附近居民田畝水旱皆得播種”[4]。建議雖好,但海河水系易淤特性使京師附近開河引水抗旱灌溉具有極大難度,即使新開之后可用,很快也會淤塞。且海河水系易沖決堤壩,水利設施修建成本極高,保存亦極難[5]。鑿井、引河看似直接有效,但技術條件限制使其無法真正解決干旱問題。因此全部希望只能寄托在祈雨上。
(五)祈雨
自成湯禱于桑林開始,歷代帝王一直肩負著祈雨重任,并由此形成一套完整祈雨和祭祀體系。清朝統治者從順治十四年開始在圜丘舉行祈雨儀式,康熙皇帝也非常重視祈雨,尤其“京師為天下根本之地,乃幾月不雨,朕甚憂之,欲躬行祈禱”[6]。但康熙、雍正時期未建立常雩制度。
乾隆七年,直隸京師附近發生春夏連旱,乾隆皇帝先是在宮內“虔誠祈禱”,三月戊子日,“上詣黑龍潭祈雨,祭昭靈沛澤龍王之神”[1]。五月戊寅,“夏至,祭地于方澤,上親詣行禮”[1]。五月十七日夜出現降水。乾隆七年五月癸酉,乾隆皇帝定雩祭典禮,規定“每歲屆期致祭一次”[1],是為常雩。乾隆八年開始實行。
乾隆八年夏旱嚴重。乾隆八年,四月辛丑,“諭:軍機大臣等,京師正在望雨,近畿之地想亦同然”[1]。此年乾隆皇帝本欲親自行大雩禮,但因“太醫院臣奏:圣體微患初愈,不宜勞動。左右大臣言皇上誠敬之心,至純至切,足以昭格穹蒼,雩祭為常行之典,不必今歲一定親行”[6]。于是命恒親王弘晊恭代行禮。但此次祭祀未得降水,旱災依然持續。六月壬子,又“著禮部即速虔誠祈禱”[1]。直到六月“二十二三及二十五六等日,京師連得透雨”[1],旱情方得以緩解。
乾隆九年春旱嚴重,自二月起乾隆皇帝諭“自冬徂春,雨雪稀少,今清明已屆,農事方殷。朕心深為憂惕,宮中默禱,已非一日矣。此時雖未至雩祭之期,亦當敬謹祈求,以期膏澤早降。著禮部、順天府虔誠祈禱,速議舉行”[1],開始祈雨。三月庚辰“遣官祭黑龍潭昭靈沛澤龍王之神”[1]。辛卯日,“上詣黑龍潭,祭昭靈沛澤龍王之神”[1]。接連祈雨。四月乙卯日,舉行常雩,“祀天于圜丘,上親詣行禮”[1],依舊無雨。五月己卯,乾隆皇帝去暢春園向皇太后問安,諭“朕詣暢春園問安,皇太后雖慈訓屢頒,寬慰朕躬,而每見皇太后以天時亢旱,憂形于色,朕心更為不寧。今日太后從寢宮步行至園內龍神廟,虔誠祈禱。朕敬聞之下,惶恐戰栗,此皆朕之不德,不能感召天和,而累母后焦勞,至于此極。為人子者,實無地可以自容”[1]。五月戊子,“夏至,祭地于方澤,上親詣行禮”[1]。直到五月十六日才得大雨。
通過比對各類賑災措施,發現唯有實現降水的“祈雨”方為解決旱災的根本之策,而在無法人工降雨的清代,降水只能是自然運行的結果。但有效降水被歸因于乾隆皇帝祈雨,此歸因在實錄和地方志中如何呈現?
三、中央和地方:兩種歷史書寫
京師在直隸環抱之中,中央朝廷穩定與直隸息息相關。乾隆七至九年直隸尤其是京師附近發生旱災直接威脅清朝統治,故而乾隆皇帝極為重視祈雨,乾隆七年正式制定的雩禮,即為制度層面反映。
通過梳理乾隆七年至九年朝廷緩解災情的各類措施,可清楚發現,只有降雨方為消除旱災根本之策。實錄在歷史書寫時旱災、祈雨和降雨三個環節緊密聯系,任何一環節出現問題,均損害皇帝權威。首先是旱災發生,乾隆皇帝自認己之不德所致,“京師旱暵特甚,病暍者多,此皆朕不德”“此皆朕之不德,不能感召天和”“曰予不德,小民何辜”[1]。其行為顯然是效法商湯祈雨禱于桑林“余一人有罪”[7]的說辭,表面上順民愛民,實際神化自我,證明只有受命于天的皇帝方可溝通天人。其次是由誰祈雨,乾隆七年至九年祈雨行動中,皇帝、親王、皇太后、禮部、順天府均參與祈雨,但是祈雨權力完全來自皇帝。恒親王是代乾隆皇帝祈雨,禮部、順天府是在皇帝授權和督促下祈雨。最后祈雨一定會應驗。“旱災——降雨”等自然現象成為神化皇帝、維護皇權的工具,故而乾隆七年至九年皇帝祈雨雖經曲折,也被視為應驗。《乾隆朝實錄》記載即完全遵行此邏輯。
通過《清實錄》的記載基本還原乾隆七年八年九年的旱災過程及朝廷救災措施代表中央朝廷的話語體系。
相比于《清實錄》的詳盡細致記載,地方志中記載顯得分散而不完整,但在一些縣志中依然留下記錄。
《續天津縣志》卷首《恩典》載:
乾隆八年,發帑及粟賑濟天津、河間荒歉。
乾隆九年,撥豫、東二省谷石運津以資賑糶[8]。
卷一《星土祥異》載:
乾隆八年五月,大旱苦熱,土石皆焦,桅頂金流,人多熱死。自春不雨,至于夏六月始雨,晚禾槁而復青。秋大有年。
乾隆九年,夏無麥[8]。
《大城縣志》卷十《五行志·災異》載:
(乾隆)八年,大旱,炎風如炙,人多暍死,二麥盡枯,秋禾未種[9]。
《寧津縣志》卷十一《雜稽志·災祥》載:
(乾隆)八年,大旱,炎風如災,人多暍死[10]。
《東安縣志》卷九《禨祥志》載:
(乾隆)八年五月,大暑,人多暍死。
(乾隆)九年,夏不雨,上虔禱,甘霖立沛。先是總督高奏請發粟兩千石振借貧民,免其還倉,是秋歲大稔[11]。
縣志記載未見乾隆七年春夏連旱狀況,可見乾隆八年、九年旱災基本狀況。賑災措施以發粟為主,此為皇帝和中央朝廷權威在地方上的體現。只有《東安縣志》中記載乾隆皇帝祈雨效果,“九年,夏不雨,上虔禱,甘霖立沛”。從乾隆九年祈雨過程記載來看,絕非“上虔禱,甘霖立沛”的簡單過程。《東安縣志》之所以如此記載,或出于兩方面考慮,一是因文體所限,關于禨祥災異記內容盡量簡練,故未長篇羅列求雨過程。二是出于維護皇權需要。乾隆九年祈雨不僅乾隆皇帝本人參加,皇太后也赴龍神廟,可見求雨期盼之強烈。縣志中記載為“上虔禱,甘霖立沛”,將降雨神化為皇帝帶來的祥瑞。值得說明的是,中央直接被皇帝控制,歷史書寫只能為維護皇權服務,地方對此可有不同理解,或可闕而不載。事實上地方與中央歷史書寫一致,可見地方完全服從中央控制。當直隸地區發生旱災時,中央既給予地方物質賑濟和便利政策,也給予精神統一管控,確保距離北京最近的直隸政治穩定。地方則在歷史書寫中以頌揚方式予以記載和回應。對于祈雨的記載,中央和地方不同的歷史書寫將禨祥與政治、中央與地方、旱災與祈雨關聯組合,均發揮了神化皇帝、維護皇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