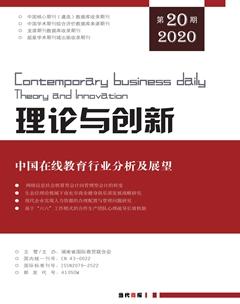弘揚延安精神 傳承紅色基因
王月圓
“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1969年,28000名來自北京的知識青年懷揣著理想信念來到延安,他們將大好的青春年華奉獻給了這片紅色的沃土,他們吃苦耐勞、艱苦奮斗、求知若渴,將延安精神深深烙印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之中,為革命老區注入了新思想、新方法、新動力。
初到陜北的北京知青們面對的不僅是陌生新奇的生活環境,還有許多現實的困難。比如,如何使用柴火灶?如何用當地的方言同大家交流?如何耕地、除草、收割、打壩、修梯田等等,這些都是擺在北京知青面前需要解決的難題。此時,陜北鄉親們手把手地幫助知青們站穩腳跟,熱心地為知青出點子,他們用樂觀向上、頑強拼搏的精神,使北京知青找到了現實的努力方向,奠定了老區文教、醫藥、生活全新發展的基礎。
丁愛笛,人稱“丁牛”,他在延川縣張家河村插隊落戶,插隊期間他擔任過四次生產隊長,四次大隊書記,當時的生產隊基本都是大鍋飯,大家干活時普遍存在出工不出力的現象,尤其是夏收剛結束,地里追肥需要挑糞的量更大,但個別人總是偷偷地將糞沿途倒掉減輕重量,帶壞了整個挑糞隊伍的風氣。為了剎住這股歪風邪氣,在一次挑糞途中,丁愛笛守在上山送糞必經的一棵老杜梨樹下,將腰間別著的秤砣往樹上一掛,每來一個人就攔下來把所擔的糞稱一稱,這下有人露餡了,有的壯小伙只挑了25斤不到,而有的婦女足足挑了100多斤。丁愛笛把自己挑的145斤糞放在旁邊,誰要是不服氣也可以來稱一稱。總結大會上丁愛笛對少挑糞的人按比例扣除相應的工分。這下炸鍋了,有當街罵的,有去公社告狀的,甚至給縣革委會寫信舉報,但是丁愛笛生生抗住壓力,堅持實事求是,團結周圍的群眾按規定辦事,就這樣“丁牛”的外號響徹十里八村。在豐收的分紅會上,丁愛笛更是大膽創新,提出將按勞動分配的比例由原來占總收入的20%提高到30%,這一次丁愛笛繼續“牛”到底,大家工作積極性得到了大幅提升,年底又獲得了豐收。他將實踐數據結合理論思想,發表了一篇如何提升工人積極性的文章,引起了陜西省委領導的高度重視,丁愛笛就靠著這么一股牛勁,帶領著延川縣張家河村的鄉親們脫貧致富,將落后的小山村建設成模范山村。
在北京知青中,仍然有許多人因為各種原因沒有能夠離開這里,他們成為黃土地的守望者,為延安的發展奉獻了一生。汪桂蘭就是留延北京知青的一個典型。1969年1月,從北京第一師范畢業不久的她來到宜君縣堯生公社思彌大隊插隊落戶,同年7月走上講臺,成為一名人民教師。她克服了和學生之間的語言障礙、生活習慣的不同以及教學方法不當等重重困難終于成長為一名合格的鄉村教師。可就在農村生活了整整9年后,1978年后半年,北京傳來確切消息,當年因為“錯分配”的原因,1969年從北京第一師范畢業的學生現可落實政策回京。雖說落實政策是個好事,可是一個頗為殘酷的現實橫亙在汪桂蘭的面前:早在1974年汪桂蘭已與黃陵縣雙龍中學的數學老師白昕輝結為連理,并且有了兩個孩子,一家人生活得十分幸福。而政策規定得很明確,只允許知青一人返京,配偶及子女不在此列!汪桂蘭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之中,兄弟姐妹中就缺她一個,遠在北京的老母親早就盼她回來團圓。多少個夜晚,汪桂蘭都難以入睡,腦海里充斥的東西太多了,一會兒是北京大都市的風貌,一會兒是黃土地熱情、淳樸的民風;一會兒是舉家團聚的歡樂情景,一會兒是已經與自己生活了4年的丈夫及兩個孩子的身影,還有當地學生們那一張張稚嫩的面孔和一雙雙渴求知識的眼睛。看著十多個在當地結婚的同伴一個一個全都與丈夫離了婚,只身返回了北京,汪桂蘭也曾猶豫過、痛苦過,但最終她放棄了回城。她心里明白:雖然通情達理的丈夫沒有阻攔,可自己一旦回去,這個家就散伙了,丈夫的人生可能就要改變,孩子們就會失去親娘。當然,促使汪桂蘭做出人生這一重大決定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她已經習慣了這里的一切,這里有她的追求,有她所鐘愛的事業。當時首都教師嚴重缺乏,北京市教育局先后給汪桂蘭來過4封信,希望她回京執教,汪桂蘭都謝絕了。多年以后,汪桂蘭與友人說起此事,一臉的爽快:“不是說我多偉大,反正我當初的選擇太正確了!”1998年底,中央電視臺推出紀念改革開放20年特別節目——“20年·20人”,汪桂蘭位居其中,與體操王子李寧、打假英雄王海、“中國第一村”黨委書記吳仁寶、海爾集團總裁張瑞敏、計算機文字信息處理專家王選等齊名。《西安晚報》曾以《一個北京知青的陜西人生》為題報道了汪桂蘭的先進事跡。延安市委、市政府先后授予她“學雷鋒、學英模先進個人”“弘揚延安精神先進個人”、延安市“勞動模范”的稱號。
在上山下鄉的熱潮中,北京知青用青春書寫了一首首可歌可泣的壯麗詩歌,更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弘揚著延安精神。
憶往昔,崢嶸歲月稠;看今朝,延安精神薪火相傳、永不熄滅。在如今這樣一個世界形勢瞬息萬變,祖國發展日新月異的時代,秉承延安精神,弘揚主旋律,是時代的呼喚,是發展的需要。讓我們把自己錘煉成延安精神的傳承者、發揚者、宣傳者,將“延安精神”發揚光大,代代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