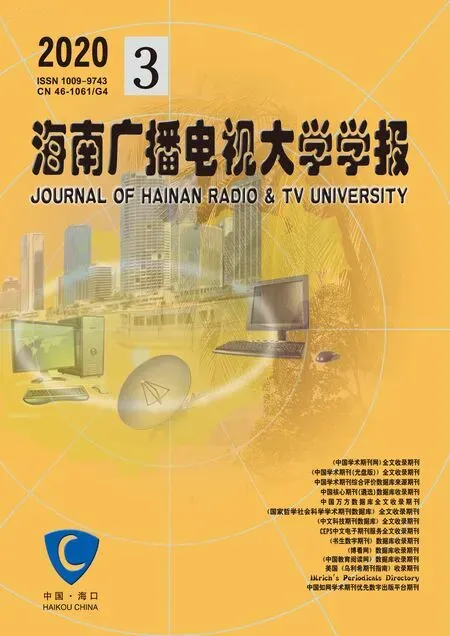莎士比亞悲劇《奧賽羅》的寶萊塢式呈現:電影《奧姆卡拉》的跨文化演繹
張怡靚
(延世大學 人文藝術學院,韓國 原州 26493)
新世紀以來,全球對莎士比亞戲劇再演繹的興趣激增,特別是以亞洲為首的非英語國家對莎劇的重現,改編和再演繹的熱度和產量已逐漸超過英語國家。在跨文化交流和跨媒介演繹熱潮中探尋莎士比亞戲劇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處的地位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議題:究竟莎士比亞是所謂全球化品牌的遮蓋下,西方霸權主義文化傳播的武器?還是成為了基礎原材料在區域再創作過程中注入本土文化元素,重新加工成為民族特色產物重新走入西方甚至世界舞臺?作為莎士比亞著名四大悲劇之一的《奧賽羅》以其跌宕起伏的劇情和獨特的悲劇藝術展現形式被亞洲導演以多種形式進行跨媒介改編與演繹。2006年,由印度導演威紹·巴拉德瓦杰(Vishal Bharadwaj)執導的電影《奧姆卡拉》正是改編自《奧賽羅》,在莎士比亞全球化視閾探索和改編浪潮中應運而生。該電影在2006戛納電影節展出并被選中在開羅國際電影節放映,導演紹威·巴拉德瓦杰被授予最佳電影藝術貢獻導演獎。《奧姆卡拉》以展現印度政治、文化為主的跨媒介演繹,給莎翁的傳統經典劇本添加了新鮮的寶萊塢元素,熒幕中劇情設計與角色設定基本與原作品《奧賽羅》保持一致,但電影對人物形象的塑造與人物關系沖突的描寫扎根于印度本土文化特別是種姓制度文化,充分體現了區域電影改編、再演繹與莎士比亞戲劇全球化傳播之間的雜糅關系。
一、印度種姓政治下的愛情悲劇
電影《奧姆卡拉》的故事情節基本延續了莎劇《奧賽羅》的悲情基調,同樣圍繞愛情、嫉妒與陰謀為主線展開敘述。電影的歷史背景設置在后殖民時期,擺脫英國殖民統治的印度逐漸開始探索現代化的民主制發展道路,同時也導致印度國內各方政治勢力爭權奪利,特別是北方邦沖突不斷。男主人公奧姆卡拉(Omkara)和多莉(Dolly)的悲慘愛情故事就發生在北方邦西部的密魯特市。男主角奧姆卡拉作為支持當地政治家巴里薩布(Bhaisaab)的幫派領袖,在一次躲避追殺的逃亡中偶然遇到了收留他的多莉,并深深愛上了這位來自印度上流社會,高種姓階級的印度姑娘。多莉的父親是印度主流社會有名望的律師,束縛于印度根深蒂固的父權制傳統,多莉被迫接受父親的包辦婚姻。而在婚禮當天,奧姆卡拉 “綁架”走了傾慕已久的多莉;私奔多日,多莉最終在政治家巴里薩布的調解下,再一次回到家中勇敢的向暴怒的父親承認自己心中所愛是奧姆卡拉。面對父親的斥責和警告,身著印度傳統紗麗服飾的多莉,目光溫柔而堅定的告訴父親自己決定放棄一切追隨自己的愛人。
電影《奧姆卡拉》成功將莎翁原著《奧賽羅》中對男女主人公奧賽羅(Othello)和苔絲狄蒙娜(Desdemona)膚色差異描寫和種族差異的隱喻改寫成了反映印度傳統種姓制度和社會政治的等級差異,以戲劇性方式呈現了印度種姓造成的階級矛盾;奧姆卡拉和莎劇中的被稱為摩爾人(Moor)的奧賽羅[1]都屬于低等族裔,是主流社會的他者。雖然印度是在發展中國家中較早建立起民主體制的國家,但其由來已久的種姓制卻是其民主體制無法擺脫的身份政治—“種姓政治”,且逐漸與國家民主制進程相融合,形成了印度獨特的種姓政治發展趨勢[2]。奧姆卡拉因為父親來自高等種姓,母親是社會地位極為低下的“賤民”而被戲虐的稱為“雜種”。由于印度嚴格的種姓制度和社會等級意識,奧姆卡拉的他者身份使他一直生活在缺乏身份認同和被主流社會邊緣化的自卑中。在種姓文化根深蒂固的印度,高種姓女子下嫁給低種姓丈夫,被視為是對家族的“玷污”與“背叛”,巨大的社會階級差異是導致奧姆卡拉與多莉愛情悲劇的根源之一。
二、東方男性焦慮的多維度呈現
電影對多莉和奧姆卡拉人物關系的塑造隱喻了印度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與傳統父權制社會結構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受傳統父權制社會意識形態影響,印度女性被認為是男性的附屬品,被長期禁錮于家庭活動中,完全依從于男性。而來自高種姓,受過印度高等教育的多莉,受到西方新自由主義影響,是西化的印度“新女性形象”[3]的化身。電影中形象和服飾塑造上,多莉的膚色比奧姆卡拉白且時常以淺色傳統服飾出境,暗示了兩人一黑一白、一高一低的的不對等社會地位。成長于傳統印度社會,奧姆卡拉長期受到父權制思想傳統的影響,對多莉的愛充滿物化占有欲,視其為自己的私有財產。在電影中,奧姆卡拉多次回想起多莉的父親對他的警告“一個可以愚弄自己父親的女人終將不屬于任何人”(she who can dupe her own father will never be anyone’s to claim),這句臺詞反復以多種形式出現在電影敘事中,推動了劇情發展。奧姆卡拉對于多莉抵抗父親包辦婚姻產生了極為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十分慶幸多莉不顧原生家庭阻撓和反對,放棄一切選擇出身卑微的他作為丈夫;但這同時也成為奧姆卡拉揮之不去的陰影:如果代表父權制家庭權威的父親無法完全掌控多莉,那么被稱為“雜種”、 作為社會的他者的自己又如何完全將多莉據為己有?這一矛盾心理激起了奧姆卡拉的無意識焦慮和男性氣質危機。這句臺詞既交代了奧姆卡拉對多莉猜忌的根源,更展現了多莉作為后殖民國家新女性意識覺醒與其父親和奧姆卡拉所代表的印度父權制社會意識間巨大的文化差異與矛盾沖突。
此外,電影通過對莎劇中人物原型凱西歐(Cassio)身份的適當改編,也使劇情變得更加耐人尋味。奧姆卡拉與凱肅之間的沖突呼應了印度后殖民時代消解殖民話語的需要[4]。這場愛情悲劇的導火索源于奧姆卡拉的副手狼(Langda)因奧姆卡拉提拔另一位副手凱肅(Kesu)為副將而心生嫉妒,一心想陷害并除掉凱肅,因而設計制造凱肅與多莉“偷情”的證據,誤導奧姆卡拉懷疑自己的妻子與他的愛將通奸。電影結局處,被嫉妒蒙蔽了雙眼的奧姆卡拉以為自己經受到愛情與友誼的雙背叛,在電影結尾處親手殺死了心愛的多莉。電影中,凱肅是存在于印度種姓階級之外的西方人物形象。他會說英語,是帶著西方白人男性獨特自由氣質且獨立于印度種族階級系統之外的存在。凱肅是多莉的大學同學,一個融入印度生活,卻代表殖民霸權主義形象的白人。凱肅和多莉身上擁有共同的東西方文化雜糅氣質,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奧姆卡拉缺乏身份認同的自卑與性別焦慮,以及面對西方強大男性霸權主義氣質而產生的東方男性焦慮。因凱肅的存在而產生的嫉妒、焦慮、不安等情緒最終致使奧姆卡拉輕信了反派狼的讒言,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劇。
在表現狼誤導奧姆卡拉,誣陷多莉與凱肅有奸情的情節時,電影以交叉蒙太奇方式進行敘述,空間敘事交錯進行。房間里,多莉為了討好奧姆卡拉,向凱肅學習彈奏吉他唱英文歌曲“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房間外,是狼故意安排奧姆卡拉發現多莉與凱肅單獨“約會”,并多次向奧姆卡拉質疑為何多莉和凱肅會挑選奧姆卡拉不在的時候“故意”獨處,暗示兩人有“奸情”。隨后劇情推向一身黑衣的奧姆卡拉回到房間,鏡頭聚焦一襲白衣的多莉在窗邊邊彈邊唱。電影畫面中,多莉手握吉他羞澀的彈奏愛的悠揚贊歌;此刻一心想討好奧姆卡拉的多莉與內心充滿猜忌與憤怒的奧姆卡拉形成了強烈對比。近焦鏡頭下奧姆卡拉的面部表情展現出此刻的他對多莉的舉動不是感動,而是西方霸權文化對東方社會他者的挑釁。鏡頭下兩人一黑一白的服裝差異更是鮮明刻畫了兩人不可融合的差異性。作為印度幫派首領,擁有強壯身材和過人膽識的奧姆卡拉本應是強大男子氣概的形象代表,但因為他來自低種姓階級和“雜種”身份使他長期被主流社會邊緣化,面對高雅而自由奔放的多莉時,奧姆卡拉覺得自己始終無法在多莉面前建立父權制威信,兩人之間因此而存在著巨大的信任危機。
電影結尾處,誤以為妻子和凱肅一次又一次的玩弄和背叛了自己的奧姆卡拉始終不明白為何多莉會選擇凱肅而不是自己,忍無可忍的他痛苦的問妻子“是我缺什么嗎?”正是這個疑問,徹底暴露了奧姆卡拉無意識的男性焦慮和東方男性氣質危機。在隨后兩人的對話中,奧姆卡拉并沒有給多莉真正解釋的機會,最終含淚用枕頭殺死了多莉。奧姆卡拉的這一舉動表面上是懲罰出軌的多莉,實際上是在緩解自己的男性焦慮所采取的極端做法。嫉妒凱肅的白人皮膚,嫉妒凱肅和多莉一樣受到過高等教育,嫉妒他們都曾受到西方自由主義文明的開化。此時的凱肅并不僅僅是普通男性,他和奧姆卡拉之間的沖突也不僅僅是男子氣概的競賽,而是代表西方霸權主義和現代文明與印度民族主義和本土文化之間的矛盾。此外,奧姆卡拉與多莉之間的悲劇,展現的是印度高低種性階級之間和現代化新女性意識覺醒與父權制社會傳統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從情節表達層次上看,多莉父親的警告多次以話外音形式出現在奧姆卡拉腦海中,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是展現電影主題的內在線索,代表著多莉悲慘結局的根源所在—她身上渴望自由與無差別愛情的新女性氣質既是吸引奧姆卡拉也是激起丈夫猜忌的主要原因。
三、女性主義元素
這部電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一部對印度女性主義的探索。除了刻畫異性戀之間復雜的愛情和男性之間的氣質博弈外,多莉與奧姆卡拉的妹妹銀都(Indu)之間的的女性友誼也給電影敘事增添了更多女性主義色彩。父權制社會下,印度女性活動長期受制于家庭區域。因此在奧姆卡拉外出時,多莉的大部分時光都是與銀都共同做家務中度過。她們與家庭中其他印度傳統農村婦女圍繞在一起做飯,打掃衛生,制作手工,籌備婚禮。雖然銀都來自低種姓階級,卻與多莉代表的印度高種性、新女性之間并沒有任何芥蒂。隨著劇情發展,多莉和銀都之間的相互喜愛和相互依存感逐漸增強。多莉跟著銀都學習當地料理,努力融入這個與她原生階級有著巨大差異的新家庭。鏡頭多次對準兩人在院子里嬉笑打鬧,婦女們圍坐在一起,使觀眾充分感受到了女性團結的力量。
面對比自己社會階級高,勇敢追愛的多莉,銀都的眼神充滿了驚喜和崇拜。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多莉喚醒了銀都的女性意識。在奧姆卡拉和多莉多次因誤會產生矛盾時,銀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調和作用,她不止一次勸說哥哥要關心、愛護多莉。電影結尾處,銀都發現多莉死于哥哥之手,而自己的丈夫狼竟然是幕后策劃這一切的罪魁禍首時,銀都勇敢地說出了事實真相,證明所謂“通奸證據”的腰帶是她拿走,而不是多莉獻給凱肅的。得知真相的奧姆卡拉懊悔不已,絕望的對狼說“我不會殺死你,殺你是對你的解脫,我要讓你活著的每一天都在煎熬中贖罪!”然而,就在狼走出房門的那一刻,銀都追上來親手殺死了自己的丈夫。銀都的這一舉動不僅是為多莉報仇,更是凸顯了女性力量的崛起,捍衛了以她和多莉為代表的印度女性尊嚴,強調了女性主義視角。這部電影既向觀眾展現印度女性在社會束縛和家庭制約下產生的深厚姐妹情誼,也通過大熒幕間接向觀眾作出暗示,新時代的女性力量不可小覷。
四、莎士比亞全球化視域下的印度寶萊塢改編
雖然電影《奧姆卡拉》在情節設計和改編上以忠于原著為主,但電影本身的人物形象刻畫,視覺效果和音樂設計都極具寶萊塢特色。電影作為一門綜合性藝術,通過特定鏡頭表達和視覺傳達,加之本國的歷史和文化底蘊為基礎,更為直觀的展現出背景國家的社會狀況[6]。電影除了反映印度本國種族社會制度外,還以現實主義視角關注了印度的黑幫沖突、政治腐敗等社會問題,同時又起到了印度傳統文化和歌舞表演的傳播作用。作為文化生產的一部分,電影《奧姆卡拉》通過將本土印度音樂舞蹈文化融入莎士比亞文本,創造了高雅文化與本土流行文化的新型歌舞片,為印度電影加入莎士比亞的全球化傳播發行做出了巨大貢獻,同時也增強了莎士比亞經典戲劇在印度普通觀眾的曝光度[5]。這部寶萊塢式的電影呈現,并不僅僅是西方霸權文化影響下的產物,更是寶萊塢向世界展現其電影藝術文化滲透力和社會文化功能的影響力。電影本身交織著“印度”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家與世界等跨文化主題,通過其獨特的美學傳統和生產模式,通過影像敘事反映印度保守傳統的一面以及傳統文化與現代商業社會下的文化沖突[6]。
這部電影充分展現了導演威紹對原著的寶萊塢式改編。莎劇中作為凱西奧和苔絲狄蒙娜“通奸證據”的手帕,在電影中被巧妙的換成了印度紗麗的腰帶。歌舞是印度商業電影的重要特點之一。這部電影也同樣加入了充分展示印度寶萊塢風格的歌舞演出,表演者誘人美麗曼妙的舞姿和臺下觀眾的歡呼雀躍,夸張的表演營造出歡快的節日氣氛。值得注意的是,該電影語言采用的不是寶萊塢慣用的印度語(Hindustani), 而是貼近當地鄉村人民文化習慣的印度方言卡里波利語(Khariboli Dialect),寶萊塢利用地方優秀的傳統文化藝術資源,既提升印度觀眾的文化歸屬感,也為莎翁的經典悲劇文本增添喜劇視覺效果,使得印度電影出口躍居世界第二位,僅次于美國。反觀印度本國電影市場,好萊塢僅占市場份額的5%,寶萊塢出產的電影不僅在數量上取勝,也是第一個非西方社會生產的主流文化產品。寶萊塢電影除了在電影敘事技巧上借鑒好萊塢制作風格,其音樂和舞蹈創作,電影審美也十分國際化[7]。觀眾在觀影時,既體驗了充滿異域風情的莎士比亞悲劇的另類改編,同時也對印度本土文化多了一分了解。
五、結 語
海外學者在《寶萊塢莎士比亞》(BollywoodShakespeares)一書中提到:“寶萊塢電影《奧姆卡拉》不單純是一部簡單的莎士比亞戲劇的跨媒介改編,而更多的是寶萊塢對經典文學作品再書寫和再創造能力的證明[8]”。即使沒有莎士比亞的《奧賽羅》文本做對比,該電影也是一部高度根植在印度社會語境化,反映印度社會現實的愛情悲劇。全球化視域下的莎士比亞戲劇早已成為一種全球化品牌,在國際市場上供寶萊塢借鑒、改編再演繹以展現本民族獨特文化,增加國際宣傳噱頭。因而區域改編可以說是莎士比亞全球化傳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既是全球化的產物,也是推動文化全球化發展的動力。該電影也以其悲喜交加,雅俗共賞的精彩呈現吸引了觀眾的眼球,強化了觀影的情感體驗。歡快的印度歌舞和民族特色鮮明的印度服飾加上著名莎士比亞的悲劇故事使得這部電影實現了寶萊塢藝術性與商業性的完美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