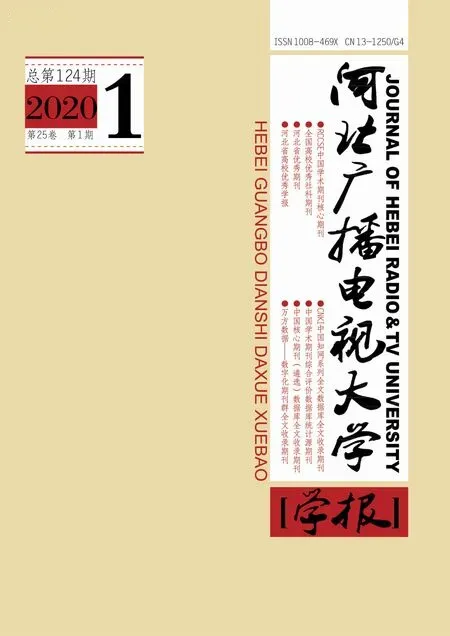民國北京政府時期京師社會救助機構探析
韓雨樓
(河北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0024)
社會救助是社會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國家的政府對其處于困境的人民具有義不容辭的救助責任。民國北京政府在社會救助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改革,出臺和完善相關救助政策,組建了粥廠、收容所、教養機構等慈善場所。賑委會和新設置的警察廳是政府救濟的主要實施者,此外,來自社會上的多元救助方式是對政府救助的必要補充,為處于底層的邊緣人群提供了切實有效的幫助,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影響。
一、粥廠
“民以食為天。”在京師百姓的日常開銷中,占比最大的是食物消費,達到了68.8%,①李景漢:《北京最低限度的生活程度的討論》,《社會學界》,1929年第3卷,第3-5頁。在特殊時期甚至達到85%左右。社會救助體系中,食物救助是關鍵性的一環。對于陷入貧困的人群來說,獲得食物是生存的當務之急和根本需求。解決食不裹腹最直接且具有代表性的救助,莫過于設立粥廠。民國初期私人團體設廠較多,1926年后政府逐漸成為粥廠救濟的主導者,賑委會、京師警察廳作為主要負責部門,制定并形成了一套富有成效的運作模式。
官辦粥廠的資金主要來自政府財政,另有部分社會捐款(私人團體和個人捐助)。粥廠花銷與貧民數量關系密切,工具、燃料、人頭等費用基本穩定,以1915年為例,上述費用占全部運作費用的18%—26%。②(美)西德尼·D.甘博:《北京的社會調查》(上),陳愉秉等譯,北京:中國書店,2010年版,第301頁。美國經濟學家甘博在1915年的記錄中,統計出7家粥廠共施粥963 201份,費用合計為11 260.61元,所用糧食1 723.17擔,每擔價值為5.10元。當貧民數量激增導致粥廠入不敷出時,警察廳可以向總統府、內務部、財政部申請撥款。
粥廠的開放時間大多具有季節性。開廠閉廠的時間都受到季節影響,一般在秋冬季天氣寒冷之后開設,氣溫轉暖之際閉廠。部分粥廠會登報告示,通知“粥廠提前開辦” “粥廠續辦一月”等。粥廠提供的粥由小米和大米混合熬成,其中7/10是小米,3/10是大米③(美)西德尼·D.甘博:《北京的社會調查》(上),陳愉秉等譯,北京:中國書店,2010年,第300頁。,盛于木桶中抬至放粥處以鐵勺散發,每人得一勺之粥,約合4兩之米。④張金陔:《北京粥廠之研究》,李文海主編:《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社會保障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09頁。粥廠的救濟對貧民來說雖然是杯水車薪,但保證了貧民最低限度的生存,使得冬季因凍餓致死的人數大為減少。
粥廠有相應的管理制度。為使真正貧困者享用救濟粥,各粥廠也是煞費苦心。如有的粥廠會自備碗箸,要求貧民在廠內食用,既使貧困者較為體面的食用救濟粥,也避免偷奸耍滑者領粥回家飼喂雞犬,造成食物的浪費。有的粥廠實施定時關門制度,防止無良人員重復領取。頒發粥牌是粥廠通用的管理形式,粥牌由竹制、木制或厚紙板制成,作用相當于領粥證。除了一般粥牌,還有特殊的“優待牌”,對殘疾、老弱或者孕婦等不便領粥者頒發優待牌,上面寫明牌主信息,可以委托他人代為領取。有的粥廠粥牌用顏色加以區分,按性別區分(紅色女用,黃色男用)或按貧困程度區分(紅色極貧,白色次貧),領粥時以紅色優先,以此來維持秩序。據1920—1921年統計數據,京師的粥廠每廠每季領粥人數不下二十萬人,如計算全市每季領粥人數在5 167 000萬人左右。①張金陔:《北京粥廠之研究》,李文海主編:《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社會保障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13頁。其中“男丁人數相對較少(12.21%),女丁(43.72%)和幼孩(44.06%)占有絕對數量”。②丁芮:《北洋政府時期京師警察廳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2011年,第218頁。領粥的男性多有殘疾,少有強健者,婦女由于缺乏謀生的手段,更容易落入無以為繼的境地,需要接受救濟的數量遠多于男性。由此可見,每日的施粥維系著數十萬貧民的生計,粥廠作為一種長期穩定的救助方式,其作用無可替代。
二、收容所
1.育嬰堂
民國初期,隨著社會風氣的轉變和城市發展帶來的道德上的開放,棄嬰問題變得凸顯起來。加之舊有的育嬰堂設施陳舊、資金緊張、管理散漫,改造勢在必行。1917年,政府正式設立育嬰堂,經費主要來源于警察廳、市政公所、內務部和私人捐助。據1918年的財政報告顯示,官方的資助占 2/3,民間捐助達萬元以上,占1/3。③段正華:《近代中國兒童救助研究》,碩士學位論文,濟南:山東師范大學,2015年,第71頁。不過限于北京政府的財力,育嬰堂的經營一直處于入不敷出的狀態,直至南京國民政府接手后才有所好轉。京師新的育嬰堂既保留了傳統育嬰堂的特點,又采納較為科學的管理方式。依照管理條例,育嬰堂對0-3歲的嬰幼兒進行救助,一旦嬰兒被送入堂中,不具備撫養能力的父母不能將之領回。申請領養嬰兒的家庭要經過審核,領養后如出現虐待等情況,育嬰堂有權將嬰兒接回。在嬰兒的照料方面,育嬰堂采用傳統的寄養制與留養制相結合的方法,既節省了經費,也能促使乳婦對嬰兒產生感情后進而收養。育嬰堂也有不盡如人意之處,主要弊端是制度難以得到很好的實施,育嬰堂督查不力,出現嬰兒死亡而乳婦仍冒領工資的情況。④黃忠懷:《從育嬰堂到救濟院:民國時期傳統慈善事業的危機與轉型——以保定育嬰堂研究為中心》,《中國社會歷史評論》,2005年第1期。在日常管理中,北京的育嬰堂有明確的職能劃分,會計、文牘、庶務等各司其職,職責劃分清楚,體現了管理方式的進步。
2.養老院
京師的養老院是無依無靠老人的終老之所。甘博把西方慈善機構設立的機構稱為“養老院”,中國本土的機構(尤其是官方的)稱為“老人院”。甘雨胡同設有一所由外國教會組織、商業界人士籌款、外籍婦女管理的養老院,專門收容年老婦女,為她們提供較為穩定的食宿。每月的衣食總花費僅有2.10元,但是環境清潔衛生,管理也更為人性化。一些中國婦女借鑒甘雨胡同養老院的管理經驗,創辦了類似的老嫗院,有66名婦女得到養老救助。⑤(美)西德尼·D.甘博:《北京的社會調查》(上),陳愉秉等譯,北京:中國書店,2010年版,第330頁。與外籍人士創辦的“養老院”相比,老人院僅僅是維持老人生存的狀態,對其精神毫不關心,這也是中國慈善機構里的一項通病。
民國后大部分私人養老院被警方或政府接手,民間創辦養老院先經過政府審批,“大慈善家朱秀峰,現在聯合同志,集資在北城鼓樓苑地方,創辦養老院,專收年老無依貧民,已妥訂章程,呈請內務部立案,但不知能否批準”。⑥《立養老院》,《京話日報》1918年第2559期。官辦老人院需要警方推薦方能進入,也有通過“派人分赴各街市散發一種養老券”⑦《設貧民養老院》,《順天時報》1923年5月3日。的方式,使貧苦老人得以入院養老,生活條件要優于貧民救濟院,入院后就可以在老人院安度余生。⑧(美)西德尼·D.甘博:《北京的社會調查》(上),陳愉秉等譯,北京:中國書店,2010年版,第300頁。
3.瘋人院
瘋人院是收容精神病患者的機構。北京精神病患者數量較多,落后的社會觀念和醫療條件,使得這個群體的生存環境十分惡劣。許多精神病患者走失或者被遺棄后,面臨著嚴重的社會歧視,其身心受到的傷害往往更甚。
瘋人院設立始于20世紀初,建立瘋人院的目的,一是可以減輕家庭負擔,二是有利于社會穩定。民政部于1907年提議設立瘋人院,“大略以男女分為兩院,已諭令司員群議章程,不久即奏請實行矣”。①《議設瘋人院》,《順天時報》1907年10月。1908年瘋人院首設,1913年由警察廳接手管理。多數精神病人生活難以自理,病發時還可能傷害他人,對病人的核查須由警察廳負責,病人由駐地警察上報區警察署批準后住院治療,或者由家人、鄰里上報申請入院。《順天時報》載:“劉某向有瘋疾……乃于日前其瘋疾忽然大發,捉刀弄杖……其家屬畏其兇禍,遂告知巡警,許其拘至警廳。經官醫診治,確保瘋疾尚能醫治,故經警廳送派劉某入瘋人院醫治矣。”②《瘋人送院醫治》,《順天時報》1915年9月4日。1918年瘋人院搬遷新址,擴大了規模,條件也有所改善。隨著瘋人院的宣傳和人們認識的提高,增強了瘋人院的社會影響力,收養病人人數從1918年的32人③(美)西德尼·D.甘博:《北京的社會調查》(上),陳愉秉等譯,北京:中國書店,2010年版,第120頁。發展到1927年的100人以上④丁芮:《北洋政府時期京師警察廳研究》,博士學位論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2011年,第225頁。。雖然瘋人院救助的病人數量,比之全城應有之數量有很大差距,對病人的收管也更側重于有暴力傾向的病人,但作為全國第一批創立的精神病院,起到了開創性作用。
三、教養機構
1.兒童救助機構——以香山慈幼院為例
一般情況下,3歲以上的孩童不符合育嬰堂收養的要求,但這些兒童不具備獨立生存的能力。民國初期有許多民間的兒童救助機構,各方人士的籌款義舉也時常見諸報端。這一時期影響較大的私人孤兒院,往往都體現出明顯的“養”“教”結合的特點。創立于1912年的北京孤兒院原為收養烈士遺孤而設,后來擴大到收養孤兒和貧兒。龍泉孤兒院由龍泉寺的僧人主持,自清末以來,該院收養孤兒總計達3 000余名。⑤北京龍泉孤兒院編:《北京龍泉孤兒院報告書》,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04年版,第 5 頁。孤兒院除了收容兒童,還對其進行一定的文化和工藝教育,體現出明顯的人道主義關懷。1918年,一所基督教殘疾兒童養育院由教會學校的畢業生開設⑥(美)西德尼·D.甘博:《北京的社會調查(上)》,陳愉秉等譯,北京:中國書店,2010年版,第319頁。,屬于私人慈善事業,規模不大但象征京師地區關注殘疾兒童的觀念開始萌發。
北京政府救助兒童的機構以香山慈幼院最為著名。1917年直隸水災后,遺留下200余名兒童無人認領,負責督辦災情事務的熊希齡決定建立長效的救助機構對這些兒童進行教養。經過多方協商,1920年10月3日香山慈幼院正式開院,趙爾巽任董事會會長,熊希齡任香山慈幼院院長,參加開院大會的學生共700余人。香山慈幼院分男校和女校,基礎設施齊全,另開設圖書館、理化館等教育類場所,為兒童提供了較好的成長環境。“1922年下半年,熊決定男校增設中學部和中等職業部,學生接受工科教育。女校設師范部,訓練鄉村教育師資及培養本院蒙養園及小學之教師。”⑦李友唐:《北京香山慈幼院始末輯要》,《北京社會科學》,1994年第4期。除了較為完善的基礎教育,香山慈幼院還對進入大學深造的孩子進行資助,為離院的學生安排出路。在熊希齡的經營籌劃下,香山慈幼院并未出現經費短缺的困擾,并在20年代發展迅速,1930年在院人數達到1 670人,為慈幼院歷年所收兒童數目的峰值。⑧周秋光:《熊希齡與慈善教育事業》,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86頁。北京政府時的香山慈幼院經歷了最輝煌的時期,不僅完成了對兒童的“教養”,更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救助體系,代表了中國本土兒童救助的最高水平。
2.婦女救助機構——以濟良所為例
“濟良之意為凡在淪為下賤之人,濟之使得從良,而不致永陷于火坑水井也。”⑨《濟良所衍義》,《申報》1905年1月28日。北京濟良所1906年由外城巡警總廳督同紳商辦理,1907年重定章程,1913年1月由京師警察廳接管。⑩蔡恂:《北京警察沿革紀要》,北京:北京民社,1944年版,第54頁。搬遷后與京師的女習藝所和婦女感化所合并,成為綜合性的收容所。濟良所的人員構成復雜,有“誘拐抑勒來歷不明之妓女,被領家需索重價掯阻從良之妓女,被領家凌辱之妓女,不愿為娼之婦女,無宗可歸無親可給之婦女”①田濤、郭成偉整理:《清末北京城市管理法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452頁。被送到這里接受救助和監督。
濟良所的內部環境寬敞整潔,有縫紉工作的廠房,其他屋舍為傳統的四合院形制,另設有年齡較小女性所需的學堂,以及專為受救助婦女的孩子準備的房屋。婦女感化所所處位置偏僻封閉,內部環境臟亂,但管理上卻更為嚴格。除了待遇上的差別,被救助的婦女和感化所里的婦女在性質上是不同的,濟良所的婦女須結婚或被其親戚收留后方能離所,而感化所里被“關押”的婦女在刑期內無自由,在滿刑期后即可離開。②(美)西德尼·D.甘博:《北京的社會調查》(上),北京:中國書店,2010年版,第278頁。從成立之初,經費主要源于民間的籌集,政府雖有補助,但資金一直比較緊張。京師警察廳接手后,經費缺口由警察廳填補,以維持濟良所的正常運作。相關數據顯示,濟良所的年終總人數多時達到123人(1917年數據)。③孫高杰:《1902-1937北京的婦女救濟——以官方善業為研究中心》,博士學位論文,天津:南開大學,2012年,第123頁。濟良所的另一項資金來源來自于所內婦女的婚姻。婦女的照片會掛在陳列室內,甚至在大門外公開展示,有相中者就可以進入申請流程,男方需要有三家商鋪對其進行信譽擔保,禁止虐待、買賣女方,并且填寫涉及個人信息的申請表。警方核實無誤后,即可締結婚姻。男方需在喜結良緣之后向濟良所捐款,數額據男方對女方的滿意度捐付,一般來說在10元至200元不等。④(美)西德尼·D.甘博:《北京的社會調查》(上),陳愉秉等譯,北京:中國書店,2010年版,第279頁。濟良所為陷入不幸的婦女以新的選擇,體現了社會對婦女的關懷和人們觀念的進步。
3.貧民教養院
貧民教養院以收留、教化貧民為目的,屬于政府創辦的救助機構。教養院中“幼童大者十余歲,小者四五歲” “男女瘋人院等處”皆有,但凡貧民,不分男女老幼、是否殘疾,都可以進入貧民教養院。入院者既有自愿求助于教養院的,也有被警察強制帶入的。尤其冬季或出現自然災害之時,貧民和災民更需救助,除了原有的貧民教養院,還會另設災民教養院、兒童教養院等。
教養院內部設施簡陋,人滿為患。美國人甘博調查的一所教養院里,屋中九平方米的面積,由一層木板分隔為上下兩層,通常會住15人左右。如此逼仄的住所,即便在有人管理的情況下也難以維持房間的衛生狀況,特別在寒冷的冬晚,由于供暖不足,人們只能盡量把通風口封緊,致使屋內空氣無法流通。教養院給貧民提供衣食的救助,貧民的衣物很多是警察換下的舊衣,“所穿之衣服者,系巡警換下之舊制服,滌去泥污而改造者”,⑤《教養院參觀記》,《順天時報》1916年12月30日。這些破舊的衣服不足以御寒。貧民能得到的食物是小米粥和咸菜,大致是每人小米1斤,咸菜2盎司(50克)。⑥(美)西德尼·D.甘博:《北京的社會調查》(上),陳愉秉等譯,北京:中國書店,2010年版,第327頁。教養院內設有養病室安置病患,重病患者有單獨的屋子,但是由于衛生條件及醫療水平的有限,病人的死亡率較高。
貧民教養院具有了初步“教”的性質,教養院里的兒童“應對進退皆有秩序”,院內設授課室,聘請教員教課。其他有勞動能力者每天要出門勞動,勞動者每日得到5個銅板,但單純體力勞動無法使他們掌握可以謀生的技能。如果貧民選擇離開教養院,就不得不淪為乞丐。如果貧民無法謀生,可以回到教養院,但若有行乞之事,則不會再被收容。從貧民教養院的實際管理來看,教養院“教”的成分仍然較少。政府希望教養院起到指導貧民自立的作用,但從實施效果看,顯然難以從根本上解決貧民的困境,出院者禁止行乞的規定則更像一種警戒。
4.教養局
教養局主要為收容“輕刑”犯人所設立,目的側重于維護治安和施行教化,另附有教養貧民的職能。教養局收留的犯人來自各個階層,犯罪情節不算嚴重,刑期均不超過一年。其中有因虐待買賣濟良所領回的妻子的商人,有素行不良、行偷盜之事的乞丐,有因違反規定被送至教養局“以示懲戒”的巡警等。⑦《巡警送教養局》,《順天時報》1917年10月30日。也有一些人是被家人送入教養局的,多因家中無法管教,希望教養局能代為約束管制。男性貧民、災民也可以進入教養局,但需經警察核實情況,符合貧困的標準方可入局。局內的工作有“搓繩子、剪裁、木工活、鐵匠活和紡織”⑧(美)西德尼·D.甘博:《北京的社會調查》(上),陳愉秉等譯,北京:中國書店,2010年版,第314頁。,這些勞動有些在專門的工棚進行,有些在露天進行。犯人和貧民在一起勞動,衣食由教養局提供,但是他們拿不到報酬,還需要戴著腳鐐。每周日允許貧民出門放松,而犯人不享受這項權利。貧民和犯人是分開住宿,居住擁擠不堪且衛生條件極差。即便如此,教養局提供的幫助對身處于困境中貧民仍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根據1927年3月警察廳統計數據,教養局每日人數在180人左右,成為京師社會救助事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5.游民習藝所
北京政府時期京城里開辦有不同類型的習藝所,有為女童所建的女童習藝所(屬私人慈善機構,所內女童40人左右,主要學習刺繡),有為囚犯所建的監獄習藝所,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游民習藝所。游民習藝所最早由清政府的刑部設立,北京政府時期先由內務部負責,1917年轉由警察廳接管。①(美)西德尼·D.甘博:《北京的社會調查》(上),陳愉秉等譯,北京:中國書店,2010年版,第314頁。游民習藝所僅招收8歲以上的男童和年輕男性,并為入所人員提供食宿。
《順天時報》曾對游民習藝所進行過詳細的介紹,內容包含生活環境、教授課程、管理制度等。習藝所的宿舍為“X”字形,共分四間,每鋪都有規定名額,可容納700人生活。房間內部注意通風,床鋪、地面清潔。所內浴室、理發室、病房、操場等基礎設施一應俱全。所內人員“每周洗一次澡,每十天剃一次頭,吃飯時有一定的開水供應”,主要食物是咸菜、菜湯和小米粥,每人每月的伙食費平均為2元。②(美)西德尼·D.甘博:《北京的社會調查》(上),陳愉秉等譯,北京:中國書店,2010年版,第318頁。游藝所的課業“等于普通小課程度,有圖文、修身、國書、算數、手工、體操、歌唱等科目”,工徒每日還要做工,有木工、制肥皂、織布等項目。這些工徒制品“名目繁多,各種皆有”,在國貨市場上也占有一定份額,是游藝所收入的重要補充。18歲后工徒可以離所另謀職業,或由警察為他們尋找一份工作,也可繼續由游藝所雇傭。甘博在評價游民習藝所時,指出習藝所存在預防時疫的不足和娛樂項目的匱乏等弊端,影響青少年的教養效果。
晚清到近代最重要的轉變時期就是北京政府階段,這一階段不僅有社會的激烈變化,各種自然災害也頻頻來襲,對社會救助的需求急劇增加。上述原因促進了北京政府時期社會救助事業的快速發展,政府既延續了舊有的社會救濟制度和機構,也有所創新發展,新變化體現在新的管理模式和新開設的機構上(如濟良所等);民間的社會救助事業更加繁盛,救助方式和機構的設置更加靈活多樣,可謂百花齊放。在內憂外患的政治局面下,政府作為社會救助的最大主體,對社會救助事業與其應盡的職責雖然有較大差距,但其社會救助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在惡劣的自然環境和動蕩的社會環境下,切實救助了數量眾多的底層人民。社會救助事業緩和了社會矛盾,維護了社會穩定,為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社會救助事業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