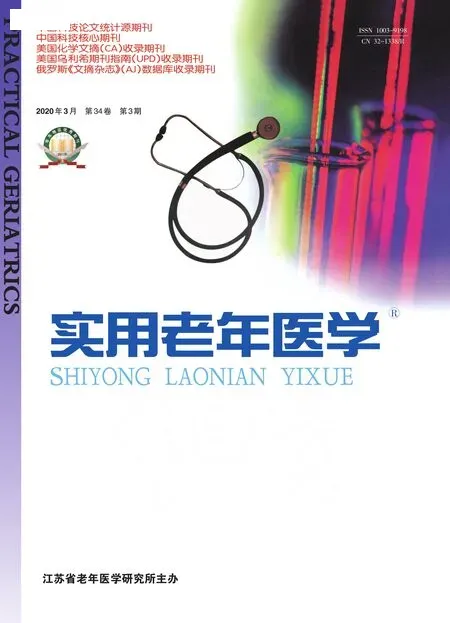1 例副腫瘤小腦變性病例回顧及文獻學習
丁晨云 雷運貴
作者單位:212300 江蘇省鎮江市,丹陽市中醫院腦病科
1 病歷資料
病人男性,64 歲,因“左肢不利2 月,右肢不利10 d”于2017-01-29 入院。 病人2016-11-24 突發左手端碗不穩,于市人民醫院查頭顱MRI 陰性,考慮缺血性腦血管病,予以抗PLT 聚集等治療,癥狀好轉,2016-12-04 出現左下肢活動不利,言語欠清,復查頭顱MRI陰性,仍予以抗PLT 等治療,癥狀緩解。 2017-01-28 癥狀加重,并出現右肢乏力,行走不穩,飲水嗆咳,遂至我院進一步住院檢查。 發病前病人無感染史,平素無寵物飼養史,家族中無類似病史。
既往有高血壓病史,否認DM、心臟病病史,否認肝炎、結核等傳染病史,有輸血史,無外傷及中毒史,否認藥物和食物過敏史,否認冶游及性病史,少量煙酒史。
入院神經系統查體:神清,精神稍萎,記憶力、計算力、定向力正常,吟詩樣語言,雙瞳孔等大等圓,直徑3.0 mm,光敏,無眼震,雙側鼻唇溝對稱,伸舌居中,聽力正常,懸雍垂稍左偏,軟腭上抬可,咽反射遲鈍,四肢肌力5 級,四肢肌張力偏低,腱反射(++),左側偏身痛覺減退,雙側巴氏征(-),雙側霍夫曼征(-)。 雙側指鼻試驗及跟膝脛試驗均(+),閉目難立征(+),寬基步態,腦膜刺激征(-)。
輔助檢查:血常規、生化、凝血常規、甲狀腺功能、乙肝兩對半,HIV 抗體、梅毒抗體、男性腫瘤標志物均正常。 腦脊液壓力、常規、生化、細菌培養均正常。 上腹部B 超示:肝囊腫;膽囊息肉樣變。 胸部CT:(1)兩肺炎性變;(2)肝囊腫可能。 頭顱MRI+MRA 無特殊。
入院后經初步分析,病人老年男性,亞急性病程,以雙側共濟失調伴延髓受損為特征,定位雙側小腦、延髓病變,定性考慮變性病可能。 2017-02-04 轉外地某醫院住院,復查腦脊液常規、生化正常。 免疫學檢查:IgG 為26.4 mg/L,IgM 為0.3 mg/L,IgA 2.1 mg/L。頭顱MRI 平掃+增強:兩側基底節區、兩側額葉少許腔隙灶;兩側頸動脈鞘旁淋巴結稍腫大。 根據病史及檢查結果,排除了腦卒中、顱內腫瘤、中樞感染、中毒,及遺傳性、酒精性共濟失調等病因,遂臨床診斷為亞急性小腦變性;予以甲強龍沖擊治療后好轉,并囑定期復查腫瘤指標。 2 個月后病人激素減量,再次出現共濟失調,于2017-06-29 入我院,神經系統查體:神清,語言不清,記憶力、計算力、定向力正常,雙瞳孔等大等圓,直徑3.0 mm,光敏,無眼震,雙側鼻唇溝對稱,伸舌居中,聽力正常,懸雍垂稍左偏,軟腭上抬可,咽反射遲鈍,左側肌力5 級-,右側肌力5 級,雙側肌張力減低,感覺、腱反射正常,病理征(-),雙側共濟減退,閉目難立征(+)。 肝臟轉氨酶升高>10 倍;腫瘤標志物癌胚抗原(CEA)、糖類抗原(CA)199、神經元特異性烯醇化酶(NSE)、細胞角蛋白19 片段(CYFRA21-1)、鐵蛋白(FERR)均升高>10 倍,總前列腺特異性抗原(TPSA)、游離前列腺特異性抗原(FPSA)、甲胎蛋白(AFP)、CA125 正常。 胸部CT+上腹部CT 示:(1)左肺門占位,兩肺散在少許炎性變,縱膈淋巴結稍增大;(2)第2胸椎左側及右側部分肋骨髓腔內局限性密度增高;(3)肝內多發低密度灶;(4)脾區類圓形軟組織密度影。 診 斷: 肺 癌 多 發 轉 移, 副 腫 瘤 綜 合 征(paraneoplastic neurological syndromes, PNS)。 2017-07-22 病人死亡。
2 討論
自身免疫性腦炎從廣義上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經典的副腫瘤性疾病,另一類是抗神經元自身抗體相關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狹義的自身免疫性腦炎(AE)]。兩者的靶抗原有異,前者為神經元細胞內抗原,通過細胞免疫反應引起不可逆的神經元損害,對免疫治療效果差[1];后者為抗神經元表面受體或突觸蛋白,通過體液免疫反應,引起相對可逆性的神經元功能障礙,對免疫治療效果好[2]。
副腫瘤性小腦變性(paraneoplastic cerebellar degeneration,PCD)也稱亞急性小腦變性,是累及中樞神經系統最多見的PNS,可以并發各種惡性腫瘤。 近年研究發現,其病理機制是機體產生抗體對原發腫瘤的免疫應答,從而產生小腦變性[3]。 病理組織學特征是小腦皮質彌漫性變性,蒲肯野細胞大量減少,炎性細胞浸潤不明顯[4]。 臨床多見于成年人,病情進行性加重,多數在發現腫瘤之前有神經系統癥狀體征,主要表現為小腦受累,部分累及腦干,少數有情感、智能或精神障礙。 目前臨床發現的副腫瘤抗體如抗Hu 抗體、抗Yo 抗體等,可用于早期腫瘤診斷及預后判斷,但副腫瘤抗體與腫瘤的臨床表現及種類并非對應關系[5]。另外有文獻研究了18F-脫氧葡萄糖(FDG)PET 全身顯像,其能夠較準確的診斷PNS,有助于及早發現潛在的惡性腫瘤[6]。
臨床上,基層臨床醫師對副腫瘤性疾病的誤診遲診不在少數。 燕蘭云等[7]曾報道1 例先后誤診為Mille-Fisher 綜合征和Wernicke 腦病的亞急性小腦炎。本例病人首發表現為卒中樣癥狀而被誤診為缺血性腦血管病,2 個月后病情加重,臨床診斷為亞急性小腦變性,7 個月后發現原發腫瘤灶。 回顧分析,病人亞急性起病,以共濟失調及延髓癥狀為主,2 次頭顱MRI 均無特殊,不支持血管病;無感染史、中毒史、家族遺傳史、飲酒過量史,傳染病指標陰性,腦脊液檢查陰性,可排除中樞感染、中毒、遺傳性、酒精性共濟失調病因。 頭顱MRI 未發現占位性病變,腫瘤指標正常,排除顱內腫瘤及轉移瘤。 定性考慮變性疾病,鑒別診斷還需考慮以下疾病。
(1)橄欖腦橋小腦萎縮(OPCA):OPCA 是以腦橋及小腦萎縮為病理特點,以小腦性共濟失調為特征的進行性變性疾病。 多于50 歲左右起病,散發型多見,男女均可患病,進展緩慢,平均病程5 ~6 年,除小腦損害外,可有多系統受累,如PD 綜合征、錐體束征、自主神經損害。 CT 或MRI 顯示小腦和腦干萎縮。 MRI 腦干十字征分6 期,早期可正常或表現為腦橋淺縱線,晚期方可見十字征[8]。 本例病人病程短,病情進展較快,頭顱MRI 顯示小腦及腦干均萎縮不明顯,OPCA 證據支持不足。
(2)Bingswanger 病(BD):表現為大腦半球白質彌漫性脫髓鞘性病理改變,是以慢性高血壓、皮質下白質變性、癡呆等為特征的綜合征。 臨床表現多樣,可以表現為共濟失調、球麻痹、尿失禁、癡呆、精神行為異常等。 典型的影像表現為腦萎縮、白質疏松和腔隙性腦梗死。 本例病人有高血壓病史,但頭顱MRI 無半卵圓中心及腦室旁深部白質的異常信號,可排除。
通過本案回顧學習,因此類疾病早期易誤診漏診,提示我們對考慮診斷為PCD 的病人需保持警戒心,定期復查腫瘤指標,盡可能檢查特異性自身免疫性抗體及行PET 檢查,以盡早發現原發腫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