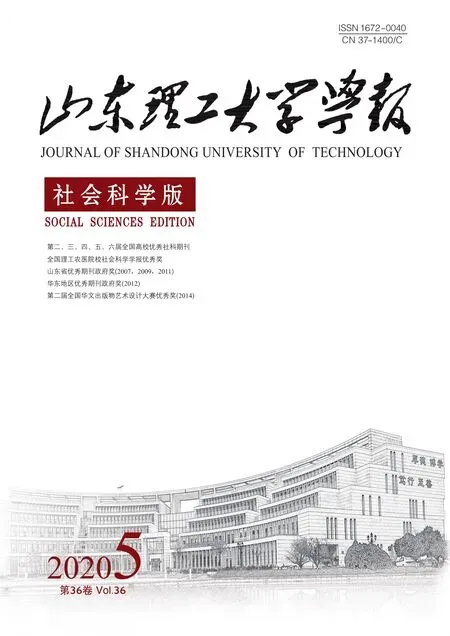高密年畫的歷史與傳承研究
——以“順興齊記”年畫坊為例
趙 娜
年畫是中國民間藝術形式的典型代表之一,高密年畫是傳統年畫的重要分支。考察高密年畫這一傳統非物質文化遺產,有助于我國傳統文化形象以及文化遺產保護等各方面工作的開展。本文考察高密年畫,目的在于為后來的研究者提供前期研究基礎。總體看,通過對高密年畫的歷史淵源、發展形式和傳承現狀進行考察,一方面可以促進人們對于高密年畫的了解,有助于其發掘與保護;另一方面又可以透過高密年畫對整個民間年畫的現狀“窺一斑而見全豹”,為了解中國傳統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現狀提供一份微觀調研報告,展現當前高密年畫等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傳承上的問題與機遇。
一、高密年畫的歷史淵源
年畫根植于廣大民間,題材豐富,內容詼諧,是我國民間文化發展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從歷史淵源看,年畫的起源至少在北宋時期就已經出現端倪,一種類似于年畫的民間美術形式被稱為“紙畫”。宋代文人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中就有關于“紙畫”的記載,展現了當時家家戶戶貼紙畫的熱鬧場景,“相對梁家珠子鋪馀皆賣時興紙畫,花果鋪……”[1]。雖然這種藝術形式主要流行于民間,但向來傳承有序,并在歷代的文人記述中多有體現。如明代劉若愚在《酌中志》也有一段相關記載:“冬至后,室內多掛《綿羊引子》畫帖,司禮監刷印《九九消寒圖》。”[2]可以推斷明代稱年畫為 “畫貼”。清朝道光年間,文人李光庭在《鄉言解頤》一書中寫道:“掃舍之后,便貼年畫,稚子之戲耳。”[3]年畫由此定名。作為民間藝術形式之一,年畫不僅十分具有代表性,而且歷史悠久,可以作為一種典型的研究對象來探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流傳與保護。
高密縣歷史悠久,并在歷史積累中形成了豐厚的人文傳統和民間藝術表達。高密縣古稱夷維,屬萊國。“《水經注》應劭曰:縣有密水,故有高密之名……密水入濰。維以兼密通稱……蓋自其源言之謂之高”[4]。在這樣的記錄當中,我們可以很清晰地了解高密縣名稱的來源及其悠久的歷史。高密年畫的起源與高密縣的歷史相比似乎要晚很多。事實上,作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的高密年畫,其起源可以上推到清代康熙年間。在清代康熙年間,高密年畫就已經成為當地老百姓日常生活尤其是在節慶日當中不可或缺的一種歡慶形式。這種現象十分容易理解,因為明清兩代物質文化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平民階層開始擁有審美的權利,并且在生活中也獲得了一些如年畫這樣的藝術品。人們對于審美或生活的樂趣開始有了追求。在這種情況下,高密年畫能夠興盛起來,也是整個社會物質文化發展的表現。
高密年畫的歷史發展中存在著諸多階段,尤其近現代以來,雖然民間藝術擁有極強的生命力和延續性,但是特定時期的國家意識形態往往也可以左右民間藝術的發展,如年畫這樣與日常大眾的生活息息相關的藝術形式也被用來進行社會審美趣味的塑造。新中國成立以后百廢待興,需要向大眾宣傳一種積極昂揚的生活奮斗精神,表達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在這樣的背景下,年畫作為與大眾生活息息相關的藝術形式,最容易深入到千家萬戶,起到廣泛的宣傳作用。如此,年畫的內容就開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從古代的才子、佳人、觀音轉換到現代的工人、婦女等題材,實現了一種社會風尚和審美趣味的轉換。
當前在全球化背景下,中華傳統文化成為了我們塑造國家文化形象的重要資源。以傳統年畫為代表的民間藝術重新登上了歷史舞臺,被人們所關注和保護。在這樣的情況下,探討和分析高密年畫的歷史淵源、發展現狀就更有深遠的意義。這不僅是對于高密年畫這種藝術形式的發掘和保護,也是基于一種國家文化形象的宏大敘事目的的學術行為。當然,對于傳統民間藝術形式的挖掘和保護不能僅僅停留在對它的背景和歷史淵源的考察上,還要以動態的視角去觀察它所形成的發展形式,以及這些發展形式在之后的興起與泯滅情況。就本文而言,我們不僅要考察高密年畫的歷史淵源,還要從具體的發展形式入手,考察高密年畫在悠久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獨特表現形式。就高密年畫而言,其先后產生了三種發展形式,并形成不同的發展和結局。
二、高密年畫的表現形式
如上文所言,同其他的民間年畫一樣,高密年畫的發展歷史同樣較為悠久,并在此過程中產生了不同的展示形式,比如撲灰年畫、半印半畫、木版年畫。其中,撲灰年畫是高密年畫中發源最早的表現形式。撲灰年畫,顧名思義,就是以灰為主要創作原料的一種年畫類型,在用灰進行大面積的鋪設以后,可以運用毛筆和其他工具進行細節的勾勒和填充。從目前掌握的文獻資料來看,撲灰年畫具體何時生成已經無從考證。從古代藝術文化的發展特點來看,古代文獻中沒有關于它的完整記載是有其特定原因的。因為在古代文人藝術占據了絕對的權威地位,年畫這樣的民間藝術是不入流的,因此沒有被文獻記載也在情理之中。雖然高密縣歷史悠久,而且歷史文化資源非常深厚,但卻沒有文獻去對民間藝術進行專門整理,也沒有文獻記錄撲灰年畫的誕生時期。今天看來,雖然在康熙時期就已經有關于高密縣在過年的時候更換門神的記載,但是其中并沒有提及更換的是撲灰年畫還是其他的年畫形式。《濰坊文化志》中有關于高密撲灰年畫誕生地點的零星記載。該書記載,高密撲灰年畫最早產于大欄鄉公婆廟和夏莊鎮沙嶺子等村,撲灰年畫的前身為手繪年畫。明代民間文人畫、廟宇壁畫的表現方法和繪制技巧給撲灰年畫的形成以很大啟示,傳至清乾隆年間為淡彩撲灰年畫,道光年間由于天津楊柳青年畫傳入,加上受到楊家埠木版年畫的影響,高密撲灰年畫逐漸形成兩大派系,即墨屏和大色畫。同時在工具和技術上也有改進,形成半印半畫年畫,與木版年畫三者并存[5]。
高密年畫的第二種形式是半印半畫。從表現技法來看,它和撲灰年畫有相似之處,即都是采用了印和畫兩種手法。事實上,它極有可能就是從撲灰年畫的形式發展而來的,是撲灰年畫的細化和升華。可以說,它是在撲灰年畫的基礎上,吸收了天津楊柳青和濰坊楊家埠民間年畫的刻印技術,又加上了自己的創造,從而形成一種迥異于前三者的獨特藝術形式。具體而言,它通過對于木刻技術的引入,改變了原來以灰為線條的主要塑造形式,采用木版線條作為輪廓,又加上了綠和橘黃兩種套色版,所以在工藝方面更進一步。其實,它的用色遠非前兩種如此簡單,另外還包括粉色、大紅色、全青色等一些色相十分純凈的顏色,最后在局部重點部位涂上明油即成。從效益的角度看,雖然它的效果比撲灰年畫更加豐富,層次更多,但是它的工藝技法卻比撲灰年畫更簡單,縮短了工藝流程,在經濟效益方面也有所提升。如上文所言,明清兩代是物質文化蓬勃發展的時期,面對著需求量劇增的市場,高密年畫作為一種面向大眾的商品,必然要考慮到經濟成本和工藝流程。因此,半印半畫是一種應時而做的產物。當然,這種發展并不十分徹底,事實上,在此后不久,高密年畫就開始脫離“繪制”的繁瑣制作流程,而采用全部的木版印制,這也就是持續到今天的高密木版年畫。由此可見,撲灰年畫以及半印半畫形式之所以變得沒落,很大原因就是因為工藝繁瑣、經濟效益低等缺點而不能適應市場競爭。
高密木版年畫是高密年畫的第三種形式,也是最新的一種形式。這種形式同樣起源于清朝(1)清朝末年,北村“同順堂” “萬聚”“齊萬順”等畫子店為了提高經濟效益,努力提高年畫技藝,在撲灰年畫、半印半畫的基礎上,又發展了全色套印方法,即木版年畫。參見:高密縣政協文史資料編撰委員會編《高密文史資料》(第九輯)。。如上文所言,為了提高經濟效益,木版年畫成為脫胎于撲灰年畫和半印半畫的年畫形式。在今天,我們可以看到高密木版年畫的制版技術十分精湛,其用力粗獷,線條挺拔簡練,展現出與楊家埠年畫明顯不同的藝術風格,具有典型的北方特色。它對于形體的表現并不如撲灰年畫和半印半畫那么精細,但是卻充滿力量感和張力。在題材上也始終圍繞著山東民間文化以及民間風俗故事進行刻畫,在形式和內容上是獨樹一幟的,比如老鼠娶親、老鼠嫁女,還有桌圍、灶馬、窗頂、窗旁、門神、增福財神、“黃財神”(不上顏色的財神)等。由此高密木版年畫也在全國木版年畫領域具有了一定的地位。為了年畫經營,年畫藝人們用盡各種辦法推進木版年畫的繁榮昌盛。為了打破地域界限,擴大年畫市場,一些高密年畫藝人曾到膠縣方子街賣年畫。隨后,嶗山沙子口、日照、東北等地也迎來了“順德永”“瑞盛和”“瑞盛祥”等作坊的年畫藝人推銷他們的年畫。這一時期,琳瑯滿目的木版年畫,走進了千家萬戶。這也可以算是年畫商業模式的最初雛形。
當前,高密木版年畫的制作已經成為當地重要的經濟來源之一,并且成為了當地的文化名片。作為重要的副業之一,它不僅為當地民眾提供了就業機會和經濟效益,而且逐漸成為了高密甚至山東的重要民俗文化資源。今天,高密年畫作坊遍布全縣三十多個村莊。一些民間藝人利用農閑的時間進行刻版、印版以及售賣,形成了“村村作畫,戶戶作坊”的景象。這種蓬勃的發展現狀不是一種偶然現象,它與當前大力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塑造國家文化形象有很大關系。同時,高密木版年畫的傳承與發展也與經濟活動緊密相連。換句話說,從目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角度講,只有當它成為一種商品,在社會上有固定的受眾群體和固定的經濟收入,才能維護其生存地位,并形成一定的社會影響,最終達到保護物質文化的作用。因此,我們不僅要考察高密年畫的表現形式,還應該將視線落腳在當前的傳承現狀上,討論其目前的發展機遇和傳承問題。
三、高密年畫的傳承現狀
當我們探討高密年畫的傳承現狀和發展問題時,不可避免地遇到當前傳統非物質文化發展的一個悖論:一方面,隨著近年來商品經濟和消費文化的沖擊,傳統非物質文化遺產開始逐漸被擠出主流的消費市場,被一些快餐式的、碎片化、無深度的現代商品所補位,填充了消費者的頭腦,讓人們無暇顧及在此之外的東西。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或者說后現代主義的文化語境中,同質化現象發生在社會的方方面面,尤其是文化的同質化成為當前各國必須考慮的一個嚴峻問題。在網絡化、全球化的消費與競爭語境中,整個地球變成了觸手可及的空間,人們對于各種文化信手拈來,各種文化也在此過程當中實現轉換和吸收,最終越來越趨同化,喪失自身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形象。因此,為了維護自身的文化地位,建構國家文化形象,我們又必須去關注那些被遺落在視野之外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可以說,傳統非物質文化是塑造當前文化形象的重要資源之一。這種悖論是當前民間藝術不得不面臨的一個窘境。從年畫的角度看,前者導致年畫在社會的快速發展和商品經濟的猛烈沖擊下,受到了沉重的打擊,經濟效益逐漸下降,真正從事該行業的藝人和傳承者越來越少。后者表明民間木版年畫并沒有到窮途末路的境地,反而面臨著一個不可多得的時代機遇。國家的宏觀提倡和時代需求決定了木版年畫將會重新崛起,重新回到人們的消費視野和審美視野之中。在此,我們以高密的“順興齊記”年畫作坊為例,討論當前高密年畫的傳承現狀和時代機遇。
“順興齊記”是高密夏莊鎮年畫藝人齊傳新經營的一家年畫作坊。我們在高密的調研中得到如下資料:“順興齊記”創立于清朝末年,是齊傳新的曾祖父齊記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后來被很好地傳承下來。這是一個家庭作坊式的年畫作坊,齊傳新16歲時就開始了他的學徒生涯,跟著木版年畫師傅學習木版年畫工藝,在木版年畫制作方面他非常有天分,也非常勤奮。他在18歲那年學成出徒,學會了一整套年畫制作工藝(勾線稿、刻線版、印制年畫、裝裱等)。齊傳新從事木版年畫手藝幾十年來,創作了大量作品,每一時期的作品各有特點。早期線版作品有《岳飛傳》《清史演義》等,作品運用西洋繪畫中的焦點透視、近大遠小、明暗畫法,具有強烈的視覺沖擊力。中期線版作品有《水滸》《西游記》《三國人物》等,作品在人物造型方面,身長較短,多夸大主要人物頭部,突出主體形象,使主體形象占滿整個畫面,給人穩健之感。晚期線版作品有《鏡花緣》《石頭記》《東周列國》等。作品人物精神飽滿,表情安定、祥和;人物臉部刻畫較為細致,突出面部特征。近年來齊傳新為蘇州、北京、新疆、東北等地刻畫了大量的人物畫版,成為遠近聞名的刻版大師,作品銷往全國各地及海外。訂購齊傳新線版作品的一般都是北京、天津、東北的客戶,據了解,這些客戶先以低價買走這些木版年畫的線版,再到藝術市場或者其他途徑以高價賣出,這些線版主要為收藏用。
據筆者調查,現在愿意學習木版年畫制作的人越來越少,高密的木版年畫傳承人已經寥寥無幾,家庭傳承中也出現了“斷層”現象。令人驚喜的是,齊傳新的木版年畫手藝得到了傳承。在高密,木版年畫與其他傳統手工藝一樣也有著“傳男不傳女”的說法。齊傳新有三個孩子,老大老二是女兒,老三是兒子。齊傳新的兒子從小跟隨父親學刻版,現已成家。齊傳新的兒子兒媳都跟隨父親學會了刻版,齊傳新兒子的線版作品《麻姑獻壽》曾經獲得重慶民間藝術展一等獎。除此之外,齊傳新還帶了幾個徒弟,現在都已經出師。
新世紀以來,隨著我國對傳統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挖掘與保護,一些以往沒有被發現的優秀文化遺產開始展現在人們面前。高密年畫歷史悠久、傳承有序,是我國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本文以“順興齊記”為例,對高密年畫的歷史淵源、發展形式與傳承現狀進行探析,希望以此能夠增進人們對于高密年畫的了解,為相關學術共同體的探討提供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