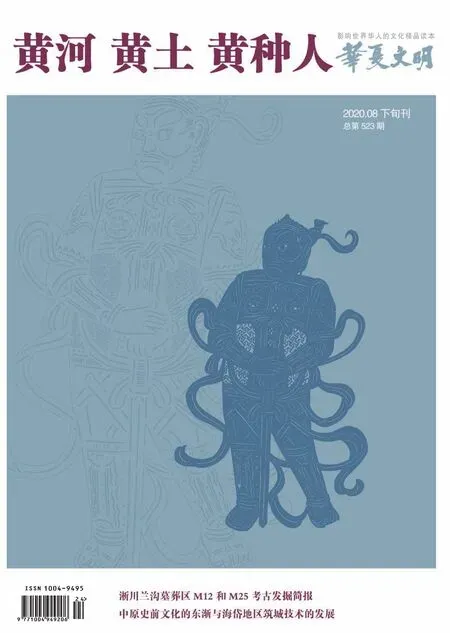中原史前文化的東漸與海岱地區筑城技術的發展
曹凌子 郭崇文
截至2020 年年初,中國境內已發現史前有垣城邑逾百座,主要分布于北方、中原、海岱、巴蜀、江漢、太湖等六大史前文化區。 其中,中原、海岱兩區經由考古工作證實的史前城邑數量較多,規劃布局、筑城技術等因素呈現出多樣化、復雜化,甚至一定程度先進性①這里所謂“先進性”是相對而言,畢竟“北方模式”“南方模式”城邑所處宏觀自然環境、微觀自然環境與“中原模式”城邑存在差異。的態勢, 已有學者對史前城邑筑城技術給予過不同程度或不同類別的專題關注[1]。 然而,就已刊文獻而言,從文化交流、文化因素傳播視角專門考量中原地區先民對海岱地區先民史前筑城技術影響的探討為數偏少。 作為史前社會復雜化與早期文明化進程中重要的物化載體之一, 圍垣城邑及其建筑技術的相關研究有進一步深化的必要。 有鑒于此,我們擬從中原地區史前文化因素東漸的視角對這兩大文化區圍垣城邑乃至其他相關問題略陳管見,不當之處,懇請方家批評、指正。
一、中原與海岱地區史前圍垣城址筑城技術概覽
就已有考古發現來看, 中原地區史前圍垣城邑計15 處共16 座, 其中屬于仰韶時代后期仰韶文化大河村類型、下王崗類型的有2處,分別為鄭州西山[2]、淅川龍山崗[3];屬于龍山時代后期陶寺文化的有山西襄汾陶寺早期城、陶寺中期城[4],王灣三期文化的有博愛西金城[5]、溫縣徐堡[6]、登封王城崗[7]、新密古城寨[8]、新密新砦[9]、平頂山蒲城店[10]、郾城郝家臺[11],后崗二期文化的有河南濮陽戚城[12]、濮陽高城[13]、安陽后崗[14]、輝縣孟莊[15],造律臺文化的有淮陽平糧臺[16],合計13 處14 座。 也有學者曾將新鄭人和寨聚落視作龍山時代城邑組成[17],但限于材料公開程度,所出器物指向的該城邑年代與新砦文化的關聯似乎并不能排除,故本文暫未將該城列入其中。
海岱地區史前圍垣城邑有25 處26 座,其中屬于或可能屬于龍山時代前期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有5 處,分別為山東濟南焦家[18]、滕州西康留[19]、五蓮丹土[20]、日照堯王城[21],安徽固鎮垓下[22];屬于龍山時代后期海岱龍山文化時期的有20 處共21 座, 分別為山東陽谷景陽崗[23]、茌平教場鋪[24]、陽谷王家莊、陽谷皇姑冢、茌平尚莊、茌平樂平鋪、茌平大尉、東阿王集[25]、東阿前趙[26]、濟南城子崖[27]、鄒平丁公[28]、淄博桐林[29]、壽光邊線王[30]、五蓮丹土龍山早期城、五蓮丹土龍山中期城、日照兩城鎮[31]、日照堯王城、費縣防故城[32]、沂源東安故城[33]、滕州莊里西[34],江蘇連云港藤花落[35]。 其中個別城邑年代或許更早, 如地處魯北地區的焦家被認為可能始建于仰韶時代后期的大汶口文化中期后段。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遺址之中,以教場鋪聚落為代表的魯西北幾處聚落作為城邑的可能性在考古學界尚存歧見①承認或否定景陽崗以外魯西北地區上述聚落為城的學者兼而有之,此處僅以張學海、孫波先生觀點為例引用。,[36],本文雖暫從其屬于城邑的舊識, 但也認為其性質究竟如何仍需留待將來更為深入、 系統的考古證據加以驗證。 此外,新近發現的滕州西孟莊遺址海岱龍山文化小型圍墻[37]的發現,似乎為該區史前聚落考古探研提供了新證, 但從現階段材料來看, 其作為城的可能性似乎還很難得到學界公認。
除上述存在墻垣的城邑外, 這兩大文化區都存在一定數量的環壕聚落。 據不完全統計,單以龍山時代環壕為例,中原地區如鄭州大河村、禹州瓦店、汝州煤山、舞鋼大杜莊、方城平高臺、 信陽孫寨等, 海岱地區如招遠老店、平度逄家莊、青島南營、日照蘇家村、日照大桃園、臨朐西朱封、桓臺李寨、桓臺后埠等,可能在當時社會中發揮著高于普通聚落的作用。 早于龍山時代的仰韶時代環壕聚落乃至裴李崗時代環壕聚落在當時聚落群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許也與不存在相關圈圍設施的聚落有差異。 筆者并不否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贊同環壕聚落作為城邑的可能性與合理性,并認為同時存在環壕及圍垣的城邑建筑技術有綜合審視的必要, 但由于這些僅存環壕設施的聚落不存在城垣這種可以作為地方特色標志的物化載體,在討論筑城技術時,本文暫予擱置, 單取城垣為證說之。 待將來條件成熟時,或可另文專論環壕相關議題。
就筑城技術視角而言,城壕、城門及其他相關附屬設施系這兩區乃至其他文化區共有之現象, 存在特殊性、 區域性的可能相對較小,而墻基的處理方式、城垣主體的建筑方式則可在一定程度上作為區域文化因素來看待和比對分析。
在墻基處理方式上, 中原地區存在基槽的城址有西山、陶寺早期城、陶寺中期城、王城崗、新砦、古城寨、郝家臺、孟莊等,平地起建城相對較少,所占比重相對較低;另有兩三處城垣,囿于材料公布程度,雖暫不詳知其是否存在基槽等設施, 但其作為基槽城的可能性尚不能被輕易排除; 海岱地區除藤花落可能存在基槽外, 其余城址皆為平地起建[38]。就城垣主體的建筑技術來看,中原地區版筑城有西山、陶寺早期城、陶寺中期城、王城崗、古城寨、郝家臺、平糧臺、戚城、孟莊,夯筑城有龍山崗、徐堡、新砦(不排除存在版筑因素的可能)、蒲城店、高城、后崗,堆筑抑或“拍筑”城有西金城,版筑比例最高,夯筑次之,僅使用堆筑一種技術的罕見;在既往材料中,海岱地區較為明確的版筑城僅景陽崗、藤花落2 處,莊里西可能存在版筑技術因素;近年新發掘的焦家城也存在版筑證據,可能使用夯筑技術的城有城子崖等幾處,余者皆為堆筑城,堆筑城比例最高,夯筑城次之,版筑城占比最低。
綜上,中原、海岱二區皆為土城,因其在城墻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相似性而被合稱為史前城邑的“中原模式”[39]。 與長江流域等區的史前城垣相較, 中原與海岱地區的建筑技術在某些方面可能更為復雜, 是先民基于當地既有自然環境的文化適應策略,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當時相關文化區內部先進生產力的代表。 總的來看,兩區都存在堆筑、夯筑及版筑城垣,但與海岱地區相較,中原地區多為基槽式城垣, 版筑—夯筑的復雜技術使用率高。 在上述筑城技術統計分析的基礎上,新近有學者認為, 以狹義中原地區為代表的這種最復雜、 可能更為先進的筑城技術可稱為“中原模式”下的“河洛亞模式”,海岱地區這種次復雜、 可能也具有一定進步性因素的筑城技術則被稱作“中原模式”下的“海岱亞模式”[40]。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不同文化區之間筑城技術的差異性除來自文化與社會的原因外,更重要的影響因素可能仍在于自然環境。長江流域諸文化區、 北方文化區土壤等自然資源與“河洛亞模式” 所指向的狹義中原地區、“海岱亞模式” 所代表的海岱地區的確存在顯著差異。 即便中原、海岱二區之間的土壤等一系列自然因素也存在差異。
二、史前時期中原文化東漸與海岱文化西進的大勢掃描
作為中國史前黃淮流域的兩大文化區,中原與海岱地區地理位置相近、 生態環境相似, 至遲自裴李崗時代起已開始文化間的交流與融合。 就狹義的史前階段(下限在龍山時代,廣義的“史前”或可包括二里頭時代)來看,這種雙向的交流到仰韶時代顯著增多,龍山時代延續并進一步發展了仰韶時代中期以來的強化交流態勢。 在相當的程度上可以認為, 中原文明的最終形成離不開海岱地區史前文化的貢獻, 海岱地區早期文明中也不乏中原地區史前文化的因素。 鑒于諸多考古學研究者曾對黃淮流域這兩區史前文化的交流做過考古學視域下的文化因素分析考察,既有研究已然鞭辟入里,在中原、海岱兩大史前文化區交往聯絡大勢已漸趨清晰的學術背景下, 可能即使基于新考古發現的文化因素比較分析也難脫其范式。 故而本部分擬對此前學者相關研究成果作學術史視域下研究綜述式的梳理, 一則借以熟悉兩區之間的文化交流演變態勢, 二則通過研究史的回顧管窺相關學者的研究思路、心路歷程,三則在此基礎上嘗試提出新的假說。
(一)兩區裴李崗時代文化關聯
裴李崗時代,中原地區裴李崗文化興盛,分布范圍遍及河南省域, 后李文化在山東核心區也呈現出了明顯的發展態勢, 一改李家溝時代各自所在文化區的居址分布態勢甚至文化發展程度。 早在20 世紀80 年代,較早參與過裴李崗文化知名遺址發掘、 對裴李崗文化研究有卓越貢獻的李友謀先生較早關注裴李崗文化在所處時代的領先性問題, 通過對年代、發展水平及影響力的對比,李先生得出了裴李崗文化領先于磁山和老官臺文化、在華北地區領先的觀點[41]。 雖未直接涉及同時代今河南與山東地區的對比, 但裴李崗文化的發展程度可見一斑。 20 世紀90 年代,學界對這兩支文化皆給予了較大程度的關注。 欒豐實先生在對后李文化的專題研究中, 認為兩者在文化發展早中期,曾“缺乏人員接觸和文化交流”,后李文化偏晚階段,裴李崗文化先民又東進至此, 使得當地文化面貌改變不小[42]。 進入21 世紀,隨著考古發現的日益增多與材料的逐漸發表, 學界對兩者間的文化關聯思考更多。 譬如韓建業先生的研究,若干裴李崗文化因素在其末期傳入海岱地區,促使北辛文化的形成[43]。 另據靳松安先生在博士學位論文中所做的文化分析, 后李文化的小口壺、個別侈口罐、乳足缽等器物皆系裴李崗文化影響的結果[44]134-135。 此后,在紀念裴李崗文化發現30 周年學術研討會上,部分先生的文章也涉及二者關聯。 例如,趙世剛先生據遺物遺跡論及二者時, 認為后李文化不但不可能對裴李崗文化產生影響, 反而受到了后者影響[45];欒豐實先生論及裴李崗文化與東方地區諸文化的關聯時, 認為后李文化受其影響更多一些, 并重申了裴李崗文化對北辛文化的影響[46];鑒于裴李崗文化的影響力,張松林先生提出“裴李崗文化時代”的概念[47],與欒先生既往提出的“裴李崗時代”[48]遙相呼應。靳松安先生在研究生課程教學中也曾專設裴李崗文化的領先性一節, 啟發研究生檢索資料并在文化因素分析基礎上判斷裴李崗文化的成就及其影響。 上述數例,遠非學界前輩及后學對裴李崗文化與后李文化交往關系關注、研究之全部,但裴李崗文化對后李文化的影響及其在所處時代局部區域內的影響力已可見一斑。
單就裴李崗文化、 后李文化二者的彼此關聯甚或文化交流而言, 這一階段似以裴李崗文化對后李文化的影響為主。 至遲在裴李崗文化末期可能已經存在人群往東等方向的遷徙,合力促成了誠如韓建業先生所言的“黃河流域文化區”乃至“雛形早期中國文化圈”的形成[49]。
(二)兩區仰韶時代的文化關聯
仰韶時代, 中原地區的考古學文化為仰韶文化早、中、晚期,海岱地區則以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早期、大汶口文化中期為代表。 在這一并不短暫的時間范圍內, 兩地之間考古學文化的相互交流與影響漸次加深。 從文化發展進程來看,仰韶時代前期、中期,北辛文化、 大汶口文化早期發展程度可能未及仰韶文化,似以中原對海岱地區的影響略占優勢,到仰韶時代后期, 隨著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強勢發展, 兩者間的交流以海岱地區對中原地區的強勢影響為主[50]。
據欒豐實先生的文化因素分析, 北辛文化的鼎、小口雙耳罐、三足缽等一系列器物皆是中原地區前一時期裴李崗文化的典型因素,可在裴李崗文化中找到原型;即使到了更晚的大汶口文化,以獐牙、豬牙、龜甲等隨葬的習俗亦與裴李崗文化的賈湖人有著較高的相似性[51]。 這些文化因素很可能皆系裴李崗文化及其余波影響的結果。 韓建業先生則認為, 北辛文化中的裴李崗文化因素并非直接來自裴李崗文化本身, 而是經由雙墩文化這一媒介傳入海岱地區的[52]。 此外,鑒于以廟底溝類型為代表的仰韶文化的外向態勢, 韓建業先生提出了“廟底溝時代”[53]的命名。 雖然學界對北辛文化受裴李崗文化影響的模式或路徑的問題尚存歧見, 但北辛文化乃至后續大汶口文化中若干與裴李崗文化相似的因素確系較為明顯的現象。
就同時代文化因素的互動來看, 靳松安先生在其博士學位論文中作了系統且翔實的對比研究,北辛文化的小頭球腹壺、大口圜底缸、彩陶裝飾等都是明確的仰韶文化因素,可能與仰韶文化的影響有或多或少的關聯;而仰韶文化的三足釜等若干器物則系北辛文化因素或其變體。 大汶口文化早中期的缽、矮領罐、網紋彩陶罐等器物、彩陶等裝飾可能來自仰韶文化,仰韶文化的長頸壺、盆形鼎、部分折腹器與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影響有關,此外,后者的背壺、部分尊或尊形器、豆等已經進入中原地區[44]135-155。
此外,何德亮先生研究顯示,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弧線勾連紋、白衣花瓣紋、八角形圖案的技法與仰韶文化相似, 可能是在后者影響下形成的[54]。 隨著仰韶文化逐漸衰落,大汶口文化崛起并呈現出迅猛發展的態勢, 文化分布地域進一步擴大。 據杜金鵬先生研究,至遲自大汶口文化中期開始, 中原地區的局部已被西進的大汶口人占據, 發展為大汶口文化潁水類型[55]。
(三)兩區龍山時代的文化關聯
龍山時代, 中原與海岱地區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態勢進一步強化。 龍山時代前期,大汶口文化晚期強勢崛起,發展勢頭強勁,中原地區進入了蓄勢待發的廟底溝二期文化、 大河村五期文化階段。 這兩個地區間的交流在某些方面可能仍是海岱文化占據優勢地位。
趙芝荃等先生認為, 大汶口文化晚期對仰韶文化、 中原龍山文化早期的影響較為突出[56]。 仍據靳松安先生的博士學位論文,廟底溝二期文化、大河村五期文化的袋足鬶、平底尊、 部分杯具等一系列因素皆來自大汶口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晚期的深腹罐、部分帶流器等則可能與中原的影響有關[44]156-163。誠如張翔宇先生所言, 大汶口文化的影響不但促進了不同地區先民的融合, 而且為中原地區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礎[57]。
龍山時代后期,隨著王灣三期文化、后崗二期文化、造律臺文化、陶寺文化等文化所指向社群的強勢崛起, 中原地區一度恢復了對外文化交流中的外向態勢, 但根據現有考古記錄, 同時期的海岱龍山文化也處于蓬勃發展階段, 二者間的交流大致處于相對而言較為平等、互有往來的狀態。 如學界長期爭訟未休的造律臺文化/類型或王油坊文化/類型究竟屬于中原文化傳統還是海岱文化傳統,還是二者之間的過渡地帶雙向文化因素相互雜糅問題[58],或許正是二者你來我往、頻密交流的反映。
早在20 世紀90 年代初, 靳桂云先生在論及海岱龍山文化城子崖類型與后崗二期文化關系時, 曾注意到二者在差異性以外的相似性[59]。 欒豐實先生則更明確地提出,在二者的交往中, 海岱龍山文化對后崗二期文化的影響是主要的,受后者的影響是次要的[60]。 張富祥先生則認為, 河南龍山文化與山東龍山文化相互影響,并舉了素面鬲、建筑、冶銅技術等實例[61]。 靳松安先生在博士學位論文中綜合考察了兩區文化的問題, 認為王灣三期文化、 后崗二期文化、 造律臺文化中的折盤豆、直領甕、子母口器物等可能與海岱龍山文化甚至大汶口文化的影響有關, 而海岱龍山文化中的夾砂深腹罐、甗、白灰面房屋等則可能是中原龍山諸文化影響的產物[44]156-177。
需要說明的是,前述梳理難稱全面,但已可大致管窺這兩大文化區在不同時代的文化關聯及其互動態勢。 雖然不同學者研究篇幅、關注重點甚至立場可能存異, 但其基于文化因素的分析是兩區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得益于學者們的既有研究,中原與海岱地區史前考古學文化交流乃至融合的趨勢愈加明顯地呈現于學界乃至公眾面前。 二者之間尤其是文化接壤地帶的考古學文化面貌呈現出相對復雜的狀態, 直至二里頭時代后期,豫東、魯西南等地的岳石文化面貌仍呈現出較為明顯的來自豫西、豫中、豫北乃至冀南等地的因素[62]。
(四)“中原-海岱史前相互作用圈”的形成
無獨有偶, 除上述以陶器為主體的考古學文化因素外, 古代文獻史料中也有相關線索。 如《史記·五帝本紀》載“黃帝……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帝王世紀》稱黃帝“得風后于海隅,登以為相”①有研究認為,風后即東夷中風夷的首領,參見程有為2006 年2 月發表于《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的《中原文化、海岱文化的互動與漢民族的形成》。;《史記·五帝本紀》亦載“舜耕歷山,漁雷澤,淘河濱,作什器于壽丘……東巡狩, 至于岱宗”,《史記·五帝本紀》又云“舜……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倘若這些記載有一定合理性因素甚或確如部分學者所言乃早期族群的歷史記憶[63],或可認為其系史前時期中原與東夷族群存在密切聯系的反映。 前輩學者考證典籍后,得出了夷夏族人因混合而文化發展的結論[64],甚至認為這一階段的華夏與東夷民族可能已結成部落聯盟[65]。 將這些證據與考古學文化現象結合起來觀之,二者似乎在某種程度上存在互證的可能。 但需要再次強調的是,現有考古發現已在一定程度上具備書寫史前史的條件,史前史的證據主要應從考古發現中找尋,不宜在文獻史料甚或神話傳說的基礎上硬套考古記錄。
總的來看,與其他文化區相比,中原、海岱兩區史前考古工作開始比較早, 發掘遺址比較多,就大的尺度而言,考古學文化序列較為完整,各時期文化面貌相對清晰,為兩地不同時期文化交流與互動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另從大的地理條件來看, 兩地具有相似的生態環境,生業經濟也有相似的演進模式[66],農業復雜化進程在時代的尺度上大致呈同步態勢,文化演進過程具有相似性、相關性。 至遲從裴李崗時代起, 二者之間已開始了較為頻繁的交流。 在后續的歷史演進中,這兩個地區聯系緊密、相互滲透、彼此影響,“黃河流域文化區”逐漸形成并鞏固發展,進而促使“文化上早期中國”[67]的態勢更加明朗。
當然, 二者間的交流與融合建立在彼此發展的基礎上。 從長遠來看,二者曾存在過共同繁榮的時期, 但在交流中的主從關系上也一度呈現出此起彼伏、此消彼長、互通有無、你來我往的態勢, 兩地史前先民在競爭中交流,在融合中發展。 在中、東部地區史前考古工作視域下, 在已有考古記錄尤其龍山時代考古大發現的基礎上, 或可將關系密切的中原、海岱兩大史前文化區合稱為“中原—海岱史前相互作用圈”甚至“中原—海岱史前文化共同體”。 在這一動態的交流互動過程中,二者相互融合, 吸收對方的有利文化因素為我所用, 為彼此的文化發展注入了盎然生機與不竭動力, 最終促進了雙方文化與社會的共同進步與向前發展。 筑城技術的傳播作為文化交流的一個切面, 在雙方社會復雜化進程中扮演了較為重要的角色, 可能是兩大區域史前先民之間交流與互動的重要產物。 石器時代以來這兩大文化區之間的交流與競爭態勢到青銅時代前期繼續發展,并已結成得到學界相對比較認可的“聯盟”[68]關系。 因此,則龍山時代甚至更早即已生根萌芽的 “中原—海岱史前相互作用圈” 對二里頭—二里崗時代商夷聯盟的形成奠定了社會、文化、歷史乃至心理基礎。
三、相關問題的討論
(一)中原地區史前文化因素東漸的兩種模式
從地理形勢來看,地處黃淮流域的中原、海岱地區大部屬于平原、丘陵地帶,二者彼此之間不存在崇山峻嶺等難以逾越的交通阻隔。 前已述及,就二者之間的交流而言,以互動為主,部分時段海岱地區占據主導地位,部分時段中原地區又處于強勢位置。 文化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群互動的反映,其表現形式有人群遷徙、貿易、戰爭,等等。 在這一漫長的雙向互動過程中, 可能既有中原先民的東進,也有海岱先民的西遷。
在中原先民東進、 海岱先民西遷這兩種可能的模式作用下, 中原地區的文化因素逐漸東向擴展。 據前所梳理,文化因素分析所顯示的文化間交流或許表明, 自裴李崗時代以來, 中原地區先民可能已開始了向東遷徙的歷程,不斷把中原文化因素帶入海岱地區,在這種跨區域橫向、 跨時代縱向的文化接力過程中, 海岱地區考古學文化中逐漸增加了前一時代或同時代中原地區的文化因素。 在一定程度上或可認為, 中原先民東進過程中所帶來的相關因素或許是中原文化東漸的主要模式。 除此之外,海岱先民西遷對海岱地區文化面貌的轉變也有著不容低估的影響。 類型學分析與聚落考古研究結果顯示, 到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時期, 海岱地區人群的西遷愈加頻繁,規模亦遠勝于前[69]。 雖不排除這些西遷的海岱族人在進入中原地區后有留在當地定居者, 也可能有短暫避難或強勢入侵后再返回海岱地區者, 他們無形之中起到了二區之間文化傳播使者的作用。
(二)文化交流載體的多元化
一般情況下, 兩種都存在一定發展程度的文化間交流是雙向的。 同理,就文化傳播的物質載體而言,也往往是多樣的,幾乎不存在只傳播一種文化因素的交流。 以史前食物全物化進程為例,既有中國起源的粟、黍等粟類作物的西傳, 也有西亞起源的小麥等麥類作物的東進。 此外,不同地區獨立起源的家養動物豬、狗、牛、羊等也逐漸融合到同一文化中[70]。 又如青銅時代全球化或青銅時代世界體系[71]的形成,除上述食物的多向傳播與交融外,還存在以青銅冶煉為主的冶金術、土坯建筑技術甚至思想觀念等精神世界因素的跨區域雙向乃至多向交流。
中原與海岱地區史前文化的交流也是如此,除上述陶器、石器等生活用具、生業工具外,也有諸如“白灰面”房屋建筑方式的交流。此外,龍山至二里頭時代小麥等作物,黃牛、綿羊、山羊等家畜,青銅工具與青銅鑄造技術等也很可能是這兩個文化區之間文化交流的重要載體或物化表現形式。 精神觀念方面的交流也有為數不少的證據, 譬如筑城過程中的人骨、獸骨祭祀坑,在中原地區與海岱地區不少史前城邑遺址的考古發掘中都有所發現,這些行為應是特殊信仰觀念的反映,在今后的城邑考古尤其城垣及其相關建筑技術的研究中應對這些現象予以更多關注。
多種形式的載體在文化間的交流中相繼(明顯不同時代)或打包(大致同時)進入另一文化區, 體現的正是文化交流中多元化的交往方式和表現形式。 在這種多元化的文化交流中,筑城技術作為集物質、技術、觀念、認知等多種因素于一體的表現形式, 無疑是中原與海岱地區文化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 是兩區文化與社會發展、 經濟與技術進步的一定寫照。
(三)中原史前筑城技術對海岱地區影響
就已有考古工作來看, 中原地區對海岱地區史前筑城技術的影響, 既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存在較為明朗的物化形式。 前已述及,至遲自裴李崗時代起, 中原地區文化因素不斷東漸,經廟底溝時代的強勢發展,仰韶時代后期—龍山時代前期進入了短暫的低谷,到龍山時代后期又迎來了新的高峰。 多種文化因素進入海岱地區, 對當地文化面貌的形成和改變有較為重要的影響。 另外,中原地區史前圍垣城邑最早者在絕對年代上早于海岱地區最早者,技術上也可能領先于海岱地區。 一般情況下, 時代早的因素會對晚一些的文化有影響, 發展程度高的文化對處于滯后狀態的文化①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在很多方面呈現出高度的發達性與領先性,但就筑城技術而言,若認為版筑技術復雜程度高于普通夯筑,普通夯筑技術復雜程度高于堆筑,則其確實較中原地區落后。的影響也要更大一些。
中原地區占據數量優勢的基槽式技術、版筑技術在海岱地區相對少見甚或罕見,甚至并未出現于海岱地區的文化核心地帶。 在焦家遺址新證公布之前, 我們曾認為海岱地區至早在龍山時代后期的海岱龍山文化早期偏晚階段甚至龍山文化中期才出現了版筑城垣,不但在時代上遠晚于中原地區,而且在數量上也遠少于中原地區。 孫波先生過去曾較為明確地提過海岱地區版筑等先進筑城技術受到中原地區影響的觀點[72],近期又重申了此種認識[73]。 隨著這兩大文化區考古發掘工作的持續開展, 這一論點的支撐性證據一度愈加明顯, 唯焦家遺址大汶口文化城垣的新證增添了問題的復雜性。 然而,僅就焦家一處城垣的考古發現,尚不足以推翻既往認識。 在現階段考古記錄的基礎上, 或仍可認為城垣版筑技術、 基槽技術有可能且很有可能系中原史前文化因素東傳進入海岱地區的產物。
四、結語
本文以中原地區史前考古學文化因素的東向傳播為視角,探討了來自中原地區的先進筑城技術對海岱地區城邑建設的可能性影響。 “中原模式”史前城邑中的“河洛亞模式”“海岱亞模式”城址作為史前土筑城垣高技術、高復雜性的代表,在早期文明化進程中起著重要作用。 中原地區史前的基槽、版筑技術相對而言較為進步,對海岱地區筑城技術的發展可能起到了較為重要的影響。除筑城技術以外,這兩大文化區史前先民在其他技術、經濟、觀念甚至政治、軍事等諸多方面都存在較為廣泛且深入的交流。 隨著今后考古發現的不斷增多與重復驗證,若無挑戰性、反對性材料出現,我們或可暫時將關系密切的中原、海岱兩大史前文化區合并稱為“中原—海岱史前相互作用圈”,甚或在有更多證據支撐的基礎上稱其為“中原—海岱史前文化共同體”。 此外,需要說明的是,以大的時代概念為尺度的分析模式只是相對共時的比較,與考古研究尤其聚落考古中的“共時性”[74]概念尚存較大差異,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本研究結論的確鑿性。 本文所提的假說可能僅是多種可能性中的一種,猶待更多發現、更多證據加以檢驗,至少現階段的考古記錄并不足以使其具有排他性。譬如,過去有學者曾提出中原地區部分城址系大汶口文化人群筑造或受東夷集團侵擾而出現的不同見解[75],就可能不失為另一種極具合理成分的有益解讀。此外,來自自然環境的差異乃至個別發掘者對海岱區史前城垣技術公布不詳甚至不確切等方面的因素也可能對本文所提假說存在一定沖擊。 隨著田野考古工作繼續開展與城市考古研究的不斷深入,這一問題的認識或將更加清晰。
五、后記
近年來, 隨著焦家遺址大汶口文化中期偏晚階段至晚期城的發現與材料的逐步公開, 海岱龍山文化的筑城技術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可以在該文化區內部向前追溯的可能性跡象。 盡管如此,似乎也未能完全排除中原地區史前城邑所表現出來的更為復雜且進步的技術對海岱地區龍山時代甚至后一階段二里頭時代, 如岳石文化城垣乃至其他建筑技術影響的可能。 需要說明的是, 在本文中, 我們未能將城垣與其他相關文化因素諸如城垣附屬建筑、城壕、臺基、房屋、灰坑、窖穴、 墓葬等一系列遺跡尤其是房屋的建筑方式予以綜合考察, 這也使得現階段的推論仍處于假說甚至很大程度上屬于假說的狀態,故此本文的初步認識可能仍難免失于片面,將來或可另文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