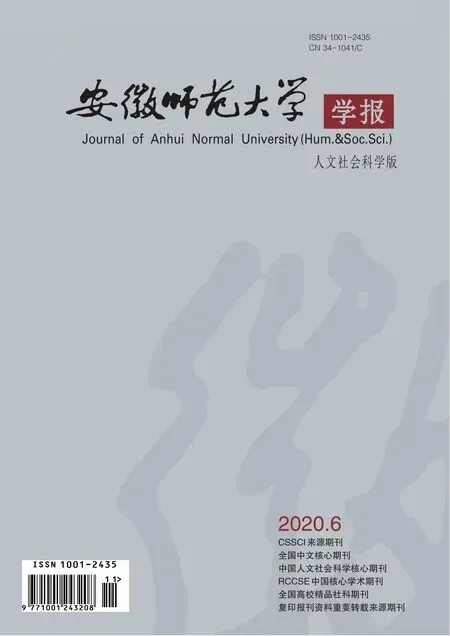北宋生活世界與飲酒精神的多重變奏*
貢華南
(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哲學系,上海200241)
大宋建國之初,趙匡胤“杯酒釋兵權”①司馬光《涑水紀聞》載:“上因晚朝,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酒酣,上屏左右謂曰:‘……吾今終夕未嘗敢安枕而臥也。’……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涑水紀聞》,中華書局2017年版,第12-13頁)鞏固了趙家天下。一場酒獲取了意想不到的權力,這一象征性事件也向大宋臣民做出了重大允諾:權力不可覬覦,美酒可以共享。太祖以實際行動踐行自己的諾言,每日與眾臣共飲。據司馬光記載,太祖曾曰:“朕每日宴會,承歡致醉,經宿未嘗不自悔也。”[1]7每日宴飲至醉,第二天就會后悔。為何“自悔”?因為宴飲傷財?傷身?還是后悔當初做出的允諾?后人難以得知,但飲酒已經成為大宋的要事,此卻無疑。
宋建國之初,學校廢頓,儒釋道三教的創造力萎靡,人們的精神生活處于蒼莽之中,貧瘠又淺陋。飲酒可以滿足欲望、愉悅情志、和樂人群,與詩文樂舞天然結盟。因此,它具有強大的精神功能,被時人當作精神生活之依靠與最重要的展開方式。皇帝帶頭宴飲,百官樂此不疲,士大夫積極參與,政府刺激鼓勵,自上而下地掀起了濃厚的飲酒之風。飲酒主導并支撐起世人的精神生活,這在中國歷史上還是頭一回。
從潛意識層面看,北方強鄰在側,從皇帝到士大夫都由強大對手之壓迫而感受到了自身的有限性。外在緊張造就內在緊張,如何化解精神緊張?緩解、消除對手帶來的壓迫感,以及有限身的沮喪與無奈,飲酒也是個很好的答案。從實際考慮,大量宴飲可以帶動、促進社會的繁榮。凡此等等,都將飲酒推到了時代聚光燈下。
一、飲酒人之常情
大宋建立,政府開始嘗試統一管理酒、曲。宋太宗淳化五年,朝廷“詔征天下酒榷”。宋真宗景德四年,確立了“榷酤之法”,榷酤制度正式施行。
消費是經濟運轉的必要環節,也是促進經濟、社會繁榮的保障。宋人深諳此道。為了刺激民眾消費,政府煞費苦心,甚至使用最古老、最粗俗的方法——色誘。據載:“新法既行,悉歸于公,上散青苗錢于設廳,而置酒肆于譙門,民持錢而出者,誘之使飲,十費其二三矣。又恐其不顧也,則命娼女坐肆作樂以蠱惑之。”[2]23中央政府出面引誘民眾飲酒,這在歷史上絕無僅有。鼓勵民眾飲酒,這首先表明大宋對酒的價值認同。
除了引誘民眾飲酒,大宋政府更是皇帝以身作則,帶頭飲酒,自上而下地引導國民飲酒。首先,大宋在制度層面規定了國家的宴飲的儀式。
宋制,嘗以春秋之季仲及圣節、郊祀、籍田禮畢,巡幸還京,凡國有大慶皆大宴。天圣后,大宴率于集英殿,次宴紫宸殿,小宴垂拱殿,若特旨則不拘常制。凡大宴,……宰相率百官入,宣徽、閣門通唱,致辭訖,宰相升殿進酒,各就坐,酒九行。每上舉酒,群臣立侍,次宰相、次百官舉酒;或傳旨命酹,即搢笏起飲,再拜。或上壽朝會,止令滿酌,不勸。中飲更衣,賜花有差。宴訖,蹈舞拜謝而退。[3]2683-2684
“國有大慶皆大宴”,這保證了大宴的頻率。國家層面的宴飲每年有春秋季、仲、圣節、郊祀、籍田禮(祭祀農神)、飲福大宴等數個。宴有大小,分置于不同地點,有不同規模,或酒九行,或酒七行,或酒五行。大宴之時,按照等級從皇帝、宰相到百官分別舉酒而飲。宴飲皆有歌舞配合,助酒興,成禮儀。另外,皇帝幸苑囿、池御,觀稼、畋獵,暮春后苑賞花、釣魚、賞雪等,以及所至皆設宴,謂之曲宴。每次宴飲,都會極歡而罷。如《宋史·禮志》記載:“大雨雪,帝喜,御玉華殿,召宰臣及近臣謂曰:‘春夏以來,未嘗飲酒,今得此嘉雪,思與卿等同醉。’又出御制《雪詩》,令侍臣屬和。后凡曲宴不盡載。……嘉祐七上十二月,……復宴群玉殿,酒行,上曰:‘天下久無事,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之,宜盡醉,勿復辭。’……出禁中名花,金盤貯香藥,令各持歸,莫不沾醉,至暮而罷。”[3]2692-2693皇帝鼓勵飲而醉,于是參飲者“莫不沾醉”。有時興起,皇帝甚至會逼迫大臣狂飲,如酒量超絕群臣的宋真宗勸李宗諤酒:“寇準在中書,多召兩制會飲私第,酒酣氣盛,必閉關苛留之,往往侵夜,畏謹者甚憚焉。(李)宗諤嘗預會,日既夕矣,而關不可啟,遂于門扉下竊出,得馬以走。于是上勸宗諤酒,宗諤堅辭以醉,且云日暮,上令中使附耳語云:‘此間不須從門扉下出。’宗諤皇恐致謝,上笑而頷之。”[4]1738又如宋徽宗對蔡攸灌酒:“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頻以巨觥宣勸之。攸懇辭不任杯杓,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也。’”[5]298以權勢迫使臣下狂飲,甚至不管大臣死活,酒場何啻戰場!飲酒本為和樂,無約束反墜入不祥,這在宋初司空見慣。不過,在此狂野飲酒風氣下,眾臣亦多見怪不怪。
除了朝廷宴飲,大宋還為官僚宴飲專門設置相關經費。官僚之間有公費公宴,其中包括公款接待上級巡視、同級公差、本地官員節日舉行宴會、出差踐行宴會、升遷賀喜宴會,等等。官僚工作宴飲需要“公使錢”,范仲淹還特別為此上奏:“切以國家逐處置公使錢者,蓋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還,有行役之勞,故令郡國饋以酒食,或加宴勞,蓋養賢之禮,不可廢也。”[4]3384有行役之勞者,國家理當以酒食犒勞。這是古禮,也是范仲淹特別力主恢復的古代傳統。“富而好禮”,這是孔子以來士人的理想。其時,經濟繁榮,文化疲敝,范仲淹以“禮”為念而不憂貧,實不足怪。
官僚辦公時公費宴飲,其居家日常也頻繁宴飲。有條件的在自家官邸宴飲,如名臣寇準特好在自家擺宴豪飲。“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后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6]15國家重臣好夜宴劇飲,每每歡飲達旦,燭淚成堆。酒風之盛,可見一斑。
無條件在家宴飲的官員也有辦法,那就是在條件齊備的酒肆進行。此類史籍亦多有記述,如魯宗道: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諭德,其居在宋門外,俗謂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有名于京師,公往往易服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托何事以對?幸先見教,冀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嘆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備具,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自此奇公,以為可大用。[6]1-2
魯宗道所描述的百物備具,賓至如歸的酒肆在當時汴京實屬尋常。據《東京夢華錄》記載,京師汴梁酒樓眾多,且環境、服務都高端大氣。所謂“凡京師酒店門首,皆縛彩樓歡門,唯任店入其門,一直主廊約百余步,南北天井兩廊皆小子,向晚燈燭熒煌,上下相照,濃妝妓女數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喚,望之宛若神仙。……大抵諸酒肆瓦市,不以風雨寒暑,白晝通夜,駢闐如此。”[7]71酒樓硬件齊備,布置奢華,通宵達旦服務齊全,在此接待賓客確是方便。
在酒肆招待賓客并不奇怪,讓人詫異的是宋真宗對飲酒的態度。魯宗道知真宗對飲酒的態度,也可以說盡人皆知真宗對酒的態度,那就是將飲酒視為“人之常情”。飲酒需備果蔬、樂妓①據《西湖游覽志余》載,杭州每有新太守上任,營妓都出境迎接陪酒。蘇東坡任杭州太守時也辦過不少這類宴會。這種情況隨著南宋理學的興起有所改變。政府開始限制官員狎妓,規定妓女只能為官員提供歌舞和陪酒這類活動,不能發生性關系。,所以,宴飲消費巨大。從積極方面看,消費帶動經濟發展與社會繁榮。但另一后果,就是攀比消費走向奢靡,人心浮夸而頹廢。這種現象也為當時有識之士注意,如司馬光不無憂慮地寫道:
近歲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圣中,先公為群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酤于市,果止于梨、栗、棗、柿之類;肴止于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量月營聚,然后敢發書。茍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8]806
從高層到農夫走卒,奢靡可謂全民風尚。世間虛華多“為目”——做給他人看而不“為腹”——滿足自己需要。“為目”比如走向攀比,宴飲中酒、果、器皿的使用遂不斷水漲船高。奢靡日起,風俗頹弊。然而,飲酒被視為人之常情,不飲,情何以堪?
二、人生不飲何為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記·禮運》)古來宴飲與女樂就結伴而行。大量宴飲不僅促進了大宋酒業的繁榮,也同時推動著文化的復興。在大宋文化復興過程中,晏殊當居首功。《宋史》評價晏殊:“自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興學自殊始。”[3]10196他不僅有“興學之功”,而且自覺以宴飲推動詞學勃興。當然,他對飲酒意義的領悟也不同凡響。
晏殊身居高位,為當時詞壇盟主,喜宴飲,開一代文采風流。他終生好學不倦,興學而培養、舉薦了大量人才。其為人“性剛簡,奉養清儉”。[3]10197剛直節儉,但在崇尚宴飲的時代風尚熏染下,亦不厭宴飲。據沈括《夢溪筆談》記載,當他的同事都去嬉游宴賞時,晏殊與他的弟弟卻一直在讀書。皇上覺得晏殊謹厚,就讓他去東宮教太子讀書。任命之后,皇上與他面談,他回答說:“臣非不樂宴游,直以貪無可為。臣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也。”皇上覺得他很誠實,就更加喜歡他了。這段為人稱道的典故道出了晏殊愛宴飲的本性。
在其獲得高官厚祿之后,晏殊果然踐行“若有錢,亦須往”之說,放開宴飲。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上載:
晏元獻雖早富貴,而奉養極約。惟喜賓客,未嘗一日不燕飲,而盤饌皆不預辦,客至旋營之。每有佳客必留,但人設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實蔬茹漸至,亦必以歌樂相佐,談笑雜出。數行之后,案上已粲然矣。稍闌,即罷遣歌樂,曰:“汝曹呈藝已畢,吾當呈藝。”乃具筆札,相與賦詩,率以為常。前輩風流,未之與比。”[9]127
值得注意的是,晏殊一方面“奉養極約”,另一方面又“未嘗一日不燕飲”。如果這是事實,這只能說明北宋高官生活之奢靡。晏殊每天的宴飲,有賓客,有蔬果,有美酒,有歌樂,還有詩詞創作。在一定意義上,晏殊的宴飲發揮著聚集人才,紹續華夏慧命的作用。“稍闌,即罷遣歌樂……乃具筆札,相與賦詩,率以為常。”飲而不淫,以此助詩興,直接推動著宋詞的繁榮,也間接主導著思想文化的勃興。
晏殊的宴飲在其大量詞作中有反映,最出名的是這闕《浣溪沙》:“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這是晏殊首次被貶謫后的作品。當時他由樞密副使(掌管軍事的副丞相)謫降為宋州知州。原本一帆風順的仕途,無端受挫。這讓晏殊的感受力受到了極大的磨練。宦海沉浮對官僚或許是常態,但對個人卻意味深長。上升的欲望折回自身,光陰去似飛,燕子又歸來,此身如落花,注定老去,思之惟有無可奈何。身與境中美好事物留不住,又如何慰藉這千古之無可奈何?“酒一杯”或許是晏殊為代表的宋初人所能想到的最好解決辦法。
酒無法止住春花落去,也不能讓歡會不散。但是飲酒卻可以改易飲者的心境,首先,酒可解憂。所謂“一杯銷盡兩眉愁”(《浣溪沙》),以酒消愁,這是人類古老的辦法。晏殊一生勤于政務,遇到的問題自然不少,一時之煩悶愁苦更是尋常。他也深諳飲酒消愁之理,頻繁飲酒大都基于此。“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閑離別易銷魂。酒筵歌席莫辭頻。”(《浣溪沙》)頻頻飲酒,他也多能得酒之趣。比如,在酒中重溫昔日歡好,也可以喚起人對眼前人事物的珍愛。
身是有限身,“不死”(道教)與“再生”(佛教)為虛幻。讓有限身充實豐裕最好的辦法就是飲酒,所謂“暮去朝來即老,人生不飲何為”(《清平樂》)。“人生不飲何為?”這對常人來說是個問題,對晏殊則是答案,盡管包含著深深的無奈。把飲酒當作對抗老去的唯一方法,不管是被倏忽的生命流逝所逼迫,還是出自對酒的真誠熱愛,單單把“飲酒”與“人生”直接關聯,已經讓飲酒獲得了深沉的生存論意義。人生中還有比飲酒更重要的事情嗎?還有比飲酒更有意義的活法嗎?這些問題一旦問出,酒對精神生活的意義就立馬呈現出來。由此不難理解,“酒筵歌席莫辭頻”會成為他一貫的態度與主張。酒后寂寥愁苦,意興闌珊,物事蕭瑟,依舊有酒宴相招,這都不成其為問題。
人生的悖論很多,人們會一方面感慨時光易逝、人生短暫,另一方面,生雖有限,但日常生活之單調卻讓生身乏味難耐。飲酒賦予了日復一日的單調生活以情趣,從而使平庸的日常增添了生命厚度。“雪藏梅,煙著柳。依約上春時候。初送雁,欲聞鶯。綠池波浪生。探花開,留客醉。憶得去年情味。金盞酒,玉爐香。任他紅日長。”(《更漏子》)花開時節,賓客共飲,推杯把盞,在花酒間消磨平庸時日,留得無窮情味。初春過后,夜短日長,花酒間的日常生活有了情味,也不用擔心無聊白晝如何過的問題了。“任他紅日長”道出的正是晏殊在獲得意義的日常生活之后之欣慰與從容。漫漫長夜對于古往今來的愁人亦是個問題,與嘉賓共飲不失為解決問題的好辦法。“座有嘉賓尊有桂。莫辭終夕醉。”(《謁金門》)與嘉賓同醉,共同沉浸在昏暗的黑夜。沒有煩惱與恐懼,這份幸福只屬于愿意終夕醉的人。
秋日肅殺,情意蕭條,飲新熟之酒卻可調適心境。“菊花殘,梨葉墮。可惜良辰虛過。新酒熟,綺筵開。不辭紅玉杯。蜀弦高,羌管脆。慢飐舞娥香袂。君莫笑,醉鄉人。熙熙長似春。”
(《更漏子》)紅玉杯對著蜀弦羌管與舞娥香袂,和樂似春歸。以飲酒應對季節變換,這是遠古的生活智慧,醉鄉人可謂醉得有道。
以飲酒消遣情懷,晏殊的門生多有承繼。其中,文采風流最近其師的是歐陽修。他的“人生何處似尊前”(《浣溪沙·堤上游人逐畫船》)顯然繼承了“人生不飲何為”的信條。“尊”即“樽”,流連“樽前”在他乃人生最美之處,也是人生最好的選擇。歐陽修以“醉翁”自號,似乎其一生值得標持的僅僅是醉酒。葉夢得《避暑錄話》載有歐陽修飲酒佳話:“公每暑時,輒凌晨攜客往游,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余朵,以畫盆分插百余盆,與客相間。遇酒行,即攜妓取一花傳客,以次摘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戴月而歸。”[9]102攜客游,伎樂相伴,傳花飲酒,戴月而歸,飲酒被裝點得如此高雅,足見其雅興高致。
在《醉翁亭記》中,歐陽修著力描述了宴飲之盛:“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喧嘩者,眾賓歡也。蒼顏白發,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
熟悉的官宴——太守宴,熱鬧的觥觚交錯,宴酣而樂,樂而醉。官員不僅不避諱宴酣,還極力美化,惟恐天下不知。這在中國歷史上并不多見。當然,記憶的選擇總是基于記痕的深度,由放松享樂的宴飲而獲得的精神滿足深刻難忘,在其人生中亦屬難得,故有此記。
三、酒味多于淚
晏殊仕途雖有波折,然一直位居高位,其飲以高朋滿座之宴飲為主。相較而言,蘇軾仕途坎坷,享受高朋滿座宴飲的時光主要在度過黃州之劫后。如宋人記載:“元佑七年正月,東坡先生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開,月色鮮霽。先生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色,秋月色令人凄慘,春月色令人和悅,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能詩耶!這真詩家語耳。’遂相召,與二歐飲。”[10]120據其晚年貶居惠州時所記:“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者……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者。”(《書東皋子后傳》)東坡年少時不飲,后入仕,為宴飲風氣所染才開始喝酒。東坡酒量不行,但愛飲,且愛與客同飲。此時東坡及其家人都已經習慣了充滿詩意的賓客宴飲,好像其一直生在詩酒之中一般。
其實不然!東坡因反對王安石新法而離京,在杭州任通判,在密州任知州,后調任徐州知州、湖州知州。其間時有歡飲。如作于神宗熙寧九年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所述:“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當時蘇軾在密州做太守,中秋之夜一邊賞月一邊飲酒,直到天亮,甚是歡樂。在“烏臺詩案”后,先坐牢百日。出獄后,被貶為職位低微的黃州團練副使。其間,蘇軾生活窘迫。但他很快適應了新環境,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學會了釀酒,能夠時常飲酒——多為獨飲。蘇軾在《蜜酒歌并敘》中提及他跟隨道士楊世昌學會了作蜜酒,并以詩記下釀造過程:“真珠為漿玉為醴,六月田夫汗流泚。不如春甕自生香,蜂為耕耘花作米。一日小沸魚吐沫,二日眩轉清光活。三日開甕香滿城,快瀉銀瓶不須撥。百錢一斗濃無聲,甘露微濁醍醐清。君不見南園采花蜂似雨,天教釀酒醉先生。先生年來窮到骨,問人乞米何曾得。世間萬事真悠悠,蜜蜂大勝監河侯。”雖然窮困,但自耕東坡,有余糧還能釀酒、飲酒,這給了東坡莫大的精神安慰。
精神安頓下來,蘇軾恢復了往日的灑脫,頻繁攜友出游,當然每次總有美酒相隨。或醉在黃州鄉間酒家,如:“頃在黃州,春夜行蘄水中,過酒家飲,酒醉,乘月至一溪橋上,解鞍,由肱醉臥少休。及覺已曉,亂山攢擁,流水鏘然,疑非塵世也。”(《西江月·頃在黃州》)或飲酒赤壁,如作于宋神宗元豐五年的《念奴嬌·赤壁懷古》:“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及“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前赤壁賦》)“‘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于是攜酒與魚,復游于赤壁之下。”(《后赤壁賦》)無酒不游,無酒不歡,酒成為游賞歡聚的必要條件。。
其實,蘇軾在其詩篇中從不同角度都談到了酒之真味,比如“酒中真復有何好,孟生雖賢未聞道。醉時萬慮一掃空,醒后紛紛如宿草。十年揩洗見真妄,石女無兒焦谷槁……”(《孔毅父以詩戒飲酒,問買田,且乞墨竹,次其韻》)飲酒不僅可以“萬慮一掃空”,而且可以“見真妄”。“真妄”問題即“道”的問題,以飲酒領悟“真妄”無疑是對秦漢發展起來的“味道”方法論的繼承與發展。人生雖如夢幻泡影(《洞庭春色賦》),達觀一些看,有生之年亦有不少樂趣。釀酒、飲酒之神奇,足以散痹頑、洗愁顏。更有甚者,飲酒可“逃天刑”:“曾日飲之幾何,覺天刑之可逃。”(《中山松醪賦》)有限之身,壽夭有定,多病多愁,這是天之所命。清醒者對于“天刑”多有無可奈何之感。飲酒移易人的心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調適愁病。東坡多飲之后,信念增強,以致于“覺天刑之可逃”。“覺”一時情緒語也,東坡亦自知。時過境遷,東坡的看法又會隨情緒而改易。如:“生前富貴,死后文章,百年瞬息萬世忙,夷齊盜跖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憂樂兩都忘。……達人自達酒何功,世間是非憂樂一來空。”(《薄薄酒二首》)將“達”歸結為“達人”,而否定“酒之功”,最終又陷入空幻之中。不過,換個角度看,在真幻之間流轉,正可謂以人生來實證“酒味多于淚”之真義。
四、飲而在
魏晉士人追求“醉”,其目的性很強,那就是逃避名教(如劉伶),或拒絕與當權者合作(如阮籍)。宋代士人的“醉”,其目的性較弱,一部分人因一時之失意而解憂(如蘇軾、歐陽修),更多的人是因為喜歡飲酒而醉(如寇準等)。
對于石延年來說,飲酒即他的存在方式。他不斷探究飲酒之法,翻新他的存在方式,如“囚飲”——露發跣足,著械而坐;“巢飲”——飲于木杪;“鱉飲”——以槀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徒飲”——夜置酒空中;“鬼飲”——匿于四旁,一時入出飲,飲已復匿,等等。[11]421-422這些飲法奇怪至極,不僅不合禮儀,甚至越出常情。
愛飲者多喜呼朋喚友,享受酒席間熱鬧氣氛。石延年有酒即可,至于飲酒環境如何,他并不在意。據《宋史·石延年傳》載:
延年喜劇飲,嘗與劉潛造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飲多,以為非常人,益奉美酒肴果,二人飲啖自若,至夕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傳王氏酒樓有二仙來飲,已乃知劉、石也。延年雖酣放,若不可攖以世務,然與人論天下事,是非無不當。[3]13071
對飲而不交一言,讓酒直接作用于飲者,各自享受酒味,這在常人看來是怪異。石延年專注于酒本身,拒絕在酒與人之間夾雜多余者,包括語言、他人的目光。飲酒就是飲酒,而不是其他。飲酒本身價值自足,不能將飲酒附著其他目的。這種對酒之癡迷具有傳奇色彩,宋人為此生出不少傳奇故事來,如:
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鄰有一豪家,……曼卿即著帽往,坐于堂上。久之方出,主人著頭巾,系勒帛,不具衣冠。見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禮。……酒五行,群妓皆退,主人亦翩然而逝,略不知揖客。曼卿獨步而出,言豪者之狀,懵然不分菽麥。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問其近鄰,云其人未嘗與人通往還,鄰家亦不識面。古人謂之錢癡,信有之。[12]91
這個故事頗具魔幻色彩。按照戲家之言,石延年因“癡”(酒)而生(對酒之)“情”,因“情”而生“幻(夢)”。“幻(夢)”生出“主人”,“主人”依照“幻(夢)者”而生。所生非世俗可見之人,或只存在于延年的思想世界。凡俗雖不可見,然卻有跡可循。首先,“主人”喜飲酒,與延年同類。其次,“不具衣冠”亦“全不知拱揖之禮”,乃專注于飲酒的純粹的飲酒人。第三,二人相交只為一飲,飲完即不相干,所謂“翩然而逝”“閉門不納”是也。
癡情于酒,酒與身同在,酒沒則人亦不在矣。石延年之卒正因不飲:“仁宗愛其才,嘗對輔臣言,欲其戒酒,延年聞之,因不飲,遂成疾而卒。”[12]98對常人而言,戒酒會使身體更健康。對真正的飲者,不飲則失去存在的理由,成疾而卒乃飲者必然的歸宿。在大宋,皇帝之言為法令。皇帝欲其戒酒,實以外在之法禁飲者之身家性命。對石延年個人,此乃悲劇。
五、酒近于道
隨著飲酒之風興起,釀酒技術不斷提高,北宋也出現了大量關于酒的著作。對于酒的釀造過程,蘇軾《東坡酒經》描述最為詳細:
南方之氓,以糯與秔,雜以卉藥而為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麫而起肥之,和之以姜汁,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為率,而五分之,為三斗者一,為五升者四。……既水五日乃篘,得三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篘半日,取所謂贏者為粥,米一而水三之,操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潤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為五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猛也。篘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13]1987-1988
好酒需要良餅、精麴等上等的原料,更需要精細的手藝進行量的控制、時間火候的把握。當然,以性味正為指標的美酒更依賴制作者的味覺,所謂“以舌為權衡”是也。水質、冷暖、火候、水米的比例等多重不斷隨權衡而調整的因素決定了酒之性味,或微苦,或少勁,或和而猛,或醇而豐。東坡對酒藝的描述反映了宋代制酒技術之精良,當然也與東坡本人長期用心于酒有關。
就理論水平說,最高的當數竇蘋的《酒譜》與朱肱的《北山酒經》。這些著作不僅總結了酒的制作工藝,還對酒的特性,酒對人的意義等主題做了深入的考察。這些著作的出現,表明宋人對酒精神已經達到高度的理論自覺。
竇蘋《酒譜》對酒源、酒之功過、性味等問題做了細致的考察。
第一,對酒源的考辯。駁斥了儀狄、神農、黃帝作酒等無稽之說,以及人類作酒與天有酒星相關等附會之說。竇蘋認為,酒是“智者作之,天下后世循之”。[14]9但酒之作不晚于《夏書》《孟子》時代,這種謹慎的態度值得稱道。
第二,對酒之功過做了相對辯證的說明。首先,酒有大功于建功立業。如勾踐與士同醉,秦穆公投醪于河,三軍共飲而告捷,等等。人們以禮飲酒,或以德將酒,溫克而事美。其次,沉湎于酒,誤事亂德。從商紂王以酒亡國以來,不乏前赴后繼者。因此可以理解,歷代多有酒誡,以警醒世人。
第三,對酒之性味的總結。《酒譜》引用《本草》 之說認為“酒味苦、甘辛,大熱,有毒”。[14]159自先秦以來,對酒的性味的認識大都是“甘”,如《戰國策·魏策二》:“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聯系釀酒流程,這比較好理解。釀酒過程中,谷物發酵所得的酒,酒精含量低,味甘。欲得“辛”味,必須將這些酒多次發酵。到了宋代,釀酒技術已經高度發達。宋人已經掌握了先“甘”后“辛”的釀酒工藝,對酒的性味的認識也相應推進。
第四,對宋代困于酒原因的揭示。對個人來說,酒可療疾,也可致疾。致疾的原因是酒性熱,過量飲酒,熱氣破壞了身體平衡。人們過量飲酒的思想根源是放縱欲望,由此導致理智的紊亂。所謂“今之人以酒為漿,以妄為常,醉以入房”。[14]159“以酒為漿”是把酒當飲料解渴,“醉以入房”是說酒色同時不知節制。“以妄為常”則是說執迷于醉后幻相,理智迷失。這些都可以說是“酒氣獨勝”的表現。
朱肱的《北山酒經》在對酒的性味、功過等方面的看法與《酒譜》一致,“酒味甘辛,大熱,有毒。雖能忘憂,然能作疾。……酒所以醉人者,曲孽氣之故爾”。[15]6對酒的性味的看法,朱肱沒有像竇蘋那樣說明其出處,“甘辛,大熱,有毒”或許是竇蘋、朱肱那代人的通行看法。“曲孽氣之故”即“酒氣獨勝”,表述不同,實質為一。但朱肱著《北山酒經》,其對酒的看法亦有獨特之處。
第一,他強調了酒對人類的必要性。所謂“禮天地,事鬼神,射鄉之飲,鹿鳴之歌,賓主百拜,左右秩秩,上自搢紳,下逮閭里,詩人墨客,漁父樵夫,無一可以缺此”。[15]19“無一可以缺此”表明酒對各個階層民眾都是必要的。基于此,他批評了佛教戒酒觀念,而竭力為酒辯護。“惟胡人禪律,以此為戒,嗜者至于濡首敗性,失理傷生,往往屏爵棄卮,焚罍折榼,終身不復知其味者,酒復何過耶?”[15]19過度飲酒,傷身亂性,但此非酒之過。將酒的價值與人的行為分割,這是對漢人(如孔融)觀念的承襲。
第二,朱肱明確提出“酒之功力,其近于道”的觀點,飲酒亦是精神的修煉。具體說,飲酒可以滿足人安身立命的精神需要。“平居無事,污尊斗酒,發狂蕩之思,助江山之興,亦未足以知曲蘗之力、稻米之功。至于流離放逐,秋聲暮雨,朝登糟丘,暮游曲封,御魑魅于煙嵐,轉炎荒為凈土。酒之功力,其近于道耶?與酒游者,死生驚懼交于前而不知,其視窮泰違順,特戲事爾。彼饑餓其身、焦勞其思,牛衣發兒女之感,澤畔有可憐之色,又烏足以議此哉?鴟夷丈夫以酒為名,含垢受侮,與世浮沉。”[15]23-24對于普通人來說,日常生活(“平居”)是平庸的,飲酒能夠為平庸的生活帶來不平凡的驚奇。對于失意落拓之人,灰暗的心態需靠飲酒完成轉換。死生、窮泰等人身際遇亦需要飲酒來調節。進言之,不管處境如何,飲酒都可以充當精神生活之依靠。在此意義上,朱肱將“酒”與“道”并提。
第三,酒近于道是因為酒可以“移人”。飲酒不僅可以作用于人的身體,而且能夠變化人的氣質情性。“善乎,酒之移人也。慘舒陰陽,平治險阻。剛愎者熏然而慈仁,懦弱者感慨而激烈。陵轢王公,紿玩妻妾,滑稽不窮,斟酌自如,識量之高、風味之媺,足以還澆薄而發猥瑣。”[15]31酒以熱力貫通血脈,使人膽氣豪發,性情移易。人在酒的作用下“變形”,存在的多重可能性由此轉化為現實。
六、余 論
大量宴飲,浮華腐化著人心,而人欲的放縱往往導致人性的墮落。宴飲等繁華的世俗生活帶來諸多思想文化問題,也刺激、推動著理學的興起。反對“苦教”的理學家對宴飲并不拒絕。周敦頤將飲酒視作遠離、超越俗塵的生活方式①如“一日復一日,一杯復一杯。”“青山無限好,俗客不曾來。”(周敦頤:《周敦頤集》,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64、65頁);邵雍則以微醺來通達造化之原②如“半醺時興太初同”“太和湯釅半醺時”。(邵雍:《邵雍集》,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290、300頁);程顥時而會“莫辭盞酒十分醉”。③程顥、程頤:《二程集》,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477頁。程顥曾監汝州酒稅,負責酒的生產,對酒非常熟悉,這與程顥追求“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不無關聯。程顥抱怨“旁人不識予心樂”,“旁人”恐怕不僅指普通民眾,還應包括當時的儒者。當然,程顥的志向不是做狂飲的“名士”或“詩家”,而是成就圣賢。可見,大程子已不復戀酒、嗜酒,而是堅持定心定性,將酒納入天理心性之中。馮夢龍《古今談概》記載:兩程夫子赴一士夫宴,有妓侑觴,伊川拂衣起,明道盡歡而罷。次日,伊川過明道齋中,慍猶未解。明道曰:“昨日座中有妓,吾心中卻無妓;今日齋中無妓,汝心中卻有妓。”(馮夢龍:《古今譚概》,中華書局2018年版,第19頁)伊川自謂不及。此雖是文人趣談,但對二程的刻畫卻是準確的。其中的細節也大體符合北宋的特征,如士大夫頻頻宴飲是北宋的常態,“有妓侑觴”也是朝廷允許的事情。通過飲酒來肯定、重建世間的美好生活,這是理學家的一項使命。隨著“苦”意淡化,升天入地的詩酒激情下落到世俗生活。世間的功業——名利——成為美好生活的核心內涵,這直接造就了人欲的放縱,心靈的墮落。飲酒是精神秩序的突破者,并不能充當精神秩序的構建者。理學家提出所以然、所當然、必然相統一的“天理”來收拾人欲的放縱與心靈的墮落,正是對大宋近百年浮華世俗生活所帶來問題的回應。當然,規訓飲酒乃天理題中應有之義。看起來,理學的興起與北宋社會經濟的繁榮同時出現,但顯然,二者并非前因與后果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