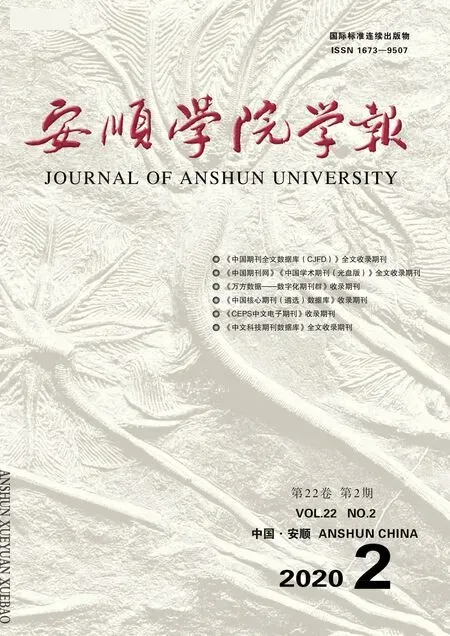黔中屯堡地區(qū)的碑刻類別及價值略論
——以安順市西秀區(qū)為例
劉 夢 李聚剛
(1、2.安順學院人文學院,貴州 安順561000)
碑刻文獻為中國地方鄉(xiāng)土史料之重要組成部分,按碑刻記載內(nèi)容劃分,可分為纂言、紀事、述德等類,具體到全國不同地區(qū),又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出地域特點。例如,太原晉祠博物館韓革通過調(diào)查太原地區(qū)明清時期的碑刻,得出這些碑刻主要涉及自然災害、農(nóng)民起義、家訓、鄉(xiāng)規(guī)民約、祈雨、賦稅等方面。[1]烏江流域社會經(jīng)濟文化研究中心彭福榮、黎露通過地方史志和田野考察認為,烏江流域歷代碑刻文獻以歌功頌德、紀事抒情、立約警示為主,涵蓋政治經(jīng)略、經(jīng)濟開發(fā)、交通建設、教育振興、民風載記、鄉(xiāng)村治理、文藝交游等領域。[2]照碑刻所在地點劃分,有寺廟、道觀、清真寺等宗教場所之碑刻,有文廟、武廟、城隍廟、名宦祠等祠宇場所之碑刻,又有鄉(xiāng)誼公所、商旅會館等商紳人士聯(lián)絡互助場所之碑刻,還有宗族祠堂及在數(shù)量上占絕對主體地位的墓碑石刻。
目前,輯錄及利用碑刻進行歷史或文化的研究,也已受到學界高度重視并產(chǎn)生出一系列論著成果,這些成果主要體現(xiàn)在利用會館碑刻研究商業(yè)發(fā)展,利用宗教碑刻研究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及其民間信仰形態(tài)與社會生活,利用墓志碑銘研究家族歷史及人物履歷,利用各類紀事碑刻研究自然災害、生態(tài)環(huán)境、邊疆開發(fā)和民族關系等。其利用宗教類碑刻研究民間信仰與社會生活者,如趙世瑜利用明清京師泰山信仰的碑刻資料,對廟會中的積德行善作了社會生活史方面的生動研究。[3]又如梅莉據(jù)武當山現(xiàn)存碑刻對明清湖北民眾武當朝香習俗進行了討論。[4]其他以碑刻為主體或輔助資料研究歷史文化、生活民俗等地方社會各方面事象的成果亦不勝枚舉,恕難一一枚舉。
安順黔中屯堡地區(qū)碑刻富集,類型多樣,理應受到地方學術研究及文物保護的重視。茲據(jù)田野調(diào)查所見屯堡區(qū)域部分碑刻為例,對其類型及價值略加闡發(fā),以促進此類文獻的發(fā)掘、研究和保護。
一、碑刻的整理和分類
黔中屯堡聚落有豐富碑刻資源,其廟宇之內(nèi),井渠之旁,樓閣牌坊之側,家族祠墓之中,碑刻幾乎寨寨可見。大略言之,可分為禁約、紀事、述德、纂言等類。
(一)禁約類碑刻
所謂禁約,亦即禁止、約束之意,在鄉(xiāng)土社會里包括提倡與反對的一體兩面。黔中屯堡碑刻文獻中,不乏禁約類碑刻。這類碑刻大率可分為兩類,一類以禁止為主,一類以要求為主,前者即通常所謂禁約碑,后者多為告示。
1.禁約碑
安順禁約碑之較具交表性者,如移置于市區(qū)武廟內(nèi)保存的“永禁估葬碑”。其碑有二,可見晚清安順“估葬”之現(xiàn)象及地方政府厲禁之態(tài)度。二碑各載曰:
永禁估葬碑(一)
欽加同知銜署普定縣正堂兼辦玉字全軍營務處加三級記錄五次……再行剴切嚴禁事:
照得民間喪葬,如有恃強攙奪,霸估扛抬,多取雇值 不容本家雇人抬送者,立拏究辦,定例……普屬素有不法地棍,創(chuàng)名“圍上”,每遇民間喪葬,輒即恃強霸估抬送,任意勒索,迭各前任出示嚴禁在案,乃……該不法地棍 仍蹈故轍,冒稱營兵圍上,任意霸估抬扛。獨不知營兵名糧,由守而戰(zhàn)而馬,挨序撥補,可至將備……因喪葬勒索,甘心為人輿仆賤役,且訛詐勒磕,均為例所不容,以身試法,雖至愚者不為也。此等惡轍明系不……射,冒稱營兵,情殊可恨。現(xiàn)據(jù)本城舉貢紳耆,以恃兵結黨估抬喪葬公懇翦(剪)除以杜民害公稟前來,除批示并……撫、臬、藩憲立案,有犯嚴行懲辦,永遠嚴禁外,合亟出示勒碑曉諭。為此示,仰城鄉(xiāng)內(nèi)外軍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如……行雇人抬送,倘有不法地棍冒稱營兵,到爾等喪家霸估抬扛,任意勒索,立即嚴拿捆解送縣。抑或詐穿號……營字樣,亦即捆送赴營,一面到縣具稟,以憑盡法懲辦。但不得挾嫌妄拿,致于并究,各宜凜遵毋違。持示。
右諭通[知]
光緒元年六月初九日示
奉撫部院曾批,據(jù)稟是否可行,仰按察司核議詳覆飭遵。
按察使司林批,據(jù)該前縣席令稟,安郡一帶無業(yè)游民,創(chuàng)名圍兵,每遇喪葬,分界估抬,任意勒索,請酌加[懲]……情一案,仰安順府轉飭,如稟辦理。
安順府正堂周批,據(jù)稟已悉,應否加系鐵桿之處,仰候撫臬憲批示辦理。
大清光緒二年歲次丙子四月吉日合郡紳耆公立。
永禁估葬碑記(二)
欽加三品銜補用道署理安順府正堂加十級紀錄二……
欽加同知銜調(diào)署普定縣事永從縣正堂加五級紀錄……
出示勒石曉諭以垂久遠事,案查前據(jù)屬普定縣席令具稟,郡……民闖名圍兵估抬喪葬,請示辦理酌加系桿一案,奉準撫、臬憲批示如稟辦理在案。茲據(jù)合郡舉貢生耆聯(lián)名公稟請示……前來,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仰合郡紳耆軍民人等知悉,除由……遠禁止外,嗣后遇有喪葬,聽民自便,不準分界估抬,倘敢不遵……喊稟來轅,定按上憲批示辦理,絕不姑寬。其各凜遵毋違,特示。
右諭。
光緒二年三月初四
大清光緒二年歲次丙子四月吉日合……
2.告示碑
告示之碑與禁約之碑猶如一體兩面者,一以示禁為主,一以勸倡為先,實不可嚴為區(qū)分。安順市西秀區(qū)劉官鄉(xiāng)金土村金齒組永興寺大門內(nèi)側有“太平天子碑”一幢,反映出清中后期安順地方有關夫馬攤派問題,有重要的歷史價值。碑文如下:
太平天子碑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云貴二省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加十級紀錄二十次覺羅;
欽命貴州等處承宣布政司布政使加九級紀錄二十次公;
欽命貴州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加八級紀錄十九次董批:差役膽敢勒索并折收夫馬銀,大[干]法紀,仰安順府嚴提究報,毋稍袒狥,并粘件發(fā)特授貴州安順府正堂加七級紀錄十五次曾批,仰普定縣查明前藩憲出示章程,準潘昂等勒石遵守可也。署貴州安順府普定縣正堂加五級隨帶軍功加三級紀錄六次崔批,本縣□遵前藩憲告示,復出示曉諭地方在案,即照此準其勒石可也,切切。抄奉欽命貴州等處承宣布政司布政使加四級紀錄九次百,為嚴禁濫派以恤民累事,照得一切差使所用夫馬,例應給價雇,不得按田攤派,有累苗民。今本司蒞任以來,查得普民潘昂等具控差役張順等濫派勒折一案,查該站路當孔道,凡遇上下差使往來,額設馬不敷應付,固不能不藉資民力,但竟按田濫派夫馬,大屬違例,除已往不究外,合行出示嚴禁。為此示,仰該縣官□□差人役遵照。嗣后差使到站,如用夫在一百名之內(nèi),用馬在五十匹以內(nèi),不許向民間攤價雇。若用夫在一百名以外,用馬五十匹以外,仍照向定章程,在于縣屬六里地方照例發(fā)給價值輪流平雇,不得偏枯。倘敢再行按田派累以致民怨沸騰,或經(jīng)告發(fā),或被訪聞,定即官參役處,斷不姑寬。該民苗人等倘因有此示,遂抬價指勒居奇,以致有誤要差,亦即一并究治不貸。本司言出法隨,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右諭通知
大清嘉慶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忠興里公立
普定五里五枝紳士約頭苗民等
在屯堡村寨所見禁約類碑刻又以村規(guī)民約為最多,生產(chǎn)生活公共設施保護及使用規(guī)范次之,因二者皆為常見,茲不具錄。禁約或告示類碑刻往往因事而起,雖以禁約之條款為主,然紀禁約本末緣起之時,仍多涉及一些具體的事件,是又有紀事為主之碑刻。
(二)紀事類碑刻
明清黔省紀事類碑刻記載之內(nèi)容大概包括廨宇祠廟等公共建筑創(chuàng)修重修、土流疆界等糾紛調(diào)處、家族或村落大事紀錄、水利設施建設始末等。安順屯堡區(qū)域內(nèi)紀事類碑刻較夥,其中又以記敘公署、祠宇、廟宇、觀寺等公共建筑由來及重修始末的碑刻為最,它如記載基層場市創(chuàng)設、家族遷徙入黔及其始祖本末、水利等公共生產(chǎn)生活設施建設等碑刻亦不少見。其祠廟建設類碑刻如安順武廟內(nèi)所藏普定縣城隍碑,碑載:
縣城隍廟記
安順改設郡治,普邑附郭而居,于今百八十年矣。相傳府城隍廟,乾隆五十六年奉敕封為威靈侯。鬼神之為德,由來尚矣。道光丁未歲,崇君埜漁視事普定,以縣無城隍,猶郡無邑,誠缺典也。勸捐建廟,工未竣而更調(diào)他邑,后之接任者無暇及此。咸豐元年四月朔,鴻儒捧檄而來。次日謁廟,先一夕夢峨冠博帶二神,一在室之中,一在室之左,蓋別居也。既然,詣府、縣兩城隍廟,恍如夢境,因異之,以為神明有所使令耳。時甫下車,民事倥傯,未遑經(jīng)理,非敢緩也,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之意也。閱數(shù)旬,庶務略有端緒,爰集紳耆父老,告以夢中實跡,首先捐廉為倡。于是好善樂施者踴躍捐輸,而后殿、兩廡,與夫前門甬道得以落成。于戲,天下無不可為之事,所患志之不篤,心之不誠耳。抑又聞之,誠身明善乃居官之先務,敦倫紀,正風俗,無一非有司誠身明善以感格乎!神明默助之所致,而果報不爽,幽明一理,賢不肖無不知之。特以利欲所蔽,求其為忠而不以為忠,求其為孝而不以為孝,求其為弟而不以為弟,放僻邪侈,無不為己,直以天高難問,善者以怠,惡者以肆,是故神道設教,使民之所畏敬,庶幾一道德而同風俗也。鳴乎,圣人之為慮深且遠矣,是為記。
咸豐二年正月下浣署普定令余姚邵鴻儒撰
民國《續(xù)修安順府志》云,普定縣城隍廟在城南隅原習安書院舊址,內(nèi)一碑云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知縣崇夢漁建修,又一碑云咸豐二年(1852年)普定縣余姚邵鴻儒創(chuàng)建,“未知孰是”。[5]卷十三《名勝古跡志·石佛寺》,469前引碑記道光丁未歲即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時任普定知縣者崇璟,咸豐《安順府志》載其為襄紅旗漢軍,道光二十六年任,二十八年接篆者魏承柷,[6]卷二十八《文職官譜·普定縣知縣》,386碑記崇埜漁即崇璟。由碑記可知,普定縣城隍廟創(chuàng)建于知縣崇璟,工未竣而他調(diào),續(xù)成事于知縣邵鴻儒,并非“未知孰是”一語可推諉者。
又如安順市西秀區(qū)雙堡鎮(zhèn)五顯廟所存“重修碑記”,碑記主要敘述了重修廟的原由、規(guī)模、捐款數(shù)目、人數(shù),末尾署“大清嘉慶八年□月初十日立”字樣。該五顯廟還有該五顯廟神像“重塑碑記”一幢,碑上文字業(yè)已風化,漫漶不清,只依稀可見:
吾國以神道立國,迄今已數(shù)千年矣。各鄉(xiāng)□□□□□□設日新全。我堡中五顯廟雖然前人創(chuàng)造,而神像多已朽壞,故我堡老□□等見之不忍,斯茲工師陳鏡清由省上來,特請重塑五顯神像一堂,□□助功德之人,開列下左:首人黃汶英十元……(后面依次是人名及捐款數(shù)額)。
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吉日立
碑文大概講了重塑五顯廟神像的事由及集資修建五顯廟的捐款數(shù)目等。從碑刻落款的時間來看,兩次重修五顯廟的時間相隔近百年,可見民間信仰在傳統(tǒng)村落社會具有較強的持續(xù)性。
還有記載賦役分擔、市場開設的碑刻。安順屯堡文化研究專家呂燕平曾發(fā)現(xiàn)此類碑刻三幢,分別為現(xiàn)存于西秀區(qū)七眼橋鎮(zhèn)雷屯村永峰寺內(nèi)的雷屯“科糧碑”,七眼橋鎮(zhèn)章莊村吳屯組興隆寺內(nèi)的吳屯“賦役碑”和雙堡鎮(zhèn)張官村永興寺內(nèi)的雙堡“市場碑”。[7]該雙堡“市場碑”,因其碑額有“承先啟后”四字,亦可名之曰“承先啟后碑”。此碑原立于雙堡場壩,后遭損毀,因此碑涉及雙堡市場開設緣由及張官堡村淵源,張官堡村民將其移至永興寺存放保護。該“承先啟后碑”載:
承先啟后
蓋事有創(chuàng)于前者,必有繼承于后,乃能永垂不朽,事跡不墜。如我堡內(nèi)之先人,自征南以來,二十姓人分編五旗,屯墾于此。當日政府原為寓兵于農(nóng)之計。后以人口繁衍,生活用品不便,遂協(xié)商開場,以便以有易無,乃訂寅、申二日趕集,名曰“雙堡場”。迨政府安糧,此場面積載糧肆斗,分五旗負擔,每旗八升,勒碑為記,有糧串可憑。嗣因日久年遠,其碑損壞,字跡模糊。經(jīng)我旗內(nèi)之人合議,重勒碑石,用志不忘,亦承先啟后之意云耳,是為序。
張官堡五旗二十姓人眾重立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吉日[8]
此碑反映雙堡開設場市的經(jīng)過,對于研究安順村鎮(zhèn)基層集市的由來以及明清屯堡社會的基層組織形式等有一定參考價值。諸如此類關于地方經(jīng)濟的碑刻,還有刻于石碑而非書寫于契紙的文書,呂燕平等曾在安順市普定縣號營村發(fā)現(xiàn)一幢性質(zhì)為田地買賣契約的石刻,并將之命名為“號營碑刻契約文書”。[9]2
屯堡村寨中時間較早的紀事類碑刻,多為研究村落歷史的重要憑據(jù)。如安順市西秀區(qū)七眼橋鎮(zhèn)聯(lián)橋村有舊廟一座,內(nèi)有“勒碑石刻”一幢,載:
勒碑石刻
嘗言先人之基有勛于后。自洪武年間至處,卜居安邑,開基創(chuàng)業(yè),來所……百十余畝,荒蕪未辟,涸無會急,復維躊躇,拮本處苑池之永載溝,過……而漸就。至康熙年間,時雨集足,洋洋湧及堤崩流而不至,何以供……屯地段插標著明――肖家沖陸地一沖,兩邊坡地為界,又人人……薛家壩門口,抵山腳,通大河廟腳,石關交界,舊屯抵東巖時家交界,肖志仁屯糧共十十六擔六斗五升四合,丁銀三兩八錢伍分□碩,在安順上納。勒碑為據(jù)
將本廟香燈之產(chǎn)業(yè)開列于左:
其有所遺留廟田,平山田地,上下二坵,們留一坵,燕子地田山坵又二坵,舊屯門口八坵,長泥凹田二坵,石關口田地一坵,又兩所門口田一坵,載屯糧一旦(石)四斗七升……
乾隆元年六月初八 公諭同立
因年久漫漶,兼之采訪者抄錄文字時匆忙,該碑文辨識或多錯誤。不過,從已知碑文來看。該碑仍有利于了解聯(lián)橋村的起源、發(fā)展、土地分配以及屯糧分擔狀況。
再如西秀區(qū)劉官鄉(xiāng)水橋組小廟內(nèi)有“永垂千古”碑,該碑碑額有“永垂千古”四字,故以名之。該碑因年代久遠,加之保護不當,碑文字跡已相當模糊,稍能辨識者有“有云南入托神以庇蔭……存也,而神之為人常祀者,有如……”“通天都府五顯華光大帝也哉。緬□我水橋合堡先……”“有數(shù)石”“買置數(shù)……”“特之日用□□謹序勒石”“各屯分大小拾”“田一分”、 “四丘”“東木橋載租三斗”“□官二姓同拾載租八斗”“肖家”“雙堡”“乾隆”等字樣。落款為“□□肆拾伍年”。可以推測,該碑文字若能進一步辨識,當有利于了解水橋堡及附近村寨的起源、發(fā)展,并可了解清乾隆前后的地方社會經(jīng)濟及土地分配概況。在水橋堡小廟右側上廂房內(nèi)還有一塊石碑,碑文亦因年代久遠而漫漶不清,難以辨認,只能看到明朝“天啟元年”等殘缺信息,又或涉及明末奢安之變對于黔中地域社會的影響。
(三)述德類碑刻
述德,即稱頌功德,多為后學晚輩或后代對碩德耆舊或先祖前賢功德的稱頌。將頌揚之辭或功德之事刊之于石,即為述德碑。相較于前述紀事類碑刻而言,此類述德碑在屯堡區(qū)域更為夥見。黔中屯堡碑刻中的述德碑有功德碑、去思碑等幾種類型:
一是功德碑,以捐助錢、物及勞力修繕廟宇、公共水利和路橋等“善事”為主,間亦以捐助貧弱為“功德”。對“做功德”之人或事勒石以記載之,以為勸善之典型,具有鄉(xiāng)土歷史和現(xiàn)實意義。
黔中屯堡區(qū)域的功德碑可謂寨寨皆有,農(nóng)村社區(qū)聚落內(nèi)部及旁近山上廟宇、公用水井、村內(nèi)路橋及其他公共設施等,村民或族人自發(fā)捐助錢財物資及勞力以助蕆事者,多樹有功德碑。安順舊州有兩幢功德碑,一幢為“再詠觀瞻”功德碑,有人名而事跡不詳,“乾隆五十二年丁未歲孟夏月立”;另一幢亦有人名、捐款數(shù)目,具體事跡不詳,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立。雙堡鎮(zhèn)亦有一碑,記有人名,為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四月立,因碑額有“流芳百代”字樣,可名之為“流芳百代”功德碑。
二是個人墓志銘或德行碑。墓志銘多由志和銘兩部分組成,志多以散文形式敘述逝者名諱、籍貫及生平事略,而銘則用韻文概括全篇,對逝者一生作出評價。安順武廟內(nèi)現(xiàn)存有“滔公和尚墓志銘序”半幢,抄錄如下:
師名深滔,字一清,嘉慶壬戌七年六月廿一日戌時于郡城西大街皇殿門口生長人氏。推本白姓,父登富,母張氏。嘉慶十五年冬十二月初八日,赴鐘山守真和尚座前披薙為徒。課頌之余,助勞創(chuàng)修本山藏經(jīng)樓。事廿一年,師命監(jiān)理三官廟,協(xié)同郡城紳士創(chuàng)建文昌宮,功成供神,兼任焚獻香燈。道光元年,師開期,得受法戒,仍歸本廟應事。八年,師復開期,職當尊證。十年,狗場眾姓迎請住持斗姆閣。十二年,轉歸本廟,兼修文昌宮前官所。廿五年,重□□宮大殿。廿九年,改造文昌宮牌□□硐石門。又咸豐七年,重□□堂金像,輝煌殿宇,兩廂房宅,新設大殿匾封,重修頭門之金匾。□當創(chuàng)置,終歸之境,略敘由來,□□□之,以俟后之得識云耳。
武廟內(nèi)又有《春漁席公明府折獄城隍廟遺思》,抄錄如下:
城隍二字始于泰爻,縣令一官昉[于]秦代,要惟有補于社稷,斯交贊夫幽明。甲戌夏,春漁席公奉檄至斯,發(fā)硎伊始,善政善教。既公頌于鼎甲之樓,余韻余情,復庚歌于城隍之廟者,緣公明如秋月,德比春風。小大之獄必以情,智珠在握。奷宄之尤未遽服,孽鏡高懸,遂乃刻意更新,早謀經(jīng)始。惜瓜期甚促,象教未竟裝潢,查城難留麟仁,多遺抱負。公今去矣,民敢忘哉!惟是藥不必多品,療病者佳;官不必三公,宜民者貴。合計公一年于茲,百廢俱舉,興學校則具少陵廣廈之心,育民生則懷白傅大裘之意。嫠婦可無泣,緯惠乃柏舟。盜賊罔敢穿窬,威加符澤,從此行春有腳,到處奉如明神。作則因心,無愧古之循吏。此特天衢之發(fā)軔,江水之濫觴矣,爰頌曰:城隍有神,縣令□□。令耶神耶,宅心不隔。安得去矣復來,補神工未了之規(guī)。
光緒二年六月吉日合郡紳耆公立
去思碑或遺思碑皆以述德為先,而兼有述德功能的數(shù)量最多的碑刻無疑是墓碑。立碑于墓前,以憑子弟后人節(jié)令祭掃,寄托哀思。甚或以彰顯宗族在村落中的地位,幾乎是屯堡區(qū)域的普遍“共識”。
此外,碑載屯堡鄉(xiāng)民入黔始祖或族中功名之裔的傳略及其支系在黔分布情形的碑刻,各村寨多亦有之,要皆以追述先祖功德為旨,亦可歸入述德類碑刻。
(四)墓碑及其他碑刻
修墓而立碑的傳統(tǒng)在屯堡區(qū)域尤其深厚,墓碑分布于地頭山腳而為村寨內(nèi)外最尋常的景觀,尤其在家族墓地,墓碑更可謂鱗次櫛比。其中,民國及現(xiàn)當代所立墓碑最多,晚清民國墓碑也不少見,清前中期甚至明代墓碑間亦有之。如安順舊州甘橖村郭院塘南面土山周家大墳處,有清代“教授周公文軒墓”,其墓碑碑身刻文:“誥授奉政晉封中憲大夫賜同進士出身鎮(zhèn)遠府教授周公文軒之墓”;上款為立碑時間“光緒丙申年嘉平月下浣立”,碑身左側列后輩子孫之名,有“男重光、耿光、錫光、恩光;孫玉麟、瑞麟、英麟、炳麟、明甫;重孫鳳岐、鳳翔、鳳錦、鳳□、鳳林、鳳池奉祀”等文字。該墳山除周文軒墓外,還有其祖輩、父輩、叔伯及子侄之墓,多亦有碑,由這些墓碑可知該族在地方的繁衍之概。周文軒,亦即周之冕,字藻庭,文軒其號也,民國續(xù)修《安順府志》有傳,云周氏“生道光甲申(1824),卒光緒己丑(1889),得年六十有五。有子四:長重光,乙亥順天舉人;耿光,處士;錫光,乙酉拔貢,刑部主事;恩光,廩生”,[5]卷六《人物志·周之冕傳》,304正與墓碑相合。諸如周家大墳一類家族墓地,屯堡村寨幾乎每村皆有數(shù)處,多歷清代民國及至今日仍屬族人葬所,民間纂修譜牒族志,地方研究家族或村落歷史,必有賴于大量墓碑文獻的支撐。
屯堡村寨之民,相當部分為明初“洪武征南”“洪武填南”而來,此為區(qū)域性共同記憶,故鄉(xiāng)民尤重入黔始祖墓、分支祖之墓、有功名之族裔之墓的修造,其墓碑亦屢經(jīng)重樹,有由明代至清代至民國至現(xiàn)今屢次改樹新碑,通過此種方式傳衍共同的家族記憶,這對明清至今屯堡社會的穩(wěn)定延續(xù)起到重要支撐作用。
與墓碑相類的是碑柱,如安順董官屯,為安順及附近地區(qū)董氏入黔始居地之一,該村董氏家族墓地有入黔始祖董成公墳塋。墓前有兩巨型石柱,底座為巨型石龜,石龜以赑屃為名。民間相傳赑屃擅長負重,故以之馱碑,有流芳百世、長久保存之寓意。在董成墓前的兩根碑柱上,分別書有“淵源肇自隴西,披堅執(zhí)銳,當年曾為明皇安社稷;支流丕振黔南,登科及第,今日尤能盛朝立功勛”的碑聯(lián)。此類碑聯(lián),有墓碑處大多有之,屬于墓碑整體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只是絕大多數(shù)并不以碑柱形式呈現(xiàn)。
安順屯堡碑刻,除上述數(shù)類,還有一些內(nèi)容、形制或篆刻背景較為特殊的碑刻,現(xiàn)以市武廟內(nèi)“關帝詩竹碑”和七眼橋塘房村“石佛寺碑記”為例說明之。
“關帝詩竹碑”,現(xiàn)存于安順武廟內(nèi)。碑額有“關帝詩竹”四個大字,碑身刻有竹,還刻有說明性文字:“弘治二年十月十八日,揚州淘河獲出環(huán)鈕共重二斤四兩”,碑右上角以“×”形式鐫文“漢壽亭侯之印”,兩行文字交叉共一“亭”字。碑左下角附詩一首,云:“不謝東君意,丹青獨立名。莫嫌孤葉淡,終久不凋零”。竹畫的右下方亦刻一方印曰“漢壽亭侯之印”。該碑因竹葉走勢組字,構思巧妙,獨具匠心。碑上之詩出自三國故事,謂劉備敗于曹操且關羽被俘,被俘之關羽備受曹操優(yōu)禮卻朝夕思歸劉備,因恐劉備疑其心跡,遂作墨竹藏詩圖(一名“風雨竹”)一幅以明志。據(jù)碑載,當系明弘治時人于揚州獲印而立碑于黔地安順以志其事,此碑之作,或為某流職官員借以紀事抒懷,亦間接說明諸葛、關羽等三國故事,早在明中期已流行于黔中一帶。詩竹碑旁又有石刻“關帝圣君像”一幢,碑額有“關帝圣君像”五字,因以名碑。該碑中間刻一方鈕,下鐫有“漢壽亭侯之印”文字的印章,再往下即關帝圣君像。
此外,武廟內(nèi)院墻根處,還有殘碑若干塊,能看到如“陸軍第四十……第三連駕駛……陶君……”“民國三十三年”等殘缺信息,聯(lián)系廟內(nèi)碑柱“先烈之血,主義之花”之聯(lián),碑柱所刻“血花園”之名,可知為抗戰(zhàn)時期黔中愛國主義教育重要陣地,抗戰(zhàn)安順籍烈士當亦于武廟內(nèi)附祀。
“石佛寺碑記”原載于石佛寺石碑,該碑最初在安順城東二十五里的七眼橋鎮(zhèn)塘房街村石佛寺發(fā)現(xiàn),本地人稱寺名“大寺廟”。石碑幾經(jīng)輾轉,現(xiàn)保存于西秀區(qū)云峰大明屯堡文化博物館內(nèi)。此碑從右至左分數(shù)排刻有:“石佛寺記”“開山第一代祖”“佛海和尚”“國公傅友德、沐英、 捐建”“大明壬午年立”等文字。但是,對于該碑,地方文史愛好者曾提出兩個疑問:其一,為何石佛寺碑記上的落款不冠以在位皇帝年號而稱“大明壬午年”呢?其二,石佛寺是否真為傅友德、沐英二人捐建,又立碑之時佛海和尚是否健在?[11]
該石佛寺,弘治《貴州圖經(jīng)新志》載作石佛庵,云:“在衛(wèi)城東二十五里阿若鋪西,庵倚孤峰,巖洞宏敞。昔人鑿石佛于崖下,前建法堂。成化十六年鎮(zhèn)守云南太監(jiān)錢能改建殿宇、僧房、廊廡、山門,為一大蘭若矣”。[10]卷十四《普定衛(wèi)軍民指揮使司·寺觀·石佛庵》,153民國《續(xù)修安順府志》亦載石佛寺:“在城東時家屯大路旁。有石佛在洞中,相傳元時飛來。居民設寺祀之。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年傅友德、沐英捐建,僧佛海住持。清康熙三年(1664年)僧道盛重修。嘉慶十三年(1808年),僧育清又重修”。[5]卷十三《名勝古跡志·石佛寺》,468石佛寺與石佛庵,雖名有寺、庵之異,然明之阿若鋪即后之時家屯,二志所載實同指一寺而言。
又明初壬午年即明建文四年(1402年),其時開拓滇黔之征南正副將軍傅友德、沐英等皆已先后故去,正值“靖難之役”最后一年,朱棣已篡位而尚未改元“永樂”,朝廷為掩“建文”年號而以“洪武”繼之,按理當作“洪武三十五年”。碑記稱明而以干支而不以“建文”紀年,說明當時已是建文四年下半季,因朱棣已篡位成功,以“建文”落款為犯忌大罪。石佛寺住持不敢落款“建文”,又不愿接受朱棣朝廷續(xù)以“洪武”年號之安排,故選擇以干支落款的折中辦法,“壬午”二字約略可見滇黔士民對明初三位君主之態(tài)度。同時,亦可推測佛海時仍存世,正是因為他身歷洪武十五年(1382年)至三十五(1402年)年前后之世事變遷,得以方外之人而一力主持如此紀年之辦法。
石佛寺于明初捐建,成化改建,捐建者傅、沐二氏及改建者錢能等,生前皆權勢煊赫且能代表朝廷顏面之人,故地方亦斷不可草草為事,歷有數(shù)年乃至十數(shù)年當在情理之中,似不因傅、沐二氏已歿而否認其捐建之功德。由明清民國地方史志可見,石佛寺自建成后一直為地方一大勝景,該寺在明初初建、明中期拓建,皆歷有年所,耗費建材、民力頗多,斷非數(shù)月年余可蕆事者。
二、黔中屯堡碑刻的價值
安順屯堡碑刻種類繁多,體量龐大,尤以屯堡村寨為最多,挖掘各類碑刻的文獻文物文化價值,對于屯堡鄉(xiāng)民、地方政府與地方文化研究單位來說,既有重要意義,也是亟待重視的工作。現(xiàn)就屯堡碑刻的學術研究價值約略言之:
第一,對研究安順地區(qū)的社會生活、風俗民情有參考價值。如武廟內(nèi)所藏兩幢“永禁估葬碑記”,明確呈現(xiàn)出晚清安順城區(qū)存在的霸估扛抬現(xiàn)象。又如雙堡“市場碑”記載雙堡基層場市開設的過程,反映出明代衛(wèi)所基層組織形態(tài)和清代中后期地方社會生活等狀況。還有安順屯堡村寨普遍存在關于各類廟宇、祠宇的“重修碑記”“重塑碑記”等,對于研究地方歷史文化有著重要的價值,如“滔公和尚墓志銘序”“石佛寺碑記”和各種形式的功德碑等,反映出地方社會的民間信仰形態(tài),屯堡社區(qū)內(nèi)部與社區(qū)之間民眾熱心公益、守望相助、積德行善的普遍行為和社會心理,而這對維系屯堡社區(qū)的穩(wěn)定和公序良俗無疑起到重要作用。
第二,對研究“大歷史”影響下的“小歷史”有重要參考價值。對于黔中屯堡地區(qū)明代以來的歷史而言,“國家話語”(國家制度)的影響且深且遠,幾乎無處不在地體現(xiàn)于屯堡民眾日常生活之中。如劉官鄉(xiāng)金齒村永興寺內(nèi)“太平天子碑”記載了驛道附近生活的民眾承擔的馬匹和人力等驛遞負擔及由此引起吏民沖突的案例,反映出安順地方賦役的民間承載形態(tài),為國家制度影響“民間”歷史的重要憑證;又如“(普定)縣城隍廟記”,記載修建城隍廟的來由及經(jīng)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晚清安順的流職官員與地方紳耆的關系。在相當數(shù)量的碑刻記載中,國家的“在場”有充分的體現(xiàn),“國家”是屯堡地域社會發(fā)展不可或缺的“基因”。這種“基因”基于屯堡區(qū)域共同的“洪武征南”的起源記憶,基于與周邊族群相比較而積淀的在科舉、仕宦、經(jīng)商及與地方官府打交道的文化心理優(yōu)勢。
第三,對于研究屯堡人的家族歷史、屯堡村落的由來和發(fā)展有重要的輔助作用。雙堡“市場碑”記載張官堡村的先民“二十姓人分編五旗,屯墾于此”,劉官鄉(xiāng)水橋組“永垂千古碑”載有“水橋合堡”“四丘”“肖家”“雙堡”“乾隆”等字樣亦可推知該碑有助于了解水橋堡及附近村寨歷史發(fā)展。他如舊州鎮(zhèn)甘橖村之周友軒墓,周文軒墓;西秀區(qū)雙堡鎮(zhèn)許官村徐氏家族墓地的墓碑、張家祖墳墓碑等,都相當程度上記載了地方重要家族代表性人物的基本履歷信息,可據(jù)之與地方史志相參照,為研究地方或家族歷史的重要參考。
第四,文學價值。安順屯堡碑刻種類多樣還體現(xiàn)在多種文體上,有敘事散文,還有詩詞、對聯(lián)、駢體散文等。如“關帝詩竹碑”所載詩句、董官屯董成墓碑柱上的對聯(lián)等。此類敘事清楚,文采斐然的碑刻,在具有歷史研究價值的同時,也具備一定的文學價值。
總之,有“石刻檔案“之稱的碑刻,因事因人因言而立碑,在黔中屯堡地域社會久遠而深厚的傳統(tǒng),故黔中地區(qū)也有數(shù)量龐大且類型多樣的碑刻留存。鑒于碑刻對于黔中傳統(tǒng)耕讀文化傳承的重要功能性價值,對于地方歷史與文化研究的文獻意義,理應加強碑刻文獻調(diào)查與輯錄。同時,相當一部分的碑刻更因涉及家族、村寨乃至地方的重要官員、知名人士,或明清以來的重要歷史節(jié)點,如洪武征南、明清鼎革、三藩之變、乾嘉苗變、咸同變亂、抗日戰(zhàn)爭等,這些碑刻更具有一定的文物保護價值,也應展開充分調(diào)查以摸清這類特殊文獻文物文化的“家底”而不至日漸損毀湮沒而徒嘆奈何。
[后記]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得到安順學院孟凡松老師的悉心指導,謹致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