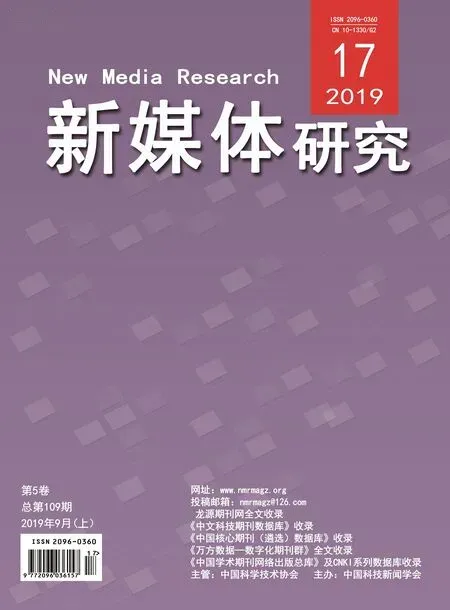娛樂的狂歡:網絡直播間里的陜北說書考察
師天武
摘? 要? 網絡直播是新興的視頻娛樂方式,一些民間藝人從中看到了新機遇。直播平臺簡單易操作,于是他們便通過直播表演的方式來推廣當地民俗,使人們足不出戶就能通過網絡平臺了解到千里之外的鄉風民俗。但這種依賴直播技術的民俗文化展演在傳播過程中也暴露出諸多現實問題。文章以網絡直播平臺上的陜北說書表演為例,淺談此類民間藝術在網絡直播過程中存在的現實困境。
關鍵詞? 直播平臺;泛娛樂化;陜北說書;藝術本真
中圖分類號? G2? ? ? 文獻標識碼? A? ? ? 文章編號? 2096-0360(2020)17-0025-03
陜北說書是流行于陜西北部榆林與延安兩地的民間說唱文學種類,是早些年間一群窮苦盲人運用當地民歌小調演唱一些民間傳說與故事而形成的藝術形式。在物質生活匱乏的年代,陜北說書是當地人們茶余飯后的主要消遣與娛樂方式。現如今,現代科技帶來了更多樣化的娛樂方式,電視、電影或者廣場舞都是目前比較主流的休閑娛樂方式,陜北說書也不再是人們休閑娛樂的唯一選擇。不過令人稍感欣慰的是,這兩年在網絡直播間里浮現出了不少以陜北說書為題材的表演。網絡直播的出現為陜北說書提供了新的表演平臺與發展契機。從線下到線上傳播策略的改變使得陜北說書的傳播范圍更廣,影響力更大,讓更多的人能借助互聯網上的各類資源直觀感受陜北說書的藝術魅力。不過這種基于網絡直播表演的陜北說書卻受到了娛樂化潮流的侵蝕,自身的藝術風格與藝術特色也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消解。
1? 泛娛樂化下的陜北說書直播
步入21世紀以來,大眾媒介呈現多種多樣的娛樂化趨勢,人們的精神與物質生活逐漸步入了泛娛樂化時代。“所謂泛娛樂化,是指以娛樂為終極目標的一種社會現象,奉行快樂至上的原則,追求及時行樂,尤其是感官的刺激體驗,秉持將娛樂進行到底的精神。”[1]一切文化內容都無聲無息甚至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這正是如今互聯網直播平臺的真實寫照。在這片“流量為王”的土壤上,消費主義和娛樂訴求正瓦解著原有的價值體系。盡管流量的確能夠反映用戶對于視頻內容的喜好程度,但其背后更多的是刻意的炒作、對事實扭曲與向市場的妥協,其衡量尺度與標準仍是一種經濟指標。對于任意一部視頻作品來說,較高的點擊與轉發評論量會引起廣告商的興趣,廣告的植入無疑給視頻制作者帶來經濟利益。部分傳統民間藝人或是出于傳播效果的考慮,或是純粹為了盈利,他們在網絡直播的表演過程中唯流量至上,在直播與創作中刻意迎合受眾與市場,傳統民俗的藝術性與歷史內涵被人為的割裂。這種流量經濟沖擊了藝術本真,使得基于直播平臺表演的民間藝術也逐漸變得面目全非。
陜北說書最初的產生是一批窮苦盲人運用當地民歌與小調演唱的一些故事和傳說,在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時期后,演變為一種新的獨立的藝術形式。隨著網絡直播熱潮的興起,許多藝人從線下演出轉向了線上表演,直播平臺上也多了許多陜北說書表演。然而直播間里的說書表演卻受到了娛樂化浪潮與流量經濟的侵蝕,許多必要文化元素被他們選擇性保留甚至完全剔除,直播平臺上殘存下來的只是作為一門說書的手藝,而且這門手藝還被人為地附著了許多純粹出于娛樂而有的特質。直播平臺上的娛樂化訴求侵蝕了陜北說書的藝術本真,這表現在其內在的書詞與音樂的使用、外在藝術表現形式和社會文化功能都在直播的過程當中損耗,導致最終呈現在觀眾面前的是不完整乃至被扭曲的陜北說書表演。
2? 直播平臺上的陜北說書形象
2.1? 合成音樂取代傳統伴奏樂器
三弦或琵琶是陜北說書表演最主要的伴奏樂器,依據藝人所使用樂器的不同,陜北說書又可以分為“三弦書”與“琵琶書”兩種流派。說書藝人在現場表演時手上撥弄著三弦或琵琶,腿上還綁著甩板。除此之外,四頁瓦、木魚、二胡、笛子、鑼也都可以作為表演時的輔助樂器,由其他藝人或助手在旁邊伴奏。但在網絡直播間里,藝人們缺乏專業的助手與足夠寬敞的場地,因此他們表演的往往是單人出場的坐場書,讓藝人們同時使用這些樂器也是不現實的。說書藝人們偶然發現他們可以借用直播平臺自帶的合成音頻來模擬現實樂器的擊打。于是他們有舍棄了一些傳統的伴奏樂器,被拋棄最多的是腿上的甩板。或許是因為電腦合成的配樂更加清晰與穩定(因為甩板在實際表演中容易出現錯打的情況),他們直接選用已經合成與錄制好的錄音來替代甩板擊打的聲音。同時他們又保留了甩板的現實存在,觀眾以為聽到的是清脆的甩板聲,實則是電腦后期模擬的音效。另一部分人更為灑脫,他們拋棄了陜北說書的所有傳統樂器,最重要三弦或琵琶也被扔到一旁,大方地拿起了話筒并走上舞臺,使陜北說書變成了陜北“演書”。但現代化的配音與伴奏最多只能當作輔助配樂的形式而存在,絕不能完全代替現實樂器。因為樂器的運用不僅是為了演奏出音樂,還是作為藝術品的存在和一種陜北民俗文化的象征,具有現實的觀賞價值。說書人懷抱三弦或琵琶,腿綁甩板,自彈自唱,從容不迫地講述故事。這種樸素且簡單的表演形式正是陜北說書的藝術特色,也是其區別于其他地域民俗文化的突出特征。基于科技的進步而簡化或拋棄原有的藝術本真,這也是目前網絡直播間里的陜北說書表演所面臨的現實問題之一。
2.2? 通俗化語言替代了陜北方言
中國地域遼闊,各地區的文化習俗與語言各有特色,因此素有“十里不同音”的說法。方言是通行于某些地區的語言,它便于當地民眾進行日常的交流。然而對于外地人來說,方言卻給他們造成了交流與理解上的障礙。陜北說書的口頭表現——陜北方言是一種使用于陜西省北部及其附近區域的漢語方言。通常來說,陜北方言除了部分山西、甘肅與內蒙古人可以聽懂外,對大部分不了解陜北文化與語言的觀眾來說都存在聽辨上的困難。直播間里的說書藝人在表演時也發現了晦澀的陜北方音會影響觀眾的欣賞效果。基于此,他們做出了兩點改變。第一是字幕的運用,在直播后生成的視頻回放中配以字幕的解說,便于觀眾更易于理解說書表演的書詞內容。但這不足以解決根本的問題,現實中部分的方言詞匯存在無法用普通話對應的問題,即使勉強對應上了,也存在理解上的困難。說書藝人們注意到這個問題后,做出了第二點改變——他們簡化或刪除了部分陜北說書用詞,用更便于聽辨與理解的詞語代替原有的晦澀用語。這種改變似乎聽起來是可行的,但在實際運用中卻被往往被藝人們過度運用,任意修改的書詞內容完全脫離了陜北說書原有的書詞程式,喪失了一種語言美。
傳統的陜北說書中有大量的“圪”頭詞的使用,陜北方言詞語的一大特點是“圪”頭詞眾多。使用“圪”頭詞,可以使音節整齊勻稱,使表意顯豁,給人以生動鮮活的感受[2]。例如:黑頭發染得白圪生生,黑襖黑褲穿一身,黑緞繡鞋腳下蹬。(《彭祖夸壽》)中的“白圪生生”。直播平臺上的某位說書藝人在表演這段《彭祖夸壽》時,無論在后期字幕還是現場的說唱中都對“圪”頭詞進行了模糊化的處理,這種做法尚待商榷。網絡直播間里的觀眾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便于他們更好地了解與欣賞,說書藝人們對部分難以理解的書詞內容做出修改,這一點可以理解。如果說這種做法是陜北說書對外“走出去”的合理傳播策略的話,那么對于陜北說書書詞與傳統口頭程式的顛覆則是走向了極端。在直播平臺上,有不少說書藝人只是借用了陜北說書的曲調與樂器,書詞的內容上則與陜北說書毫無半點瓜葛。雖然這類作品是少數,但這種“掛羊頭賣狗肉”式的作品卻獲得了不少好評與點贊,評論區固然有少部分尖銳的批評,但點贊與叫好的喧鬧還是蓋過了少數理性的聲音。這種傾向與目前互聯網的娛樂化潮流不無關系,長久來看也不利于陜北說書的生存與發展。
2.3? 社會文化功能的消解
陜北說書與河北、山東、河南等地民間說唱文學的區別,除了表演形式、說書人所使用的方言和音樂曲調外,主要在于其所蘊涵地域文化特征[3]。通過直播平臺的表演,陜北說書從線下面對面的表演轉向了熒幕前的直播,從現場化轉向了屏幕化。然而,陜北說書除了娛樂功能外,還與陜北文化密不可分,包含其他社會文化功能。陜北說書被人們冠以民間藝術,而所謂“民間”字樣,意味著它扎根于民間并與鄉土生活息息相關,除了娛樂化的功能,更多的是它在鄉土生活中扮演的社會文化功能。比如陜北說書在婚喪嫁娶儀式中的功能、在老人壽誕中的功能、在小兒滿月紀念儀式中的功能,在喬遷新居儀式中的功能,在新房奠基儀式中的功能,在廟會民間信仰儀式中的功能,在祈雨儀式中的功能等[4]。此外,按照鄉間的習俗,說書表演在開始前還會有一系列的準備環節,比如請神、參神、安神等環節。出于各種條件的限制,這些功能都無法在直播平臺上實現。而對這些非娛樂化的功能,在直播間里藝人們也往往閉口不談。失去了這種社會文化功能的陜北說書表演流失了一部分藝術觀賞價值,淪落為一門只供人取樂與消遣的傳統手藝。總之,直播平臺上的說書表演雖然取得了娛樂大眾的效果,卻丟掉了其在生活中的儀式感與社會功能,而后者才是陜北說書存在的真正藝術與社會價值。
2.4? 其他藝術形式的亂入
陜北說書只是黃土高原上眾多民間藝術的一種,與其形式上相仿的還有陜北民歌,它們都是陜北地區特有的口頭藝術。在現實生活中,許多陜北藝人們身兼數門絕活。無論是陜北說書、民歌、秧歌還是“花兒”,他們都可以在現場根據觀眾的興趣與需求隨意切換。傳統線下的表演面向的大多是陜北當地的受眾,他們自然能分得清楚陜北說書與其他陜北藝術的界限。然而,直播平臺面向的觀眾對于陜北說書的了解相對有限。筆者在某直播平臺上觀察了幾位說書藝人的表演,在標題為“陜北說書”的直播表演中,或多或少的夾雜了陜北民歌的表演。或許是由于說書表演的書詞內容較為陳舊,曲調上也頗為單一,難以對觀眾產生持久的吸引力。基于此,說書藝人們不得不各展所長,不斷豐富自己直播間的表演內容。這種做法的確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受眾關注,但卻不利于他們了解原汁原味的陜北說書。此外,還有部分藝人在說書表演時將現代歌舞融入到了陜北說書中,在說書表演時邀請了幾位專業的舞蹈演員在后場伴舞。從觀眾評論與滾動的彈幕來看,舞蹈演員吸引了觀眾的關注,自己的說書表演反倒成了陪襯。部分直播平臺里的陜北說書融合了舞蹈、表演以及舞美等藝術形式,乍一聽覺得這是陜北說書的創新,但實際上卻模糊了陜北說書的本來面貌與藝術價值。
3? 結語
隨著網絡數字技術和智能終端的發展和普及,新媒體給信息傳播帶來了巨大的變革,陜北民歌的傳播開始呈現出“平臺多樣化、傳播速度快、范圍廣、方式多元化”的特點,這“為陜北民歌的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5]相較于傳統的線下表演,網絡直播平臺的出現打破了時間與空間的界限,使得陜北說書等傳統民俗能借助開放的網絡平臺得以有效傳播。但陜北說書表演卻也受到了網絡平臺上流量經濟的沖刷與娛樂潮流的影響,因而呈現出了以下特點。
第一,陜北說書的書詞內容,特別是部分特色的方言詞匯呈現出了一種通俗化的趨勢,這是為了便于直播間里其他地區的受眾理解。但這種過度的通俗化影響到了陜北說書的藝術本真,不利于陜北說書的長期傳播與發展。
第二,直播平臺上的音樂特效與伴奏功能被說書藝人過度使用,甚至逐漸代替了傳統的說書樂器。陜北說書的傳統樂器不僅僅是為了演奏出合拍的音樂,更是作為一種陜北文化象征的存在,不應被現代科技打造出的仿真音樂所代替。
第三,陜北說書在民間生活中不僅僅是具有娛樂大眾的功能,它有著更為豐富的社會文化功能,它也是作為一種儀式感的存在。“網絡傳播的信息形態包括了文字、圖片、聲音、影像、動畫等幾乎所有的符號形式,并且能夠實現這些符號形式在同一文本中的融合。”[6]但這些符號形式都傳遞不出陜北說書在民間生活中扮演的功能。
第四,為了博得網絡觀眾的駐足與關注,直播間里的藝人在表演之余還結合自身所長融入了陜北民歌等其他藝術形式的表演,甚至是現代的歌舞。這就破壞了陜北說書的總體藝術風貌,模糊了陜北說書與其他藝術形式的界限。
總之,直播平臺上的大多數說書表演已經失去了它所依賴的文化語境,淪為純粹逗人取樂的表演。因此,如何利用好網絡直播來傳播陜北說書又是一個全新的話題。
參考文獻
[1]蔡李玲.尼爾·波茲曼文化娛樂思想研究[D].福州:福建師范大學,2016.
[2]汪東鋒,梁蕓霞.試論陜北說書的語言藝術[J].榆林學院學報,2020(1):25-26.
[3]趙學清,孫鴻亮.社會語言學視角下地民俗語言研究方法[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2):150-154.
[4]郭明軍.山西介休三弦書的宗教內涵與社會功能論析[J].宗教學研究,2017(3):265-270.
[5]蘇曉暹,滕文莉,楊程茜.新媒體環境下陜北民歌傳播的困境與對策[J].今傳媒,2018(7)69-70.
[6]郭慶光.傳播學教程[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