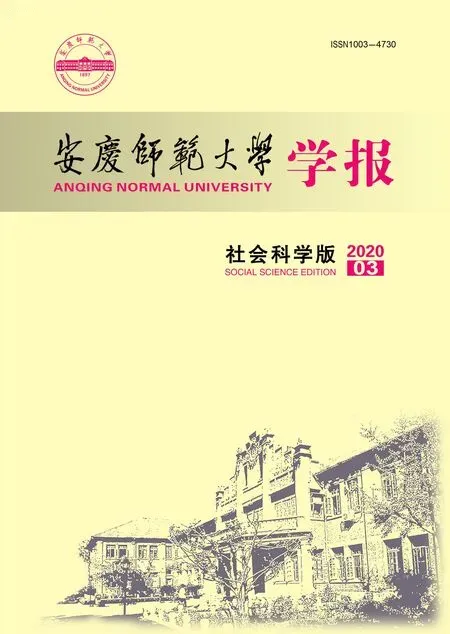公共危機視域下新自由主義的本質
羅 弋,羅本琦
(1.合肥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安徽合肥230009;2.安慶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安徽安慶246133)
新自由主義發端于20世紀30年代,從一開始就是作為凱恩斯國家干預主義的對立面,同時也作為與社會主義對立的經濟理論而存在,從而決定了新自由主義不僅僅是一種經濟理論,也是政治意識形態。其基本思想有三:在經濟理論方面宣揚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在政治理論方面否定公有制、否定社會主義、否定國家干預;在戰略和政策方面鼓吹以超級大國為主導的全球一體化。當新自由主義隨著全球化的浪潮被推廣到資本主義世界之外時,它的政治功能便更加凸現出來,因為新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輸出的其他“主義”乃至資本、制度等等一樣,都不過是某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推行霸權主義的工具,是他們為實現其國際政治目的而制造公共危機的手段。近百年的歷史已經證明并繼續證明,新自由主義還是人類應對公共危機的重大障礙。
一、霸權主義的工具
霸權主義指國際關系中大國、強國憑借軍事和經濟實力,超越國際法、國際政治格局現狀擴張勢力范圍,操縱國際事務,干涉他國內政,甚至進行武裝侵略和占領,稱霸世界、主宰世界的強權政治、強權政策。霸權主義作為國際關系中的現象抑或作為一個概念的提出,都與資本主義有著內在聯系。從理論上說,資本主義的邏輯與霸權主義的邏輯有著天然的內在一致性;從歷史上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從一開始就把霸權主義作為他們對外關系的基本戰略。從資本與制度的輸出到意識形態滲透,都成為推行霸權主義的手段。
資本主義的邏輯與霸權主義的邏輯有著天然的內在一致性,因為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與人性的貪欲以及人性的種種罪惡的張揚是分不開的。當文藝復興的思想家們把人性的尊嚴與價值從封建面具里剝離出來并高歌人性的光輝時,他們并沒有注意到抑或有選擇地遺忘了人性中還有丑惡的一面。伴隨著文藝復興的傳播,早期資產階級原始積累不斷擴大與人的私欲不斷膨脹以及物質享受和奢靡泛濫,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無節制的私欲與資本的結合決定了資本主義必然以利益的無限增殖為終極目的,對外擴張與霸權自然是資本主義發展“應有之義”。正如馬克思曾指出的那樣:“如果有20%的利潤,資本就會蠢蠢欲動;如果有50%的利潤,資本就會冒險;如果有100%的利潤,資本就敢于冒絞首的危險;如果有300%的利潤,資本就敢于踐踏人間一切的法律。”[1]事實上,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透過人文主義的表象,我們不難看到日益膨脹的冒險主義、利己主義,這些冠之以“時代精神”的“主義”與資本的原始積累高度結合,構成歐洲向世界擴張的原動力,從而也決定了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跨越是跟歐洲國家的資本原始積累及其海外擴張分不開的。考察資本主義的歷史,本質上就是謀求世界霸權、爭奪世界霸權的歷史。在霸權主義思維下,一切理論、制度與資本都演變成為實現霸權的工具。
至于“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的前身——本來就是霸權主義的一奶同胞,是資本主義理論的核心,是資本主義踐行霸權主義、對外擴張的理論依據和遮羞布。雖然“自由主義”到啟蒙運動時期才被正式升華為資本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自由主義。但早在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者們就把它作為與封建主義斗爭的武器。早期的資產階級就已經自覺地用它的基本思想武裝自己。從公元1500 年左右開始,歐洲殖民者就在自由主義精神的激勵下(本質上說是在利益的驅使下)為開拓市場“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2]。正是在自由主義旗幟下,資產階級用了不到四百年的時間就瓜分了整個世界。只是隨著資本主義內部危機的惡化,隨著社會主義的崛起,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們才在對自由主義的檢討中構建了一個“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依然扮演著霸權主義工具的角色。在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陷入“經濟滯脹”的背景下產生的“華盛頓共識”就是美國的金融霸權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結合的典范。20世紀70年代末,西方壟斷資本操縱的一些國際經濟組織曾在華盛頓達成了一系列共識,核心內容就是將“新自由主義”作為其改革藥方向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推薦。在20世紀70至90年代期間,美國控制的國際金融組織向所有遭遇經濟危機而借貸的國家強制推銷美國精英精心準備的所謂宏觀經濟政策。
新自由主義所蘊含的“自由”在現實世界是以實現美國金融霸權的“自由”為核心的。美國反對貨幣貶值,貨幣穩定便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規定。當債務國貨幣貶值能為美國帶來巨大收益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又強迫債務國實行貨幣貶值。顯然,美國從來都不是遵守國際法,維持世界平衡的“正義的世界警察”,而是雙重標準行事,將新自由主義作為霸權主義工具的國家。新自由主義與霸權主義結合的原理通過“華盛頓共識”的推廣而呈現得十分清晰:
第一,美國向全世界兜售的“華盛頓共識”,致力于實施貿易自由,開放市場。按照“共識”,急需發展農業生產的發展中國家必須敞開市場,進行自由貿易,但美國自己不會更改貿易協定中的農業保護主義,實際上美國自己在實現農業現代化道路上就對投資進行高額補貼。那些第三世界國家如果要解決糧食作物缺乏問題,就要套用歐美成功的模板:提供保護性關稅,對投資進行補貼,從而跳入新自由主義的陷阱。第二,“華盛頓共識”要求接受“共識”的國家放松對外資的限制。美國自己的重要行業的安全是十分重視的,即便國際收支赤字不斷提升,也不可能讓自己的關鍵領域資產,如航空、銀行、軍事和科技公司被外國人收購。但熱衷于對別國重要領域的資產大肆收購,以實現對其關鍵部門的控制。常用的手段是,伙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貸款、投資等強迫第三世界國家接受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策略,憑借對國際金融組織的操縱,制定符合自己利益需求的援助政策,以實現對別國經濟主權的控制,既為國際金融資本開辟了自由市場也限制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半個多世紀以來,新自由主義作為美國霸權主義的工具,成功地遏制了二戰以后其他國家快速發展的勢頭。
二、制造公共危機的手段
新自由主義產生后就被少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奉為圣經,并努力推廣到發展中國家乃至敵對國家。但其目的絕不是象他們標榜的那樣,是為了幫助其他國家謀求發展。半個多世紀以來,新自由主義的觸角伸向全球各地。實踐證明,無論南美國家、俄羅斯還是東南亞等國家,按照新自由主義所規劃的路線進行改革的,無一例外都造成了國內嚴重的公共危機。
我們不妨回顧一下20世紀中期以來新自由主義輸出及其造成的后果。
先看一看新自由主義在南美的實踐。南美洲國家基本上都經歷過殖民統治,因此形成了經濟社會的發展對發達的“中心”國家的依附定勢。獨立之后的南美諸國雖然政治上的獨立了,社會與經濟上的先天劣勢決定了他們還得依靠發達的“中心”國家的支持,當然接收新自由主義思想是先決條件。阿根廷曾經被認為是實行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樣板。20 世紀80 年代后的阿根廷政府對“華盛頓共識”深信不疑,開始按照新自由主義的標準實現國企私有化、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和投資自由化,出售了大部分關系國家經濟命脈的國有企業和金融銀行。阿根廷最大的十家銀行大部分為外資控股。外資銀行順利“接管”阿根廷金融陣地后立即通過經營阿根廷比索與美元之間的業務,不斷擴大美元流量,實現對阿根廷金融銀行領域的控制,削弱政府失調控金融的能力,進而成功實現“鳩占鵲巢”。當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機爆發時,政府只能等待國際金融機構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貸款緩解危機。但他們等來的不是曾經的援助承諾,而是用國有資產進行抵押貸款。于是,阿根廷失去了幾乎所有的國有資產,因為無力進一步獲得抵押貸款,金融危機加劇,經濟狀況一落千丈,貧窮和饑餓席卷全國。據統計,1980 年至1992 年的十多年間,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南美國家貧困人口,從1.36億猛增到2.66億[3]。
新自由主義在蘇聯的實踐有著更豐富的內涵。蘇聯解體是霸權主義勝利,它證明了新自由主義在制造公共危機進而削弱敵國國力方面巨大的功能。20 世紀初,第一個社會主義政權建立起來以后,資本主義世界曾聯合武裝鎮壓,也曾嘗試“經濟戰”“金融貨幣戰”“軍備競賽”“輿論戰”等一系列手段,都沒有實現扼殺這一新生政權的目的。但卻成功地通過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滲透實現了肢解蘇聯的目的。正如前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所說:“我們一直采取行動,削弱蘇聯經濟,但是遺憾的是,無論我們怎么努力,蘇聯的政治形勢長期保持十分穩定,我們陷入了困境。不過很快我們得到情報,說蘇聯領袖逝世后,經我們幫助的人可以繼任,借助他能夠實現我們的想法,這個人就是戈爾巴喬夫。”[4]20 世紀80 年代中期蘇聯的改革,雖然是在社會主義旗幟下進行,時任蘇聯領導人已經不知不覺地接受了新自由主義,并將新自由主義的精神融入改革實踐當中。反省蘇聯解體前的改革措施,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都是新自由主義的翻版。經濟改革的“500 天計劃”直接針對“公有制壟斷”,完全是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徹底顛覆了社會主義經濟,直接地在經濟基礎上促使了蘇聯的解體。意識形態的多元化以及放棄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則直接迎合了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目標。因而,加拿大的經濟學家邁克爾·萊博維茨說:“當蘇共黨內的主導勢力更多地趨向于遵從資本主義邏輯時,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必定走向終結。”[4]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新自由主義實踐在世界各地造成的公共危機正是少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目的。通過制造公共危機以搞亂別國社會秩序,進而實現削弱敵國勢力或控制敵國的目的,是霸權主義的行為模式之一,輸出意識形態則是制造公共危機進而實現這一目的手段。
為什么選擇制造公共危機的方式達成目的?新自由主義何以能夠制造公共危機?
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因為公共危機是社會運行過程中發生的可能危及公共安全和正常秩序的危機事件。公共危機指向對象是特定區域的所有公民,容易引發社會恐慌。公共危機可能造成巨大的社會破壞,因而,能否處理好公共性危機被視為考驗政府執政能力的重要指標,成為民眾評價政府的重要參數。一場公共危機造成的實際破壞力——包括對社會的破壞和對政府的影響,往往超過一場戰爭,而引發公共危機的成本則遠遠小于一場戰爭。殖民時代結束以后,隨著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制度及意識形態對立的產生和發展,這種行為模式便被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廣泛使用。
新自由主義之所以能夠制造公共危機,則需要從意識形態的對抗性以及社會穩定機制中求解。每一個國家或社會都是一個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建立起來的穩定的系統。國家或社會的穩定性取決于經濟社會文化政治等各種要素的協調。其中,文化是受歷史影響最為深遠并難以改造的要素,同時也是一旦受到沖擊則破壞性不可估量且難以復原的要素。或許正因為如此,早在殖民時代早期,歐洲殖民者們就在武裝殖民的同時,不遺余力的把他們的某此文化元素傳播到世界各地。20世紀以后的世界文化交流中,意識形態(特別是政治意識形態)的作用備受關注,自然在選擇文化武器時被作為首選。在一個國家中只要成功培養一批持異端立場者,就為造成公共危機創造了可能。正如美國前中央報局局長羅伯特·蓋茨在談到蘇聯時所說:“我們知道,無論施加經濟壓力還是進行軍備競賽,甚至用武力也拿不下來。只能通過內部爆炸來毀滅它。”[4]由于新自由主義宣傳的欺騙性,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的推銷與貸款等經濟支持或相關“援助”是捆綁操作,而且伴隨著對相關力量的額外扶持,從而使新自由主義在異國他鄉被接受的概率大大提高。
三、人類應對公共危機的障礙
在國際關系的實踐中,基于新自由主義的本質和公共危機的特點,新自由主義常常被改造為制造公共危機的手段。基于同樣的原因,當公共危機發生時,新自由主義又成為人類應對危機的障礙,阻礙人類命運共同體健康發展。
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在用生命的代價證明著這一事實。當中國政府和人民全力投入疫情防控時,一些國外媒體卻用所謂“人權”對中國的防控措施指手畫腳。當疫情在歐美世界局部地區漫延時,從民眾到政府,非但沒有引起警惕,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有人通過“舔馬桶”向“新冠病毒挑戰”,有人聲稱“既使得了新冠,也不能阻止我去參加聚會!”在西歐和美國都發生了數萬人規模的游行或刻意組織的聚會,以彰顯“自由”。有些國家政府則糾纏不同制度和意識形態之分,不是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民生命健康,而是念念不忘重啟經濟、恢復商業。全球疫情爆發背景下這種種現象的背后,實際上都是根深蒂固的新自由主義觀念。民間對“新冠病毒挑戰”也好,官方念念不忘的經濟重啟也罷,都不過是新自由主義追求的所謂“自由”和利益至上的價值目標的體現。
如果把視野再拉長一點,我們會發現,早在數年前,新自由主義就為歐美社會應對公共危機埋下隱患。有研究表明,無論是歐洲的英、法、意等國還是美國,在過去的十余年中都在擴大私有化領域,把更多的公共服務投入交給私人去做,這一政策直接后果就是公共服務投入下降,據統計,當下疫情最突出的國家,也正是公共服務投入下降最突出的國家。有專家撰文指出:“英國疫情迅速加劇,國家束手無策的最大的原因是公共服務過度私有化,特別是國民健康服務體系(NHS)的過度私有化和低預算進而引發的全民公共衛生安全危機。”[5]
客觀地說,新自由主義成為人類應對公共危機的障礙,并非某些國家的主觀愿望。少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外推銷新自由主義,固然有通過意識形態滲透他國制造公共危機以實現其政治目的之動機。但他們或者未曾想到被他們奉為圣經的新自由主義會成為他們自己應對公共危機的障礙。但這場全人類的公共衛生危機不可阻擋地檢驗著每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檢驗著每一種價值體系或理論形態。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事實證明:新自由主義強化個體利益與自由,無視或者淡化公共利益與秩序,而公共危機恰恰是不分高低貴賤一視同仁的,新自由主義與公共危機客觀上相輔相成,而與人類應對公共危機行為針鋒相對。實踐證明:應對公共危機需要人類共同的一致的協同行動,放棄暫時的狹隘的自由才能保障更長久的大眾的自由,犧牲眼前的經濟利益才能贏得長遠的可持續的發展。實踐證明:私有化框架內構建不了應對公共危機所需要的治理體系和服務體系,加強國家主導的公共衛生系統建設和相關生產服務體系的完善,是人類應對未來公共危機的不二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