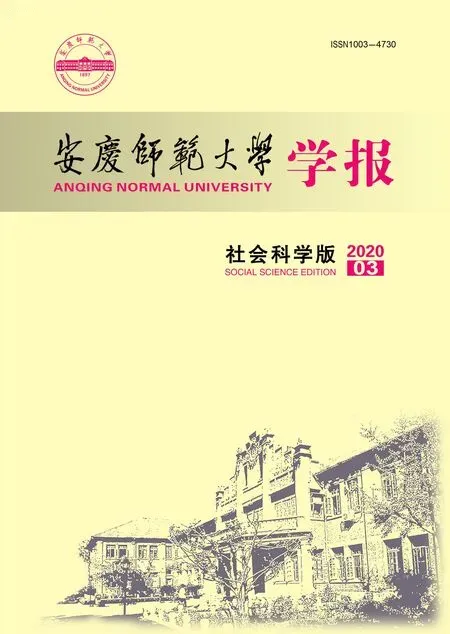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的史學價值
范宇焜
(太原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山西太原030024)
《漢書》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在中國史學史上有很高地位,班固在繼承紀傳體史書撰寫方法的基礎上,開創了皇朝史撰述的格局,歷代“諸儒共所鉆仰”[1]。東漢至南北朝時期,不斷有學者對《漢書》進行注音和釋義,約三十余家。隋唐之際,以劉臻、蕭該、包愷為代表的學者以治《漢書》而聞名于世,繼而有顏師古繼承家學,鉆研《漢書》,并吸收前人研究《漢書》的成果,撰成《漢書注》,成為“漢書學”的一代宗師。《漢書》開創了中國古代正史的撰述格局,其“漢紹堯運”的內在精神符合中國古代皇朝統治的需求,輔以其“言皆精練,事甚該密”[2]20-21的歷史敘事方法,使得古代正史撰述“自爾迄今,無改斯道。”[2]20-21《漢書》在思想與技術層面的特點,使其在兩宋時期成為學人研究的一個重點,產生一些“漢書學”研究專書,南宋學者王應麟的《漢藝文志考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筆者從宋代“漢書學”發展的視野,就《漢藝文志考證》的“漢書學”價值展開討論,以就教于方家。
一、文化復古與漢書學
王應麟(1223—1296),字伯厚,號深寧居士,慶元府(今浙江寧波)人,淳祐元年(1241)舉進士。《宋史·儒林列傳》記載王應麟少通六經,著有《深寧集》一百卷、《困學紀聞》二十卷、《詩考》五卷、《漢藝文藝志考證》十卷、《通鑒地理考》一百卷、《漢制考》四卷、《小學紺珠》十卷、《玉海》二百卷等,共計二十二部。王應麟非常重視對漢代制度、名物的考證,在《漢制考》中,他引用許多經書、經注。《漢書·藝文志》在《七略》的基礎上,“刪其要,以備篇籍”,開創中國古代正史《藝文志》的先河,著錄了先秦至西漢時期的眾多典籍,是歷史上最早的目錄學文獻。《漢書·藝文志》的這一特點為王應麟所重視,他撰寫《漢藝文志考證》十卷,明確地以專題研究的形式對《漢書·藝文志》中的相關內容展開考據。這使王應麟成為宋元“漢書學”的代表人物之一。《漢藝文志考證》在考證對象及研究方法方面具有鮮明的特點,對其后的文獻考據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宋代文化復古的傾向彌漫于整個社會,這使得王應麟本人對漢代制度有著非常濃厚的興趣,進而依托《漢書》文本展開研究,這使他有撰寫《漢藝文志考證》的基礎。宋代統治集團對三代制度十分向往,這反映在社會文化方面是宋代成為歷史上仿制三代禮器的高峰期。兩宋時期官府與民間仿制的三代青銅器據統計數量達六百余件[3],宋代仿古青銅器的制造與這一時期金石學的興起相互促進,在學術上形成考三代典章,復三代禮制的風氣[4]。宋人對三代制度的追慕,又是以考察漢代制度為主要依托的,這種傾向從王應麟所作《漢制考自序》中可窺一二。王應麟在《漢制考自序》中講到三代禮法的發展,顯現出他對三代禮法的推崇,他認為禮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三代損益,至周大備。夫子從周與從先進之言,所謂百世可知者,其法著于《春秋》”。至周平王東遷之初,由于“守古之士猶多”,還可以保證“則封建之制猶可尋也”,而到春秋時期,齊國管仲“作內政而寄軍令”破壞了以往的兵制,晉國施行爰田制破壞了故有的經濟制度,晉文公設執秩官主管爵秩改變了舊的官制,鄭國鑄造刑書而使法律制度產生變革。這些行為在王應麟看來導致了“禮幾亡矣”,他雖然懷念三代禮法,但一定程度上也認識到歷史變化的法則,他說:“生民之理有窮,則圣王之法可改,古其不可復乎。”[5]1-2在他看來,宋代距三代太過久遠了,很多當時的情況無從知曉,而通過漢代典章制度了解三代制度就成為一條非常好的途徑,他說:
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猶近于書之典誥也;郎衛執戟之用儒生,猶近于王宮之士庶子也;司徒府有百官朝會殿以決大事,猶近于外朝之詢眾也;牧守有子孫,郡國有辟舉,庶幾建侯之舊;丞相進見,御坐為起,在輿為下,庶幾敬臣之意。三老掌教化,孝悌力田置常員,鄉遂之流風遺韻亦間見焉。是之取爾,君子尚論古之人,以為漢去古未遠,諸儒占畢訓故之學,雖未盡識三代舊典,而以漢制證遺經,猶幸有傳注在也。冕服、車旗、彝器之類,多以叔孫通禮器制度為據,其所臆度無以名之,則謂若今某物。及唐儒為疏義,又謂去漢久遠,雖漢法亦不可考。蓋自西晉板蕩之后,見聞放失,習俗流敗,漢世之名物稱謂知者鮮焉,況帝王制作之法象意義乎!此漢制之僅存于傳注者不可忽、不之考也[5]3-4。
王應麟列舉漢代皇帝親自撰寫詔書等事例,與古制相比較,認為在很多方面具有相似之處,漢代諸儒“雖未盡識三代舊典”,但通過這一時期的傳注,仍然可以“以漢制證遺經”。王應麟指出這條通曉三代禮法的途徑后,又提到自西晉滅亡后,通曉漢代名物稱謂的人十分罕見,鑒于“漢制載于史者,先儒考之詳矣,其見他書者,未之考也”的情況,他撰寫了《漢制考》一書。王應麟充分論述了漢代制度與三代禮法的關系,為實現追慕古風的目的,就必須考察漢代制度,而考察漢代制度自離不開研讀《漢書》諸志書,在此過程中,為了盡可能還原漢代制度的樣貌,就不得不對相關文獻作梳理及考察。如此看來,在《漢制考》和《漢藝文志考證》成書時間尚不確切的情況下,《漢藝文志考證》有可能是王應麟漢代制度研究的“副產品”,但無論如何,《漢藝文志考證》是王應麟“漢書學”研究興趣下的產物。
二、考證類型與方法
這里,先論《漢藝文志考證》的考證類型與方法。
《漢藝文志考證》是中國歷史上首次對《漢書·藝文志》展開的專門系統研究。具體來說,《漢藝文志考證》的考證對象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是對《漢書·藝文志》著錄典籍的考證,其二是對《漢書·藝文志》各序記載歷史情況的考察。
從《漢藝文志考證》對典籍的考證來說,《漢書·藝文志》共計一萬五千余字,所著錄典籍近六百種。據筆者統計,《漢藝文志考證》對其中二百九十余種進行考證,典籍數量上不及《漢志》一半,但篇幅上約是《漢志》的四倍。王應麟嚴格按照《漢書·藝文志》所著錄典籍的順序,將他認為需要考證的條目摘取出來,進行解釋說明。對于不同類型的典籍,王應麟基本上采取一視同仁的態度。歷代學人對《六藝略》下著錄的儒家經典發論較多,為王應麟所重視。而對于《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諸略下著錄的典籍,王應麟也進行了仔細的考訂,這顯現出他在文獻考據方面的深厚素養。王應麟對《漢書·藝文志》的考證主要有以下三種類型:
其一是訂正《漢書·藝文志》所著錄典籍的訛誤。如《漢書·藝文志》記載:“《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6]1709在南宋嘉定十七年白鷺洲本《漢書》中,此條下已有劉敞注曰:“當作十七,計其篇數則然。”[7]但沒有關于這一說法的進一步解釋。王應麟從劉敞說,并展開考證,他援引《漢書·儒林列傳》的記載:“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按今《儀禮》,《士禮》有《冠》、《昏》、《相見》、《喪》、《夕》、《虞》、《特牲饋食》七篇,他皆天子、諸侯、卿大夫禮。”又引南宋《儀禮》學者張淳的論斷:“漢初未有《儀禮》之名,疑后漢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也。”[8]156通過王應麟的考據,訂正了《漢書》中“《經》七十篇”的說法,今中華書局本《漢書》雖未錄劉敞注文,但已經吸收了十七篇的觀點。
其二是對著錄典籍相關歷史情況的考證。《史記》在《漢書·藝文志》中著錄于《六藝略·春秋》下,該條目下稱《史記》“十篇有錄無書”。王應麟用不少筆墨考證了這一問題,《漢藝文志考證》記載:
東萊呂氏曰:“以張晏所列亡篇之目,校之《史記》,或其篇具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無書也。其一曰《景紀》,此其篇具在者也,所載間有班書所無者。其二曰《武紀》十篇,唯此篇亡。衛宏《漢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本紀,極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過,武帝怒而削去之。’衛宏與班固同時,是時兩紀俱亡,今《景紀》所以復出者,武帝特能毀其副在京師者耳,藏之名山固自有他本也。《武紀》終不見者,豈非指切尤甚,雖民間亦畏禍,而不敢藏乎?其三曰《漢興以來將相年表》,其書具在,但前闕敘。其四曰《禮書》其敘具在,自‘禮由人起’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五曰《樂書》,其敘具在,自‘凡音之起’而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六曰《律書》,其敘具在,自書曰‘七正,二十八舍’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七曰《三王世家》,其書雖亡,然敘傳云‘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則其所載不過奏請及策書。或如《五宗世家》,其首略敘,其所自出亦未可知也。贊乃真太史公語也。其八曰《傅靳蒯成列傳》,此其篇具在,而無刓缺者也。張晏乃謂褚先生所補,褚先生論著附見《史記》者甚多,試取一二條與此傳并觀之,則雅俗工拙自可了矣。其九曰《日者列傳》,自‘余志而著之’以上皆太史公本書。其十曰《龜策列傳》,其序具在,自‘褚先生曰’以下乃其所補爾。方班固時,東觀、蘭臺所藏十篇,雖有錄無書,正如古文尚書,兩漢諸儒皆未嘗見,至江左始盛行,固不可以其晚出,遂疑以為偽書也。”[8]176-177
《漢書·藝文志》記載《史記》另有十篇“有錄無書”,張晏在《漢書·司馬遷傳》注中說:“遷沒之后,《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間,儲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9]顏師古作注時除指出張晏“《兵書》”亡佚有誤外,其余皆從張說,認為其中四篇是褚少孫偽作,《史記索隱》、《史記集解》也都從此說,《史記》缺佚十篇的結論似已確鑿。至唐代,劉知幾認為:“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錄而已。”[2]313宋代以前,關于《史記》“有錄無書”的問題,至少存在十篇缺佚或十篇未成兩種說法,但王應麟都不認同,他引用呂祖謙的說法闡明自己的觀點,對張晏提及的十篇逐一考證,其結論是:一是依據衛宏《漢舊儀注》,十篇中僅有《五帝本紀》缺佚;《三王世家》雖也已不存,但其中記載的僅是奏策罷了,其贊為司馬遷所作。二是《景紀》、《漢興以來將相年表》、《傅靳蒯成列傳》都是司馬遷自己的手筆。三是認為《禮書》、《樂書》、《律書》中的一部分為司馬遷所作,其余則“草具而未成”。四是指出《日者列傳》、《龜策列傳》除去“褚先生曰”的部分都是司馬遷所作。得出這樣的結論,其依據首先是《漢舊儀注》。其次是以“褚先生曰”的部分與司馬遷的記載相比較,從褚少孫與司馬遷文辭特點差距的角度進行推測。再次是以古文《尚書》的流傳情況相類比,推斷《史記》十篇沒有亡佚的可能性。王應麟在“《太史公》”條下的考證內容皆引呂祖謙《東萊別集》中的內容[10],自己并未發論。面對前人的種種結論,呂祖謙沒有實際的證據佐證其觀點。但王應麟獨引呂說,無疑說明他對這一問題的見解。從《漢藝文志考證》引呂祖謙考《史記》語以后,關于《史記》十篇缺佚狀況的討論成為學術界關注的問題,直至清代,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梁玉繩在《史記志疑》中,都受呂祖謙和王應麟觀點的影響,認為《史記》十篇是部分亡佚。近人余嘉錫專作《太史公書亡篇考》[11],對此問題有細致的分析。《漢藝文志考證》對典籍的考證內容于王應麟的學術研究有重要意義,經研究者統計,在他所編類書《玉海》中,關于典籍的考證內容與《漢藝文志考證》相同或相似的達一百八十余條[12]。
其三是對《漢書·藝文志》各篇序文所記載歷史情況的考察。在此過程中,王應麟注意考鏡其源流。如對《漢書·藝文志》載“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6]1707這一說法,王應麟引用《東觀漢記》、《漢書》顏師古注、《漢書決疑》、《史通》等多種文獻材料,列舉古文《尚書》為孔子后人孔鮒所藏或孔惠所藏兩種觀點,對史料中記載的具體情況進行對照[8]143。王應麟對古文《尚書》的真偽并無任何懷疑,而是將注意力放在發現古文《尚書》的過程上。這里需要說明的是,王應麟所引《漢書決疑》的觀點,源于《隋書·經籍志》中的記載,《隋書·經籍志》成于唐高宗顯慶元年(656 年),而顏師古于貞觀十九年(645)年已經去世,以此可以推定,王應麟這里所引用的《決疑》非顏游秦所作,而是指南宋時王逨所撰《西漢決疑》,今《西漢決疑》已佚,《漢藝文志考證》尚錄有兩條《西漢決疑》的觀點,也顯現出《漢藝文志考證》的文獻價值。
在考證《漢志》各序所記載的歷史情況時,王應麟注重這些歷史情況在宋代的影響,如他對《漢書·藝文志》道家小序中“法家者流蓋出于理官”[6]1736的說法展開考證:
范氏曰:“申、韓本于老子,李斯出于荀卿,學者失其淵源,其末流將無所不至。”朱文公曰:“申、韓之學淺于楊、墨。”東萊呂氏曰:“《六經》孔孟子之教,與人之公心合,故治世宗之。申、商、韓非之説與人之私情合,故末世宗之。”兼山黃氏曰:“九家之學,今存者獨刑名家而止耳,佛老氏而止耳。髙者喜談佛老,而下者或習刑名,故兩家之説獨存于世。秦、梁至于敗亡。”蘇氏曰:“自漢以來,學者雖鄙申、韓不取,然世主心悅其言,而陰用之。小人之欲得君者,必私習其說,或誦言稱舉之,故其學至于今猶行也。”[6]233
按照王應麟所引順序,分別引用了范祖禹、朱熹、呂祖謙、黃裳、蘇軾關于法家學說的言論,這些觀點無一例外都是宋代學人所作,總體來看都是承認法家學說在宋代社會中的位置,并分析法家學說能夠流傳并為時人接受的原因。這一歷史情況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認識有很大不同,今有學者從專業研究的角度也注意到了這一問題[13]。王應麟的考訂使人對法家“蓋出于理官”的記載有更深刻的認識,同時能夠了解法家學說在宋代的發展狀況。這顯現出王應麟考證與宋代社會狀況密切結合的時代感。
由以上三種考證類型來看,王應麟的考證方法具有鮮明的特點。一方面是王應麟大量援引他人學說,自己很少發論。清代學者王鳴盛評價《漢藝文志考證》說王應麟“所采掇亦甚博雅”[14]。王應麟所選取的材料大多出處明確,觀點鮮明,這使《漢藝文志考證》的具備較高的學術價值。大量對他人觀點的引用并不意味著《漢藝文志考證》僅是一部學說的匯編,如《史記》亡佚十篇的問題在宋代以前就至少有兩種說法,古文《尚書》的真偽宋人亦有質疑,王應麟在不同說法的基礎上考證,遴選出他認為可信的觀點進行輯錄;又如《漢藝文志考證》和《玉海》中都有關于《子夏易傳》的考證,在以材料廣博著稱的類書《玉海》中,關于《子夏易傳》的解釋收錄有《唐會要》《中興館閣書目》《周易正義》《舊唐書·經籍志》《國史志》《孔子家語》《郡齋讀書志》以及程迥、朱震等多種觀點,《漢藝文志考證》中則對以上幾家觀點不予采納,這無疑反映出王應麟對這一問題的學術見解。另一方面是王應麟援引眾家說法時,特別重視宋代學人的觀點。王應麟所引廣博,無論是出自史學家、文學家或是理學家,只要是他所見到的,對考證問題有意義的說法都被收錄進來,所引宋代人觀點出自歐陽修、司馬光、邵雍、鄭樵、沈括、“三蘇”、陸游、程頤、程大昌、楊時、晁說之、呂祖謙、朱熹、洪邁、朱震、孫坦、葉夢得、周必大等等,共計五十余家。可以說,《漢藝文志考證》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宋代學人觀點基礎上的考證,所考內容不限于文獻,王應麟對許多學術問題的精當考證在宋代學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三、研究范疇及其影響
在對《漢書·藝文志》進行細致梳理、考訂的基礎上,王應麟進而輯補,這已超越了一般意義上“考證”的范疇。
王應麟將“其傳記有此書而《漢志》不載者亦以類附入……凡二十六部(實二十七部)。各疏其所注于下而以‘不著錄’字別之其間。”[15]在補錄《漢書·藝文志》時,王應麟的態度嚴謹而慎重,如“《子夏易傳》”條即是突出一例:
《子夏易傳》不著錄
《隋志》:《周易》二卷,《子夏傳》殘缺,梁六卷。《釋文序錄》:《子夏易傳》三卷,卜商。《七略》云:“漢興韓嬰傳。”《中經簿錄》云:“丁寬作。”張璠云:“或馯臂子弓所作,薛虞記。”《唐志》二志,今本十卷。案陸徳明《音義》云:“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故曰比。”今本作“地藏水而澤,水得地而安”,但小異爾。“束帛戔戔”作“殘殘”。又云“五匹為束三玄二,纁象陰陽”,今本無此文,蓋后人附益者多。景迂晁氏曰:“唐張弧偽作。”孫氏曰:“漢杜子夏之學。”唐司馬氏曰:“《七略》有子夏傳。”《十録》六卷或云韓嬰,或云丁寬。《中經簿》四卷[8]132-133。
關于《子夏易傳》的真偽問題,學術界至今尚存爭論,學者們或認為《子夏易傳》為真本,或認定是唐代張弧偽作,或認為是除張弧外的其他人偽作[16]。王應麟在補錄“《子夏易傳》”條時已經注意到關于其作者、卷數的多種說法,他引用唐人陸德明和北宋學者景迂晁氏(晁說之)的觀點,認為《子夏易傳》或存在后人附會的內容,或為唐張弧偽作。王應麟無法判斷各家說法是否正確,但他補錄此條,認定《子夏易傳》應是是先秦時期的一部重要經傳。陳振孫在《直齋書錄解題》中亦著錄《子夏易傳》,他與王應麟有著同樣的疑惑:“隋、唐時止二卷,已殘缺,今安得有十卷?”[17]4陳振孫同援引晁說之的說法,但他亦無法作出最終判斷,“姑存之以備一家”[17]4。王應麟補錄“《子夏易傳》”條時,對于此書流傳至宋代的真偽,持相當謹慎的態度。關于《子夏易傳》的本來面貌,仍將是學術界繼續探討的問題。王應麟對《漢書·藝文志》典籍的補錄是建立在“有”或“無”判斷基礎上的,他對于相關典籍真偽等問題,在廣求異說的基礎上并未作進一步論斷。
王應麟在補錄《漢書·藝文志》條目的基礎上對一些典籍作輯佚。經部著作是王應麟輯佚的重點。如《漢書·藝文志》中《六藝·易》下不著錄“《連山》、《歸藏》”,王應麟補錄此條,引桓譚《新論》曰:“《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漢世蓋有二易矣。”[8]130-131并指出有隋人劉炫偽作的十卷《連山》,《歸藏》至當時僅存《初經》《齊母》《本蓍》三篇。對這兩部已經亡佚的易書,王應麟予以輯佚,通過《水經注》和《帝王世紀》所引內容輯出《連山》佚文兩條,又通過《爾雅疏》、傳注、《周易·明夷》中的記載輯出《歸藏》佚文十九條。王應麟對《連山》、《歸藏》的輯佚對后世學人產生直接的影響,清代學者馬國翰在《玉函山房輯佚書》中,對這兩部易書的輯佚就將王應麟的輯佚成果盡數吸收。除經書以外,王應麟補錄《漢令》《神農》《石氏星經》《星傳》時也對這些著作有輯佚,如他在補錄“《漢令》”條后,依據《晉書·刑法志》記載解釋《漢令》說:“漢時決事集,為令甲以下三百余篇。”[8]232-233進而參考《漢書》《宣帝本紀》《哀帝本紀注》《平帝本紀注》《蕭望之傳》《江充傳注》《百官表注》等材料,輯《漢令》條令名稱和具體內容共計二十九條。王應麟在輯佚過程中對不同類型的典籍都給予了足夠的重視,他對文獻的態度令人欽佩。
四、結 語
由以上論述可見,《漢藝文志考證》在研究范疇上有兩個大的方面,一是就《漢書·藝文志》的相關記載進行考證,二是就《漢書·藝文志》的著錄原則進行文獻輯補。
王應麟有關《漢書·藝文志》的專門研究開創了目錄學與考據學結合的先例,其著作中關于《漢書》的諸多考證成果為學人的漢代歷史研究以及漢代史學研究提供了參考。《漢藝文志考證》作為歷史上第一部以專題研究的形式系統考證、輯補史志目錄的研究專書,在考據學和目錄學上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文獻考證的角度看,王應麟之后的學人對歷代正史中的《藝文志》《經籍志》展開考證,其考證方法為后代學人所普遍接受。明人焦竑撰《隋書經籍志糾謬》,以《隋書·經籍志》研究對象展開專門考證,這種考證方法在清代考據學家中間更加盛行。僅以《漢書·藝文志》為對象的考證,就有王仁俊《漢書藝文志考證校補》、沈欽韓《漢書藝文志疏證》、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拾補》《漢書藝文志條理》、劉光蕡《前漢書藝文志注》等。其中,王仁俊所撰《漢書藝文志考證校補》,是直接在《漢藝文志考證》架構基礎上進行的進一步考證,其標目設置,考證內容、方法都與《漢藝文志考證》有不少相同、相似之處。
從目錄學發展的角度看,王應麟之后的學人對歷代正史《藝文志》《經籍志》進行補作。對于前代正史未作《藝文志》《經籍志》的情況,清代考據學家們在王應麟補錄《漢書·藝文志》條目原則的基礎上,對歷代史志目錄進行了補作,如姚振宗《后漢藝文志》《三國藝文志》,錢大昭《補續漢書藝文志》,顧櫰三《補后漢書藝文志》,侯康《補后漢書藝文志》《補三國藝文志》,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王仁俊《補宋書藝文志》《補梁書藝文志》《西夏藝文志》,厲鶚《補遼史經籍志》、錢大昕《元史藝文志》等等。這都顯示出《漢藝文志考證》在文獻考證和目錄學方面的深遠影響。
王應麟作為南宋“漢書學”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漢書學”成就在中國古代“漢書學”發展史上有顯著的地位。王應麟首次將《漢書·藝文志》作為研究對象撰成專書,是“漢書學”發展至南宋時期深入發展的一個標志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