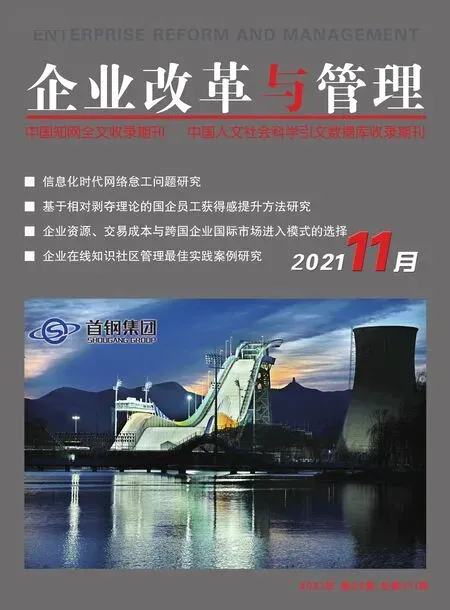信息化時代網絡怠工問題研究
郭 鍇 楊明霏
(浙江師范大學 教師教育學院,浙江 金華 321004)
一、前言
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第4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0年12月),我國網絡使用者規模已達到9.89億,普及率為70.4%,網絡在我國得到了廣泛的普及和使用,已經成為我們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工具。
對于企業來說,網絡是一把雙刃劍,員工可以使用網絡去更便捷、更有效率地完成他們的任務,但越來越多的員工也會選擇利用工作時間使用網絡來達到放松休閑、逃避工作的目的,網絡已經模糊了工作和個人的分界。針對這一現象,學者們提出了網絡怠工這一概念,網絡怠工不僅具有與傳統怠工行為相類似的負面影響,而且更加的普遍和隱蔽,會給組織生產帶來嚴重的威脅和損失。
近兩年,新型冠狀病毒全球肆虐,居家隔離線上辦公成為不少企業的無奈之選。在這種形勢下,組織更加無法有效地發覺和管理員工的網絡怠工行為。因此,這種信息化時代下的新型怠工應當受到管理者和研究者的高度重視。
二、網絡怠工的源起和概念
網絡怠工的研究始于國外,國內也被譯為網絡閑逛、網絡閑散、非工作上網、網絡偏差行為等。Kamin在1995年首次使用“cyberloafing”(網絡閑散,指上班時間從事與工作不相關活動)一詞指代員工在工作期間上網娛樂的新型工作偏差行為;Guthrie和Gray(1996)把員工不符合組織目標而進行的信息系統使用行為稱為垃圾計算機行為(Junk computing),其主要強調該行為對于組織的無用性;1999年美國新聞周刊的一篇文章中出現了“cyberslacking”一詞被譯為非工作上網行為,同年被牛津英語詞典和麥克米倫詞典收錄,將其定義為,員工利用組織提供的網絡從事與工作無關的行為;也正是在這一年,我國學者徐陽(1999)首次將網絡怠工這一概念引入國內;Lim(2002)提出“cyberloafing”是指員工在工作時間內出于個人目的使用網絡和移動通信設備從事與工作無關活動的異常行為,其對網絡怠工的定義受到了廣泛的引用和論證。
我國學者戴春林(2014)總結了國內外對于網絡怠工的研究,并將網絡怠工的基本內涵歸納為,(1)員工在工作時間進行;(2)通過組織的互聯網系統進行;(3)出于員工個人目的;(4)往往以生產力降低或組織目標受損為代價;張和云等(2016)通過總結先前的研究,提出網絡怠工具有隱蔽性強,普遍性廣,危害性大這三大特點,提醒企業應當對其重視。
三、網絡怠工的影響因素
針對影響網絡怠工發生的變量,研究者進行了大量的、多角度、跨學科的研究,目前學界對網絡怠工的研究主要從員工個體因素和工作場所相關因素這兩個方面切入。
1.個體因素
根據Katinka等(2019)對網絡怠工的影響因素分類,個體因素還可以進一步分為人口統計學和人格特質、與個人生活習慣相關的因素。
(1)人口統計學和人格特質
從人口統計學特征來看,以往的研究普遍發現:男性、年輕人、性格更外向的人、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在工作時間更有可能進行網絡怠工。相反,高情商、誠實、自律、盡責的人更少地去網絡怠工。究其原因,這些都是正面人格特質,當員工具有這些特質時,往往更加的盡職盡責,更加具有服從性,傾向將注意力放在手頭的工作上。
(2)個人生活習慣
許多研究表明,員工進行網絡怠工與他們個人的生活習慣密不可分。例如,一些研究發現有私人事務的員工(例如有副業,有債務)更傾向于進行網絡怠工。這可能是在員工心中,私人事務遠比本職工作更為重要,因此,會在工作時間使用網絡來處理私人事務。近年來,有不少研究將員工睡眠質量通過自我情緒耗竭和網絡怠工聯系起來,比較合理解釋是白天的工作任務和工作壓力會導致員工睡眠時長減少,睡眠質量也隨之降低,從而降低白天工作的內在動力,產生網絡怠工行為。
2.環境因素
根據Katinka等(2019)對網絡怠工的影響因素分類,環境因素還可進一步分為工作因素與企業政策因素。
(1)工作因素
研究發現,職位更高、收入更高、壓力更大的員工更傾向于網絡怠工。職位更高收入更高的員工一般都屬于管理層,受到的監督較少,進行網絡怠工時不會認為有太多的不妥,而壓力大的員工則會通過網絡怠工將自己從現實的壓力下暫時解脫出來。而當工作內容非常無聊的時候,員工也會通過網絡怠工來給自己增添樂趣。然而,那些認為工作非常有意義的員工很少會網絡怠工,這些員工可能認為網絡怠工會浪費時間,從而耽誤自己的職業發展。
(2)企業政策因素
企業規模和員工網絡怠工有著密切的聯系,一些研究發現,企業規模越大,員工越不容易網絡怠工;企業對員工進行網絡監控和外部限制越多,企業關于工作時間互聯網使用政策更規范,員工會更加忌憚,擔心網絡怠工被發現而受到懲罰,從而很少去網絡怠工;而當員工感到組織對自己造成威脅時,譬如職場暴力等,員工傾向于進行更多的網絡怠工,以此當作暫時的解脫和對職場不公的回應。相反,當企業公正水平較高時,員工也會有較少的網絡怠工行為。
四、未來研究的展望
隨著網絡怠工研究的發展,網絡怠工領域的研究已經進入了更為成熟的發展階段,這對現有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帶來了更大的挑戰。對于研究者而言,可以從以下方面進一步開展研究。
1.開展縱向研究及聚合研究
目前對于網絡怠工的研究主要采用橫斷研究,而橫斷研究的數據很難驗證變量間的因果關系,因而難以確定員工發生網絡怠工的真正動機和演化過程。并且與縱向研究相比,橫斷研究不能較為完整地了解組織層面對網絡怠工的影響。而通過縱向研究和聚合研究可以較為直觀地發現網絡怠工的起因及結果,并能進一步分析其因果關系。
2.采取新的研究方式和方法
由于網絡怠工的敏感性,對負面行為的研究面臨著巨大的挑戰。采用問卷法要求參與者進行匿名自我報告是目前研究者最常用、最有效的方法。然而即使是匿名,也會存在贊許性偏差。由于網絡怠工的隱蔽性和危害性,參與者承認自己的網絡怠工行為可能會傷害其內因自尊,即便是完全匿名,參與者也有可能會隱瞞其部分網絡怠工行為。目前大多數研究都采用自我報告法,這種單一數據來源的橫斷設計會制約研究結果的可靠性,可能會因為社會贊許性導致較大誤差。也有研究并不是通過研究者直接聯系到的參與者,而是通過人事部門等中間人作為中介來面對參與者的,但參與者可能會因為中間人的解釋偏差、暈輪效應等使得研究結果大打折扣。
因此,研究者應該考慮將自我報告得到的結果使用其他方法進行重復驗證。同時,也要嘗試使用新的研究方法,比如模擬實驗法,現場觀察法等方式研究網絡怠工,以提高研究的科學性和嚴謹性。如有可能,在人事測評中發現員工潛在的網絡怠工傾向,這將是一項非常具有挑戰性和實用價值的研究。
3.關注網絡怠工的兩面性
目前關于網絡怠工的研究,多把網絡怠工當作一種負面行為。人們往往從常識出發,簡單地將網絡怠工歸咎于員工缺乏自律、品行和修養不高等道德范疇。正是基于“網絡怠工錯在員工”的前提,現有研究幾乎完全聚焦于如何減少或禁止網絡怠工,采取“壓服”式管理策略。殊不知,如果不從問題的本質出發,針對網絡怠工的深層心理根源對癥下藥,其結果必然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難以取得顯著的效果。
近年來,有不少學者開始質疑這一假設。有研究發現網絡怠工會提高員工的情緒體驗,并能進一步提高員工的工作投入。還有一些研究發現,很多時候員工并不是自愿地進行網絡怠工,而是將網絡怠工作為一種應對工作場所負面信息的方式,比如巨大的工作壓力、職場暴力、工作太無聊等。因此,網絡怠工要比我們最初想象的復雜得多,這也給研究者帶來了更大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