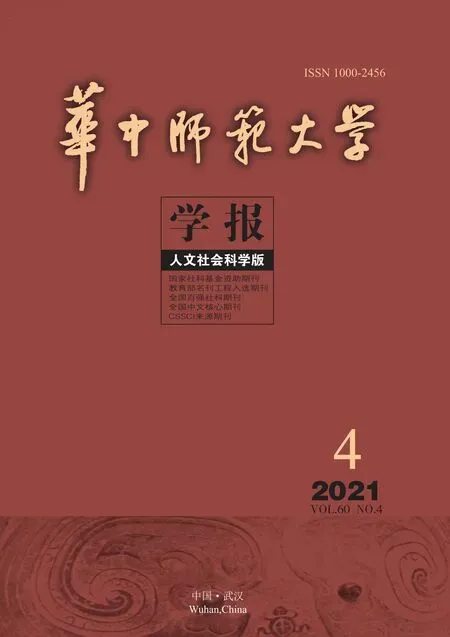文學研究會文學批評實踐的理論特征
——以現代文學書評為中心
顧金春 孫穎超
(南通大學 文學院, 江蘇 南通 226019)
文學研究會的文學批評創作豐富,與創作實踐相輔相成,推動了文學創作的發展。其中文學書評作為文學批評的一部分,在這個過程中亦發揮了重要作用。文學書評一般是指為書籍所撰寫的批評。作為一種與文學作品相依而生的特殊文體,文學書評是一種“副文學”,主要承擔推介功能和多維度深度解讀文學作品的功能,是一種獨立自由且生動別致的文學批評。盡管中國文學書評歷史悠久,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文學書評出現在新文學產生之后的五四時期。這個時期文學研究會的文學書評創作取得很大成績,為現代文學書評創作無疑起到了先導作用,也為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建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不過由于文類的特殊性,相關的研究鳳毛麟角。回到歷史的現場,我們發現文學研究會的書評有自身的鮮明理論特點,其對于現代文學觀念的形成和發展、現代文學創作的變革與促進、中西文學批評理論的交流與融合,都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深入探討文學研究會作家群的現代文學書評創作,不僅能重新認識“為人生”的理論主張,清晰看到文學研究會文學批評與創作實踐的交互發展過程,而且還能深刻感受到現代文學發展過程中文學書評發揮的巨大作用。
一、文學研究會現代文學書評的熱潮與成績
文學研究會的創作以小說與詩歌聞名,在20世紀20年代產生巨大影響。之所以取得如此成績,與文學研究會不斷總結自身創作經驗、重視經驗的積累是密不可分的。
首先,文學研究會具有自覺的批評意識。盡管處于現代文學批評的發軔期,但文學研究會已經認識到文學書評的重要作用,無論組織機構還是文學刊物都把文學批評作為作家的重要職責。據文學研究會會務報告的記錄,文學研究會特設讀書會之批評文學組,旨在討論個人對于小說的見解,批評會員的創作與翻譯,報告關于小說原理、小說史、小說名著等內容,從社團會務章程上強調作家必須具備文學批評的意識。同時,他們身體力行,大力倡導新文學書評的創作。早在創辦會刊《文學旬刊》時,他們就將文學批評定位為“短小精悍的沖鋒隊”,“它的手段是批評、指摘,把社會從醉夢中喚醒來”①。《小說月報》雖是文學研究會的代用刊,但也極力提倡書評創作,它于1921年開設“創作討論”專欄,又于次年開設“創作批評”專欄,1923年又設立“讀后感”專欄等。正是文學研究會的高度重視,新文學書評才以一種獨立文體的形式出現在世人面前。
其次,在這樣濃厚氛圍的影響下,文學研究會成員積極參與文學書評創作,由此掀起書評創作的熱潮,并取得相當可觀的成績。據粗略統計,文學研究會作家的現代文學書評有一百余篇,大多發表在社團會刊《文學周報》上,其余發表在《語絲》《小說月報》《北新》《開明》等刊物上。它們不僅內容博雜豐富,同時形式也繁雜多樣,為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建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相比同時期創造社及后來的新月社等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作家的書評創作起步早、參與者多、書評對象廣泛、書評形式多樣、書評成果豐富,我們可以從書評主體、書評對象、書評文體等方面一窺文學研究會現代文學書評實踐和批評建構的全貌。
雖然文學研究會成員有170多位②,但據舒乙在《文學研究會和它的會員》一文中考證:從來沒有在《小說月報》和文學研究會其他刊物上發表過作品的有58位,大概占社團會員總數的三分之一;還有發表作品較少、影響較小的作家大概占三分之一;真正從事文學創作的只有61位,約占社團會員總數的三分之一。在現代文學書評的創作上,據粗略統計,創作過文學書評的成員有31位,其中鄭振鐸、茅盾、趙景深、周作人、朱湘、朱自清等26位作家文學書評創作數量較多,另外還有5位如吳文祺、顧仲彝等書評數量較少。通過以上數據可以看到,文學研究會作家群中創作新文學書評的成員占比較高,很多成員都屬于兼顧創作和書評的“兩棲作家”,既從事新文學創作、有著實際創作的經驗,同時又實踐現代文學理論與書評創作,具有比較系統的文學批評知識與方法。此外,他們當中諸如周作人、朱湘等都具有較高的文學素養和扎實的知識結構,不僅浸染著深厚的文學傳統,而且較為廣泛地接觸了西方文學,視野開闊。如茅盾的《讀〈吶喊〉》從內容與形式兩個方面肯定魯迅的創作以新形式表現新思想,周作人的《〈揚鞭集〉序》為中國新詩的發展提出“模仿與獨創之消長”的建設性意見,趙景深的《魯迅的〈弟兄〉》則借西方心理學理論闡釋中國現代小說文本,等等。這些都足以代表文學研究會新文學書評的創作實績,反映了特殊時代下現代文學批評的成長歷程。
文學研究會現代文學書評的評論對象十分廣泛,主要集中在新文學的創作上。他們多以跟蹤式評論的方式,批評討論現代文學作品和出版物。首先,文學研究會文學書評以現代小說和詩歌的書評居多,占總量的一半,幾乎涉及當時發表的所有現代小說和詩歌。尤其是冰心、王統照、葉圣陶、魯迅、周作人、徐志摩、郭沫若等影響力較大的作家作品,如潘垂統的《對于〈超人〉〈命命鳥〉〈低能兒〉的批評》、茅盾的《讀〈倪煥之〉》、趙景深的《魯迅的〈弟兄〉》、冬芬的《讀〈談虎集〉》、朱湘的《評徐君志摩的詩》等。其次是現代散文和戲劇的書評,相對而言這部分書評較少,代表性的作品有佩弦(朱自清)的《〈燕知草〉序》、許杰的《讀王成組君的〈飛〉》、王以仁的《沫若的戲劇》和顧仲彝的《評三出創作的劇本》等。另外,還有文學理論批評如陳望道的《美學概論的批評底批評》、王伯祥的《歷史的〈中國文學批評論著〉》,文學刊物批評如華秉丞(葉圣陶)的《關于〈小說世界〉的話》、損(茅盾)的《〈創造〉給我的印象》和方璧(茅盾)的《歡迎〈太陽〉》,童話批評如鄭振鐸的《〈稻草人〉序》等。與此同時,文學研究會書評的目光還投向了文學以外的諸多領域,比如風俗民情、社會事件等,比如趙景深和周作人談論過中西迷信“發須爪”,周作人與學生談論情殺事件“無理心中”等,由此可見文學研究會文學書評對象的豐富性和趣味性。
文學研究會書評對象的廣泛性必然帶來書評形式的多樣性,但由于文學研究會的書評創作正處在中國現代文學書評的發展初期,書評文體還較為稚嫩,主要有“序跋式”“讀后感”“雜談”“書信”等四種形式。“序跋式”書評如俞平伯的《〈憶〉序》、朱自清的《〈梅花〉的序》、周作人的《〈竹林的故事〉序》及《〈談虎集〉后記》、劉復的《〈瓦釜集〉代自序》等,這些都是為作品所作的序跋式評論。“讀后感”書評如1923年徐調孚、顧均正、潘家洵等在《小說月報》“讀后感”專欄發表的葉圣陶《火災》《歸宿》等小說的讀后感。“雜談”書評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1921年鄭振鐸以西諦為筆名在《文學周報》連續發表二十四則《雜談》,討論翻譯、新舊文學、血與淚的文學以及文學如何表現人生等問題。而“書信體”書評既有書評家的單向批評,如1925年俞平伯以書信的形式在《文學周報》發表對白采《羸疾者的愛》的批評,又有書評家與作者及讀者的雙向互動,如1928年朱湘與趙景深在《文學周報》公開發表的關于《草莽集》的書信。
上述文學研究會的現代文學書評創作,雖脫胎于中國古典批評,甚至有的還殘留著一些古代文學批評的痕跡,形式也比較隨意,顯得不夠成熟與規范。但這些書評宣揚新的文學理念,立足社會現實,倡導心靈情感的共振,以開放的視野融匯西方理論,表現出鮮明的理論特征,反映了中國現代作家試圖擺脫固有傳統羈絆、借鑒西方文學理論來建構中國現代文學批評話語體系的努力。
二、宣揚新文學理念的啟蒙指向
文學研究會在其成立宣言中就明確提出自己的文學主張,認為“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游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文學將承擔起新的責任,“文學是一種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③。文學研究會在對鴛鴦蝴蝶派等舊文學的批判中突出了文學“為人生”的主張,這一文學觀內涵豐富,從“人的文學”到“為人生”的文學再到“血和淚”的文學,構成了文學研究會“為人生”的文學主張及文學批評理論的基本脈絡。文學研究會的現代文學書評創作正秉承與實踐了這種文學觀念,文學研究會成員通過抨擊鴛鴦蝴蝶派等封建舊文學的觀念,以跟蹤式的書評創作表達自己對現代作家作品的看法,并以此宣傳“為人生”的文學理念來啟發民眾心智,期望通過文學來從思想意識形態角度影響整個社會人生,進而實現以文學改革社會的遠大理想。
1918年,周作人提出了“人的文學”這一新文學理念,從抨擊儒教道教的非人文學入手,提出新文學需要的是以“人道主義為本”“對于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字”,這一理念中“人”的提出,具有強烈的啟蒙意義。周作人運用生物進化理論闡述人性,指出人“是從動物進化的”,強調關注“人”的生活,尤其是“人的靈肉二重的生活”,以此反對“妨礙人性的生長,破壞人類的平和的東西”的“非人的文學”。由此告訴國民如何真正認識人、發現人,以實現文學啟蒙的“祛魅”作用。“人的文學”概念一經提出,現代文學書評即與此形成呼應之勢。1923年,顧頡剛發表《〈火災〉序》(《文學旬刊》第93期),稱“讀了圣陶的小說,只使得我們對于非人的行為起了極端的憎惡,而對于人的本性起了親切的回省和眷戀”④,批判非人的冷漠與無情,呼喚人的本性、愛與生趣。
周作人還在《人的文學》中以“兩性的愛”和“親子的愛”例證“人的文學,當以人的道德為本”⑤,強調“男女兩本位的平等”和“戀愛的結婚”,認為文學作品中包含“本于天性”的愛才是真正的人道主義文學。受此影響,1923年許杰發表《讀王成組君〈飛〉》(《小說月報》第14卷第3期),他在文中稱贊女主人公燕燕追求女子解放、為女子爭人格自由的勇敢行為,以此響應“人的文學”是講求男女平等的文學,是追求女性解放的文學。在“人的文學”的基礎上,周作人又提出了與貴族文學相對的“平民文學”的概念,補充和說明了“人的文學”的內涵。對“平民文學”的提倡主要是要求作家的創作要從平民生活中取材,書寫平民的現實人生,表現普通人們普遍與真摯的感情。1925年,周作人在為廢名寫的《〈竹林的故事〉序》中稱自己很喜歡這部小說,說它不是“逃避現實的,也不是什么大悲劇大喜劇,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這卻正是現實”⑥,認為作品寫的正是我們所見人生的一部分,是以真摯的文體記錄真摯的思想與事實。隨后,1926年王任叔發表《讀〈飄浮〉》(《文學周報》第232期),他評價文本是“剪裁了人生的片段來到文字上”,“描寫特殊事實而帶有普遍性”,斷言作者是以“誠實的態度去觀察人生”⑦,以普通的文體記錄普遍的事實與思想。這些正是對周作人“平民文學”理論的生動闡述。
1920年,茅盾對“人的文學”進行了重新闡釋,他將周作人以個人為本位的文學擴展為服務于整個社會與民族的文學,提出“文學是為表現人生而作的。文學家所欲表現的人生,決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會一民族的人生”⑧。這一范圍的擴大首先表現為他對普通大眾的啟蒙,只有使中國底層民眾覺醒才能全面實現文學為整個社會人生服務。在評《戲劇》第四號時,茅盾指出,“中國的民眾,關于賞鑒藝術,實在程度太低”,“他們實在不懂什么叫做‘近代’,什么叫做‘思想’,更不懂什么‘近代思想’……所以攻擊舊戲也還得降格遷就,使民家懂得批評的話,才行”⑨。可見,他的批評文字已經溢出了批評對象而向外擴散,帶有鮮明的啟蒙傾向,認為在使民眾感受到戲劇趣味的同時,還要從理性上啟發他們,引導民眾脫離舊思想的支配,向著新的路途前進。其次,他堅信“文學是人生的反映(Reflection)。人們怎樣生活,社會怎樣情形,文學就把那種種反映出來。譬如人生是個杯子,文學就是杯子在鏡子里的影子”⑩。他的早期代表性書評文本《讀〈吶喊〉》(《文學旬刊》第91期)認為魯迅所寫的這些小說都是“舊中國的灰色人生的寫照”“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辛亥革命,反映在《阿Q正傳》里的”。他將魯迅的小說與中國近現代以來的重大社會事件聯系在一起,并試圖說明魯迅小說是對這些重大事件的藝術反映,以此建立借小說反映現實人生,并通過小說中的“啟蒙人生”來宣揚“為人生”的觀念。
1921年,鄭振鐸也從批評鴛鴦蝴蝶派文藝入手,號召創作“血和淚的文學”,疾呼“我們所需要的是血的文學,淚的文學,不是‘雍容爾雅’‘吟風嘯月’的冷血的產品”。這不僅從理論上豐富了“人的文學”的思想內涵,而且以啟蒙理性的目光審視人們的生活,發出了“血與淚”的吶喊。這一觀點在批評整個文學界現狀的同時,倡導文學直面社會人生中的苦難艱辛,揭露底層民眾真實的生存狀況和精神境遇。王任叔的書評《讀〈飄浮〉》承繼了這種思想,肯定了許杰所寫“掙扎的灰色的人生”是為眼前的現實與人生,反對那些敘寫“多角形的戀愛”、“無病呻吟”、“沒有人生的實感”、“宏觀巨構不可一世”和“開流水賬”的作者與文章。同時,“血與淚文學”對“游戲的”“消遣的”文學的抨擊也恰恰表現出文學研究會成員對文學嚴肅性的強調。如葉圣陶以華秉丞為筆名發表的書評《關于〈小說世界〉的話》,他在文中抨擊星期六派小說“絕不思想,絕不觀察,只是在那里胡說”,“要知小說不是罵人和打趣的工具,不是只顧空想的夢話,不是生活浮面的記錄,尤其不是游戲地罵人,游戲地空想,游戲地記錄”,認為做文學是“一件非嚴肅非當真不可的事業”。
文學研究會成員對“為人生”的實踐,更多的是將文學作為一種功利性活動,他們不是把自己的書評對象視為獨立的單一文學現象,而是把它看作與周圍社會環境、整個文壇發展狀況甚至與整個民族人生聯系在一起的整體中的一部分,通過現代文學書評將文學作品與整個社會人生聯系起來,進而完成整體的普遍性啟蒙和指導。
三、現實主義批評觀的實用傾向
“現實主義”的概念在現代文學上的興起與“為人生”的文學觀緊密相連,可以說,現實主義是“為人生”的主導方向,“為人生”是現實主義的主要內涵。但需要注意的是,“五四”時期的理論家和活動家亟待以文學改良社會,還來不及搞清“現實主義”的涵義和本質特征,就熱情地宣傳起來,在文藝上將“自然主義”和“現實主義”(寫實主義)混同起來,如茅盾曾在“關于自然主義的討論”中說,“文學上的自然主義與寫實主義實為一物”。謝六逸在《西洋小說發達史》中也認為“其實自然主義與寫實主義,在實質上并沒有什么區別”。但這并未影響現實主義文學的推進和發展。1922年現實主義的倡導達到高潮,文學研究會成員茅盾、李之常等人在《小說月報》展開“關于自然主義的討論”,并以茅盾的《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作結,之后現實主義開始被一般讀者所接受,日益成為衡量創作和批評的標準,現實主義批評觀由此也成為文學研究會的一個重要的實用傾向。
在《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中,茅盾從抨擊三種舊派小說入手,認為中國現代的三種舊派小說存在三種問題:在思想上信奉“游戲的消遣的金錢主義的文學觀念”;在技術上不但不重描寫,“卻以‘記賬式’的敘述法來做小說”,而且“他們不知道客觀的觀察,只知主觀的向壁虛造,以至名為‘此實事也’的作品,亦滿紙是虛偽做作的氣味”。若要排除這三種錯誤的觀念,就要提倡文學上的自然主義,以自然主義之藥醫新文學創作之疾。在以自然主義批評文學作品時,茅盾從三個方面提出要求:一是要實地觀察、客觀描寫,注重文學描寫的真實性;二是就題材而言,“自然主義是經過近代科學的洗禮的”,我們要“把科學上發見的原理應用到小說里,并該研究社會問題,男女問題,進化論種種學說”;三是就作品現實意義而言,“小說家選取一段人生來描寫,其目的不在此段人生本身,而在另一內在的根本問題”。即作家并不是單純地為事實做記錄,而是要借文本反映本質問題、人生觀等以深化作品的現實意義。
首先,在作品描寫的真實性方面,文學研究會書評把矛頭直指舊文學失真淺浮的描寫。華秉丞(葉圣陶)在《關于〈小說世界〉的話》中批評舊派小說“絕不思想,絕不觀察,只是在那里胡說,要知小說不是罵人和打趣的工具,不是只顧空想的夢話,不是生活浮面的記錄”,小說的描寫不是流水賬,而是“一個完整的結晶體”。可見他反對小說是游戲地記錄,而主張小說的描寫要“進入人心的深處,要察知世間的真相”。俞平伯在《文藝雜論》中表示“文藝的價值不是美和善而是真實”,換句話說,即是要將各個心靈上的現象,老老實實地公布出來。文學研究會書評家在批評舊文學描寫不忠實的同時,也推崇新文學創作中真實描寫的佼佼者。如天用(朱湘)評價魯迅的《吶喊》是一部妙文,原因在于文本描寫得真實動人,“使讀者讀到的時候,忽然間腦中光明起來,心理發生一種近于愉快的感覺”,認為描寫鄉村生活的八篇,篇篇都有美妙的地方,《明天》《故鄉》都描寫得很真,尤其是閏土的描寫,是真實而深刻的人生。與此同時,文學研究會的文學書評中也不乏對現實描寫過度作品的批評,如方璧(茅盾)在《王魯彥論》中批評其小說集《柚子》雖大多作品描寫得自然樸素,但對《小雀兒》《毒藥》不甚喜歡,認為這幾篇小說的描寫太過,太富有教訓意味,進而提出“小說就是小說不是一篇宣傳大綱,所以太濃重的教訓主義的色彩常常無例外的成了一篇menace或累贅”。
其次,在作品取材方面,文學研究會作家的書評關注作品中所反映的社會問題。如1921年潘垂統發表的《對于〈超人〉〈命命鳥〉〈低能兒〉的批評》(《小說月報》第12卷第11期)一文,認為《超人》表現了近年來一般青年墮落頹喪的問題,《低能兒》則是將生理學、心理學、衛生學、社會學等科學知識應用到小說以暴露家庭社會的罪惡。1923年顧均正的書評《葉紹鈞君的〈歸宿〉》(《小說月報》第14卷第4期),批評了《歸宿》一文所反映的兩性間的戀愛問題和性的苦悶。同年,顧頡剛的《〈火災〉序》(《文學旬刊》第93期)一文稱葉圣陶小說再現了教育界的情形,如《飯》《脆弱的心》《義兒》等。可見,在現實主義理論倡導和文學研究會書評創作的互動下,“問題小說”才一度成為現代文學的創作熱潮,體現了務實的現實主義批評傾向。當然,在這個階段,文學研究會作家對“偽”現實主義的創作也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和清醒的認識,如玄(茅盾)在評《小說匯刊》時提及上海出現了“灰色小說匠”的現象,認為他們以迎合社會心理為目的,專門加工趕制粗劣品還冠以“社會問題”“離婚問題”等名詞混淆視聽。再如,1928年顧仲彝于《新月》第1卷第10期發表《評四本長篇小說》,批評《愛的幻滅》一文的戀愛題材用得太濫了,在當時文學界能找出十多篇,并不能為文學創作帶來新意。同時,茅盾在他署名郎損的《評四五六月的創作》一文中也指出當時大多數創作都是以“男女戀愛”為題材,而且寫得都很概念化,批評“大多數創作家對于農村和城市勞動者的生活很疏遠,對于全般的社會現象不注意,他們最感興味還是戀愛,而且個人主義的享樂的傾向也很顯然”。這表明現實主義批評要求作家要創作全面表現社會現象的作品,而非僅僅關注個人生活的小小一角,同時也認為要避免概念化、觀念化的貼標簽式創作。
再次,在作品的現實意義方面,文學研究會作家不僅要求客觀描寫與反映現實,還要求透過文字的外衣映射出作者的理想并應用到現實方面。“文學一方面描寫現實的社會和人生,他方面從所描寫的里面表現出作者的理想,其結果:社會和人生因之改善,因之進步,而造成新的社會和新的人生。這才是真正文學的效用。”顧仲彝在批評茅盾的小說《野薔薇》時,認為作品折射出什么都是失望、什么都是幻滅的人生觀,這種消極的情緒會使一般的青年往絕望的路上走。而“文藝為領導青年向上的明燈”,所以他至誠地希望茅盾以后能夠“慎重將事”。類似的還有潘垂統關于許地山《命命鳥》的批評,他否定了這篇作品“荒謬的”“引人厭世的”立意,認為“學力幼稚的青年很容易被他誘惑”,進而產生悲觀厭世的情感甚至了結人生。此外,方璧(茅盾)在《歡迎〈太陽〉》中提出“作者所貴乎‘實感’不在‘實感’本身,而在于他從這里頭得了新的發見,新的啟示,因而有了新的作品”。由此可見,文學研究會作家的書評不僅重視作品的現實主義描寫方法,而且把能否表達益于社會人生的積極意義作為衡量一部作品是否成功的重要標準。
四、倡導心靈共振的情感取向
文學研究會的文學書評倡導現實主義文學批評,雖然在某些方面表現出實用性和功利性,但它并沒有抹殺文學的藝術本質,而是強調文學要以情感人。正如周作人在《新文學的要求》中所說,人生派文藝“是容易講到功利里邊去,以文藝為倫理的工具,變成一種壇上的說教”,而正當的解說“便是著者應當用藝術的方法,表現他對于人生的情思,使讀者能得藝術的享樂與人生的解釋”。這一論述抓住了文藝的情感性這一特征,避免了文藝變成倫理說教的功利化工具。文學研究會文學書評重視文藝作品中的情感要素,形成了以現實主義為基礎的獨特的文學批評情感體驗。
“批評文學,最宜注意之點,還是情感。”這點早在文學研究會建設文學理論之初就已經成為共識。鄭振鐸在解釋“血和淚的文學”這一文學觀念時就注意到“文學是情緒的作品”,文學“為人生”的意義是在“情緒”的表現中完成的。他在《新文學觀的建設》中再三表明作品情緒表現的重要性,“文學是人類感情之傾泄于文字上的”,“他的使命,他的偉大的價值,就在于通人類的感情之郵”,“人類情緒的流泄于文字中的,不是以傳道為目的,更不是以娛樂為目的。而是以真摯的感情來引起讀者的同情的”。葉圣陶也曾說:“作者持真誠態度的,他必深信文藝的效用在喚起人們的同情,增進人們的了解、安慰和喜悅;又必對于他的時代,他的境地有種種很濃厚的感情。”鄭振鐸等人則從文學表現的對象、文學的價值和文學的作用等方面極力推崇“感情”在文學中的地位,側面反映了人生派文學在批評中既追求客觀之真,還追求主觀真實,要求創作主體在作品中傾注真情實感,從客觀與主觀兩方面實現文學全方位的真實,以求藝術之真。
文學研究會書評對作品情感要素的肯定,首先直接體現為書評中“感動”“同情”與“眼淚”等詞語的高頻出現,這些看似簡單的表述卻是書評家與作品產生強烈心靈共振的結果。他們在創作主體情感動人的文本中感受到底層社會平民生活的艱辛、兵荒馬亂歲月中民不聊生的慘狀以及普遍存在的社會、家庭和青年等方面的問題,由此生成了主觀情感的自然流露。如顧頡剛在《〈火災〉序》中稱:“《隔膜》這一集,最使我感動的,是下一半。這一半寫的情感,幾乎沒有一篇不是極深刻的”,還指出俞平伯在讀時也“不禁淚下”,作品所寫的社會問題、教育問題等都是大眾有所共鳴的現實景象。更甚者,某些文本內容還與書評家自身的經歷機緣重合,這更增強了文本的主觀情感真實與讀者共鳴體驗。如敦易《對于〈寂寞〉的觀察》一文即是如此,小說寫到的童時回憶引起敦易的共鳴,他為文中濃厚的母愛動容,評論冰心的作品“令人受極大的感動”,“賺了不少的眼淚”。文學研究會作家對情感的這一詮釋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文學研究會文學書評偏向于現實主義社會批評的不足,使批評不再局限于分析作品的具體社會背景與時代條件,也不再局限于通過文學作品折射整個社會,而主張把情感看成是某種神秘的、純主觀精神的流露,由此加深了讀者對作品的主觀感受與理解。
其次,文學研究會書評在直接表達同情與感動的同時,還注重創作主體對其筆下人物、生活的態度和評價,希求通過作品的情緒力量對社會人生發生作用。如潘垂統在評《超人》時肯定冬芬(茅盾)所說“誰能看了何彬的信不哭?”他稱這篇作品應該能引起同情,認為文中的描寫包含著熱烈的眼淚和無限的凄慘,最能拯救近來一般青年的墮落和頹喪,在感動中使一般的青年覺悟。再如,1924年王以仁于《文學周刊》第40期始連續發表三節《沫若的戲劇》,文章認為郭沫若雖并不曾提倡人道主義、非戰主義以及“血和淚的文學”,但是讀他的作品會熱淚滿面、血潮澎湃,因為從他的文本中可以看到他對勞工、乞丐、失業的人們充滿了同情心和憐憫心,而對資本家與渾濁的都會滿是憎惡的態度,如此鮮明表達情感的作品恰是真正的有生命的文學。
文學研究會書評從文學作品的情緒感覺角度切入批評,一方面肯定作品主觀情感的重要,另一方面也能從一定程度上糾偏“為人生”的功利傾向,更好地促進“為人生”主張的實行。也正是因為過于重視情感的表達,使得這種情感顯得有些夸飾而不太真實,所以后來這也引起一些反思與批評。如魯迅在《反對“含淚”的批評家》一文中提到“批評文藝,萬不能以眼淚的多少來定是非。文藝界可以收到創作家的眼淚,而沾了批評家的眼淚卻是污點”。甚至后來朱光潛針對20世紀20年代以眼淚多寡評文學的現象專門撰寫了《眼淚文學》一文,指出“能叫人流淚的文學不一定就是第一等的文學”,“用淚表達得出的思致和情感原來不是最深的,文學里面原來還有超過叫人流淚的境界”,因此呼吁“作者們少流一些眼淚,或許可以多寫一些真正偉大的作品;讀者們少流一些眼淚,也或許可以多欣賞一些真正偉大的作品”。不可否認,魯迅、朱光潛的批評確實指出了文學研究會書評創作中存在的某些問題,但是此時新文學書評創作畢竟尚處萌芽期,缺乏理性精神,而更重視閱讀感受和印象,并且,多數書評家還缺乏深厚的理論修養和批評實踐,因此所寫多為感想的抒發和讀后感式的批評,還無法真正建立具有深刻理性思考和嚴密邏輯思維的文學批評體系。
五、融匯西方理論的世界面向
“五四”新文化運動拉近了中國與西方的距離,西方各種哲學社會科學思潮大量涌入中國,從尼采“超人哲學”、叔本華“意志論”到泰納“三因素”、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可以說中國現代文學的產生與發展無一不伴隨著西方近現代哲學社會科學思潮的影響,現代文學書評方面也不例外。茅盾曾發表過這樣的議論:“我們現在講文學批評,無非是把西洋的學說搬過來,向民眾宣傳。”這雖然帶有夸大的成分,但卻從側面反映了現代文學批評與西方文學思潮的密切聯系。
西方文學思潮的傳入使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批評語言和思維方式發生了明顯變化,一方面人們在接受西洋文學思潮的同時,自覺地吸收新術語新概念,并運用于文學批評中;另一方面則在于學習西方的現代思維方式,如茅盾所說“介紹西洋文學的目的,一半果是欲介紹他們的文學藝術來,一半也為的是欲介紹世界的現代思想——而且這應是更注意些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學習“世界的現代思想”,重在以新思想新觀點去觀察當時的一切問題和現象并力求發現新意見。在文學研究會的文學書評創作中,西方文學思潮對其影響明顯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以茅盾為代表的社會學批評,二是以周作人為代表的印象主義批評,三是以趙景深為代表的現代心理學批評。以這三方面為代表,新文學書評逐步形成了以“他者”界定自己,借用西方批評理論來觀照“自我”的批評局面。
茅盾的文學批評受到泰納種族、環境和時代的“三因素”理論的影響,但又有所不同。泰納所強調的“環境”是指地理、氣候等自然環境,而茅盾所說的“環境”更多是指社會環境;泰納所理解的“時代”因素是較為抽象的,而茅盾將“時代”具體化為一個有階級區分和對立的時代,因此他的書評多以作品的社會背景和時代風氣為切入點。與此同時,茅盾還吸收了泰納的整體性批評思維方式和宏觀批評方法,即將作品的內容分析和作家及社會人生和文學發展聯系在一起。如書評《讀〈倪煥之〉》即是對這一批評理論的實踐典范,他稱《倪煥之》是第一部“把一篇小說的時代安放在近十年的歷史過程中的”,用時代性理論分析評價作品,通過這種方式將文學與時代發展緊密結合在一起。由此可見,茅盾批評作品的整體性特征,是將作品看作與周圍社會環境聯系在一起的整體中的一部分,是整個時代社會的一個標本。社會學批評方法在現代文學書評中影響廣泛,許多書評家們開始運用“情節”“題材”“人物”“結構”“環境”等批評術語,如趙景深與孫席珍的《從〈奔波〉講到小說的結構》一文是從小說“結構”入手來構建批評;顧仲彝的《評三出創作的劇本》則是從戲劇“情節”入手評價作品是否合于人情、合于人生的邏輯等。這種批評術語的轉變不僅以鮮明的現代氣息表現了與古典文學批評的分野,而且也為批評家提供了批評作品的新切入點。
以周作人為代表的印象主義批評主要是受到法朗士印象派批評的影響。印象主義批評“強調批評家的主觀投入和瞬間印象,期望以批評的方式表達自己對作品或人生世界的‘印象’”,注重從直觀感覺和印象去把握作品,這與中國古典鑒賞式、感悟式批評有相似之處。周作人曾將批評看作是欣賞、是個人閱讀的感受以及人生體驗的具體化,“我們只能鑒賞,或者再將所得的印象寫出來給別人看,卻不易批評”。他稱自己“所寫只是感想小篇,但使能夠表得出我自己的一部分,便已滿足,絕無載道或傳法的意思”。周作人的書評創作大多是一種閱讀后的雜感或隨筆,而不是理論系統化的批評。比如他在《〈竹林的故事〉序》中開篇即表示“我不是批評家,不能說它是否水平線以上的文藝作品,也不知道是那一派的文學,但是我喜歡讀它,這就是表示我覺得他好”,這種印象式的批評雖然多以自己的感悟替代對作品的細致分析,同時也缺少理論上的闡述,但卻以真實簡單的文風在這一時期書評創作中獨樹一幟。
現代心理學批評是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為基礎的。弗洛伊德學說于20世紀20年代初期傳入中國,在接受這一理論的同時,文學研究會作家在書評創作中也嘗試運用了這一理論。如趙景深書評《魯迅的〈弟兄〉》則是運用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理論,解釋了張沛君夢見弟弟死了的夢,“夢是實際生活的缺陷的填補,凡在日間所感到不滿的,這種欲望在夜間便可滿足”。這一書評顯示了文學研究會作家不再滿足于自己的感悟、印象,而是運用新的思維,采用理性分析來解讀現代文學作品。當然,這些書評并非嚴格意義上的精神分析學,但精神分析學說讓書評家們發現了古典文學批評尚未涉足的“心理”領域,他們從簡單的心理評價開始,一步步打開了隱秘心理世界的大門。如徐霞村批評李健吾的《西山之云》,稱《紅被》的心理捕捉得很好,“雖然遠不如愛倫坡和安得列夫二人寫得那樣精細”,但是單從嘗試創作的角度,不得不說是一部難得的作品;羅美(沈澤民)在《關于〈幻滅〉》中稱作者“忠實地去反映他們的心理”,不僅寫出人深處的心理而且還有深刻的時代烙印。趙景深此后也多次從心理描寫的角度批評作品,如《白癡》《新書介紹》等。
文學研究會的書評創作在借助西方文學理論打開批評新思路的同時,也出現了某些不和諧的現象,有些作家過于依賴于西方文學,出現了某些偏頗。如吳文祺在《駁〈旁觀者言〉》中批評繆鳳林的《旁觀者言》引用很多西洋學者的言論作為自己的主張的護符,有“洋裝偶像”之嫌。趙景深在《〈梔子花球〉序》中也提醒批評家們注意區分“引證外國的文學家來裝潢‘門面’,說得像煞有介事”的作品。在詩歌方面,這一流弊則更為突出。如1926年朱湘的書評《評聞君一多的詩》(《小說月報》第17卷第5期),文中批評聞一多的詩歌用字太累,是上了西方文學史者的當或者是誤解了他們;他還寫了書評《翡冷翠的一夜》(《文學周報》第326期),批評徐志摩學習白朗寧的詩歌理論學得肉麻等。對于這種流弊,周作人曾在《〈揚鞭集〉序》中提出“融化”這一方法以促進中國新詩的發展,他說“新詩的成就上有一種趨勢恐怕很是重要,這便是一種融化”,“新詩本來也是從模仿來的,它的進化是在于模仿與獨創之消長”,“自由之中自有節制,豪華之中實含青澀,把中國文學固有的特質因了外來影響而益美化,不可只披上一件呢外套就了事”。“融化”這一方法不僅適用于中國新詩的發展,而且也是我們面對所有西方文學思潮的態度。盡管我們在文學批評方面落后于西方,但不能簡單機械地以西方的批評標準為標準,以西方的批評方法為手段,甚至將中國文學視為具有西方文學特征的文學,而是要以中國文學和文學批評的獨特性為前提,吸收融合西方有益的理論方法,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文學書評。周作人的“融化”這一提法確實是一種高屋建瓴的思考,對于當下文學批評的發展仍具有警示意義。
結語
文學研究會的現代文學書評創作是特殊時代環境的產物。不可否認,這些文學書評創作在理論主張方面有些概念模糊、以偏概全;在實踐方面也存在文體淡漠、理論淺薄等弊端;在肩負社會責任的情況下,作家們往往急于事功,所作書評多指向文學外圍的社會人生,所論偏向功利化,有時甚至忽略文學本身的藝術價值和審美體驗。盡管如此,但瑕不掩瑜,我們無法抹殺這些文學書評的價值和意義。首先,文學研究會的書評創作宣揚了文學社團的理論與主張,尊崇共同的信仰和價值觀念,從為現實人生的角度出發,旨在以文學啟蒙大眾、以文學改良社會、以文學實現理想,以自身的創作實踐促進了現實主義理論體系的完善與成熟,為我們重新理解文學如何“為人生”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其次,文學研究會的書評創作是在中西文學批評理論的匯融下產生的,它反映了現代文學觀念的發展與完善,有助于我們深入了解現代文學和思想文化的轉型發展歷程;再次,文學研究會書評創作驅動了作家的文學創作實踐,增進了理論批評與創作實踐的交互發展,也加強了作家成員之間的切磋交流,加深了彼此之間的友誼。但最重要的還是文學研究會的現代文學書評創作,在理論自覺和實踐自覺的交互促進下,不僅推動了“為人生”文學的健全發展,創建了一支“為人生”戰斗的文學批評新軍,還初步建構了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理論話語體系,為后來文學批評的建設積累了豐富、寶貴的經驗。
注釋
①真:《最近的出產:讀小說月報第13卷第6號》,《文學旬刊》1922年第40期。
②趙景深:《現代作家生平籍貫秘錄》,見《文壇憶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3年,第203頁。
③《文學研究會宣言》,《小說月報》1921年第12卷第1期。
⑤周作人:《人的文學》,《新青年》1918年第5卷第6期。
⑧佩韋:《現在文學家的責任是什么?》,《東方雜志》1920年第17卷第1期。
⑨玄、路:《最近的出產:‘戲劇’第四號,新中華戲劇協社出版》,《文學旬刊》1922年第42期。
⑩沈雁冰:《文學與人生》,《四川開江縣縣立中學校校友會會刊》1926年創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