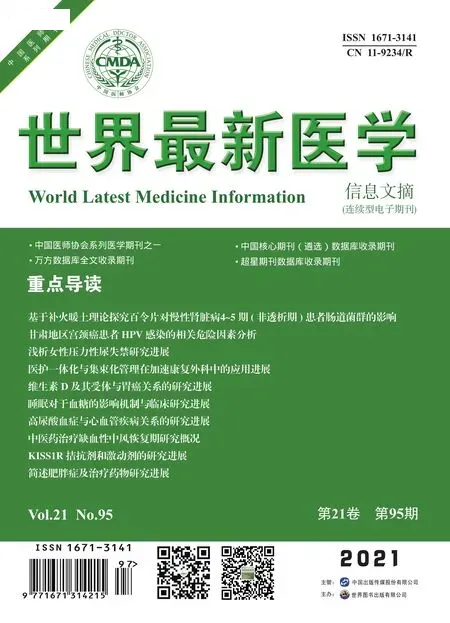淺議從厥陰病論治面部炎癥性皮膚病
李月瑩
(湖北中醫藥大學第一臨床學院,湖北 武漢 430061)
0 引言
面部炎癥性皮膚病是一類可由多種原因導致的發生在面部的皮膚病,臨床中常見的有痤瘡、玫瑰痤瘡、面部脂溢性皮炎、激素依賴性皮炎等疾病;痤瘡是好發于顏面及胸背部的,以黑頭、白頭粉刺,炎性丘疹、膿皰為主要特點的慢性炎癥性毛囊皮脂腺疾病;玫瑰痤瘡是毛細血管長期擴張、毛囊蟲及局部反復感染、食物及精神刺激等綜合因素導致的發生于鼻及鼻周的慢性炎癥性疾病;面部脂溢性皮炎是發生在面部皮脂溢出部位的一種慢性丘疹鱗屑性、淺表炎癥性皮膚病,可伴瘙癢;糖皮質激素依賴性皮炎系長期反復外用糖皮質激素,破壞了表皮通透屏障、降低了角層含水量,誘發軀體產生一連串的炎癥反應。現代研究認為本類疾病與以下因素相關:不正確的護膚方式、光損傷、感染、激素水平、皮膚類型等[1]。由于現代人群生活作息不規律、常過食肥甘厚味、加之受“疫情”及“后疫情”時代下長期佩戴面罩的影響,該類疾病的發病率近年來呈顯著上升的趨勢。現代人出于社交及審美需求,對面部皮膚病的治療期待值也逐漸提高。
中西醫在治療該類疾病各有優勢,西醫以口服抗生素、激素,外涂抗炎、抗微生物、促角質溶解等外用藥膏為主;必要時可聯合水氧、LED 紅黃藍光及多種激光療法[2],在治療本類疾病中能夠起到一定的療效,但其往往具有治療費用較高、治療周期較長等不足之處,聯合應用中醫藥在治療該類疾病中能起到提升療效、縮短病程等作用。中醫對該類疾病的辨證多從“風””濕”“熱”三邪入手,醫家多施以清熱化濕之劑,對于部分辨證得當者可收獲較滿意療效;但若辨證有失偏頗,如對體質陰寒或真寒假熱者久施苦寒之劑,可造成患者皮疹仍在但出現腹痛、泄瀉等中焦虛寒表現的寒熱錯雜之象,此類“上熱下寒”的病機特點與《傷寒論》中厥陰病的辨證特點相應,此時有應用厥陰病方證之機。
1 厥陰病在面部炎癥性皮膚病辨證中的應用
《傷寒論》經方派大家胡希恕先生認為,《傷寒論》中六經辨證來自八綱辨證,在傳統的八綱辨證中,病位分表、里,而表、里兩端無法完全概括疾病的病位特點,故仲景率先提出“半表半里”的概念;半表半里在同一病位上,有陰陽兩類不同的為證反應,其陽證《傷寒論》謂之太陽病,其陰證《傷寒論》謂之厥陰病[3]。由《傷寒論》第326 條“厥陰之為病,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熱,饑而不欲食,食則吐蛔,下之利不止”可見,厥陰病的病因病機為寒飲郁于半表半里,不得出表、入里,郁而化熱,而呈現出“上熱下寒”的復雜證候特點。其中“饑而不欲食,食則吐蛔,下之利不止”為“下寒”的臨床表現;“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熱”為“上熱”之征。應當注意的是,厥陰病的“消渴”與陽明病的“口干、口渴”有所不同,陽明病為里實熱證,其口渴為熱盛津傷所致,需大量飲冷水來緩解其“口大渴”的里實熱狀態;而厥陰病的口渴見述于《傷寒論》第326 條“厥陰病,渴欲飲水者,少少與之愈”,可見其口渴緣于寒郁化熱而產生的上熱,稍飲水即可緩解。
面部炎癥性皮膚病多以面部淡紅色至鮮紅色皮疹為特點,易于反復發作,常于外部環境發生變化(多見于遇熱時)可加重,這個特點可視作厥陰病中“上熱”的辨證指征。此外,證屬厥陰“上熱”的中醫證候可見于:患者訴偶有口干、但飲水不多;證屬“下寒”的中醫證候可見于:手足厥冷、冬季加重,大便稀溏或先干后稀,進食生冷易腹瀉,舌淡紅或暗紅,舌苔白膩,脈沉或弦[4]。
2 常用三類厥陰病代表方的方證分析
厥陰病的治則與半表半里陽證少陽病相類,不宜“汗、吐、下”,當用“和”法。以寒熱藥物相配,辛開苦降、溫下清上。其代表方證有“胸脅滿微結”之柴胡桂枝干姜湯證、“嘔而腸鳴、心下痞”之半夏瀉心湯證、“蛔厥”“或久利”之烏梅丸證等,這三類方證均歸屬于厥陰病范疇,但在藥物組成、臨證要點、適用范圍等方面均有不同之處,以下將對其各自的辨證特點及應用指征做詳細闡述,以資鑒別。
2.1 “胸脅滿微結”之柴胡桂枝干姜湯方證
柴胡桂枝干姜湯出自《傷寒論》第147 條“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胸脅滿微結、小便不利、咳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為未解也,柴胡桂枝干姜湯主之”及《金匱要略·虐病》“柴胡桂枝湯方,治瘧寒多,微有熱,或但寒不熱,服一劑如神效”。由上述條文可看出,此為少陽病誤用下法轉為在半表半里陰證的厥陰病。柴胡桂枝湯方證的辨證要點為“寒多熱少”或“但寒不熱”;即必可見畏寒、四肢厥逆等虛寒表現,或可并見頭汗出、口干、往來寒熱、心煩等微熱之象。本方證適用于證屬厥陰,而尚無中焦虛寒表現的患者。
該方由柴胡半斤、桂枝三兩、干姜二兩、瓜蔞根四兩、黃芩三兩、牡蠣二兩、炙甘草二兩組成。方中柴胡解寒熱邪氣、推遲致新,以治“心下微結”;以辛溫之干姜伍苦寒之黃芩,辛開苦降,暢中焦氣機;瓜蔞根潤燥生津、牡蠣收斂止渴;桂枝配伍甘草降逆調氣;同時,干姜可溫陽逐飲。臨床中若患者寒甚、或兼見寒凝血瘀,當辨為太陰厥陰合病,可合用赤小豆當歸散、當歸芍藥散等太陰病方;若上焦熱甚,可加入小劑量清熱解毒藥物,如選取五味消毒飲、涼血五花湯中具有清熱、解毒、涼血功效的幾味藥物以助疹消熱退。
2.2 “嘔而腸鳴、心下痞”之半夏瀉心湯方證
半夏瀉心湯出自《傷寒論》第149 條“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證仍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予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為逆,但蒸蒸而振,卻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硬痛者,此為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為痞,柴胡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及《金匱要略·嘔吐噦下利病》“嘔而腸鳴,心下痞者,半夏瀉心湯主之”。本方證條文詳細闡述了少陽病小柴胡湯證誤下后,由于津液虧虛而陷于陰證,出現了“滿而不痛”的“心下痞”之證,且兼見“嘔而腸鳴”的中焦虛寒表現[3]。臨床中患者可表現為:口干,四肢厥冷,心下痞滿,大便偏稀或進食生冷后易腹瀉。應當注意的是,隨著時代變化,當代社會高度工業化、經濟高速發展、人均生活水平大幅提升;“誤下”不僅限指前醫過用泄下之品;也可見于起居無常、耗損陽氣,調護不當、失于保暖,或飲食不節、嗜食生冷肥膩之品等不恰當的生活習慣;因此在臨床采集病史時,應仔細詢問,緊抓“心下痞”“嘔而腸鳴”的辨證特點,不可單單憑借前醫遣方用藥的思路來貿下定論。
該方由半夏半斤,黃芩、干姜、炙甘草、人參各三兩,黃連一兩,大棗十二枚組成,系小柴胡湯生姜換為干姜,去柴胡加黃連組成。方中半夏合干姜溫陽建中、祛飲止嘔;黃芩合黃連解熱除煩;人參、大棗、甘草并用補虛和中、振發胃氣,體現了“辛開苦降”“寒熱同調”的組方思想,臨證加減思路與柴胡桂枝干姜湯方證相類。
2.3 “蛔厥”“或久利”之烏梅丸方證
烏梅丸出自《傷寒論》第338 條“傷寒脈微而厥,至七八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此為臟厥,非蛔厥也。蛔厥者,其人當吐蛔。今病者靜,而復時煩者,此為臟寒。蛔上入其膈,故煩,煩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蛔聞食臭出,其人常自吐蛔。蛔厥者,烏梅丸主之。又主久利”。本條方證闡明了厥陰病寒熱錯雜的“蛔厥”與太陰病純寒無熱的“臟厥”之間的區別。烏梅丸方證中,患者的虛寒程度明顯較上述柴胡桂枝干姜湯、半夏瀉心湯兩方證更強,可因寒飲停伏日久而表現出四肢厥逆、或腹痛時緩時作、或虛寒久利的中焦、下焦虛寒證候;同時兼見煩躁、時欲嘔的上熱之候。
在本方中,君藥烏梅以苦酒漬之,大酸大斂、補虛兼顧止瀉;附子、干姜、細辛、蜀椒四味辛溫藥物聯用,可辛溫驅寒、溫里溫下;人參、當歸和補氣血;黃連、黃柏清在上之微熱;桂枝調沖降逆。全方酸苦辛甘并用,擅長治療虛寒自下迫、虛熱上浮的半表半里的厥陰病虛寒證,在臨證應用時需與太陰病方證仔細鑒別。
3 驗案舉隅
嚴某,女,44 歲。2017 年8 月16 日初診。訴面部起紅斑伴瘙癢2 年余。曾外用多種自購不詳藥膏,皮疹易反復發作。查體見雙面頰部淡紅斑伴毛細血管擴張,散在分布針尖至米粒大小的鮮紅色及暗紅色的丘疹。刻下見:畏寒,肢涼、冬四逆,夜尿5 次,大便干結、2-3 日1 行,口中和。舌淡暗,邊齒痕,舌苔薄白,脈沉。依據其病史及臨床表現,診斷為糖皮質激素依賴性皮炎,辨為虛火上炎證,予潛陽封髓丹加減。
一周后復診,患者訴皮疹未減輕,刻下諸證同前。復辨為厥陰太陰合病,予柴胡桂枝干姜湯合當歸芍藥散加減,處方為:柴胡12g、桂枝10g、干姜6g、生龍骨15g、生牡蠣15g、天花粉15g、黃芩10g、炙甘草6g、當歸6g、赤芍10g、川芎6g、生白術20g、茯苓10g、凌霄花10g、赤小豆15g,7劑,水煎服,分溫二服。
8 月30 日,三診,皮疹減輕約1/3。刻下見:四逆,眠可,大便2 日1 行,夜尿減,舌淡暗,薄白膩苔,脈沉。辨證同前,予上方續服14 劑。
9 月13 日,四診,訴紅斑較前減輕,進辛辣食物后皮疹反復,口唇糜爛。刻下癥:大便日1 行,舌淡紅邊齒痕,水滑苔,脈弦細。辨為厥陰太陰合病病,予半夏瀉心湯合赤小豆當歸散加減,處方為:姜半夏15g、黃芩10g、黃連3g、黨參10g、干姜10g、大棗10g、炙甘草6g、赤小豆15g、川芎6g、紅花6g,7劑,水煎服,分溫二服。
9 月19 日,五診,紅斑減輕2/3 以上,患者訴服上方藥后胃部偶有不適,大便日2 行,舌淡暗,邊齒痕,脈沉。仍辨為厥陰太陰合病,予上方去生白術、加蒼術10g,續服14 劑。兩周后復診,患者皮疹持續減輕,訴畏寒、四逆減,胃部不適已,口中和,大便正常,夜尿1 次。續予柴胡桂枝湯合赤小豆當歸散加減治療一月余,患者面部紅斑、丘疹基本消退,口中和,二便無異,畏寒肢冷較前明顯緩解。
按:本案首診辨證時忽視了患者畏寒、肢冷、冬四逆等虛寒表現,僅針對虛火上炎論治,方選潛陽封髓丹,7 劑后未見明顯療效。二診時,結合了患者上熱下寒的厥陰病表現及夜尿頻、里虛寒甚的太陰病表現,辯為厥陰太陰合病,此時患者尚無中焦證候,故選用柴胡桂枝干姜湯合當歸芍藥散,清上溫下,加用凌霄花10g,助清在上之熱。服7 劑后患者皮疹消退約1/3,療效顯著,續服14 劑。四診時,患者訴進食辛辣食物后皮疹有所反復,且出現口唇糜爛,仍辨為厥陰太陰合病,此時考慮到柴胡桂枝干姜湯清上溫下之力稍弱,改為半夏瀉心湯合赤小豆當歸散加減,加強溫補虛寒、調和氣血之力。五診復診,皮疹減輕2/3 以上,患者訴服上方后偶感胃部不適,考慮可能為上方中生白術性寒涼所致,遂去生白術、改為蒼術10g,續服14 劑,再次復診訴胃部不適已,而厥陰太陰合病諸證仍在,故續予柴胡桂枝湯合赤小豆當歸散加減治療1 月余,患者皮疹漸消、上熱下寒的癥狀均得到有效緩解。
4 結語
綜上,面部炎癥性皮膚病在臨床中頗為常見,其患處位于暴露部位、發病與先天稟賦及后天養護各方面均相關,且易受各類理化、生物因素的刺激,病程常纏綿反復;而患者對容貌需求較高使得本病的臨床治療頗具難處。本文立足于厥陰病的病機及方證特點,將傳統經方辨證與臨床實踐相結合,淺議了該類疾病證屬厥陰時的辨證論治法則,具體應用情境及臨證加減尚需在臨床實際中多加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