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葉黃時
◎倪 苡
盛秋厘遠遠地看著小虎,小虎坐在那尊石像旁,兩條前腿撐著它高高昂起的頭,兩只銅鈴似的眼睛,亮閃閃的,一眨不眨地盯著盛秋厘。
盛秋厘倚靠在銀杏樹干上,一片銀杏葉悠悠地從她的頭發滑到她的鼻尖,轉了半個圈,悄悄落到地上。老張最喜歡秋天,最喜歡秋天的銀杏樹。老張說秋天的銀杏葉像極具韻味的女人,尤其那黃色,不媚不佻,亮麗中不失端莊。關于這句話,老張是和盛秋厘飯后散步時,隨口溜出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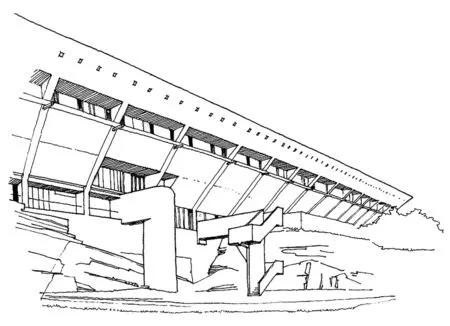
老張說完這句話,盛秋厘看了老張一眼。盛秋厘眼里的老張就是個悶葫蘆,和老張生活幾十年,還真不知道他這悶葫蘆里裝的什么藥。按理說,他這木頭似的人,怎么可能看花非花,看葉非葉呢?
盛秋厘在想老張的比喻,怎么偏偏把銀杏葉比喻成女人呢?可不可以比喻成蝴蝶?她還沒把老張的這個比喻琢磨透,老張又開口了,說這葉的外形,也是蠻精致的,該流線條的流線條,該直線的直線。這老張研究銀杏葉還上癮了?盛秋厘反問一句,那么秋天的樹葉哪個不是黃色的有流線條的呢?也對呀,小厘說得有道理,怎么就對著銀杏葉說瘋話呢?老張不說話了,默默拉起小厘的手,繼續散步。
后來盛秋厘獨自一人來到公園,坐在老張常坐的那張長條木椅旁,看著隔條小道的銀杏樹。滿樹黃黃的銀杏葉密密的,金燦燦的。那密,那金色,完全不是凋零的氣味,簡直真的像一個完全成熟的少婦,肆意地綻放著她的美。再看看木椅后面的無患子樹,首先葉形還真的不如銀杏葉精致,再看看顏色,黃中帶枯,色澤暗沉,何況葉子掉得像老人的頭發,稀稀疏疏的,確有很濃的朽的氣息。盛秋厘心里服了,老張是有眼力的。
金黃的銀杏葉還在,有眼力的老張卻不在了。老張走了一個月了,走得很突然,就一個跟頭的事,老張就永遠地把自己深埋在這個秋天,把他所有的喜怒哀樂存封在那永遠閉著的眼睛里。盛秋厘收起目光,低下頭,踩著沙沙的銀杏樹葉,朝小虎走去。小虎站起來,從石像走向長條木椅,圍著木椅轉了一圈,然后乖乖地走到盛秋厘身邊。這畜生似乎每次都是故意賴著不走,非要盛秋厘在過去的時光里走一段,直到盛秋厘淚流滿面,或者哽咽,或者身子軟得站不住蹲下去,小虎才肯回家。這小虎其實不小了,都六歲了,但叫它老虎,似乎又不太妥當。
小虎是老張母親遺物中的一件,老張母親去世的時候,小虎才三個月。老張把小虎領回家時,盛秋厘一百個不情愿。母親去世的那一年,老張兒子剛結婚,住出去了。老張也正好退休,天天在機關忙碌的他,突然退休,閑得慌,弄條狗陪著,挺好的呀。
盛秋厘不愿意,就算老張照顧小虎像當年照顧兒子一樣。可是兒子長大會洗臉刷牙,會上抽水馬桶,會給盛秋厘倒杯水,這小虎會嗎?家里不知道會被小虎糟蹋成什么樣子呢。兒子身上有乳香,可小虎身上,老張哪怕一天給它洗澡十遍,它身上就是有狗腥味。盛秋厘是個小有潔癖的舞蹈演員,小虎領回家的第一個年頭,老張不知受了盛秋厘多少無名火。老張這人就是脾氣好,一輩子沒有對盛秋厘高聲過,對的錯的全都包攬。盛秋厘的閨蜜周小雅,跟盛秋厘聊天的時候,話題轉著轉著就繞在老張身上,周小雅說老張的優點數不勝數,一輩子也聊不完。年輕時的盛秋厘不覺得自己有多幸運,甚至覺得老張有點慫。但老張也不慫啊,老張在機關是出了名的有能力的干部,從一般科員干到一把手局長。盛秋厘有時想想都覺得好笑,這么個半啞的人,怎么個當領導的。為這事,盛秋厘還專門溜進了老張的報告廳,臺上的老張那哪是老張啊,中年婦女的偶像啊,連盛秋厘這樣心高氣傲的女子都被折服了。風度、才學、磁性的聲音,依稀的皺紋和白發都看不見了,英俊得很。打那以后,盛秋厘覺得自己確實嫁對了。
盛秋厘領著小虎走一步歇一步,大衣被風吹得貼在身上,越發顯得單薄。本來身體纖瘦的盛秋厘,在老張走了的這一個月,像夏天出了冰箱的冰淇淋,化了一大圈。除了這瘦,再看看她那蹣跚的步子,這哪像一個全市聞名的舞蹈演員,她的左腿麻木得快邁不動步子了。
明天就要被兒子接到另一個城市了,本來老張剛死,兒子就要接走盛秋厘,盛秋厘不走。盛秋厘認為自己可以的,可以在這里再和老周待些日子,卻不知道自己的身體敗得這么快,怎么渾身都是病了呢?前些日子,早上剛起床,莫名其妙地腳下像踩空了一樣,一跪一趴就那樣摔倒在地,頭暈目眩。好一會兒都爬不起來,不知道是哪里使不上勁。盛秋厘當時就哭了,怎么可以活得這樣狼狽!
最近腰疼得連掃地都干不了了,掃個客廳都要去沙發躺兩次。還有要命的左腳掌,有次盛秋厘狠狠掐自己的左腳掌,卻沒有痛覺。那次盛秋厘氣瘋了,去廚房里拿了把菜刀,要宰了自己。可她不知道從哪里下手,該砍哪里可以一刀了結這條殘命?
還有小虎,這一個月,只有四個休息日,小虎是吃飽了肚子的。休息日盛秋厘兒子都過來,盛秋厘兒子來的日子,盛秋厘像個沒事人一樣,她不想讓兒子替自己擔心。可兒子一走,盛秋厘有時候一天都不做飯,蒸一個紅薯可以是一頓午飯,買一個包子可以是一頓晚飯。
終于有一天,盛秋厘倒在床上,連口水也喝不上,她頭暈腰疼腳麻,身體的三個重要部位一起襲擊她時,她妥協了,答應去和兒子一起生活。當時的小虎在客廳和房間之間轉來轉去,小虎這一個月也明顯瘦了,它渾圓的身體有了骨感,甚至連走路都是哲學家般的踱步。和老張散步時,小虎從來都是奔跑著的,它跑一陣子,把老張甩下一大截,然后再跑回來,如此來來回回,每晚的散步它大約都要跑四至五倍的路程。老張看著前面蹦跳著的小虎,心情會無理由的陡好。據說泰迪犬最長壽命是15年,沒有了老張,小虎成不了長壽的那個。是你命不好。盛秋厘嘆息道。
次日,盛秋厘來公園就是和老張說一聲的,和老張的銀杏葉道個別,和老張的長條木椅道個別。夕陽照在盛秋厘的頭發上,有幾根白發自動跳出來,在風中飄啊飄的,說不出的傷。這黃昏時分,公園里有三三兩兩的散客,可誰能認出,這是當年市劇團自編自演拿了省一等獎舞蹈《閃閃的紅星》的領舞呢?
盛秋厘走一步回一下頭,她希望老張在她的哪次回頭中,會突然現身。她知道那只能是幻覺,可她希望出現一次幻覺,她就要離開這個城市了,難道走了一個月的老張,已經不來這里了?這一個月,就算下雨,盛秋厘打把傘,也是要來這里轉一下的。老張在世的時候,一年365天,他至少有300天都會來這里坐坐。老張曾經說過,小厘啊,心悶的時候,來這里坐坐,就覺得好多了。有老張的日子,盛秋厘從來沒有心悶,只有心火,但有了心火,沖老張發,發完就罷。
這一個月,盛秋厘心也悶啊,可來這里,不奏效啊,心似乎更悶了。在盛秋厘的記憶里,老張在這公園的時間比在家長,偶爾在家,老張基本上都在書房。老張在書房搗鼓什么?盛秋厘有次悄悄溜進去,老張真的在電腦上改講話稿。盛秋厘進去,老張沒有和盛秋厘說一句話,不知道有沒有看見她,如此兩三次,盛秋厘沒有討到老張的半句只字,每次看見的都是老張眉頭緊鎖盯著電腦。從此,盛秋厘再也沒有進過書房。
老張走了的這一個月,有次,盛秋厘打開書房的門,才跨進去一只腳,她就趕緊把腳收回來,關緊了門,書房里一絲陽光都沒有,可她隱隱約約看見電腦前的老張,滿頭刺眼的白。盛秋厘常常盯著老張的照片,希望看出一個幻覺,可以和老張說幾句話,問問老張,如果那天不去釣魚,老張會躲過這一劫嗎?那天和誰釣魚的呢?怎么會摔趴在河岸上呢?
盛秋厘希望在任何地方遇上幻覺中的老張,就是不想在書房。盛秋厘心里有點恨書房,發過誓的,絕不踏進書房半步。毫不夸張地說,老張從沒在書房和她說過一個字。她以為老張走了,她可以與書房和平相處的,哪知還是氣場不合。
兒子來了電話,約好了第二天接母親的時間。盛秋厘在家里左看看右看看:廚房,上班時,老張基本不在家吃飯,退休后,老張學做飯,好像沒天賦,一直沒學會,就放棄了,盛秋厘煮什么他就吃什么,從不嫌咸嫌淡;客廳,就那沙發,老張坐著看新聞的沙發,在白如晝的燈光下,不殘留老張的一絲氣息;再者就是床了,除了出差,老張無論早晚,哪怕有時是三點,他也堅持天天回家的。到了床上的老張,都是聽盛秋厘說些閑事,是最有耐心的傾聽者。老張還是小張的時候,蠻有活力的,不知道從什么時候起,小張突然成了老張。剛開始時盛秋厘還不習慣,故意找茬生氣。老張把盛秋厘往懷里摟摟,拍拍她的頭她的背。盛秋厘在老張懷里象征性地掙幾下,就平心靜氣了。漸漸地,這種和平的睡覺方式成了習慣。那么這床,好像也沒有被老張打上更深的烙印。
兒子張守一按約定時間來接盛秋厘的時候,盛秋厘和小虎都坐在沙發上。張守一環顧四周,沒見行李箱,絲毫不見要出門的跡象,母親不會要變卦吧。自從父親去世后,張守一每晚都要打一個電話給母親。有一次正和母親通話時,母親說的眩暈病犯了,沒說上幾句話,手機里傳來“啪”的一聲響,然后手機里就沒了聲音,急得張守一差點當晚就從八十公里開外的城市趕過來,好在隔了一會兒,手機里傳來了母親的聲音,母親說的是茶杯摔在地板上了。
這次一定要把母親接走,張守一自己動手給母親收拾行李,來到母親房間,房間里有點亂。床上的被子分不清橫豎正反,自由又散漫地臥在那里;衣服像被貓玩耍過的線團,沒有源頭擠擠挨挨地團在沙發上,衣架上倒不見幾件衣服。除了這些,房間里還有一股很濃的膏藥味。張守一鼻子一酸,這哪像自己心目中母親的房間。張守一的印象中,母親是這個城市中最講究的女人。張守一最初的記憶里,不談衣服,就是紅領巾,母親也要把兒子脖子上的紅領巾整理得服服帖帖,才肯帶兒子上學去。
母親還有點小潔癖。記得有次放學,來接兒子的盛秋厘遠遠看見,兒子和“鼻涕王”黃毛手拉手排在散學隊伍的第三排。當天晚上,張守一的手不知被母親洗了多少遍,向來疼兒子的母親突然心狠了,張守一小手被搓得通紅,像是不被洗掉一層皮,母親就不罷休。第二天的放學,老師安排張守一排到隊伍的第二排,手拉手排隊出校門的換成了一個干凈的女生。此后,張守一似乎懂了母親的心,不是迫不得已,手決不碰臟東西,以至于在后來的很多年,成了一種怪癖。現在的張守一也是盡量避免跟人握手的。
磨蹭了半個多小時,盛秋厘把小虎送給了小區門衛,拜托門衛用點剩飯剩菜給小虎一條活命。小虎是不宜帶到兒子家的,孫子才五歲,有條狗在家是不安全的。
忙妥了所有,終于出門了。張守一邊開車一邊時不時從后視鏡看母親。自父親去世后,母親陡然老了,從前的母親,哪怕退休后,也是不化妝不出門,母親說的不化妝的臉就像臉沒洗干凈一樣,走出門會不自在。可現在后座上的母親,不要說化妝了,就說那頭發,今天早上母親肯定沒有梳過,至于昨天或者前一天有沒有梳過,也是不確定的。
汽車在高速上急駛,母子兩個都沉默不語,各想各的心事。盛秋厘看著迅速往后倒退的綠化帶,很多心事來不及整理,都一閃而過,像跳跳糖,沒法停留,亂七八糟的蹦蹦跳跳。她抬頭看看天,還是云朵安靜,無論汽車怎么飛馳,云朵都安靜地懸浮在天空下。記得老張退休后的第一天,坐在公園的長凳上,拉著盛秋厘的手說,小厘啊,以后我們的生活就是“望天上云卷云舒,看庭前花開花落”。當時盛秋厘把另一只手搭上去,緊緊地握著老張的那只手,安慰老張失落的心。
如今的她,成了需要安慰的人。她理解兒子的苦心,兒子是舍不得她這個母親,可兒子不知道母親的用心。
媳婦葉拉是個獨生女,她的出生是個意外,她是她母親四十五歲懷上的,能夠在這個年齡懷上并生下她,實在算個奇跡。葉拉自小到大都是公主的做派,偏偏兒子吃那一套。葉拉的父親在葉拉十六歲時就去世了,葉拉和張守一結婚時就強調過,她母親是要一起過來的。張守一回家跟父母商量了這事,盛秋厘不愿意,可不久葉拉就懷孕了,這婚事就是提前到來的寶寶給促成了。
婚后葉拉母親相當于免費的保姆,這也正合盛秋厘的意。所以從兒子結婚的一開始,盛秋厘就不怎么去兒子家。
如果不是自己的身體不爭氣,盛秋厘還是不愿意去兒子家的。現在的情況更復雜了,葉拉的母親已經中風在床了,所有的家務都保姆干,保姆也不知道換了多少個了。不是工資的事,是保姆覺得活實在是多,接送孩子上幼兒園,照顧在床的老人,還要買菜做飯打掃衛生。從早到晚真的是屁股沾不到板凳,忙個不停。
就在盛秋厘想兒子家事想得頭大的時候,張守一問母親要不要進服務區。盛秋厘說自己不需要去,隨兒子進去不進去。張守一和母親拉起了家常,說最近的這個保姆是個鄉下人,肯吃苦,人勤快。讓母親過去了之后,有什么事,盡管讓母親使喚保姆。還說把母親接過來,他這個做兒子的心里踏實多了。母子倆聊著聊著,盛秋厘居然睡著了。老張去世后的這一個月,盛秋厘從來沒有睡得這樣安穩過。
一進兒子家門,保姆就趕緊從鞋柜里拿拖鞋。盛秋厘換鞋時看了一眼客廳,還算整潔。再看看保姆,確實是個老實巴交的農村婦女,年紀有點偏大,約莫六十幾了,有些粗壯,不過看上去干干凈凈,干活也利索。
盛秋厘先去了葉拉母親的房間,和葉拉母親聊了幾句,其實不是聊天。就盛秋厘說了幾句,然后再猜猜,葉拉母親雖說話很努力,盛秋厘是聽不懂的。葉拉母親嘴巴不關風,聲音從嗓子出來,不經過嘴巴的處理,是形成不了語言的。
晚飯的時候,葉拉帶著兒子多多回家了。葉拉叫聲“媽”。又讓正換鞋的多多叫“奶奶”。多多眼睛盯著沙發上的iPad叫了聲 “奶奶”,就奔向了沙發,玩起了iPad。盛秋厘看著多多,心中悲喜參半。張守一招呼大家吃飯,保姆到葉拉母親房間喂飯。
盛秋厘就這樣在兒子家住下了,生活又是另一番樣子。每個上班時間,家里就剩下三個老人。保姆送孩子買菜的時候,家里就盛秋厘和葉拉母親兩個人,這個時間盛秋厘總在家里轉來轉去,房間里的葉拉母親總是在哼哼唧唧的,不知道在說什么,盛秋厘進去問她有什么可以幫忙的,她總是搖搖頭。這個時間盛秋厘如果出門,把葉拉母親一個人扔家里,她覺得有點不近人情,但天天聽著葉拉母親吐字不清的發音,盛秋厘特別難受。
每次,保姆買菜回來,把菜往廚房一放,就去葉拉母親房間。保姆是個訥言的人,每天只做事,不多話,你不問她不說。盛秋厘決定進去看看,盛秋厘一推門,估計只看了半眼,就迅速關上了門。她看見了葉拉母親光著的下半身,那是怎樣的兩條腿,已經完全萎縮成兩根骨頭了。還有一旁的保姆,正在給葉拉母親換尿不濕。
盛秋厘回到自己的房間,往床上一躺,又趕緊坐起,她覺得自己想吐,她去客廳喝了幾小口水。以前盛秋厘在家的時候,總是悲傷老張走得太快,這幾天她看著葉拉母親的臥病在床,她倒覺得老張前世積德了的。未來的自己如果也像葉拉母親這樣,倒不如早點了斷自己。可是,未來誰知道呢?說不定未來的自己不想死呢?
盛秋厘盯著從葉拉母親房間出來的保姆,接下來保姆應該做飯,盛秋厘看她洗不洗手。保姆直接進了廚房,盛秋厘看見保姆在廚房里用水沖了一下手。盛秋厘讓保姆去衛生間用洗手液認真把手洗一下,保姆沒有任何異議地接受了。
環境對人的影響是暗自發力,不動聲色的。兒子張守一并沒有對母親說什么,盛秋厘自來了兒子家后,雖說還是時不時思緒就繞到老張身上去,但她的日常已經漸漸地又變回了從前的她。現在頭發梳得一絲不亂,口紅也用上了。
是啊,在這個家里,如果盛秋厘再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她就和葉拉母親站成一隊了。兒子是外企的高管,葉拉是外企的翻譯,自然每天都打扮得鮮亮的。孫子多多自然不要說了,葉拉給多多買的衣服都是上千的,好在盛秋厘是見過世面的,不然還真的會常常被孫子衣服的價格驚到。保姆雖是農村人,但每天都把自己拾掇得清清爽爽的。盛秋厘有次問了兒子關于保姆的工資,月薪7500。這工資在一般的小城市,就是高薪了。可是沒有這般價格,誰肯天天忙屎忙尿的。
有人群就有矛盾,盛秋厘平日里跟保姆說不上三句話,開始時盛秋厘和保姆的相處,是一問一答,她們雖是同齡人,可畢竟層次不一樣,三觀不同。后來她們之間好像做不到和平相處了,是從氣味開始的。
保姆每天下午將碗筷洗好后,有一個小時的空閑時間,這一個小時,保姆在衛生間基本要呆上半小時。有一次保姆剛從衛生間出來,盛秋厘剛好進去,盛秋厘一進去,一陣異味迅速穿過鼻孔,直往五臟六腑里鉆。盛秋厘趕緊退出,找來電風扇,放在衛生間門口,開最大風速,朝衛生間里面吹。
不管保姆是什么文化層次,盛秋厘此舉一出,保姆臉上憋得通紅。保姆嘴角動了動,似乎想說什么。盛秋厘做完這些,嫌棄地看了保姆一眼,回到了自己的房間。
盛秋厘和保姆之間的關系就此緊張起來。但保姆買菜煮飯接送孩子,還真的做得無可挑剔。保姆平時做飯處處還是挺小心的,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對葉拉母親的飯菜總是有點含糊。比如有次盛秋厘就看見葉拉母親專用的碗筷沒洗干凈。也沒有進消毒柜。如果是偶爾的一次,也就罷了。可是盛秋厘發現,保姆不將碗筷放進消毒柜,已是常態。
但盛秋厘知道了這事,她卻沒有和保姆說,難道盛秋厘覺得其它碗會染上相同的氣味不成?問題出在一次晚上的魚湯。保姆做好飯后,盛了一小碗去喂葉拉母親,就在保姆低頭端碗的時候,一縷頭發從保姆耳邊垂下來,直接晃進了魚湯,頭發在魚湯里劃了一個漂亮的弧線。保姆走向衛生間,仔細地洗了那縷頭發。收拾完那縷頭發,保姆繼續端著那碗加了頭發味的魚湯,向葉拉母親房間走去,盛秋厘往保姆面前一橫,擋住了去路。狠狠地盯著保姆,保姆迎著盛秋厘的目光,毫不退卻,只是人繞了圈,從盛秋厘旁邊走向了葉拉母親房間。
盛秋厘站在葉拉母親的房門口,看著保姆喂那碗魚湯。葉拉母親似乎餓極了的樣子,用尚能動的一只手,不停地拉碗,要往自己嘴里灌。可她的嘴像壞的,保姆的一勺魚湯,只能進去半勺,還有半勺都順著嘴角流在了圍脖上。
一碗魚湯很快見底了,葉拉母親突然用沒有中風的那只手,一把抓住碗,隨即摔在地板上。保姆習以為常地撿起碗。
碗當然沒有被摔壞,難道葉拉母親摔碗是常事?怪不得專用碗是不銹鋼的。
盛秋厘還是站在葉拉母親的房門口。保姆把碗勺放回洗碗池,又去葉拉母親房間,給她解圍脖。葉拉母親不知道是不是沒吃飽。她含糊不清的語言,很是憤怒,像是在咒罵,同時用她尚能活動的那手掐著保姆的手腕,指甲摳進表皮,血印子都出來了。
保姆忍不住了,接下來的一個動作,讓盛秋厘觸目驚心,保姆朝葉拉母親臉上狠狠地吐了一口痰,轉身就離開。
葉拉母親幾乎是嗷嗷叫了,怎么叫也沒人搭理,盛秋厘愣在門口,保姆沒事一樣在廚房忙活。葉拉母親看著盛秋厘,聲音漸漸低下去,用她那只沒中風的手,從枕頭邊拿出一張抽紙,擦去臉上的口水。
當天晚上,還沒等盛秋厘想好,要不要讓兒子辭退保姆,保姆卻先開口了。保姆跟張守一說,到了發工資的時間了。張守一疑惑地看了保姆一眼,還是拿起手機轉賬了本月的工資。這保姆來這里半年了,從沒主動開口要過工資。果然,后頭還有戲,保姆說明天要回趟老家,家里老人生病了。
第二天保姆真的走了。付了工資再請假,這都是有預謀的,肯定就是不再回來了。
張守一聯系中介,讓盡快再找個保姆。中介回復,他這家保姆難找,要找個不怕苦不怕臟的,關鍵還要力氣大的,所以急不來。
沒了保姆,盛秋厘當然要候補上。早飯很簡單,雞蛋牛奶面包。接著送多多,多多幼兒園離家五百米。不知道是沒睡醒還是什么的,沒走到一百米,多多要奶奶抱。盛秋厘因為老張的事傷心過度,大傷元神。哪抱得動多多走幾百米路。盛秋厘左哄右哄,多多就是蹲在路邊不走。后來盛秋厘發火了,多多才勉強起來,邊走邊哭,說這個奶奶沒有保姆奶奶好。
盛秋厘的心里被多多給弄得亂糟糟的,去超市買了兩三個菜。回到家,葉拉母親的聲音一陣高過一陣,對的,換尿不濕的時間到了。換還是不換呢?
糾結中的盛秋厘先去廚房,可葉拉母親的叫聲越來越響,最后幾乎是慘烈。盛秋厘只能硬著頭皮上。葉拉母親看見盛秋厘進來,嘴里嘰里咕嚕的像是抵抗。她雖中風,腦子還是好使的,她不肯親家母伺候自己。
雖然葉拉母親沒有交談的能力,盛秋厘還是告訴她,保姆有事回家了。說著盛秋厘輕輕掀開葉拉母親腿上的被子,瞬間,臭味像剛放出籠的鳥兒,立刻飛滿了整個房間。盛秋厘一陣反胃,她忍著,給別人擦屎擦尿,除了自己的兒子,這輩子還真的沒干過,可兒子的屎尿沒這么臭啊。就算是多多,盛秋厘也沒有給換過幾回尿不濕,多多是葉拉母親帶大的。人這一生啊,該有多少劫,半劫都逃不過,這不是還債來了?
葉拉母親已經哭得出了聲,盛秋厘來不及哭,換完尿不濕就奔衛生間干嘔,干嘔幾口清水后,盛秋厘也淚流滿面了。
這才小半天,盛秋厘已經覺得日子是熬不下去了。保姆什么時候來,是個未知數。
中午的飯只準備兩個人的,盛秋厘煮了青菜粥,番茄炒蛋。她把雞蛋夾成小碎塊,放在菜粥里。盛秋厘先給葉拉母親系上圍脖,然后喂她,只能半勺半勺的喂,不然外溢的較多,房間里還有難聞的渾濁氣味,床上是癱瘓的形容枯槁的老人,葉拉母親邊吃飯邊流淚,盛秋厘從心底涌上一股悲涼。
下午的時間是打掃衛生和煮晚飯,還要接孩子。好在多多放學時沒有要奶奶抱,好像精神十足。盛秋厘和多多恰好相反,此時她已經很疲倦了。等到把晚飯忙好時,盛秋厘頭暈,美尼爾氏綜合癥犯了。她飯都沒吃,就上了床。
張守一和葉拉一進家門,葉拉母親在房間拼命叫,小夫妻倆來到床邊,猜測了半天,才知道葉拉母親,要求把自己送進養老院,不送進養老院,她表示自己再也不吃飯。
小夫妻倆又來到盛秋厘的房間,喊盛秋厘起來吃晚飯,盛秋厘頭暈得起不來。葉拉在一旁道歉,說都是因為照顧她母親給累的。
當晚,小夫妻倆聯系了本市最好的康復醫院,決定將葉拉母親送進康復醫院。
所謂康復醫院,其實就是個養老的地方。條件相當不錯,日夜有護工照顧,像葉拉母親這種生活不能自理的,護工每兩個小時要給病人翻一次身,護工不可偷工減料,有攝像頭呢。每個人的食譜都要針對個人的情況特定的。
張守一又請來了保姆,這次請保姆容易多了,少了一個身體健壯的條件,來了個二十幾歲的小姑娘。
盛秋厘身體時好時差,腰疼要貼膏藥,活血要吃中藥,弄得家里像藥房,時時彌漫著濃濃的藥味。如此的光景持續了一個多月。葉拉的臉色沒那么好看了,有時候連晚餐桌上小夫妻倆也在爭論。不過,到底爭論什么,盛秋厘聽不懂,估計在說這藥味的事。不然,他們為什么用英語爭論,為什么偏偏讓自己聽不懂呢?盛秋厘自己去辦手續,也住進了康復醫院。
剛開始住進去,盛秋厘感覺還好,像她這種能下地活動的,上午九點還有個保健操時間。沒有了一個人住在家里的寂寞,也沒有了住在兒子家的不安。
幾個月后,盛秋厘感覺就不大對勁了,一些能做保健操的人有幾個相繼躺床上去了,一些躺床上的又相繼有幾個變成空床位了。像這深秋樹上的葉子,只見掉落,不見新生。
老張已經走了十三個月,這些天盛秋厘總是夢見老張,她想回家一趟,去公園坐坐。
盛秋厘坐在那條斑駁的長條木椅上,輕聲說:“老張,我看你來了”。出去了整整一年,盛秋厘發現,自己的心突然安靜了,魂還是在這里。盛秋厘環顧四周,公園里的一切照舊,只是樹葉有些稀疏了。老張喜歡的那棵銀杏樹,沒幾片樹葉了,像老人的頭發或牙齒,屈指可數。
小虎!真的是小虎!不知它從哪里冒出來的。小虎更老了,它的毛發像枯草,那雨水沾不住,油花水亮的毛發,遺落在歲月里。它圍著木椅轉了一圈,對著盛秋厘搖了搖尾巴,就又坐在那尊石像旁,依然那個姿勢,依然那個位置。
盛秋厘淚光閃閃地看著小虎,又突然轉頭向上看,她看見老張在云端向她招手,并真真切切地喊了她一聲:“小厘!”
盛秋厘覺得自己的身子越來越輕,越來越輕,像飄向天上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