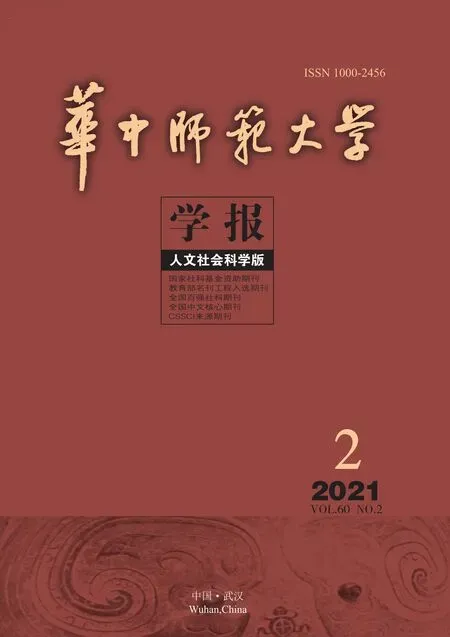智能多樣性與機器人“無心有智”論
楊足儀 向鷺娟
(華中師范大學(xué) 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 湖北 武漢 430079)
人工智能(簡稱AI)的迅速發(fā)展對人類的衛(wèi)生、保健、通訊、交通、軍事、教育、文化、政府、社會治理等造成多方位的巨大影響,以至有人驚呼人類已進入了“智能社會”。目前,有包括中國、美國、英國、日本、印度、新加坡等十多個國家和歐盟宣布了本國或地區(qū)的人工智能戰(zhàn)略。俄羅斯總統(tǒng)普京更是預(yù)言,能夠領(lǐng)導(dǎo)人工智能發(fā)展的國家將是“世界的統(tǒng)治者”。
當(dāng)人類大舉開發(fā)人工智能,當(dāng)智能機器可以像人類一樣自己計算、自己決策時,我們不禁要問:人工智能到底有多“能”?它能如人類一樣“能掐會算”嗎?人工智能與人類智能之間有何區(qū)別?要弄清這些問題,勢必又涉及下面的問題:什么是智能?智能劃分的標(biāo)準(zhǔn)是什么?它是不是人類特有的?顯然,這些已經(jīng)不僅僅是科學(xué)的問題了,還涉及哲學(xué)等問題。美國AI專家盧格爾(G. E. Luger)指出:“如果人工智能的工作想要達(dá)到科學(xué)的水平,我們還必須處理一些重要的哲學(xué)問題,尤其是那些與認(rèn)識論有關(guān)的問題,或是智能系統(tǒng)是怎樣‘知道’它的世界的問題。”①科學(xué)家彭羅斯(R. Penrose)也說,人工智能終究無法回避“思維的功能在何種程度上依賴于和它相關(guān)聯(lián)的身體結(jié)構(gòu)?精神能否完全獨立于這種結(jié)構(gòu)?……相關(guān)結(jié)構(gòu)的性質(zhì)必須是生物的(頭腦)嗎?”②無疑,這些問題的積極探索與深入思考,既具有重要的工程技術(shù)意義,又有人工智能的哲學(xué)意義。
一、機器人“無心”但不一定無智能
問機器智能到底有多“能”實際上就是問:機器人是否有像人類一樣的“心眼”?或者說,智能機器是否如人一樣有一顆充滿靈性的心靈?要弄清楚這個問題,就得以人心為智能的“原型實例”,探討下列問題:人“心”或“心靈”究竟是什么?機器智能有“心”嗎?機器是如何“計算”和“算計”的?現(xiàn)代人工智能是否能跨越通向人類智能的鴻溝呢?這需要哲學(xué)和眾多學(xué)科的跨界聯(lián)合,開展集成研究。
“心”或“心靈”究竟是什么?這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是包含著許多問題的問題域,如“心靈”的語詞、概念問題,心靈的本體論地位問題,心靈內(nèi)容,心靈結(jié)構(gòu),心靈特性,心與身、心與世界的關(guān)系以及普通人的心理結(jié)構(gòu)、心理運動學(xué)、動力學(xué)、原因論等。高新民教授曾將這些“硬核”集中概括為心靈語義學(xué)問題與心理語言的本質(zhì)問題、心理現(xiàn)象學(xué)問題、心靈本體論問題、心靈認(rèn)識論問題以及心理現(xiàn)象的獨特特征等五大問題③。
人類對人自身的心身認(rèn)識是從心和身兩個方面切入的。從詞源學(xué)和詞義學(xué)的視角看,“心靈”(mind)是從古老的“靈魂”(soul)演變而來的。古代世界大多數(shù)民族都有靈魂觀念,古希臘人把它叫作“psyche”,古羅馬人稱“普紐瑪”,古印第安阿爾袞琴部落人叫“奧塔赫朱克”,阿比彭人叫“洛阿卡爾”,祖魯人則稱“吞吉”④。中國古代,靈魂往往與神靈或鬼魂掛鉤,“神為魂,靈為魄。魂魄者,陰陽之精,有生之本也。及其死也,魂氣上升于天為神,體魄降于地曰鬼”⑤。即所謂“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古人的靈魂信仰其實就是將人二重化:人是肉體實在的人和無形靈魂的人,即相信兩個實體的存在。原始思維在把握靈魂的人時,往往以直觀、想象、類比、猜測、隱喻等方式比附這個世界的神秘,并用“命名式”給“靈魂”安名立姓,這就產(chǎn)生了“心”、“心靈”、“靈魂”等各種各樣的心理詞語,這也表明古人已經(jīng)涉及靈魂及其與身體的關(guān)系問題。
科學(xué)時代,傳統(tǒng)哲學(xué)構(gòu)筑的心靈宇宙不斷瓦解,神秘的靈魂不斷地“祛魅”,心靈問題演變?yōu)樾睦韱栴}、心腦問題,被納入更廣闊的科學(xué)視野之中,成為哲學(xué)探討之外,還包括了對作為具體經(jīng)驗科學(xué)的心理學(xué)、腦科學(xué)、神經(jīng)科學(xué)、醫(yī)學(xué)、生理學(xué)、人工智能、語言哲學(xué)等眾多學(xué)科的研究對象。迄今,對意識的跨學(xué)科、多學(xué)科的研究中,形成了認(rèn)知心理學(xué)、人工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認(rèn)知神經(jīng)科學(xué)(即NCC進路)及生成認(rèn)知等四種(也稱4EC進路)并行不悖的研究進路和方法策略。其目的是模擬人腦的結(jié)構(gòu)、機能、性質(zhì)及動力系統(tǒng)的機制,確定心智能力,尋找智能計算結(jié)構(gòu)和意識的神經(jīng)相關(guān)物,將心—身難題轉(zhuǎn)化為身—身問題,以消解“解釋鴻溝”。
當(dāng)代,多路并進的研究形成的科學(xué)的心理圖景和心身學(xué)說,揭示了人類心靈宇宙的地形學(xué)、地貌學(xué)、動力學(xué)及結(jié)構(gòu)論和原因論,為我們刻畫了一幅大腦新世界:在靜態(tài)結(jié)構(gòu)上,大腦由一千多億個神經(jīng)細(xì)胞組成,整個大腦包括兩個半球,其功能既分化又整合,具有高度特異化的功能;在動態(tài)結(jié)構(gòu)上,大腦是一個功能分布式的復(fù)雜結(jié)構(gòu),心理、意識活動就是由這個特殊而又復(fù)雜的結(jié)構(gòu)系統(tǒng)完成的⑥。科學(xué)證明:在大腦系統(tǒng)中,不存在控制中心,沒有獨立存在的“心靈”。所謂的心靈或意識是什么呢?著名生理學(xué)家克里克的“驚人假說”指明,意識是“神經(jīng)元以40-50赫茲頻率發(fā)放”⑦。意思是意識是對神經(jīng)元行為的一種描述方式,好比我們說“水”和“H2O”時一樣,是對同一個東西的兩種描述方式。神經(jīng)學(xué)家埃德爾曼的“動態(tài)核心假說”(the reentrant dynamic core)認(rèn)為,意識是大腦的神經(jīng)元群在幾分之一秒內(nèi)強烈地相互作用形成與腦其余部分有明顯功能性邊界的神經(jīng)元群聚類(functional cluster),即“動態(tài)核心”,而意識的主觀特性即所謂的“難問題”實際上就是對動態(tài)核心的高階分辨(high-order discrimination)。至于意識的“劇場假說”、“探照燈假說”、“微管假說”、“樹突子—心理子假說”、“心理神經(jīng)一元論”等各種意識理論,其主導(dǎo)傾向都是唯物主義的當(dāng)代形態(tài),是人類對自身宇宙之謎的一種最新解答,體現(xiàn)了在意識研究問題上的跨學(xué)科的綜合性與科學(xué)前沿性。
不可否認(rèn)的是,時至今日,古老的靈魂觀念至今仍以三種基本形式存在著并產(chǎn)生影響:一種是“民間心理學(xué)”(簡稱FP),這是前科學(xué)的常識概念框架,是遠(yuǎn)古靈魂觀念改頭換面后繼續(xù)潛入、內(nèi)化于文明社會的思想觀念之中,成了人的文化心理結(jié)構(gòu)以及關(guān)于人、關(guān)于世界的常識圖景,是“我們對人的認(rèn)知的、情感的和目的性本質(zhì)的最基本理解”⑧。第二種是二元論,這是深藏于哲學(xué)、心理學(xué)、腦科學(xué)等具體科學(xué)之中成為許多科學(xué)理論的基本預(yù)設(shè)和本體論承諾。在這種概念體系中,原始的靈魂往往被當(dāng)作獨立精神實在而承諾下來,進而探討心與身、心理世界與外部世界的關(guān)系,從而形成了二元論及其發(fā)展譜系。至今,大多數(shù)哲學(xué)家和心理學(xué)家心底回蕩的是二元論的幽靈。第三種是心身同一論。這種形式中的靈魂觀念同化于一元論的框架之中,形成對身心統(tǒng)一的理解,如當(dāng)代英美哲學(xué)舞臺上活躍的各種形式的物理主義(還原的、非還原的)對心的性質(zhì)所做的形而上學(xué)的解釋。身心同一論盡管規(guī)避了人的二重化斷裂,達(dá)到了身心的統(tǒng)一,但實際上,它并未擺脫二元論的臼窠。如唯心主義一元論將心靈拔高為唯一本原,比二元論更加激進,而唯物主義一元論在理解大腦和思維時,又把笛卡爾的精神實體請了出來,它們的骨子里始終附著著民間心理學(xué)及其二元論的幽魂。
可見,研究心靈的本質(zhì)就是要把心理實在、心理狀態(tài)、心理現(xiàn)象和心理觀念、心理語言區(qū)別開來,以確定我們是在什么意義上談?wù)摰摹?茖W(xué)已經(jīng)證明,大腦中只有神經(jīng)元、神經(jīng)元結(jié)構(gòu)、神經(jīng)活動和狀態(tài);大腦無心,大腦中沒有“機器幽靈”。就心靈的本體論和實在性來說,它就是“身體活動”,心靈和意識是對“身體活動”的一種描述或解釋。
既然人無“心”(mind),而機器智能主要是以人心為智能的“原型實例”而對人類智能的模擬,這種模擬無論是從結(jié)構(gòu)上、功能上還是狀態(tài)或別的模擬,究竟在什么意義上說機器有“心”,在什么意義上說機器無“心”的問題也就很清楚了:機器人“無心”但不一定無智能。
二、智能解剖的“原型實例”與機器智能新論
當(dāng)智能機器像人類一樣會“算計”時,我們勢必要問:人工智能究竟有多“能”?何為智能?劃分智能的標(biāo)準(zhǔn)是什么?人工智能與人類智能有何區(qū)別?人工智能會取代人類智能嗎?
目前,從特定的角度看,人工智能確實在某些方面顯示出超越人類智能的本領(lǐng),人工智能的開發(fā)也取得了許多突破性進展,如俄羅斯團隊開發(fā)的“Eugene Goostman”軟件通過測試,被33%的對話參與者認(rèn)為是人類。以深度學(xué)習(xí)為主要原理開發(fā)的圍棋程序Alpha Go和采用古典線性計算的撲克機器人Libratus在與人類高手的對決中大獲全勝,凸顯出人工智能的巨大優(yōu)勢,以致支付公司聯(lián)合創(chuàng)始人伊隆·馬斯克(E. Musk)、微軟公司聯(lián)合創(chuàng)始人比爾·蓋茨(B. Gates)都公開宣稱,計算機的智能潛力遠(yuǎn)超人類,人工智能是人類最大威脅之一。
但深入其中就會發(fā)現(xiàn),AI的研究實際上碰到許多攔路虎,步履維艱。一些人甚至提出,已有的人工智能并不是真正的智能,就像弗里德曼(D. Freedman)所說:“近四十年光景里,人工智能領(lǐng)域并沒有什么實質(zhì)性的突破。”⑨杰夫·霍金斯(J. Hawkins)也對AI研究提出嚴(yán)厲批判,認(rèn)為“人工智能正面臨著一個根本的錯誤,因為它無法圓滿地解決什么是智能的問題,或者說‘理解某個事物’到底意味著什么。回顧人工智能的發(fā)展史及其建立的原則,我們可以看到這一領(lǐng)域的發(fā)展偏離了正確的方向”⑩。可見,AI研究首先必須弄清楚機器智能的“原型實例”,確定智能的樣式和標(biāo)準(zhǔn)以實現(xiàn)智能。
回顧人工智能發(fā)展史,會發(fā)現(xiàn)智能專家基本上是以種種“原型實例”為智能研究的樣式的,如自然算法中的進化算法、群智能算法、退火算法等。
所謂自然算法就是轉(zhuǎn)向自然,研究大自然是怎樣設(shè)計和締造智能的歷史過程,弄清智能的根源和機理去模擬非人事物表現(xiàn)出的智能現(xiàn)象。這類研究往往是以自然界典型的生物系統(tǒng)和物理系統(tǒng)的相關(guān)功能、特點和作用機理為基礎(chǔ)而建立的有別于以人類智能為模擬的“原型實例”的一種人工智能算法,包括遺傳算法、蟻群算法等種種形式。持這種主張的智能專家認(rèn)為,智能的標(biāo)準(zhǔn)在于能解決問題,表現(xiàn)為生存下來,有適應(yīng)性等。盧格爾就指出,“智能世界就是生存下來的世界”,“分布的基于主體的結(jié)構(gòu)和自然選擇的適應(yīng)性壓力綜合在一起,形成了智力的起源和運作的強大的模型”。
根據(jù)自然算法的能解決問題的智能標(biāo)準(zhǔn),生物的進化被看作問題求解尋優(yōu)的過程,即能夠在不同的環(huán)境中尋求最優(yōu)生存的能力。進化計算正是通過對生物進化的過程與機理的模擬,形成了各種計算形式,如遺傳算法、進化策略、進化規(guī)劃、協(xié)同進化算法、拉馬克克隆選擇計算等。它們不僅發(fā)現(xiàn)了生物智能,確認(rèn)了智能的多樣性,并力圖將其運用到機器上,產(chǎn)生了大量新的人工智能形式。
群智能算法是在對蟻群、鳥群覓食行為的觀察與模擬基礎(chǔ)上產(chǎn)生的。人們發(fā)現(xiàn)原本沒有或只有很少智能的個體集合在一起,相互作用,能顯現(xiàn)出群智能,解決原本只有人類才能解決的問題,甚至由于其群體特性,能更好地適應(yīng)環(huán)境的變化,表現(xiàn)出某些優(yōu)于人類智能的特點。如蟻群算法“針對的是離散的優(yōu)化的問題”,在機器上的實現(xiàn)能夠更快、更精確地解決各種分配問題、子集問題、機器學(xué)習(xí)問題等。粒子群算法是基于群體協(xié)作的隨機搜索算法,能夠通過迭代找到最優(yōu)解。
退火算法則模擬的是無生命的自然事物的退熱過程及機理,如將金屬物體降溫過程中的自然規(guī)律引入優(yōu)化機制,就能夠解決大規(guī)模的優(yōu)化組合問題。作為一種隨機尋優(yōu)算法,它根源于自然事物本身固有的聚集性與彌散性,既能“引導(dǎo)分析進而聚集到最優(yōu)點所在的區(qū)域”,又能“把分析分散到其他區(qū)域,減少遺漏最優(yōu)點的概率”,表現(xiàn)出人類智能遍歷和收斂的特性,體現(xiàn)出獨特的智慧特征。
解剖智能的“原型實例”說明,“人并不是唯一有智能的動物,地球生命活動中的生物進化、個體發(fā)育和免疫、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大腦思維、社會系統(tǒng)、生態(tài)系統(tǒng)都表現(xiàn)出了某種形式的自然智能”,由此引發(fā)了關(guān)于智能及其標(biāo)準(zhǔn)的爭論。高新民教授將人工智能的劃分標(biāo)準(zhǔn)主要歸結(jié)為計算主義的智能標(biāo)準(zhǔn)、反計算主義的智能標(biāo)準(zhǔn)、介于二者之間的智能標(biāo)準(zhǔn)以及新生的外在主義的智能標(biāo)準(zhǔn)。
計算主義的智能標(biāo)準(zhǔn)認(rèn)為,智能在本質(zhì)上就是計算,人類的思維是受規(guī)則控制的,可以通過純形式的轉(zhuǎn)換得以實現(xiàn)。盡管對計算的邏輯闡述有多種,但都試圖從形式上說明計算的概念,將其看作獨立于物理實在的屬性。計算主義強調(diào)推理的有效性取決于形式的形式主義越來越受到質(zhì)疑。聯(lián)結(jié)主義(廣義計算主義的一員)對此進行了一定的修正,認(rèn)為智能的基本元素不是符號,而是神經(jīng)元,利用生物大腦結(jié)構(gòu)構(gòu)建的人工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能夠從計算上實現(xiàn)直覺、經(jīng)驗推理等能力,從而克服符號計算結(jié)構(gòu)的局限性。
反計算主義的智能標(biāo)準(zhǔn)則主張,智能的本質(zhì)在于有意向性,即在于所處理的內(nèi)容與外部世界的關(guān)聯(lián),而不只是形式上的轉(zhuǎn)換。其著名代表塞爾(J. R. Searle)認(rèn)為,意向性是以特定生物組織,即經(jīng)過漫長進化的生物大腦為基礎(chǔ)的一種生物現(xiàn)象,“無論大腦在產(chǎn)生意向性時所做的是什么,都不可能存在于例示程序的過程中,因為沒有一個程序憑借自身而對于意向性來說是充分的”。在塞爾看來,計算機與人一樣進行文本處理、理解規(guī)則,與外部世界發(fā)生關(guān)系,看似有意向性,其實,機器的轉(zhuǎn)換只是一種純形式的轉(zhuǎn)換,這種意向性最多是派生的,與人的原始意向性有根本的區(qū)別。他斷言,已有的AI由于沒有意向性就不是智能。盡管塞爾的觀點遭到了不少的反駁,但贊揚與肯定之聲仍是主流,認(rèn)為他揭示了人類智能意向性的根本特征,以及AI研究陷入困境的根源。
介于計算主義和反計算主義之間的智能標(biāo)準(zhǔn),可以說兼有上述二者的特點。如哈瑞(R. Harré)肯定了塞爾將意向性作為智能標(biāo)準(zhǔn)的合理性,但又認(rèn)為意向性是屬人的,而不是大腦,大腦只是人思考的一種工具,計算機卻“可能是人的大腦的一個好模型”。彭羅斯提出人類的智能離不開意識,“如果沒有意識相伴隨,真正的智慧是不會呈現(xiàn)的”。而意識具有主動性,能夠做出判斷,以算法為基礎(chǔ)的人工智能根本無法實現(xiàn)智能,只能將希望寄托于量子計算機。
新生的外在主義智能標(biāo)準(zhǔn)則認(rèn)為,智能并不存在于人的頭腦之內(nèi),而是以非單子性的、跨主體的、關(guān)系性的方式,彌散在主客之間。它強調(diào)外在對象、環(huán)境等情境因素對智能的產(chǎn)生具有重要作用,從而導(dǎo)致了寬智能觀的產(chǎn)生。
如此眾多的智能標(biāo)準(zhǔn)使得人工智能難以擺脫目前的困境。反計算主義雖然指出了人類智能區(qū)別于人工智能的根本所在,但無法說明人類的有些智能現(xiàn)象,如純粹的計算活動、數(shù)學(xué)運算、專家編程等并沒有意向性。由此,也就不能完全否認(rèn)現(xiàn)有的人工智能所表現(xiàn)出的推理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專家系統(tǒng)等與智能無關(guān)了。泛智能主義將智能擴展到非人的自然事物上,認(rèn)為智能不僅廣泛存在于自然界、人類社會,還能為人類所創(chuàng)造,從而產(chǎn)生了模擬自然事物功能的自然計算等,推動了人類對智能的認(rèn)識。但從人工智能的目的即模擬甚至超越人類智能來看,對非人事物功能的模擬并無實質(zhì)性意義。
迄今,人類智能依然是未解之謎。但是,科學(xué)已經(jīng)揭示它是由許多不同類的現(xiàn)象所組成的集合體。人類智能是由“不同種類的智能成分,通過它們之間的各種相互作用進行不同形式的集成過程,構(gòu)成不同層次和不同性質(zhì)的智能集成體,在一定條件下智能集成體涌現(xiàn)新的特性”。即智能具有多種多樣的樣式、性質(zhì),并且處于不斷的生成中。在此意義上,很難對智能做統(tǒng)一、固定的把握,但這并不代表就無法認(rèn)識。智能作為一種心理現(xiàn)象,有其外在的行為表現(xiàn),并且隨外部環(huán)境的變化,表現(xiàn)為多種不同的智能形式,能“在空間和時間中進化并不斷自我校正”。每個智能實際就是一種功能模塊,集合在一起形成不同的能力。因此,AI研究應(yīng)當(dāng)在堅持智能多樣性的基礎(chǔ)上,以具體的人類智能的個例為模型建構(gòu)人工智能,從而實現(xiàn)飛躍式發(fā)展。
三、機器智能的“計算”與“算計”
毫無疑問,智能機器有智能。那么,這是否意味著機器人可以像人類一樣會“計算”和“算計”?機器人的“計算”和“算計”如何實現(xiàn)呢?
國際計算理論家、人工智能專家馬爾曾將機器計算之事歸結(jié)為三步走:第一步,把要處理的現(xiàn)實問題抽象成一個可以清晰定義的問題;第二步,能清晰定義的問題是否是能計算類的問題;第三步,在可計算的范圍內(nèi)找到算法,并在機器上執(zhí)行運算,完成計算。目前,人工智能在這三個方面所做的大量計算的局部領(lǐng)域遠(yuǎn)遠(yuǎn)超出人類的計算能力。然而,機器智能要像人類一樣“算計”,必須要解決三大問題:一是意義問題,二是意識與意識體驗問題,三是自主性與覺知問題。其中,意義問題可以歸結(jié)為語義問題,即,機器理解語言嗎?意識、意識體驗與覺知的問題可以歸結(jié)為意識的特性問題,尤其是意識的感受性問題,即“意識的難問題”。而這三個問題又可以總歸為一個問題,即“意向性缺失難題”,這是當(dāng)前制約人工智能發(fā)展的瓶頸問題。
“意向性”(intentionality),是指意識、心理指向于或關(guān)聯(lián)于外物的傾向性和能力,就是某種“關(guān)于性”(aboutness)。“意識狀態(tài)指向某些東西,即使它指向的東西不存在,它仍是有意向性的。在很多情形中,意識實際上是意識到某物,而‘意識到’中的‘到’是關(guān)于意向性的。”我們?nèi)祟愐揽恳庀蛐裕梢詫ν獠渴澜缱龀龇磻?yīng),形成具有意義的意識思想。也就是當(dāng)我們把握外在對象時,在心靈、思維中把對象呈現(xiàn)出來,通過意向性把握這種內(nèi)在的對象。而對意識的對象、內(nèi)容進行描述、表達(dá)時,必須使用語言、符號描述和表征心理活動、心理過程、心理狀態(tài)和心理屬性,這就是心理語言。如“想”、“愿望”、“相信”、“心靈”、“意識”等,盡管它們是常識心理學(xué)的語言,現(xiàn)在也成了科學(xué)心理學(xué)的術(shù)語。
當(dāng)代神經(jīng)科學(xué)、心理學(xué)研究表明,當(dāng)人們用心理語言如實地報告自己大腦內(nèi)部過程或狀態(tài)時,確定發(fā)生了其對應(yīng)的、有本體論地位的東西,絕不是子虛烏有。當(dāng)然,存在的東西怎樣去設(shè)想、解釋與構(gòu)建則是另一回事了。無論怎樣解釋心理事件及其狀態(tài)與過程,都必須借助于語言,即主要從語形、語義、語用三個維度進行語言分析。語言分析學(xué)、分析哲學(xué)通過對心理語言的發(fā)生學(xué)路徑及對心理語言的“語法分析”、“用法分析”與澄清,還原心理語言所表達(dá)的“原旨原意”。對于人類的心身事件,我們已經(jīng)認(rèn)識到思維運動形式的多樣性,并用“想”、“思考”、“憤怒”、“喜悅”等豐富的語詞來描述大腦內(nèi)的心理活動的多樣狀態(tài)。至于說這樣的心理活動是機械運動、物理運動、化學(xué)運動(如電沖動、神經(jīng)遞質(zhì)的傳遞)還是更高階的運動形式,這就需要神經(jīng)科學(xué)、物理學(xué)、化學(xué)、生物學(xué)、醫(yī)學(xué)、心理學(xué)、哲學(xué)等多學(xué)科的聯(lián)合研究。
科學(xué)揭示,人類心理活動是物質(zhì)的高階活動,心理語言表述的是物質(zhì)活動的高階運動。人類“意識”活動的層次應(yīng)是大腦皮層回路、皮層區(qū)域間有放電模式參與的動態(tài)自組織層次,“‘意識’一詞縱有多種涵義,也不能在低層次的化學(xué)水平上或甚至是更低層次的物理水平上來加以解釋。我把這種自量子力學(xué)這個下層地下室向意識閣樓的跳躍的企圖稱作‘司閽之夢’”。克里克、埃德爾曼、李別特等著名神經(jīng)科學(xué)家的實驗科學(xué)成果,對我們觀察、探尋人腦內(nèi)發(fā)生了什么,查明心理語言的真實所指與意義,不僅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資源,而且更加確證了恩格斯、列寧一再強調(diào)的思維運動是物質(zhì)的高級運動形式。
總之,意向性、語義性、意義性及內(nèi)容性是人類智能指向外部世界的根本特性。正是因為意向性,人才能自主地將被加工的對象與外部世界關(guān)聯(lián)起來,表現(xiàn)出主動性、靈活性與意識性。
當(dāng)前,人工智能在大量計算的局部領(lǐng)域遠(yuǎn)遠(yuǎn)超出人類的計算能力,如在深度學(xué)習(xí)、大規(guī)模計算、邏輯推理、面部識別、語音轉(zhuǎn)換、復(fù)雜的游戲、疾病診斷、自動駕駛等方面進展快速,Alpha Go以及日本的Fugaku(富岳),美國的Summit、Sierra,中國的神威“太湖之光”(Sunway Taihulight)、天河二號(TH-2),意大利的HPC5等計算機的超級運算能力震撼了人類。而這些系統(tǒng)是多個人類個體和多臺機器網(wǎng)絡(luò)、大數(shù)據(jù)平臺和云計算平臺即時連接成的并行的集群式智能,包含著以人的認(rèn)知為核心的認(rèn)知能力和智能的特征及其本質(zhì)。
從形式上看,計算機所做的運算與符號加工,如財務(wù)管理、智能辦公、智慧社區(qū)、智慧城市、尚克的能理解故事的系統(tǒng)等所做的復(fù)述幾乎都是事關(guān)外在事態(tài)的,照說是有意向性、語義性的。但是,這種意向與人類原始固有的意向性不同,它是派生的意向性。對此,卡明斯(R. Cummins)做了獨到的分析。他指出,計算機在做運算時產(chǎn)生了三種關(guān)系:硬件狀態(tài)間的關(guān)系、計算機狀態(tài)間的關(guān)系以及計算符號與外在對象間的關(guān)系。這三種關(guān)系以及三種關(guān)系之間不是自身自然產(chǎn)生出來的,而都是基于設(shè)計的程序和操作人員的解釋,是外部強加的,不是機器智能固有的意向性,即塞爾所說的不過是存在于計算機編程和使用者心里的“信息加工”,這個事實是在計算機范圍之外的事。
目前,機器智能工作基本都是句法形式的轉(zhuǎn)換,即計算機科學(xué)家威爾遜(S. Wilson)所說的機器智能“不會直接從周圍環(huán)境中汲取所需,而只能坐在那兒,直到人們給它們信號,然后也僅僅是復(fù)制這些信號而全然不知它的意義”。克里克說,在觀察和理解物體意義時,“即便是最現(xiàn)代的計算機也顯得無能為力”。正因如此,斯蒂克(S.Stich)、丹尼特等認(rèn)知科學(xué)家稱智能機器只是句法機,不是語義機,這就是困擾當(dāng)前人工智能發(fā)展的“意向性缺失難題”。
究竟如何破解“意向性缺失難題”呢?目前,國際上以麥金(C. McGinn)的“意向性建筑術(shù)”、尼倫伯格(S. Nurenburg)等人的本體論語義學(xué)、卡明斯(A. Cummins)的解釋語義學(xué)及布魯克斯(R. Brooks)的無表征智能理論對“意向性缺失難題”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在此,僅就“意向性建筑術(shù)”、本體論語義學(xué)做簡要闡述。
既然意向性是人工智能與人類智能的根本差別,那么,要想建構(gòu)真正的人工智能,首先必須弄清楚意向性究竟是如何產(chǎn)生的。麥金提議通過向大自然學(xué)習(xí),著力研究人的意向性是怎樣被大自然締造出來的,以探討意向性的建筑術(shù)。他認(rèn)為思維以心理模型為基礎(chǔ),主張利用模型方法,研究意向性的機制,弄清“內(nèi)容的結(jié)構(gòu)基礎(chǔ),即讓認(rèn)知機制成為可能的條件”。在分析克賴克(K. Craik)、約翰遜-萊爾德模型論的基礎(chǔ)上,他提出“模型憑自己就足以實現(xiàn)內(nèi)容,而不依賴于其他的表征系統(tǒng)。因此模型為關(guān)于內(nèi)容的理論提供了一種自足的基礎(chǔ)”。然而,模型也受到塞爾“中文屋論證”的挑戰(zhàn),以及難逃“小人難題”。于是,麥金強調(diào)需要將心理模型置于因果—目的論之中,實現(xiàn)目的論與模型論的結(jié)合。在他看來,大自然的進化之手已經(jīng)為人類安裝好了特定的心理模型,能夠按照某種規(guī)則起作用,但模型只是實現(xiàn)意向性的基本結(jié)構(gòu),本身并不是意向性。只有將模型置于一定的包含著目的、行為傾向、因果相關(guān)事態(tài)的背景之中時,才能顯現(xiàn)內(nèi)容、產(chǎn)生意義。
本體論語義學(xué)是破解“意向性缺失難題”的另一條重要徑路,具有極強的實踐和工程技術(shù)價值。其倡導(dǎo)者尼倫伯格甚至公開宣稱它能使機器具有語義學(xué)或意向性。從語義學(xué)上看,能處理語義是人類語言能力最根本的特征。“人工智能如果不能使用自然語言作為其知識表示的基礎(chǔ),建立不起不確定性人工智能的理論和方法,人工智能也就永遠(yuǎn)實現(xiàn)不了跨越的夢想。”20世紀(jì)60年代,自然語言處理產(chǎn)生了以關(guān)鍵詞匹配技術(shù)為基礎(chǔ)的語言理論系統(tǒng),如SIR、STUDENT等;70年代,出現(xiàn)了以句法—語義分析技術(shù)為基礎(chǔ)的系統(tǒng),如LUNAR、SHRDLU、MARGIE等;80年代以后,進入了新的發(fā)展階段,誕生了本體論語義學(xué)等自然語言理解系統(tǒng)。
本體論語義學(xué)認(rèn)為人類智能之所以有意向性、語義性,能夠把符號與外部世界關(guān)聯(lián)起來,理解和產(chǎn)生意義,就在于人有本體論知識,能夠?qū)φZ詞做本體論定位,賦予其特定的語義值。而這里的本體論不同于哲學(xué)上的本體論,指的是人們在日常生活、學(xué)習(xí)中自發(fā)形成的關(guān)于世界上各種事物、屬性、關(guān)系等的一種概念圖式。通過它,任何詞語一旦進入人類視域,都能被快速歸類,置于某一框架之中,賦予特定的屬性。如當(dāng)人們聽到“紅”,立刻就能將其放入相應(yīng)的類別,如是一種屬性,為某物所具有等。因此,本體論語義學(xué)認(rèn)為要使機器像人一樣具有這種能力,首先應(yīng)當(dāng)讓機器也有這種知識,建立相應(yīng)的本體論圖式。
在對人類如何加工自然語言有了較為清晰的認(rèn)識后,就有可能通過模擬類似的條件,讓機器表現(xiàn)出對意義的識別,從而也具有語義加工的能力。尼倫伯格等通過對Stratified模型的分析,指出機器要實現(xiàn)語義加工需要經(jīng)過文本分析、形態(tài)學(xué)分析、詞匯學(xué)分析、句法分析、確定基本的語義從屬關(guān)系等,具備加工器和靜態(tài)知識資源,從而使智能機器不再通過純形式的過程來完成語義分析。
然而,本體論語義學(xué)所生成的意義仍然離不開操作者的解釋,依舊缺乏主動性、自覺性、意識性。麥金對意向性的認(rèn)識也有缺陷,受到民間心理學(xué)、“小人論”等的影響。可以說,無“心”的機器就是目前人工智能的局限。
機器智能要真正突破“意向性缺失難題”,和人類一樣獲取語言加工文本意義的能力,開拓工程實踐朝著應(yīng)用化、實用化、商業(yè)化發(fā)展,就必須努力解開意向性之謎、語義之謎,為機器語言翻譯、信息整合、文本處理、人機深度對話等應(yīng)用技術(shù)提供更堅實的理論基礎(chǔ)。無疑,人工智能的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注釋
③高新民:《西方心靈哲學(xué)的問題、前沿爭論與歷史發(fā)展》,《廣西社會科學(xué)》2000年第4期。
④愛德華·泰勒:《原始文化》,連樹聲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年,第419-420頁。
⑤方向東:《大戴禮記匯校集解》(上),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595頁。
⑥楊足儀:《心靈哲學(xué)的腦科學(xué)維度》,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2011年,第65頁。
⑧P. M. Churchland, “Folk Psychology,” in P. M. Churchland and P. S. Churchland, eds.,OntheContrary, Cambridge: MIT Press, 1998, p.3.
⑨戴維·弗里德曼:《制腦者》,張陌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第29頁。
⑩杰夫·霍金斯:《人工智能的未來》,賀俊杰等譯,西安:陜西科學(xué)技術(shù)出版社,2006年,第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