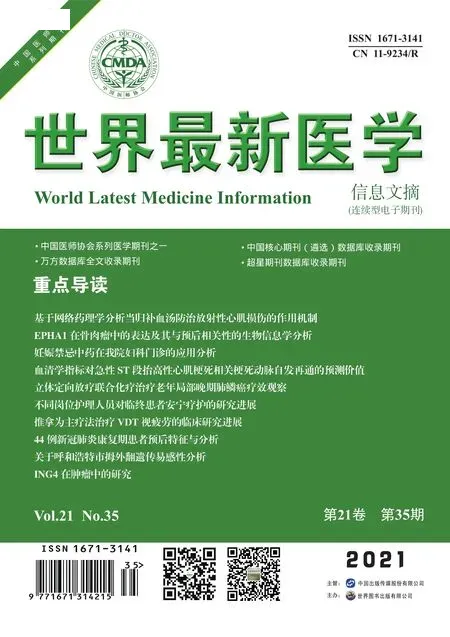慢性炎癥對癌性貧血影響的研究進展
張靖宜,陳乃耀
(華北理工大學附屬醫院,河北 唐山 063000)
0 引言
癌性貧血(CRA),亦被稱為癌癥相關性貧血,是一種常繼發于癌癥,并對患者生活質、治療效果、疾病進展及遠期生存率都存在極大負面影響的臨床癥狀。雖然當前癌癥患者的貧血被廣泛認為與放、化療毒性高度相關,但在開始任何抗腫瘤治療之前,已經有許多患者在初診時出現貧血。從病理生理學上來看,癌癥患者的貧血原因可分為四種既可彼此獨立又能重疊的類別:(1)增殖性貧血;(2)包括常見的炎癥/慢性疾病性貧血(ACD);(3)溶血性貧血;(4)其他病因和不確定的病因[1]。盡管CRA的病因很多,但在臨床研究中,CRA往往會表現出與慢性炎癥性貧血(ACD)相似的血液學特征。近年來國內外研究證實,相關炎性因子(IL-1,TNF-α、IL-6等)及炎癥標志物(C反應蛋白,纖維蛋白原,鐵蛋白,鐵調素,促紅細胞生成素和活性氧等)在癌癥患者體內免疫學改變的影響下,對癌性貧血發生、發展中起著至關要的作用[2]。癌癥患者的CRA患病率很高,但目前在免疫學層面上更為有效的針對癌性貧血的治療手段仍需繼續探索。因此,本文以慢性炎癥對癌性貧血的影響為重點,對癌性貧血的概述及炎性因子在癌性貧血中的作用機制進行綜述,以期對臨床上探索和發展癌性貧血的治療方法有所助益。
1 癌癥貧血的流行病學特征
貧血是癌癥患者最常見的血液學表現,惡性腫瘤患者群體中有40-64%患者患有貧血[1]。同時,癌癥患者的貧血發病率亦因惡性腫瘤原發部位不同而有差異。據我國2015-2016年相關臨床指南顯示,我國癌癥患者中貧血的發病率為60.83%。其中上消化道癌伴貧血發生率最高(66.99%),其次是乳腺癌(64.2%)、肺癌(60.38%)[3]。癌性貧血發生率很高,但當前有關癌性貧血的大型臨床回顧性及前瞻性研究仍較少,因此針對于國內癌性貧血患者的相關臨床統計及對照試驗對我國癌性貧血的深入研究及治療也是十分有必要的。
2 癌性貧血的相關實驗室特征
既往各項研究表明,無特殊情況發生時,癌癥患者的貧血類型常以正細胞正色素性貧血(MCH≥27pg,MCV在80-100 fl之間)為主[4-6]。但當整個癌癥病程是長期的,隨著疾病進展,患者體內的炎癥標志物(包括C反應蛋白,纖維蛋白原,IL-6,TNFα,IL-1β,鐵蛋白,鐵調素,促紅細胞生成素和活性氧)的平均血漿水平升高,由于其所代表的炎癥在鐵代謝中的負面作用,鐵調節肽—鐵調素(hepcidin)水平會顯著升高,患者常出現一種有別于絕對性缺鐵(AID)的特殊性鐵缺乏狀態,被稱為功能性缺鐵(FID),使得患者在體內儲存鐵充足的情況下,循環鐵量不足,血清鐵水平顯著降低,呈現出以CRA為主的貧血情況[7][8]。隨著體內鐵代謝紊亂,且少數由于合并出血或營養等,紅細胞的大小和血紅蛋白含量可以出現不同程度的減少,會出現非再生性正核或微核貧血[9],但在癌癥患者發生癌性貧血的整個病程中,炎癥所誘導的功能性貧血,仍占主導作用。
這種慢性炎癥性貧血作為一種低增生性貧血,盡管存在明顯的長病程持續性貧血,但卻表現為網織紅細胞計數降低(<25,000 / microL)。其他標志性實驗室指標包括血清鐵濃度正常或降低(男性正常范圍為55-160μg/ dL,女性為40-155μg/ dL),總鐵結合能力降低(轉鐵蛋白飽和度STAT<50%),鐵蛋白值正常(30-500 ng/mL)或增加(≥500ng/ mL)[10]。在癌癥患者中,一旦診斷出貧血,患者體內的FID和AID往往會同時出現,因此ACD和IDA也常同時出現[11],這為臨床醫生的診斷和治療造成了一定的困擾。近年來有關應用可溶性轉鐵蛋白受體與log鐵蛋白的比例幫助區分FID與AID相關的貧血癥已經逐漸被主流認可[12]。此外,骨髓涂片普魯士藍染色也可將患者分為IDA和ACD組。成鐵細胞中可染鐵、有核紅細胞前體在IDA和ACD中均減少,巨噬細胞的染色鐵在IDA成陰性,而在ACD中呈陽性[13]。
3 促炎細胞因子對癌性貧血的影響
目前業已廣泛證明,促炎細胞因子,特別是IL-1,TNF-α和IL-6可能通過誘導以下因素影響紅細胞生成:紅系祖細胞的增殖反應減少;巨噬細胞對紅細胞的破壞增加;和減少類紅細胞前體對EPO的反應。此外,這些細胞因子的長期活動是主要導致晚期癌癥患者發生多種代謝和營養變化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促炎性細胞因子通過破壞能量代謝和營養狀況,促進了CRA的發病[2]。
3.1 IL-6
就IL-6而言,它可以通過影響紅細胞生成過程中的不同層面而造成CRA的發生。在許多疾病狀態下,IL-6都與血紅蛋白濃度呈負相關,目前已經提出IL-6是賦予炎癥相關的鐵調素轉錄的主要分子,IL-6-hepcidin抗菌肽軸更是促進功能性缺鐵的發生的主要途徑[14]。IL-6可通過鐵調素啟動子上的信號轉導子和轉錄激活因子3(STAT3)結合位點進行介導,通過內質網應激或氧化引起的肝細胞損傷會增強Stat3活性導致Hepcidin表達增加[19]。嚴重細菌感染釋放的脂多糖(LPS)激活toll樣受體4(TLR4)信號傳導,繼而通過刺激hepcidin表達的巨噬細胞增強IL-6的產生,從而改變正常的鐵代謝,造成CRA典型的功能性鐵缺乏[15]。在經典的BA和松節油小鼠模型中,鐵調素被敲除的小鼠與野生型小鼠相比,貧血和鐵缺乏癥狀會較輕,提示了hepcidin對鐵利用及貧血的意義[16]。但是值得注意的是,hepcidin敲除小鼠仍然表現出一些ACD的特征,包括紅系祖細胞、紅細胞生成和紅細胞數量減少。2014年Langdon JM等人的實驗證明,在BA模型中,IL6基因敲除小鼠也部分受到AI的保護,并且紅細胞生成恢復對速度更快,表明IL6通過抑制紅細胞生成在AI病理生理學中具有獨特的作用[17]。值得注意的是,IL-10可通過抑制炎癥因子,調節STAT3信號通路,下調鐵調素表達和抑制TfR表達來改善鐵代謝并減輕貧血[18]。
IL-6亦可通過其他途徑影響紅細胞生成,2014年McCranor BJ等人實驗使用人類紅白血病TF-1細胞系來模擬紅系使其成熟,并暴露于不同劑量的IL-6,結果證明IL-6可顯著抑制依賴EPO的TF-1紅細胞成熟,盡管IL-6不會降低與血紅蛋白合成相關的基因的表達,但可使得血紅蛋白合成受損,同時,他們還觀察到IL-6下調了在紅細胞生成后期表達的SLC4a1基因的表達。這些發現提示血紅蛋白合成抑制可能與IL-6依賴性有關。同時,他們也證明了IL-6可能在成熟損害線粒體功能細胞導致受損的血紅蛋白生產和紅系成熟,這是一種獨立于hepcidin - Fe途徑抑制Hb合成的機制[14]。
3.2 IL-1與TNF-α
IL-1β可通過刺激CCAAT增強子結合蛋白(C / EBP)δ(一種轉錄因子)的表達,從而導致hepcidin通過hepcidin啟動子上的C / EBP結合位點進行轉錄活化[19]。而對于TNF-a來說,眾多研究證實在癌癥患者體內,TNF-α與hepcidin的變化高度正相關,但2018年Cherry-Bukowiec JR等人實驗提出,hepcidin與TNF-α血清濃度可能無關[20]因此,有關TNF-α與hepcidin的關系,仍需國內外學者繼續探索。除了對hepcidin的直接作用可引起癌性貧血,二者引起癌性貧血的部分原因也應歸因于Epo的合成受損。促炎細胞因子IL-1和TNF-α可抑制體外Epo基因表達和Epo蛋白分泌[21]。2002年La Ferla K 等人研究了轉錄因子GATA-2和NF-κB在人肝癌細胞系HepG2中通過IL-1beta和TNF-α調節Epo基因表達的作用,證明GATA-2和NF-κB似乎都參與了IL-1beta和TNF-alpha在體外對Epo基因表達的抑制作用,并且可能是體內炎癥疾病中Epo合成受損的原因[21]。2017年Cluzeau T等人也證明在骨髓異常綜合征患者中,TNF-α和IL-1β可通過激活GATA-2和NF-κB抑制EPO的轉錄和細胞加工[22]。同時值得注意的是,腫瘤壞死因子-α和白介素-1,也可抑制類紅細胞前體細胞的生成,最終導致貧血的發生[23]。
3.3 IFN-γ的作用
IFN-γ可以引起患者急性貧血的發生,它在體內直接作用于巨噬細胞,以改變內吞作用并引起血細胞攝取,從而導致嚴重的貧血[24]。同時,增加的IFN-γ會對造血干細胞(HSC)穩態產生負面影響,使HSC偏向于自我更新而分化,最終導致HSC區室耗盡[25]。IFN-γ、IL-12和IL-6也可以引起巨噬細胞活化綜合(MAS),而IFN-γ介導的促紅細胞生成不足正是暴發性Toll樣受體9(TLR-9)誘導的MAS 貧血的主要原因[26]。而在多發性骨髓瘤所致貧血中,更是提示了IFN-γ和TNF-α可增加腫瘤壞死因子家族中的Fas在紅細胞上的表達,促進了紅細胞的凋亡[27]。而與此同時,IFN-γ不僅可以阻止了類紅細胞譜系的發生,而且還能加速類紅細胞的分化過程,最終導致紅細胞生成窗的清除。它甚至可以在不存在促紅細胞生成素(EPO)的情況下強大地啟動早期分化[28]。早在2011年Libregts SF等人的實驗證明,IFN-γ可誘導鼠類和人類類紅細胞前體中干擾素調節因子-1(IRF-1)和PU.1的轉錄因子表達,PU-1 可以通過抑制 GATA-1與 DNA 的結合削弱其作用,從而減少了紅細胞的壽命及形成[29]。而2020年Wang W的研究團隊則證明,IFNγ-IRF1軸在紅細胞生成中起著雙向作用,從而阻礙了對紅系譜系的訪問,并推動即將來臨的細胞趨向分化終點前進[28]。
3.4 HMGB1
作為一種非組蛋白染色質相關蛋白,高遷移率族box-1(HMGB1)可從壞死細胞被動釋放或響應炎癥刺激而被免疫細胞主動分泌,并在多種人類疾病(包括自身免疫性疾病,神經退行性疾病和癌癥)中起著關鍵作用。HMGB1的過表達已被證明在多種類型的癌癥中,包括乳腺癌癌,結腸直腸癌,肺癌癌和肝細胞癌[30]。既往研究表明,HMGB1具有上調促炎性介質表達的能力,在健康小鼠中給藥可通過增強TNF和IL-6的釋放來介導貧血[31]。同時,HMGB1作為一種重癥患者體內產生的促炎性細胞因子,也與癌癥患者的死亡率增加相關。2015年,Yang H等人的實驗證明rHMGB1未能引起循環鐵調素的顯著增加,但HMGB1可通過干擾血紅蛋白穩態來誘導貧血,提示HMGB1可能是炎癥性貧血的治療靶標[32]。
4 總結及展望
慢性炎癥在CRA的發生發展及轉歸中起著絕對性的作用,近年來,有關炎癥在癌性貧血中的發生機制已經越來越得到臨床醫生及實驗室工作者的重視,除本文中所描述的幾項炎性因子外,仍有許多炎性因子及其相關作用靶點值得大家去關注。而且,由于臨床上癌癥患者的貧血常混雜多種病因共同出現,能夠做到精確判別癌性貧血并對其進行有效的狀態改善和治療仍是臨床上相對困難的一項診療工作,因此有關CRA的發生及與癌癥進展機制間的重疊和串聯,仍需要得到臨床醫生更高級別的重視。深入了解慢性炎癥在CRA中的影響機制,將對探索癌性貧血更為有效、精準的治療手段產生更大的正面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