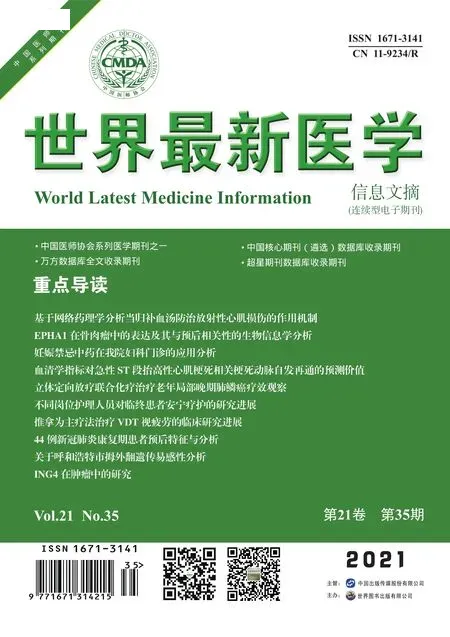腸道菌群和膽結石的研究進展
張乾,左磊,張小冬,溫波,任建軍
(內蒙古醫科大學附屬醫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0)
0 引言
膽結石病是全球范圍的常見病、多發病。在歐洲和其他發達國家[1],膽結石的發病率可高達20%,這也是醫療成本增加的主要因素。而在我國膽結石的發病率約為4.2% ~12.1%[2]。近幾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們生活方式的改變以及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膽結石的患病率處于逐漸上升的趨勢。膽結石疾病是由遺傳、環境、局部、全身和代謝異常等復雜因素相互作用引起的[3]。由于膽結石形成因素多,所以其病理生理較為復雜,主要有以下幾點[4]:致石基因及遺傳因素的不同;膽汁膽固醇分泌不平衡;膽固醇成核異常/結晶;膽囊運動受損;膽囊腔內高分泌和粘蛋白凝膠積聚;免疫介導的膽囊炎癥;腸道因素包括膽固醇吸收、腸道運動遲緩和腸道微生物群改變。隨著腸道測序技術的發展以及對腸道菌群功能的不斷發現,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腸道菌群的動態平衡對人體的健康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近年來相關研究表明,膽石癥患者腸道微生物群的失調可能與膽結石的形成密切相關[4],但腸道菌群影響膽結石形成的機制仍不清楚。因此,本文就腸道菌群與膽結石的相關性及腸道菌群影響膽結石形成的可能機制進行闡述,為腸道菌群在未來膽結石的研究上提供一定的參考依據。
1 腸道菌群的組成及功能
腸道菌群被稱為“我們遺忘的器官”,其擁有多達1000個細菌物種,編碼約500萬個基因,執行宿主生理和生存所需的17種功能[5]。大多數成人微生物群生活在腸道中,僅在人類的結腸中微生物的密度就超過了1011 cell/g,約1-2kg[6]。腸道菌群包括需氧菌、兼性厭氧菌和厭氧菌,以專性厭氧菌或兼性厭氧菌為主。其中擬桿菌門和厚壁菌門的數量占90%以上[7],其余有變形菌門、疣微菌門、放線菌門、梭桿菌門、雙歧桿菌、藍藻細菌等[8]。人體健康與腸道菌群的組成和功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腸道菌群像是我們的一個器官,提供了干預性治療的新路徑。腸道菌群參與物質和能量的代謝,促進免疫系統的發育成熟,形成黏膜屏障,并保護宿主免受病原體攻擊[9-13]。一般情況下,腸道菌群按一定比例組合,各菌群間互相制約、互相依存,在質和量上形成一種動態平衡。但在某些情況下這種平衡被打破,即腸道菌群失調,可導致人類疾病的發生。腸道菌群的失衡與克羅恩病、腸炎、肥胖、糖尿病以及心血管疾病等代謝性疾病有關[14-18]。因此,腸道菌群對人體的健康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2 腸道菌群與膽結石的相關性
基于解剖學的角度來說,認為膽囊通過膽囊管—膽總管—十二指腸,與胃腸道是一個整體,同屬于消化道,腸道細菌可逆行進入膽道,影響膽道細菌,進而影響膽結石的形成。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有學者提出細菌在膽結石發病機制中的重要作用[19]。隨著腸道菌群測序技術的進步,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腸道菌群和膽結石存在著明顯的相關性。吳韜等人[20]利用新興的高通量的二代測序的方法(焦磷酸測序),通過大規模的分析細菌的16S rRNA基因,第一次揭示了膽囊結石患者存在明顯的腸道菌群失調,研究結果發現正常人和膽囊結石患者腸道菌群存在差異,膽結石患者的腸道細菌中變形菌門(Proteobacteria)較正常人顯著增高;三個腸道細菌糞桿菌屬(Faecalibacterium),毛螺菌屬(Lachnospira),羅氏菌屬(Roseburia)較正常人顯著減少。Wang等人[21]通過對C57BL/6小鼠飼喂成石飼料的研究表明,膽固醇成石小鼠腸道菌群豐富度和多樣性均降低,主要表現為厚壁菌(Firmicutes)的低表達,同時厚壁菌門(Firmicutes)/擬桿菌門(Bacteroidetes)的比例降低。另有研究發現與健康人群相比膽囊結石患者糞便中瘤胃菌科(Ruminococcaceae)和顫螺旋菌屬(Oscillospira)種類增加,但細菌多樣性顯著降低[22]。馬俊[23]研究表明,無癥狀膽囊結石患者較健康人將比,乳酸菌、普拉梭菌、毛螺科菌、羅氏菌屬明顯降低,變形菌門的含量顯著升高。鄧太平等人[24]研究表明,膽結石組的腸桿菌、腸球菌、鏈球菌的菌落數明顯高于健康組,雙歧桿菌和乳酸桿菌的菌落數與健康組相比顯著下降。杜國濤等人[25]近期研究發現,膽結石患者與將康人相比。雙歧桿菌和乳酸桿菌的含量顯著減少,而大腸桿菌、腸球菌、葡萄球菌和酵母菌則相反。這些均提示腸道菌群的失衡可能對膽結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腸道菌群影響膽囊結石形成的機制目前尚不明確。
3 腸道菌群參與膽結石形成的可能機制
3.1 腸道菌群可能通過影響膽汁酸代謝進而影響膽結石的形成
膽汁酸是膽固醇的主要代謝終產物,具有表面活性作用,在脂質的吸收和利用過程中起重要作用。膽汁酸是由膽固醇通過至少14種肝臟酶的協同作用合成的[28]。膽汁酸有兩條合成途徑[27]:經典途徑和替代途徑。經典途徑是初級膽汁酸合成的主要途徑,占人類初級膽汁酸合成總量的90%,因該途徑的中間產物為中性類固醇,故也稱中性途徑。膽固醇7α羥化酶(cholesterol 7α-hydroxylase,CYP7A1)是經典途徑中的限速酶,甾醇12α羥化酶(cholesterol 12α-hydroxylase,CYP8B1)、甾 醇27α羥 化 酶(cholesterol 27α-hydroxylase,CYP27A1)也參與催化這一途徑,經過一系列酶促反應將膽固醇轉換為鵝去氧膽酸(CDCA)和膽酸(CA)。替代途徑是合成初級膽汁酸的另一途徑,因該途徑產生酸性類固醇故也稱酸性途徑,該途徑由CYP27A1和氧固醇7α羥化酶(oxysterol 7α-hydroxylase,CYP7B1)催化,主要產生鵝去氧膽酸,占人類初級膽汁酸合成總量約10%。在肝細胞內初級膽汁酸分別與甘氨酸和牛磺酸結合形成具有生理作用的結合膽汁酸,后通過肝細胞膽小管側膜上的膽鹽輸出泵(bile salt export pump,BSEP)泵入膽小管,進入膽囊,然后進入小腸。結合膽汁酸則在回腸頂端鈉依賴性膽汁酸轉運蛋白(apical sodium dependent bile acid transporter,ASBT)重吸收后,與回腸膽汁酸結合蛋白(ileal bile acid-binding protein,IBABP)結合,經基底側膜有機溶質轉運體 (organic solute transporter,OST)α/β重吸收進入門靜脈血流。門靜脈中的膽汁酸最后被肝細胞通過鈉離子依賴性牛磺膽酸鈉協同轉運蛋白(Na+-taurocholate cotransporting polypeptide,NTCP)介導結合膽汁酸轉運、有機陰離子轉運多肽1(organicanion transporting polypeptide1,OATP1)介導游離膽汁酸轉運,兩者共同介導循環膽汁酸重新被攝入肝細胞,上述過程稱為膽汁酸的腸肝循環。膽汁酸總量的95%經腸肝循環重新回到膽汁酸池,僅有5%左右經腸道排出體外。膽汁酸動態平衡受到膽汁酸對CYP7A1活性和表達的負反饋作用以及通過法尼醇X受體(farnesoid X receptor,FXR)和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19(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19,FGF19)的信號傳導的調控。
腸道菌群在膽汁酸的修飾和轉化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結合膽汁酸在腸道中通過膽鹽水解酶(bile salt hydrolase,BSH)生成游離膽汁酸。目前研究表明,腸道中存在著廣泛的可以產生BSH的細菌[28]。腸道中的游離膽汁酸在7α脫羥基菌的作用下生成具有疏水性的次級膽酸石膽酸(DCA)和脫氧膽酸(LCA)。現研究表明,具有7α脫羥基活性的菌主要有僅Clostridium屬以及Lachnospiraceae和Peptostreptococcaceae[29]。Sayin等[30]研究表明,與無菌小鼠相比,正常小鼠的膽汁酸池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小鼠回腸上皮細胞表面的FXR表達水平上調,FXR進一步誘導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15(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15,FGF15,人體中為FGF19)的表達,進而抑制CYP7A1、CYP27A1的活性,從而抑制膽汁酸的合成。與此同時Sayin 等人還發現牛磺-β鼠膽酸(taurobeta-muricholic Acid,T-βMCA)是FXR的天然受體拮抗劑,能夠減輕對CYP7A1的抑制作用,從而促進膽汁酸的合成。Out等人[31]試驗表明,腸道細菌能夠通過刺激腸道上皮細胞中轉錄因子GATA4的表達,抑制 ABST的表達,從而導致回腸末端膽汁酸的重吸收減少。相反膽汁酸也會影響腸道菌群的組成,小鼠口服1.25~5.00 mmol/kg 體重的膽汁酸,其腸道菌群中厚壁菌屬的比例由54%升高至94%~98%,而其中擬桿菌和放線菌的比例則顯著降低[32,33]。Ava等人[34]研究發現,膽汁酸受體FXR 基因缺陷型小鼠的腸道厚壁菌屬數量顯著上升,而擬桿菌屬數量顯著下降,這是由于FXR 受體缺陷時膽汁酸的分泌增加導致的,這提示膽汁酸可通過FXR 信號通路影響腸道菌群組成。Degirolamo 等[35]用乳酸菌、雙歧桿菌和嗜熱鏈球菌組成的混合益生菌飼喂小鼠,結果發現,該混合益生菌能夠顯著增加腸道中厚壁菌屬和放線菌屬的數量,降低擬桿菌屬和變形桿菌屬的數量,增加糞便中膽汁酸的排出量,降低腸道FGF15的表達水平,提高CYP7A1 和 CYP8B1的活性,從而增加肝臟膽汁酸的產量。早在1996年Berr等人[36]就研究表明,7a-脫羥基腸道細菌可增強膽結石患者DCA的輸入量和膽汁膽固醇飽和度。有趣的是近期Wang 等人[37]研究表明,膽結石患者與健康人群相比,初級膽汁酸和次級膽汁酸顯著增高,且7a-脫羥基腸道細菌顯著增加。這些研究強有力的證明腸道菌群和膽汁酸代謝存在著明顯的相關性,且膽汁酸的的代謝在膽結石的發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因此腸道菌群可能通過調節膽汁酸代謝進而影響膽結石的形成。
3.2 腸道菌群可能通過影響腸道屏障進而影響膽結石的形成
腸道既是人和動物對營養物質消化、吸收和代謝的主要場所,也是保障機體內環境穩態的先天性屏障,被譽為“機體的第二大腦”。腸道屏障是一種半透性結構,允許吸收必須的營養素和免疫感應,同時限制致病分子和細菌,維護機體腸道健康。在正常情況下,腸道粘膜屏障由機械屏障、化學屏障、生物屏障和免疫屏障組成。腸道微生物的構成的微生物屏障是腸道屏障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微生物競爭黏附等機制抑制有害病原菌在體內定值與增殖,保護機體免受外界病原體和毒素的入侵[38]。研究表明,腸道菌群失調可能破壞腸粘膜屏障,并可能增加對某些疾病的易感性[39]。腸粘膜屏障的破壞會使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更容易的通過腸道屏障進入肝臟。正常的情況下少量LPS通過腸道屏障進入肝臟,通過激活肝臟的免疫系統將其清除。然而,在腸道粘膜屏障功能破壞的情況下,腸肝循環平衡受損,腸道易位細菌及腸源性LPS增加,后者可通過模式識別受體如Toll樣受體4(tolllike receptor-4,TLR4)激活肝臟免疫細胞,最終誘導炎癥和促炎細胞因子的產生,從而幫助清除入侵的病原體[40,41]。王學軍[42]等人通過對膽結石組和對照組的膽汁酸分析,發現膽結石組中LPS的含量顯著高于對照組。與此相契合的是,白順滟等人[43]發現膽色素結石患者腸道粘膜通透性較健健康組相比存在明顯的降低。因此我們猜測腸道菌群失衡會導致腸道粘膜的通透性,影響LPS的易位,并激活肝臟的免疫,其分泌的炎性細胞因子通過旁分泌方式,改變了肝細胞的正常代謝,并有可能通過信號傳遞系統,改變細胞內某些酶的活性和表達,從而在膽石的形成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3.3 腸道菌群可能通過影響免疫進而影響膽結石的形成
腸道菌群在宿主免疫系統的發育和成熟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一點在無菌小鼠身上得到了最清晰的證明,這些小鼠從出生起就被培養成完全沒有任何微生物的動物。與常規飼養的小鼠相比,這些動物表現出嚴重不發達的腸道免疫系統[44]。腸道菌群可調控宿主免疫,包括調節性T細胞(Treg)、TH17、TH1等免疫細胞[45]。腸道菌群除自身參與調節免疫外其代謝產物短鏈脂肪酸(short chain fatty acids,SCFA)也參與免疫的調節。SCFA是碳鏈1-6的有機羧酸,是腸道菌群發酵碳水化合物的主要終產物,其主要包括乙酸、丙酸和丁酸[46]。腸道菌群產生的SCFA在保護腸道粘膜屏障[47]和免疫中發揮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SCFA通過減少巨噬細胞、中性粒細胞及樹突細胞的募集和遷移,并抑制T細胞和B細胞的分化,以調節免疫應答和炎癥[48]。有趣的是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膽結石和免疫存在著明顯的相關性。免疫系統在膽固醇結石發病機制中的作用的證據來自Maurer等人[49]的研究,其發現喪失T或B細胞功能的Rag缺陷小鼠與野生型小鼠相比其成石率顯著降低,將脾細胞或T淋巴細胞向Rag缺陷小鼠移植,發現其結石形成率明顯增高,而B細胞的移植卻沒有結石形成率的明顯變化,該研究證明T細胞免疫在促進膽固醇膽結石形成方面發揮了深遠的作用;此外,還證明了T細胞和固體膽固醇晶體在膽囊中誘導了強力的Th1介導的局部炎癥反應。李平等人[50]研究發現,急性和未發作的膽結石患者均存在T淋巴細胞亞群比例失調,急性發作時,CD3+、CD8+T細胞升高,使免疫應答增強。有趣的是,近期Mu?oz等人[51]研究表明,膽結石中含有中性粒細胞的胞外DNA及其產生的彈性蛋白酶,中性粒細胞外殺菌網絡(neutrophil extracellular traps,NETs)對膽結石的形成是必須的,人源和鼠源的膽結石中均存在NETs,并且膽結石的形成和生長需要先天免疫系統的活化。這些研究表明腸道菌群可能通過調節免疫進而影響膽結石的形成。
4 結語
綜上所述,腸道菌群的改變與膽結石的形成密切相關,腸道菌群可能通過影響膽汁酸代謝、腸粘膜屏障和調節免疫等機制,參與膽結石的發生和發展,但這些可能的機制需要我們進一步研究闡明。由于膽結石作為一類代謝性疾病,因此,腸道菌群最可能通過改變人體代謝或其自身產生的代謝產物進而影響膽結石的形成,這需要我們對膽結石患者的代謝產物進行檢測并與腸道菌群進行關聯。希望從腸道菌群靶向治療的角度為膽結石提供新的防治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