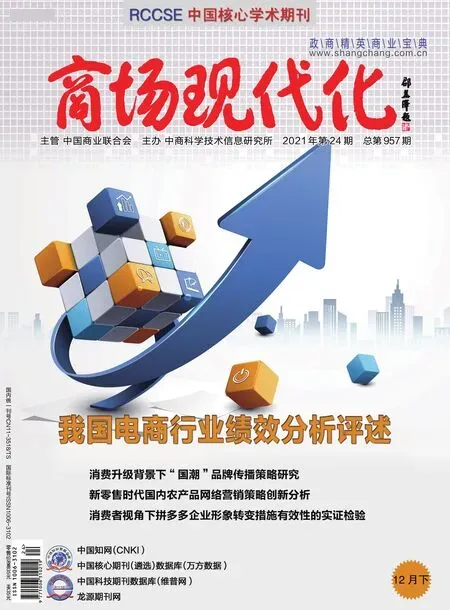混改背景下非國有股東制衡與企業績效文獻綜述
陳伊竹
在我國不斷推進國有企業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之下,國內外許多學者對國企混改的政策后果進行了大量的理論和實證研究。下面本文將就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經濟效果進行文獻回顧。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經濟效應
正向作用。全球部分混改國家的經驗證據基本一致表明,當國有企業被全部或部分民營化后,其經營業績將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提高(Megginson and Netter,2001)。Porta&Silanes(1999)通過對墨西哥的國有企業研究認為民營化改革大幅度地提高了企業利潤。Megginson&Netter(2001)認為將國有企業全部或部分民營化以后,不僅提高了企業盈利能力,還對經濟體的經濟水平和就業情況具有促進作用(Beladi&Chao,2006)。Maw(2002)研究認為,在混合所有制改革過程中,為了完成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原國有股東可能會保留對企業的控股權,這也會影響企業的治理效果。
此外,我國也有大量文獻研究了我國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正向影響。混合所有制是一種產權制度、財產組織制度之間相互吸納的一種耦合(何立勝等,2005)。國內大量研究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彌補市場化不足,穩定國民經濟發展(趙晶),提高公司績效(郝陽等,2017),改善國有企業高管薪酬業績敏感性(蔡貴龍,2018),增加企業研發投入水平(解維敏,2019)的同時抑制非主要研發的投入(楊興全,2021),抑制債務融資錯配(盧佳瑄,2021),提升企業創新效率(王業雯等,2017)和生產率(劉嘩等,2016),改善公司內部控制(劉運國,2016),提高企業承擔風險的能力,進而提升營業收入企業價值(楊興全等,2018),提振經濟增速(許召元等,2015)。
反向作用。也有大量的研究表明,混合所有制過程中并未出現上述所說的業績增加的現象,相反業績還出現了一定的下滑(Sun and Tong,2003),因為單純的股權混改并不能改善國有企業績效(馬連福,2015),現實中非國有股東“同股不同權”的境遇大量存在(陳良銀,2021)。可能是由于國有企業被民營股東掏空(涂國前等,2010)、股權制衡度過高(徐莉萍等,2006)、增加了新的代理沖突等原因。
二、非國有股東治理效應的文獻綜述
從股權性質角度分析。非國有股東的引入,為獲得預期回報,將會有較強的動機推動企業建立約束激勵機制(Gupta,2005),在創新投入(李文貴,2015)、投資效率(祁懷錦,2018)、高管薪酬激勵(蔡貴龍,2018)等方面有較好的治理效果,與企業治理效率的改善程度正相關(陳曉珊,2019)。在股權結構多元化的背景下,第二大股東若有效制約第一大股東,需承擔監督職能,當股權性質多元的情況下,大股東之間的監督動機才會超過合謀動機(魏明海等,2013)。但非國有股東僅持有國有企業股權不能有效改善內部控制水平,參與董事會高層決策治理才能更好地改善企業內部控制結構(劉運國,2016)。劉星和劉偉(2007)指出,股權性質可以影響股東間制衡效應,當第一、第二大股東分別是不同性質的股東時,制衡效應是有效的,但若前兩大股東均為非國有股東時,制衡效應可能不盡如人意。李明娟等(2020)通過實證分析發現,顯著提升國有企業資本配置效率的因素是民營股權比例的提升。陳艷利(2020)通過對競爭性國有上市公司研究發現非國有股東治理水平的提升可以有效促進國有企業股利的穩定上升,尤其在地方國有企業、市場化程度與融資約束較低的樣本地區更顯著。郝云宏和汪茜(2015)以“鄂武商控制權之爭”為案例,研究發現非國有股東與國有股東對于企業控制權的爭奪是符合效率原則的市場化行為,且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非國有股東可以通過爭奪董事會表決席位和其他非控股股東聯合等方式對國有大股東進行制衡。所以在中國當前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斷推進的背景下,想要有效改善公司治理問題,需要大股東在保持一定股權集中度的條件下,構造股權多元化、股權制衡的治理體制(劉星等,2007)。
從現金流權角度分析。現金流權是指股東通過持股比例獲取企業經營成果的分享權。對于控股股東來說,現金流權也代表其分享企業利潤、經營成果的激勵。非國有股東的引入,非國有股東的引入,大股東之間的股權制衡和現金流量權制衡均可以有效緩解企業內部的代理成本(張旭輝等,2012)。
三、董事會制衡文獻綜述
1.非國有股東董事會制衡效應
董事會作為公司治理結構中的核心機構,其發揮的紐帶作用有利于減少代理成本,提高公司盈利水平。在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非國有股東通過股權委派人員進入董事會、監事會進行決策、監督,保障其權益,進而可以吸引更多的優質股東和優質資源,提高企業盈利能力和治理能力。郝云宏和汪茜(2015)運用案例分析法提出了當前國有企業改革中控制權爭奪引發沖突的解決建議,即非國有股東作為第二大股東,通過向國有企業董事會、監事會委派董事、監事等路徑有效制衡國有大股東。劉運國等(2016)從內部控制質量視角實證分析發現,只有在競爭性、地方性國有企業中,非國有股東才能通過參與董事會治理有效改善國有企業內部治理問題。由此可見,國有企業改革中引入的非國有股東需要通過參與董事會治理,才能較好地提高企業的經濟績效。張任之(2019)從高管腐敗角度實證分析發現,國有企業改革中引入的民營股東只有通過委派董事并參與公司的經營決策,可以有效緩解高級管理人員腐敗的問題,但這種方式在壟斷性行業中并不顯著。吳秋生和獨正元(2019)從國有企業負債水平的角度分析,認為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程度越高,企業的負債水平越低,且相較于股權結構而言,企業高層治理結構的改革更有益于緩解企業高負債水平的困境。
2.非國有股東董事會制衡強度
從非國有股東董事會權力與非國有股權對混改國企經濟后果的影響研究來看,學者們一致認為前者的影響作用強于后者。在對比兩者影響作用強度的同時,也有學者對兩者之間內在的影響關系進行了探討。謝海洋等(2018)認為相較于股權結構安排而言,董事會結構安排對企業績效的影響更大,所以混改重點是控制權安排,應基于非對等權力讓渡部分控制權給非國有股東。劉漢民等(2018)也通過實證研究發現,董事會結構安排對企業經濟績效的影響更強,從而證實了持股比例與企業控制權之間是不對等的。鄭志剛(2019)通過對比股權結構對企業經濟績效與董事會結構安排對企業經濟績效之間影響的差額部分,引出了“超額委派董事”,即實際控制人可能通過委派超額董事來抑制經營決策中產生的反對票。
四、委托代理問題文獻綜述
對于國有上市公司而言,較長的委托代理鏈條導致所有者缺位,錯綜復雜的委托代理層級引發了信息不對稱和道德風險(黃天添,2020),進而形成的“廉價投票權”導致無法合理監督國有企業(張維迎,2015),而且缺乏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難以使管理者利益與企業利益統一(金宇超等,2016),管理層可能為了自身利益造成投資不足或投資過度(向東,2020),損害企業價值(Jouahn等,2005)形成了第一類委托代理成本。由于國有控股股東的一股獨大,大股東可能會利用關聯交易手段侵占和掏空公司利益(余桂明等,2004),使得國有上市公司可能還面臨著國有控股股東與非國有中小股東之間的利益沖突,通過對企業利益的侵占和掏空,對企業內部治理決策質量帶來不利影響(何巍,2020),即第二類委托代理問題。李向榮(2018)認為國企天然存在多重代理,引入私人投資主體減少了國有產權代理人的機會主義行為,減少了經理人的代理成本。Marcelin(2015)認為國有企業改革引入民營股東,促進了企業監督治理效率的提高,且對于產權保護較弱和金融機構落后的國家更為顯著。建峰(2020)研究得出對高管的超額薪酬實施“限薪令”可以有效降低國有企業委托代理成本,但同時也降低了報酬對高級管理人員的激勵作用,即雖然此方法產生了新的收益,但也產生了一定損失。蔡地(2012)等研究發現,若國有法人作為制衡股東進入國有企業后,不僅制衡結構難以發揮作用,且容易導致其他非國有股東與高管合謀,不利于改善委托代理問題(涂國前等,2010)。王蘇楠等(2021)站在中小股東角度研究發現,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越高,第二類委托代理成本越嚴重,對創新產出負面影響越大,同時嚴重降低了公司經營效率(何巍,2020)。
五、社會性負擔文獻綜述
根據社會交換理論,個體與群體之間的互動根本上是一種互換物質的關系,社會的形成即是人類交換行為的結果。根據此理論,Homans(1958)認為由于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雙向尋租行為,所以國有企業承擔了一定的社會性負擔。一方面,政府干預導致了國有企業承擔了更多的社會責任。因為國企具有“政治”與“經濟”雙重屬性,政府將其作為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目標的工具(葉靜怡等,2019)。魏紀泳(2021)提出地方政府行為目標分為內生性目標和外生性目標,內生性目標是指地方政府根據自身所擁有的資源和現有條件可實現的公共管理目標;外生性目標是指地方政府根據上級下達的整體發展戰略而制定的總體目標。當地方政府的外生性目標超過該地區可供使用的資源時,各級政府官員為政治晉升、發展政績,使國有企業承擔更多除盈利以外的目標,將穩定就業、維護穩定等職能附加至企業(周黎安,2007),這也使得國有控股公司存在較為嚴重的冗余雇員問題(曾慶生等,2006;Shleifer&Vishny,1994),扭曲企業投資行為,降低企業投資效率(魏紀泳,2021)。同時相較于非國有企業而言,政府干預國有企業成本更低,這也使得國有企業常常處于干預之中(Sppington&Stinglitz,1987)。另一方面,國有企業通過與政府之間的特殊紐帶關系,可以獲得政府補貼、稅收優惠等優惠政策(戴亦一等,2014)。當國有企業面臨財務困境時,“政府兜底效應”發揮作用(胡寧等,2018),政府通過特殊貸款安排、招標優先、稅收優待等方式對其進行救濟(王紅建等,2015)幫助企業渡過難關。
六、文獻評述
本文在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下,分別從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經濟效應、非國有股東治理效應、董事會治理效應以及非國有股東通過影響企業委托代理成本和社會性負擔進而改善企業績效五個方面進行綜述。通過對現有的國內外學者的文獻進行閱讀整理,可以發現國內外學者對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對企業的績效影響觀點尚不統一,而多數學者從不同角度分析認為國有企業改革中引入非國有股東對原國有大股東起到了制衡作用,但需要滿足委派董事參與董事會治理等條件才能有效改善公司內部治理水平。對于國有企業中的委托代理成本,第一、第二大股東的性質和持股比例對于企業產生的委托代理成本至關重要,只有形成有效制衡,才能有效緩解此類問題。從社會性負擔角度來看,混合所有制改革形成的股權制衡可以有效緩解企業承擔的政策性負擔,但同時也會損失政府給予國有企業的特殊優待,所以股權制衡是否能通過緩解國有企業社會性負擔進而改善企業績效的結論仍值得研究。
國外學者的研究大多從混合所有制改革對企業績效、利潤及治理效率角度出發,研究特定地區民營化給企業帶來的正向或反向作用。對于企業委托代理成本和社會性負擔的研究,多數研究都是圍繞其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但缺乏從制衡角度研究分析,缺少混改中引入非國有股東影響企業績效的路徑研究。國內學者對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較為豐富,主要通過實證研究法,研究主要集中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對企業績效的影響,但對企業績效是促進作用還是阻礙作用并沒有得到一個一致的觀點。且對于混改中非國有股東治理作用,研究多從股權性質、股權結構等角度出發,缺少從非國有股東制衡角度的研究,對于混改研究中董事會制衡的研究多數表明制衡能夠提高會計信息質量、績效等方面,也較少有研究將非國有股東影響企業經濟績效的路徑綜合研究。
參考文獻:
[1]Megginson W L,Netter J M.From state to market:A survey of empirical studies on privatization[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1,39(2):321-389.
[2]La Porta R,Lopez‐de‐Silanes F,Shleifer A.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J].The Journal of Finance,1999,54(2):471-517.
[3]Beladi H,Chao C C.Does privatization improve the environment?[J].Economics Letters,2006,93(3):343-347.
[4]Maw J.Partial privatization in transition economies[J].Economic Systems,2002,26(3):271-282.
[5]葉玲,王亞星.混合所有制改革下公司治理結構的動態調整路徑研究[J].當代財經,2018(08):69-76.
[6]王業雯,陳林.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促進企業創新?[J].經濟與管理研究,2017,38(11):112-121.
[7]綦好東,郭駿超,朱煒.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動力、阻力與實現路徑[J].管理世界,2017(10):8-19.
[8]曾詩韻,蔡貴龍,程敏英.非國有股東能改善會計信息質量嗎?——來自競爭性國有上市公司的經驗證據[J].會計與經濟研究,2017,31(04):28-44.
[9]尹興強.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與公司現金持有[D].石河子大學,2017.
[10]郝陽,龔六堂.國有、民營混合參股與公司績效改進[J].經濟研究,2017,52(03):122-135.
[11]楊興全,尹興強.國企混改如何影響公司現金持有?[J].管理世界,2018,34(11):93-107.
[12]李向榮.混合所有制企業國有股比例、制衡股東特征與公司績效[J].經濟問題,2018(10):101-104.
[13]姜孟芮.混合所有制、股權混合度和非效率投資[D].浙江財經大學,2017.
[14]馬連福,王麗麗,張琦.混合所有制的優序選擇:市場的邏輯[J].中國工業經濟,2015(07):5-20.
[15]許召元,張文魁.國企改革對經濟增速的提振效應研究[J].經濟研究,2015,50(04):122-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