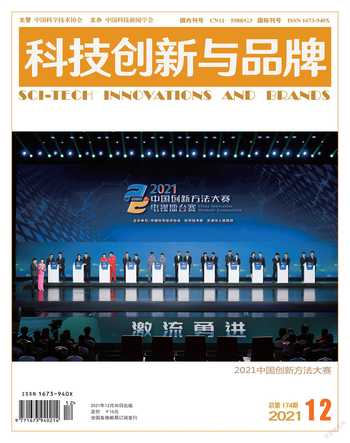構建萬物互聯時代的通用標識代碼生態體系
陳淑蓮

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深入推進,我國正在加速邁入萬物互聯的數字化時代。標識代碼作為萬物在數字世界唯一的身份標識,是互聯網重要信息入口和大數據資源的重要獲取手段,在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取得了廣泛的應用和發展,已經成為我國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時,如何構建我國自主標識代碼體系,重構國際標識代碼標準話語權,也成為了當下關注焦點。近日,本刊記者專訪了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科技委副主任、中關村工信二維碼技術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碼院”)院長張超。
加快標識技術全球化服務
“這是中國在標識代碼領域里的里程碑事件,我們首次成為全球代碼發行機構,擁有了向全球分配基礎代碼資源的資格。”在談到最近成立的MA標識代碼管理委員時,張超對本刊記者說道。
時間回到2018年8月,此時的中碼院獲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歐洲標準委員會(CEN)和國際自動識別與移動技術協會(AIM)三大國際組織共同授權,成為國際代碼發行機構,發行代碼“MA”成為了全球二維碼統一標識的專屬代碼。這是首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設立在中國的全球代碼發行機構。就此,由中碼院主導成立,負責管理運行MA代碼的統一標識代碼注冊管理中心成為了與國際物品編碼協會(GS1)、美國電氣和電子工程師協會(IEEE)、萬國郵政聯盟(UPU)等大型國際組織并列的國際代碼發行機構。
為推動MA標識體系在數字經濟發展和數字中國建設中發揮更好的支撐作用,加快自主標識技術全球化服務,2021年8月2日,中碼院與中國工業互聯網研究院牽頭成立了MA標識代碼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委會),負責指導、協調MA的管理運作,加強MA標識體系在智能城市、先進制造、工業互聯、數字技術等領域的應用。
MA標識體系作為中國首個自主可控,同時具有全球頂級節點管理權和代碼資源分配權的國際標準標識代碼體系,可以對各種不同對象(物、事、人)標識統一管理,同時基于MA標識建立的碼標體系具有命名、確權、保護、管理的功能。“基于MA的碼標一經注冊,在全球范圍內即可被認可,具有唯一性,其作用就像人類交往的‘護照’、人機互聯的‘域名’,是萬物互聯數字時代的‘數字身份證’。”張超解釋說道。由于MA標識代碼體系能夠實現“對象”統一編碼和互聯互通,因此其不限于二維碼載體應用,包括漢信碼、QR碼、龍貝碼、GM碼等多種碼制的生成、識讀,此外,還可與更多物聯網領域中的RFID、傳感器、芯片等新一代載體技術結合,對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和產業數字化轉型起到重要支撐作用。
“中國首次擁有了向全球分配基礎信息資源的資格。過去我們向別國申請、購買標識代碼,不但被他國掌握基礎數據,造成國家信息安全問題,還要為此交付一筆費用,現在則由他國向我們申請,由我們統一管理。其次,我們在標識代碼領域第一次有了國際標準話語權。過去我們要向國外機構申請代碼,由國外評估我們是否達到標準,現在只要由我們國家相關機構評審通過即可自動符合ISO/IEC 國際標準。”張超說道,不過他也坦言,由于這個領域過于基礎,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意識到它的重要性,但卻和我國經濟風險和數字信息安全問題息息相關。
建立自主可控的標準生態體系
“自主可控”是張超在采訪中最常提及的一個詞。標識代碼是組織機構及人、事、物對象的標識域名,也相當于組織機構的“數字身份”,一經注冊即可在全球范圍內被認可,通常與二維碼、RFID等載體組合呈現。
“標識代碼是數據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重要的核心資源。數據之爭,就是資源之爭。但若數據一經流動,就會涉及到數據安全保護問題,因此最好先用標識代碼對數據進行確權,以最大限度確保安全。目前大部分標識代碼規則制定權掌握在歐美國家手中,我們希望中國能逐漸擁有制定相關規則的更多話語權,這不僅涉及到數據安全問題,更關乎國家信息安危。”張超說道。
過去,由于我國標識代碼起步較晚,管理相對滯后,尚未建立起國家層面統一的協調管理機制,導致我國標識代碼產業呈現無序發展和無序競爭的局面,沒有形成產業力量,且我國尚未形成統一的標準體系,基礎標準雖已建立但尚未推廣普及,行業相關應用標準各自為政、互不兼容,不同標準之間、不同體系之間不能互聯互通,應用很難規模化推進。
以標識代碼體系最重要的載體之一二維碼為例,國際上對二維碼技術的研究始于上世紀80年代末,作為存儲、傳遞和識別的技術應用到商業、交通、工業生產、軍事等各個領域,并制定了相關的國際行業標準和國際ISO標準。我國對二維碼的研究始于1993年,并隨著手機二維碼的應用普及迎來了發展時期。但由于國外起步早,由行業組織和大型廠商引導,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商業模式,迅速掌握了行業話語權和產業控制權,基本壟斷了識讀設備、打印設備及相關產業配套,而我國二維碼囿于商業模式封閉、發展機制不靈活,錯失了行業發展的戰略機遇。這也導致了中國雖然是全球二維碼應用最大的市場之一,但過去卻沒有太多國際話語權,甚至連國內常見的QR Code二維碼也來自于日本。“所幸我國在技術層面和歐美日等國家基本處于同一水平,沒有太大的技術難點,甚至在糾錯能力方面還高于國外標識代碼,因此不存在技術問題,只要處理好標準和規則問題,中國就有一爭之力。”
2018 年 5 月 25 日,歐盟發布了《一般數據保護法案(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679/2016, GDPR )》,看似是保護公民數據隱私,但從另一個角度來分析,同時也制定了全球數據的管理規則,以一種更合理的方式去掌握信息管理的話語權。與此相對應,為促進工業互聯網標識解析體系健康有序發展,工信部也于今年6月1日正式發布了《工業互聯網標識管理辦法》,這是我國標識代碼領域首部正式法規。
“成立管委會是為了推動我國自主的國際標準標識代碼體系生態建設,加快MA體系的全球化服務。”張超稱管委會不僅是MA標識代碼的管理協調機構,也是一個技術組織,其核心任務是重構國際標識代碼標準體系。“我們一直在與發達國家搶時間,在努力加快全球服務,就是為了提高MA全球產業布局,至少在我們的國家,我們需要更多的中國標準。”張超認為面對全球貿易的新秩序,以及國外標識代碼技術體系和標準體系的挑戰,倘若中國不能加快建設自主技術體系和標準體系,強化自主標識代碼規則體系的建立和“走出去”戰略,繼續大范圍應用國外標準和專利技術,任由國外技術標準主導產業應用,將會進一步喪失我國在標識代碼行業競爭方面的話語權。
目前,MA標識注冊和解析系統已完成國產服務器和操作系統適配,并已與國家工業互聯網標識解析頂級節點完成對接測試。與此同時,MA標識代碼已在全球30多個國家和地區應用,解析總量超過3200萬余次。
夯實智慧城市基礎
城市代碼是張超極為關注的一個領域。在萬物互聯時代,數據資源是智慧城市建設的重要基礎,更是城市得以“智慧”的保障,而統一標識代碼作為信息系統的數字底座,更是基礎中的基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全球已啟動或在建的智慧城市有1000多個,其中位于中國的就有超過500個。中國智慧城市建設規模在2019年已達1600億元人民幣,僅次于美國。但在這個過程中,智慧城市建設的一些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張超認為“重頂層、輕底層”,各部門、各行業編碼不統一、數據不互通、應用不融合,是當前影響智慧城市建設、城市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因素。因此如何科學解決城市之間、城市內部各部門和各行業之間的代碼統一和數據互通問題,成為促進空間信息數據共享共建、消除部門信息壁壘、強化政府職能的重要手段。
張超認為可以用城市代碼標識體系作為解決中國智慧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有力工具,如將各個城市及城市管理對象分配“數字身份證”,從“根”上實現城市各要素代碼統一和標準化。如:石家莊城市代碼為MA.156.1301,其城管部門標識代碼MA.156.1301.01,交通部門標識代碼MA.156.1301.02等,以此類推,可以迅速在醫療衛生、城市管理、道路交通、公安監察等領域進行較為廣泛的使用。此外,未來每一個公民還可以認領屬于自己的一個二維碼,它可以集成個人的全部信息,甚至替代身份證、戶口本、銀行卡等證件,真正實現信息時代的萬物互聯。“我們可以將所有智慧數據平臺都集合在城市代碼標識體系上,通過集成發揮全部的作用。”張超說道。
智慧城市代碼標識體系是由中國自主研發、自主分配和管理,具有統一分配規則、分布式存儲解析、代碼不可篡改的特性。由此搭建起全市統一的基礎標識體系,實現城市內部和城市間各要素的互聯互通和數據共享,并不斷延展基于代碼標識的新型智慧城市應用場景,有力支撐智慧城市建設,成為“新基建”的重要組成部分。
這幾年隨著數字經濟不斷推進發展,越來越多人逐漸意識到標識代碼的重要性,尤其是“十四五”規劃將數字經濟單獨成篇,并提升到前所未有戰略高度,張超認為標識代碼已經迎來了發展高峰期,真正進入發展快車道。談到下一步計劃,張超提到未來會在管委會框架內,在智慧城市體系、產品溯源體系、企業編碼體系、內外部管控體系的數字化管控領域發揮更多作用,和不同產業鏈上的行業機構、龍頭企業等形成不同領域的專業委員會,以此深入研究不同領域的標準應用和生態建設。“我們希望能和更多人一起推動MA標識代碼標準體系建設,助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提升。”
編輯/馬銘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