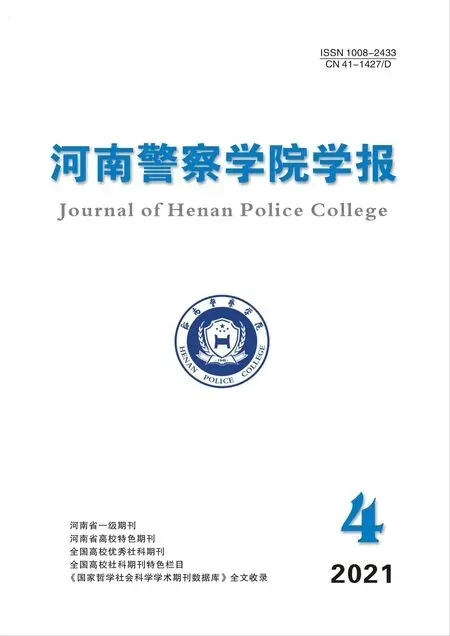黑惡勢力犯罪的社會原因分析
——以文化沖突理論為視角
翟藝丹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刑事司法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3)
一、黑惡勢力的性質
無論是在理論層面還是在實踐層面,黑惡勢力都可被視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雛形。換言之,黑社會性質組織是黑惡勢力發展的最終階段。這就意味著,兩者在文化、組織構架、犯罪成因等方面具有共通性與相似性。由于“黑惡勢力”這一概念并未在規范性文件中得到明確,所以,若要對“黑惡勢力”的概念進行界定,還需對“黑”“惡”“勢力”三個詞采用解構的方式進行深入剖析。
(一)“黑”與“惡”的概念界定
黑惡勢力之所以被冠以“黑惡”之名,其原因有三點。一是,黑惡勢力通常都是以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形式呈現,而黑社會性質組織中的“組織”可以被定義為“以追求經濟利益為基本目標,以暴力和賄賂為主要手段,具有組織機構的層次性、組織功能的分解協調性、組織指令的規范性和組織成員的穩定性、組織形態由低到高的有序性的實施犯罪行為的組織系統。”[1]在此基礎上,黑惡勢力犯罪與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基本上可以做同質化理解。另外,黑社會性質組織是惡勢力團伙發展的高級階段,二者前后相繼,生長軌跡呈線性形式[2]。
二是,在黑惡勢力中,對“惡”字可以進行雙層遞進式理解。其一,“惡”是“善”的相反概念。在社會一般人的認知中,“惡”會觸及每個具有同情心與正常道德素養的社會人的道德臨界點。在“惡”的理念指導下采取的行為,大多會觸犯社會的統一道德規范,并且會對人的權益造成各種侵害。其二,“惡”并非局限于道德層面上的判斷,還可以將其上升為刑法的高度。在刑法層面上,“惡”主要侵害人身、財產等專屬性法益,也會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政治穩定等造成侵害。
(二)“黑惡勢力”的基本特征
“黑惡勢力”一詞最早可追溯至1979年刑法規定的流氓惡勢力犯罪。1995年后,“黑惡勢力”這一概念更多地被用于市場經濟監督管理領域與社會治理領域[3]。在2009年的《辦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座談會紀要》中,國家首次將“黑惡勢力”這一概念納入法律規范文件中,并且明確“黑惡勢力”即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的雛形。隨著掃黑除惡的逐步深入,“黑惡勢力”一詞被理論界、實務界廣泛接受。筆者認為,可將“黑惡勢力”的特性類型化為內在關聯性、外在逐利性、行為共生性、共同危害性四部分。
其一,內在關聯性。“黑惡勢力”內部均具備一定的組織性,并且通過發展組織內部的底層人員,不斷向外部延伸。“勢力”便是根據上述發展路徑,在一定的區域內逐步形成的。“黑惡勢力”可在共犯體系之內解決,其組織規模較大并極具穩定性。其組織內部具有較為嚴密的層級劃分與分工,組織內部各個層級之間呈金字塔型。實務界認為,“黑惡勢力”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大于一般意義上的共同犯罪,其涉案人員至少為三人或三人以上。在犯罪組織中,參加人員承擔的角色并不相同。如果案件由多人參加,并且形成較為固定的組織,也可將之稱為犯罪集團[4]。
其二,外在逐利性。對于非法經濟利益的追求,是黑惡勢力犯罪的最終目標。其獲取非法經濟利益主要通過以下幾種行為手段:一是通過暴力手段獲得經濟利益,如收取保護費、敲詐勒索、綁架等;二是通過非法經營的方式獲取高額利潤,如高利放貸、開設賭場,或搞套路貸等。
其三,行為共生性。“黑惡勢力”犯罪大多通過暴力手段或以暴力相威脅等方式進行犯罪活動。“黑惡勢力”的成員在完成組織安排的任務時,具有一定的暴力性。換言之,黑惡勢力組織的罪犯通常在犯罪動機、主觀目的、實行行為等方面具有共同性。在多數黑惡勢力犯罪中,上級對下級的犯罪行為進行了明示或默許,其犯罪行為具有共生性。
其四,共同危害性。“黑惡勢力”的活動范圍限定在一定的區域或地域內。在合法社會控制力量弱化的地方,非法社會控制力量就會滋生[5]。也就是說,在一定的自然區域或行政區域內,非法社會控制力量會從事違法犯罪活動。黑惡勢力的社會危害行為一般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在固定的區域及一定的行業內采取暴力等手段侵害公民的權益,或者壟斷某一行業;二是對一定區域內的行業采用非法手段進行控制;三是黑惡勢力對一般的民眾實施一定的心理強制或非法的威懾控制。
二、對黑惡勢力“文化”的解讀
(一)黑惡勢力“文化”的產生
“文化”一詞具有極為豐富的內涵。英國人類學家愛德華·泰勒在《原始文化》一書中指出:“文化或文明,從其廣泛的人種史的意義上說,是將知識、信仰、藝術、倫理、法律、風俗囊括在內的,是包括一個人掌握的任何能力和習慣在內的復雜的整體。”[6]基于此,可以用文化的抽象性特征解讀社會中發生的各類現象,并且對其根源從特有的文化視角進行解讀。文化是社會的特有存在,從社會存在可以反推出個體在文化中的位置。即,個體的文化形成于其社區歷代相傳的生活模式與準則。從個體獨立之時,其所處的風俗就在打磨與塑造個體的經驗與行為。到個體具有辨別能力時,其便能成就自身文化且參與其中。而這種被參與的團體,便是具有同質性的個體的集合。因此,從個體出發可將文化總結為歷史與當下全部信息的沉淀與累積。在群體與組織內,文化的共同指向性更為顯著。這是因為,生活在社區中的個體大多處于同等階級,其教育、經濟水平、生活模式更為一致。在社區之外的社會中,則存在著不同等級的階級,根據默頓的失范理論,社會中的每個階級的文化目標與規范化方式不盡相同。
在以群體為單位的黑惡勢力組織當中,也會構建出特有的“文化”。黑惡勢力組織的形成絕大部分具有自發性。這種自發性通常伴隨著黑惡勢力組織成員之間人格及行為的相互影響,這種互動對成員之間的內部關系起到一定的調節作用。黑惡勢力組織成員并非被動,或被強行灌輸不同于社會主流文化的價值觀,而是自發、主動地接受黑惡勢力組織特有的“文化”觀念。
在黑惡勢力組織中,由于組織成員的行為具有一致性,所以個體會存在一種默認此行為標準的心理傾向。換言之,個體通過群體對外采取相同的行為方式,他們會逐漸產生趨于一致的判斷與認知。這種一致性,在每一次群體活動中不斷得到加強和鞏固,從而導致個體自覺接受群體行為所體現的“文化”觀念。個體往往將群體的信仰、態度和價值觀等作為自己的參照標準和榜樣,加以認同和模仿[7]。個體與個體之間也會在心理方面、行為順從方面產生相互作用。這樣一來,黑惡勢力組織通過個體的互動,確立了一定的標準,繼而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規范。
(二)黑惡勢力“文化”的規范作用
作為個體,人生來便處于文化當中,并且天生具有接受與選擇關于自身及與他人關系的知識的稟賦。從其接觸社會初始之時,便開始了漫長的適應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經由來自環境、他人的訓誡或者教導,加之自身的領悟與學習,人們便會汲取及接受各種正式或非正式途徑傳播的觀念。若將這些觀念視為具有獨立價值的要素,便是文化要素。個體都對這些文化要素存在著正常(順應)或異常(反抗)的回饋與反應,并且經由這些方式制定出自己認同的文化規范。因此,社會中只要存在人的集合體,就必然有行為規范的存在。換言之,行為規范是普遍存在的,它們不是哪一個規范集團的創造物,它們也不附從于任何政治界別,它們的表現形式也不局限于法律規范的形式[8]。
個體需要通過黑惡勢力組織的一系列活動滿足自身的安全。同時,長期的團體生活與共同行為成為維系組織成員之間契約關系的紐帶。這一紐帶不僅使成員的認知、意識、行為判斷的差距縮小,更使得組織成員產生了對團體利益的認同。黑惡勢力組織的特有文化規范不僅能夠填補個體成員在主流社會文化中的滿足感與存在感的缺失,更能夠在獲得組織高層的贊賞后,進一步增長對組織的認同。犯罪組織成員無一例外地在犯罪組織中得到贊賞、滿足、安定的正面感覺[9]。
三、對黑惡勢力犯罪的文化分析
(一)文化規范沖突的根源
規范是為個體行為提供的范式與參照構架。文化規范,意指在一定狀態下某一類型的群體遵從的特定的行為方式與共同承認的行為規則。也可以說,文化規范意指生存于某一社會環境中的個體在特定的情況下應當根據何種標準采取行動的規則。規范沖突即為,生存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的社會群體產生的行為與認知上的差異。
塞林提出的“文化沖突”概念,對黑惡勢力犯罪的文化分析具有重大意義。塞林認為,文化沖突產生于社會變遷之中,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現象。但是變遷中衍生出的犯罪定義與法律分類不足以應對極具動態性的犯罪現狀,所以,二者皆不足以成為犯罪學研究的基準。因此,應當重新確定一個更具普適性的基準,從而可以將行為規范的任何變化囊括其中。塞林認識到,在犯罪定義中反映出的法律標準,即便是在最好的情況下,也不過是人為與專斷的標準;在最壞的情況下,則是忽視了與“一般社會利益”相沖突的其他重要社會行為[10]。塞林提出的文化沖突這一概念,即為社會范疇中相悖于主流文化的其他文化。文化沖突與犯罪的關鍵區別在于,文化沖突下產生的行為是否踏入刑法設定的中線之內。這一判定標準的根據在于,刑法是社會的主流文化規范,并且將社會的主流文化整體呈現于法律規范之中;犯罪行為則是與此類社會主流文化相背離的現象。
黑惡勢力組織成員不遵循社會主流文化,將黑惡勢力的文化觀念及內在固有的規范顯現于外在行為之中。多數黑惡勢力組織的文化規范與社會主流文化規范的產生與構成方式存在差別,黑惡勢力組織的文化規范基本上建構于社會主流文化規范的對立面。換言之,黑惡勢力組織以消極態度對待社會主流文化規范,且不承認社會主流文化規范的正確性。
黑惡勢力組織的犯罪文化存在兩類相悖于社會主流文化規范的需求,一是與傳統合法獲取經濟利益的手段相反的行為方式,即,黑惡勢力組織采取非法手段獲取不正當的經濟利益;二是黑惡勢力組織需要在社會主流文化之中實現,并且黑惡勢力組織實施犯罪行為的最終目的是為了獲取最大化的經濟利益。實際上,當犯罪人把“掙大錢”作為自己價值體系的核心時,他們是在遵守而不是僭越社會規則[11]。獲取財富這一要素是社會的主流文化中的關鍵要素。黑惡勢力組織以獲取財富為首要目的,實際上便是對主流文化目標的認同。只是其獲取財富并非依靠制度性手段,而是采用了與社會常規性制度手段全然不同的方式。
(二)黑惡勢力對主流文化規范的否定評價
犯罪以一種非法的形式存在著,或者說,犯罪這一現象在人類的特定歷史時期總是在社會生活中占有一定的比重。犯罪現象集中表現著不同群體或個體之間的沖突與對立,是社會矛盾在各類生活場所中的凸顯。犯罪是犯罪人基于其感情的行為判斷和選擇,這種判斷和選擇囊括了犯罪人從事犯罪的原因與欲望。需要指出的是,促使犯罪人實施犯罪行為的種種要素,則與犯罪人所處群體的文化息息相關。所以,可以借用犯罪人所處群體的文化背景對犯罪人的犯罪行為進行解讀。其一,犯罪行為是孕育于文化之中的社會現象,若要對犯罪人實施的犯罪行為深入探究的話,必然離不開對犯罪文化背景的分析。其二,如果僅僅對文化及背景進行淺層了解的話,也不會讀懂犯罪原因的深層含義,換言之,犯罪問題必須要從文化的視角進行深層解讀[12]。不論哪一類社會群體,其文化目標的確立都是以這個社會文化中的主流價值觀念為基準,同時以規范性的制度(法律規范)設定來作為達到文化目標的手段,而這些手段則將能夠最為有效達到文化目標的方法排除在外(如犯罪)。當社會中的成員都能夠接受社會統一價值觀念所形成的文化目標,并能夠采用合理且合法的制度性手段將文化目標予以實現時,便不會產生緊張情緒從而避免引發社會越軌行為。反之,當個體無法應用合理且合法的制度性手段達成文化目標時,就會出現目標與手段失衡的情況,進而引發個人的緊張情緒,并使行為處于失范狀態。大多數黑惡勢力犯罪的組織成員在實施犯罪行為的初期,或多或少都會存在此類緊張情緒,并且其實施的行為多會在合法與非法之間反復跳躍。但由于黑惡勢力組織具有集團性,這一特性便會將成員因實施越軌行為而產生的自我懷疑與愧疚等情緒進一步消解,導致其向黑惡勢力的文化觀念逐步靠攏。
塞林認為,可以將刑法視為行為規范體系中的一種,且其為禁止的行為規范。同時,刑法也列明了違反禁令的行為人所應承擔的懲罰方式。刑法規范的特征以及其所規定的禁止行為的類型或種類、懲罰的措施與方式,都取決于社會中對立法活動施加影響的集團的特點[13]。人類作為個體,生來便處于文化當中。同時,人類天生具有選擇和他人建立何種關系的稟賦,從其在接觸社會初始之時,便開始了漫長的適應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經由環境、他人的訓誡或者教導、自身的領悟與學習,人們便可以汲取各種正式或非正式的觀念。對個體而言,大多存在著正常與異常的反應方式,這類反應的判斷標準就是群體制定的規范。只要有社會集團的存在,便肯定伴隨著行為規范的存在。極端地說,行為規范是普遍存在的,它們不是哪一個社會集團的創造物,它們也不附從于任何政治界限,它們的表現形式也不局限于法律規范的形式[14]。上述規范為個體的反常行為提供范式與參照構架,文化沖突便是合法行為與非法行為之間的沖突。它們是文化生長與文明生長過程中的副產品,有時被認為是行為規范從一個文化復合體或區域遷移到另一個文化復合體或區域的結果[15]。而上文中所提及的刑法規范與行為規范,并非一成不變的,其會隨著社會文明的發展而產生變化。其中,刑法中有關犯罪的定義在不同的時間段內也不盡相同,在不同的地域中更是存在定性層面的差異,這事實上是不同的社會階段中社會規范與行為規范相異的體現。
亞文化都是在主流文化的影響下產生的。換言之,亞文化根植于主流文化之中,其產生卻代表著主流文化的反向延伸。黑惡勢力組織成員不僅普遍認同社會主流的文化目標,并且其在進行犯罪活動以外的日常活動中所實施的行為仍然遵循著主流文化的目標與規范性的制度。這是因為黑惡勢力組織成員對于社會主流文化的認同具有趨向性。規范性制度如果能夠對黑惡勢力組織成員實現文化目標起到積極的作用,那么,組織成員便會遵循這一規范性制度手段;倘若制度性手段不能使其實現文化目標,那么組織成員就會否定規范性制度從而采取其他能實現文化目標的手段。
黑惡勢力組織成員將自身所實施的犯罪行為進行內在合理化,并且將自身認同的價值觀念進行中和。而后,組織成員對于法律規范的認同與否,是決定其在主流文化與組織文化沖突時進行選擇的關鍵要素。因為法律代表著主流文化規范,如果組織成員積極地對法律規范進行否定,抑或是對法律產生消極認同的態度,都會導致組織成員與主流文化相背而行。與此同時,此類成員便會以黑惡勢力文化為主導,繼而實施犯罪行為。其中,也有組織文化認為,作為主流文化規范的法律是“非法”的,這里的“非法”意指組織成員對文化規范的全面否定。換言之,黑惡勢力組織成員對于組織文化的認同度遠遠高于主流文化,并且其所實施的犯罪行為便是將此類組織文化的思想外化于具體的行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