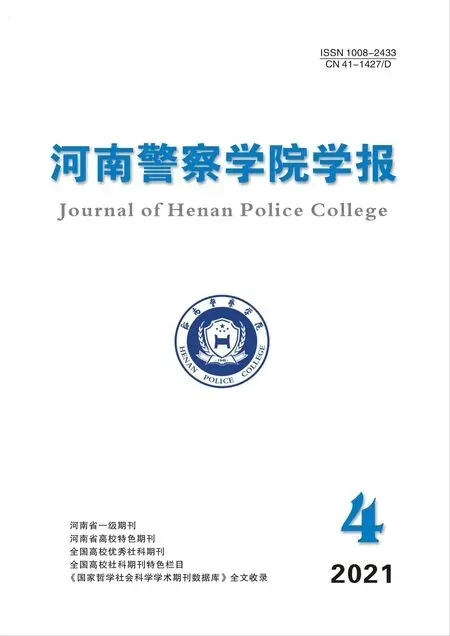醉酒型危險(xiǎn)駕駛罪司法境遇與刑法結(jié)構(gòu)之反思
王 禎
(廣東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 法學(xué)院,廣東 廣州 510230)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7年發(fā)布了《關(guān)于常見犯罪量刑指導(dǎo)意見(二)》(下稱《意見》),其中第一條的規(guī)定便是為了改善醉酒型危險(xiǎn)駕駛罪在司法實(shí)務(wù)中的適用狀況,提高緩刑、免刑適用率,應(yīng)對近年來該類案件數(shù)量的快速增長。該條對醉酒型危險(xiǎn)駕駛罪的定罪量刑工作做出全新的表述,要求司法機(jī)關(guān)審理“醉駕”案件時(shí),應(yīng)當(dāng)在全面考慮行為人的醉酒程度、駕駛機(jī)動車的類型等多種因素的前提下,綜合案件實(shí)際情況進(jìn)行定罪量刑。其中,對情節(jié)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行為,不予定罪;情節(jié)輕微的,可以免予處罰。《意見》對危險(xiǎn)駕駛罪所作的規(guī)定表面上是對本罪的定罪量刑進(jìn)行指導(dǎo),但實(shí)質(zhì)上是對我國刑法結(jié)構(gòu)的反思。如何將刑法結(jié)構(gòu)由“厲而不嚴(yán)”向“嚴(yán)而不厲”或“中罪中刑”轉(zhuǎn)變,縝密刑事法網(wǎng),構(gòu)建包含重罪、輕罪、輕微罪在內(nèi)的層次分明的犯罪分層體系,已經(jīng)成為刑法必須面對的問題。
一、醉酒型危險(xiǎn)駕駛罪的司法現(xiàn)狀
(一)“酒駕”型危險(xiǎn)駕駛罪在刑事案件中的占比逐年上升
《刑法修正案(八)》設(shè)定本罪是為了解決2011年前后引起強(qiáng)烈社會反響的“醉駕”問題。因此,危險(xiǎn)駕駛罪入刑之初,條文中只規(guī)定了兩種情形,即“醉酒駕駛機(jī)動車的”與“在道路上追逐競駛的”。后來,《刑法修正案(九)》又增加了“超速”“超載”以及“違反危險(xiǎn)化學(xué)品運(yùn)輸規(guī)定”三種情形。為初步了解醉酒型危險(xiǎn)駕駛罪的司法現(xiàn)狀,筆者在北大法意司法案例網(wǎng)站中以“一審案件”“危險(xiǎn)駕駛罪”“醉駕”“緩刑考驗(yàn)期”為關(guān)鍵詞查詢了歷年的司法案例。從本罪2011年設(shè)立之時(shí)起,至2020年12月31日,共查詢到一審判決書1289613份。其中,涉及“醉駕”情節(jié)的一審判決書共1198670份,占總數(shù)的92.9%。其中,2011年至2016年共有一審判決書415218份,而《意見》公布后的2017至2020年共有一審判決書783452份(1)數(shù)據(jù)來源于北大法意,查詢時(shí)間2021年4月28日http://www.lawyee.org/PubPage/List?PageID=21。。從數(shù)據(jù)中可以直觀地看到,“醉駕”案件在危險(xiǎn)駕駛罪中占有極高的比例,自其入刑以來,每年的案件數(shù)量以極快的速度增長。雖然本罪在遏制酒后駕駛行為,提升道路安全方面發(fā)揮的作用功不可沒,但不能忽視龐大的案件數(shù)量帶來的社會問題。特別是,司法資源被大量消耗在本應(yīng)屬于輕微犯罪甚至是行政違法行為的“醉駕”案件中,許多行為人也因此背上了犯罪前科。此外,伴隨著本罪案件數(shù)量的快速增長,其每年在全國刑事案件中占據(jù)的比例也越來越高。“在罪名剛剛出臺的2011年,其占全國刑事案件總數(shù)的比例為1.4%,隨后便一直以較高的速度增長,2012年所占比例達(dá)到6.5%,2013年已經(jīng)占據(jù)總數(shù)的9.4%,2014年為10.7%,達(dá)到總數(shù)的十分之一。”[1]2018年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bào)告》顯示,因危險(xiǎn)駕駛罪而被起訴的案件占全年被起訴案件的11%(2)2018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bào)告,查詢時(shí)間2021年4月28日https://www.spp.gov.cn/spp/gzbg/201803/t20180325_372171.shtml。。到了2019年時(shí),這個數(shù)字已經(jīng)達(dá)到了17%,危險(xiǎn)駕駛罪一躍成為公訴機(jī)關(guān)起訴人數(shù)最多的罪名(3)2019年全國檢察機(jī)關(guān)主要辦案數(shù)據(jù),查詢時(shí)間2021年4月28日https://www.spp.gov.cn/spp/xwfbh/wsfbt/202006/t20200602_463796.shtml#1。。
(二)入罪率高且緩刑適用率低
在案件數(shù)量巨大的同時(shí),危險(xiǎn)駕駛罪還伴隨著入罪率極高、緩刑適用率低等特點(diǎn)。就全國而言,從“酒駕”入刑至2020年年底,一審判決中緩刑適用率僅為11.4%。就地方而言,大部分地區(qū)對醉酒型危險(xiǎn)駕駛罪采用嚴(yán)罰化的態(tài)度,基本不適用或很少適用緩刑。“從酒駕入刑至2012年8月29日,北京市一中院下轄的八個區(qū)、縣基層法院在一年多的時(shí)間里,共判決‘醉駕’案件320起,而在這320起案件中,沒有一個嫌疑人被適用緩刑、免刑,所有犯罪嫌疑人均被判處實(shí)刑”[2];“在酒駕入刑的第二年,沈陽市各個基層法院與中級人民法院未對任何一起從事‘醉酒’型危險(xiǎn)駕駛罪的犯罪嫌疑人適用緩刑,均判處實(shí)刑。”[3]雖然也存在判決較為寬松的地區(qū),比如,“廣東、安徽、重慶、云南等地對‘醉駕’的刑罰適用比較寬松,入刑一年后,這些地區(qū)使用緩刑、免刑的比例達(dá)到了40%,甚至有法院高達(dá)73%”[1]。但整體上來說,在《刑法修正案(八)》出臺后、“醉駕”剛剛?cè)胄痰膸啄陼r(shí)間里,緩刑適用被嚴(yán)格控制,各地司法機(jī)關(guān)為了迎合嚴(yán)懲醉酒駕駛機(jī)動車的民意,基本上都開啟了嚴(yán)罰模式。令人感到意外的是,“醉駕”入刑的數(shù)年后,雖然此類案件的數(shù)量在不斷上升,但許多法院的判決卻悄然改變了態(tài)度。“沈陽市各地區(qū)司法機(jī)關(guān)對醉駕案件的處理態(tài)度不再如醉駕剛?cè)胄虝r(shí)那樣嚴(yán)罰,反而逐漸趨向于輕緩化。最重要的依據(jù)便是近年來沈陽市各級人民法院對‘醉駕’案件進(jìn)行緩刑適用時(shí)發(fā)生了變化。2015年的緩刑適用率已經(jīng)從最初的0增長為10.5%,而在隨后的2016年則猛增至21%,較醉駕入刑之初,已有明顯改變。”[3]
不能忽略的是,局部地區(qū)的輕緩化無法改變整體的嚴(yán)刑化。從整體上來看,“醉駕”案件數(shù)量劇增的趨勢沒有改變,嚴(yán)格控制緩刑、免刑適用的態(tài)度也沒有改變。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主要是嚴(yán)刑思想與民意影響(4)雖然近年來機(jī)動車數(shù)量的快速增長也是造成案件數(shù)量攀升的原因,但不可否認(rèn)重刑主義與嚴(yán)罰化民意的影響才是其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的影響因素。。其一,對于“醉駕”行為的規(guī)制,在立法時(shí)便已受到嚴(yán)罰民意的影響,隨后這種影響又進(jìn)入司法領(lǐng)域。其二,除民意影響外,部分學(xué)者與司法工作人員在面對“醉駕”案件時(shí)陷入了一種思維怪圈,即本罪最高刑僅為拘役,而拘役已經(jīng)十分輕微,為了達(dá)到懲罰犯罪、維護(hù)社會穩(wěn)定的目的,應(yīng)當(dāng)少用或不用緩刑、免刑,否則會使本罪成為一個空懸的法條,缺乏震懾力,無法完成刑法預(yù)防與懲罰犯罪的使命。
在上述民意與司法工作人員重刑思想的雙重影響下,“醉駕”類案件往往不被適用緩刑、免刑。然而,這種降低緩刑、免刑適用率以提高刑法威懾力的思維并不可取。緩刑、免刑適用率不應(yīng)當(dāng)與個罪的最高刑掛鉤。一直以來,無論是學(xué)界還是實(shí)務(wù)界,許多人固有的犯罪觀便是“罪刑一體”。即,有犯罪便意味著要被科以實(shí)際的刑罰。這種思想仍然不斷地對我國的刑事司法產(chǎn)生影響,而危險(xiǎn)駕駛罪的出現(xiàn)是對這種思想的沖擊。“醉駕”應(yīng)當(dāng)在情節(jié)較為惡劣時(shí)才受到刑法的規(guī)制,但是從立法中可以看到,“醉駕”情形并不要求“情節(jié)嚴(yán)重”或者“情節(jié)惡劣”。“最終做出這樣的選擇,原因之一是民眾對嚴(yán)懲‘醉駕’的呼聲已經(jīng)高漲到了影響立法的程度,立法者不得不順應(yīng)民意;之二是行政措施在以往的時(shí)間里難以有效約束‘醉駕’,不得不用刑事措施進(jìn)行規(guī)制。”[4]這種社會治理的過度刑法化不僅體現(xiàn)在近年來刑法罪名越來越多,修正案越出越快,而且體現(xiàn)在司法實(shí)務(wù)中占據(jù)主流的重刑化判決之中。
綜上所述,可以將“醉酒”型危險(xiǎn)駕駛罪案件數(shù)量日益增多而緩刑適用率卻一直維持在一個較低水平的原因歸納為:我國酒文化的氛圍濃厚。雖然本罪已經(jīng)實(shí)行十年,但醉酒駕駛機(jī)動車的行為仍然頻發(fā)。不可否認(rèn)“酒駕”入刑的積極作用,但司法部門對于本罪的認(rèn)定往往十分機(jī)械,缺乏彈性。在較長的一段時(shí)間內(nèi),許多地區(qū)的司法部門都是為了迎合民意,對“醉駕”實(shí)行嚴(yán)罰化的政策或態(tài)度。在這種民意影響下,某些城市甚至出現(xiàn)了一年內(nèi)所有嫌疑人均被判處實(shí)刑而無適用緩刑、免刑的情況。近年來,此種情況雖然有所緩解,但不得不承認(rèn),司法機(jī)關(guān)在處理危險(xiǎn)駕駛案件時(shí)嚴(yán)罰化的態(tài)度仍未從根本上改變。
二、“醉酒”型危險(xiǎn)駕駛罪緩刑適用之探析
如上文所述,在“醉駕”入刑的十年時(shí)間里,雖然案件數(shù)量每年以極快的速度增加,但緩刑適用率仍不高。學(xué)界以及實(shí)務(wù)界對本罪的定罪量刑尤其是緩刑適用問題出現(xiàn)了三種不同的態(tài)度,衍生了三種不同的學(xué)說。
(一)緩刑適用的學(xué)理爭論
首先出現(xiàn)的是占據(jù)主體地位的“慎重適用論”,這也是“醉駕”入刑后最早誕生的學(xué)說。該學(xué)說在“醉駕”入刑初期受到大量學(xué)者和司法工作人員的贊同,認(rèn)為“醉駕”既然最高刑只有拘役,而我國飲酒后駕車的情況又十分嚴(yán)峻,為了提升刑法威懾力,降低“醉駕”數(shù)量,應(yīng)當(dāng)對嫌疑人慎重適用緩刑、免刑,“不能將醉駕不入刑作為此類犯罪處理的常態(tài),刑法本身對人造成的痛苦就是對抗犯罪的不可缺少的‘易感觸的力量’”[5]。這種學(xué)說是重刑主義思想在醉酒型危險(xiǎn)駕駛罪中的展開,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nèi)容:首先,公安機(jī)關(guān)應(yīng)當(dāng)把住嚴(yán)防醉酒駕駛的第一關(guān)。公安機(jī)關(guān)在立案偵查的過程中,不可放任“醉駕”行為的滋生,要將其中大部分都納入立案范疇之中;只有那些真正情節(jié)顯著輕微,且沒有造成危害的行為,才可以根據(jù)案件具體情形將其排除于立案范圍。其次,公訴機(jī)關(guān)對公安機(jī)關(guān)移送的“醉駕”行為進(jìn)行核查時(shí),要確保大量案件均應(yīng)被起訴,法院也應(yīng)當(dāng)對其定罪。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diǎn),由于本罪的最高刑只有拘役,若大量適用緩刑、免刑,難以保證刑法的威懾力,因此對酒駕行為適用緩刑、免刑應(yīng)當(dāng)十分慎重,數(shù)量不可過多,或者盡量不用。可見,提出“慎重使用論”的學(xué)者往往以本罪最高刑過低為由,否定在判決時(shí)適用緩刑或免刑。“醉駕的最高刑只有拘役,其刑罰本身就很輕,若在此基礎(chǔ)上還對行為人適用緩刑或免刑,將無法讓行為人受到相應(yīng)的制裁,感受到刑法的威懾力,最終會影響治理效果。”[6]不僅是學(xué)界,許多從事司法實(shí)務(wù)的工作人員也紛紛表示,為了強(qiáng)化對“醉駕”行為的管理,鞏固案件處理的社會效果,從而弘揚(yáng)立法精神,應(yīng)當(dāng)盡量減少緩刑與免刑的適用,其亦是“慎重適用論”的支持者。
其次,是認(rèn)為本罪只要依照法律規(guī)定適用緩刑、免刑即可的“等同適用論”。該學(xué)說認(rèn)為,無需將危險(xiǎn)駕駛罪與其他犯罪進(jìn)行區(qū)分。一方面不應(yīng)采用嚴(yán)罰化觀點(diǎn),人為降低本罪緩刑、免刑適用率;另一方面也不必故意提高緩刑、免刑的適用率。“對于其中情節(jié)輕微的部分,如果根據(jù)案件事實(shí)認(rèn)為不需要判處刑罰,可以對行為人依法免予刑事處罰;依據(jù)案件事實(shí)認(rèn)為符合緩刑適用條件的,應(yīng)當(dāng)依法對行為人適用緩刑。”[7]但“醉駕”作為我國每年數(shù)量最多的案件,其情形與其他犯罪不太相同。立法本身的目的是為了懲罰其中一部分行為人,而挽救其他行為人,同時(shí)降低飲酒駕車的數(shù)量。如果本罪在適用時(shí),與其他罪名不進(jìn)行區(qū)分,以相同的比例適用緩刑、免刑,其實(shí)也是一種簡單粗暴的方式,這種“一刀切”的方法既不符合刑法的謙抑性原則與刑罰的經(jīng)濟(jì)性原則,也與立法目的不符。
最后,是希望在“酒駕”案件的審理過程中能夠?qū)π袨槿藘?yōu)先適用緩刑、免刑的“優(yōu)先適用論”。其希望能以輕緩化而非嚴(yán)罰化的態(tài)度處理“酒駕案件”,增加此類案件緩刑的適用率,并且不人為排除此類案件免刑的適用。雖然近年來我國學(xué)界對“酒駕”行為逐漸主張輕緩化,司法機(jī)關(guān)對“醉駕”嚴(yán)罰化的態(tài)度也有所緩解,部分地區(qū)不再出現(xiàn)全年沒有一個“酒駕”案件適用緩刑的現(xiàn)象,但持有“優(yōu)先適用”觀點(diǎn)的學(xué)者與司法工作人員仍然是少數(shù)的。
(二)“但書”條款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之構(gòu)建
在“醉駕”入刑之初,“慎重適用論”便占據(jù)主流地位,多數(shù)學(xué)界的學(xué)者以及司法實(shí)務(wù)機(jī)關(guān)的工作人員對“醉駕”往往采取嚴(yán)罰化的態(tài)度,這也迎合了社會上的民意。但近年來,特別是在《意見》公布后,建議增加緩刑、免刑適用的意見越來越多,也有越來越多的法官愿意在此類案件中嘗試適用緩刑、免刑。但是,《意見》雖然為“醉駕”類案件適用緩刑、免刑做出了指導(dǎo),但并未給出一個切實(shí)可行的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用以判斷在何種情形下應(yīng)當(dāng)或可以適用緩刑、免刑。
本文認(rèn)為,行為人醉酒程度極低的,可以依據(jù)案件的具體事實(shí),認(rèn)定其無罪或給予緩刑、免刑處理。此處的醉酒程度,應(yīng)當(dāng)是對多方面因素綜合后得出的結(jié)果。依照我國現(xiàn)行法律法規(guī)的規(guī)定,只要行為人血液中酒精濃度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就已經(jīng)達(dá)到了“醉駕”的程度(5)需要注意的是,浙江省2012年已將該標(biāo)準(zhǔn)調(diào)整為120mg/100ML,2017年再次調(diào)整為180mg/100ML,并且規(guī)定不達(dá)140mg/100ML的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而只要符合該標(biāo)準(zhǔn),則無須判斷行為人的真實(shí)精神狀況與辨認(rèn)識別能力。該標(biāo)準(zhǔn)是“醉駕”入刑之初受民意影響產(chǎn)生的。但從生理學(xué)與醫(yī)學(xué)的角度看,并不符合客觀情況。每個人生理特征的差異導(dǎo)致其對酒精的耐受程度不同,飲酒后不一定都會造成自身控制能力與辨認(rèn)能力的減弱。即使飲酒數(shù)量相同,其控制能力與辨認(rèn)能力減弱的程度也不一定相同。具體來說,對于酒精耐受程度較高的個體,往往會出現(xiàn)測量時(shí)行為人雖然血液酒精含量已經(jīng)達(dá)到了80mg/100ML,但其精神狀態(tài)并未產(chǎn)生明顯變化,亦不會影響其正常的駕駛行為。也有可能出現(xiàn)行為人雖然血液酒精含量并未達(dá)到80mg/100ML,但其精神狀態(tài)已經(jīng)錯亂,辨認(rèn)能力與控制能力嚴(yán)重下降,無法再正常駕駛機(jī)動車輛。很明顯,血液酒精含量未達(dá)標(biāo)準(zhǔn)但精神狀態(tài)已經(jīng)急劇下滑的情形更易造成危害,具有更大的社會危害性。若僅僅按照80mg/100ML的濃度標(biāo)準(zhǔn),則無法懲罰危害性更大的行為,這明顯不符合罪責(zé)刑相適應(yīng)原則。因此,可以將醉酒駕車的標(biāo)準(zhǔn)分為主觀與客觀兩部分,客觀部分為原先的濃度標(biāo)準(zhǔn),可以繼續(xù)嚴(yán)格執(zhí)行。而主觀部分則是當(dāng)場對行為人進(jìn)行行為能力的測試,用以判斷其精神狀態(tài)與控制、辨認(rèn)能力。最終綜合主客觀判斷結(jié)果,對于那些沒有明顯超過濃度標(biāo)準(zhǔn),且控制能力與辨認(rèn)能力沒有明顯下降的行為人,可以認(rèn)定為“情節(jié)顯著輕微危害不大”或“情節(jié)輕微”,最終不予定罪或適用緩刑、免刑。
三、新型刑法結(jié)構(gòu)之構(gòu)建
刑罰的輕微化使危險(xiǎn)駕駛罪成為刑法中特殊的個體,有學(xué)者將其形容為“平整的鍋底凹下去的那部分”。隨著社會的快速發(fā)展,在經(jīng)濟(jì)不斷上行的同時(shí),各種各樣的犯罪行為也不可避免地伴隨產(chǎn)生。以“醉駕”為例,其案件數(shù)量在不斷攀升,這本身便有私家車數(shù)量不斷增加的原因。在車輛很少的時(shí)代,“醉駕”是一個無從談起的話題。既然社會發(fā)展的同時(shí)新的犯罪行為也在不斷產(chǎn)生,那么刑法如何隨著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而轉(zhuǎn)型,以此來應(yīng)對全新的犯罪現(xiàn)象,便成為一個必須直面的問題。
二十世紀(jì)八十年代,儲槐植教授曾提出“嚴(yán)而不厲”的刑法結(jié)構(gòu)的構(gòu)思。近年來,同樣有學(xué)者提出了“中罪中刑”的刑法結(jié)構(gòu)的觀點(diǎn)。兩者其實(shí)都是對我國目前“厲而不嚴(yán)”的刑法結(jié)構(gòu)的反思與發(fā)展,實(shí)質(zhì)都是由嚴(yán)密的法網(wǎng)和較為輕緩的刑罰代替原先的重刑主義。這樣便不再僅僅是刑罰輕重的問題,而是涉及了犯罪圈大小的問題。在刑法將危險(xiǎn)駕駛罪的最高刑規(guī)定為拘役后,學(xué)者們對這種全新的立法動向表達(dá)了不同觀點(diǎn)。有學(xué)者認(rèn)為,“‘醉駕’入刑可以認(rèn)為是我國分層化的開端,因?yàn)檩p罪的增多,必然導(dǎo)致刑法結(jié)構(gòu)的分層化,最終可以據(jù)此形成‘重罪—輕罪—輕微罪’的全新刑法結(jié)構(gòu)”[8]。但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僅有輕罪入刑并不代表我國刑法啟動了分層化的進(jìn)程,個罪的輕型化不足以完成最終刑法結(jié)構(gòu)的轉(zhuǎn)變,而是應(yīng)當(dāng)引入“微罪”處理機(jī)制。“‘醉駕’入刑,不論是從立法時(shí)所設(shè)定的法定刑角度看還是從審判時(shí)的宣告刑角度看,該罪都是典型的‘微罪’,只有在引入‘微罪’處理機(jī)制后,才能最終形成全新的刑法結(jié)構(gòu)”。[2]表面上看,“醉駕”入刑只是刑法對社會活動管理的又一次擴(kuò)張,但其背后所涉及的內(nèi)容應(yīng)當(dāng)是輕微罪體系的引入與刑法結(jié)構(gòu)的完善。
通過對我國刑法結(jié)構(gòu)現(xiàn)狀的描述,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雖然這種全新的立法動向確實(shí)存在,但不同學(xué)者對其卻有不同的解讀。第一種觀點(diǎn)認(rèn)為,“醉駕”入刑,表明我國刑法已經(jīng)開始構(gòu)建輕罪、重罪同時(shí)存在的犯罪分層體系,以后將會慢慢形成輕重分級的結(jié)構(gòu)。而后一種觀點(diǎn)則認(rèn)為,“醉駕”入刑恰恰表明我國犯罪分層的刑法結(jié)構(gòu)尚未開始建立,不僅需要在罪名方面,也需要在其他多個方面進(jìn)行完善。本文支持第二種觀點(diǎn)。“醉駕”入刑雖然對我國目前的刑法結(jié)構(gòu)產(chǎn)生了沖擊,但這并不代表新型的刑法結(jié)構(gòu)已經(jīng)開始建立。“事實(shí)上,犯罪分層是一種十分復(fù)雜的刑事制度設(shè)計(jì),不僅僅涉及重罪、輕罪、輕微罪等不同層次的罪名,還應(yīng)當(dāng)涉及融實(shí)體法、程序法及刑事政策于一體的完整的犯罪反應(yīng)系統(tǒng)。”[9]正是由于我國“厲而不嚴(yán)”的犯罪結(jié)構(gòu)仍然存在,而輕重分層的新型犯罪結(jié)構(gòu)尚未建立,才導(dǎo)致對醉酒型危險(xiǎn)駕駛罪始終以嚴(yán)罰化為主流。而通過犯罪分層,刑法結(jié)構(gòu)將重建,其對犯罪行為的反應(yīng)將轉(zhuǎn)化為“重罪-輕罪-輕微罪”多個子系統(tǒng),“其中對重罪的反應(yīng)系統(tǒng)將較為穩(wěn)定,可以貫徹重刑主義思想;而對輕微犯罪的反應(yīng)系統(tǒng)將較為活躍,處罰溫和化、輕微化得以落實(shí)。兩者各成體系,互不影響”[9]。
(一)以“去重刑化”為核心的“嚴(yán)而不厲”的刑法結(jié)構(gòu)
“罪”是刑法結(jié)構(gòu)中“嚴(yán)”的部分,反映出一個國家刑法法網(wǎng)是否嚴(yán)密,能否讓行為人難逃法網(wǎng),作用在于控制嚴(yán)重的社會越軌。想要遏制犯罪行為的發(fā)生,首先應(yīng)當(dāng)編織好“法網(wǎng)”,使犯罪圈既不過大也不過小。而“刑”則是刑法結(jié)構(gòu)中“厲”的部分,代表了法定刑的嚴(yán)厲程度。“厲而不嚴(yán)”的刑法結(jié)構(gòu)在刑罰方面表現(xiàn)得十分嚴(yán)苛,但法網(wǎng)嚴(yán)密程度卻遠(yuǎn)遠(yuǎn)不足。與之相比,“嚴(yán)而不厲”的刑法結(jié)構(gòu)在面對不同犯罪行為時(shí),處置手段將更加合理。 “嚴(yán)而不厲”的刑法結(jié)構(gòu)的特點(diǎn)是刑法的分層化、輕緩化與法網(wǎng)的分級化、嚴(yán)密化。應(yīng)當(dāng)注意的是,“嚴(yán)而不厲”也有一個度的限制。“嚴(yán)”不是要求刑事法網(wǎng)的范圍無限擴(kuò)大,導(dǎo)致罪名越來越多,越來越龐雜,而是看法網(wǎng)是否存在漏洞。“厲”也不是要求法定刑嚴(yán)格程度無限制地降低。“嚴(yán)而不厲”采取一種“寬而淺”的結(jié)構(gòu),對類似于“醉駕”類的案件,采取非犯罪化、非刑罰化、非監(jiān)禁化的處置措施;對一些傳統(tǒng)刑法中十分嚴(yán)重的犯罪則采取犯罪化、刑罰化、監(jiān)禁化的手段。具體而言,“在對犯罪行為的反應(yīng)方式上,不再僅僅依靠刑罰來應(yīng)對,而是積極拓寬其他制裁措施的適用”[10],努力增加其他刑罰以外的方式,如具結(jié)悔過、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同時(shí)對輕微罪增加緩刑、免刑的適用。“在反應(yīng)時(shí)間上,由消極的事后反應(yīng)轉(zhuǎn)變?yōu)榉e極的事前防衛(wèi)。”[10]
(二)以“限制犯罪圈”為核心的中罪中刑的刑法結(jié)構(gòu)
近年來,有學(xué)者針對“嚴(yán)而不厲”的刑法結(jié)構(gòu)提出了一些建議,在肯定其合理性與科學(xué)性的基礎(chǔ)上希望能夠?qū)⑵溥M(jìn)一步完善。“我國未來的刑事政策與刑法結(jié)構(gòu)取向應(yīng)當(dāng)是在‘嚴(yán)而不厲’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出‘中罪中刑’的模式,既不偏向于嚴(yán)罪,也不偏向于厲刑,而是中和、適中。”[11]
刑法結(jié)構(gòu)所要解決的主要是定罪與量刑問題。一方面,從定罪的角度看,主要問題是如何確定犯罪圈的大小,即刑事法網(wǎng)的嚴(yán)密程度。“中罪中刑”的刑法結(jié)構(gòu)提倡的犯罪圈大小是一種適中的模式,即在確定犯罪圈大小時(shí)不對“嚴(yán)”過于迷信,不認(rèn)為利用刑事法網(wǎng)圈定各種犯罪后可以解決所有社會問題,也不過于強(qiáng)調(diào)刑法的謙抑原則,而對某些原本應(yīng)受刑法規(guī)制的行為不聞不問。采用犯罪圈適中的立場,就必須將某些并非通過刑法才可以規(guī)制的行為排除于犯罪圈之外,比如“醉駕”就不屬于必須通過刑罰手段才能得到解決的問題。此外,對部分在司法實(shí)務(wù)中已經(jīng)形同虛設(shè)的犯罪,可以將其排除于犯罪圈之外,考慮采用非犯罪化的處罰方法。當(dāng)然,假如以后遇到了新的嚴(yán)重危害社會安全、穩(wěn)定的問題,仍然可以通過擴(kuò)大犯罪圈的方法,對新的社會問題予以規(guī)制,但必須在謹(jǐn)慎地、經(jīng)過反復(fù)論證的情況下才能對新出現(xiàn)的社會問題犯罪化。我國刑法一直存在修訂過于頻繁的問題,且很多時(shí)候一次修訂會增加大量新的罪名。從刑法典實(shí)施的1997年至2021年,在這24年的時(shí)間里,已經(jīng)連續(xù)出臺了十一部刑法修正案。頻繁地對法律進(jìn)行修訂,必然會造成對法律體系穩(wěn)定性的破壞和對法律本身權(quán)威性的踐踏,所以,頻繁修訂刑法的利弊得失還須再三權(quán)衡。“同時(shí),這種修改也反映出了過于重視政策性的思想。”[11]刑法修訂應(yīng)當(dāng)至少間隔五年以上,且每次修改的內(nèi)容不宜過大,出臺的罪名不宜過多,以此來維護(hù)刑法的權(quán)威性與穩(wěn)定性。
另一方面,就刑罰幅度而言,主要問題是刑罰的分層,重罪配以較高的刑罰,輕罪配以較低的刑罰,不同分層分別對不同的犯罪行為進(jìn)行規(guī)制,從我國實(shí)際出發(fā)為不同罪名選擇適當(dāng)?shù)男塘P幅度,防止重刑主義思想影響輕罪的判決,同時(shí)也避免輕刑化的“跟風(fēng)”趨勢影響重罪判決。“中罪中刑”認(rèn)為,無論是片面的重刑主義還是片面的輕刑化,都會對我國的刑法結(jié)構(gòu)矯枉過正。片面的重刑主義將會嚴(yán)重?fù)p害行為人的利益,不利于權(quán)利保障,若其影響到危險(xiǎn)駕駛罪等輕罪判決,便會產(chǎn)生降低緩刑、免刑適用的問題。而片面的輕刑化則會使被害人的權(quán)益遭到踐踏,無法滿足我國刑法“有罪必究”的基本要求,若其影響重罪的判決則會降低刑法的報(bào)應(yīng)機(jī)制,導(dǎo)致犯罪成本過低,嚴(yán)重破壞刑法的威懾力。
(三)“嚴(yán)而不厲”與“中罪中刑”的刑法結(jié)構(gòu)帶來的啟示
無論采用何種學(xué)說,刑法結(jié)構(gòu)的主要研究對象都是我國的犯罪圈與刑罰量。所謂刑法結(jié)構(gòu),是把刑法的各個要素進(jìn)行整合,并將其搭配組合最終形成針對不同情形做出不同反應(yīng)的組合形式。“嚴(yán)而不厲”與“中罪中刑”都強(qiáng)調(diào)在構(gòu)建刑法結(jié)構(gòu)時(shí),必須確保其內(nèi)部要素(罪名)合理,搭配(刑罰)均衡。因?yàn)樾谭ńY(jié)構(gòu)是否合理,與其所設(shè)置的犯罪圈大小及刑罰輕重密切相關(guān)。在詳細(xì)分析了上述兩種刑法結(jié)構(gòu)的特點(diǎn)之后,本文認(rèn)為,想要對我國目前的刑法結(jié)構(gòu)進(jìn)行優(yōu)化,第一應(yīng)當(dāng)科學(xué)劃定犯罪圈。在設(shè)定全新罪名的同時(shí),應(yīng)當(dāng)將一些無須刑法規(guī)制或形同虛設(shè)的罪名剔除。同時(shí)為了確保刑法的穩(wěn)定性,犯罪圈的調(diào)整不應(yīng)過于頻繁。第二應(yīng)當(dāng)對刑罰進(jìn)行分層,對刑罰投入量與罪行的配比進(jìn)行權(quán)衡。對重罪可以采用重刑主義,對輕罪則盡量采用輕緩化的處置方式,以滿足刑法結(jié)構(gòu)內(nèi)部要素配置合理、均衡的要求。
同時(shí),還應(yīng)當(dāng)引導(dǎo)民意正確參與,而非主導(dǎo)立法、司法。“若一旦發(fā)生結(jié)構(gòu)錯位,就可能引發(fā)刑事政策系統(tǒng)的混亂。” 以醉酒型危險(xiǎn)駕駛罪等輕微犯罪為例,一旦嚴(yán)罰民意占據(jù)主導(dǎo)作用,一是“會引發(fā)前置的羈押性強(qiáng)制措施的適用,為確保被判處監(jiān)禁刑的犯罪人到案而采取羈押性強(qiáng)制措施”[12],二是會擴(kuò)大后續(xù)的非刑事性社會制裁。司法判決如果過度受到民意的影響,則會產(chǎn)生輕罪嚴(yán)罰化的結(jié)果,監(jiān)禁刑大量適用而緩刑、免刑適用反而更低。監(jiān)禁刑一旦被廣泛地適用,會使大量犯罪嫌疑人喪失作為其唯一生活來源的工作。設(shè)立這類輕罪的目的是通過懲罰小部分人而警醒大部分人。監(jiān)禁刑適用范圍過大,會激發(fā)更多的社會不穩(wěn)定。因此,若想實(shí)現(xiàn)立法的初衷,將“醉駕”行為對社會穩(wěn)定的影響降至最低,司法工作人員必須在整個刑事訴訟中保持獨(dú)立的思考與判斷,確保罰當(dāng)其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