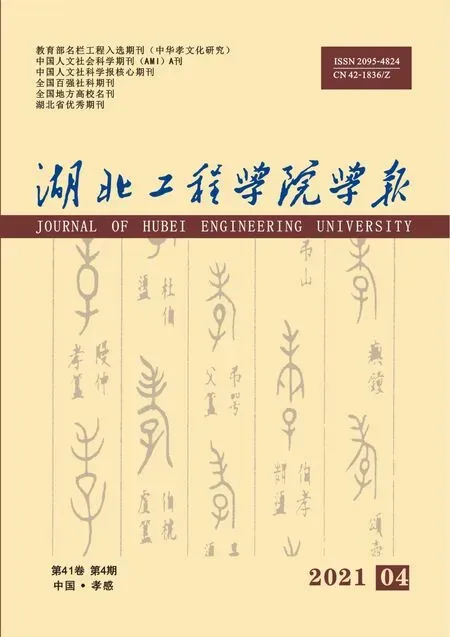對傳統孝道的反思
孫君恒,關殷穎
(武漢科技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 武漢 430081)
中國傳統孝道,扎根于中國文化土壤, 是中國老百姓倫理道德精神的支柱之一。孝道,慎終追遠,光宗耀祖,家國情懷,溢于言表。但不加分辨,簡單照搬,全盤接收,并不可取。真正抓住孝文化的真諦,并根據社會發展和現實需要對其進行當代闡釋與創造轉化,是當務之急。本文針對傳統孝道中存在的問題,對傳承孝道文化進行一點思索。
一、孝子典型中的問題
《二十四孝》記錄了二十四則元代以前的孝道故事,其二十四孝圖,活靈活現,家喻戶曉,對于推廣孝德功不可沒。時至今日,對之仍然存在誤讀、誤用,過度強調古代的孝親榜樣,容易導致真正孝文化的變味、變質,有的孝道與當今文明格格不入。魯迅先生曾經一針見血地批評這種“孝道” 對青年人是一種摧殘。魯迅先生指出,《二十四孝》中很多都是愚孝,里面的很多觀點有封建余孽,其中宣揚的孝道“親權重,父權更重”[1],父對于子,有絕對的權威,這種不平等的父子關系,是一種長者本位思想,不適合講究人格平等的現代社會要求。現舉三例說明。
1.嘗糞。《二十四孝》中有“嘗味知瘥念疾父,糞甜淚咸心焦苦”的說法,贊美庚黔婁通過嘗糞來觀察父親的病情。其孝行可嘉,但從道義論、效果論、正義論角度來看, 這樣的孝行不僅缺乏基本的倫理學基礎與醫學、科學常識, 更缺乏現實可操作性,這種做法不值得效仿。
2.喂蚊。吳猛八歲時就孝順父母,當時沒有蚊帳,怕父母遭蚊叮咬,吳猛夏夜讓蚊子恣意叮咬自己,不驅趕,好讓父母安心入睡。這個故事感人,立意固然好, 但其孝道缺乏智慧,其單純的善良動機、濃厚的理想主義道德傾向,反而影響了民智的開啟, 只能將吳猛當成純真的道德偶像。這種孝道不切實際,難以推廣。
3.埋兒奉母。侍奉母親是應該的,“埋兒奉母”是“慘絕人寰”的行為,讓人心驚膽戰。埋兒,在今天屬刑事犯罪行為,不值得宣揚。以現代法律和倫理觀來審視, 這種以犧牲親人或他人利益、生命而達到行孝目的的行為,顯然違背了人道主義的基本原則,也喪失了人性、親情、法理。
簡言之,封建社會宣揚的“孝道”,由于社會歷史與科學精神的局限性,我們在汲取精華的同時,也要去其糟粕。《二十四孝》作為孝道的經典范本,在今天,我們需要用批判的精神去繼承,不能簡單照搬。
二、“三年之喪”的守孝問題
“三年之喪”在我國古代喪服制度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影響已有數千年,親人離世,哭悼、守靈、安葬、守孝三年是最基本的禮儀。孔子的《論語·陽貨》指出:“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史記》載孔子歿后,其弟子皆結廬守墓,服喪三年,唯子貢思慕情深,三年之后復獨居三年始歸,今山東曲阜孔林仍然有子貢廬墓處、子貢手植楷,見證了子貢的赤誠之心。在今山東、河南等地,仍有守孝三年的習俗。
三年之喪,合乎人之常情,也有法理、道德的要求。意大利著名教育家蒙臺梭利說:“人生的頭三年勝過以后發展的各個階段,勝過三歲直到死亡的總和。”[2]三年之喪,不是僅僅為了守喪而強調守喪,其中的意義在于對故人撫養、貢獻的感恩與悼念,對人的價值的尊重,對后人的教化。《詩經·蓼莪》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醫學、生理學常識告訴我們,嬰兒從出生到三歲之間,是兒童成長至關重要的時期,民間有“三歲看大,七歲看老”的說法。“三”字在中國古代意味著多。幼兒三歲是生理和心理發育的關鍵時期,在科學不發達的古代,孩子三歲之前夭折的概率大,父母為此付出最多。從此角度上說子女起碼應該守孝三年,以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古代強調“舉孝廉”,將忠孝作為選拔官員的標準之一,是道德的試金石。古代帝王倡導三年之喪,身體力行,朝廷準官員守喪假,以此鼓勵孝道。《左傳·昭公十五年》強調:“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杜預注說:“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清朝的昭梿在《嘯亭雜錄·阿司寇》記載:“御史李玉明復上疏請行三年喪禮。”清代顧炎武的《日知錄·三年之喪》、 趙翼的《陔馀叢考·三年喪不計閏》等,都強調三年之喪。《儀禮·喪服》中所提出的子為父母、妻為夫、臣為君的三年喪期,直至西漢編纂的《禮記》一書,對三年喪期內的守喪行為在容體、聲音、言語、飲食、衣服、居處等方面,提出了具體的標準。如喪期內不得婚嫁、不得娛樂、不得洗澡、不得飲酒食肉、夫妻不能同房,必須居住在簡陋的草棚中,有官職者必須解官居喪等等。宋高宗的《起復詔》稱:“三年之喪,古今之通禮也”。
三年之喪的孝德禮儀,從唐代開始得到法律強化。唐代給官員喪假,禁止父母去世時娛樂,特別重視守喪行孝。《唐律疏儀》規定,居父母之喪,“喪制未終,釋服從吉,若忘哀作樂,徒三年;雜戲徒一年” 。居親之喪,違背居喪法律,要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喪制未終,釋服從吉,杖一百”,“居父母喪,生子,徒一年”,“父母之喪,法合二十七月,二十五月內是正喪,若釋服求仕,即當不孝,合徒三年;其二十五月外,二十七月內,是‘禫制未除,此中求仕為‘冒哀’合徒一年”,“居父母及夫喪而嫁娶者,徒三年,居期喪而嫁娶者杖一百”,“父母之喪,解官居服,而有心貪榮任,詐言余喪不解者,徒二年半”。為了保護和鼓勵喪葬行孝,唐代法律明文保護墓地、墓穴、陪葬品、墓志銘等,當時社會流行厚葬并刻墓志銘,對逝者蓋棺論定,再現、評價、表彰其一生,對其歌功頌德。居“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是創作墓志銘的高手,堪稱古今墓志銘第一人。宋代文學家蘇軾、歐陽修等也寫下了很多碑文、行狀、墓志銘,期望傳統美德在家族、社會發揚光大,極大地助推了傳統孝道的傳承。清代的《大清律例》,傳承唐代孝親的法律和道德合一的規定:“凡居父母及夫喪而身嫁娶者,杖一百;若男子居喪娶妾,妻女嫁人為妾者,各減二等……若居祖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喪而嫁娶者,杖八十。”《清通禮》載:“凡喪三年者,百日剃發。仕者解任。士子輟考。在喪不飲酒,不食肉,不處內,小入公門,不與吉事。”孝德上升為法律條文,自律和他律相互結合,良知與強制相輔相成,使守喪成為官方倡導的道德價值和民間遵守的規范。
守孝三年的典型,歷史多有記載。如《禮記·檀弓上》中“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孔子的弟子子貢;《宋史·趙宗憲傳》中的趙宗憲“居父喪,月余始食食,小祥菇落果實,終喪不飲酒食肉,比御猶狒入者久之” ;徐珂的《清稗類鈔·孝友類》稱連城張鵬翼篤信程、朱,行事遵禮,“居喪,疏食三年,不外游,不內寢,動必以禮”。儒家的服喪制度幾乎流傳于中國整個封建社會,影響持久深遠。對父母、長輩、故人等,心存敬意和感恩,加以緬懷,慎終追遠,繼往開來,這些古禮還是有意義的。三年之喪的倫理規范,并非出于外在壓力,而是自然親情的適當表達。外在的禮儀只是表現方式,若沒有真情實感,一切只會淪為形式。子女對待父母,在禮節方面做得十分周全,如果內心缺乏敬意與愛心,也算不上真正孝敬父母。或者為了博得美名而弄虛作假,與孝精神完全背離,實質就是不孝。
今天的社會,人口流動大,工作地及居住地大都遠離原生家庭,使 “三年之喪”的古老禮儀面臨創新問題。恪守古代禮儀,不讓人們流動和外出工作,專門在家守孝三年,也很不現實。譬如當今沒有專門的守喪假,國家規定直系親屬的喪假為1-3天。守喪也沒有對應的、嚴格的、具體的、細致的規定,《殯葬管理條例》(2012年修正本)第一條只是強調了喪葬管理的原則要求:“為了加強殯葬管理,推進殯葬改革,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制定本條例”,第十四條強調:“辦理喪事活動,不得妨害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權益”。
喪葬禮儀簡化改革,守孝的時間機動靈活,在今天成為常態。傳統孝德精神的傳承,應隨時代的變化而改變。我們認為對逝者保持尊敬、表達哀思最為重要,完全可以根據家庭成員的情況(時間、財力等)安排隆重而簡樸的喪禮,三年之內心系逝者,孝親思想和行為溢于言表,就是當今被認可的做法。如在湖北、河南農村有的地方紀念逝者仍然有頭七、三七、五七、三周年等祭祀習俗,就是簡化了的三年之喪的做法,為老百姓所接受。又如抗日戰爭期間,著名哲學家馮友蘭的母親去世,而馮友蘭、馮景蘭、馮沅君兄妹三人都在昆明。“一個月之后,她的兩個兒子才千里迢迢趕回奔喪”[3]。馮友蘭、馮景蘭兩兄弟回唐河老家奔喪,在寒冷的冬天守靈、送葬,披麻戴孝,守了二十余天后,在馮家的墓地上,啟父親舊塋,入母親新棺,“葬父母于同穴,其永寧于九原”(馮友蘭《祭母文》), 其《祭母文》彰顯了子對母親功德的感念,盡了孝心。馮友蘭同時發布訃聞,完全按照中國傳統的喪服制度和訃聞格式,由親到疏按五服喪制而列,涵蓋了馮氏家族的至親關系,特別是五服喪制中的禮制在此訃聞中得以全面體現,孤哀子女媳是“泣血稽顙”,齊衰期服孫、孫女是“泣稽首”,功服夫弟即馮友蘭的叔叔馮漢異是“拭淚拜”,期服侄、侄女是“泣稽首”,而最遠的小功服、緦服是“拭淚頓首”,表達了一個文人對儒家傳統喪禮的傳承。[4]盡管馮先生沒有居家守孝三年,但其孝行不可否認。
當今的喪葬方式也發生了變化,大多改變了厚葬、棺葬的傳統,守喪時間壓縮,守靈、守喪的地點、方式和追悼方法不一,有的在醫院或殯儀館進行,追悼會、追思會、獻花圈、豎墓碑在今天常見。“喪事從簡,提倡符合現代精神的葬儀。比如說,可以提倡樹葬,植樹一株,把死者的骨灰埋入樹下,既省了土地又美化了環境。參加葬禮的人每人帶鮮花一枝, 在向死者致辭默哀后,留下鮮花靜靜離去,不更能表達悼念之情嗎?”[5]
三、清明節上墳祭祀問題
清明節起源于春秋時期,晉文公為了紀念介子推,將寒食節的第二天定為清明節。傳統孝道主張清明節上墳祭掃祖墓,清明祭祖成了中華民族傳統習俗之一, 歷來被炎黃子孫高度重視,表達生者對已逝親人和先輩的悼念。
在父母身邊盡孝,到親人墓地祭祀,是傳統的行孝要求,若時間和條件允許,這樣做是應該的。《論語·里仁》指出:“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有人斷章取義,忽略了“游必有方”。若父母現在還抱著子女一定要待在自己身邊的思想,估計連孔子都不會同意。父母年邁時,子女因工作需要長期在外,但應告訴父母自己的去向、歸期,提前安排好父母的生活,使其安度晚年,也不失為盡孝。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曰“子有四方之志”,修、齊、治、平的實現,要求務必走出家門,走向社會。當今社會的流動性更強,普通老百姓經常外出打工,現代科技發達,人們通過手機、微信等與家中父老聯系,做到工作家庭兩不誤,與傳統孝道不矛盾。親情永遠,千金難換,行孝方式不拘一格。“作為子女常回家看看, 常打電話問問, 可以消除老年人心情抑郁、惆悵孤寞、心理失落、自悲自憐等情緒, 使‘空巢’不常空, 這也是子女應盡的精神贍養義務。”[6]遠方的游子永遠是父母的牽掛,“街頭巷尾看見滿頭白發的父親或母親拄著拐杖眺望遠方, 無疑他們在等待自己的親人歸來。當你看到這一幕時, 你就會感覺到‘父母在, 不遠游, 游必有方’的意義了”[7]。
清明節的祭祀方式,也應隨時代的發展而變化。其實,古代漢族的清明祭祀就有兩種基本方式,按祭祀場所的不同可分為墓祭、祠堂祭(家廟祭)。墓祭最為普遍,祠堂祭是宗族的共同祭祖方式。有的農村家庭在中堂條桌上的祖先神龕或者牌位幾案上,擺上香爐、蠟扦、花筒、供品,燒上三支香,叩拜或者鞠躬三次,默念祈福和感念語。當代,公共墓地的森林綠化率越來越高,為了保護環境,防止火災,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焚燒紙錢等,清明節去墓地獻花就成為時尚。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人,如果清明節不能回鄉掃墓祭祖,可以選擇在網絡上祭祀,在自己的QQ、微信、抖音上紀念故人;也可以寫親人的回憶錄,在親朋好友中分享,表示對先人功德的懷念,激勵后人奮發進取,為家為國爭光。
簡言之,今天的清明祭祀需要實質上的心存敬意、形式上的靈活多樣,無論是在家鄉、他鄉,都可以做得到、做得好。
四、養老方式變革問題
當今社會生活節奏加快,職業和工作地點流動大(有的是漂洋過海的“地球人”),孝文化對處理老齡社會下的家庭代際和諧、親子關系, 解決養老問題,形成尊老風尚,構建和諧社會都具有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如何行孝才能真正發揚光大傳統孝道并且與當今社會契合,成為老齡化社會的突出問題之一。行孝的方式也應隨時代更新。《詩經·爾雅·釋訓》對孝的解釋為“善事父母為孝”;《說文》的解釋為“善事父母者, 從老省、從子, 子承老也”。許慎認為“孝”字是由“老”字省去右下腳的形體, 和“子”字組合而成的一個會意字。父慈子孝,上下互動,才能使孝道文化源遠流長,永續發展。
孝道講究物質贍養與精神安慰相結合。精神贍養古已有之, 一直蘊含在孝道中, 并且是孝的重要方面。古代社會為保證孝的推行, 不僅在思想理論上進行大力宣傳, 而且采取了一套相應措施加以保障。當今社會的保障與福利越來越完善,有養老保險金的老人吃、喝、住、用不成為問題,精神上的安慰,成為老人的第一需要。但精神贍養難以保證,特別是獨生子女家庭,一對夫婦在養孩子的同時還要贍養四位老人, 有的甚至更多。在履行贍養義務時, 他們往往力不從心,無暇顧及老人的情感需求。還有人把贍養父母僅僅看作是一種法律責任、物質需要的滿足,而不是道德義務、精神需要的滿足,與父母溝通交流少,對父母的嘮叨缺少理解,在細微方面關注不夠。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社區、老人服務機構可以補位,發揮其社會服務功能。《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2018年修訂版)第三十七條主張:“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和有關部門應當采取措施,發展城鄉社區養老服務,鼓勵、扶持專業服務機構及其他組織和個人,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緊急救援、醫療護理、精神慰藉、心理咨詢等多種形式的服務。” 當代敬老、養老出現很多新問題,尋找新的孝道方式,成為當務之急。
養老行孝需要尋找適合的方式,當今大致有如下三種基本方式。
1.家庭養老。這是傳統的養老方式。在自己家里,自由自在,多代同堂,享天倫之樂,方便和親友來往,是農耕時代鄉土社會悠久的習俗。“家有一老,如有一寶”,老年人能夠幫助年輕人料理家務、照顧孩子,還能夠傳授生活、工作方面的經驗與智慧。如果父母與子女分居兩地,不能經常見面,也可以利用電話、微信視頻來彌補。特別是在中國老百姓最重視的傳統節日如春節、元宵節、清明節、中秋節等,要回家看看,盡盡孝道。民間對老人的生日特別是“六十歲”“七十歲”“八十歲”等生日非常重視,一般都要舉行慶祝儀式,子女此時除到場慶賀外,送禮物、送“紅包”已經在百姓間流行。無論社會養老機構如何普遍,服務如何周到,家庭養老的優勢是不能忽視的,子女近距離照顧老人,人間親情、溫情是不能替代的。建議有關部門出臺老人戶口隨子女遷移或者其他便民政策和措施(如異地醫療報銷制度就大得人心)。
2.養老院專業養老。我國已經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 隨著老人的增多, 養老機構大量出現已成為一種符合社會發展潮流、不可或缺的養老方式。養老院對入住老人直接負責,提供周到細致全方位的養老服務, 讓入住老人滿意, 是養老院的職責所在, 也是評價一家養老院是否稱職的最根本標準。養老院有專業陪護人員,生活、醫療等設施一應俱全,是老年人尤其是高齡老人的理想去處。例如,武漢某高校的教授夫妻,2021年已經95歲,其子女都要照看自己的孫子,無暇照顧二老,教授夫妻現在就安居在武漢某社會福利院。教授是運籌學專家,對此也有籌劃,尋覓過最優化的方案,最后認為這是不二的選擇。我們認為這未嘗不是最佳方案。
3.社區養老。《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第三十八條強調:“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和有關部門、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應當將養老服務設施納入城鄉社區配套設施建設規劃,建立適應老年人需要的生活服務、文化體育活動、日間照料、疾病護理與康復等服務設施和網點,就近為老年人提供服務。發揚鄰里互助的傳統,提倡鄰里間關心、幫助有困難的老年人。鼓勵慈善組織、志愿者為老年人服務。倡導老年人互助服務。”在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無法滿足的情況下,社區提供養老服務也是一種不錯的方式。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社區的養老服務已逐步出現和發展起來。現在不少老齡化程度高的社區,在街道辦事處的統籌下,都成立了社區集中養老機構。社區是老人熟悉的環境,知根知底,能夠為老人提供天然的“近水樓臺”優勢,且費用較低,擁有周到的、專業的服務,又離家近,還可以經常回家,自由往來,免除了繁重家務,非常受老人歡迎。如上海、武漢等地有的社區已經實施,效果好,得到廣泛肯定。
五、小 結
孝道經典是豐富的思想文化遺產。對于當代社會而言, 如何批判地繼承這些遺產,大力弘揚中華民族孝文化美德,是一項重大而嚴肅的歷史使命、時代課題。孝文化的培育和發展有助于健全社會主義公民的人格, 有助于建立和諧家庭, 有助于構建和諧社會,有助于提升民族凝聚力、幸福度、獲得感。因此在現階段, 充分發揚優秀孝道文化、推進優秀孝道文化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但孝文化建設不能僅僅停留在觀念層面, 應當引導和規范人們的孝德行為。季羨林先生強調:“我們當然不能再提倡愚孝;但是,小時候父母撫養子女,沒有這種撫養,兒女是活不下來的。父母年老了,子女來贍養,就不說是報恩吧,也是合乎人情的。”[8]
孝的本質在于仁愛之心。愛親應該是家庭美德,孝之愛表現在多個方面, 如養親、尊親、思親、義親等。孝的價值就在于愛老人,為家爭光,展示家國情懷。我們應該充分利用傳統節日與人生儀禮等特定時節,大力培養人們的孝德善念。在傳承孝文化時,應該發揚光大其積極因素,剔除其糟粕,并且尋找適合當下的內涵、條件,創造性地加以靈活運用。[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