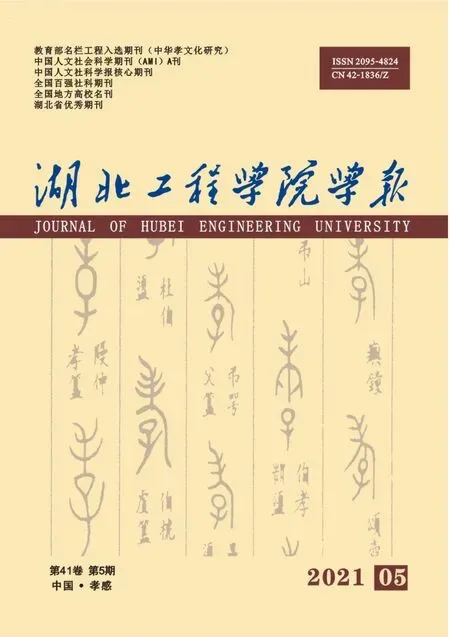柳詒徵人倫觀探析
肖朝暉
(武漢市社會科學院 文化與歷史研究所,湖北 武漢 430019)
一、近代中國的人倫批判和道德革命
晚清以來,受自由、平等、民權等西方近世文明價值觀念的影響,中國傳統(tǒng)倫常道德開始遭受沖擊與批判。譚嗣同在《仁學》中疾呼要“沖決倫常之網(wǎng)羅”,他對傳統(tǒng)“綱常名教”提出了尖銳批評:“仁之亂,則于其名……名者由人創(chuàng)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則數(shù)千年來,三綱五倫之慘禍烈毒,由是酷焉。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軛民,父以名壓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挾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2]在譚嗣同筆下,三綱五倫是尊者、貴者等在上者壓制、束縛卑者、賤者等在下者之具,毫無平等和自主權可言,唯朋友一倫充滿平等精神,他主張以朋友之道貫通其余四倫,從而廢除其余四倫。譚嗣同對中國傳統(tǒng)倫常秩序的抨擊開近代綱常批判、人倫批判之先河,余英時就稱譚嗣同的綱常批判是中國近代史上一次破天荒之舉,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他同時提醒“《仁學》動搖了人們對君臣一綱的信念,但似乎還沒有沖擊到整個綱常的系統(tǒng)”[3]。陳萬雄指出,要到20世紀初,尤其是1903年春“拒俄運動”和“蘇報案”的相繼發(fā)生,“一種具革命性的反傳統(tǒng)文化的革新思想才真正出現(xiàn)”。[4]118彼時,種種宣揚“三綱革命”“打破禮教”的思想言論大量出現(xiàn),蔚為風潮。(2)參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所收相關文章,對這一時期反傳統(tǒng)思潮的研究見周積明《晚清反傳統(tǒng)思潮論綱》,《學術月刊》2002年第8期。及至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對傳統(tǒng)倫理道德的批判達至頂峰。新文化運動倡導者批評傳統(tǒng)倫理道德有兩大關鍵性理由:其一,道德是進化的,并非萬世不易,它隨著社會生活、經(jīng)濟狀況、生產(chǎn)方式的變遷而變遷。傳統(tǒng)倫理道德為封建宗法時代的舊道德,不適于現(xiàn)代生活。“道德之為物,應隨社會為變遷,隨時代為新舊,乃進化的而非一成不變的,此古代道德所以不適于今之世也。”[5]其二,中國傳統(tǒng)三綱五倫的道德規(guī)范強調片面服從,旨在維護尊卑貴賤的階級制度,是不平等的道德,使為臣、為子、為妻者喪失獨立自主人格,這與以個人主義為本位、尊重個人自由、注重人格平等的西洋近世文明根本不相容,欲輸入西洋文明,鞏固和維持共和政體必須吐棄重在尊卑階級的傳統(tǒng)倫理觀念。
梁啟超是近代中國“道德革命”首倡者,戊戌變法失敗后,流亡日本的梁啟超在救亡圖存的急切心理下,于1902年—1906年間在《新民叢報》連載“新民”諸論,掀起“道德革命”。在《論公德》中,梁啟超將道德劃分為“人人獨善其身”的私德和“人人相善其群”的公德,他指出雖然中國的道德發(fā)達極早,但“偏于私德,而公德闕如”,《尚書》《論語》《孟子》諸書所教導的十之九都是私德。梁啟超又以泰西新倫理與中國舊倫理相比較,中國舊倫理分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倫,泰西新倫理分為家族倫理、社會倫理和國家倫理。按照泰西新倫理的分類,五倫中父子、兄弟、夫婦為家庭倫理,君臣為國家倫理,朋友為社會倫理,表面上看似乎與泰西新倫理無甚差別,但梁啟超在自注中指出,中國傳統(tǒng)倫理重在“一私人對于一私人之事”,朋友、君臣不足以盡社會、國家之大體。在他看來,朋友是兩私人之相知,君臣亦全屬兩個私人間的感恩效力,無當于泰西新倫理所重的“一私人對于一團體之事也”。故而,他總結道:“若中國之五倫,則惟于家族倫理稍為完整,至社會、國家倫理,不備滋多。”[6]540梁啟超關于私德、公德的劃分以及對中國傳統(tǒng)倫理偏于私德的認定影響甚為深遠。對公德的提倡與追求成為時人道德革新的重要目標,偏重于家族倫理亦成為時人指責中國傳統(tǒng)倫理道德的重要方面。胡適在《四十自述》中曾坦言:“《新民說》最大的貢獻在于指出中國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許多美德……他指出我們所最缺乏而最須采補的是公德”,讓年輕的胡適認為在中國之外還有更為高等的民族與文化。[7]劉師培在所著《倫理學教科書》中同樣闡發(fā)了中國傳統(tǒng)道德偏于私德即家族倫理的看法,他說:“中國古籍,于家族倫理,失之于繁;于社會倫理,失之于簡”,并指出家族倫理存在兩大弊端,其一即“所行倫理僅以家族為范圍。中國人民自古以來,僅有私德,無公德。以己身為家族之身,一若孝弟而外,別無道德;舍家族而外,別無義務”。[8]
從晚清至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近代“道德革命”或“倫理革命”包含三方面內容:第一,道德隨時代而變遷,不存在固定不變的道德傳統(tǒng);第二,中國傳統(tǒng)倫理道德偏重于私德,即家族倫理,致使國人缺乏國家觀念,導致在近代中西競爭中不斷失敗;第三,五倫以及由之發(fā)展而來的三綱要求卑者、賤者單方面絕對服從,綱常倫理成為束縛人性、壓制自由之具。伴隨綱常批判而來的是對忠、孝等中國傳統(tǒng)道德核心德目的抨擊與否定。那么,傳統(tǒng)倫理道德是否要隨時代全盤變遷;中國傳統(tǒng)道德是否全然屬于家族倫理,而無社會倫理、國家倫理;三綱五倫是否為鉗制人生之具,使個體喪失獨立自主之權。凡此種種,皆是柳詒徵人倫觀所要面對的問題。正是在新文化運動批判傳統(tǒng)人倫道德觀念,“非孝”“家庭革命”等種種沖擊傳統(tǒng)倫常秩序的言論和舉動高漲的時代背景下,柳詒徵出而為五倫辯護,試圖在近代政治、思想、社會變革的新局下重新闡釋五倫,揭示人倫理念在現(xiàn)代社會中應有的價值。
二、五倫的重新詮釋
1.五倫新詮。1924年,柳詒徵在《學衡》刊發(fā)《明倫》一文對君臣、父子、夫婦三倫予以重新詮釋,強調中國傳統(tǒng)人倫道德的現(xiàn)代價值。(3)《明倫》一文僅對君臣、父子、夫婦三倫作了重新詮釋,此三倫在五倫中最為重要和關鍵,在古代被稱為大倫,在近代受謗最多,故《明倫》著重于此三倫。在同時期“什么是中國的文化”的演講中,柳詒徵提及兄弟、朋友之倫,唯此二倫在近代爭議較少,柳詒徵在演講中也未作特別的詮釋,故此處以君臣、父子、夫婦三倫為重點。
伴隨著辛亥革命,中國由帝制走向共和,君主政體被推翻,君臣一倫已喪失其制度基礎,似乎已無任何存在與提倡的必要,“君臣之義,不合共和之制,既非時宜,則當廢矣”[9]。柳詒徵指出,以為無皇帝便無君臣是不明君臣之義。他認為君臣之義“廣矣”,并不局限于天子與諸侯、皇帝與宰相。君臣實際上是“首領與從屬之謂”,無論何種社會組織,都有君臣的存在,如“學校有校長,公司有經(jīng)理,商店有管事,船舶有船主,寺廟有住持,皆君也。凡其相助為理,聘任為佐,共同而治者,皆臣也”[10]318。也就是說,任何社會組織皆存在首領與從屬,“君臣其名,而首領與從屬其實。君臣之名可廢,首領與從屬之實不可廢”[10]318。不存在“無君”的社會組織,即使是土匪也有頭目,若要完全達至“無君”的狀態(tài),則必然要廢除社會組織,“茍欲無君,必須孑身孤立,盡廢社會組織,我不用人,亦不為人所用,然后可以無君”[10]318。這自然是不切實際的。柳詒徵為君臣一倫的辯護和重新詮釋不是為復辟帝制張目,他意在提醒時人不可也不必拘泥于君臣之名,要以更廣闊的視野看待君臣關系和君臣之倫,廣義的“君臣”,即“首領與從屬”是社會組織存在的必需,人類一日不脫離社會組織而孤身存在,則社會必然存在君臣或首領與從屬關系。
父子之倫亦為當時人詬病,種種非孝言論盛極一時,批評孝道是專制政治之根據(jù)有之,揭示孝是一種不平等的道德有之,宣揚“父母于子女無恩”亦有之,在五四前后形成一股非孝浪潮。儒家看重人倫尤其是父子之倫,因其關乎人禽之辨,《儀禮·喪服傳》有言:“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柳詒徵據(jù)此指出,父子之倫是由禽獸、野蠻人進至文明后而有的,它是人類與禽獸之區(qū)別所在。西方社會同樣存在父子關系,但惟有父單方面盡其養(yǎng)子、教子之義務,子卻不必養(yǎng)其父(4)子女不養(yǎng)父母是在域外生活和游歷的中國知識人士極易感知到的中西差異,時在康乃爾大學求學的胡適,于1912年的一次有關中國子女與父母關系的演說中就對“美國子女不養(yǎng)父母”的現(xiàn)象有所訾議(見胡適的《胡適留學日記》,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年出版,第62頁)。,缺少了中國父子關系中的互助精神,于父子一倫有缺。在柳詒徵看來,如果對于自己有生、養(yǎng)、教之恩的父不相扶助,轉而高談盡心竭力幫助其他毫不相關之人,“是無本也,是無情也”。[10]318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稱孝為儒家所創(chuàng)的宗教,聲稱儒家注重的孝道只教人做一個兒子,而不教人做一個人。柳詒徵對此批評道:“不知教人為子之道,正是教人為人。”[10]318個人在社會關系中有著多重角色,一面為子,一面可以為父,一面又可以為夫為婦,不能說做兒子便不能為人,如同不能說為夫為婦便不能為人。可以說儒家的做人之道即蘊含在如何為子、為父、為夫、為婦之中。柳詒徵認為西方物質文明的成就固然高過中國,但論及為人之道,西方尚存在禽獸及野蠻人的余習,一大表征就是父子之倫有缺。人倫在此由人禽之辨轉化為中西之別。
傳統(tǒng)中國,男女婚姻不以兩性相悅為基礎,婚姻的目的也是為了“合兩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后世”。自清末以來,女子解放、自由戀愛、愛情至上等觀念日益盛行,對傳統(tǒng)男女及夫婦關系造成沖擊。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有關婦女解放、自由戀愛、婦女貞潔等問題的討論更是熱烈,夫婦之倫隨之處于變化動搖之中。柳詒徵用《易經(jīng)》“咸”“恒”兩卦說明夫婦之義,“咸”,感也,代表男女相感,相當于時人所謂的愛情;“恒”,久也,代表夫婦恒久,即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柳詒徵指出,時人惟知情感之用,對恒久之義有所未喻。專恃感情,則易變而難久,必繼之以恒,恒意味著“一夫一婦,同甘共苦,白頭偕老”。他認為那種只知情欲,奉愛情至高無上的是“但計好惡而不計利害”,這不利于發(fā)達人群和維持社會,古圣昔哲正是鑒于男女相悅但計好惡而不計利害,乃“提倡夫婦之義,而以與子偕老為正宗”。[10]319在柳詒徵看來,中國的夫婦之道最能體現(xiàn)互助之義,由于人倫禮教的關系,男女相感并繼之以恒,即感情為追求恒久的理性所節(jié)制,不至于終身擾攘于婚姻問題,可以專其心力處理家庭、服務社會。反觀西方社會,柳詒徵曾在報上閱知一美國女子一生結婚至數(shù)十次,這讓他深感“夫此一人終身擾擾,惟婚姻問題是謀,安能寧心一意,為家庭社會國家有所盡力”[10]319。柳詒徵高度贊揚中國夫婦之倫體現(xiàn)的互助精神,“婦之助夫,天職也,夫之助婦,亦天職也……天職所在,不顧一身,雖苦不恤,雖勞不怨,于是此等仁厚之精神,充滿于社會,流傳至數(shù)千年,而國家亦日益擴大而悠久,此皆古昔圣賢立教垂訓所賜,非歐美所可及也”[10]320。
2.五倫與互助。從柳詒徵對五倫的重新詮釋可以看出,他特別強調五倫所體現(xiàn)的互助精神。這與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互助論的盛行有關。一戰(zhàn)創(chuàng)深痛巨,促使西方反思自身文明,“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場規(guī)模空前的大廝殺,這場大劫難引起世界輿論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責難,于是互助論在西方、在世界廣為流傳”[11]。早在清末,中國無政府主義者就開始譯介《互助論》有關內容,一戰(zhàn)進一步推動了互助論在中國的流布,一時間“互助”之說競相流傳,“其說亦漸漸傳至中國,而國人亦棄其物競天擇之口頭禪,而談互助矣”[12]。互助論的核心要旨是動物乃至人類的生存與發(fā)展,都離不開種類間的互助。由此,柳詒徵認識到“中國幾千年來的倫理,就是講的互助”[13]201。在他看來,《大學》所言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父止于慈,為人子止于孝,都是互助,五倫皆“提倡人之互助,促進人之互助,維持人之互助”[10]317。如其重新詮釋下的廣義君臣關系,“無論是皇帝,是校長,或是任何團體的領袖,都應不應該存一個仁愛之心呢?幫助他人做事的人,無論是人臣,是商店的伙計,或是工廠的工人,不都應該竭心盡力做事嗎”[13]202。又如父母教養(yǎng)子女,子女在父母疾病和衰老時奉養(yǎng)扶助;又或如朋友間“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的患難相顧、利害相共,這些都是五倫互助精神的體現(xiàn)。近代批判三綱五倫的一大理由即是傳統(tǒng)倫理道德片面地要求臣、子、婦絕對服從于君、父、夫,充滿支配性與壓制性。柳詒徵強調五倫的互助性,顯然暗含了對此種看法的批評。
3.五倫與二人主義。1917年,陳獨秀在一次有關道德概念和道德學說之派別的演講中稱:“現(xiàn)今道德學說在歐西,最要者有二派。其一為個人主義之自利派,其二為社會主義之利他派。此二派互為雄長于道德學說界中。自于吾國舊日三綱五倫之道德,既非利己,又非利人。既非個人,又非社會,乃封建時代以家族主義為根據(jù)之奴隸道德也。此種道德之在今日,已為討論之價值。”[14]柳詒徵則指出“這種個人主義,多數(shù)人的博愛主義”都免不了有些偏執(zhí),個人主義“求一己的快樂,不顧到大眾”,博愛主義“不問同國、同種、同鄉(xiāng)與否,都是一律平等,大有民胞物與之概”。[15]288于是柳詒徵將充滿互助精神的五倫釋之為“二人主義”。在柳詒徵看來,安身立命之法以儒家所倡人倫為最善。人生在世,無非是要妥善處理人與人之各種關系,“一身而外,無遠而非人也”,如何得其條理,握其樞要,始終是儒家所著意講求的。孔子之教,個人欲應付處理多人,必須從二人做起。人與人相對之類別,盡括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倫之中。父子固然不只二人,然就一父對一子而言,則是二人,其余君臣、夫婦等皆是如此。二人主義是達到“仁”之境地的必經(jīng)階級,“故凡一人對于任何一人,能以恕道相處相安,由此即可對大多數(shù)之人,亦相處相安”[16]20。如果不經(jīng)二人主義,即不從最親最近之人出發(fā),而高談其他大多數(shù)人,必然會帶來種種亂象,“今人動稱四萬萬同胞,又矢口輒講大同主義,然家庭則父子革命,兄弟參商。始焉求偶妬奸,繼也離婚失戀。于是置之社會,則叛黨賣友;對于國家,則媚外喪權。軍旅倒戈,商賈倒帳,紊亂冥棼,不可救藥”[16]21。其根本原因在于“失其倫序而已”。
由相關性分析結果可知,和消費者圖片評估水光感的結果具有顯著相關性的參數(shù)有:專家視覺評估皮膚光澤度、皮膚粗糙度、色斑明顯程度;儀器評估L值、a值、ITA值、R0值、R3值、SESC值、VOLUME值。
個人主義過于追求一己之私利私欲,易生流弊;博愛主義看似理想高遠,實則不分親疏、遢等無根。二人主義既非個人主義,亦非博愛主義,二人主義是要在二人相對待的關系中以對方為重,彼此互助,“能夠犧牲一己之幸福,去幫助他人;遷就自己,以成全他人”[15]288。這種在家庭中養(yǎng)成的犧牲自己、幫助他人的熱忱和習慣,“到了社會團體里,就肯幫助主持的人為公服務了”,“到了為國家服務時,自然也情愿將自己一身致之于君、于國,仿佛身體都不是自己的一樣” 。[15]291柳詒徵并非要抹殺個人主體地位,他特意強調犧牲自己、幫助他人要出于個人之自愿,若父和君責備子和臣去死,那就是殘忍刻毒不可為訓。正是這種由父子天性推及兄弟、朋友、君臣的二人主義,然后才有人愿意竭身事國,成為造就中國廣土眾民、歷史悠久的根本精神。
三、作為中國文化中心和主體的人倫
1.人倫是中國文化的中心。1924年,柳詒徵應邀于江蘇省立第五師范學校演講“什么是中國的文化”。在演講中,柳詒徵提到當時頗為盛行的整理國故運動,他將此運動的研究內容分為小學、金石、目錄、文學以及歷史五種。在國故研究者看來,他們所從事的就是中國歷史文化研究,正如首倡者胡適在《〈國學季刊〉發(fā)刊宣言》中所宣稱的:“國學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國的過去的文化史;國學的方法是要用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文化的歷史。國學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國文化史。”[17]柳詒徵認為這些學問都屬于中國文化,是中國文化的重要內容,但這些并不是中國文化的中心和主體,“吾人精于訓詁,彼未嘗不講聲韻、文字之變遷。吾人工于考據(jù),彼未嘗不講歷史制度之沿革。吾人搜羅金石,彼未嘗不考陶土之牘、羊皮之書。吾人耽玩詞章,彼未嘗不工散行之文、有韻之文”[15]287。也就是說,小學、金石等內容均不足以顯示中國文化的特色。中國文化的中心必須為中國所特有,而世界其他國家所沒有。在此,他主張運用比較的眼光,要講清中國文化的特色,必須先明了歐美文化的情形。眾所周知,歐美文化的一大特色是富于宗教色彩,反觀中國,中國人缺乏宗教觀念,而富于倫理思想,在柳詒徵看來,這才是中國文化的特點,“建立人倫道德,以為立國中心,纚纚數(shù)千年,皆不外此,此吾國獨異于他國也”[15]287。小學、金石、目錄、文學、歷史種種,皆是中國文化中心之人倫道德的附屬物,“訓詁,訓詁此也;考據(jù),考據(jù)此也;金石所載,載此也;詞章所言,言此也。亙古及今,書籍碑版,汗牛充棟,要其大端,不能悖是”[15]287。
眾所周知,新文化運動的一大功績是文學革命,簡單說即以白話取代文言。在柳詒徵看來,新文化運動對中國文化不在于把“之”字改作“的”字,把“乎”字改作“嗎”字的文學革命,而是在試圖推翻相傳千年的倫理,“西人信仰耶穌,崇拜上帝,對于宗教的觀念非常堅強,中國既沒有宗教,如果不拿倫理來維系人心,那末,人群之墮落不是很可怕嗎”。[13]205柳詒徵主張作為維系人心的人倫之道不能被推翻,本無多少宗教觀念的國人,若無倫理相維系,勢必導致人群的墮落。于是,他在演講中呼吁要明白中國文化是以倫理為主體,然后在此基礎上吸收世界各國的學說,“借以取長補短”,那么中國的前途自然會好。他甚至還希望聽講者能將中國注重五倫的倫理精神傳播到世界各國,使外人真正知曉中國文化的中心之所在,“不是小學,不是金石,不是目錄,不是文學,不是歷史,而是五倫”。[13]205
2.對民國墨學研究風氣的批評。清代考證學的興盛促進了諸子學的發(fā)展,因諸子的著作在時代和用語上與經(jīng)籍相近,可用以佐證經(jīng)籍的訓詁、校勘等。及至晚清,西學開始大規(guī)模輸入中國,諸子學說有可與西學相比附的內容,尤其是墨學中的部分內容與聲光化電氣的西方格致之學相類,“清季學者,震于西人制造之學,則盛稱墨子之格術”[18]479。民國時期,墨學研究風氣更盛,此時研究墨學諸人看重的是墨學作為儒家的反對者和墨學與西方哲學的相通。柳詒徵就說:“今人多好講墨學,以墨學為中國第一反對儒家之人。又其說近于耶教,揚之可以迎合世人好奇鶩新之心理,而又易得昌明古學之名。故講國學者莫不右墨而左孔,且痛詆墨子拒墨之非。”[19]201這里牽涉到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一個重大問題,即作為先秦顯學之一的墨學緣何在戰(zhàn)國以后趨于滅絕。在當時趨新人士看來,墨學象征著中國學術思想最為自由的黃金時代,而自漢武帝采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鉗制措施后,中國學術思想歸于儒家一統(tǒng),造成中國此后數(shù)千年學術思想不得自由發(fā)展的黑暗局面,為近代中國的落后埋下深遠的禍根。作為諸子學說之一的墨學自然也在儒學獨尊的大環(huán)境下消沉。
柳詒徵對儒學獨尊導致墨學沉寂的看法表示反對,他指出,戰(zhàn)國以后墨學久絕是由于墨學自身“刻苦太過,不近人情”“互相猜忌,爭為巨子”和“鶩外徇名,易為世奪”[18]574,而最為根本的原因是墨學拂天性、悖人情,即違背了從天性出發(fā)的人倫。柳詒徵引《孝經(jīng)》“父子之道,天性也”指出,儒家立言,處處根據(jù)人之天性,是從人本身出發(fā)再推及他人,主張“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而墨子認識不到出于天性的父子之道,試圖透過這一層,使人皆視人如己,如在《兼愛》篇中主張“視人之室若其室”“視人身若其身”“視人家若其家”“視人國若其國”。他指出,墨子之言看上去至仁至公,實際上違背了人之天性。人對吾之老幼與對他人之老幼存在著天然的區(qū)別,儒家主張推己及人的差等之愛,而墨學主張視人如己的無差別之愛。柳詒徵認可和贊賞孟子對墨學“兼愛是無父,無父是禽獸也”的批評,前已述及柳詒徵認為父子之倫是人類與禽獸野蠻人的區(qū)別,而墨子倡導的兼愛,“愛人之父若己之父而毫無差等,是人盡父也,人盡可父,尚何愛于己之父?父子之倫即不成立。世間惟禽獸不知有父”[19]203。
柳詒徵對墨子兼愛的批評緊扣天性的人倫,這與自孟子以下歷代儒者對墨學的批評并無二致。他的批評看上去似乎是老調重彈,實則是欲通過批評墨學針砭當時學界揚墨抑儒的風氣。他觀察到“自晚清以來,學者好揚墨子之學,沿及今日,遂有倡非孝之論,甚至有謂異時世界止有朋友一倫,若父子、夫婦、兄弟之倫均須廢去者”[19]203。正是對違逆天性、有悖人倫的墨學的盲目推崇導致了當時非孝言論的盛行,甚至有取消除朋友一倫外其余四倫的嚴重后果。這對持人倫為中國文化中心的柳詒徵來說是無法接受和認可的。
四、抉發(fā)忠孝古義
人倫有五,與人倫密切相關的是忠孝節(jié)義等德目,這些德目在古代中國曾是衡量評判個體道德的最高標準。而在近代激烈的道德革命和人倫批判大潮中,作為傳統(tǒng)中國核心德目的忠、孝亦遭抨擊和否定。1924年,孫中山在“三民主義”演說中述及自己的親身見聞:
前幾天我們到鄉(xiāng)下進了一所祠堂……看見右邊有一個“孝”字,左邊一無所有,我想從前一定有個“忠”字。像這些景象,我看見了的不止一次,有許多祠堂和家廟都是一樣的……由此便可見現(xiàn)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為到了民國,便可以不講忠字。以為從前講忠字是對于君的,所謂忠君;現(xiàn)在民國沒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所以便把他拆去。[20]
在一般民眾心目中,以為“忠”便是指忠于君主,既然共和的民國沒有君主,那么“忠”便無所施,故將“忠”字鏟去。鄉(xiāng)間祠堂和家廟雖拆去“忠”字,然尚將“孝”予以保留。至于在都市一班追求自由、平等、進步的新知識人士那里,“孝”亦在鏟除之列。
在《中國文化史·忠孝之興》一章中,柳詒徵通過對夏道的分析展示了自己對忠、孝的看法。夏道尚忠而本于虞,《禮記·表記》云虞帝“有忠利之教”,柳詒徵認為“忠利之教”應以《左傳》“上思利民,忠也”和《孟子》“教人以善謂之忠”來理解,指君主及官吏忠于民。因此,“忠”并非專指臣民忠于君上。此“忠”指居職任事者,竭盡心力求利于他人。有關夏道的記載無多,而墨子盛稱夏道,柳詒徵遂借由《墨子》推知夏道。根據(jù)《墨子》古時圣王節(jié)用利民的記載,堯舜等圣王完美地詮釋和象征了“忠”的真實內涵:“其忠于民以實利為止,不以浮侈為利。外以塞消耗之源,內以節(jié)嗜欲之過。于是薄于為己者,乃相率勇于為人,勤勤懇懇,至死不倦。”[18]133《墨子·節(jié)葬篇下》還記載了堯、舜、禹“道死”的事跡,這令他深感“此犧牲之真精神,亦即尚忠之確證也” 。他于是發(fā)揮為:作為人主,不貪權位、不恤子孫,將一己之生命貢獻于國民而無所惜,至死猶想著教化遠方異種之民,這就是君主及官吏忠于民之“忠”義。他嚴厲批評不知忠之古義,但以臣民效命于元首為忠的“后儒”,“于是盜賊豺虎,但據(jù)高位,即可賊民病國,而無所忌憚;而為其下者,亦相率為欺詐叛亂之行,侈陳忠義而忠義之效泯焉不可一睹”[18]133。這都是學者不明古史,不通“忠”之古義之過。
夏道在尚忠之外,“復尚孝”,章太炎即有《孝經(jīng)本夏法說》。鄭玄注《孝經(jīng)》“先王有至德要道”句時稱“禹,三王最先者”,蓋自夏禹,官天下一變?yōu)榧姨煜拢跷挥蓚髻t變?yōu)閭髯樱侍刂匦⒌馈A簡⒊凇墩摴隆菲袑鹘y(tǒng)五倫觀念歸結為偏重于家庭倫理的私德,孝亦隨之局限于家庭之內,“就此,孝不再像在傳統(tǒng)社會中那樣,支撐起整個傳統(tǒng)道德體系的大廈”[21],而僅僅成為“私德上第一大義”[6]540。于是,在古代世界,貫通家、國乃至天下,充滿公共性的孝由此蜷縮于家庭之內,成為無關國家、社會的私德。(5)有關“孝”在近代的“私德”化和“孝”在古典世界中的公共性分析參見陳壁生的《從家國結構論孝的公共性》,《船山學刊》2021年第2期。柳詒徵則闡揚古義,他引《孝經(jīng)·開宗明義章》和《禮記·祭義》指出“孝之為義,初不限于經(jīng)營家族”[18]135-136。經(jīng)籍中對孝內涵的描述不僅指順從親意,舉凡增進人格、改良世風、研究政治、保衛(wèi)國土,皆涵蓋于孝道之中。他又以禹殫心治水為例說明禹雖干父之蠱,但禹惟孝其父,所以才能盡力于國家、社會之事,“其勞身焦思不避艱險,日與洪水猛獸奮斗,務出斯民與窟穴者,純孝之精誠所致也”[18]136。后世以順從親意為孝實在是一種狹義的理解,在家庭中生發(fā)培養(yǎng)的孝德可推廣及國家、社會,“禮俗相沿,人重倫紀,以家庭之肫篤,而產(chǎn)生巨人長德,效用于社會國家者,不可勝紀”[18]136。
柳詒徵對忠孝之德的闡發(fā)注重抉發(fā)忠、孝的古義,批評、反對后世對忠、孝的偏狹和曲解。忠不專指忠于君主,而實有君主及官吏忠于人民之義;孝也不專指孝順父母,而實可推擴及國家、社會。于是,忠、孝之德依然有著不可磨滅的價值。忠、孝與祖先崇拜共同構成了柳詒徵所稱道的“此夏道之有關吾國歷代之文明者”[18]137。忠、孝被視為中華文明的關鍵性要素,可見柳詒徵對忠孝之德的高度推崇。
五、結 語
“五倫的觀念是幾千年來支配了我們中國人的道德生活的最有力量的傳統(tǒng)觀念之一。它是我們禮教的核心,它是維系中華民族的群體的綱紀。”[22]56而在近代歐風美雨的侵襲下,伴隨著近代中國經(jīng)濟狀況、生產(chǎn)方式、社會制度的變革,傳統(tǒng)倫常觀念和秩序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沖擊。五倫及忠孝等德目成為批判和否定的對象。激進的趨新人士企圖全盤否定中國傳統(tǒng)倫理道德的價值,代之以崇尚個人為本位的西式個人主義。但正如賀麟在《五倫觀念的新檢討》中所表明的,無論對當時流行的新觀念,還是傳統(tǒng)的舊觀念,都有加以批評、反省和重估的必要,唯有從舊的傳統(tǒng)觀念中發(fā)見最新的近代精神,才是真正的推陳出新。無可諱言,傳統(tǒng)倫理觀念在實踐和具體落實過程中,有過僵硬、腐朽的內容,成為某種束縛、壓制性的力量,但不能因此就從根本上否定人倫的價值,“不能因噎廢食,因末流之弊而廢棄本源”[22]57。作為維系中華民族幾千年的道德傳統(tǒng),在中華民族歷史演進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的五倫自有其深刻的人性和歷史文化根據(jù)。柳詒徵在新文化運動全盤否定中國傳統(tǒng)倫理道德價值時,起而重新詮釋五倫,抉發(fā)忠孝古義,體現(xiàn)了在近代激烈道德革命和人倫批判大潮中,文化保守主義者竭力發(fā)掘和闡揚固有道德傳統(tǒng)現(xiàn)代價值的努力。柳詒徵堅信人倫是中國文化的中心和主體,與世界其他國家以宗教、法律或武力組成的國家不同,中華文明以人倫立國,這是鑄造中國廣土眾民的歷史悠久的根本精神。柳詒徵的人倫觀對于認識中華文明的獨特性,發(fā)揚五倫的互助精神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