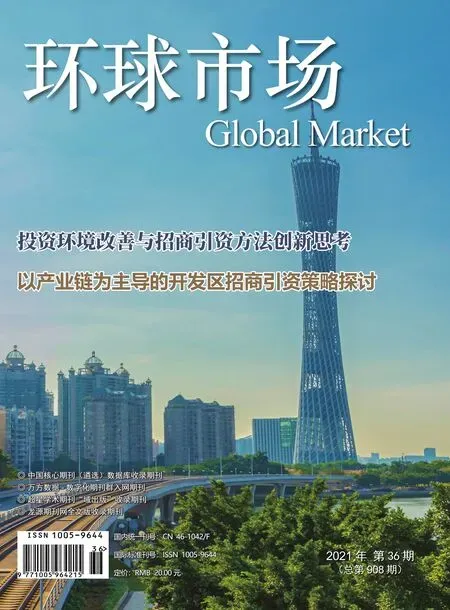B公司管理層過度自信與投資決策
陸欣怡 杭州電子科技大學
一、引言
2015年3月,B公司登陸創業板。作為第一個拆解VIE結構回歸A股的互聯網公司,迅速成為整個A股的明星。從B公司創始人、董事長兼CEO的志向來看,B公司的野心遠不止此。上市不久就開啟瘋狂多元化擴張模式,而財務報告卻顯示經營吃力,凈利潤下滑。僅僅五年,400億的市值僅剩9227萬,慘淡收場。CEO說過:“B公司走到今天這個地步,99.999%還是要怪自己。”B公司衰敗離不開CEO戰略定位模糊、多元化的投資決策失誤。管理者過度自信是造成冒進的擴張決策的重要原因。本文采用盈利預測偏差法衡量B公司管理層過度自信程度,從投資量與投資效益角度剖析企業投資效益,并分析管理者過度自信的內外原因,以此提出抑制管理層過度自信的對策建議,期望為企業改善內部治理,優化投資決策,提升價值提供參考。
二、文獻綜述
(一)管理層過度自信衡量方法
學者對于管理層過度自信的衡量標準較為多樣,目前多集中在以下幾種方式。第一,持股比例的變化。Malmendier和Tate(2005)[1]認為當管理層持有企業的股票期權或股票,且有好的行權時機,不行權的行為是過度自信。郝穎等(2005)[2]與李丹蒙等(2018)[3]根據管理層在當年持股數量的變化來衡量過度自信;第二,盈利預測偏差法。Lin等學者(2005)[4]首次提出管理層高估盈余代表其存在過度自信。姜付秀等(2009)[5]在統計盈余預測信息時也使用該方法;第三,高管薪酬比例。Hayward和Hambrick(1997)[6]以管理層最高的薪酬和第二高的薪酬之間的比值度量過度自信。國內學者姜付秀等(2009)[5]以及竇煒等(2019)[7]使用公司薪酬最高的前三位管理者的薪酬之和以及高管的薪酬總和作比較;第四,管理者個人特征。余明桂等(2013)[8]根據管理層性別、年齡、學歷、教育背景和職位權力構建指標;第五,主流媒體評價。Hayward和Hambrick(1997)[6]搜集美國主流媒體對樣本公司CEO的各類評價,并給予評價賦分以此衡量CEO過度自信;第六,消費者情緒指數。Oliver(2005)[9]首次根據消費者對當下及將來經濟情況的個人感受的統計結果研究探討資本結構與管理層信心的關系;第七,企業景氣指數。余明桂等(2006)[10]將國家統計局統計的企業家對公司及行業未來的發展呈樂觀的態度作為衡量指標;第八,并購頻率。Doukas和Petamezas(2007)[11]以公司在3年內發生過5次并購為界,劃分管理層的過度自信程度。施繼坤等(2014)[12]則將每年并購次數大于等于兩次設定為管理層過度自信界線。
(二)管理層過度自信與投資決策
學者對投資行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投資效率、投資程度、擴張形式投資、并購形式投資方面。Roll(1986)[13]認為過度自信的管理層容易高估被并購企業的價值,增加并構成本,影響公司未來業績。Malmendier和Tate(2003)[14]指出過度自信的管理層高估了他們創造回報的能力,并具有較高的平均收購率,尤其針對多元化并購。郝穎、劉星和林朝南(2005)[2]認為高管普遍存在過度自信,這既造成高投資又不利現金流反應性,決策效率低下。姜付秀、張敏和陸正飛(2009)[5]分析過度自信心理對公司擴張的影響,發現過度擴張使得公司更容易陷入財務困境。從管理者有限理性角度分析,劉柏(2017)[15]發現管理層在國際并購中更容易低估社會、法律等影響,表現過度自信并對并購業績產生明顯的負向作用。張立民等(2017)[16]在探究持續經營審計意見、管理層自信與投資效率關系時,發現管理層過度自信易造成企業過度投資或投資不足,降低投資效率。苑澤明等(2018)[17]佐證了這一結論。
三、B公司管理層過度自信與投資決策
(一)管理層過度自信情況
主流媒體評價與消費者情緒指數具有較強主觀色彩;企業景氣指數不能反映具體公司情況;B公司高管兼CEO的特性不適用高管薪酬比例指標;高管持股比例與高管薪酬比例數據不易獲取。故本文采用上市公司年度盈利預測偏差法以及歸母凈利潤預測偏差法衡量個案公司B公司管理層過度自信。數據均來源于公司年報及業績預告。因2019年年報缺失,2019年數據調整為半年度數據。
2017年營業收入實際值為16.25%,處于預測區間10%-40%的下限,說明B公司雖然沒有較大的預測偏差,但管理者對于營業收入上限的預測抬升較大,表明到2017年管理層仍看好公司前景;2015-2017年公司歸屬于母公司凈利潤的實際值均在預測范圍內,且與營業收入相似,公司對歸母凈利潤的上限預測較高,進一步佐證了管理層對公司走勢向好態度。2018年對歸屬于母公司的凈利潤預測完全偏離實際值,預測虧損小于實際值的1.2倍左右,體現管理層的過度樂觀。2019年一反常態,歸母凈利潤實際值較預測值低,說明管理層可能已經意識到自身的過度自信,結合公司實際經營狀況與走勢,悲觀判斷該年數據。
(二)過度投資進程與投資績效
1.B公司過度投資進程
2015年3月B公司成立M子公司,進軍VR行業;2015年7月與動漫、物流、數碼影音公司共同推出AI電視;同月投資S科技旗下演藝公司,涉足影視行業。2016年3月收購G科技并聯合T游戲公司,步入游戲與海外領域;2016年6月推出體育APP,實現其在內容、體育服務和商業三大板塊的生態布局;2016年10月開始向互聯網金融業進發。2017年起,多元化進程放緩,重心轉移到互聯網電視行業。
2.B公司投資效益
(1)投資量逐步疲軟
公司2016年與2017年投資增速快,2018年期投資量快速放緩,2019年持續下降。其中,2016、2017年固定資產環比投資增長是由子公司TS購買電視機模具以及其他資產所致。2018年B公司采購量減少,同時處置、報廢服務器,以及2019年子公司B公司智能清理固定資產導致固定資產同比大幅下降。無形資產方面,由2016至2017年研發項目達預定可使用狀態的增長到2018年的放緩與2019年的負值。綜上,從前期大量投入到后期采購量下降、處置資產充分說明公司投資量降低。同時,服務器資產屬于主營業務相關資產,大量處置、報廢是由于前期過度投資導致經營重心偏移,主業收入降低,使得資產報廢淘汰。
(2)投資績效加速下滑
2015年投資效益系數為負且數值較大,是由于處置固定資產導致資產增加為負,且當年營業收入較上年增長68.85%,其中品牌廣告收入同比增長70%,VIP用戶增值業務收入同比增長1371%。2016年投資效益系數為近幾年最高值,表明當年投資帶來的收入效果最好且效益最佳。隨后投資效益系數由峰值逐步下滑,2018年斷崖式下降,總資產周轉率變動情況也如此。此外,2016年起總資產凈利率與銷售利潤率指標開始為負并加速降低,銷售凈利潤率變動幅度尤為顯著。且需注意,由于本文選用2019年半年度數據,若以整年計算可能降幅更大。進一步來看,資產負債率逐年上升,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凈額在2016年達到峰值。其后由于購建資產減少,處置報廢收益增加,使得現金凈流量逐漸減弱。再次印證前文投資量下降的結論。
綜上,B公司2016年投資量最大,但其投資的投入與產出水平相比其他年份較為匹配。該年投資效率較高表明公司涉足體育與智能硬件領域有所收獲。而2018年起投資放緩,投資績效表現不良,說明長期來看以開拓非主營領域的投資質量下降,投資效益呈現疲軟狀態。且2018年以來的投資指標變動不排除是管理層認識到決策有誤,抑制過度自信的結果。
四、管理層過度自信原因分析
(一)內部結構混亂,管理者獨攬大權
B公司管理者職位由創始人、董事長兼任。內部管理結構與治理結構并沒有完全分離,不存在管理者與股東的代理沖突。創始人兼任CEO有利于董事會決策更好地貫徹執行。這恰恰是CEO意圖構建“集團生態圈”,大肆擴張,不斷變換戰略定位卻無人制止的直接原因。然而,CEO獨攬大權,削弱董事會其他成員與監事會的能力是造成其過度自信的環境基礎。
(二)股權結構松散,治理層過度信任
股東希望實現財富最大化,管理層則可能謀求私利而不顧股東利益,因此產生代理沖突。B公司董事長兼任CEO緩解了代理問題。也正是由于管理者不僅是董事長還是創始人,股東相信CEO能夠最大程度地為公司長遠發展、提升價值考慮。加之股權結構松散,故治理層對其牽制作用微弱,造成董事會放權給CEO,監事會放松對其決策行為監管的局面。
(三)管理者認知偏差
管理者認知偏差主要受管理者自身性格與市場反響影響。CEO曾說,“未來B公司將會成為100億美元公司中的一員”,這足見其自信與野心。在市場追捧、市值抬升、行業觀仰的環境下,管理者的不理智決策越發明顯。他自以為公司此前功績均來自其功勞,并篤定“集團生態圈”能為他創下新佳績,因此在缺乏風險考量、存在認知偏差的道路中越行越遠。
五、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B公司管理層確實存在過度自信現象對公司營業收入與歸母凈利潤預測較為樂觀。該現象具體體現為其盲目多元化擴張,構建“集團生態圈”的投資行為。而在其過度自信下主導的投資行為除去2016年初顯成效,此后年份投資效益并未優化,投資績效反而大幅下降。這與管理者戰略定位不清、投資決策失敗有直接聯系。2018至2019年公司投資的投入量顯著下降,這可能是由于管理者在績效下滑后被迫意識到其先前決策的果斷與盲目,故減少投資并宣稱回歸主業。此外,公司內部結構混亂、股權結構松散、治理層牽制薄弱、管理層認知偏差都致使B公司管理者呈現過度自信。
(二)研究建議
其一,完善公司內部治理結構,加強權力制衡。不管是兩權分離經營的公司還是如同B公司一人多職的公司,都需要治理層的認真投入。明確自身崗位職責,有效監督并指正管理者行為;其二,加強內部風險管理。識別公司的經營風險和潛在危機,積極與管理層溝通,評估風險點,健全風險預警機制與應對措施;其三,管理層糾正決策的認知偏差。借鑒B公司從“神壇”跌落事件,管理層需警惕自身過度自信,不過分樂觀,真實地結合企業發展現狀及市場環境,明確企業定位,制定科學有效的戰略 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