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fù)P棄:美國(guó)新批評(píng)的作品本體論建構(gòu)
張文初
新批評(píng)(New Criticism)作為20世紀(jì)著名的批評(píng)流派,通常是英美并說(shuō),稱為“英美新批評(píng)”。本文只討論美國(guó)新批評(píng)。英國(guó)新批評(píng)學(xué)者瑞恰茲(I. A. Richards)、燕卜蓀(William Empson)等雖然是一般性地言說(shuō)新批評(píng)時(shí)不可忽視的重要人物,但新批評(píng)的主體是在美國(guó)。蘭色姆(John Crowe Ransom)、退特(Allen Tate)、沃倫(Robert Penn Warren)、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維姆薩特(W. K. Wimsatt)、比爾茲利(Monroe C. Beardsley)、韋納克(René Wellek)等一大批富有建樹(shù)的學(xué)者的同時(shí)涌現(xiàn)構(gòu)成了美國(guó)新批評(píng)群星璀璨的局面。無(wú)論是其影響力的形成,還是其具體思維活動(dòng)的展開(kāi),美國(guó)新批評(píng)都具有區(qū)別于英國(guó)新批評(píng)的重大特征。由此,美國(guó)新批評(píng)可以作為獨(dú)立的文學(xué)批評(píng)流派進(jìn)行研究。美國(guó)新批評(píng)的作品本體論建構(gòu)是導(dǎo)致美國(guó)新批評(píng)在20世紀(jì)中期得以一度雄踞美國(guó)批評(píng)界的一個(gè)基本特征。作品本體論是基于“文學(xué)四要素”之別并否定以此區(qū)別為基礎(chǔ)形成的世界本體論和作者本體論的文學(xué)本體觀。作品本體論建構(gòu)意味著把文學(xué)作品作為文學(xué)和詩(shī)學(xué)的本體加以確認(rèn)。所謂“把作品”作為“本體”,可分兩層面理解。相對(duì)于文學(xué)來(lái)說(shuō),它視“作品”為文學(xué)活動(dòng)的“根本”、為詩(shī)藝的最終實(shí)在。就作品本身來(lái)說(shuō),它確認(rèn)作品的自律性、自立性,把作品作為依靠作品自身而存在的東西;用美國(guó)新批評(píng)學(xué)者蘭色姆的話來(lái)說(shuō),它確認(rèn)“作品自身為自身而存在的自主性”[1]。
學(xué)界咸知,在浪漫主義詩(shī)學(xué)以前,理論家們習(xí)慣于用“詩(shī)”(即“文學(xué)”)來(lái)囊括“詩(shī)人”和“詩(shī)歌作品”;這時(shí)的“詩(shī)”,重心是詩(shī)中所敘寫(xiě)的現(xiàn)實(shí)世界。從其不自覺(jué)的重心所在來(lái)說(shuō),這種詩(shī)學(xué)可稱之為“世界本體論”詩(shī)學(xué)。浪漫主義詩(shī)學(xué)以自覺(jué)揚(yáng)棄世界本體論的姿態(tài),開(kāi)啟對(duì)詩(shī)學(xué)主體性維度的思考。浪漫主義認(rèn)為詩(shī)藝活動(dòng)由詩(shī)人心性決定;或者是詩(shī)人的情感或者是作者的想象或者是創(chuàng)作者的某種特殊才能,導(dǎo)致了詩(shī)藝活動(dòng)的發(fā)生和作品的存在。在詩(shī)藝活動(dòng)中,詩(shī)人心性是第一位的。“詩(shī)所敘寫(xiě)的世界”和“詩(shī)歌作品”都只是內(nèi)在于“詩(shī)人”心性并由詩(shī)人心性所決定的第二性因素。后浪漫主義時(shí)代的詩(shī)學(xué)關(guān)注的重心由“作者”向“作品”轉(zhuǎn)移,由此開(kāi)啟“作品本體論”主導(dǎo)詩(shī)學(xué)的時(shí)代。美國(guó)新批評(píng)作為20世紀(jì)西方“作品本體論”大潮中的一股激流,以獨(dú)具特色的方式凸顯了現(xiàn)代詩(shī)學(xué)的“反世界性”“反作者性”。美國(guó)新批評(píng)學(xué)者雖然不都像蘭色姆一樣直接使用“作品本體”或“作品本體論”之類的術(shù)語(yǔ),但他們都是自覺(jué)地以作品為本體的。既是批評(píng)原則又是具體研究方式的新批評(píng)的著名的“細(xì)讀”(close reading)以作品本體地位的設(shè)定為前提:細(xì)讀即是對(duì)作品細(xì)密且封閉性的研讀。新批評(píng)學(xué)者反復(fù)言說(shuō)“詩(shī)”和“詩(shī)歌”的本體性,幾乎無(wú)一例外的是,他們的“詩(shī)”或“詩(shī)歌”指的都是“詩(shī)歌作品”。退特說(shuō)“詩(shī)的張力”,沃倫說(shuō)“純?cè)娕c非純?cè)姟保剪斂怂拐f(shuō)“詩(shī)的悖論”:這里的“詩(shī)”既不是傳統(tǒng)詩(shī)學(xué)對(duì)詩(shī)的一般本質(zhì)的哲學(xué)規(guī)定,也不是指作為人類活動(dòng)方式的詩(shī)歌創(chuàng)作或欣賞,也不是指詩(shī)人、詩(shī)派、詩(shī)風(fēng)、詩(shī)潮或詩(shī)學(xué)團(tuán)體之類現(xiàn)象,而純粹就是指詩(shī)歌的作品。蘭色姆說(shuō),對(duì)于詩(shī)歌和批評(píng)而言,關(guān)鍵性因素是“詩(shī)歌作品的手法”,“這種手法并不是藝術(shù)品中所能發(fā)現(xiàn)的平凡材料所特有的,也不是其他材料所特有的,而是那種藝術(shù)的”[1]。藝術(shù)品的手法構(gòu)成藝術(shù)的獨(dú)特形式;反過(guò)來(lái),“藝術(shù)的特殊性”也就體現(xiàn)在“藝術(shù)品的手法”上。暫且不說(shuō)“藝術(shù)品的手法”是否完全等于“藝術(shù)品”,但在“藝術(shù)品”包含“藝術(shù)手法”這一點(diǎn)上,它確認(rèn)了“藝術(shù)品”對(duì)于“藝術(shù)”的關(guān)鍵性。布魯克斯明確指出,新批評(píng)學(xué)者作為“形式主義批評(píng)家主要關(guān)注的是作品本身”[2]。布魯克斯的“新批評(píng)10條”①中第2、第3、第4三條都集中在對(duì)作品本體性的言說(shuō)上:“文學(xué)批評(píng)主要關(guān)注的是整體,即文學(xué)作品是否成功地形成了一個(gè)和諧的整體……”,“一件文學(xué)作品內(nèi)部的形式關(guān)系可能包含著邏輯關(guān)系,但一定會(huì)超出邏輯關(guān)系”,“對(duì)于一件成功的作品,形式和內(nèi)容是不可分的”[2]。海德格爾的藝術(shù)哲學(xué)認(rèn)為,藝術(shù)和藝術(shù)家、藝術(shù)作品三者不容混淆:藝術(shù)作品和藝術(shù)家具有相互的決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相看作對(duì)方的“本源”;“藝術(shù)”則高于“藝術(shù)家”和“藝術(shù)作品”,是二者共同的“本源”[3]。新批評(píng)的習(xí)慣則是:既以“詩(shī)人”和“詩(shī)歌作品”的區(qū)別排斥“詩(shī)人”,又用“詩(shī)歌作品”將“詩(shī)”囊括于自身之內(nèi)。對(duì)比海德格爾的觀念,新批評(píng)的做法是:“藝術(shù)”(“詩(shī)”)不僅失去高于“藝術(shù)作品”(“詩(shī)歌作品”)的資格,而且連自身的獨(dú)特性也喪失了;“藝術(shù)家”(“詩(shī)人”)則同樣失去了可與“藝術(shù)作品”并肩而立的地位。總之一句話,在海德格爾眼中,“藝術(shù)”(“詩(shī)”)是第一性的;在美國(guó)新批評(píng)這里,第一性的則是“藝術(shù)作品”(“詩(shī)歌作品”),不是“藝術(shù)”(“詩(shī)”)②。
一
作為否定“世界本體論”和“作者本體論”的觀念,美國(guó)新批評(píng)的“作品本體論”可從建構(gòu)的邏輯層面理解。這一邏輯層面由四重?fù)P棄③構(gòu)成。第一,它排斥功利、道德,確立審美的第一性。第二,它否定科學(xué)的言說(shuō)方式,推崇詩(shī)歌言說(shuō)的獨(dú)特性。第三,它否定作品的生成論研究,堅(jiān)持作品的非生成性。第四,它拒絕機(jī)械論,強(qiáng)調(diào)作品的內(nèi)在生命與有機(jī)性。要說(shuō)明的是,這里的“邏輯”不絕對(duì)排除歷時(shí)性的顯現(xiàn)。而且,在歷時(shí)性顯現(xiàn)的層面,它可既有長(zhǎng)時(shí)段歷史過(guò)程的壓縮,也有即時(shí)性歷史情形的嵌入。隨著過(guò)程的推進(jìn),前后不同層面之間會(huì)有差異。此種差異在美國(guó)新批評(píng)學(xué)者身上常構(gòu)成他們內(nèi)部不同觀點(diǎn)的并立與碰撞,有時(shí)甚至形成較為激烈的理論交鋒。
功利和審美的對(duì)立是自康德以來(lái)的第一美學(xué)觀念。隨著19世紀(jì)象征主義、唯美主義運(yùn)動(dòng)的興起,審美的非功利性更加深入人心。與審美和功利的對(duì)立密切相關(guān),審美-藝術(shù)同道德的分離也在很多美學(xué)家詩(shī)學(xué)家的頭腦中展現(xiàn)出來(lái)。而且也是在象征主義、唯美主義產(chǎn)生以后,審美-藝術(shù)對(duì)功利的排斥和對(duì)道德的排斥常常被放在一起加以討論。英國(guó)形式主義美學(xué)的代表人物克乃夫·貝爾說(shuō):“藝術(shù)是超越道德的”;“藝術(shù)把我們從人們?nèi)粘;顒?dòng)的世界提升到一個(gè)審美的世界中。在審美的瞬間,我們和人們的利害計(jì)較完全隔絕;我們的期待和記憶被阻止了;我們被升華到了生活的潮流之上”[1]。貝爾的言說(shuō)在19世紀(jì)末期和20世紀(jì)初期極具代表性。
美國(guó)新批評(píng)繼承了現(xiàn)代美學(xué)去功利、去道德的觀念。蘭色姆說(shuō):“我認(rèn)為,詩(shī)人與其說(shuō)是在控制道德體驗(yàn),還不如說(shuō)是在進(jìn)行道德松綁,在忘卻”;“一首‘完整的’或者說(shuō)肌質(zhì)豐滿的詩(shī)總是表明,迷障已被穿透;作者已經(jīng)擺脫了俗念纏身時(shí)對(duì)于事物抱有的難以打破的功利心”[4]。布魯克斯說(shuō):“文學(xué)不是宗教的代用品”“文學(xué)的目的不在于成就道德規(guī)范”[2]。退特從反功利、反道德的立場(chǎng)出發(fā),批評(píng)“傳達(dá)謬見(jiàn)”和“社會(huì)詩(shī)”,譴責(zé)那種“把道德的、政治的和社會(huì)的健康狀況要盡的責(zé)任,全部都推到詩(shī)人身上”的觀念[5];退特認(rèn)為這種觀念就是雪萊早在19世紀(jì)初就批評(píng)過(guò)的功利意識(shí):“我們的功利計(jì)較超過(guò)了我們的領(lǐng)悟能力,而我們吃下去的東西則超過(guò)了我們能消化的限度”[5]。為什么要去道德、去功利?因?yàn)樗鼈兣c審美對(duì)立:“人們處于現(xiàn)實(shí)而非審美階段時(shí),才會(huì)關(guān)注道德”;審美位于道德和功利之上,“擺脫了道德的糾結(jié),才有審美;審美不涉善惡,無(wú)視道德熱情”[4]。
對(duì)比傳統(tǒng)和同時(shí)代歐洲學(xué)者的觀念,美國(guó)新批評(píng)去功利、去道德的審美觀注重從文學(xué)作品內(nèi)外特性的區(qū)別上定義審美與功利-道德的差異。在美國(guó)新批評(píng)學(xué)者看來(lái),文學(xué)作品包含兩個(gè)方面:作品的內(nèi)在特性(the internal)和外在特性(the external)。審美特質(zhì)就是作品的內(nèi)在特性,比如,蘭色姆說(shuō)的“肌質(zhì)”、布魯克斯說(shuō)的“悖論”、維姆薩特說(shuō)的“具體的普遍性”。作品的功利性、道德性則是作品的外在特性。崇尚審美,也就是崇尚作品的內(nèi)在特性;而去功利、去道德則是抑制作品的外在特性。傳統(tǒng)和與美國(guó)新批評(píng)同時(shí)代的歐洲學(xué)派反功利、反道德的審美觀則看法有異。傳統(tǒng)和同時(shí)代的歐洲注重從審美和功利的自身特性上定義自身并區(qū)別于對(duì)方;這一“定義”和“區(qū)別”與作品的所謂內(nèi)在性、外在性無(wú)關(guān)。康德論審美、法國(guó)唯美主義者戈蒂葉反功利、前引英國(guó)形式主義者貝爾說(shuō)藝術(shù)和功利-道德的分離都是如此。
要說(shuō)明的是,美國(guó)新批評(píng)以審美取代功利-道德并不是從實(shí)體性因素的層面絕對(duì)排斥功利-道德在文學(xué)作品中的進(jìn)入,而只是說(shuō)要確立審美第一性的地位。審美第一性不絕對(duì)排斥功利、道德等作為第二性因素的參與。無(wú)論傳統(tǒng)、同時(shí)代的歐洲和美國(guó)新批評(píng)在這一點(diǎn)上應(yīng)該說(shuō)都是一致的。不過(guò),比較起來(lái),在不排斥“第二性因素”參與這一點(diǎn)上,美國(guó)新批評(píng)似乎也更為開(kāi)明、寬容與辯證。美國(guó)新批評(píng)學(xué)者沃倫的“不純論”就可從這一點(diǎn)上理解。沃倫1943年作“純?cè)娕c非純?cè)姟?“Pure and Impure Poetry”)一文,強(qiáng)調(diào)詩(shī)歌作品是不純的;任何想要讓詩(shī)作絕對(duì)“純凈”的想法都注定會(huì)失敗。沃倫的“不純”,意思是詩(shī)作中會(huì)含有與詩(shī)意相反的他所謂的“雜質(zhì)”,比如“丑惡的言辭和丑惡的思想”[6]。盡管沃倫沒(méi)有明確指出“雜質(zhì)”與功利、道德有關(guān),但這“丑惡的言辭和丑惡的思想”中很難說(shuō)不包含功利和道德。對(duì)比法國(guó)詩(shī)人兼評(píng)論家瓦雷里的“純?cè)娬摗保謧惖摹安患冋摗泵黠@可作為美國(guó)新批評(píng)更為“開(kāi)明、寬容”的例證。瓦雷里只強(qiáng)調(diào)詩(shī)歌用語(yǔ)言來(lái)“完成一項(xiàng)從本質(zhì)上來(lái)說(shuō)無(wú)實(shí)用價(jià)值的工作”“創(chuàng)造與實(shí)際事物無(wú)關(guān)的一個(gè)世界”[7],完全不談詩(shī)作中應(yīng)該有沃倫所說(shuō)的那種“雜質(zhì)”的進(jìn)入。瓦雷里的觀點(diǎn)是典型的歐洲反功利論的觀念。
另外,還可說(shuō)明,“美國(guó)新批評(píng)的作品本體論以審美對(duì)于功利和道德的否定作為邏輯第一步”是從整體上、基本方向上說(shuō)的。“基本方向上”的述說(shuō)不絕對(duì)排除具體歷史行程中某些復(fù)雜情形的存在。蘭色姆《新批評(píng)》一書(shū)中談到的美國(guó)學(xué)者溫特斯的批評(píng)就可看作美國(guó)新批評(píng)本身復(fù)雜性的呈現(xiàn)。蘭色姆指出,溫特斯也重視作品,其批評(píng)中包含有“非常優(yōu)秀的東西”,即作品的“結(jié)構(gòu)分析”[4]。在重視作品這一點(diǎn)上,常有人把溫特斯也列入新批評(píng)學(xué)者的行列,讓其和瑞恰茲、艾略特的批評(píng)并列。但是,溫特斯不但不排斥道德,反而極力推崇。蘭色姆對(duì)此作了激烈的譴責(zé):“道德說(shuō)教在溫特斯的著述中隨處可見(jiàn)……他的道德說(shuō)教以種種奇怪的形式出現(xiàn)。在批評(píng)家的眼里,道德說(shuō)教是稗草,不是谷禾。”[4]“溫特斯沉溺于這種道德主義……他對(duì)新批評(píng)的影響是有害的。”[4]不能否認(rèn)在一定程度上溫特斯的批評(píng)也屬于“作品本體論批評(píng)”,但也不能因?yàn)闇靥厮古u(píng)的“道德化”就認(rèn)定美國(guó)新批評(píng)“作品本體化的建構(gòu)”不存在以審美取代功利-道德的傾向。“基本方向”是以審美取消功利-道德的,是蘭色姆代表的方向。溫特斯的情形只說(shuō)明:正是因?yàn)樗哂械赖禄卣鳎羞`“基本方向”,所以不能看作典型的作品本體論批評(píng)。
二
相對(duì)于審美-詩(shī)藝與道德-功利的對(duì)立,詩(shī)性言說(shuō)同科學(xué)言說(shuō)的背離對(duì)于美國(guó)新批評(píng)來(lái)說(shuō)更為重要。分析仍可從蘭色姆開(kāi)始:“正如莫里斯先生所說(shuō),科學(xué)是陳述性的,科學(xué)陳述具有預(yù)言價(jià)值。但藝術(shù)使用的是圖像符號(hào),作為對(duì)個(gè)別現(xiàn)象的表現(xiàn),圖像符號(hào)具有偶然性,難以預(yù)測(cè)。藝術(shù)似乎只讓我們預(yù)見(jiàn)到某種程度的不可預(yù)見(jiàn)性。”[4]蘭色姆的這段論述談到的是科學(xué)言說(shuō)的“陳述性”和詩(shī)歌言說(shuō)的“圖像性”之間的區(qū)別。其中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可預(yù)見(jiàn)性”和“不可預(yù)見(jiàn)性”的對(duì)比。它是蘭色姆思想的關(guān)鍵詞。退特的思想同蘭色姆的思想在很多方面接近。退特說(shuō):“‘詩(shī)是語(yǔ)言表達(dá)的最完整的形式。’它不是可證實(shí)科學(xué)的領(lǐng)域,也不是我們自己的投射(表達(dá))。然而它是完整的……它在富有想象力的偉大作品中達(dá)到完整的狀態(tài),并不是實(shí)證主義科學(xué)所追求的那種實(shí)驗(yàn)完整的狀態(tài)。實(shí)證主義科學(xué)的責(zé)任在于證實(shí)那些有限的技術(shù)。科學(xué)的完整是一種抽象,包括專門(mén)化了的方法之間的合作的完美的典型。沒(méi)有一個(gè)人可以體驗(yàn)科學(xué),或體驗(yàn)一門(mén)科學(xué)。因?yàn)椤豆啡R特》的完整不是實(shí)驗(yàn)所決定的狀態(tài),而是被體驗(yàn)的狀態(tài)。”[5]退特的“區(qū)別論”涉及多個(gè)方面:詩(shī)不可證實(shí),詩(shī)不是自我的投射,詩(shī)富有想象力,詩(shī)是具象性的、體驗(yàn)性的,如此等等。不過(guò),在退特看來(lái),最主要的區(qū)別是“完整性的差異”:科學(xué)提供的是抽象的、由專門(mén)化技術(shù)造成的“完整”,詩(shī)則可以構(gòu)建訴諸于人性體驗(yàn)的具象性的“完整”。
蘭色姆的“不可預(yù)見(jiàn)性”同“可預(yù)見(jiàn)性”的對(duì)立、退特的“完整性差異”,著重關(guān)注的都是“效果”,詩(shī)性言說(shuō)不同于科學(xué)言說(shuō)的效果。布魯克斯論詩(shī)性言說(shuō)和科學(xué)言說(shuō)的對(duì)立時(shí)則特別重視兩種言說(shuō)結(jié)構(gòu)方式的不同。在布魯克斯看來(lái),科學(xué)是命題結(jié)構(gòu)、邏輯結(jié)構(gòu)。詩(shī)歌則由悖論、反諷、隱喻、意象等特殊的詩(shī)性方式結(jié)構(gòu)而成。在《精致的甕》附錄之二的開(kāi)頭,布魯克斯談到全書(shū)的研究時(shí)說(shuō):前面諸章的探討形成了本書(shū)的觀念;這些觀念的目的是“使詩(shī)歌脫離同科學(xué)命題、歷史命題、哲學(xué)命題的競(jìng)爭(zhēng)。如前所述,詩(shī)無(wú)法沒(méi)有遺憾地命題化……”[8]。布魯克斯不僅反對(duì)將詩(shī)歸結(jié)為命題,而且強(qiáng)調(diào)詩(shī)中類似于命題方式的陳述也不能像科學(xué)著述中的命題那樣理解,比如濟(jì)慈《希臘古甕頌》中的“真即美,美即真”就不能作為科學(xué)命題解讀。詩(shī)歌拒絕科學(xué)命題,也就是拒絕脫離語(yǔ)境的邏輯分析。“詩(shī)人不能像科學(xué)家那樣去分析自己的經(jīng)驗(yàn);不能像他們那樣把經(jīng)驗(yàn)割裂成不同的部分,區(qū)分相互的不同,并把各部分歸納成不同的類別。詩(shī)人最終的任務(wù)是將經(jīng)驗(yàn)一體化。他必須回到人們從自身經(jīng)驗(yàn)中所感知的那種經(jīng)驗(yàn)的一體性之中。”[8]
詩(shī)性言說(shuō)同科學(xué)言說(shuō)的對(duì)立在詩(shī)學(xué)史上同樣有深厚的淵源。柏拉圖所說(shuō)的詩(shī)與哲學(xué)的差異、亞里士多德眼中的詩(shī)與歷史的區(qū)別,都蘊(yùn)含著后代人所說(shuō)的詩(shī)性和科學(xué)對(duì)立的萌芽。浪漫主義作為反撥理性主義的運(yùn)動(dòng),在前所未有的縱深層面凸顯了詩(shī)性和科學(xué)的對(duì)立。濟(jì)慈著名的“消極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認(rèn)定:詩(shī)人需要的是“能夠處于含糊不定、神秘疑慮之中而能避免汲汲于事實(shí)真相與根由”的能力[9]。這種“能力”明顯同科學(xué)思維的能力對(duì)立,因?yàn)榭茖W(xué)的目標(biāo)就是“事實(shí)真相與根由”,消除“含糊不定、神秘疑慮”。進(jìn)入19世紀(jì)末和20世紀(jì),詩(shī)學(xué)反科學(xué)言說(shuō)的呼聲前所未有地高漲。在馬拉美、瓦雷里等人的象征主義言說(shuō)中,我們可以聽(tīng)到很多激烈的攻擊科學(xué)與理性的抗議。美國(guó)新批評(píng)在這方面的特點(diǎn)是,自覺(jué)不自覺(jué)地把詩(shī)性同科學(xué)的對(duì)立建立在實(shí)證性的、技術(shù)性的層面上,而較少?gòu)男睦韺W(xué)和哲學(xué)形而上學(xué)的層面展開(kāi)。退特說(shuō)他“關(guān)心的是,把一種實(shí)用還原原理強(qiáng)制地、著迷似地運(yùn)用到我們經(jīng)驗(yàn)的一個(gè)已經(jīng)形成的范疇中去,這范疇的特征是它給我們的完整的知識(shí)和整體的經(jīng)驗(yàn)”[5]。這里,我們要注意的是他說(shuō)的“實(shí)用還原原理”。布魯克斯說(shuō)的詩(shī)歌的“非命題性”、退特說(shuō)的“完整性差異”、蘭色姆說(shuō)的“詩(shī)歌的圖像性”就都屬于這種“實(shí)用還原原理”,也就是說(shuō)它們都是偏向于針對(duì)作品實(shí)際情形的技術(shù)性的研讀。它們與歷史上詩(shī)學(xué)的同類性言說(shuō)明顯不同。后者如亞里士多德論詩(shī)與歷史的區(qū)別是哲學(xué)層面的闡釋、濟(jì)慈的“否定能力”凸顯的是心性的特殊,可歸入心理學(xué)范疇。
詩(shī)藝-審美同功利-道德的對(duì)立本質(zhì)上著眼的是作為人類活動(dòng)的一般特性的區(qū)別。詩(shī)性言說(shuō)同科學(xué)言說(shuō)的對(duì)立則是源自兩種言說(shuō)性文本的不同。相對(duì)于“人類活動(dòng)一般特性”,關(guān)于文本和作品的言說(shuō)就建構(gòu)作品本體的行程而言顯然是一種推進(jìn)。而就美國(guó)新批評(píng)內(nèi)部不同理論家的思考來(lái)說(shuō),也可以認(rèn)為,布魯克斯式的“言說(shuō)結(jié)構(gòu)”的探討較之于蘭色姆式的“不可預(yù)見(jiàn)性”的“言說(shuō)效果”的探討體現(xiàn)了更強(qiáng)烈的也更具直接性的對(duì)于作品本體性的關(guān)注。
三
美國(guó)批評(píng)家里奇(Vincent B. Leitch)說(shuō):“在新批評(píng)形式主義者看來(lái),‘生成’(genetic)批評(píng)和‘接受’(receptionist)批評(píng)是應(yīng)該被唾棄的批評(píng)方法。”[10]里奇的論斷是精確的。對(duì)生成批評(píng)和接受批評(píng)的拒絕構(gòu)成了美國(guó)新批評(píng)作品本體論生成的又一學(xué)理上的追求。作為前接受美學(xué)時(shí)代的批評(píng)流派,成為美國(guó)新批評(píng)主要論敵的是生成批評(píng),不是新批評(píng)整體上衰落之后才勃然興起的“接受批評(píng)”。因此,從其作品本體論建構(gòu)的角度看,要重點(diǎn)關(guān)注的也就是對(duì)生成批評(píng)的拒絕。生成批評(píng)的發(fā)生和與之相反的對(duì)生成批評(píng)的拒絕,學(xué)理上關(guān)涉三個(gè)方面:其一,作者生平和作品的關(guān)系;其二,作者意圖和作品的關(guān)系;其三,時(shí)代、歷史和作品的關(guān)系。在新批評(píng)產(chǎn)生之前,美國(guó)批評(píng)界特別重視“其一”和“其二”兩個(gè)方面。新批評(píng)的反叛也相應(yīng)地主要從顛覆“其一”“其二”入手。布魯克斯說(shuō):“形式主義批評(píng)家主要關(guān)注的是作品本身。作者心理的聚焦會(huì)導(dǎo)致批評(píng)家離開(kāi)作品,轉(zhuǎn)向傳記和心理學(xué)的研究。”[2]針對(duì)美國(guó)斯多爾教授(Stoll)“一首詩(shī)的詞句是出自頭腦而不是出自帽子”之類的刻薄調(diào)侃,維姆薩特和比爾茲利在《意圖謬誤》中寫(xiě)道:詩(shī)歌作品“不是作者自己的(它一生出來(lái),就立即脫離作者而來(lái)到世界上。作者的用意已不復(fù)作用于它,它也不再受作者支配),這詩(shī)已是屬于公眾的了。詩(shī)呈現(xiàn)于語(yǔ)言,而語(yǔ)言是公眾特有的東西;詩(shī)的內(nèi)容則是對(duì)人類的言說(shuō),人類是公眾知識(shí)研究的對(duì)象。”[11]
概括美國(guó)新批評(píng)反叛生成批評(píng)的理由,可以看到主要是兩個(gè)方面。第一,作品是客觀性的超個(gè)人性的存在。作品屬于公眾,不屬于作者個(gè)人。它講述的是超越個(gè)人生活和作者思想的,關(guān)乎人類、歷史、時(shí)代的生活內(nèi)容。它使用的語(yǔ)言也是超個(gè)體性的。上引《意圖謬誤》的論斷說(shuō)的就是這一方面。第二,就作品的構(gòu)成因素而言,它與導(dǎo)致它生成的原材料迥然相異。不僅作品實(shí)際描寫(xiě)的情事、實(shí)際表現(xiàn)的意義不可能同作者的生平經(jīng)歷、思想意圖相同,作品的形式性因素更不可能在作品之前或作品之外的某個(gè)地方找到。韋勒克和沃倫合著的《文學(xué)理論》關(guān)于“文學(xué)和傳記”“文學(xué)和心理學(xué)”兩章的討論重點(diǎn)辨析的就是這一方面。二人的“辨析”理由充分,富有說(shuō)服力。在美國(guó)新批評(píng)看來(lái),“生成批評(píng)”的主要謬誤在于忽視創(chuàng)作的自主性、能動(dòng)性、創(chuàng)造性,不知道作品是作家當(dāng)下創(chuàng)造的產(chǎn)物,不理解作品不具有先在性。被學(xué)界視為美國(guó)新批評(píng)先驅(qū)的艾略特說(shuō):“一首詩(shī)一旦作成,世上就又發(fā)生了一件新事物,任何在其之前產(chǎn)生的事物都不能夠用來(lái)完全充分地解釋這一事物。”[12]“生成批評(píng)”不懂或無(wú)視艾略特所說(shuō)的這種情況。
維姆薩特和比爾茲利是強(qiáng)勁地維護(hù)作品本體地位、反對(duì)生成批評(píng)的學(xué)者。二人合著的名文《意圖謬誤》就是為反擊生成批評(píng)而作。在剖析生成批評(píng)的謬誤時(shí),二人指出:“意圖謬誤混淆詩(shī)和詩(shī)的生成,這種混淆哲學(xué)家們稱之為生成謬誤(the Genetic Fallacy)。”[11]新批評(píng)唾棄生成批評(píng)的哲學(xué)依據(jù)就是哲學(xué)家們對(duì)“生成謬誤”的剖析。哲學(xué)家說(shuō):“生成謬誤”是“用其起源或得以產(chǎn)生的最初環(huán)境來(lái)判斷、評(píng)價(jià)或解釋某物”;它無(wú)視“事物的起源與其目前的狀態(tài)之間很可能存在著某些根本的差別”;比如,“人類起源于猿,并不意味著他們現(xiàn)在還是猿”[13]。如果說(shuō),在一般哲學(xué)層面上,“生成論”的闡釋范式都是錯(cuò)的,是謬誤,那么,文學(xué)就更不可能也更不應(yīng)該用“生成”來(lái)闡釋。在文學(xué)的世界里,一方面,人類的創(chuàng)造性得到了空前的表現(xiàn);另一方面,文學(xué)獨(dú)有的要素,比如其形式性因素,會(huì)爆裂性一般地出現(xiàn),從而使作品成為前所未有的存在體。作品的爆炸源自對(duì)作品魔術(shù)性因素的引爆。認(rèn)為作品的形式,比如作品的語(yǔ)言,具有魔術(shù)效應(yīng)和爆炸性,是現(xiàn)代歐洲詩(shī)家常有的看法。法國(guó)光明會(huì)的理論認(rèn)為,“詞不是人類的偶然產(chǎn)物,而是來(lái)自宇宙的原初統(tǒng)一體(Ur-Eins);詞的敘說(shuō)造成了敘說(shuō)者與這樣一種來(lái)源的魔術(shù)化溝通”[14]。馬拉美認(rèn)為,“藝術(shù)地處理一種語(yǔ)言”,等于“召喚魔術(shù)”[14]。胡戈論蘭波的時(shí)候說(shuō),定義蘭波作品的一個(gè)關(guān)鍵詞是“爆發(fā)”(Explosion)[14];蘭波對(duì)詩(shī)人的定義則是“憑借具有暴力性質(zhì)的幻想爆破世界的工作者”[14]。在確認(rèn)作品形式性因素的魔術(shù)性、爆炸性方面,美國(guó)新批評(píng)并不是最極端的一派。美國(guó)新批評(píng)更多地關(guān)注意義,偏重從意義自身的形式來(lái)解讀詩(shī)歌,并不特別重視那種敵視意義的、顛覆意義的形式。但僅就“意義的形式化”而言,美國(guó)新批評(píng)也有理由認(rèn)定“作品”絕不同于導(dǎo)致作品產(chǎn)生的“諸因素”。由此,在他們看來(lái),“生成批評(píng)”理應(yīng)被唾棄。
“生成謬誤”的觀念暗含了對(duì)“連續(xù)性”(coherence )的否定,因?yàn)槿绻髌凡荒軓摹吧伞钡慕嵌壤斫猓鸵馕吨髌放c之前和之后的因素沒(méi)有關(guān)聯(lián)。非連續(xù)性(incoherence)不是新批評(píng)的觀念,也不是新批評(píng)所屬時(shí)代的主導(dǎo)性觀念,而是本質(zhì)上同新批評(píng)相對(duì)立的后現(xiàn)代主義的觀念。新批評(píng)對(duì)“非連續(xù)性”的暗示源自對(duì)作品實(shí)際情形同所謂“前在因素”的區(qū)別的考察。這種“考察”本質(zhì)上是共時(shí)性的思考,因?yàn)樗菑膶?duì)兩種情形的靜態(tài)比較而來(lái);它與后現(xiàn)代主要從歷史事變和歷史主體心理自身的歷史性變化否定“連續(xù)性”有區(qū)別。后現(xiàn)代的“否定”不是“共時(shí)性”的,而是“歷時(shí)性”的。也正是因?yàn)橛写藚^(qū)別,所以新批評(píng)拒絕“生成謬誤”時(shí)對(duì)“非連續(xù)性”的暗示不會(huì)帶來(lái)后現(xiàn)代式的對(duì)新批評(píng)自身詩(shī)學(xué)觀念的懷疑和顛覆。但另一方面,兩種“非連續(xù)性”畢竟相通,所以,新批評(píng)的“非連續(xù)性暗示”在某種意義上也構(gòu)成了對(duì)完全異質(zhì)性的后現(xiàn)代詩(shī)學(xué)的召喚,這也就等于說(shuō)新批評(píng)揚(yáng)起的石頭在不經(jīng)意之間也砸向了自身。
四
基于上述三個(gè)層面的揚(yáng)棄,新批評(píng)走向了作品。但要讓作品真正成為本體,則僅有三個(gè)層面的揚(yáng)棄還不夠。本體化的最終成就來(lái)自作品自身的真正的自主、自立,來(lái)自作品自身生命的形成。英國(guó)新批評(píng)的奠基人瑞恰茲說(shuō):“詩(shī)歌是有生命、有感覺(jué)、有知覺(jué)的自行存在的事物;有關(guān)詩(shī)歌是一個(gè)有機(jī)體的所謂隱喻并不是什么隱喻,而是陳述事實(shí)。”[12]美國(guó)新批評(píng)學(xué)者承襲了瑞恰茲的“詩(shī)歌自立”的觀念。詩(shī)歌自身生命的形成在蘭色姆的“肌質(zhì)”、退特的“張力”、維姆薩特的“存在”以及諸人公認(rèn)的“神跡性比喻觀念”中都有所顯示。前曾說(shuō)到蘭色姆“肌質(zhì)”的一個(gè)特征是它的不可預(yù)測(cè)性。要補(bǔ)充的是,蘭色姆談“肌質(zhì)”時(shí)還非常強(qiáng)調(diào)它的“不可駕馭性”。蘭色姆說(shuō):“詩(shī)歌的肌質(zhì)”即“自由的細(xì)節(jié)”[4],詩(shī)歌“不斷提供令人激動(dòng)的細(xì)節(jié)”,“其物質(zhì)構(gòu)件……具體而微,難以駕馭”[4]。與“科學(xué)世界”的“易于駕馭”相比,詩(shī)歌恢復(fù)由肌質(zhì)造成的“更難駕馭的本原世界”[4]。“不可預(yù)測(cè)”“不可駕馭”強(qiáng)烈地暗示出詩(shī)歌有一種屬于自身的特有的力量,詩(shī)歌有“自身的生命”。維姆薩特和比爾茲利說(shuō)詩(shī)歌“是一種即時(shí)存在(is)”[11]。雖然兩人在《意圖謬誤》中闡釋詩(shī)歌的“即時(shí)存在”時(shí)用了“布丁”“機(jī)器”之類的事物,似乎認(rèn)為詩(shī)歌是無(wú)生命的物體;但深入領(lǐng)會(huì)兩人的思想,只能認(rèn)為布丁之類的無(wú)生命性只是用來(lái)說(shuō)明詩(shī)歌對(duì)詩(shī)人意圖的排斥,并不能用來(lái)說(shuō)明詩(shī)歌是無(wú)生命的物體。在《具體普遍性》中談到詩(shī)歌的“存在”時(shí),維姆薩特說(shuō):“好的故事詩(shī)就像扔往池塘里的石子,它扔到我們的心里,激起的同心圓不斷地向四面蕩漾開(kāi)來(lái)——而這一切是由詩(shī)自身的結(jié)構(gòu)造成的。”[15]“同心圓”向“四面蕩漾”說(shuō)明“同心圓”是運(yùn)動(dòng)型的;“同心圓”有擴(kuò)展自身的力量。這力量就水上波紋而言,來(lái)自于石頭的擊打,屬于外力作用。但詩(shī)的同心圓擴(kuò)展的力量,不來(lái)自外部,就源自詩(shī)自身,源自“詩(shī)的結(jié)構(gòu)”。詩(shī)自身有一種導(dǎo)致自身運(yùn)作的力量,這同蘭色姆說(shuō)詩(shī)“不可駕馭”一樣,等于表明詩(shī)具有自身的生命。
“生命”的根本機(jī)制是依據(jù)自身的力量自我生長(zhǎng)。“生長(zhǎng)”表現(xiàn)為“過(guò)程”,過(guò)程的延續(xù)源于自身的內(nèi)在力量。詩(shī)歌自身生命的獲得在于詩(shī)歌能依據(jù)自身的力量自我生長(zhǎng):其內(nèi)含的意義不斷發(fā)展、深化、升華。而從詩(shī)歌研究的角度言,詩(shī)歌本體論建構(gòu)的最佳方式則是經(jīng)由闡釋性言說(shuō),生動(dòng)而真切地展現(xiàn)詩(shī)歌生命的律動(dòng)。布魯克斯的《精致的甕》就常常具有這樣的效果。布魯克斯說(shuō)詩(shī),總是關(guān)注詩(shī)歌的動(dòng)態(tài)過(guò)程,著眼于詩(shī)歌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凸顯詩(shī)歌內(nèi)在結(jié)構(gòu)的前驅(qū)性沖擊,因而能讓讀者像瑞恰茲說(shuō)的那樣,確實(shí)真切地感受到“詩(shī)歌是有生命、有感覺(jué)、有知覺(jué)的自行存在的事物”。
不過(guò),要說(shuō)明的是,所謂詩(shī)歌生命的律動(dòng),仍然是就創(chuàng)作和感受詩(shī)歌的主體即人來(lái)說(shuō)的。詩(shī)歌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悖論、反諷、意象、隱喻等等,也都是人的意識(shí)活動(dòng)的內(nèi)容。拋開(kāi)人而言的詩(shī)歌作品,只是物質(zhì)性的存在,或者是物理性質(zhì)的聲音(口頭作品),或者是無(wú)生命的物體(書(shū)寫(xiě)作品的紙張、電子設(shè)備)。在這樣的層面上,詩(shī)歌的“生命”也仍舊是人的生命;就其作為物質(zhì)性存在者的紙張、聲音等而言,詩(shī)歌無(wú)“生命”可言。就物質(zhì)實(shí)體擁有“生命”這一點(diǎn)來(lái)說(shuō),“生命”一詞只是隱喻,不是“實(shí)寫(xiě)”。由此,應(yīng)否決瑞恰茲“有機(jī)體對(duì)于詩(shī)歌不是隱喻而是事實(shí)”的斷言。但另一方面,“詩(shī)歌生命”之說(shuō)依舊有辯護(hù)的理由。相對(duì)于人的意識(shí)的學(xué)科性構(gòu)成、功利性指向、日常性組建,同樣屬于人的意識(shí)范圍的詩(shī)歌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是由詩(shī)歌作品所含全部要素凝聚而成的晶體。人的學(xué)科意識(shí)、功利意識(shí)、日常意識(shí)體現(xiàn)的是人作為知識(shí)主體和行動(dòng)主體對(duì)于某些事物的認(rèn)識(shí)、意愿。這些認(rèn)識(shí)、意愿直接秉承人的生存意志,直接受制于人的生活經(jīng)歷、歷史境遇。而以詩(shī)歌內(nèi)在結(jié)構(gòu)形態(tài)出現(xiàn)的人的意識(shí)卻超越人的意識(shí)的學(xué)科性、功利性、日常性,超越人的具體生活經(jīng)歷、歷史境遇,超越人的當(dāng)下性生存意志。它是一種完全作品化的、體現(xiàn)作品“意志”的意識(shí)。此種意識(shí)構(gòu)成的“生命”就其“不斷發(fā)展、深化、升華”的機(jī)制來(lái)說(shuō),它與人的實(shí)際生命的成長(zhǎng)等值同構(gòu)。一方面,完全作品化層面上形成的詩(shī)歌作品的“生命”完全不同于人的功利性日常性生存構(gòu)成的生命。另一方面,它又確實(shí)體現(xiàn)了人的生命的本質(zhì)特征;就此兩方面的結(jié)合而言,人們有理由用“有機(jī)生命”來(lái)描述詩(shī)歌的內(nèi)在奧妙。瑞恰茲說(shuō)的“不是隱喻”可以成立。
“四重?fù)P棄”關(guān)注的是新批評(píng)自身的學(xué)理邏輯。任何一種理論建構(gòu)除了自身學(xué)理邏輯的演繹之外,還有一個(gè)極為重要的方面,即社會(huì)歷史文化的制約和推動(dòng)。美國(guó)新批評(píng)的作品本體論建構(gòu)也是如此。何以崇尚審美而拒絕功利-道德?何以對(duì)詩(shī)性言說(shuō)同科學(xué)言說(shuō)的區(qū)別那么敏感?何以注重存在本身而鄙薄生成?何以青睞有機(jī)性而厭惡機(jī)械性?這些都不是能夠從“崇尚”和“拒絕”本身就可以說(shuō)明的。它們需要從廣闊深厚的歷史語(yǔ)境上理解,不過(guò)這已經(jīng)是逸出本文范圍的使命了。
注釋:
① 布魯克斯《形式主義批評(píng)家》(1951)一文列舉了他所贊賞的十條批評(píng)原則。這十條,可看作是他對(duì)于新批評(píng)的界定。
② 原因當(dāng)然是海德格爾對(duì)“藝術(shù)”和“詩(shī)”的理解同新批評(píng)的理解完全不同。
③ 揚(yáng)棄,sublation,是黑格爾哲學(xué)的著名術(shù)語(yǔ)。黑格爾的“揚(yáng)棄”是針對(duì)某一個(gè)特定對(duì)象的否定之否定,即一種有肯定結(jié)果的否定。本文的“揚(yáng)棄”也包含有“否定”與“肯定”兩個(gè)方面的含義,但不只針對(duì)某一個(gè)特定對(duì)象,與黑格爾的原意略有不同。
④ 要注意的是,蘭色姆以新批評(píng)代表的身份批評(píng)溫特斯的道德化傾向與前述“新批評(píng)的審美第一性允許道德等作為第二性因素在作品中的參與”不矛盾。溫特斯的問(wèn)題不是“道德作為第二性因素參與”的問(wèn)題,而是試圖把道德作為第一性的、壓倒審美的問(wèn)題。由于用道德壓倒審美,所以溫特斯的觀念不能視作代表新批評(píng)整體傾向的觀念;由于他也重視作品,所以,他又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是參與新批評(píng)運(yùn)動(dòng)的學(xué)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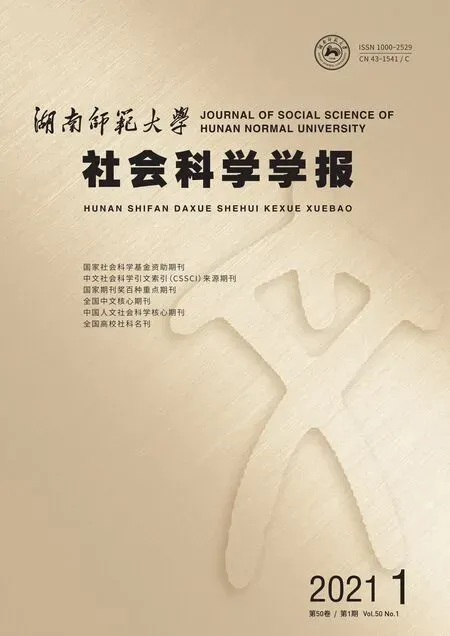 湖南師范大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學(xué)報(bào)2021年1期
湖南師范大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學(xué)報(bào)2021年1期
- 湖南師范大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學(xué)報(bào)的其它文章
- 大數(shù)據(jù)驅(qū)動(dòng)下廣告學(xué)研究范式的轉(zhuǎn)換
- 系統(tǒng)性金融風(fēng)險(xiǎn)與監(jiān)測(cè)預(yù)警:一個(gè)綜合分析的視角
- 實(shí)踐與立法之背離:民事訴訟逾期舉證規(guī)制機(jī)制的實(shí)證考察
——以《民訴法》第65條和《民訴解釋》第102條為主要考察對(duì)象 - 國(guó)際貨幣金字塔:中國(guó)的位置及行動(dòng)策略
- 高校出版社發(fā)展水平測(cè)度及高質(zhì)量發(fā)展路徑探究
- 排遣與消遣:近代知識(shí)群體閱讀《紅樓夢(mèng)》的日常心態(tài)
